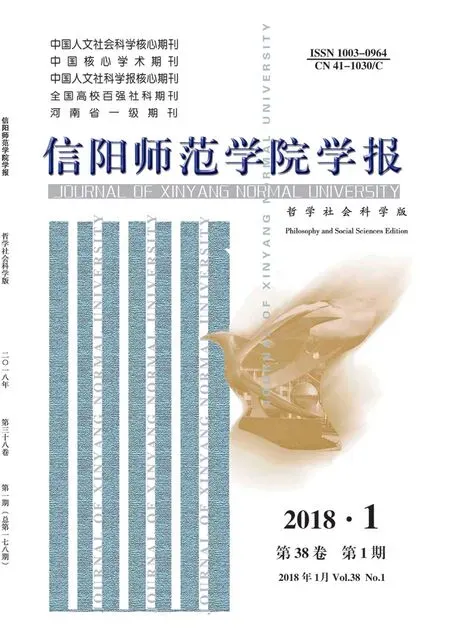加冕与脱冕
——《五号屠场》的狂欢化艺术特征
汪凡凡
(信阳师范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加冕与脱冕
——《五号屠场》的狂欢化艺术特征
汪凡凡
(信阳师范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冯内古特的代表作《五号屠场》是一个高度狂欢化的文本,小说在艺术思维、人物形象、结构与语言以及时空体等几方面均体现了鲜明的狂欢化的艺术特征。《五号屠场》充满了对话性,以民间话语颠覆官方权威,并采用了脱冕型结构,体现了狂欢节的自由平等精神和交替变更精神。
《五号屠场》;狂欢化;艺术特征
狂欢节是中世纪盛行的民间节日,它暂时颠覆等级,打破规约,将边缘与中心倒置;狂欢式属于浸透了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事物模式,是狂欢节庆典活动中礼仪、形式等的总和;狂欢化则指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就是所谓的狂欢化”[1]175。狂欢节的笑声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嘲讽,体现了平民话语的喧哗,实现了不同话语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在文学作品中狂欢展现为一种场面,充满了荒诞的人与事,以及对宏大事件的加冕和脱冕。美国著名后现代派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以德累斯顿大屠杀为历史背景,通过描述主人公比利的人生经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并对人类命运做出深刻的反思。《五号屠场》是一个高度狂欢化的文本。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指导,从狂欢的加冕与脱冕、狂欢的人物形象、狂欢的语言与体裁等方面评价这部小说,揭示小说狂欢化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
一、狂欢化的艺术思维
狂欢化的思维模式具有鲜明的双重性,官方与民间、生与死、尊贵与卑贱等相互交织、互相依存,人们可以具体地感受到事物的更替和颠覆的精神。所以,狂欢化思维是一种相对性与双重性的思维。同时,相对于独白性思维,狂欢化思维也是一种对话性、开放性的思维。独白性思维是封闭、排他的,认为无须交流与对话就能把握真理,不允许异己声音的存在。而狂欢式的思维相当于狂欢节上人们之间的亲切交流与对话,形成一种众生喧哗的局面。狂欢广场是自由、开放的世界,在此人们用粗鄙、幽默的话语嘲讽正统、严肃的事物,表现了语言的开放性,从而形成了对话。
《五号屠场》不是纯粹的战争回忆录,它展现的是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残忍的历史真相被戴上了“道义”的桂冠。正如狂欢节以笑话来“反对官方世界而建立自己的世界,反对官方教会而建立自己的教会,反对官方国家而建立自己的国家”[2]335,小说以对话性的狂欢思维模式建构了对德累斯顿大轰炸的解读,通过民间话语的喧声来挑战官方权威,对官方的历史观进行了“脱冕”,揭示了一段隐秘的历史,让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发了人们对这一事件重新反思,彰显了民间话语喧嚣的权利。在官方的鼓动与诱导下,人们普遍认为德累斯顿大轰炸是反法西斯暴行及实现人类解放的正义之举,而冯内古特认为德累斯顿根本没有战略价值,这样的轰炸完全是赤裸裸的屠杀,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却被认为是应该付出的代价。冯内古特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当我们加入战争时,我们觉得政府是尊重人的生命的,尽可能不伤及平民百姓。德累斯顿只是一个由平民居住的城市,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然而盟军轰炸并毁灭了它。然后政府却对此撒谎。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1]190此外,冯内古特对战争场面进行了非传统描写,并颠覆性地塑造了反英雄人物形象,德累斯顿轰炸经过作者笑谑地“脱冕”而变得毫无意义。在冯内古特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没有炮火硝烟,也少有血腥恐怖,相反战争场面是滑稽可笑的。“德累斯顿除了矿石一无所有,石头热得烫手,街区没有一个活人”[3]29,这一没有任何立场的叙述实为对战争的嘲讽。小说以比利在大轰炸时的藏身之所——屠宰场地下仓库命名,喻指战场是一个大的屠宰场。在人物描写方面,小说中没有任何可以称为“英雄”的人物,交战双方都是一些对战争没有丝毫影响的小人物,诸如无知的孩童和羸弱的老人等,他们被官方的宣传所愚弄或为了生计而去给战争当了炮灰。冯内古特谈到对德累斯顿大袭击的感受时说:“英美的屠杀与德国纳粹的暴行没有什么两样。说是为了正义而战,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些受害者,就不会这么想了,这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没什么两样。”[2]69二战后,科技突飞猛进,但两次世界大战扫荡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信仰,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怀疑。
二、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在狂欢广场上,人们插科打诨、嬉笑怒骂,滑稽可笑的骗子、小丑、傻瓜等成了狂化节的主角。他们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空体,他们是中世纪荒诞文化的典型人物,是人们宣泄感情的载体。“他们独具特点和权力——作为这个世界的外人,不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任何人生处境也都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看出了每一种处境的反面和虚伪”[2]133。这样的狂欢化人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其本身不是外在所表现的人,他们的存在是另外某种存在的反映。这些形象给了作者一个“面具”及观察世界的立场,使其可以置身于生活之外窥探生活,揭露陈规惯例,嘲弄不合理的存在,揭示出世界的虚伪和荒谬。对狂欢节主角的加冕与脱冕是整个狂欢仪式的核心。在《五号屠场》中,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小丑式的“反英雄”人物形象,两者不同的命运揭示了战争的荒谬,消解了战争的崇高意义。
主人公比利正是狂欢节的主角,他作为一位先知的加冕和脱冕者极具喜剧效果。从外貌来看,比利是一个活脱脱的丑角形象。他是一名随军牧师助理,是个对友无益、对敌无害的滑稽人物。他不会保护自己,对死亡漠不关心,要靠别人拖着打着才能往前走;在战俘营里,比利也是逆来顺受,毫无反抗精神,但就是这样一个“窝囊废”却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存活下来。比利没有为正义而战的信念,也没有建立功业的追求,却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而满怀一腔报国热情而投身战斗的人非但没有消灭敌人,反而死在了战俘车上。比利具有滑稽、亲昵、粗鄙、愚蠢的“傻瓜”特质,他的存在具有反讽意味;周围人与比利截然不同的遭遇与命运又反映了战争的荒谬。比利的“傻瓜”形象是被脱冕的耶稣,“小丑和傻瓜是处于冥界中的上帝的变形”[2]311。小说首先对比利进行“加冕”,其中比利与基督耶稣相暗合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小说开始引用圣诗“牛群哞哞叫,圣婴惊醒了”[3]5,描述了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情景,暗示救世主——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的诞生。比利接受了特拉法玛多星球的时间观及死亡观,相信过去、现在、将来将永远存在;人的死亡只是在特定时间点的死亡,回溯过去却是活着的,所以人不必反抗,只需安然地接受现状。“看到一具尸体,他想到的只是死者在那个特定时间状况不好,但同一个他在其他时间则安然无恙”[3]77,这种看待时间的方式和上帝全知的视角极为相似;并且比利义不容辞地将这些外星思想宣传给自己的同胞,以期减轻人类的痛苦。并且比利的职业是配镜师,配镜师的存在是为了给人们配上矫正眼镜以正视生活的真相,并拯救人类、减轻人类的痛苦。然而,小说对比利进行加冕的同时又脱冕,瞬间提升并降格,造成一种狂欢的效果。比利这个“耶稣”所传播的福音不可能给人类带来救赎。小说中出现死亡之处,总伴有一句“事情就是这样”[3]52,从而将死亡消解到无所谓的地步,但不面对灾难与死亡并不意味着能够避免其发生。“自那二十五年以后,比利在伊利昂登上了一架租用的飞机。他明知飞机要失事,但不想说出来遭人取笑”[3]135。比利对生活漠不关心,无所作为,从不反抗、不质疑不合理的存在,他不可能拯救世人。当比利向前来配镜的男孩讲述自己的外星经历时,他遭到了非议和指责。如果说耶稣有众多的信徒,那么比利则是孤家寡人,连他的家人都对其布道难以置信并引以为耻。比利的皇冠岌岌可危,狂欢的人群争相为他脱冕,使其原形毕露。比利只是饱受荒诞生活折磨的小人物,自身难保,更不能拯救人类。他自命不凡的福音不过是一种精神鸦片,使人浸淫于美好的幻想中,暂时忘却人生的苦难。小说把丑角形象比利“加冕”为“狂欢之王”后使他发表演讲,布道宣传,让他讲述荒诞的故事,然后脱去其神圣的冠冕,将其拉下神坛,进行嘲讽和鞭笞,揭示出残酷的现实。
三、狂欢化的结构与语言
狂欢化的艺术思维赋予了文学体裁多样性和文本对话性的特征。巴赫金指出:“狂欢化帮助人们打破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思想之间、多种风格之间存在的壁垒。”[4]177狂欢化在文本中提供了一种建立大型对话的可能性,从独白走向对话,从专断走向开放。《五号屠场》所体现的结构上的大型对话框架和语言的微型对话框架与巴赫金狂欢诗学的对话性、开放性十分契合。
《五号屠场》借用新闻、抒情诗、绘画、科幻小说等文体,形成了不同的话语指向及众声喧哗的局面,笑谑并消解严肃体裁。由不同体裁的镶嵌拼贴而组成的杂语都是观察世界、体现事物价值的特殊视野。在小说中,作者不做明显的训诫与评判,由读者理解不同体裁的指向性及含义,给读者带来陌生化体验,既包含着作家自己的理解,也期待着读者的交流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体系。小说充满了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评价之争,体现了各个阶层的不同视野,而作者通过其意向来折射自己的意向,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比利消极的宗教信条与冯内古特的人道主义情怀形成对比,从而使文本与文本及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展开了对话,形成杂语、多元的世界。此外,冯内古特将一些历史文献、圣经教义、新闻报道等内容与英美两国对德累斯顿轰炸有关的历史记录拼贴在小说里,体现了语言的狂欢化。
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占有独特的时空位置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巴赫金在阐释“复调”时指出:“主人公对自己和世界的议论,同一般作者的议论,具有同样的分量和价值。两者以特别的方式相结合。”“复调”打破了由作者专断独裁的“独白主义”倾向及作者与人物之间的不平等格局。对作者意志进行节制的目的在于使其在特定方向上扩大、深化和重建自己的意识,并能涵纳诸多他人的意识。作者刻意保持一种在时空、价值和意义上均外在于人物的位置,使作者与人物的意识交融,处在一个对话的开放体系内,从而消解了作者的绝对权利,使得人物通过对话与作者平起平坐,人物作为独立主体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思想。“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占有独特的时空位置和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这些在赋予我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我的无能:我不能对世界进行全面的网罗获取,如时空景观,甚至我的形貌都不能直接进入我的视野”[4]181。但比利具有不同于作者视角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时空旅行”上。通过比利的时空旅行,作者就能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幻想之间来回穿梭,既能以外星视角观察战争,从而消解战争的意义,又能把比利的经历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上,从而扩大了战争的创伤。因此,比利的视域是对作者视域的补充。
四、狂欢化的时空体
时空体是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结构特征的概括,也是巴赫金发掘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狂欢化的时间将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等诸点上,此时即使是一个瞬间,其意义也超越了几年甚至数十年。狂欢化的空间则把情节集中在人物命运发生突然的转折性变化的场所。小说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交织在一起形成狂欢化的时空体。
《五号屠场》蕴含着狂欢的时空。主人公比利逃脱了线性时间的束缚,“从时间链上脱开了”[3]21,经常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穿梭,几乎每次停留都会面对危机四伏的窘境:德累斯顿轰炸、战俘遭遇、无爱的婚姻经历、外星人绑架之难等等,连他自己都不知下一次将会出现在何时何地。如“圣诞节前夜,比利就像汤匙一样蜷缩在流浪汉旁边。他进入梦乡,通过时间旅行回到1967年——那个遭到来自特拉法玛多星球的飞碟绑架的夜晚”[3]68。通过狂欢化的时间,小说将过去和未来结合起来,使读者处于“时间门槛”的边缘,同时向内和向外,从而超越固定视角来理解小说。再如,“记忆中的未来告诉比利,大约再过三十天——这个城市将被炸成碎片。他也知道,对面的大多数人也将死于非命。事情就是这样”[3]109。鲜活的生命即将在比利眼前丧生,而人们却无能为力。冯内古特“在二十世纪生命的惨状和我们能够理解其全部现实内容之间的差距之间建起了一座桥”,将小说的叙事置于一个更高和更宽广的视角上。在同一时间点上,比利经历了巴赫金所说的“门槛时间”,跨越了两个不同的空间。小说有大量的这种切换,如“他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仍在哭泣,但回到了卢森堡,与许多战俘走在一起”[3]33。场景突然变换,犹如电影的蒙太奇,比利在战后优裕的生活环境与战俘营的苦难生活空间之间跳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果在战后的和平年代,比利仍忧心忡忡,担心自己重回二战战场,体现了战争对人们的心理创伤;如果回到二战时期,比利明知即将发生的事情,却只能任其发展,更体现了人们对战争及荒谬现实的无能为力。这些跳跃的场景都由作者精心选择,且在每个点上都有特定的故事发生,并出现了危机、剧变与命运转折。以巴赫金的狂欢时空体理论为指导,小说采用“时空旅行”模式把历时与共时结合起来,从而使作者能够在历史、现实与想象之间自由穿梭,并带给了读者特殊的阅读体验。
“从总体上看,狂欢并非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是一种‘变态’,其存在与兴盛有着自己的文化语境和内在逻辑”[6]33。《五号屠场》没有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细节描写,而是通过多种手法构建了一个多重话语体系,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参照域。小说杂而不乱,多种体裁拼贴交错,空间与时间混杂铺陈,成为各色人物上演悲欢离合的大舞台。小说形成一个大型的狂欢广场,体现了鲜明的狂欢化特征。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M].虞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4]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 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6] 鄢 鸣.狂欢:真实抑或想象——狂欢理论的应用与反思[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3):107-111.
CrowningandDecrowning——CarnivalArtisticCharacteristicsinSlaughterhouse-Five
WANG Fanfa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 of Slaughterhouse-Five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postmodern writer Vonnegut is a text with high carnivalization. In terms of artistic thinking, character im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as well as time and space, it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Carnival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laughterhouse-Five is totally conversational, subverting the official authority with folk discourse and applying the decrowning structure,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spirit of alternation.
Slaughterhouse-Five; carnivalizati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韩大强)
10.3969/j.issn.1003-0964.2018.01.027
2017-10-08
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2014BWX011)
汪凡凡(1979-),女,河南信阳人,在读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与研究。
I712.074
A
1003-0964(2018)01-01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