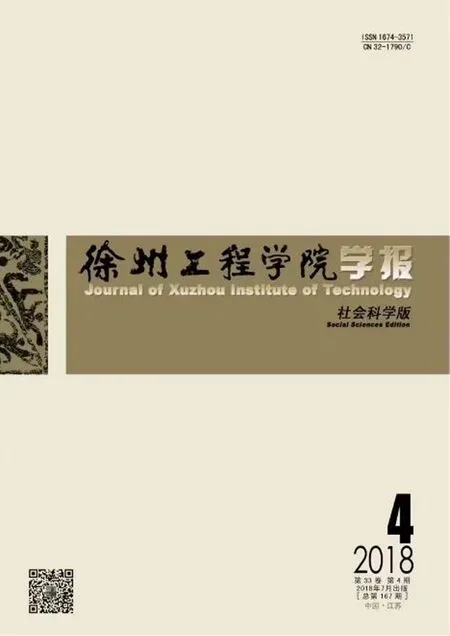符号、文本、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作为当前传播与媒介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自20世纪30年代起,至今已经历了四次范式转移。但是在媒介素养研究的过程中却缺乏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法,这是当前媒介素养研究的一大困境。符号学理论则有可能为此提供方法论的理论资源。约翰·菲斯克指出:“符号学主要是一种旨在建立广泛的应用原则的传播理论方法。它关注的是传播如何伴随语言体系与文化体系,特别是符号体系、文化及现实的结构关系而进行。”[1]符号学以文本分析为核心,主张文本表意的主体在于文本接收者的阐释。这与媒介素养研究中的两个主体——媒介文本与受众,正好是相互对应的。沿着符号学的路径探讨媒介素养研究的核心议题,有可能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
一、媒介素养:术语激辩与范式转移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F.R.利维斯(F.R.Leavis)和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仍然处于各种争议和辩论之中,就连“媒介素养”的称谓,由于各个学者的研究视角和出发点不同,也存在区别,除媒介素养外,“在媒介素养教育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如英国,较多地使用的是‘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而在澳大利亚使用频繁的则是‘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在其它国家还使用‘媒介理解’(Media Awareness)这个概念”[2]。
迄今为止,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全国媒介素养领导会议”对媒介素养的定义:“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获取、分析、评估、传播信息的能力。”[3]不过这个概念的致命伤在于:将媒介素养圈定在人使用媒介的能力,并且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自媒体时代,通过一定的培训或学习,人人都能掌握一套获取信息的技术手段。然而若认知媒介文本背后隐匿的社会文化内涵,却非仅仅是技术手段的问题。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学者詹姆斯·波特的观点,波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当我们面对媒体时,能够对媒体上的信息做出意义上的解释,并且形成一系列的观点”[4]。波特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一种知识习得的能力,其关键因素在于个人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包括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认知以及批判性质疑等能力。波特的这个定义为我们理解媒介素养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将关注重点从信息文本转移到了受众这里。
另外从词源的构成上来说,“媒介”是一个包含内容相当广泛的概念,如果按照“media”的本意来理解的话,它指的是传媒机构。但是现在人们泛化了它的意思,一般指的是新闻或讯息的文本形态。我们姑且沿着这个思路,将“媒介”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新闻、广告等。那么,所谓的这些媒介文本远远不是简单的信息。与这些媒介文本相关的,还包括各种伴随文本、先后文本、副文本等,它们是理解某个特定媒介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换句话说,一个人仅仅能够读懂媒介文本的明示意是不够的。盖伊·塔奇曼将新闻看作是一种知识的活动,新闻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框架。或者如约翰·彼得斯所言: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
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素养”这个概念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其意指“阅读的能力以及博学的状态”[5]。这个定义虽然比较模糊,但是它包含了将个体的知识作为素养的一个标准。国际上权威的《牛津辞典》则将素养概括为三个方面:读写能力、文字知识、教育状况。综合来看,关于素养的概念是指利用习得的知识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素养与媒介认知具有几多相似之处。詹姆斯·波特论述了媒介素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它能够“教会人们更多有关媒介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不是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产业以及媒介的负面效果;它需要更深层次上理解人们每天使用的媒介,如何利用这些媒介达到他们的目标,并且避免整日暴露在媒介之下从而可能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后果”[6]。
媒介素养研究范式的转移,大体与对媒介素养概念的理解是相一致的。这四次范式转移分别是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1960年代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能力,1980年代的批判性媒介素养,1990年代之后的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
前三次范式主要关注的是媒介内容,特别是早期媒介研究的精英主义观点认为,媒介提供给受众的大多是低水平、格调庸俗的产品,它们腐蚀了青年一代的心灵,被认为是社会道德衰退的罪魁祸首之一。而晚近关于参与式媒介素养研究的范式,则与当下流行的受众理论是分不开的。作为能动的主体,现代社会的受众不但能够对媒介内容进行批判性解读,而且能够基于当下的新媒介技术,利用它们参与公共领域和社会权利的建构,在社群当中学会自我表达,在交流中形成民主社会的观念。
二、媒介素养的文本分析:索绪尔与罗兰·巴尔特符号学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早期,学者们主要关心那些粗俗的媒介内容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并为此深深忧虑。社会各界将媒介产品视如“流毒”,各种反媒介行为此起彼伏。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对媒介的认知有限,因此面对大众媒介的泛滥却束手无策。这种状况的改观是随着西方社会教育的发展而出现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媒介内容并不总是有害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媒介文本的分析,需要持有批判性质疑和解读的能力,如果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解读媒介文本则是一个祛魅化的过程。
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就是人的观念表达系统,从语言符号问题推而广之,我们整个社会现实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由此索绪尔提出了构建一门符号学的设想:“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7]从符号的表意机制来看,符号主要由两种元素构成: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也是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第一原则,这种任意性在现实中是约定俗成、不可论证的。比如十字路口的红灯,当它亮起来的时候,意味着过往的车辆必须停下来,这是一种规则,违反它就会遭到相应的惩罚。
一般说来,很少有符号作为孤立的个体产生意义,符号的表意存在于与其它符号的关联之中。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符号表意都存在于由符号构成的两个轴上:聚合轴与组合轴。雅柯布森于20世纪50年代将聚合轴的功能定为选择与比较,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与粘合。同时雅柯布森认为,选择与连接是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二元维度。聚合轴的特点,是将所有可供选择的符号进行比较之后,选择符号发送者认为最合适的一个,从而排除其它的符号。作为文本的建构方式,一般人比较难以理解,它是隐匿的。组合轴的特点则是文本的构成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聚合在前,组合在后,并且就文本的构成方式来看,相对于聚合,组合是显性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有的媒介文本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构成的。因为按照李普曼的说法,记者们精力有限,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发生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们不可能采访到所有发生的新闻,它们也不可能全部成为媒介机构报道的对象。各个媒介机构会根据利益需求或相应规则对记者采集的新闻进行选择。
罗兰·巴尔特拓展了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领域内的符号学研究,将符号学应用于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即关注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罗兰·巴尔特看来,任何符号的意指化过程都包含两个序列,而意识形态产生于符号意指化第二序列,即隐含意之中。
当代的媒介建构主义认为,媒介文本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按照阿尔都塞的“询唤”或者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说,“对媒介进行的意识形态分析,试图揭示某些观点和信仰是如何通过媒介再现被合法化,被‘制造成真实的’”[8]。换句话说,呈现在媒介文本上的内容不是全部现实的摹写,按照上文提及的符号表意方式,媒介文本是一种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在媒介文本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文本形式,一种是“源文本”,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外一种是“新闻文本”,即记者或编辑们对源文本的加工与整理。因此,呈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的媒介文本经历了由源文本到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以及其它复杂的生产机制和社会因素。因此说,媒介文本再现是意识形态的,它必然要表达某种观念或者意义。
通过媒介文本再现与意识形态表达,符号表意完成了两个序列的意指化过程。巴尔特符号意指化第二序列中隐含意和神话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传达意识形态,巴尔特称之为“意识形态修辞”。在符号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意指化的方式来维持文化中的迷思和隐含的价值观,从而构建的是关于现代社会的种种神话。在关于什么是现代神话的定义上,巴尔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认为“神话是一种讲述”[9],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一种意指作用的形式。
运用符号学理论解读媒介文本的再现方式,与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可以呼应起来。批判性媒介素养注重的是分析媒介文本符码和规约的技能,对文本内容呈现的刻板印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和质疑。批判性媒介素养关注五个核心议题:非透明性原则、编码与规约、受众解码、内容与讯息、动机[10]。非透明性原则作为批判性媒介素养中的第一原则,认为所有的媒介讯息都是建构之物,马斯特曼说,媒介的内容生产和意义表达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媒介再现,它包含了复杂的媒介内容选择、加工和社会文化符码的植入,媒介内容隐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动机在于为了获取权力或者其它利益。
三、媒介素养的受众理论:皮尔斯符号表意模式
媒介素养研究除了对文本的关注之外,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是受众。从符号表意的过程来看,接收者是传播得以实现的要素。因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来自受众的阅读活动与文本的互动,未被受众阅读的文本只是作为等待理解的符号体系,被受众接收的文本才是创造并生成意义的文本。
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意义只有在文本符号与读者阐释活动的互动中才能显现出来。与此对应的是,读者不能将自我从这样一种交流中分离出来;相反的是,阅读活动能够刺激读者使之与文本紧密联系并且创造文本发生效用所必需的条件。这样文本与读者就处于对等的状况下,不存在主客体相对立的情况,因而意义不再是被限定的客体,而是一种被体验的结果。”[11]伊瑟尔的这段话旨在表明读者并非被动的接受文本的召唤,而是一种创造性的主体间行为。
不过这样的观点在传播理论研究早期是没有市场的,包括在批判性媒介素养研究之前。人们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媒介传播效果研究上,被动的受众研究理论直到1970年代之后才发生了转向,斯密塞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商品阅听人”的概念。真正从受众角度研究媒介理论,以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两位学者为主要代表:约翰·菲斯克和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是从大众文化角度来分析受众理论的,他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宰制性的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之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的反应,并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12]因而在大众文化中,受众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角色,他们也是意义的生产者。
斯图亚特·霍尔主要是从受众解码的视角来谈论受众理论的,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认为,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根据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线性模式,仅仅关注了信息的交流层面而未能考虑到传播过程中复杂的关系结构,而实际上传播过程仅是传播过程中的一部分。电视内容生产、流通、接受实际上是三个既关联又区别的独立过程,受众的接受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被受众接受的电视文本其意义话语无法表达。在此基础上,霍尔提出了积极的受众理论。
从斯图亚特·霍尔解码方式出发,戴维·莫利等人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修正主义理论,“把意义的构成看作是文本和受众的社会地位、话语地位相互作用的过程”[13]。这就给受众解读媒介文本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受众的解释是媒介文本表意的核心要素。这样一种理解媒介文本的模式,与上文提及的索绪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路明显不同。索绪尔或者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聚焦的是文本,而现在我们所论述的解读模式则是将解释者作为关键因素,它对应的是另外一种符号学思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模式。
不同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学模式,皮尔斯的符号学模式是三元的,什么是符号?皮尔斯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它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理解,如此,它就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物的意义。这样,它就是一个符号,或者表征。”[14]从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号意义的生成特别依赖符号使用主体的运用和解释,尤其是符号接收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皮尔斯在建构符号学模式的过程中受到了康德对事物范畴划分的启发,根据康德的哲学解释,世界上事物被划分为十二个范畴,皮尔斯将其精简为三个范畴:范畴A、范畴B、范畴C。其中范畴C扮演着联结范畴A与范畴B关系的中介者的角色。这三个范畴分别对应着皮尔斯符号学模式中的三项:符号(sig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
解释项的提出是皮尔斯符号学模式创造性的表现,它是符号主体使用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交流能力的表征,符号意义的表达具有开放性,符号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符号意义自身不断累积的过程,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学模式中,符号表意的过程就是:“(1)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一个是解释项。(2)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3)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延绵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15]当符号在社会文化系统中被叠加使用后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意义,因此符号意义的使用和传播就不会停滞,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中,会形成循环表达的意义流。但是如果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符号自身的意义也可能会被附加上新的表意元素,从而形成新的意义表达。
根据皮尔斯的符号表意模式,受众对媒介文本意义的阐释就是开放性的,媒介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局限在封闭的框架中。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赋予现代社会公众更多的媒介近用权,他们需要更多的在建构社会身份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表达。马斯特曼指出,现代社会公众所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能力,就在于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媒介表达,在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上,显现出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观。
四、结语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媒介素养研究中的文本分析与受众研究,可以作为媒介素养研究一种普适性的方法论基础。根据媒介研究专家们对媒介文本特征的分析:“媒介讯息是建构的;媒介讯息生产与政治、经济、社会及其美学语境相关;媒介意义的生成是在受众、文本和文化三者之间展开的;媒介讯息依据不同的语法规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特征和象征系统;媒介表征在人们理解社会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符号学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媒介文本的这些特征,并且利用媒介参与到社会的交流和互动中去,能够对媒介文本的内容作出批判性的解读,而不至于受到媒介内容文化霸权的宰制。可以认为,符号学的理论方法在培育现代社会公众媒介素养能力的问题上具有某种普适性,从批判性媒介素养发展媒介交往能力,从参与式媒介素养出发构建参与式文化,使得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成为构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5.
[2]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
[3]HANS MARTENS.Evaluat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Concepts,Theor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2010(1):2.
[4]W.JAMS POTTER.Theory of Media Literacy:A Cognitive Approach[M].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2004:59.
[5]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69.
[6]W.JAMS POTTER.Argument for the Need for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4(48):266.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8.
[8]泰勒,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
[9]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M].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1991:106.
[10]凯尔纳,谢尔.迈向批判性媒介素养:核心理念、争鸣、组织与政策[J].刘晶晶,王莹节,译.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1):72-74.
[11]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9-10.
[12]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3.
[13]柯伦.重新评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
[14]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5.
[1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4.
[16]RENEE HOBBS.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48):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