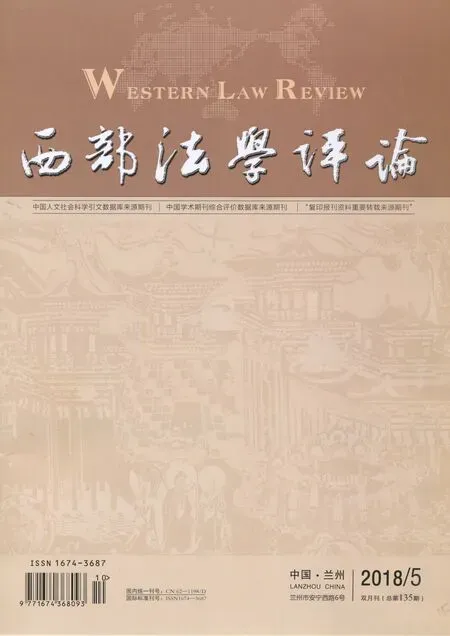论我国刑法视野中的无罪过故意侵权行为
——以殴打诱发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为例
夏尊文
实务中,殴打诱发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以下简称“此类案件”)的行为定性,是一个令人困惑不已的问题。[注]关于实务中对此类案件定性的困惑,参见冯建红、吴敏:《特殊体质命案的罪与罚》,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7/30/content_164870.htm,2017年8月11日访问。控方往往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进行指控,辩方往往以意外事件为由进行辩护。法院的裁判则往往支持有罪指控,而对辩方的理由不予采纳,但也不一定完全认同控方所指控的罪名,时而认同控方指控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时而将控方指控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纠正”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从法理上看,无论控辩双方的观点,还是法院的裁判,都有失妥当。学术界对此类案件有过一些研究,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总体上不太令人满意。[注]学术界对此类案件的分析论证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客观归责论的运用,参见李文军:《故意伤害致特异体质者死亡案件处断争议之辨析》,载《法学》2010年第8期;孙运梁:《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件中的刑事归责问题》,载《法学》2012年第12期;周光权:《客观归责方法论的中国实践》,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因果关系论的运用,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68页;陈兴良:《口授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161页。传统方法的运用,参见张明楷:《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蒋太珂:《被害人特殊体质司法现状的刑法理论分析》,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韩忠义:《一般殴打行为致特异体质人死亡之责任承担》,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2月14日C03版;石欢欢:《致特殊体质者死亡定性问题研究——以李维军、李红军故意伤害案为例》,兰州大学2016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20—27页。鉴于此,本文拟从此类案件的理论基础出发,对此类案件的行为定性展开分析论证,提出合理可行的定性取向,供司法实务参考,同时求教于司法实务工作者与学界同仁。
一、理论基础
此类案件的定性牵涉到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关系、刑事罪过与民事过错的关系,只有先厘清这些关系,才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
(一)刑事罪过与民事过错的关系
在历史上,刑事罪过与民事过错之间总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法国学者丹克(Tunc)提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经历了一个从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合一到逐渐分离的过程。[注]Andre Tunc,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4, Torts, Introduction, J.C.B.Mohr(Paul Siebeck)Tubingen, 1974.p.29.转引自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在罗马法时代,侵权同犯罪并无严格的区别,侵权法是刑法的合伙人。[注]C.L.Williams,The Aims of the Law of Torts,ibid,p156.转引自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我国古代的律典也呈现民刑合一、以刑为主的格局,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注]参见童伟华:《刑民不分与刑民有分——以比较法为视角》,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由于长期实行民刑合一的法律制度,我国古代无系统完整的侵权法。[注]参见徐振华:《中国近代侵权法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6页。一直到清朝,才开始形成刑民案件的立法分野。[注]参见郑琼:《各行其道:刑民冲突案件的审理思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冲突为视角》,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12期。法律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生活中,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经常发生交叉,在杀人、伤害等案件中,一个行为可能既构成侵权行为也构成犯罪行为,在这样的案件中,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可以同时并用。[注]有的学者认为,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经常发生规范竞合。所谓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规范的要件,致该数个规范都得到适用的法律现象。参见前引[3],王利明书,第231—232页。但是,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也并非总是发生交叉,因此,为了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区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必须严格区分刑事罪过和民事过错。[注]同前引[3],王利明书,第233页。不过,泛泛而谈民事过错和刑事罪过的关系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民法上的故意、过失与刑法上的故意、过失加以区分,有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
(二)民法上故意与刑法上故意的关系
关于民法上故意与刑法上故意的区分,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民法上故意的成立,通说一向采所谓的‘故意说’(Vorsatzheorie),认为须有违法性(违反义务性)的认识,而违法性的错误当然排除故意……在刑法理论上,除故意说外,尚有责任说(Schuldtheorie),认为故意与故意责任应加以区别,故意的要件是指对该当事实的认识作为责任要件是对违法的认识或有认识可能性时,始有责任非难的可能,从而违法性错误是否应负故意责任,视对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有无而定……”[注]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论者强调违法性认识对成立民法上故意与刑法上故意的重要性,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论者所举的例子,在民法上只能成立过失的行为在刑法上反而构成故意的行为,刑法上故意成立的标准比民法上故意成立的标准还低,有些令人费解。
国内通说认为刑法上的故意与民法上的故意相同。[注]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页。这种观点有些片面,毕竟二者存在区别。Grotius认为,“过错侵权责任虽然要考虑过错行为的后果,但是,过错行为与此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并非相互依赖,行为的过错性应当单独加以考虑,不受该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影响,行为的过错具有惩罚性,而行为的后果则具有损失的补偿性。”[注]同前引[4],张民安书,第66页。这种观点比较切合实际,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民法上的故意与刑法上的故意。据此,笔者初步认为,民法上的故意单纯通过行为的故意就能够认定,但是刑法上故意的认定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不能仅仅考虑行为的故意,同时还要考虑结果的故意,有的时候还可能牵涉到故意的分层问题。[注]关于刑法上的故意,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民法上过失与刑法上过失的关系
区分民法上的过失与刑法上的过失也有较大难度,因为二者都存在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所以,“民事过失通常是定义犯罪行为的一种不恰当依据”。[注]Santillanes v.State,849 P.2d 358,365(N.M.1993),转引自[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尽力对二者加以区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均认为犯罪过失的标准要比民事过失的标准高。[注]参见王雨田:《英国刑法犯意研究——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与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上引[美]约书亚·德雷斯勒书,第120页。在台湾,针对有学者依刑法的规定解释侵权行为上的过失,有的学者指出,“惟就方法论而言,民法上过失的功能及其认定标准,应有别于刑法,因为二者的规范目的不同。申言之,即刑法在于行使国家公权力,对犯罪者加以处罚,从而关于过失的认定,应采取主观说(或折中说);民法(尤其是侵权行为法)则在合理分配损害,过失的标准应采客观的标准。准此以言,在刑法无过失(主观)而不成立犯罪者,在民法上得因过失(客观)而构成侵权行为。”[注]同前引[10],第241页。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
与上述学者的立场不同,国内通说一方面认为刑法上的过失与民法上的过失相同;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法上过失的客观化。[注]参见前引[11],第666—667页。从法理上讲,刑法上的过失须以预见可能性为基础,因而刑法上的过失的判断应当采取主观标准,民法上的过失的判断应当采取客观标准。通说认为,刑法上的过失与民法上的过失相同,也存在客观化的观点有悖法理。[注]国内也有学者一方面将“对实现构成要件的危险的认识可能性”作为过失犯不法构成要件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又认同过失犯没有主观构成要件的见解,自相矛盾。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359页。
民法上过失与刑法上过失的不同判断标准集中反映在注意义务的区分上。就民法上的过失而言,行为人违反的是一种合理的注意义务。[注]参见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48页;熊进光:《侵权行为法上的安全注意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7—88页;王利明主编:《民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68—569页;前引[11],第667页。如果行为人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使其不能预见结果的发生,也要对结果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即过失责任。在英国,所有故意侵权的侵权行为根本无须行为人预见到其行为的危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所规定的行为,就构成侵权,在没有合法有效的抗辩的情况下,就必须承担责任。[注]参见胡雪梅:《“过错”的死亡——中英侵权法宏观比较研究及思考》(第Ⅱ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在英美,“原告往往在遭受被告故意侵权的时候亦可以借助过失侵权法这一更广泛的原则来责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注]同前引[4],张民安书,第235—236页。可见,在英美,对故意侵权行为完全可以提起过失侵权之诉,因为故意侵权、违法行为都能反映行为人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故意侵权、违法行为可以直接成为认定民法上过失的根据。基于相同的法理,我国当然也可以这样处理。
就刑法上的过失而言,行为人违反的是一种相当的注意义务,[注]参见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刑事法杂志社1982年版,第262—263页;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故意侵权、违法行为不能直接成为认定刑法上过失的根据。相当的注意义务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相当性,只有具有这种相当性,行为人才有预见可能性。换言之,刑法上的过失认定以预见可能性为基础。刑法不能将注意义务强加到一个不可能预见到结果发生的人身上,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能够预见’是应当预见的前提、基础。行为人若不能预见,就没有理由要求其‘应当预见’。”[注]魏克家:《认知过失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二、实务中定性存在的问题
以上述理论作为基础,可以发现,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无论法院判决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定性,还是意外事件的辩护理由,都存在诸多问题,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一)法院判决定性存在的问题
关于此类案件,有的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定性,其中有一个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审理该案的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定性,同时鉴于案件的特殊情况(被害人患有严重心脏疾病,被告人的伤害行为只是导致被害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予以减轻处罚,将一审判决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注]参见《洪志宁故意伤害案》,载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7—448页。认真分析这一定性,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将殴打的故意等同于伤害的故意,将殴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的行为。众所周知,在我国,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故意伤害罪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以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而故意伤害罪基本犯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要有伤害的故意(至少具有造成轻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的行为,造成了伤害的结果(轻伤以上),并且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该案中,被告人在主观上只有殴打的故意(旨在造成被害人暂时的肉体疼痛或者轻微的神经刺激),没有伤害的故意,客观上只实施了殴打的行为,没有实施伤害的行为,更未造成伤害的结果(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的殴打行为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的结果),因而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犯无法成立。失却这一前提,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便无从谈起。很显然,殴打的故意不同于伤害的故意,殴打的故意是一种侵权的故意,单凭行为的故意就可以认定,而伤害的故意是一种犯罪的故意,远没有侵权的故意认定那么简单。此外,殴打的行为也不同于伤害的行为,殴打只是造成被害人暂时的肉体疼痛或者轻微的神经刺激,伤害需要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结果,殴打还是伤害是需要法医通过鉴定予以证明的,要用事实说话。
其二,将侵权的过失等同于犯罪的过失。故意伤害罪结果加重犯成立的另一个条件是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至少具有犯罪过失,犯罪过失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有预见可能性。[注]张明楷教授指出,故意伤害致死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死亡具有预见可能性。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页。周光权教授同样认为,要得出过失的结论,需要对他的预见可能性进行判断。参见前引[1]。在该案中,被告人事先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并不知情,[注]参见前引[24],第447页。说明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缺乏预见可能性,既然如此,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就没有犯罪过失,因此,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就更不能成立。不过,虽然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缺乏预见可能性,不成立犯罪的过失,但是成立侵权的过失,因为如前所述,殴打的故意侵权行为成立侵权的过失并不需要对结果的发生具有预见可能性。
其三,这种定性以被告人的殴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定罪的根据,[注]参见前引[24],第447页。有失妥当。一方面,通说认为,偶然因果关系一般是量刑的根据而非定罪的根据;[注]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4—85页。另一方面,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是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在被告人主观上缺乏伤害故意、缺乏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的情况下,对被告人的行为论以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不但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潭,也不能取得教育罪犯、预防犯罪的效果。张明楷教授指出,在殴打行为偶然导致他人死亡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注]参见前引[2],张明楷文。
其四,以《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为据对被告人减轻处罚,[注]参见前引[24],第447—448页。有滥用减轻处罚的规定之嫌。关于《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立法机关起初作了如下解释:“第二款是关于犯罪分子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案件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的特殊性,如涉及到政治、外交等情况。对于有特殊情况的案件,即使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立法机关新近对本款的解释有些变化:“刑法作本款规定,就是为了赋予人民法院在特殊情况下,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作出特殊处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主要是为了防止实践中扩大适用范围或滥用减轻处罚的规定,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本款规定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的特殊性,如涉及政治、国防、外交等特殊情况。”[注]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根据立法机关对本款的解释,该案根本无关乎政治、国防、外交等特殊情况,所以,该案以本款为据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属于对本款规定的滥用。
关于此类案件,有的法院以则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这种定性基本上是法院将控方故意伤害罪的指控纠正过来的,除了存在上述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定性中将侵权的过失等同于犯罪的过失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将民法上的注意义务等同于刑法上的注意义务之嫌。[注]参见(2014)一中刑初字第1930号,(2015)兵九刑终字第00007号,载中国裁判文书网。
(二)意外事件辩护理由存在的问题
实务中,辩方往往以意外事件作为此类案件的辩护理由,根据是我国《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该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对于该条规定,立法机关以及通说均解释为“意外事件”。[注]参见前引[31],第20—21页;前引[28],第120页。学者们大多认同这一解释,至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刑法上的意外事件是否要承担侵权责任,则没了下文。有的学者在认同这一解释的同时,指出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与民法中的意外事件不是同一个概念。[注]参见金泽刚:《论狗咬人案件的刑事责任问题》,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有的学者认为意外事件在民法中是侵权免责事由,在刑法中是排除犯罪事由。[注]参见董秀婕:《刑民交叉法律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3页。
实务中,有的辩方采纳了最后一种观点,不但肯定此类案件的性质为意外事件,同时否定侵权行为的存在,主张不应要求被告人承担侵权责任。[注]参见(2014)一中刑初字第1930号,载中国裁判文书网。这种辩护意见无异于将刑法上的意外事件等同于民法(侵权法)中的意外事件。可是,殴打属于故意侵权是绝对的,既然被害人是被告人故意殴打致死,理应承担侵权责任。辩方在否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否定刑事责任的同时,以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为由连同侵权责任一并否定掉,这样不但让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而且让法官也难以接受。
因为法官不能接受辩方意外事件的辩护理由,[注]此类案件以意外事件为理由的辩护基本上以失败而告终。参见(2014)一中刑初字第1930号,(2015)兵九刑终字第00007号,(2017)渝02刑终79号,载中国裁判文书网。但又需要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所以为了追究被告人的法律责任,始终没有放弃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根据。为了将被告人的行为认定有罪,不惜将殴打的故意等同于伤害的故意,将殴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的行为,将侵权的过失等同于犯罪的过失,将民法上的注意义务等同于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将作为量刑根据使用的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定罪根据使用,甚至滥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对被告人减轻处罚。这些代价不可谓不大!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殴打被害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侵权,由于被告人事先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并不知情,因而不能预见到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为不能预见,所以这种故意不能及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故意止于违法;因为不能预见,所以其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也不存在犯罪的过失,过失止于侵权。既无犯罪故意亦无犯罪过失,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其行为无罪。最终只能以其故意侵权行为作为基础,以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为由,认定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侵权法上的过失,可对被害人的故意侵权行为提起过失侵权之诉。侵权行为人就其故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亦属理所当然。
从法理上讲,实在不该将我国《刑法》第十六条解释为“意外事件”,而应借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十八条的“无罪过造成损害”进行解释,[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十八条(无罪过造成损害)规定:“1.如果实施行为的人没有意识到而且根据案情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行为(不作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没有预见而且根据案情也不应该预见到或者不可能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则该行为被认为是无罪过行为。2.如果实施行为的人尽管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由于其生理心理素质不符合极度异常条件的要求或者不适应神经心理过重负担而未能防止这种后果发生。其行为也是无罪过行为。”《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将其解释为“无罪过行为”。“无罪过行为”只能说明行为不构成犯罪,只能免除刑事责任,而不能将所有的法律责任都免除,从而为侵权责任的认定留出空间。事实上,我国《刑法》第十六条根本不是对“意外事件”的规定,因为该条所规定的损害结果的造成跟“行为”有关,只不过行为人对自己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罪过而已。而意外事件(caso fortuito),是指非因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故,是外在于当事人的意志和行为的事件。[注]参见前引[3],王利明书,第615—616页。意外事件属于事实,而非行为。[注]刘霜:《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无怪乎意大利刑法学家帕多瓦尼慨叹:“意外事件”在刑法体系中一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注][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26页。
显然,立法机关以及通说将我国《刑法》第十六条解释为“意外事件”是对该条的误读,这种误读若再加上另一种误读——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一样可以免除民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认定就完全没了空间。这大概是司法实务中法院将《刑法》第十六条弃而不用、将此类案件认定有罪的原因所在了。
不难发现,除了立法机关、理论界,实务中的控、辩、审三方都对我国《刑法》第十六条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该条规定的不是“意外事件”,更不是能将其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等而视之的“意外事件”;该条只否认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只提供出罪通道;该条并不否认侵权法上的故意与过失,并未堵住认定侵权责任的通道;刑法上没有罪过不等于侵权法上没有过错。因此,既不能将侵权法上的故意与过失等同于犯罪的故意与过失,以入罪代替出罪;亦不能以否认犯罪的故意与过失为由否认侵权法上的故意与过失,将出罪、认定侵权责任本来可以共用的通道视为两条互不相容的通道。只有深刻领会这种立法精神,才能将这一法条用活、用好。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