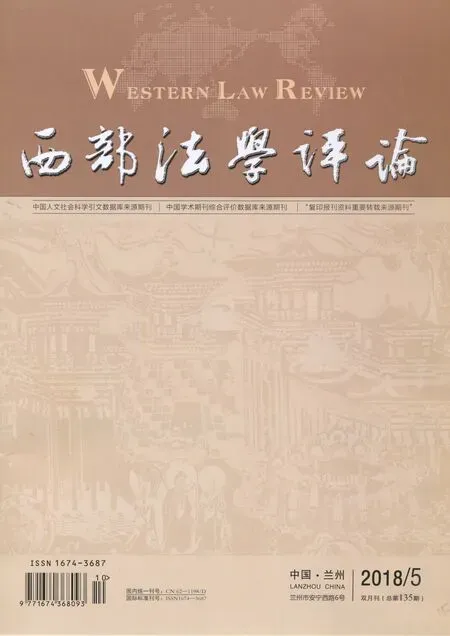论盗窃比特币的行为性质
王 卫,南庆贺
一、司法实践:出现类似案情不同定性的乱象
随着比特币的火爆,盗窃比特币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对于这类案件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类似案情不同定性的乱象。
(一)仲某盗窃比特币:被北京检方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批捕
犯罪嫌疑人仲某,系某互联网科技公司运维工程师。2016年9月,仲某在进行服务器日常维护时发现服务器内数据异常,有他人试图通过黑客手段入侵公司服务器并尝试盗取该公司比特币。在排除异常干扰之后,仲某心生歹念,利用管理员权限登录服务器并插入一段代码,将公司的100个比特币转移到其在国外网站注册的比特币钱包内,后为消除痕迹躲避追踪,仲某尝试使用了该网站的私密钱包功能,将10枚比特币投入私密钱包内,但该功能后被证实为钓鱼网站所设,存入的10枚比特币已无法找回。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纪敬玲认为,根据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颁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的相关条款,“比特币具有没有集中发行方、总量有限、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个主要特点”,“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犯罪嫌疑人仲某在被害公司的服务器中插入代码,对数据加以修改,并将数据所代表的比特币转移至其个人开户的网络钱包中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非法获取行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故,2018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犯罪嫌疑人仲某进行逮捕。[注]彭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北京检方批捕比特币盗窃案嫌疑人》,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26日第11版。
(二)武某盗窃比特币: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决武某犯盗窃罪
发生在浙江省天台县的武某盗窃金某比特币一案中,天台县人民法院却将其定性为盗窃罪。2016年2月22日晚,被害人金某在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天都花园E9栋602室上网时,其电脑桌面上打开的五个“MMM”投资平台账号及密码被和其远程链接的被告人武某窃取。被告人武某利用该五个账户及密码,通过篡改收款地址的方式盗走被害人金某账户中的比特币70.9578枚(价值人民币205607.81元),后在“火币网”交易平台上出售,并将交易所得资金提现到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武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注]参见(2016)浙1023刑初384号。
(三)如何认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VS盗窃罪
对于盗窃比特币的行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予以定性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以盗窃罪予以定性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定性为盗窃罪是否可行,即比特币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其数额该如何确定。本文将对盗窃比特币行为的定性及后续量刑展开研究,为实务部门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参考意见。
二、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予以定性不合理:存在实体与程序双瓶颈
司法实践中,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重要理论支撑是,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货币,其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存在明显差别,若将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解释为财物,有扩张解释之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胡云腾在《人民司法》发表《〈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文,明确表明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确需刑法规制,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不应按盗窃罪处理。其理由有四,一是认为虚拟财产与金钱财物等有形财产、电力燃气等无形财产存在明显差别;二是认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三是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计算方式;四是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有将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注]胡云腾、周加海:《〈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 2014年第15期。文章指出,《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在《解释》中明确,对盗窃游戏币等虚拟财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经研究认为,此意见不妥。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确需刑法规制,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不应按盗窃罪处理。主要考虑:其一,虚拟财产与金钱财物等有形财产、电力燃气等无形财产存在明显差别,将其解释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其二,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对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当然可以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量刑。其三,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计算方式。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明确了具体定罪量刑标准,适用该罪名可以罚当其罪,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其四,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有将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修改“刑法”时,在第323条将电磁记录增设为动产的范围,对窃取电磁记录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但是2003年修正时,将电磁记录又从动产的范围内删除,实际上否定了1997年的修正,对窃取电磁记录的行为规定适用专门的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来处理。其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根基,概因将虚拟财产归入传统意义上的财物存在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代表了官方观点。
事实上,理论界也有学者如此认为 ,“侵犯虚拟财产必然要通过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才能完成,在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 ,应该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从而既避免了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争议,也能很好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注]陈云良、周新:《虚拟财产刑法保护路径之选择》,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
但是,笔者认为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胡云腾大法官及相关学者的观点难以成立。
(一)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主要侵犯公法益,盗窃比特币的行为主要侵犯个人法益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位列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该章节所列罪名主要属于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侵犯社会公共法益的犯罪。具体言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犯罪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犯罪对象仅限于使用中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进一步探究、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其“情节严重”主要表现在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量”[注]该条文第一款第(四)项也罗列了违法所得或经济损失,但这不是其主要保护的法益。上,如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获取上述以外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的。即对不特定对象信息的获取。
然而,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并没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侵犯社会公共法益,也不是对不特定对象信息的获取,而是对特定对象“财物”的获取,即主要侵犯个人法益——财产权。例如,被告人武某窃取被害人金某账户中的比特币70.9578枚,后在“火币网”交易平台上出售,并将交易所得资金提现到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被告人武某盗窃比特币的行为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金某的财产权,也实际造成了被害人金某的财产损失。
(二)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如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则有损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犯罪与刑罚、刑事责任相适应、相均衡。[注]赵秉志、于志刚:《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但是,如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则明显违背该原则。为了更详细地论证此观点,笔者将犯罪嫌疑人仲某盗窃公司100个比特币的行为建模,如下图所示。

前 情犯罪过程结 果罪 名刑 罚模型一(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观点)公司准备200万元①用于投资购买比特币,并将购买后的比特币存于公司所控制的电子钱包内。仲某用非法侵入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方式盗走比特币。损失价值200万的比特币。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模型二公司准备200万元用于投资购买比特币。购买比特币前,被仲某盗走200万元。损失200万元人民币。盗窃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①②根据案发时比特币交易平台的报价,被盗100枚比特币价值200万,故此处设计为200万元。追回90枚,可在具体量刑时予以考量,此处不论述。
〔7〕根据案发时比特币交易平台的报价,被盗100枚比特币价值200万,故此处设计为200万元。
对比上述两个模型,可以发现,导致罪名不同的两个变量是犯罪手段中介入了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一元素和盗窃对象分别为200万元、价值200万元的比特币,进而导致刑罚的显著区别。
进一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何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四种具体行为和一个兜底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即,一是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二是获取第(一)项以外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的;三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台以上的;四是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五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显然,仲某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并不属于第一、二、三种具体行为。而属于第四种行为,即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注]事实上,此种认定尚存在明显弊端,因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主要保护对象应是“数据”,而不是“经济损失”,但是比特币明显不属于其所罗列的前三种情况,姑且如此定性。这也是将盗窃比特币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不合理性表现之一,此处不展开论述。当然,由于仲某造成了公司高达200万的经济损失,故其量刑应符合情节特别严重,即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分析得知,仲某盗窃比特币被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并可能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根本原因在于仲某的盗窃行为造成了公司的200万经济损失,而不在于认定仲某所盗窃的比特币属于“数据”。而类似的情况,如模型二,在同样造成公司200万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应定性为盗窃罪,并可能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难道仅仅因为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一作案手段形式的出现和盗窃对象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在刑罚上就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显然,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犯了以形式掩盖实质的错误。
(三)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如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则有损被害人行使追回相关损失的诉讼权利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犯罪嫌疑人仲某进行逮捕。虽然前文分析仲某之所以可能被量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原因,在于其造成了公司高达200万的经济损失。但这并不妨碍将犯罪嫌疑人仲某盗取的比特币认定为“数据”这一结论。事实上,该公司在后续行使追回200万经济损失的核心,就是追回“数据”——比特币。但是,该公司将会难以行使相关诉讼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简言之,即将 “物质损失 ”界定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显然,盗窃比特币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并不属于侵犯人身权利造成的物质损失,也不属于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故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畴。
那么是否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由国家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显然也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明确所盗窃的比特币为“数据”,显然,“数据”并不属于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财物”、“财产”、“违禁品”。
退而言之,可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明确所盗窃的比特币为“数据”,显然,“数据”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物质损失,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所规定的管辖范围,即双方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产生的民事纠纷。
三、以盗窃罪予以定性具有合理性:前提在于论证比特币是否属于刑法中的财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构成盗窃罪。一般认为,凡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的,构成盗窃罪。具体言之,盗窃比特币的行为,肯定属于盗窃行为,且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唯一具有争议的问题,即比特币是否属于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因此,只要论证比特币属于公私财物,那么盗窃比特币的行为以盗窃罪予以定性便具有了合理性。
(一)明确判断方法,是论证比特币是否属于财物的基本前提
前苏联著名法学家C·C·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注][前苏联 ]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729页。,“对法律案件的决定是根据三段论法作出的,其中法律规范是大前提,案件的情况是小前提,案件的决定是结论。把案件的决定看作是按照三段论法的规则得出的结论。”[注]当然,在判断事实是否符合规范时,目光必须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即不断地将规范向事实拉近,不断地将事实向规范拉近。在此意义上说 ,大前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时代,毕竞只有在事实符合规范时,才能认定事实是否成立犯罪。所以,法律规范终究是大前提,而不可能将事实作为大前提。国内学者侯国云、么惠君却持有另一种观点,其离开法律规范这个大前提,按照自己的观察先确定案件的定义,并归纳其特征,最终反向比对。[注]侯国云、么惠君:《虚拟财产的性质与法律规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
笔者姑且按照侯国云、么惠君的观点对比特币是否属于财物进行分析。比特币作为一种点对点全球通用加密数字支付系统。[注]比特币的发行与交易不依赖中央银行、政府、企业的支持或者信用担保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也不与特定商品或者实物挂钩,而是依赖对等式网络中种子文件达成的网络协议,实现单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直接交互,比特币地址之间的价值交换,具有“去中心化”特质与相对匿名性。比特币系统使用整个网络的分布式数据库来进行交易确认,其发行总量固定,并自适应地按照设计预定的速率逐步增加且增速逐步放缓,最终在2140年达到略小于2100万个的极限值。点对点分布式的时间戳服务器生成依照时间前后排列并加以记录的电子交易证明使得比特币系统能够实现无须第三方支持的数字签名加密、杜绝双重支付(伪造支付工具)。发行的比特币由完成网络运算工作量证明(“挖矿”)的比特币“旷工”获取,偖此激励其通过利用计算机硬件为比特币网络进行数学计算从而完成交易验证、提高比特币系统安全性。其具有去中心化(比特币区别于传统法定货币,不依赖于中央银行发行。)、数字化(比特币是根据中本聪的思路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是依据特定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的数字货币。)、局限性(比特币只能在网络中存在,脱离网络将会变得“看不见”、“摸不着”。)、动荡性(比特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极具动荡性,价格极不稳定。)等四个特征。比特币所具有的这四个特征明显不符合刑法上财物的特征。侯国云、么惠君的这种推理方式存在明显弊端。任何事物的属性必然具有多面性,如果抛开大前提——法律规范,其所归纳某事物的特征必然是不符合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
事实上,即使退一步说,比特币具有去中心化、数字化、局限性、动荡性这四个特征,就一定能否认其财物属性?其一,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不是财物。股票也是不依赖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而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但股票是财物无疑。其二,数字化是21世纪诸多财物的表现形式,如以支付宝和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数字化版权等,不能因为数字化的表现形式就否认它们是财物。其三,能否将其变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并不影响其是否属于财物的判断。有些物体“看得见”、“摸得着”,却不是财物,如大自然中的水、山。有些物体“看不见”、“摸不着”,却是财物,如电子版的国库券等。其四,稳定性也不是财物的当然属性。股票、期货虽是财物,但其价格也经常涨跌浮动。
回归到犯罪嫌疑人仲某盗窃公司100个比特币一案中,在判断仲某是否构成盗窃罪时,首先应该确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然后总结归纳仲某的案件事实,再得出仲某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结论。同理,在判断比特币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时,也需要以刑法上的财物作为大前提,将比特币作为小前提,判断二者是否对应,然后得出结论。在此判断的过程中,判断者必须要以刑法上的财物为指导,归纳仲某案件的事实,或者说必须提炼、明确刑法上财物的特征,然后分析比特币是否具备财物的特征,最终得出结论。
(二)更新解释理念,是论证比特币是否属于财物的价值取向
刑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必须同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便没有生命力。所以,对刑法必须采取同时代的解释。现时取向的根据在于:现时有效的法的效力之合法性并非立基于过去,而是立基于现在。[注]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 1959年版 ,第 186—187页。
而今时今日的现实,在于比特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发扩大,如比特币能够以极低的交易成本在“商品”与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等各国“货币”之间进行快捷转换,并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在全球各大比特币交易平台供市场参与者进行投资或者投机,甚至可以附加杠杆、做空、融资、融币等交易机制进行各类远期、期货、期权等衍生性交易;与亚马逊在技术设备和电子产品销售方面齐名的在线电子商务网站Newegg Inc.(新蛋)正在扩大其支付选项,表示接受加拿大客户的比特币付款;俄罗斯世界杯期间,足球迷们可以用比特币支付住宿费用;包括家电连锁商场 Big Camera、丸井(Marui)ANNEX 百货等在内的多家日本公司,已经开始支持使用比特币付款。比特币的财物属性在当今经济社会中越发明显。
总之,联想100多年前就存在的“管理可能性说”[注]“管理可能性说”认为,财物不限于有体物,具有管理可能性的无体物也是财物。其中,“物理的管理可能性说”认为,具有物理的管理可能性的有体物与无体物都是财物。例如,热、光、水力、冷气等均为财物。“事务的管理可能性说”认为,具有事务的管理可能性的有体物与无体物都是财物,如牛马的牵引力、人的劳动力以及债权、情报等均为财物。,再看比特币在当下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理由固守“有体性说”[注]“有体性说”认为,财物仅限于有体物,即必须是占有一定空间的有形的存在。,而将比特币排除在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之外。[注][日]伊藤真:《刑法各论》,弘文堂2011年第3版,第109页。
比特币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仅是动态的数据组合,同时具有可视性。上文列举的比特币在经济社会应用的诸多例子,就充分说明其正在融入经济社会,并以一种活跃的姿态,充当财富的象征。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观念,因为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比特币的财物属性,它都可以用来交易、支付、贮存。
(三)符合财物特征,是论证比特币是否属于财物的关键环节
张明楷认为,对于财物这一概念,首先必须根据财产犯罪的本质与保护法益进行解释,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物”字,就认为只有有体物才是财物。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具有三个特征,即具有管理的可能性、具有转移的可能性、具有价值性。否则,要么他人不可能侵犯,要么不值得刑法保护。[注]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载《法学》2015年第3期。
比特币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其具有管理的可能性。盗窃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换言之,相对于被害人而言,即首先要占有比特币,如果被害人不能占有比特币,就谈不上被害人拥有比特币,比特币也就不可能视为财物。比特币的官方客户端自带比特币存储功能,即一种加密“软件钱包”,只有当占有人同时启动所掌握公钥和私钥,方可打开,进而对其进行诸如支付、转移等管理。
比特币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其具有转移的可能性。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如果不能转移他人的比特币,就谈不上侵害他人的财物。比特币的公钥和私钥是一串很长的字符,行为人在掌握公钥和私钥后,可以启动比特币官方自带的转账功能,将他人的比特币转移至行为人控制的加密“软件钱包”,且不可追踪和找回。
比特币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其具有价值性。刑法中规定的任何一个罪名,背后都隐藏着国家要保护的法益。如果一种对象没有任何价值,就不值得刑法所保护,也就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财物。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价值。[注]理论界关于价值的理解,主要存在2种观点:一是财物的价值包含使用价值;二是财物的价值包含交换价值。事实上,无论哪种价值都没有指出某一对象之所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的本质属性。如,情书具有使用价值,但其显然不是财物;卖淫等服务具有交换价值,妓女提供色情服务,嫖客支付金钱,但卖淫显然不是财物,否则强奸妇女的行为就构成抢劫罪。笔者认为,根据盗窃罪的特点,只有当行为人盗窃比特币的同时,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失,才能认定比特币是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财物。无论是仲某盗窃公司比特币,还是武某盗窃金某比特币,该公司和金某都遭受了财产损失是确定无疑的。
四、以盗窃罪予以量刑具有可行性:关键在于确定犯罪数额
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虽然具有合理性,但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盗窃罪作为典型的财产犯罪,其量刑主要取决于数额的多少,如果无法计算比特币的数额,那么将盗窃比特币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就缺乏司法实践的可行性。
有观点认为,当前比特币交易平台众多,全天候发布比特币当日的成交价格、成交额等相关信息,因此,只需提取案发当日众多交易平台所发布价格的平均值就可以确定盗窃比特币的数额。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当前比特币交易价格极具动荡性,甚至存在一日之内涨跌几倍的极端情况。尤其是当其价格处于高峰阶段,容易导致量刑倚重的情况发生。
还有观点认为,可以按照行为人的销赃数额计算盗窃数额。笔者认为销赃价格往往低于实际价格。如果按照销赃数额计算盗窃数额,便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法益。
法益的价值是与法益的主题密切关联的,所以在盗窃比特币的案件中,应当考量他人是以何种方式、付出何种代价取得比特币。因此,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比特币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为认定标准。这样既可以避免出现量刑倚重倚轻的极端情况,也体现了刑罚罚当其罪的原则。那么如何确定他人所造成的损失,可以从比特币的获取途径来论证损失数额。一般来说,比特币的获取途径有三种:一是通过“挖矿”获取比特币;二是从交易平台买入比特币;三是以产品或者服务换取比特币。
(一)被害人通过“挖矿”获取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挖矿”成本
比特币是通过运行复杂程序算法得来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下载、运行软件来制造比特币。但是,随着比特币的发展,挖矿机装备竞赛越发激烈,挖掘比特币的难度已经非常大,需要拥有极高的算力才能勉强开采到。一般应当充分考量矿机投入、折旧以及挖矿所需要的人力、电费等因素,并结合全网运算能力(挖矿难度)的发展预期,大概估算每个比特币的生产成本。目前而言,一方面随着矿机硬件技术的提升,单位运算能力矿机的生产成本和能耗都在降低,但另一方面,随着矿机的增加,单位运算能力、能够挖掘到的比特币会逐渐减少。整体来看,挖掘比特币的成本在快速上升。
(二)被害人从交易平台买入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买入成本
另一个获得比特币的方法是通过交易平台用法定货币来购买,交易平台颇多,比特币与法定货币兑换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且是全天候不间断交易,且不设定涨跌限度。一般应当充分考量被害人从交易平台买入比特币实际付出的法定货币数额。同时,将案发时比特币众多交易平台所发布价格的平均值与买入时的价格进行比对,适当考量其可期待利益和损失。
(三)被害人以产品或服务换取比特币,则盗窃数额应综合考量产品或服务的公允价格
无论你从事哪种行业,只要你对比特币感兴趣,并且看好比特币的增长潜力,都可以用你的产品或服务换取比特币。一般应当充分考量产品或服务的公允价格。同时,将案发时比特币众多交易平台所发布价格的平均值与换入时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行比对,适当考量其可期待利益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