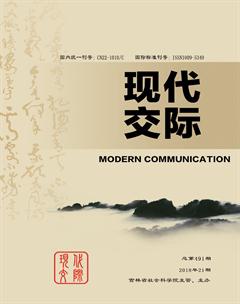浅析《回忆》中的“母亲”形象
章莉人 牛冬娅
摘要:《回忆》(1933年)是太宰治客观地回忆幼年和少年时代经历的自传小说,收录于太宰治24岁时(1932年)以遗书的形式创作的《晚年》之中。本文将分析叔母、阿竹、生母的形象和太宰治与这些人物的关系,结合弗洛伊德的“焦虑情绪”理论探讨太宰治对“母体回归”的渴望。
关键词:回忆 母亲 焦虑情绪 母体回归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21-0103-02
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岛修治,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在其短暂的15年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奔跑吧梅洛斯》《斜阳》《人间失格》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太宰治对日本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小说《斜阳》衍生出了“斜阳族”,太宰治的逝世日期为后人所铭记,由此诞生了“樱桃忌”。此外,众多的作品被译成中、英、俄等多种语言,太宰治文学遍及世界各地。其文学生涯的起点是发表了以遗书为创作目的的小说集《晚年》,该小说集收录了包括《回忆》在内的14篇作品。太宰治在《回忆》中,客观描述了自己幼时和母亲、叔母、阿竹的相处情形。这三位女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们与太宰治的人生轨迹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宰治在幼年时期,由于生母的缺席,对“母体”分离的不安与恐惧通过叔母和阿竹无微不至的关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也正是由于母爱的缺失,太宰治与叔母、阿竹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这种母爱的“缺失”和“拥有”对其思想轨迹和写作风格造成了重要影响,使太宰治终其一生寻求“母体回归”。
本文将以分析叔母、阿竹、生母的人物形象探讨母亲对太宰治的影响,并结合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分析太宰治对“母体回归”的渴望。
一、生母
太宰治的生母生于明治6(1873)年8月,从小体弱多病。尽管生了11个子女,却没有精力和体力照料,于是雇佣了乳母,因而太宰治 “对于母亲,不怎么亲近”“关于母亲的记忆,总是悲凉的居多”。[1]p25作为地主家的孩子,却不被家人重视,以至于他开始对自己抱有“罪恶感”,因而在《二十世纪旗手》中写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在太宰治的成长环境中,给他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一是津岛家是津轻首屈一指的名门、地主和富豪的家族背景,二是在传统的恪守封建秩序的环境中成长”。这是他成为矛盾体的原因,一方面讨厌自己的顯赫家世,另一方面又渴望从大家族中找到存在感,吸引家人的目光,得到应有的关怀。但“当我和兄弟们一起坐在餐桌前时,祖母和母亲也经常一脸认真地说我长得丑,我觉得很不甘心”[1]p29,在日积月累的不被重视的生活里,太宰治逐渐产生了“多余人意识”,这也为他的宿命指明了方向,他心思细腻比身边人早熟,擅长说谎包装自己,时常对人生感到不安,借助安眠药解救自己的长期失眠,喜欢用“道化”的方式取悦他人,这些都为他五次自杀体验奠定了基础。亲情的缺失,甚至可以说母爱的缺失是其根源所在。“太宰治早期放荡堕落的生活是基于母爱的缺失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行为”。[2]“甚至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与恋母情结的恶战”。[3]太宰治和多位女性有密切的关系,在其五次自杀体验中,有三次是与女性殉情。可以说女性也是太宰治的人生主题之一,他将对母爱的渴求转移到亲近的女性身上,却又由于幼年时有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因而与女性的交往又显得极为谨慎,时常担心这些女性像母亲一样抛弃自己,于是多次和女性一起殉情。这也是太宰治性格里的矛盾之处,渴求从女性那里得到母爱,却又因为担心被抛弃将其亲手毁灭。这种矛盾之处与其生母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宰治的人际交往不仅包含当下的现实需求,还涵盖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母爱的丧失体验使太宰治从小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为了缓轻母爱缺失的痛苦,他从幼年就开始逃到自己编织的空想世界里,特别是到了中后期,在数篇作品中塑造了美丽、高贵、温柔、无私的母亲形象,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母体回归”的渴望。
二、叔母和阿竹
太宰治从两岁开始由叔母抚养教育,白天和叔母的女儿们嬉戏玩闹,晚上和叔母一起睡,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曾一度以为叔母就是自己的生母,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太宰治上小学。叔母一直把太宰治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给予了无尽的关怀与温暖,在太宰治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起生母,太宰治更加依恋叔母。“那名男子带着我看神社内的各种马匾额,但我却渐渐空虚起来,哭着喊‘姆姆,姆姆”,“叔母当时正和亲戚们在远方的洼地铺着地毯喧闹着,一听见我的哭声,连忙站起来,不料却被地毯绊着脚,有如行大礼般身体摇摇晃晃的。”[1]p23当对身边的陌生环境充满恐惧之时,太宰治本能地呼唤叔母,而非其他人。可见于太宰治来说,叔母是镇静剂,也是定心丸。当看到踉踉跄跄的叔母被众人嘲笑时,心里十分不甘,于是放声大哭。“某天夜里,我梦见叔母抛下我离开家了”[1]p23,梦境是现实的映射,在太宰治的潜意识中,温柔、无私的叔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在寻求母爱的同时,对叔母随时有可能离去充满了恐惧和担忧,这种不安根源于太宰治母爱的丧失体验,也体现了太宰治“母性回归”的渴望。小说以对叔母的回忆开始,以对叔母的回忆结束,可见叔母对于太宰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母爱的缺失使得太宰治将情感寄托在生母外的其他女性身上,从幼时开始便学会用“道化”的方式取悦叔母,“逗叔母发笑”[1]p23,可以说这是太宰治日后成为“道化者”“无赖派”的早期萌芽。
除叔母外,阿竹也给予了太宰治母亲般的关怀,她在太宰治3岁时被雇为专属佣人,负责太宰治的日常起居和教育,在其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阿竹对我的教育十分热衷”“阿竹还教我有关道德方面的事”。[1]p23太宰治七岁和叔母分开,八岁和阿竹分开,开始和父母一起生活,但并没有从家人身上得到注视和关怀,也没有找到安全感,相比之下阿竹和叔母更能满足他的情感需求。“在阿竹身上,太宰治找到了心里的母亲,以及生母无法给予的安心感和踏实感,在那里找到了真正的母爱”。[4]在创作中期作品《津轻》的时候,太宰治曾回到津轻老家特意寻找阿竹,实际上这是一场寻求母爱的旅程,也是太宰治“母体回归”的渴望。
三、太宰治的“焦虑情绪”与“母体回归”
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权威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站在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了“焦虑情绪”与“母体回归”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在出生的那一刻,面临着与母体的分离,便产生了最初的焦虑情绪。“第一次的焦虑是由于与母体分离而起,也很令人寻味。我们自然要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埋有重复引起这第一次焦虑的倾向,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免得掉焦虑性情感。”[5]其学生奥托·兰克在其著作《出生创伤》中写道:“影响个体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出生时与母亲分离的‘原初焦虑,无论是神经症的还是正常的焦虑都源自于出生,源自于同母亲子宫这个安全地方的原初分离”[6],因此,当人类在面临“不安、忧虑、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7]时,就会唤起潜藏在心底的焦虑情绪,从而产生“母体回归”的本能愿望。弗洛伊德针对儿童焦虑症状,提出儿童习惯于“一个亲爱而相熟的面孔,主要是母亲”[8],当幼年的太宰治与生母分离时,其焦虑情绪便再一次加重,因此他心中对“母体回归”抱有强烈的期待,而叔母和阿竹无微不至的关怀宠爱正好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他也在潜意识里把叔母和阿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但幼时与生母分离的经历使其对于“母亲”时刻会离去充满担忧和不安,“某天夜里,我梦见叔母抛弃我离开家了”[1]p23,这种与“母体”分离的不安与焦虑情绪一直笼罩在太宰治的心头。直到他八岁时,由于叔母改嫁才被接回津岛家,这是太宰治人生中第二次经历“母体”分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恐惧、不安、担忧等焦虑情绪一次次深化,最终产生了回到原始的安全地带,即“母体回归”的渴望。“经由乳母授乳、叔母抚养的过程中,太宰治逐渐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津岛家中产生异化,潜藏在心底的母性的温柔、和善、细腻开始苏醒,并自然而然地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隐藏自己的本性。”[9]换言之,太宰治在与“母体”分离的焦虑中,采取戴上假面的方式隐藏性格中细腻、敏感、害羞的部分,以此来掩盖自己对“母体回归”的渴望。纵观太宰治的一生,我们可以知道,在他短暂的39年生涯中,经历了分家除籍、参加共产主义活动、五次自杀等事件,并将自己推到了绝对孤独的极限。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太宰治虽未得到生母的爱,却被母亲的替代者——叔母和阿竹关怀疼爱,她们的母爱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太宰治的心理空虚,但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其对母爱的渴求。在太宰治的内心深处,生母的爱是无人能弥补的,被家族疏远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特别是当被母亲认为容貌丑陋之时,更加速了自卑消极性格的形成,也由此产生了“多余者意识”,为了引起他者的关注,他用“道化”的方式取悦于人,以此来寻找存在感,这也导致了太宰治服务型人格的形成,当然这也是太宰治企图通过他者之爱弥补母爱缺失的途径。正如佐藤隆之所说,“太宰治一生的主题都是母性回归”。[10]由于母爱的缺失,不断通过与女性殉情、寻求他者之爱来填补,除此之外,将对“母亲”的渴望及其心路历程融入作品中也是途径之一。但纵观太宰治中、后期作品中被玷污、逐渐衰弱、甚至死去的母亲形象,以及太宰治自身敏感脆弱、颓废堕落、消极自卑性格的定型,可以说这场母爱追寻之旅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参考文献:
[1]太宰治.太宰治全集[M].筑摩書房,1978.
[2]奧野健男.太宰治论[M].東京:新潮文库,1984:16.
[3]山内祥史.太宰治论集 作家论书[M].东京:まゆに书房.1994:257-258.
[4]东乡克美.作品论 太宰治[M].东京:まゆに书房.1994:243.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318.
[6]司群英,郭本禹.兰克:弗洛伊德的叛逆者[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50.
[7][8]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3,326-327.
[9]原子修.母源へのいざないー大宰治論ー[J].札幌大学教養部紀要,1992:30.
[10]佐藤隆之.太宰治の強さ[M].东京:和泉书院,2007:237.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