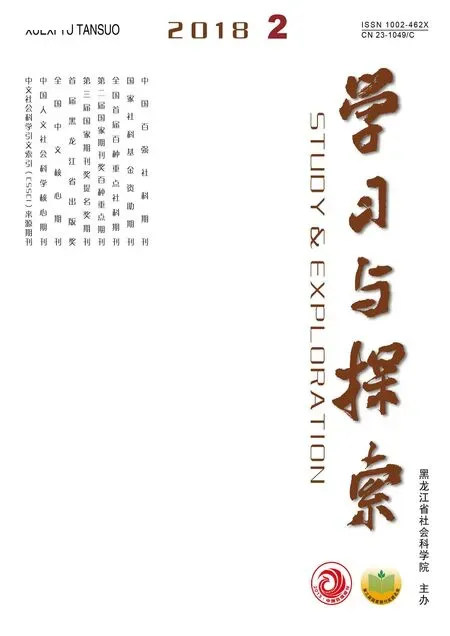从“场外征用”到“图—图”互文
——现代视觉表征的新范式及其意义生产
张 伟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肥 230036)
在人类社会的表意体例中,图像叙事无疑是最为久远也最为便捷的一种表意方式。从古老的岩洞壁画到现代的数码图像,图像凭依自身直观可感的叙事效应抢占了表意世界的强势话语,进而也验证着“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1]这一论断的公允。当然,尽管图像在人类的表征场域中一度处于主流,但多数场合图像的表意不是孤立的,图像与其他媒介的联姻成为人类社会表征文化的普泛形态,诚如W.J.T.米歇尔所言:“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要纯化媒体的冲动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创举。”[2]依托电子、数字媒介的技术支撑,现代视觉更是将表征媒介的互动发挥到极致,图像与语言、图像与声音构建的表意图式成为现代视觉表征的重要形态。与现代社会颇为显性的“语图”“图声”关系相比,现代视觉艺术还创构了一种图像文本的越界征用现象,亦即征用他者图像来融入新的图像叙事文本,实现他者图像与新的图像语境的话语对接,从而完善特定的视觉叙事。如果说“语图”“图声”是两种有着本质表意差异的媒介之间产生的意义互动,那么图像的越界征用则属于同质化媒介符号之间的一种意义交互方式。所不同的是,图像的越界征用无论是被征用的图像抑或所对接的图像语境都打破了先前既定的话语场域与意义界限,产生了一定性征的形式重组与意义联动。或许出于图像本身意义生成机理的相似性,因越界征用形成的“图—图”交互关系多是隐性的,两种图像的对接与意义生成机制多为图像表意机理的同质性所遮蔽,其形构的互文形态常被忽视。因此考察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的“场外征用”及其形成的互文关系,对现代视觉文本内在表征结构图式的深度观照乃至深化对视觉文化现代性征的审美考量,无疑都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一、古典艺术形态中的视觉征用与意义互动
作为人类社会常态的表意媒介,用图像来表征日常生活世界与交际话语体系,增强对外在世界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成为图像表意的主要职能。由此,在图像极为普泛的表征机制背后则潜隐着这样一种可能:作为表意抑或阐释手段的图像同样可以完成对他者图像的意义表征,由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逻辑,即作为表意手段的图像与作为意义主体的图像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种交互性的对应与阐释关系。换言之,作为意义阐释手段的图像同样可以用来表征其他图像,增强对另一图像文本的意义认知,进而形成图像与图像之间的表意互动。
严格地说,图像与图像之间所形构的交互形态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尽管学界尚未就这一互动关系达成理论共识,但单就图像的跨场域移植或征用而言,中西古典艺术中却不乏这一现象。宽泛而言,中西绘画中的“摹仿”亦属此列。依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有的艺术形式无非都是起源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现实的摹仿[3]。而摹仿更成为进入绘画创作场域的基本技能,中国绘画中的“临摹”与“仿”即为其典范代表。所谓“临摹”就是按照原作仿制绘画与书法作品的一种艺术创作方法。严格而言,“临摹”又可细分为“临”和“摹”两种形式,“临”是对照原作进行创作或书写,注重对原作笔意的捕捉,“摹”则是以薄纸蒙于原作进行勾勒,取其形似而笔意则稍显不足。就难易程度而言,摹易临难,中国画创作中的“仿”作一般多取自前者。无论是“临”抑或“摹”,其主旨都要力求与原作保持“相像”,在“形似”的基础上实现“神似”的升华。例如,清初的画坛一度以模古仿古著称,对传统技法“唯此为是”的王时敏对宋元名迹颇为精研,尤其追慕元代黄公望的绘画技法,其所绘《答菊图》笔法构图全用黄氏技法,采用披麻皴来勾勒山石,浓淡迷蒙的横点画法,行笔潇洒秀润,将层峦叠翠、林木竞发的山川景致刻画得淋漓尽致,与黄氏山水画稍作对照,无不看出两者之间的对应与承接关系。相对于王时敏的仿作而言,王翚的仿作则更为明显,他毫不隐讳其对先贤的仿拟之功,其所绘《仿巨然山水图》依照巨然的山水画法,山石浓点皴染,作长披麻皴,山顶画石笔墨简劲、浑厚,虽用笔较巨然轻柔,但仍清晰可见巨然画作的本来面目。
较之西方绘画的直接摹仿,中国画的仿作对原作尽管保留一定的写实成分,强调仿作与原作的“相似”,但仿作者更为注重的是仿作对原作的“形意”呈现。换句话说,在仿作中,仿作者以自身对原作的审美感知与文化体验来重新布局画面,融入自身对原作的主旨思考与审美评价,使得仿作中既有原作的某种特征与成分,又呈现出不同于原作的艺术话语与审美旨趣,这样仿作与原作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就不是一般性的“等同”与“相似”关系,而是“偏移”与“超越”关系。对于仿作与原作的关系,热奈特认为这理所当然划归为互文关系:“我把任何通过简单改造或间接改造而从先前某部文本中诞生的派生文本叫作承文本。”[4]按照热奈特的理解,先前存在的文本属于一种蓝本,而由此派生出来的文本则属于承文本,蓝本与承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评论性的攀附关系,承文本在蓝本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是蓝本嫁接的产物,相对于蓝本而言,承文本属于“二度文本”,是二度创作的结果。今天看来,古典绘画中的“临摹”与“仿”作所构建的互文关系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指涉关系,它是图像文本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互文形态,仿作与原作所构筑的关系谱系匹配于“互文”理论的多元特征。然而,古典绘画技法中的“仿作”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图像征用,或者说仿作者所征用的不是原作本身,而是一种意象,仿作与原作更不是一种同体表意模式,因而即便把仿作与原作视为一种因图像征用而形成的“图—图”互文,那么这也只能算是“图—图”交互形态的雏形样式。
除了因仿作所形构的“图—图”交互关系外,在中西方传统的绘画体例中,援引其他的视觉景观来增强画面的叙事感与审美性成为传统绘画意义表征的独特方式,于此作为另类的视觉形式,古典戏曲中的某种视觉表征与视觉符号常以特定的画面元素占据着绘画的文本结构,造成“画中有戏”的互文格局。作为明清小说、戏曲文本中普范的审美符号,插图不仅是对小说、戏曲语言文本的图像转化,同时也是对同一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视觉映射。正因如此,明清盛行的戏曲创作与演出氛围自然与小说、戏曲插图形成自发式的联姻,“援戏入图”成为明清小说、戏曲文本特有的艺术风格。就插图本身而言,戏曲元素对插图文本的介入是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标志,其介入形态通常有二:其一是以小说、戏曲插图来描绘戏曲舞台演出的情景。如明末戏曲本《荷花荡》第二十二出名“戏中戏”;其二是在插图设计中引入戏曲舞台化的版式,即明清之际小说、戏曲插图的版面设计呈现明显的舞台表演效果,插图多置于页面上幅三分之一处,横框结构,画面人物多处于同一水平线位置,平视观照视角,画面人物角色与观者几乎等距,层次感不强,回目分处画面两侧,成对称样式。这一戏曲舞台风格的小说插图以早期的福建建阳、杭州武林插图为代表。这无疑印证了“图—图”互文的现实逻辑。
与大众化的“语图”互文相比,图像的场外征用在中西古典艺术形态中并不普遍,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归属于一种小众性的审美样态。相对于语言文字的表征机制而言,图像叙事在中西方古典艺术形态中的作用力无疑是有限的,图像的越界叙事某种程度上只能由绘画这一单一的艺术方式所体现,再加上图像绘制的技术限制,直观静态的图像叙事很难满足跨境、越界的叙事诉求,即便能够越界去承担一定的叙事职责,其形成的审美效应也颇受牵制,因而图像与图像所形成的意义交互关系也并不明显,而基于技术层面上真正的图像移植与视觉征用,亦即严格意义上的“图—图”互文只有在现代视觉艺术中才能成为现实。
二、“图—图”互文的现代范式与意义生产
作为表征媒介的互动样式,尽管图像的场外征用在古典艺术形态中不乏先例,图像与图像之间也衍生出某种意义上的交互关系与审美联姻,但传统图像之间因摹仿与征引而建立的对应形态与严格意义上的“互文”仍存在差距,它所创构的仅是人类文化艺术形态中“以图证图”“图—图”互动的滥觞。随着电子、数字媒介技术的愈益发展,图像的越界移植与视觉征用在技术层面成为更为便捷的事实,而视觉时代愈益普泛化的图像表征机制也使得图像的越界征用成为图像叙事的内在诉求,可以说正是以视觉为主流表征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图像越界征用的诸多条件,使得现代视觉艺术中的“图—图”互文日渐衍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审美范式,演绎出一幅幅“以图释图”的审美镜像与文化奇观。
相对于古典艺术中图像的越界征用与互动,现代视觉艺术所建构的图像征用形态则更为多元而复杂。且不说基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图像摄录技术将图像的跨界叙事导向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审美自觉,通过摄录镜头,人们无须驻足展览馆、艺术馆、博物馆就可以全方位、近距离观察、欣赏到各种艺术、文化展品,即便是各种世界名画、雕塑的视觉镜像抑或复制品也同样充溢于现代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传统艺术鉴赏中接受者与艺术品之间的距离感在现代复制、摄录技术的支撑下愈渐弥合,现代社会主体生活在一种由艺术复制品构筑的审美境域中,进而重组着视觉时代接受主体与艺术品所特定的一种新型关系。“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5]借力现代传媒的技术支撑,图像的越界征用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但多数场合图像的越界只是传播形态发生了变化,并没有衍生出新的意义,因而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图像征用不能一概划入“图—图”互文之列。真正意义上的“图—图”互文其首要前提是图像在移植前后文本意义较之原初发生较大变化,被征用图像与新的图像文本形式上是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现代视觉艺术中的“图—图”互文导向最具典范的形态,进而更有利于管窥“图—图”关系的现代逻辑。基于上述预设条件,现代视觉中的图像征用一般可归纳为“替换式”与“插入式”两种形态。
1.“替换式”图像征用及其互文架构
所谓“替换式”图像征用指的是基于现代传播媒介的技术手段,对元图像的整体或部分的意义进行重构,在保持图像原初形式特征的基础上赋予这一图像以新的文本意义。简单地说,这种“替换式”征用就是借助特定的视觉图像来传达新的意义,同时又保持图像本身的主要形式特征。依据所替换的图像特质,“替换式”征用又可分为静态的图像替换与动感性的影像替换两种类别。顾名思义,静态的图像替换其援引的图像是单一的、静止的,是对视觉画面的某一形式结构或细节特征展开替换,从而改写了图像文本原初的意旨,并赋予这一视觉图像以新的指涉意义与文化价值。这种静态图像的意义“替换”及其构建的互文关系严格地说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20世纪初达达派画家马塞尔·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上用铅笔为蒙娜丽莎这一形象涂上了两撇胡子,并将画名更改为《长了胡子的蒙娜丽莎》,其在原作基础上对画面形式特征的局部变形与调整无疑篡改了原作的本初意义,其新构图像与原作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当然,杜尚对原作的更改某种程度上只是艺术创作中的“戏谑化”,其衍生的意义并不具有特指性与明确性,而现代视觉艺术中对单一视觉图像的形式更改与意义替换其目的性与普泛性更为明显。意大利时尚导演Davide Bedoni为世界著名运动品牌Nike创作了一套广告作品,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基本保留画作形式特征的基础上将Nike的标志植入18—19世纪的世界名画中,由此这些独具艺术价值的绘画文本被替换为代言Nike这一运动品牌的广告界面,无论是画面的形式结构、意义指涉乃至审美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今天看来,之所以选用世界名画来展开视觉改编,其主要目的就是改编者希望借助名画的审美普泛性来拓展广告的宣传效应,增强广告代言品牌的社会影响力,其构建的“图—图”关系的背后溢动着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内在驱动力。严格而言,对静态图像的“替换”,其基本前提是沿袭元图像的主流形式特征,只作局部形式的调整与变动,新构图像与元图像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比照关系,但两组图像又并非并置于同一时空中,因而其构建的“互文”呈现出一种隐性的互动色彩。
动感性的影像替换其涵盖的画面信息则要大得多,与静态的图像征用不同,动感性的影像互文不再拘泥于单纯的静止的视觉画面,而是具有一定时长、配以一定的音效与视觉表现的影像画面。随着现代视觉剪辑技术的愈益发达,基于影视基础上的影像替换与视觉改编日渐普泛,逐渐衍化为现代社会“图—图”互文的常态景观。替换式的影像征用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由电影《无极》剪辑改编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该片以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中的影视画面为蓝本,将《无极》中那段掺杂着爱情的魔幻故事衍化为一档虚拟性的法制节目,在征用电影影像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个视觉图像意义的“颠覆性”改写。尽管《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制作人胡戈称对《无极》的改编原本出于现代意义上的网络娱乐,但其精湛的剪接技术与重组手段,以及颇为完美的对口形配音,加上引入《MATRIX》以及《月亮惹的祸》作为短片插曲,使该短片一跃成为2005年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改编剧,其风头甚至超越母本电影,被誉为“史上最强评论碟”。
抛开该网络视频与原版电影的版权争议,单就两种影像的关系而言无疑契合了“图—图”互文的基本逻辑。首先,网络短片与其母本电影的影像画面所呈现的意义迥然不同。尽管网络短片沿用的影像基本上都是电影《无极》中的画面,无论是演员造型、活动背景抑或画面风格几乎完全遵循着原剧而未做变动,但两者呈现的意义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图像文本的指涉性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其次,短片制作者有目的地遴选了电影中特定的一段影像,而这段影像却又是呈现短片制作者拟定意义的最佳选择。在时长两个小时的电影画面中截取短短的20分钟,恰恰证明了这20分钟影像具备了承载短片制作者意义表征的主要功能。再次,短片制作者又不是完全拘泥于原剧的影像文本,他采用现代蒙太奇剪辑手段,在改编中添加了少许其他影像画面与特定音效,特别是短片的配音更是一种颇具个性特征的自我创构,再加上别致的音乐背景,使整部短片呈现出更为独立的文本意义。最后,这部网络短片与电影原剧属于“一体”化关系,抛开短片后期制作的添加因素,单就画面的主体特征而言仍然是电影文本的翻版。值得一提的是,择取影视中的特定影像镜头进行文本的改编最初多体现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诉求,很多严肃的影视话题经过改编者的精心包装逐渐演化为流传网络的戏谑化的视觉形态,随着这一“替换”影像的愈益成熟,新的视觉文本也逐渐生成了自身的叙事目的,形构成一个愈发独立的视觉影像形态。
2.“插入式”图像移植及其互文指向
与“替换式”征用有所不同,“插入式”图像征用并不致力于在元图像的基础上进行文本改编,从而生成意义不同的视觉图像,而是征用他者图像插入特定的视觉文本,使他者图像“移植”成为这一视觉文本的组成部分,进而弥合特定视觉文本的图像叙事与意义书写,实现某种审美效果。严格地说,“插入式”图像征用其指涉范围较之“替换式”要宽泛一些,古代小说、戏曲插图中援引戏曲舞台的设计版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图像“插入”,它与“替换式”图像征用的界限也不是特别清晰,通常要依据所征用图像与新图像之间的画面比量来进行判断。当然,这种界限较为模糊的图像征用多出现于静态的视觉图像中,真正意义上的“插入式”图像移植只有在现代视觉影像中才具有典范意义。
“插入式”图像移植的最初形态已无从考证,但随着影像蒙太奇技术的发展,这种图像移植或征用在现代视觉艺术中愈发普遍。例如,《阿甘正传》是由美国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1994年执导的一部影片,就影片本身而言,主人公阿甘经历的年代恰是美国社会在“二战”后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影片中杂糅着美国社会在这一时代发生的诸多真实事件,如亚拉巴马州塔斯卡骚乱、肯尼迪总统遇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为了增强影片的叙事效果,渲染影片所营造的真实感,影片将新闻影像“插入”影片中,造成影片与新闻影像相互杂糅的互动效应。如影片24′09″~24′20″影像呈现的是阿甘登上电视访谈节目,接下来影片切入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真实影像,诸如此般的案例在影片中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影片采取特效的形式将演员表演与历史人物进行互动,如影片中约翰逊总统给阿甘颁发荣誉勋章的影像镜头,约翰逊总统是真实的影像记录,阿甘的人物形象却是演员扮演的,这种“穿越”式视觉画面造成了影片与真实镜像之间界限的完全弥合,创设了一种更为真实的视觉效果,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就征用他者图像插入新的视觉文本,完善图像的叙事效应而言,其形成的前提大体有三种:其一是所征用图像与新的视觉文本某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内涵或图像指涉的一致性或类似性,也就是说,所征用的图像与新的视觉文本所表征的意义要有共性,两组视像的形式特征也不要有太大的差异;其二是所征用的图像所涵盖的信息容量理应是有一定限制的,亦即所征用的图像不能篡夺本体图像的地位,不能掌控新的视觉文本图像叙事的主流话语;其三是所征用的视觉图像理应是为本体图像的视觉叙事服务的,就此而言,所征用的图像原本自身意义的丰富性在征用语境中遭遇有效遏制,也只能凸显它所用以完成其服务本体图像叙事的作用机制。
诚然,无论是“以图证图”的“替换式”图像征用抑或“援图入图”的“插入式”图像移植,其援引图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完善新图像诉求的视觉叙事。换言之,所有被援引的图像不再是具备独立叙事职能的个体图像,它也丧失了这一图像原初的叙事背景以及部分话语指涉意义,渐而成为新的图像语境的组成部分,在新的图像所营造的叙事语境中,被征用的图像借力原初的指涉意义与新的视觉图像产生某种联姻,形构某种意义互动,不断形成新的文本意义与话语形态。
三、现代视觉图像越界征用的互文机理与文化症候
尽管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的越界征用更多场合下体现为图像形式层面的跨场域叙事,所呈现的多是图像叙事的场域发生某种变化,然而实质上,正是表征语境的变异造成了图像文本意义的偏移与重组,而也正是这种意义的重组造成了现代视觉艺术中别样的互文形态,成就了现代视觉表征的另类奇观。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界的显学范畴,互文的最初意旨主要体现在语言文本中,诚如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所言:“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众多文本的交汇,从中至少可以读出另外一个词语(文本)来。……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体间性,诗学语言至少可以进行双声阅读。”[6]37尽管克氏这里所提出的文本主要是指语言文本,而其内含的结构主义机理同样适切于现代视觉艺术的“图—图”关系。就图像征用所构建的新的视觉文本结构而言,无论是“替换式”征用抑或“插入式”移植无疑都是一种图像文本对另一图像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体现出颇为明显的互文本的形式特征。“文本是许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部分互相交汇与中和。”[7]依据互文理论的潜在意旨,互文本不能仅拘泥于语言层面,它更多体现为克里斯蒂娃所描绘的那种“没有引号的引语的‘马赛克’”[6]36抑或巴特所描述的那种“能指编织成的‘立体摄影的多元网络”[8]。抛开文本生产的主体性征,文本更多隐含着一种能指的空间游戏,凸显着文本意义之间相互混杂、相互指涉、相互冲突的过程,而这也恰恰吻合了现代视觉艺术图像征用所形构的“图—图”关系。
诚如前言,正是现代视觉艺术的发展积聚着视觉场域中图像越界的审美冲动,造就了普泛化的图像越界叙事的可能,并形构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审美镜像,而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作用机制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缘由。
首先,视觉时代丰裕的图像表征为图像的越界叙事提供了现实前提。作为人类社会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视觉图像一直以来都承载着意义表征的主要职能。依托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图像表征愈益成为现代社会意义呈现的普泛形态,现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图像生产、传播与消费急剧膨胀的重要时期,形构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图像丰裕乃至“滞涨”的时代。“在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9]正是因为图像表征的丰富与多元,使得对图像表征的援引与征用成为可能,丰富的图像储备以及图像常态表征的愈益主流成为撬动图像越界叙事的两个杠杆,从“供”“需”两个层面不断完善着这一越界叙事的日常化。
其次,现代传媒的发展尤其是蒙太奇剪辑手段的愈发精细为图像的越界叙事提供了技术保障。不可否认,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越界叙事的诸多场域是发生在电子、数字技术支撑的传播媒介中,动感的LED户外广告、现代影视、网络新媒体为图像的跨界征用创设了多元化的技术平台,也使得“图—图”互文成为现代视觉艺术的常态景观与普泛表征方式。严格而言,图像的越界移植更要得益于现代剪辑技术亦即蒙太奇的精臻与普泛,蒙太奇这一源自建筑却在电影学扎根的技术手段成为电影业须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对影像镜头、场面、段落的分切与组接,对影像素材的遴选与取舍,进而使内容更加主次分明、主题更加凝练集中,这一叙事优势同样成为视觉图像越界叙事的重要条件。很难想象,如果缺少蒙太奇这一剪辑技术,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的越界叙事是否仍得以可能?至少在很多层面图像之间的叙事互动都会遭遇相当程度的牵制。
再次,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的越界征用充溢着一种“写实主义”的审美冲动。“写实主义”不仅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更是诸多艺术样式表情达意的内在情结,即便是力求“写意”、追逐“虚幻”的艺术其终极目标仍然难以逃离现实主义的规约。现代视觉艺术中对他者图像的征用很多场合就是对“写实主义”的一种皈依,特别是“插入式”图像移植,所征用的图像相对于嫁接图像而言更具备“写实主义”性征,这种图像的移植无疑有助于提升嫁接图像的“纪实性”与“真实感”。在现代影视艺术特别是战争题材的影像中,援引真实的新闻镜头来铺垫影视叙事语境成为这类影像颇为普泛的现象,从《南京!南京!》到《金陵十三钗》无不如此。更有甚者,凭依现代剪辑技术,所征用的视觉图像甚至与嫁接图像形成了视觉弥合,图像之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逐步消解,进而产生了一种“超真实”的审美效应,《阿甘正传》中约翰逊总统接见阿甘的影像镜头亦是这一技术嫁接的产物。
最后,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的跨界征用契合了大众文化的审美逻辑。作为现代社会颇为典范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内在合理性以及衍进原动力,它超越了日常性的格式化生活方式乃至常规的实践活动,以极具世俗化、商业化、娱乐性以及流行性的审美特征受到大众的热情追捧,渐而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创造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态[10]。现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匹配了大众文化的演变逻辑,无论是视觉艺术的生产抑或接受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着大众文化的潜在规制,而图像的跨界征用同样也契合着大众文化世俗、娱乐乃至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易小星的《刘德华大战周杰伦》以及在《新闻联播》基础上改编的《高温联播》都是例证。这种图像征用一改元图像常态甚至宏大的主旨叙事,以戏谑、搞笑、无厘头作为影像改编追逐的目标,其目的并不在于这些改编的影像对元图像有多少意义上的承接,更多体现为一种“借旧瓶装新酒”的娱乐游戏,改编者所注重的是观者的点击量,而谋取点击量的背后则是网络媒体与影像改编者合谋的商业利益。
当然,由于现代视觉艺术中图像越界叙事的愈发普泛,规约图像互动的社会文化机制也呈现出一种泛化的趋势,不同的图像越界所隐示的文化主因可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如“替换式”的影像征用其蕴含的娱乐化、商业化属性就更为明显一些,而“插入式”的图像移植则更为追求一种写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或许正是文化主因不同程度的潜在作用,使得现代视觉艺术中的“图—图”互文才呈现出更为多彩的表现形态,绽放出更加多元的文本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图像越界某种程度上又是以牺牲元图像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意蕴为代价的。特定的图像文本在被征用的过程中遭遇了意义的撕裂,技术剪辑的背后无疑将元图像的整体性导向一种碎片化,而图像叙事的意义承接却在这一“碎片化”中难以保存,图像本身的审美意蕴自然无法在意义的断裂中得以自保。再者,图像的越界叙事又是以匹配于新的图像文本语境为基本条件的,这就使得被征用图像的意义表达不得不“屈从”于新图像的表征需要,当所嫁接的新图像以戏谑、狂欢、无厘头为基本审美诉求时,被征用的图像本身所残存的宏大主题与艺术风格只能在娱乐化的嫁接场域中渐渐消解,而当这种被肢解的视觉娱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泛景象时,不难想象它对元图像叙事所秉持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意蕴会否产生反向的侵蚀性意义。
与现代视觉艺术中“语—图”“图—声”所构建的互文谱系相比,由图像的越界征用所形构的“图—图”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现代视觉表征的新现象,因征用、移植所形成的意义对接以及风格弥合在不同的征用场合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从而使得考察现代意义上图像越界叙事的审美机理成为可能。较之语言层面的互文范式,图像征用所建构的互文尚无更多的理论支撑,但现代社会愈发普泛的图像征用现象迫切需要学界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这是视觉时代带来的新的研究命题。而只有基于诸多现实文本基础上展开理论分析,归纳出“图—图”互文的现代范式,方能更加深入地实现对现代视觉艺术的审美认知。
[1] 王弼:《周易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2] 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8页。
[4] 吉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5]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6] 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andnovelinTheKristevaReader,ed.Toril Moi,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7] Julia Kriteva,“The Bounded Text in Richter”,inTheCriticalTradition,New York:St.Martin’s,1989,p.989.
[8] Roland Barthes,Image-Music-Text,trans.Stephon Heath,London:Fontana,1977,p.159.
[9] John Berger,WaysofSeeing,London:Penguin,1973,p.135.
[10]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