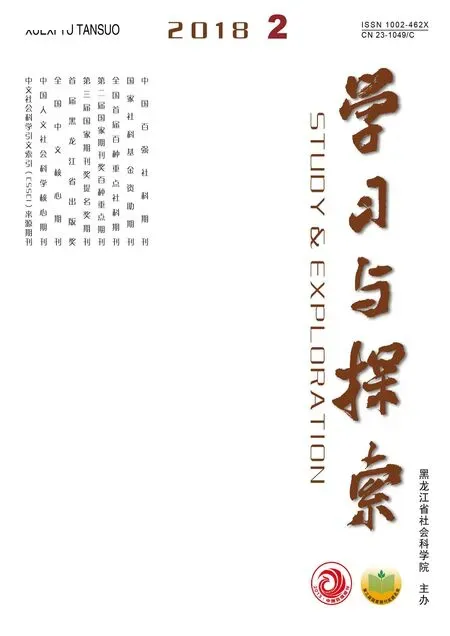《资本论》中三个崭新的因素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自我解读
王 庆 丰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马克思在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书信中谈到杜林时,指明了《资本论》这部著作具有“三个崭新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我相信,杜林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的那种心情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1]249我们知道,杜林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同凯里一样,罗雪尔也是一位庸俗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麦克劳德和罗雪尔的庸俗经济学观点给予了毁灭性的批判。杜林为了避免陷入同罗雪尔同样的处境,才来评论马克思《资本论》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杜林并没有觉察到《资本论》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剩余价值、劳动和工资。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中三个崭新因素的论述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的自我解读或自我评价。杜林之所以没有觉察到这三个崭新因素,就是因为囿于其庸俗经济学的立场。柯尔施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这三个崭新因素,他指出:“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创新,对于被我们称之为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核心的东西——在关于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直接的历史与社会的科学中,批判地扬弃经济学——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77因此,思考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中三个崭新因素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本质性区别,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性质。借用柯尔施的话来说,《资本论》的三个崭新因素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的秘密”。
一、剩余价值的崭新因素
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论》第一个或最重要的崭新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剩余价值”是《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区别所在。但是,就是在“剩余价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却饱受质疑,其中最为重要的攻击者就是洛贝尔图斯。洛贝尔图斯认为自己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在“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讨论过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据此,洛贝尔图斯认为自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马克思剽窃了自己的观点。洛贝尔图斯的这一主张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是以不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的崭新因素为前提的。在《资本论》的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有力地回应与反驳了“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荒谬观点。探讨剩余价值的起源并不意味着发明了剩余价值概念,实际上,从重商主义伊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在讨论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了。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当·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3]13重商主义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产品价值的加价”,斯密超出了重商主义的这种狭隘视界。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斯密明确指出:“一旦土地变成私人财产,地主便会向劳动者要求,几乎每一种在他的土地上采撷或栽种得来的产物,他都要分得一部分。地主要求的地租,是需要土地来进行工作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全部劳动产出的第一笔扣除额。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在收成之前很少有足够的资源维持日常生活。他的生活所需,通常需要由雇主的资本垫付。也就是说,需要由雇用他的农夫垫付。然而,除非农夫可分得一部分劳动产出,或者比较具体地说,除非农夫可以连本带利取回垫付的资本否则不会有兴趣雇用他。农夫的这种利润,是需要土地来进行工作的劳动者,无法获得全部劳动产出的第二笔扣除额。”[4]71显然,这里的第一笔扣除额指的是地租,第二笔扣除额指的是利润。
在斯密看来,无论地租还是利润都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就不需要土地来进行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产出也一样必须扣除类似的利润。在各种手工艺与制造业,大部分工人需要雇主垫付他们工作所需的材料,以及生活费或工资,直到完成工作。而雇主会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或者说,会分享他们的劳动施加在材料上面的价值。雇主享有的那一分价值,便是他自己的利润。”[1]71-72可见,斯密已经认识到:雇主(地主和资本家)的地租、利润和利息实质上都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因此,资本家赚取利润,并非由于商品在售卖过程中的“加价”,即利润不是让渡利润,而是由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马克思高度赞扬了斯密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上所达到的这一正确认识。马克思指出:“在这里,亚当·斯密又明白说明了,完成品售卖上赚得的利润,不是由于售卖,不是由于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不是让渡利润。劳动者加到原料内的价值或劳动量,会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并且是在工资形态上支付的。他们由此领回的劳动量,只等于他们在工资形态上得到的劳动量。另一个部分,形成资本家的利润;这是一个他没有买但可以由他拿去卖的劳动量。”[5]112
斯密把价值认作是对象化在商品之中的劳动,并把利润和地租认作是越过预付给劳动者的有偿劳动(工资)的界限之外而获得的劳动的剩余。由此可见,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并且在斯密这里形成的经济范畴,一直沿用到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之中。斯密从一开始就把握到资本家致富的全部秘密——从工人的劳动中攫取剩余价值,但斯密也仅仅是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而没有真正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局限性在于:“他认定这种剩余纯然是由那部分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生出以后,立即又把这种剩余,确定在利润的形态上,那就是,不把它和它所从出的资本部分关联起来,却把它看做垫支资本总价值以上的剩余,把它和‘垫支在原料和工资上面的资本全额’关联起来。他是直接在利润形态上把握剩余价值。”[5]123换言之,虽然斯密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他却把剩余价值确定在利润的形态上,从而无法形成“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斯密从经济事实当中析出了利润、地租和利息这些经济范畴,然而这些范畴都只是经济科学的比较简单的范畴,或者说只是一种简单的抽象认定,无法达到或形成《资本论》中作为具体对象和思维对象的综合的具体概念。由于斯密尚且无法自觉地提出剩余价值概念,因而也就无法自觉论证出其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内容。
我们可以认为,亚当·斯密不具备凝练出剩余价值这一科学概念的理论基础和能力。但是,更多地却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还未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更加由于其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决定着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最终没能够提出剩余价值概念。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克思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6]作为各种存在形式的利润、地租和利息与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概念本身在理论层面上有着重大的本质性的差别。
恩格斯对照化学史,突出强调了剩余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及其所蕴含的理论革命。恩格斯指出:“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3]20使化学发生革命的是拉瓦锡。拉瓦锡研究了整个燃素说,才发现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所指的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氧气。普利斯特列和舍勒只是析出了氧气,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恩格斯形象地指出:“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3]21。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已经确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确认这部分价值是由劳动构成,澄清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到这里斯密和李嘉图就“止步不前”了。原因在于,他们都被既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所“束缚”,陷于其所设定的对象中无法自拔。“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3]21
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地租、利润和利息等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称为剩余价值的“特殊部分”,而把自己对剩余价值的研究称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1]250根据恩格斯的判断,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理论核心。
《资本论》就是马克思阐明其剩余价值学说最重要和最系统的著作。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概念的全部意义在于:澄明了在现代普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和奴役关系,并向我们揭示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理论远非一个洛贝尔图斯所谓的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革命”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这一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性本质。洛贝尔图斯等人囿于其庸俗经济学的立场,根本无法理解和洞悉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所引发的重大的理论革命,因此,才会产生“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荒唐说法。
二、劳动的崭新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彻底明白“剩余价值”的崭新因素,必须追溯到“价值”,因此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劳动”是如何形成“价值”的。在研究“价值”的过程中,“劳动”概念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二个崭新因素。恩格斯指出:“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正是在追问“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的时候,马克思实现了他在《资本论》中的第二个崭新因素。马克思进而研究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正是在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崭新因素向我们显露出来。恩格斯指出:“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3]22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资本论》中第二个崭新因素就是马克思以“劳动力”代替了“劳动”概念。
马克思自己也强调,他对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包含在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中,而对于价值概念的分析,完全基于属于他自己的劳动概念才得以建构起来。马克思超越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创造了关于劳动概念的崭新的因素。全部的秘密都包含在由马克思本人发现的“劳动力”这一概念之中。马克思打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填补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概念的空白,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柯尔施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或许是通过表面上纯粹谜语的改变对传统的经济学观念即把劳动工资释义为‘劳动的价值’,做出精确的表达,即雇佣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出卖了‘劳动力’。”[2]77与剩余价值概念一样,劳动力概念也隐含着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道扬镳的全部秘密。正是由于马克思重新建立“劳动力”概念,才产生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使得导致古典经济学趋于破产的理论问题获得了全新的解答。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开宗明义地指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支付这种劳动报酬的多少。”[7]在李嘉图看来,投在商品内的劳动量,支配商品的交换价值:劳动量增加,商品价值加大;劳动量减少,商品价值减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排除了斯密价值范畴的二元论倾向,坚定地坚持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劳动。李嘉图在谈论劳动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时,相对劳动量就是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唯一因素。“李嘉图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理论并在价值量的问题上,做出了比前人更为详细的分析,尽管在他的分析中,存在着若干缺点。这是他作为最杰出的古典经济学者的一个主要贡献。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各经济范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未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8]
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全部经济问题都被抽象化为劳动的量上的比例关系问题。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虽然克服了斯密价值学说二元论的含混不清,但是却陷入了纯粹量化的、极端抽象的境地之中,并且将其奉为适用于所有历史时代的先验的、永恒真理。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各经济范畴的超历史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嘉图自认为的永恒真理却陷入了困境: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一难题致使李嘉图学派最终解体。如果斯密和李嘉图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就仅仅是纯粹的商品流通,资本的增值(剩余价值的来源)也就只能是发端于商品的加价。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告诉我们,剩余价值作为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出物。两者之间互相矛盾,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失去了解释力。
“二重性观念”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科学的分析工具和认识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8没有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就无法形成“二重性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再被当作两个孤立的要素来对待,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综合,这种综合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非简单叠加。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1]250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商品具有二重性,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因此,构成价值概念基础的劳动范畴,就决不能是李嘉图所谓的“劳动一般”,而只能是《资本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统一的“劳动”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关系之中,才能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具体的范畴来把握。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商品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这无疑应当成为分析现代社会的直接出发点。劳动者作为法律上的自由人,由于不拥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到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以便能够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基于此,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动者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成为资本增值得以可能的前提。劳动者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时,这意味着劳动者作为人的尺度却依靠物(商品)的尺度去实现,作为人的劳动者变成了作为物的商品。从商品的二重性来看,劳动者的使用价值是因为他能够提供具体劳动,劳动者的交换价值则根源于量上可通约的抽象人类劳动。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商品,因此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实质上就是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出卖。劳动者作为雇佣工人,之所以能够赋予商品以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人自身的活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作为劳动力一方面表现为具体劳动,将原有生产资料加工为新的劳动产品;另一方面,以量化的抽象劳动的形式,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既要在新的劳动产品中保存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又要生产出大于原有价值的剩余价值。资本增值的秘密通过“劳动力”概念被马克思公之于众。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通过“劳动力”概念代替了“劳动”概念,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从李嘉图设定的迷局中解放出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秘密。在《资本论》中,创造价值的概念是劳动力(活劳动),而绝非李嘉图那里抽象的劳动一般。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运行并生出大于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唯一保证。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到《资本论》的劳动力概念,实质表征着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之间经济术语的非连续性,正因为马克思用“劳动力”取代“劳动”,才有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
三、工资的崭新因素
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发展为“劳动力”概念,这也就导致与此相连的“工资”概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工资”概念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第三个崭新的因素。为了阐明工资的崭新因素,同样需要回溯到“劳动”概念。为了能够在工人中更好地进行宣传,恩格斯对马克思发表于《新莱茵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并声称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心愿。恩格斯表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9]322
马克思断言资产者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个牵涉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实质上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果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那么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如果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9]323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工厂主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而给付工人的工资就是劳动的价格。在恩格斯看来,工资如果是工人的劳动的价格,就会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是因为,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是多于我们所需要的。换言之,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9]326
因此,所谓工厂主购买工人的劳动,实质上是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被“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9]326-327。如果工资等同于劳动的价值,那么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综合。所以恩格斯才会说在劳动的价值里找到了两个价值。实际上,工资只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如果我们把工资等同于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掠夺的事实就被掩盖了,好像工资就是工人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回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9]334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如果说工人获得的工资是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工人的劳动的价值,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只支付给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0]198-199作为工资的“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且由于工资和利润的天然对立,资本家会竭尽所能地去降低工人的工资。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0]201如果准确地表述工资概念的话,工资就是维持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最低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为了全面系统地认识工资的真实内涵,马克思区分了工资的三种形态: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和相对工资。我们可以把“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称之为“名义工资”,“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称之为“实际工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区别就是工资和工资实际购买力的区别。不管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两者之间的比值如何变化,它们都必须坚守同一条基本原则:工资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无论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在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相对工资”概念。这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打开了通道。“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9]354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是工人获得的绝对工资,也就是说,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增多或减少只是相对于工资自身而言。相对工资则不然,它和资本利润形成比较关系。诚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绝对工资有所提高,但是工人工资增加的比例并没有资本利润增长的比例高,工人的相对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一事实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资本家的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也不能被消除。
利润和工资之间是天然对立的,或者说利润和工资之间是互成反比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9]355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资本利润的增速,工人的工资永远被资本家减低到最低限度。当工资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利润的增长速度,工人和资本家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社会鸿沟也愈加扩大。工人的相对贫困加剧,社会越来越缺乏公平和正义。“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9]355社会鸿沟的愈加扩大,意味着资本权力的扩大。通过工资,资本对工人的控制和统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工人对工资的依赖是工人对资本的依赖的反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资占总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资本家只需要从资本中拿出极小的一部分——工资——用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同时工人对资本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
通过工资(相对工资)首先变现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即利润和工资的对立。最终集中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当工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拥有阶级意识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更加激化和尖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1]250工资不仅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而且还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秘密。工人把自己的全部劳动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仅支付工人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11]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第一个行为属于流通范畴,而第二个行为是与交换不同的另一种范畴——生产范畴。资本家把支付工人的工资当作生产成本,它换来工人的全部生产劳动,以保证资本的生产力和资本的增值。对于工人来说,工资是通过交换来获得一定数额的货币,以购买一定的使用价值,它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于资本家或者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工资是通过支付来购买工人全部的劳动价值,以追求资本的增值,维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它是“再生产性的”。在资本家看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工厂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机器工具等是一样的,只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永远也不会真正认识到劳动价值的真实含义和利润的不合理性,无法认识到“工资”背后所掩盖的剥削关系。
《资本论》中三个崭新因素——剩余价值、劳动和工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形成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架构。剩余价值、劳动和工资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论》中三个崭新的因素,是因为马克思对这三个经济范畴的分析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狭隘的学科界限,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人的存在方式中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0]8。《资本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应当在这一框架下获得理解,这样才能真实把握住《资本论》的崭新因素,把握住《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的革命本性。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 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亚当·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5]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6]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32页。
[7]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