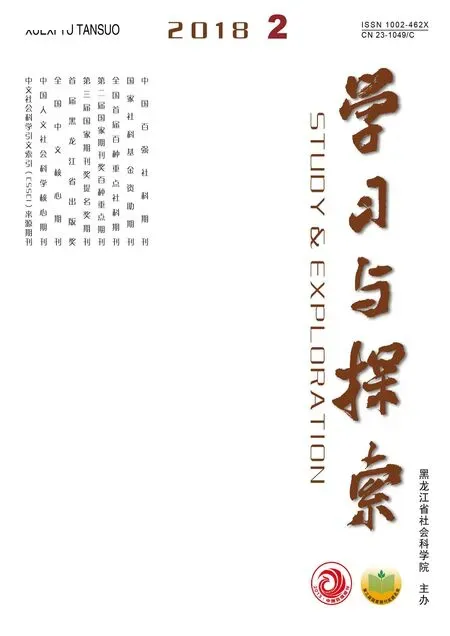从传播到哲学
——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思想理路的考察
孙 光 磊
(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杭州 310018)
众所周知,在传播学当中有着经验实证主义和传播批判理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前者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宗,后者则以批判反思为本。1938年,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传播批判理论的先行者阿多诺远走美国。由于他深厚的音乐素养,被拉扎斯菲尔德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做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并且参与了一项洛克菲勒给予支持的传播研究项目。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项目的研究路径和自己的旨趣大相径庭:因为他们对“制度本身、它的文化、社会现行状况以及它的社会经济前提不加以分析”[1]。实际上,这也是阿多诺所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和经验实证主义传播学派根本上的不同:他向往的是足够的批判空间,而不是对现实基本前提和状况一厢情愿式地接受。阿多诺如此,《启蒙辩证法》的另一位著者霍克海默更是如此。霍克海默虽然生长于一个富足的犹太商人家庭,但是却对经商没有半点兴趣,独独对叔本华、马克思等人的学说情有独钟。他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态度,创办了法兰克福研究所,致力于在新现实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与核心阵地。
一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是《启蒙辩证法》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传播学界经常借以使用的理论资源之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这本书1969年的新版前言中指出:“局外人很难想象,我们两个人在每一句话上是如何地紧密合作。”[2]1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批判理论在社会传播中承担的角色和分量,每一个概念的模糊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想象的误导。仅仅从文章标题开始的“文化工业”一词的考虑上,就能够管中窥豹,看到他们二人进行写作时审慎的态度。阿多诺说:“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了这个用语,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某种从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乃是民众文化的当代形式。但是‘文化工业’与民众艺术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在其所有的分支中,文化工业的产品都是或多或少按照特定的意图、专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出来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消费的性质。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相似,或至少彼此适应,因而自成系统,浑然一体。而这种局面之所以成为可能,全赖当代技术的能力以及财力与管理的集中。”[3]可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使用“文化工业”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着明确的内涵和特定的范围。一些学者将“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混同起来,扩大了概念的外延,从而得出《启蒙辩证法》中的批判论点过于灰暗绝望的结论,这是对“二战”和纳粹极权统治过于敏感的反映,并不适用于当下社会。事实上,从他们对概念做出的精细区别就可以回应这种论调所自有的模糊性。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2]5,而这一倒退明显地表现在电影和广播等新兴媒介之上。《启蒙辩证法》写作于20世纪的40年代,作为新兴媒介的电影和广播在此时还方兴未艾。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靠着敏锐的洞察力,对这些新兴媒介的运作模式做出了模式化、资本化、同质化、控制的加深、强制的逻辑等鞭辟入里的观察。《文化工业》里描述的传媒世界是一幅让人失望的场景,甚至带有很强的悲观色彩。笔者认为,在《文化工业》这一章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有些独断倾向的,他们先在地持有了某种立场,且这种立场虽然鲜明,但论证性并不是很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启蒙辩证法》思想肌理最富有弹性的内容并不在《文化工业》中,所以仅仅是理念上似是而非的接受《文化工业》的立场,而不去探究这一立场的来源,很容易滑向悲观和虚无。
事实上,《文化工业》反映出来的林林总总都是表象,重要的是产生这些表象的逻辑。《文化工业》中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人主体性的丧失,人类被他们所生产的对象宰制,那么这些问题的病灶在哪里呢?启蒙,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共同给出的答案,也是他们理论考察的起点。事实上,他们在书中的序言明确就指出,第一部分《启蒙的概念》是《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的理论支撑。按照他们的思路,理念的思辨应该是现实境况的先行军。对于实证主义的践行者来说,经验事实才是考察的唯一起点,因为那里包含着最“客观”“公正”“如实”的内容,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要反其道行之。阿多诺指出:“实证主义强烈地诅咒矛盾, 但是却包含着最深的内在的、而它自己又不知道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实证主义从情感上说,坚持那种最外在的、清除了一切主观意图的客观性, 然而却更深刻地陷入那种特殊的、纯粹主观的、工具的理性之中。那些自以为克服了唯心主义的胜利者, 比批判理论更深入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他们把认识主体不是实体化为一种创造性的、绝对的主体, 而是想像为一切有效性以及科学控制的固定精神。”在阿多诺看来,他们口中的“经验”恰恰是被主体架构过的“事实”,忘记主体,这是实证主义践行者操之过急产生的盲点。相比于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追问的起点首先在于我们身在何方?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现实到底从何而来?他们要对实证主义新闻学派所赖以使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反思,要回到源头,回到产生这套方法的主体中去,检视产生问题的病灶。“(织机)一踩便涌出千头万绪,梭子只见在来往飞翔,眼不见的一条经线流去……”[4]不断生成的织品背后还有条“眼不见的经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路径首先是哲学的。
二
启蒙是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历程,特别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展向普通民众,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启蒙运动为人类描绘了美好的图景,人们抱着自己的理性尽情欣赏,史无前例的相信依靠理性实现对自然的把控,未来则处于进步和自由的光明前景当中,“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诸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5],启蒙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殿军康德为“启蒙”的意涵写下了这句箴言,并且他积极的鼓励人们“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当时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达朗贝尔也曾经这样描述这一愿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着四面八方急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去路的一切。……人们头脑中的这种普遍亢奋,其产物和余波使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投下新的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6]
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反启蒙的声音也逐渐的日益壮大,法国的卢梭、德国的浪漫派以及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是批判启蒙的先行者。可以说,《启蒙辩证法》在整体上也处于这样一个批判启蒙的传统,特别是对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正是从批判的立场出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目的就是要揭示启蒙概念内在的逻辑悖论: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努力证明本来是以自由、进步理想为目的的启蒙却具有自我取消的性质,启蒙拒斥了神话,却将自己变成了神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一论点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蒙理性受到被黑格尔假设为所有意识形式固有的辩证矛盾形式的支配——根据那种观点,理性既是它自身,又是它相异的、与其自身对立的某种东西”[7]。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同样是对启蒙奉若神明的知性思维的批判。
近代社会有两个占据顶端的原则,一是来自于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的“主体性原则”,他主张“我思故我在”;另一个就是来自于经验哲学之父培根的“实用性原则”,他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这也是启蒙精神最倚重的两个原则。在“主体性原则”那里,笛卡尔使用怀疑的方式,使思维可以抽调一切的内容从而达到一个纯粹的自我,这个纯粹的自我是不可怀疑的确定性。通过这样一种思路,人最高的根据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内在的自我,自我夺去了上帝至高无上的宝座;在“实用性原则”那里,培根认为:“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把握自然,却又不得不受自然的束缚:倘若我们能够在发明中顺从自然,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2]2衡量的标准是经验的有用性,所以没有什么玄妙的秘密可言,从而也就没有开启秘密的那些希望。两个原则让近代人性观焕然一新,成为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但又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痕。毕竟,沿着这两个思路走到极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完全不同的图景:“一是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之一部分的“机械论”图景;二是人类作为自由、自觉、理性的行为者的传统图景。”[8]启蒙精神的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这是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自由与必然的冲突。也可以说启蒙更新了人性,却又带来了人性内在的分裂,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与前述的康德不同,黑格尔虽然对启蒙的精神也有所肯定,但是主要的立场却是批判的,横亘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主要历史事件便是法国大革命,康德主要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的最重要三大批判著作最晚也出版于1790年,所以他的成熟思想基本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相反,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黑格尔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正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大革命作为启蒙运动最高的成果,它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是“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9]。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吉伦特党领导人之一罗兰夫人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她本身是革命者,但却死在革命者雅各宾派的手里;她为人民追求自由,但是却在临死前说出:“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10]随后,继之而来的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皮尔同样没有逃出罗兰夫人的吊诡命运。启蒙一方面在理论上陷入分裂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现实革命的层面又将自由变成了反自由的恐怖统治,面对这样矛盾,黑格尔用极其艰深思辨的语言给出了他的思考。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他们往往奉行形式逻辑为认识的最高方式,这在黑格尔看来是纯然知性的思维方式。启蒙思想家康德要求人们的思维固守在知性的范围之内,任何试图超出知性的努力都将使得思维陷入二律背反的窘境。事实上,黑格尔并不反对启蒙思想家口中的知性力量,相反他认为没有知性抽象在感官知觉的流动现实中设定人为的分殊界线的话, 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知性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抽象、分解和区分。即便是在启蒙思想家那里,知性是与感性密切结合也是不能被否认的。黑格尔认为,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了知性陷入一种任意性当中:“知性所主张的观点是:真理建立于感性的实在之上,思想只有感性知觉给予它一内容与实在的意义下,才是思想;而理性,只要它仍然还是自在自为的,便只会产生头脑的幻影……理性限于只去认识主观的真理,只去认识现象,只去认识某种与本性不符的东西;知识降低为意见。”[11]26所以黑格尔指责启蒙思想家囿于经验知性当中,造成了世界的支离破碎。在知性之上,实际有一种更高的理性,它是纯粹的思维,是对思维的思维,具有统摄全体的能力,但是这种力量却被忽视了。
黑格尔非常欣赏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一论断超越了僵化的知性思维,将事物的规定性与他的对立面的规定性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这种辩证理性只发生在纯概念领域,也就是说,事物自身的规定性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交互关系,这种否定性的力量消解了知性毫无意义的僵化,同时又在新的意义上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使事物可以从抽象孤立中摆脱出来,获得具体而丰富的规定。“只有在规定的光明中—而光明是黑暗规定的—即在有荫翳的光明中,同样,也只有在规定了的黑暗中—而黑暗是由光明规定的—即在被照耀的黑暗中,某种东西才能区别出来。”[11]83表面上看,黑格尔在说黑暗与光明,实际上指的是两者的规定性,这属于概念和思维的领域,所以,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作用在意识当中。
如果回复到法国大革命的现实,人们知性中对自身自由的规定性缺少了否定维度,所以无非是体现了原子式存在的任意性:“自立性被推到了自为之有的一那样极端,便是抽象的、形式的自立性,它摧毁自己——它在较具体的形式中,表现为抽象的自由,为纯粹的自我,然后又表现为恶:这是最大、最顽固的错误,还自命是最高的真理。这是曲解了的自由,把自由的本质建立在这种抽象之中,还自夸是在自由本身那里获得了纯粹的自由。”[11]177而这种主体内在的抽象任意性其实是空无一物的,所以“实用性”的欲望填充了这一真空,而在这种无差别的欲望中,人的个性和规定性也就消弭了,“普遍的自由所能作的唯一事业和行动就是死亡,而且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质的死亡,因为被否定的东西乃是绝对自由的自我的无内容的点;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开一棵菜头和吞下一口凉水病没有任何更多的意义”[12]。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启蒙运动用知性僭越了辩证理性的宝座,但是知性本身并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它只能坚执在空洞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上无法迈步,最终被启蒙的“主体性”原则被架空,而这时“实用性”原则援引了人最初的本能,成为了“入室之狼”,吞噬了主体与知性。
面对启蒙所遗留下的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黑格尔的处境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之于黑格尔,就如同“二战”和纳粹极权统治之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过,对于法国大革命,黑格尔的态度更多是隔岸观火,在头脑中完成对启蒙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显得更有切肤之痛。因此阿多诺才会追随马克思的路径,认为“一种哲学如果从来没有打算面对现实,哪怕它再深刻再玄妙,都是某种现实意识形态的同谋”[13]。
三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一方面清楚的意识到近代启蒙力量内在的虚弱,这一点和黑格尔对启蒙派的观察如出一辙。康德为了调和启蒙的分裂,在物自体和现象界做了区分,内在的自我被区分为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但是事实上,康德并没有清晰说明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关系,所以“理性作为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先验自我,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观念。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类把自己组织为一般主体,并且用自觉的整体协同来克服纯粹理性与经验理性的矛盾”[2]73。当然这种场景是人类所能想象到的尽善尽美的处境,这是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向往,但是理性的另一个维度“构成了计算思维的审判法庭,计算思维通过把世界当作自我持存的目的,并且为了征服物质世界,它从单纯的感性材料中确认了客体的筹划功能。从外部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其真正性质在实际的科学中最终表现为工业社会的旨趣”[2]73。霍克海默、阿多诺清楚地看到,康德先验自我的无力之处,便是近代社会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理性和数学计算理性入侵的地方,这正是统治工业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文化工业》批判所依据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他们深得黑格尔辩证法的深义,思想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僵化的,而是处在辩证运动当中,而这种运动来自于内在的否定性,“正如同神话已经贯彻了启蒙,而启蒙也在他的每一步当中更深的陷入了神话学”[2]36。神话以被启蒙祛魅的方式保存在启蒙之中,似乎神话败给了启蒙。但是让启蒙没有料到的是,神话的生命力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行将就木的残余或者痕迹,而是充当了启蒙理性中先验认知的例子。启蒙排斥了神话,但恰恰是为将神话引入自身做的准备。“神话”代表了世界的构成图式,那种世界运行的方式是通过狡猾的行为、模仿和类比,以及被启蒙所镇压的迷信、疯狂、宗教、艺术、天才等等。“神话作为人类最初对于恐惧的反映,根本没有启蒙过程给消除,反而保存和包裹了起来,神话作为霸权力量形式背后的驱动力,将自身展现为启蒙运动本身的结果之一。”[7]37
不过即便如此,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结构,他对自己的哲学有种体系性的构想,万物从绝对精神出发,最后要复归绝对精神,而辩证法就是这个整体性结构前进的动力,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不断扬弃、发展、进步的过程;霍克海默、阿多诺则并没有这样一个进步的方向,他们的旨趣只在于揭示某种事实性的进展。特别是阿多诺,他在后来的《否定辩证法》一书中强烈地排斥黑格尔的体系化设定,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思维造成了体系的封闭与异化,甚至指出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抱有这种虚幻的愿景。阿多诺始终坚持一种非同一性,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与霍克海默的写作当中:书写的形式以断片出现,并且从始至终都无法像黑格尔那样引申出积极的结论。这表明了他对体系化的拒斥,向往一种具有恒久流动性的哲学,而这种流动性恰恰是《文化工业》的场景中完全不能容忍的东西。
从《文化工业》到黑格尔,从媒体到哲学,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独特而丰富的理论阐述,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进行文化工业批判与思考时的独特理路。甚至可以说,不了解霍克海默、阿多诺思想的渊源和内在的丰富性,不触及近代启蒙精神的危机与困境,《文化工业》的传媒成果只不过是两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出的牢骚而已。
[1] 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正的面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赵勇译,《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4] 歌德:《浮士德》(第1部),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5]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7] 卡斯卡迪 安:《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8] 亨特 伊:《康德的辩证法及其问题》,徐长福译,《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
[9]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10] 《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1] 黑格尔:《逻辑学》(上册),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页。
[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3]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7页。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