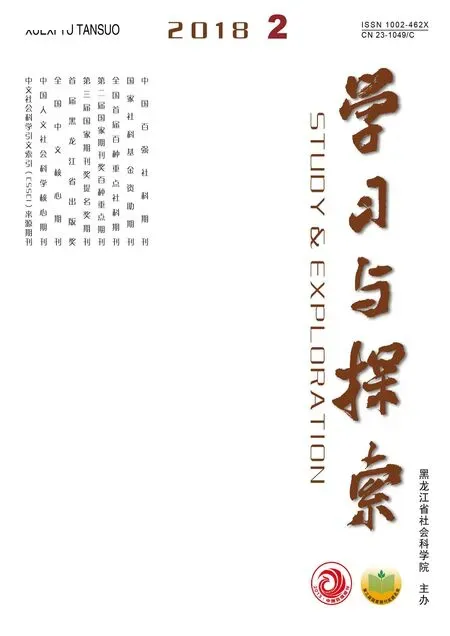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
——对垄断资本学派凯恩斯渊源的考察
张 雪 琴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出版,标志着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垄断资本学派的正式创立。在垄断资本学派走向马克思的旅途中,凯恩斯是该学派思想成长的关键人物。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与凯恩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相遇了,并且通过垄断资本学派的相关理论系统呈现了两者的历史性相遇。这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正确性和在理论上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通过对垄断资本学派思想渊源的考察,从凯恩斯对该学派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角度进行梳理与分析,呈现了该学派立足于马克思、批判性吸收凯恩斯的思想精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演进过程。
一、凯恩斯革命与关于经济停滞的辩论
凯恩斯(1883—1946)无疑是20世纪最著名且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是批判者也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对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公共生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斯威齐曾经用“典型的诚实但短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形容凯恩斯。在斯威齐看来,一方面,“凯恩斯是自从大卫·李嘉图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且他的学派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状况。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贡献,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可以得到更好的阐释”;另一方面,凯恩斯的主要缺点在于“不愿将经济视为社会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从而无法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灾难不是一个可怕的混乱,而是已经失去创造性的社会体制的不可避免的产物”[1]。
(一)凯恩斯革命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积累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总结的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转变。资本积累似乎可以不受限制,消费越少,储蓄越多,能够被用于生产的资源即投资就越多,只是偶尔会因为资金性障碍和供需不协调有所间断。因此,经济学家们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状态是积累和增长,衰退和萧条不过是资本主义暂时修复和自我调整的内在机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指出,关键的问题在于储蓄,而非对资本的需求,积累率主要取决于供给。
马歇尔的观点与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大致吻合,不过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出版之际,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它在“一战”后享受了繁荣的迷人景象,不过好景旋即被大萧条打破。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对于美国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投资与金融的不平衡只是暂时的。在通货紧缩和价格调整之后,投资重新恢复,正是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将对投资不受限制的需求视为理所当然,这后来被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然而,这时的繁荣已具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所不同的特征: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和产能利用率逐渐下滑同时并存。这表明支撑20年代繁荣的投资不可持续,过度积累和经济停滞已取代积累和增长成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常态。
正是在此背景下,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文简称《通论》)于1936年出版,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直面积累过程崩溃的事实,承认经济不会自动修复,从而为重新考虑投资理论奠定了基础。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储蓄和投资)本身存在若干缺陷。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常运转而言,剩余必须投资新的产能。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完全是一桩冒险事业,决定现有产出水平的投资决策完全视未来若干年甚至上百年的预期利润而定。“不确定性”的存在、厂房和设备中积累的生产能力过剩、市场对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以及外部扩张受限等因素均可能导致投资不足。投资的减少会导致就业、收入以及支出减少,且可能使“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漂浮着的泡沫”。这必然对整个经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经济下滑和新增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形成恶性循环。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卡莱茨基,于1933年在关于商业周期、工资以及失业问题的分析中,独立提出且详细分析了凯恩斯所谈及的问题,并将垄断程度纳入经济动态模型。在逝世前,他就投资问题谈道:“为何一旦资本主义在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偏离之后就不能在长期简单再生产中找到位置呢?事实上,只要我们不能解决对投资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一困难,我们就会对上述情形的发生有所担忧。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现代经济学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人试图在周期性波动理论中这么做。然而,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涉及到……长期趋势,这比‘纯经济周期’的情形要困难得多……对我而言,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涉及到资本设备的有效使用的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并不那么显而易见。”[2]显然,卡莱茨基的发现构成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卡莱茨基和凯恩斯共同发起了这场经济学范式革命。
概而言之,罗斯福恰恰是摒弃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范式,通过新政重启美国经济复苏。如果说凯恩斯革命以及罗斯福新政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生动地诠释了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必要,并且给出了诊治大萧条的具体办法,那么,当经济衰退在美国再次上演时,这场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关于经济停滞的辩论呈现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历史性相遇。
(二)关于经济停滞的一场辩论
在走出大萧条仅仅四年后,美国再次发生了经济衰退,到1938年,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至19%,并且在1939年仍然高达17%。经济停滞的严峻现实已经不容否认,关于经济停滞的重大辩论由此产生。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人物就是阿尔文·汉森和约瑟夫·熊彼特。1938年,凯恩斯的追随者汉森以《完全复苏抑或停滞》为题,拉开了这场重大辩论的序幕。1939年,熊彼特在其重要著作《商业周期循环理论》一书的第二卷以《为何停滞》为节标题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回应。
汉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并不必然是增长和积累,而是有可能数十年乃至永远陷入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上升和产能过剩的困境。因此,汉森的分析立足于解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投资不足,他认为这是由下述三个因素所致:地理扩张结束、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及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技术的投入尽管提高了资本使用率,但降低了资本利用率,从而不能实现完全的产能利用率。汉森认为,正是上述因素限制了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从而在储蓄过剩倾向与投资不足倾向的相互作用下,经济体系的运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经济停滞的病症。
熊彼特极为贴切地将汉森对经济停滞的解释概括为“关于投资机会日趋枯竭的理论”。为了反对汉森的观点,熊彼特把问题从探究20世纪30年代经济停滞的根源,转为探讨为何始于1933年的周期性上升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经济周期加以研究。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持续时间较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将根源归结为新政的执行人员的反商业精神所导致的反商业气氛,从而将1937年的衰退冠之以“关于停滞的新政理论”。在熊彼特看来,新政同资本主义正常运转可以兼容,但是新政的执行会打击企业家信心,影响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阻碍投资[3]。
汉森和熊彼特之争已经成为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停滞问题的经典争论。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也曾任命“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考察为何停滞会再次出现以及应该采取何种举措。按理说,这本应在整个社会掀起一股研究经济停滞的热潮,进一步反思凯恩斯革命所具有的重大启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1938年战争的阴霾遍布欧洲,希特勒于该年3月出兵强占奥地利,并于9月签署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随后战争全面爆发,人们的视线完全从大萧条转移至战时准备。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关于停滞问题的讨论近乎销声匿迹。195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斯坦德尔极富洞察力的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问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却视而不见[4]。1954年,汉森在对斯坦德尔新书的评论中颇有预见地指出,“除非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手腕,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问题,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不断下滑。这事实上将是停滞的一种表现。”[5]然而,这些关于停滞问题的讨论似乎再也无法得到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何回应。不过凯恩斯并没有被遗忘,西方主流经济学篡改了他的理论,却将他与马克思历史性相遇所呈现的经济学范式革命的火苗,连同他的追随者对凯恩斯革命的诠释,都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庙堂之外。
二、凯恩斯革命的两重意义:停滞金融化悖论
尽管大萧条点燃的经济学范式革命的火苗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熄灭了,然而,火种已播下,薪火已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异端经济学领域熊熊燃烧,映照出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二战”之后,在斯坦德尔和卡莱茨基这些先驱者的探索下,作为西方异端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垄断资本学派接过了这次相遇所点燃的火炬,并据此提出了垄断金融资本理论。
(一)经济停滞
《垄断资本》出版后不久,70年代的危机以“滞涨”的形式袭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经济增长日趋缓慢。垄断资本学派回到了汉森与熊彼特关于停滞问题的争论,他们认为由于垄断程度的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使得强烈的储蓄倾向和疲软的投资倾向所滋生的停滞问题不可避免。同时,他们提出下述三种因素是70年代对抗经济停滞的重要力量:(1)政府支出和财政赤字的增加;(2)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住宅抵押贷款为主的消费债务攀升;(3)经济体中金融部门日趋膨胀。
既然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那么如何解释从1940年到1970年近三十年间停滞近乎消失的事实呢?垄断资本学派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中,将立足点放在了投资问题上,比较了大萧条时期和黄金年代这两个时间段中投资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初步意识到需要“关于投资决定的专门理论”。他们认为,这两个时间段在投资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以推动投资的方式扭转了世界经济形势,使得原本陷入投资不足困境的垄断资本主义得以恢复。在斯威齐看来,下述五个因素是拉动投资的关键性力量:(1)战时抑制的需求;(2)战争所摧毁的对住房、汽车以及家电等物品服务的潜在需求;(3)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有助于国际贸易的扩张;(4)诸如电子技术和喷气式飞机等军事技术转为民用;(5)军备工业的发展。
同汉森一样,垄断资本学派批判了熊彼特认为新政的执行会打击企业家信心的看法,认为潜藏在垄断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之中的悲观和谨慎并没有立刻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里,垄断资本学派超越了汉森,批评了后者将停滞视为永久性状态的观点,提出黄金年代繁荣的根源在于通过战争撬动了钢铁、汽车、能源、造船以及重化工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工业的投资繁荣。但是,投资繁荣所创造的不断扩张的产能并不能摆脱产能过剩,并且后者恰恰是投资过程内在矛盾的产物。基于此,垄断资本学派认为,“强烈的投资冲动在孕育投资丰裕的同时也抑制了未来的投资,这既是战后长期繁荣的秘密也是七十年代停滞重现的根源”。概而言之,巴兰和斯威齐在理解垄断资本主义运行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与凯恩斯—汉森/卡莱茨基—斯坦德尔有机结合了起来,提出了以停滞为内核的垄断资本理论。
(二)金融化
在《垄断资本》一书出版25年后,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的分析与现实相一致,不过他也为该书没有对“最近25年里,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急剧扩张且日趋复杂化的金融部门及其对‘实体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做出解释而深感自责[6]。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学派已经注意到金融部门日趋膨胀,并据此提出金融上层建筑的概念,强调以金融与生产二分法取代实体货币二分法,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化”为内核的金融资本理论,并同以停滞为内核的垄断资本理论结合,形成了垄断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恰恰得益于凯恩斯关于投资对未来资本积累不利影响的分析,呈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历史性相遇。
凯恩斯对于投资和未来资本积累关系的考察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矛盾的本质。1929年,凯恩斯在对股灾的回应中首次提出此问题,并在对大萧条的总结中指出,“我们的资本财富是由许多不同的资产所构成的,如房屋、存货商品、制造或运输中的产品等等。然而,这些资产的名义主人,为了拥有这些资产需要不断地借入货币。在相应程度上,财富的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不是体现在实物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这种‘融资’相当程度通过银行系统得以实现。银行作为存贷双方的担保人,一方是借出资金的贷款者,一方是借入资金购买实物资产的借款者。在实际资产和财务所有者间的货币面纱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7]178
在凯恩斯看来,现代公司与现代金融密不可分,后者包括证券市场和信用贷款等,且越来越重要。凯恩斯认为,股票市场从根本上是投资人通过持有股票债券等更具流动性的纸式凭证获取财富,以降低生产性投资的风险。这就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两面性,并会表现在两种不同的价格结构上,即实际产出价格与金融资产价格,且彼此独立运行,明斯基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因此,如果公司的长期资产变为投资者的短期财务承诺,那么经济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抵押品被用于投机,金融资产价值日益膨胀且超过实际产出价值,从而在经济中产生越来越大的波动和不稳定。
对于凯恩斯而言,现代金融结构诱发了市场对生产性资产的周期性游离,并且存在由于投机泡沫不可避免的破灭从而使得整个系统趋于不稳定的可能。凯恩斯曾经指出,“如果投机者像企业的洪流中漂浮着的泡沫一样,他未必会造成祸害。但是,当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是严重的。当一国资本的积累变为赌博场中的副产品时,积累工作多半是干不好的”。因此,凯恩斯通过对投机与经济停滞关系的探讨,强调了投资对未来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
在此基础上,垄断资本学派提出对于资本积累过程而言,金融不是作为适可而止的助手,已经逐渐转变为雄心勃勃的推手,从而为考察资本积累的二重性奠定了基础。他们指出,由于生产领域的投资机会日趋枯竭,加之对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信念,使得资本为不断积累的剩余寻求有利可图的投机渠道,投机性金融一跃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引擎,由此滋生了一种长期的金融外爆。不过,在他们看来,金融外爆、军事支出以及销售努力等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有内在的限制,最终无法抵消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停滞趋势。据此,垄断资本学派提出了垄断金融资本理论,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停滞与金融化形成了一种“两难”性质的共生关系:经济发展无法离开金融化,但是经济发展最终无法忍受金融化。
三、对凯恩斯革命的反思:卡莱茨基与垄断资本学派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视为“经济周期药方”的兜售者,浇灭了凯恩斯革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迸发的革命焰火,凯恩斯革命所引发的思考并没有结束,其中就涉及对凯恩斯与卡莱茨基之间关系的探讨。比如,莫里斯·多布、青年斯威齐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常将卡莱茨基视为凯恩斯左派[8]。卡莱茨基是凯恩斯左派吗?青年斯威齐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笔者试图从垄断资本学派凯恩斯思想渊源的角度就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呈现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历史性相遇的重要意义。
(一)卡莱茨基是凯恩斯左派吗
对卡莱茨基与凯恩斯之间关系的说明,离不开卡莱茨基晚年对凯恩斯革命所做的反思,这场反思进一步再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相遇,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卡莱茨基的忠实追随者塔德马什·科瓦里克[9]。20世纪60年代初,科瓦里克受邀为卡莱茨基65岁生日写传记并对其进行专访。这将卡莱茨基带回到20世纪初希法亭、卢森堡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激烈辩论。
三十年后,当卡莱茨基再次回顾这场辩论时,他挣脱了旁观者的身份,正确地认识到卢森堡和杜冈都将总需求视为资本主义的关键,两者错在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具体现实中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比如卢森堡认为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市场解决上述问题;而杜冈认为可以通过转向资本更为密集型的生产加以解决。1968年,科瓦里克与卡莱茨基共同发表了《对“重大”改革的观察》,试图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能否在不诉诸法西斯主义或战争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框架下,理解凯恩斯革命在经济政策上的意义。概而言之,卡莱茨基强调资本权力本能地对完全就业加以抵制,认为1937—1938年的衰退反映了政府在干预和退却之间的徘徊。
斯威齐在80年代对卡莱茨基和凯恩斯有过这样一番比较,他认为凯恩斯的论述集中在从宏观层面考察垄断与停滞之间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也已开始思考寡头和垄断竞争,不过相比于凯恩斯,它们的垄断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考察单个企业和厂商具体行为方式的变化,而“卡莱茨基是第一个将宏观与微观协调起来的经济学家”,并且斯坦德尔在卡莱茨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了这一思想[10]。科瓦里克与卡莱茨基在60年代对凯恩斯革命的反思实质上是对凯恩斯革命的超越,将问题的关键置于总需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间的关系上,回到了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积累这一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相遇的具体呈现。此外,卡莱茨基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表明,他早于凯恩斯探究总需求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并且将宏观与微观进行了结合,用“凯恩斯左派”形容卡莱茨基并不恰当。
(二)从消费不足到过度积累
1963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波兰出版,这为科瓦里克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辩论奠定了基础。1967年,科瓦里克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完稿,该书以俄国民粹派对俄国为何不会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为分析起点,强调了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作用,将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根源追溯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从而为创立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9]。通过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梳理,科瓦里克坚持了卡莱茨基在《经济波动理论》中对卢森堡的看法。卡莱茨基认为,“卢森堡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无法被全盘接受,但是她在凯恩斯《通论》出版之前就已明确提出需要通过投资或出口平衡储蓄过剩”[11]255。不过,有意思的是,1938年兰格曾指出,“少数消费不足主义理论家曾经认为储蓄阻碍了投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罗莎·卢森堡”[12]。在《资本主义发展论》,斯威齐也将卢森堡封为“消费不足主义女王”,并且继承了卢森堡对杜冈的反对意见,认为投资并不必然带来增长[13]191。
科瓦里克认为,这些学者之所以将卢森堡视为消费不足主义者,关键在于他们将她的分析局限于简单再生产,因此不存在资本存量,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会出现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不足的危机。斯威齐就曾表示在积累或者增长的情形下,工人的额外消费有助于实现剩余价值[13]201。科瓦里克认为,卢森堡力图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因此将她的分析局限于简单再生产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消费不足主义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熊彼特就曾将有效需求或不开支理论作为消费不足主义的一种形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任何类型的需求限制都纳入消费不足主义[14]740。然而,这样的解释会混淆消费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毕竟生产消费与投资密切相关。不过,斯威齐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英文版的书评表明在50年代之前他尚未改变他的观点。*斯威齐表示“卢森堡的书以卓越的成就引人注目……尽管由于存在大量的分析性错误最终使得中心论点归于无效。卢森堡考察了简单再生产(这时积累已被排除了)条件下的积累困难,然后搬来了非资本主义环境作为救兵以摆脱自我导致的混乱”。参阅Paul M.Sweezy, The Present of History: Essays and Review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p.291-294.
20世纪40年代早期,斯威齐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论》,试图对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现状展开分析,有意思的是,尽管卡莱茨基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然而该书仅提到了凯恩斯,对卡莱茨基却未曾提及。1946年,斯威齐和巴兰同卡莱茨基在纽约相遇,定期进行讨论,直到1955年卡莱茨基返回波兰。这段经历完全转变了斯威齐对卡莱茨基的看法,也是斯威齐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里,斯威齐受到了来自卡莱茨基和科瓦里克的挑战,转变了他对于卢森堡消费不足主义危机的看法,并将他对危机的分析概括为“过度积累理论”。这一概念显然是受卡莱茨基以及斯坦德尔的影响,*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与停滞》一书中,斯坦德尔明确提出将经济中的投资不足作为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困难,而非消费不足。在该书《卡尔·马克思与资本积累》一章,斯坦德尔引证马克思清楚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所带来的低消费是低投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回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工资是由积累量所决定的观点。参阅Josef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2,pp.243-246.并在他回应埃佛塞·多马对他初始论点的批判中首次提出[15]。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巴兰和斯威齐放弃了工人的消费影响剩余价值实现的观点,也不再提及卢森堡和消费不足主义,并且在该书导言的脚注中,指出“本书是我们以前的著作(即《资本主义发展论》)的直接继续。它也应当被理解为反映了我们对自己以前的著作的不满意”。对于巴兰和斯威齐而言,剩余实现仍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但是这一问题以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形式呈现。上述转变有助于垄断资本学派通过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把凯恩斯革命与20世纪初期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深化了该学派对于危机问题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剥离了该学派所具有的消费不足主义色彩,将分析的中心立足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核心矛盾上,更为积极地挖掘凯恩斯革命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呈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
四、垄断资本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
垄断资本学派以对20世纪上半期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为起点,大萧条以及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垄断资本学派理论分析的基本图景。该学派大量吸收了凯恩斯关于经济停滞和投资及其对未来资本积累不利影响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以停滞金融化为内核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呈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
1966年,《垄断资本》出版后不久,曾被美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视为极有潜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后来却沦为犹太复国主义极右翼主义者的大卫·霍洛维茨盛赞该书,认为《垄断资本》的优点在于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用从凯恩斯等20世纪伟大思想家那里继承的概念范畴取而代之[16]。这实质是抹杀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历史性相遇,试图以凯恩斯取代马克思。霍洛维茨的上述评价令斯威齐非常尴尬。斯威齐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剩余这样的概念,因此对没有将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坚持到底十分后悔。霍洛维茨对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的误解将我们指向了如下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如何理解垄断资本学派的凯恩斯渊源;第二,如何看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在批判性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基本运行规律做出了科学分析,为改造世界提供了可能。垄断资本学派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经济学家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这些经济学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上,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批判性学习的材料。霍洛维茨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垄断资本学派并非从凯恩斯等大思想家那里承袭概念。相反,他们在秉持马克思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对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现实运行的分析,批判性吸收了凯恩斯等人的相关概念,呈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7]这里,马克思批判的是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末期,继续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辩护的经济学家。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会忽视经济学家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提出的重要理论洞见。2012年,《每月评论》刊载了《一些理论启示》,该文是巴兰1962年写就的草稿,巴兰在该文曾指出马克思在1872年的评论“可能过于草率并且打击面过大”[18]。
因此,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个时期,以对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具体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时期发生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即传统意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时期发生在19世纪末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际,不妨称为“垄断资本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下降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取代传统意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其科学性日益下降,沦为辩护学。与之类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登场,而这对应了晚期资本主义,或者按照垄断资本学派的命名,即“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时期”。
1963年,斯威齐提出“恐怕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马克思称之为‘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的状态”,并且认为凯恩斯可能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尚存一点科学性的伟大代表。巴兰也预见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登场,他在《一些理论启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垄断资本主义所根深蒂固的不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欲望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拜物教,这甚至超过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思想”[18]。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获得了统治地位,但却愈益无法解释现实社会问题,同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相似,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趋于停滞,资产阶级经济学危机再次上演。正如《每月评论》的编辑所言,“无论是保罗·克鲁格曼还是迈克尔·斯宾塞以及其他的著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能像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那样,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刻认真的反思。事实上诸如凯恩斯这样的革命今天已经不再可能”[19]。
概而言之,马克思与凯恩斯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历史性相遇,意味着我们应该批判性吸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学者在对垄断竞争理论的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批判性吸收了“资产阶级学院派经济学家对垄断问题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学派要发展和丰富垄断资本理论,不充分利用学院派的研究成果是难以想象的”[20]7。因此,不应将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全对立,这有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宗派化”,无益于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探讨。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并非仅存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有其阶段性,这是建构经济学理论的源头活水,否认这一点就有可能导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虚无主义倾向,无益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1] Paul M.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ScienceandSociety, Vol.10,No.4, Fall, 1946,pp.398-405.
[2] Michal Kalecki, “The Marxian Equa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Modern Economics”,SocialScienceInformation, December 1968 , pp.73-79.
[3] Joseph A.Schumpeter,BusinessCycles:ATheoretical,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nalysisoftheCapitalistProcess, Volume 2,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 pp.1032-1050.
[4] Josef Steindl,MaturityandStagnationinAmericanCapital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2.
[5] Alvin H. Hansen, “Growth or Stagna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 Vol.36, No.4, Nov.1954, pp.409-414.
[6] Paul M.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fter Twenty-five Years”,MonthlyReview, Vol.43,Issue 7, December 1991.
[7]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文集》(下卷),李春荣、崔人元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8] John King,AHistoryofPost-KeynesianEconomicsSince1936,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2, pp.49-53.
[9] Jan Toporowski, “Tadeusz Kowalik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MonthlyReview, Volume 64, Issue 8, January 2013.
[10] Paul M.Sweezy, “The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MonthlyReview, October 1980.
[11] Jerzy Osiatynski,CollectedWorksofMichalKalecki,Vol.1:Capitlaism,BusinessCyclesandFullEmploy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p.255.
[12] Oskar Lange,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 Volume 5, No.17, February 1938, pp.12-32.
[13]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 Joseph Schump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740.
[15] Dana Cloud, “The Cases of Margo RamlalNankoe, William,Nagesh Rao, and Lorettta”,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9/cloud290409.html; David Horowitz,“Susie Day, Identity, Class, and Bite Me”, 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6/day300506.html.
[16] David Horowitz, “Analyzing The Surplus”,MonthlyReview, Vol.18, No.8, January 1967, pp.49-59.
[1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8] Paul A.Baran,Paul M.Sweezy,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MonthlyReview, Volume 64, Issue 03, July-August 2012.
[19] John Bellamy Foster,etc., “Notes from the Editors”,MonthlyReview, Volume 64, Issue 3, July-August, 2012.
[20] 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垄断资本理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