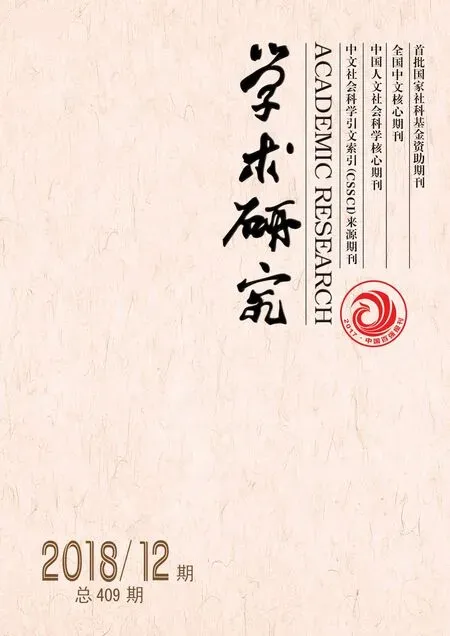回归翻译本质:解读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汪东萍
鸠摩罗什是东晋佛学高僧,于公元401年来到长安,在后秦主姚兴的大力支持下,主持长安译场长达十多年,成绩斐然,翻译了《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华首》《持世》《佛藏》《菩萨藏》等佛典33部,一共三百余卷,①[梁]释僧祐:《鸠摩罗什传》,《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34页。是佛典汉译史上与玄奘齐名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有感于前人译本存在“滞文格义”“义多乖谬”之处,与原文不相对应的地方很多,于是摈弃用儒家、道家术语格义佛学,提倡回归翻译本质,主张用解释法直接进行翻译,率先把印度佛学按照本来面目介绍到我国,其译文皆能“存其本旨”“义皆圆通”,开创了佛典汉译的新纪元。鸠摩罗什还主张译文文丽、简约,是佛典汉译的文派代表人物,其翻译的《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很多译本非常流行,《法华经》译本译出了原汁原味,被人们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正如僧肇所言,鸠摩罗什的翻译使得“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传于天北”。②[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初编本。汤用彤也赞其译经为“法筵之盛,今古罕匹”。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2页。目前学界对鸠摩罗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佛学、史学和文化领域;关于鸠摩罗什的译本也有一些研究,主要从译本的语音、词汇、主题、流行原因和译场合作等方面进行论述。然而,鸠摩罗什作为一位取得如此成就的大翻译家,其翻译思想却很少有人研究。史料上记载鸠摩罗什翻译思想的文献不多,主要包括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与僧叡改译《正法华经·受决品》”“临终前与众僧告别辞”、《思益经序》《法华宗要序》《法华经后序》等,下面依次从这六条文献解读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一、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不可译论翻译思想
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记载了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内容如下:“初,沙门僧叡,才识高朗,常随什传写。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见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①[梁]释僧祐:《鸠摩罗什传》,《出三藏记集》,第534页。僧叡的文才、学识俱佳,在鸠摩罗什主持的译场中担任笔受。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这里“西方”指的是天竺,商讨天竺语言梵文与汉语的异同。罗什认为梵文非常重视文采,参见国王有歌功颂德的唱词,拜见佛祖也以反复咏叹的唱词表示尊敬。佛经中的偈颂是梵文的一种语言形式,但把梵文翻译为汉语,偈颂唱词无法译成汉语来唱,语言失去了韵味,即使译文能够传达原文大意,却始终隔着文体差异,犹如嚼饭与人,不仅失去了味道,而且令人作呕。这段话说明罗什已经意识到译文不可能完美再现原文,表明了其不可译论的翻译思想。从此,“嚼饭与人”成为翻译史上不可译论的著名比喻,罗什也因此成为不可译论的代表人物。但事实上,梵文的偈颂唱词译成汉语来唱并非完全不可能,三国时支谦精通音律,曾用汉语创作梵呗,后来曹植也曾模仿梵文用汉语制呗。这就仿佛人们常说诗歌不可译,但历史上总有一些译得非常出色的诗歌诞生。《宋高僧传》认为翻译的本质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②[宋]赞宁:《唐京师满月传》,《宋高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7页。“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③[宋]赞宁:《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宋高僧传》,第3页。Samuel Butler认为:“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④钱锺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4页。这形象地说明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由于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独特的个性,从绝对再现原文的角度来说,一种语言无法100%再现另一种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翻译是不可能的,鸠摩罗什的不可译论翻译思想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个民族哪种语言,由于人类思想存在共性,反映思想的语言也就有了共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又是可能的,所谓质量上乘的翻译就是众多译本中最接近原文内容和形式的那一个。
另外,这条文献鸠摩罗什道出了“天竺国俗,甚重文藻”的事实,说明梵文非常重视文采。这样看来,道安所言“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⑤[晋]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出三藏记集》,第290页。和赵政所言“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⑥[晋]释道安:《鞞婆沙经序》,《出三藏记集》,第382页。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事实上佛典原文也非常重视文采,并非只有质朴一种语言风格。鸠摩罗什认为“改梵为秦”不应“失其藻蔚”,主张译文应像原文一样重视文采,翻译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而且要再现原文的文采和韵味,这是鸠摩罗什译文文丽的内在原因。
二、鸠摩罗什与僧叡改译《正法华经·受决品》:文派翻译思想
《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与僧叡改译竺法护《正法华经· 受决品》的故事经常被后人引用,其曰:“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⑦[梁]释慧皎:《晋长安释僧叡》,《高僧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1页。这里鸠摩罗什批评竺法护翻译的“天见人,人见天”虽然译出了原文意思,但“在言过质”,认为僧叡翻译的“人天交接,两得相见”比较妥当。这段话成为鸠摩罗什反对语言质朴,主张译文文丽的一个典型例子,说明鸠摩罗什反对质派翻译,主张对译文进行文饰,被后人公认为是佛典汉译的文派代表。老实说,如果单从字面来看,“人天交接,两得相见”未必比“天见人,人见天”文丽多少,但是结合当时社会流行四字结构的历史背景来看,鸠摩罗什的翻译考虑到了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因素,这是他重视读者的一种体现。翻译总是事关两头,一头是原文,一头是译文;一头是作者,一头是读者。好的翻译必须妥善处理好两头的关系,对待原文和作者,罗什是忠实地传达原文旨意;对待译文和读者,罗什则更加妥帖周到,时时处处为读者考虑。因为当时社会崇尚文丽简约,所以罗什翻译时就注重语言表达简约而直达,主旨委婉而彰显,佛祖的微远大意在译文中一目了然,这是罗什译本非常流行、深受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三、鸠摩罗什“临终与众僧告别辞”:翻译“诚实誓”和简约的翻译思想
鸠摩罗什“临终与众僧告别辞”在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释慧皎的《高僧传》中均有记载,但内容上有些出入,形成了两个版本。《出三藏记集》载“临终与众僧告别辞”曰:“什临终,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异世,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译,若所传无谬,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晋义熙中卒于长安,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化,唯舌不变。后有外国沙门来曰:‘罗什所译,十不出一。”’”①[梁]释僧祐:《鸠摩罗什传》,《出三藏记集》,第535页。《高僧传》载“临终与众僧告别辞”曰:“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后外国沙门来云:‘罗什所译,十不出一。’”②[梁]释慧皎:《晋长安鸠摩罗什》,《高僧传》,第77页。上述两个版本,从写作年代看,应该是释慧皎《高僧传》转抄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时补充了一些内容,主题都是鸠摩罗什临终时所发的翻译“诚实誓”。为什么罗什敢于发毒誓以证明自己的翻译无谬,并且有让众人检验的勇气呢?探其成因,主要有二:一是罗什精通佛法,对自己的译本有信心,相信自己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旨意;二是罗什对自己的翻译品行有信心,相信自己一生对佛典汉译事业诚实守信、问心无愧。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罗什翻译的佛典译本在我国流传最为广泛,甚至超过了玄奘译本的流通量。
《出三藏记集》所记鸠摩罗什“临终与众僧告别辞”原为严肃之事,但其后却紧跟一句后有外国沙门来曰“罗什所译,十不出一”,是说罗什译本字数不到原文的十分之一,这句话颇令人玩味,似乎有讽刺罗什译本删繁就简、有失忠实的意味。《高僧传》里增加的内容,罗什认为自己翻译的佛典中,只有一部《十诵》没有进行删减,其余三百多卷佛典全部做了删减,说明简约是罗什译本的一大特点。还有一处罗什翻译《百论》经的典故:“论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后十品其人以为无益此土,故阙而不传。冀明识君子,详而览焉。”③[晋]释僧肇:《百论序》,《出三藏记集》,第403页。另有一例,《大智释论》原文有十万偈,320万字,罗什翻译过来只有百卷,20万字。其高徒僧叡在《大智释论序》中解释了原因:“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译一往,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④[晋]释僧叡:《大智释论序》,《出三藏记集》,第387页。陈寅恪曾把罗什翻译的《大庄严论》同梵文残本进行对照,发现罗什经常删削原文繁琐重复之处,而且不拘于原文体制,往往变易原文,这些是罗什译本的不足之处。这样看来,文丽除外,简约是鸠摩罗什译本的另一大显著特点。
四、《思益经序》:摒弃格义是鸠摩罗什译本优于支谦译本的关键
这篇序言对比了鸠摩罗什和支谦翻译同一部佛经的两个译本,虽说两人都是文派译者,译文文丽、简约是其共同特点。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一是汉语表达上,支谦的汉语造诣比罗什高,其译名“持心”比罗什译本的“思益”更为贴切。序言首先把两种译本的译名“思益”与“持心”进行了对比,认为鸠摩罗什尚未完全通晓汉语,误解了事物的名称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根据佛典原意,对照汉语名义,应当用“持意”,而不是“思益”。罗什不明白“持”意,就用了“益”字,“益”表示“超绝、殊异、妙拔”之意,而“思”表示“进业高胜、自强不息”之意。支谦旧译本的佛经名称“持心”译得就很好,比较接近原文含义。究其原因,支谦是月氏国来华的第三代移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小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汉语造诣高深。而鸠摩罗什于401年来到长安,接触汉语时间不长,汉语理解和表达上仍有误区,这是造成其译名不准确的主要原因。二是原文理解上,支谦译本“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说支谦译本虽然文字漂亮,但是佛典旨意不明,让人越看越迷惑。这是因为支谦对佛典原文理解不够透彻,加上用儒家、道家术语格义佛学,导致“仍迷其旨”“幽旨莫启”,致使意思走样,译文变味,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文旨意。对原文理解不透彻是翻译的一大硬伤,这种本质上的缺陷即使穿上华丽的语言外衣,也是无法掩盖的。而鸠摩罗什为天竺世家,自幼学习佛典,精通佛学,加上梵文又是其母语,对佛典原文理解透彻,这是其译本能够正确传达原文旨意的原因。三是翻译方法上,支谦译本采用儒家、道家术语“格义”佛学,导致佛学不纯。“格义”翻译方法首创于竺法雅,《高僧传·晋高邑竺法雅》记载:“竺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仕子,咸附谘禀。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②[梁]释慧皎:《晋高邑竺法雅》,《高僧传》,第203页。是说竺法雅年少时就擅长佛学以外的学问,长大后通解佛法。其弟子对我国原有典籍下了功夫,但不擅长佛教义理,所以竺法雅就与康法朗等人,把佛经中的法数概念,比配于中国原有典籍中的相关概念,以达成理解,这一方法被称之为“格义”。后来毗浮、昙相等译者也用格义方法训导门徒。汤用彤对此解释说:“格义者何?格,量也。盖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以使人易于了解佛书之方法也。事数者何?据《世说·文学篇》曰:‘事数,谓若五阴、十二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法雅之所谓事数即言佛义之条目名相。其以事数拟比,盖因佛经之组织常用法数,而自汉以来,讲经多依事数也。《僧传》谓康法朗等以事数与外书拟配,因而生解,然后逐条著以为例,于讲授时用之训门徒,谓之格义。”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92页。简单地说,格义就是用原本中国典籍的概念解释外来佛学,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固有的概念理解外来佛学的一种方法。虽说给格义下定义竺法雅是第一人,但是格义方法的运用却始于早期的佛典汉译家安世高。安世高采用道家的“五行”“五蕴”格义佛学的“元气”,用“非常”“非身”等道家术语翻译佛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概念。事实上,初期译者大多在佛典汉译中采用了格义方法,如:支谶曾用道家术语“道行”格义佛教的“波罗蜜多”,还用道家的“本无”翻译佛学的“如性”,造成后人常常从道家角度理解支谶学说。支谦把支谶翻译的《道行般若》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般若”梵文原意为智慧,支谦翻译为“明”,用的就是道家术语。这本经提到《瑞本应起经》的一个注,支谦把释迦牟尼译为“能儒”,这是把佛祖比附为儒家大师,其格义方法简直登峰造极。但佛学思想毕竟不同于道家、儒家学说,格义方法造成佛典汉译有悖于佛典原义,偏离纯粹佛学,导致佛学不纯和佛教中国化的结果。《高僧传·晋飞龙山释僧光》记载了道安与释僧光探讨佛典汉译的一段对话:“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①[梁]道护:《晋飞龙山释僧光》,《高僧传》,第261页。这段话反映了僧光思想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容质疑。道安则意识到格义方法的缺陷,“先旧格义,于理多违”,认为弘扬教理,首先要确保翻译过来的教义准确,是否先达所用倒是不必在意。许理和认为:“道安基于自身血统和学养,意识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异,致力于探索佛法最原初的含义。”②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反对格义始于道安,但从翻译实践上彻底摒弃格义的是鸠摩罗什,他回归翻译本质,主张对梵文原本直接进行翻译,把翻译过来的正文写在竹帛之上,佛典旨意需要解释之处则在其下用注释标明。摒弃格义是罗什译本优于支谦译本的关键,从此佛学不再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恢复了本来面貌。摒弃格义也使佛典汉译回归翻译本质,走向翻译正轨,所以后人认为鸠摩罗什开创了佛典汉译的新纪元。
五、《法华宗要序》:精益求精的翻译思想
释慧观《法华宗要序》最后一段话记载了鸠摩罗什翻译《法华宗》的情况:“有外国法师鸠摩罗什,超爽俊迈,奇悟天拔,量与海深,辩流玉散。继释踪以嗣轨,秉神火以霜烛,纽颓纲于将绝,拯漂溺于已沦,耀此慧灯,来光斯境。秦弘始八年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什自手执胡经,口译秦语,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过半。虽复霄雲披翳,阳景俱晖,未足喻也。什犹谓语现而理沉,事近而旨远。又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虽冥扉未开,固已得其门矣。夫上善等润,灵液尚均,是以仰感嘱累,俯慨未闻,故採述旨要,流布未闻。庶法轮遐轸,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畅一乘。故序之云尔。”③[南宋朝]释慧观:《法华宗要序》,《出三藏记集》,第306页。这段话首先盛赞鸠摩罗什对佛学的贡献,其次介绍翻译《法华宗》的时间和译场情况,鸠摩罗什手拿佛典原本,口译为汉语,译文遵照汉语习惯表达,并与原意相符,翻译的《法华宗》译本已经达到用流利的汉语表达原文旨趣的水准。不过罗什仍不满意,认为虽然语言表面意思清楚了,但佛理仍未显现,取譬之事貌似很近,距离佛典原旨依然很远,于是继续翻译,努力译出字里行间隐藏的涵义。然后对译文进行润饰,加工成文,最后说明撰写《法华宗要序》的原因。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鸠摩罗什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翻译思想,其译本才能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法华经后序》:边译边讲、中外人共译的译场合作模式
僧叡《法华经后序》云:“法华经者,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也。以华为名者,照其本也。称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兴既玄,其旨其婉。自非达识传之,罕有得其门者。夫百卉药木之英,物实之本也。八万四千法藏者,道果之原也。故以喻焉。诸华之中,莲华最胜。华尚未敷名屈摩罗,敷而将落名迦摩罗,处中盛时名分陀利。未敷喻二道,将落譬泥洹,荣曜独足以喻斯典。至于般若诸经,深无不极,故道者以之而归;大无不该,故乘者以之而济。然其大略,皆以适化为本。应务之门,不得不以善权为用。权之为化,悟物虽弘,于实体不足。皆属法华,固其宜矣。寻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该甚远。岂徒说实归本,毕定殊途而已耶。乃实大明觉理,囊括古今。云佛寿无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无数,万形不足以异其体也。然则寿量定其非数,分身明其无实,普贤显其无成,多宝昭其不灭。夫迈玄古以期今,则万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则千途无异辙。夫如是者,则生生未足以言其在,永寂亦未可言其灭矣。寻幽宗以绝往,则丧功于本无;控心辔于三昧,则忘期于二地。经流兹土,虽复垂及百年,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幽踪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拟韵玄门,宅心世表,注诚斯典,信诣弥至。每思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既遇鸠摩罗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是岁弘始八年,岁次鹑火。”①[晋]释僧叡:《法华经后序》,《出三藏记集》,第306-307页。
僧叡这篇序言写于406年,一共三段,第一、二段分别阐述法华经的内涵、分类和旨意,第三段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介绍《法华经》的宗旨:用禅定之法控制心思,达到脱凡出俗忘情于净地的境界。其次叙说《法华经》译本流传到我国差不多有百年历史,但由于译者不理解虚空的义理,通向佛教之路并未打通;讲经者也常常背离《法华经》准则,达旨之人甚为罕见。司隶校尉和安城侯姚嵩有志于佛教,寄心于世俗之外,对《法华经》倾注了全部诚意,信仰之心非常坚定,但是每每读到译本,总感到译文有误,未达原文旨意。所幸《法华经》由鸠摩罗什重新翻译,译本终于能够义皆圆通、宏达欣畅,让读者有“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瞰”之感。最后介绍鸠摩罗什译场的情况,《法华经》由罗什担任主译,边译边讲,僧叡担任笔受,负责把罗什口译的内容传写下来,润饰加工成文。
现在回顾一下历史,佛典汉译初期均为私人合作,道安率先开辟了官方译场合作。道安去世十六年后,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主持官方译场长达十多年。其译场由后秦主姚兴亲自挂帅,规格高,规模大,接收了很多道安译场的杰出助手,汇集僧众数千人。关于译场方面的记录比较零碎,散落在序言当中。本文第四条文献记载《思益经》由鸠摩罗什主译,先把梵文译为汉语,由僧叡和道恒担任笔受,把罗什口译的内容传写下来,罗什一边口译一边宣讲,最后由笔受加工成文,翻译时把正文写在竹帛之上,解释的内容放在句子下面。第五条文献记载《法华宗》也由罗什主译,边译边讲,由笔受记录下来,最后润饰成文。这样看来,罗什译场创新了一种翻译模式,即边译边讲、中外人共译的译场合作模式。其翻译分为三步走:第一步鸠摩罗什发挥自己精通梵文、佛学造诣高深的优势,先把梵文口译为汉语,并且边译边讲,这是我国翻译史上首次把翻译与宣讲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第二步由汉语造诣精深的中华才俊担任笔受,发挥汉语优势,把罗什口译的内容传写下来;第三步对笔受传写的内容进行检查和润饰,最后加工成文。边译边讲把佛典汉译和佛学宣讲结合起来,方便大家研讨,共同参悟佛典,使佛典汉译译文经得起推敲。中外人共译一方面发挥罗什原文理解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发挥中华才俊汉语表达上的优势,有效弥补了罗什汉语表达上的不足,强强联合,大大提高了翻译质量。
综上所述,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不可译论、文派翻译、翻译诚实誓、译文简约、摒弃格义、精益求精和边译边讲、中外人共译的译场合作模式等几个方面。不可译论反映了罗什追求尽善尽美的翻译思想;删削原文、润饰译文,主张译文文丽、简约,说明鸠摩罗什沿袭了文派语言文丽、叙事简约的特点;而摒弃格义,回归翻译本质,直接对原文进行翻译,是罗什译本超越支谦等前期译者的关键,为回归纯粹佛学做出了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鸠摩罗什的翻译诚实誓和精益求精的翻译思想,罗什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位发诚实誓言的译者,也是首位重视翻译诚信和翻译态度的翻译家,特别强调译者个人品质在翻译事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最后,鸠摩罗什创新了边译边讲、中外人共译的官方译场合作模式,使译本不仅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旨意,确保内容准确,而且译文语言精美,妙趣盎然,堪称佛典汉译的上乘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