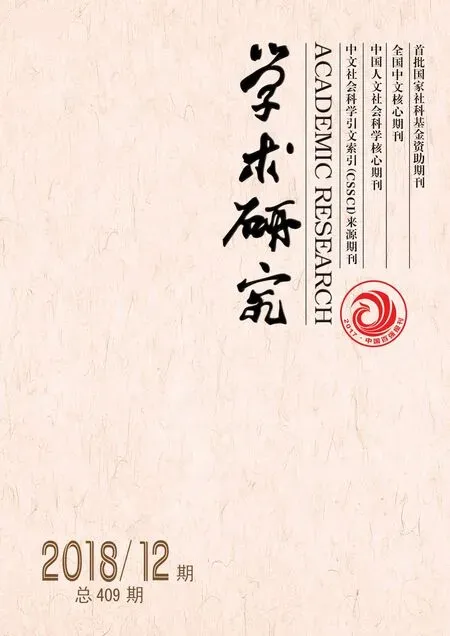兴象在中国诗学中的发展流变*
王明辉
“兴”和“象”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兴”是诗学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诗学对诗的一种根本性把握。“象”是易学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一种根本性把握,进而也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诗学中的重要范畴。两者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核心范畴在意义上的简单叠加,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后在理论层面的反映,可看作是当时学者把握和提炼中国诗歌艺术特征的理论自觉的产物。本文试从涵义变迁角度考察兴象范畴在中国诗学中的发展过程。
一、兴象之可能
兴象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出现在中国诗学领域,要从殷璠《河岳英灵集》算起,但兴象包含的意旨却远绍先秦时代。先秦时期的兴有起、始的意义,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进而成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后来又被理解为艺术审美特征和艺术生成机制。象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符号,既包含形式又包含内容。从《周易》中的卦象到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意象、兴象,象的意义极其丰富,其核心是象征。从兴与象的关系来看,《诗经》中的各种兴辞,无论其功能如何,基本都具有明显的观物取象特征。可以说,中国诗学中的兴,从一开始就与象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宋代的《集韵》中直接以象训兴:“兴,象也。”①《宋刻集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175页。这种解释代表了宋人对兴与象的新理解。虽然宋人没有对此深入阐释,但我们可以从后人的类似观点中略窥端倪。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类篇·易教下》指出:“《易》之象,《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集韵》是以象训兴,而章氏则是以兴训象,角度不同,但大意基本一致。章学诚将兴象范围界定在《周易》和《诗经》之内,并指出象与兴的共同点是变化莫测。也就是说,象与兴在各自领域中的运用非常灵活,不拘一端。这其中隐含这样一种观点,象与兴都不是直接和直白的表达方式。
闻一多将兴与象的特点提炼为“隐”,他认为:“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喻不用讲,是《诗》的‘比’)……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①闻一多:《神话与诗》,《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18页。这其实是《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和《文心雕龙》“比显而兴隐”两方面观点的结合。《周易·系辞》云:“是故易者,像也;象也者,像也”,“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②《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312页。易与象本质上的互通性在于象征性,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曲和隐。这里的曲和隐,有互文之意,但亦各有偏重。肆而隐的特点针对其事,曲而中的特点针对其言。为了追求事隐,故而言曲。由于事隐言曲,所以“辞文”“旨远”。这种含蓄委曲的特点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兴。《文心雕龙·比兴》云:“观乎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01页。这里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是对《周易·系辞》的原文引用,“婉而成章”又恰恰对应着曲和隐。借助这一思路,结合闻一多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兴与象在表现内容方面的特点是隐,对应着显,而在表现手法方面的特点是曲,对应着直。虽然兴象作为一个诗学术语的发生时间距离先秦比较远,但其内涵却受到先秦时期曲和隐特征的影响。从一开始,兴象这个术语就与直言其事的铺叙手法无关,而代表着更含蓄曲折也更复杂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审美追求。
从汉代到魏晋,人们对于兴的理解逐渐从《诗经》范围中脱离。汉代学者基本是在解释《诗经》的基础上谈对兴的理解,郑众视兴为物,郑玄视兴为事,都与象无关。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对于兴的认识和把握逐渐溢出了《诗经》范围,过渡到对多种诗体的批评,并开始出现从诗歌审美角度对兴的阐释。挚虞将兴与情感联系在一起,刘勰更进一步将兴解释为起情,钟嵘认为兴是悠远有味的艺术效果,代表了时人对兴的不同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并没有体现在当时的诗文创作中。当时的诗人更重视艺术表现上的形似和巧构,但其创作中的情与景大多各自独立,不能完美交融。从创作角度来看,当时诗人写景体物长于描摹物态,但短于融情于景。从诗论角度来看,兴与象作为诗论术语还没有被有机结合起来。
二、兴象之出现
唐初,孔颖达首次将兴与象在一个句式中联系起来,他在《周南·樛木》疏中指出:“以兴必取象,以兴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④《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页。孔颖达所谓的“兴必取象”,还停留在经学范畴内。不过,与汉代郑玄、郑众不同的是,孔颖达将兴的表现形式从二郑所言的物或事变成了象。从实在的物或者事,到虚实之际的具有创造性的象,这隐含了一种对兴的新理解。从诗学角度来看,兴必取象这一表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阐释空间。这种提法将以往并无交涉的两个重要范畴兴与象联系起来,两者的碰撞和融合,可能激发出更深刻的诗学理论。
到了中唐,借助于盛唐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了兴象这一范畴。他批评当时诗风“ (挈瓶庸受之流)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⑤《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页。品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⑥《唐人选唐诗(十种)》,第69页。品评孟浩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诗句为“无论兴象,兼复故实”。⑦《唐人选唐诗(十种)》,第91页。尽管殷璠对兴象的内涵没有具体阐释,对兴象的使用也基本停留在有无的层面上,但这仍然是一种创造性的使用。从此,兴象作为一个批评范畴正式进入了中国诗学领域。虽然这是兴象理论的萌生草创阶段,但其中颇有值得注意者。
第一,兴象是针对诗歌中视觉审美的批评术语。殷璠笔下的兴象,重视对艺术形象的视觉呈现。这里兴象主要强调诗歌所表现的图景要包含浓厚的情兴,强调情与景、兴与象的完美结合。这种图景可以是单独的物象,也可以是物象或景物的组合,但尚未指向物象叠加后所产生的整体性审美效果。
第二,兴象与兴寄有关。殷璠认为有兴象、多兴象是好诗的标准之一。兴象的对立面是轻艳,这里的轻艳是指南朝流传下来的宫体诗风。殷璠所谓有兴象是强调要有所寄托地咏物写景,而不能沉湎于脂粉香泽、旖旎风流的艺术追求。他所选的陶翰诗或充满报国之志,或抒发高远之情,全无浅薄绮靡之态,所引孟浩然的名句更是孟氏高旷心境的彰显。从此角度来看,兴象中包含着兴寄。但殷璠的兴象又与陈子昂所说的兴寄有所不同,如果说陈子昂的兴寄更偏重刚健挺拔的风骨,殷璠的兴象则偏重于雅正高远的情兴。殷璠评论陶翰诗兴象与风骨并称,也就是说,兴象与风骨各有侧重,如果风骨偏重其情感的浓烈、气势的雄健,那么兴象则偏重其物象与情兴的高度融合。此时的兴象,大体可以理解为诗歌中具有雅正高远的情兴特征的物象。
第三,兴象与典故并不矛盾。殷璠认为,故实也可以成为兴象,凝炼的典故可以使兴象包含更丰富的内蕴,这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典故图像化的思路。孟浩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一句,表面上看,所言即所见,加上自身的兴致所寄,因而与众山同饮,和孤屿共吟。但实际上,其中“对酒”“孤屿”都有所本。曹操《短歌行》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句,谢灵运《登江中孤屿》有“孤屿媚中川”句,两者的诗意都在孟诗图像化的表达中与孟氏诗意互相生发。这种观点在明清时期得到一些诗论家的认同,如李时勉认为兴象建立在学问基础上,其《戴古愚诗集序》云:“至于兴象,则在乎其人学问之至、用力之久,自当得之,非可以言喻。”①李时勉:《古亷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42册。纪昀云:“诗未有不用功者,功深则兴象超妙,痕迹自融耳。”②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4页。何焯云:“谢玄晖《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云去’一联既有兴象,兼之故实。”③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92页。何焯的评语袭用殷璠原话,谢朓“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一联,表面上看是纯写景,但暗含舜南行死于苍梧之野的典故。诗句在云水殊途、天各一方的别离之情外,还包含了一种不知可否再见的怅惘,正是典故化作兴象的范例。
第四,兴象是对南朝诗歌追求形似、巧构的继承和超越。诗歌创作多是外部对象经由诗人主体心灵观照并加以表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人们有意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兴象范畴因此应运而生。唐诗在创作上力求超越南朝形似巧构之风、重建风雅传统,从理论上唐人也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提炼。殷璠身处中唐,但他总结的主要是盛唐的诗歌特点。唐人将南朝诗风的巧构形似与汉魏诗风中的风骨兴寄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种新的诗歌高格,这种追求突出地表现在盛唐诗歌所创造的饱含情兴的艺术形象上,也就是殷璠所谓的兴象。
第五,兴象也可看作是兴会之象,即通过兴这种特殊情感方式生成的象。在唐代,兴已经作为一种创作冲动被诗人们所认识,兴的涵义逐渐与传统的托喻寄讽分别开来。人们认识到要在一种特殊的创作冲动下去描摹和刻画物象,这种状态被纳入“兴”的范畴。旧题贾岛《二南密旨》云:“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④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旧题王昌龄《诗格》云:“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须屏绝事务,专任情兴。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⑤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70页。感物而动、江山满怀就是兴,此处的兴,已经具有诗歌发生层面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唐代诗学中的兴象范畴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兴象之沉淀
从盛唐到中唐,诗歌创作潮流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对意的凸显超越了对象的追求。从杜甫到中唐的韩愈、白居易乃至以后的大历诗人,其诗风都与盛唐风格有很大不同。诗论方面也有所体现,诸如皎然《诗式》“放意须险,定句须难”、①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刘禹锡“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②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8页。等相关讨论甚多。当兴象范畴尚未被当时的诗学充分地消化吸收时,兴象玲珑的艺术风格就已经被新的艺术追求所取代。从此,兴象范畴在唐代诗学中不复出现,但唐人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并未停歇,这主要体现在对象的研究上。
其实从魏晋时起,就有人开始讨论象外的问题了。王弼解《易》时对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他说:“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③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王弼谈的是对卦象的阐释,但已经触及到“象”的内外问题。此外,佛教思想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佛僧看来,“象非真象”,④僧肇:《不真空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44页。应该“穷心尽智,极象外之谈”。⑤僧肇:《般若无知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第151页。佛学关注的是超越形象,抵达真象。这种观念与王弼有异曲同工之处,都表达了对象外的追求,进而影响到当时的绘画理论。如谢赫指出“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⑥谢赫:《古画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8页。不过,这种观念对文学的影响直到唐代中期以后才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皎然《诗议》云:“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⑦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08页。其《诗式·取境》云:“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⑧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39页。自皎然开始,唐代诗论家已经将象与境联系在一起。对于象与境问题的关键性阐释要数刘禹锡,他提出:“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⑨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刘禹锡集》,第238页。这一观点代表了唐代诗论对“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正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关于象外的讨论联系起来。只不过当时的讨论主要在哲学、佛学和绘画领域,现在却进入了诗学领域。刘禹锡认识到,在诗歌的物象之外,还存在着更广阔的艺术世界,即所谓境,境是对象的超越。关于境、情境、意境的概念,在王昌龄《诗格》中就已经提出,刘禹锡“境生于象外”的命题,更将境与象直接连接起来,正可见出中国诗学中由象发展到境的逻辑理路。兴象正可看作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不过兴象的这层涵义要到元明以后才得以揭示。
到了晚唐的司空图,象的理论有了另外角度上的提升。司空图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⑩司空图:《与极浦书》,祖保泉、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这段话指出,诗家所描绘的景物具有图像感,可以被感觉到,但却不能直接通过感官来把握。尽管这种体会是感性的,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司空图已经认识到,欣赏者从诗歌中感受到的不是具体描写的物象,而是一种超越了具体物象的象,是一种超越了具体景物的景。以前诗论中谈到象,除了物象本身之外,往往重视象所隐含的意,或者说象外的意。而司空图谈的不是象外的意,而是象外的象,司空图将之称为“象外之象”,这就将诗歌理论中的象,进一步区分出了不同的审美层次,由实体进入虚体。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审美问题,代表了唐代诗论家对象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宋代诗学体现出不同于唐代诗学的特色。自司空图“象外之象”以降,宋代诗论家开始有意避免唐诗所表现出来的绚烂色泽,而追求更深远的意境。这不仅体现在审美风格的转变,还体现在对诗歌语言表现力更加深刻地追索。宋代诗人已经不仅仅追求对景物进行穷形尽相地表现,而是尽最大可能拓展语言本身的内涵和张力,进而构建超越形似的意境。这种思路与唐人饱含情兴的象大有不同。相比唐诗,宋诗距离物理世界更远,而进入语言符号世界则更深。如果说唐诗是作者思想感情与外物交融的完美体现,那么,宋诗则是作者思想感情与语言符号互动的不懈追求。宋诗的主要追求在于理念世界和语言世界,外部物象多是意念的投射对象,大多已经失去了比兴的意味。洪亮吉曰:“唐诗人去古未远,尚多比兴,……降及宋元,直陈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兴体微矣。”①洪亮吉:《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比兴体微,象则无从附丽。因而,缪钺认为:“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凿,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②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37页。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诗学中几乎不见兴象的踪迹,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宋人很少提及兴象,但他们的思考却对后人理解和阐释兴象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如梅尧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③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7页。张炎“所咏了然在目,且不滞留于物”。④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第261页。从创作角度上不滞于物,但却可以使欣赏者了然在目,这种审美理念正是后来黄溍、胡应麟等人阐发兴象的要义所在。
四、兴象之复兴
元代诗学路向基本上沿着宗唐复古的思路展开,力图恢复吟咏性情的风雅传统。在这种背景下,元末诗论开始重提兴象。杨维桢就多次用兴象来讨论诗学问题,但更值得关注的一条材料出自其弟子黄溍之手。杨维桢有《饮马窟》诗:“长城饮马窟,饮马马还惊。宁知呜咽水,犹作宝刀鸣。”黄溍评云:“无中生岀兴象之妙。”⑤杨维桢:《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这里对兴象的理解与以前大有不同。无中生岀兴象,是指诗中没有直接表现战斗场面,但却可以由其中的饮马情景,联想到边塞征战时战马飞驰、刀光剑影的图景和情境。在此,兴象具有明显的建构功能,已经属于造境了。黄溍对兴象的这种理解非常高明,虽然没有充分展开,但却启发了明清时期兴象宛然这一诗学命题的出现。
明代兴象的使用情况与以前大有不同,运用兴象论诗者比比皆是。从明初的高棅到中后期的胡应麟、何良俊等诗论家,均从不同角度使用和阐发兴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问题。
第一,兴象被提炼为唐诗的核心审美特征。高棅倡导唐诗学,在《唐诗品汇》中多次使用兴象范畴,并将兴象置于唐诗学的批评框架中,与声律、文词、理致等共同作为唐诗的核心审美标准。高棅云:“(唐诗众体)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⑥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页。“唐代君臣以五律相倡和,由是海内词场,翕然相习,故其声调格律易于同似,其得兴象高远者亦寡矣。”⑦高棅:《唐诗品汇》,第506页。高棅将兴象作为区别唐诗初、盛、中、晚分期的重要标准之一,并提出兴象高远的判断,开后来批评者深入剖分兴象特征的先河。此后,兴象标拔、兴象玲珑、兴象深微等判断纷纷出现。不过,高棅并没有对兴象进行更深入地阐发,主要还是在唐宋诗对比的基础上对唐诗重视色调风华特征的一种提炼和把握。
第二,兴与象形式上并列出现,但涵义上各自独立。何良俊云:“只如中唐人诗,如‘月到上方诸品静,身持半偈万缘空’之句,兴象俱佳,可称名作。”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7页。清人纪昀也有类似用例:“景少司马介兹官翰林时,斋宿清秘堂。积雨初晴,微月未上,独坐廊下。闻瀛洲亭中语曰:今日楼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馀山态活’句真神来之笔。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态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则兴象俱减矣。”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9页。这种理解实际上将兴象看作一个并列词语,分别指代情兴与物象两端,强调兴象两方面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只有兴象俱佳才能成为一流的诗作。不过,这种理解分割了兴与象的密切联系,反而缩减了兴象范畴的丰富涵义。类似用例并不多见。
第三,明确提出兴象是对咏物巧似的超越。何良俊云:“袁海叟尤长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诗,世尤传诵之。而空同以为《白燕诗》最下最传,盖以其咏物太工,乏兴象耳。”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233页。袁凯以《白燕》诗成名,该诗从不同角度对白燕加以描摹,极尽工巧之能事。但明人重视对唐诗格调的总结和传承,两相对比,袁凯的艺术风格显然算不上高格。李梦阳对袁诗评价极低,何良俊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袁凯过于重视咏物本身,忽略了情兴的寄托,因而缺乏兴象。从审美角度来看,袁凯重视描摹白燕的形貌物色乃至相关典故,但这些方面都倾向于审美对象的自身性质。而兴象则超越了单纯描摹形象物色的层次,力图表现更深层次的内视性图像,追求创作主体的情兴与审美对象浑融一体的审美效果。《白燕》诗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虽然创作技艺很高明,但缺乏情兴的寄托和生命力的灌注。兴象是超越巧似的更高级审美追求,其中包含着一种创作主体的观念性投射,强调创作主体当下所思所想、情感情绪与审美对象的碰撞、激荡和融合。从追求形似到追求兴象,意味着诗歌审美从纯视觉的观察发展到感性的体验,从极力刻画审美对象的客观特征发展到尽力表现对审美对象的直觉体验和整体性把握。
第四,以兴象宛然的诗学命题对兴象进行创造性阐释,提升了兴象的理论层次。胡应麟云:“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宛然,就是看起来像什么的样子,是宛然在目的省略语,代表一种整体性视觉审美效果,是文学审美体验中语言审美向图像审美转换的集中体现。颜之推《颜氏家训》云:“(萧悫)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③颜之推:《颜氏家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1页。这里的宛然在目正代表了一种对诗歌的图像化审美。不过,颜之推所言的萧散还主要基于诗中呈现的物象。而在胡应麟那里,兴象则被阐释为是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具有整体性美感的审美形象,它具有形式特征,但却并不直接体现在以语言符号指称的物象上。胡氏认为,王勃的两首诗中都没有着力描写景物,但却兴象宛然。这里的兴象显然不是指作品中的具体物象,而是指借助词语组合间的张力在欣赏者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图像,这一图像具有可视性,但又不能被欣赏者的眼睛直接看到,需要欣赏者通过直觉来体验和把握。
胡应麟的阐释与上文何良俊的观点正可以互相印证,在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方面,两人的关注点都从实体发展到虚体,从物象到兴象。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语言符号呈现的物象看作诗歌的第一层形式结构,那么兴象就属于第二层形式结构,同样具有视觉形式意义,但却是更高层面的整体性内视图像。这种阐释极大开掘了兴象涵义的理论深度,唐诗的高格正建立在这种双层审美形式结构的基础上。兴象宛然是兴象范畴最重要的理论阐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诗学命题。
五、兴象之开拓
清代诗学继承了前代关于兴象的理论积累并有所发展。
首先,兴象所指范围扩大。清代诗论家大体上沿袭了明人对兴象的理解和阐释,但在指涉时代和批评文体方面却有了全面的开拓。在清人手中,兴象几乎可以用来品评所有文体。清人首开以兴象品评宋诗、金诗的先例。方东树评陆游《醉中戏作》云:“状少年豪举,兴象勃然。”④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64页。潘德舆云:“或谓宋诗少兴象,类不长于绝句,亦不然。”⑤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59页。梁章钜云:“金诗只一元遗山为大宗,《遗山集》四十卷,诗凡十四卷,所作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南渡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流派生拗粗犷之失。”⑥梁章钜:《退庵随笔》学诗二,《清诗话续编》,第1981页。
以前兴象所涉及的文体主要是诗歌,基本上不用于品评其他文体。清人开始以兴象品评词、赋。先著、程洪云:“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泽字句间,斯末矣。”⑦先著、程洪撰,胡念贻辑:《词洁辑评》,《词话丛编》,第1347页。邓廷桢云:“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①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词话丛编》,第2530页。此外,清人还用兴象来品评诗话。谢章铤云:“文章有创体,即为绝唱,断不容后人学步者。司空表圣《诗品》,骚坛久奉为金科玉律,国朝袁子才乃有续品之作,其语言工妙,兴象深微,吾不知媲美前修否也?”②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词话丛编》,第3476页。梁章钜云:“司空表圣《诗品》,但以隽词标举兴象,而于诗家之利病,实无所发明,于作诗者之心思亦无所触发。”③梁章钜:《退庵随笔》,《清诗话续编》,第1991页。虽然兴象的品评范围有所扩展,但其涵义并没有超出明人的阐释范围。
其次,兴象深微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追求。纪昀往往以深浅来论兴象,并多次对“兴象深微”表示赞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审美倾向。纪昀评王维《登辨觉寺》:“五六句兴象深微,特为精妙。”④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九,清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评常建《题破山寺》:“兴象深微,笔笔超妙,此为神来之侯。”⑤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1666页。这里的兴象深微当从深、微两方面来体会。一方面是深,偏重兴象之兴,也就是兴象中所蕴含的情兴寄托要深。所谓深,即不能在诗歌中将意旨直白地表现出来,而是藏蕴于对景象的描摹之中,须深入体味方可把握。纪昀不仅重视兴的情兴寄托之意,也重视兴的触物生情之意,并将两者统一在同一逻辑链条中。他说:“心灵百变,物色万端,逢所感触,遂生寄托。寄托既远,兴象弥深。于是缘情之什,渐化为文章。”由于感物而有触动,有感触就有寄托,寄托远才能兴象深,情感的抒发才能被诗文定型。在此,纪昀的关注点更在于寄托情兴的深远,“兴象不远,虽不失尺寸,犹凡笔也”。⑥纪昀:《唐人试律说序》,《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九。另一方面是微,偏重兴象之象。虽然要寄托意旨,但在表现手法上却不宜笔墨浓重,不能刻意雕琢锻炼,而应该举重若轻,以轻淡微妙的笔法加以表现,下笔虽轻,但意蕴无穷。纪昀认为:“响字之说,古人不废,暨乎唐代,锻炼弥工。然其兴象之深微,寄托之高远,则固别有在也。”⑦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序》,《 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九。纪昀深入发掘了兴与象蕴含的曲与隐的特征,并加以提炼和阐发,形成兴象深微的诗学命题。尽管纪昀的兴象多用于品评唐诗,但他对于兴象深微的强调,其实包含了很深的宋诗特色。这既是纪昀兼纳唐宋诗歌传统的体现,也是清代诗学中兴象使用范围拓展的一种表现。
在清代诗学中,兴象正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批评范畴,可惜这种趋势被后来的变化打断了。晚晴民国时期,在西学影响下的中国诗学进入新的阶段。在西学话语中,兴象很难找到恰当的对译词,因而很难被以西方话语为基本支撑的现代文论话语体系接受,于是,明清诗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兴象范畴,在现代诗学创建过程中渐渐被遗弃。尽管还有个别学者比较重视兴象,但只是零星个案而已。不过其中仍有值得关注的观点,如钱锺书认为:“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⑧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10-211页。钱锺书将兴象作为心之事,极具启发性。在他看来,兴象不是艺,不是作品本身,不是诗歌中具体的物象,这与很多批评者将兴象看成作品中以语词表现的具体物象有本质区别。在传统诗论中,兴象关系与心物关系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但钱锺书认为兴象都属于心之事,而用来抒写兴象的材料,才是物之事。这种阐释从创作角度出发,将兴象关系与心物关系区分开来,充分显示出现代学人对兴象涵义的辨析更加深入和细密。
六、兴象之新阐释
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兴象在诗学话语中基本上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象在各种文论著作中被提及,相关论文也逐渐增多。前辈学者的努力使兴象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拓展,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此的理解,但却少有学者将兴象提到中国诗学核心范畴的高度。笔者认为,在对传统阐释的传承基础上,经过当代学者的创造性阐释,兴象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首先,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兴象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层面、审美层面以及理念层面均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1)形式层面上,兴象较少关注实际层面的字法、句法、篇法,也较少区分体裁、题材,强调对诗歌第一层形式结构的超越,追求第二层形式结构。(2)审美层面上,以兴象宛然、兴象玲珑为代表的重象审美命题和以兴象深微、兴象高远为代表的重兴审美命题,代表了不同的审美指向,但两类命题并不矛盾,而是具有一定共融性,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兴象进行阐发和开拓,使得兴象理论更为丰富全面。(3)理念层面上,兴象的根本是语言的视觉化和图像化,其中包蕴着兴寄或情兴。兴象追求整体性的内视图像美,是中国古代诗学由象发展到境的重要赓续点。
其次,兴象贯穿了诗歌发生、诗歌创作、诗歌鉴赏等不同阶段,如果与当下的诗学批评和创作实践相结合,具有极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建构可能。(1)从发生角度来看,兴是生命感发,象是艺术表现,两者结合正体现了中国古典审美的特质。中国美学是生命美学,我们对于诗歌的审美应立足于生活本身,不能将诗歌与生命体验完美结合的作品,不是一流的作品。兴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触物起情,由于生活万象对生命的触动,从而引发作者情绪波动,产生出抒发情感的创作冲动。象是这种情感的表现和载体,但又不同于单纯的物质载体。兴象作为二者的结合,是古典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关键所在,可视为中国古典生命美学的代表性审美范畴。(2)从创作角度来看,兴象是超越符号象的内视图像。文字符号本身是一种象,经过提炼精选后的字、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这种象往往会被人们误认为就是审美意象,其实不然。在符号象(Verbal icon)之外,还存在一种对应的象,是通过符号象激发和建构的内视图像(Mental image),我们认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兴象。作者通过诗句中的语言符号呈现出一种固定的物象组合,并以此作为这种整体性图景的主要支点和基本结构,这也可以视作一种格式塔(Gestalt),它们规定了这种图景的本质性特点。作者炼字炼句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超越这些具体字句的整体性内视图景,读者通过阅读对这种图景进行提取和复现。(3)从鉴赏角度来看,兴象是一种具有生长性的图像化审美对象,可以看作是作品文本与读者体验到的意旨之间的中介。兴象不能直接通过文本来把握,也不能通过眼睛直接看到,它只存在于审美直观中。兴象不是作品本身,它包含了作品本身的本质特征和欣赏者的主观理解,在不同程度上会对作品进行补充、削减、完善或变形。尽管不同读者根据自身经验所想象和建构的图景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是稳定的,这也是作者的意图所在。兴象类似于诗歌中的前图像结构,具有为审美对象构形的功能,它规定了审美对象的基本结构,但并不填充全部细节,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兴象大体属于唐诗学领域,多与宋诗学对举。而在当下,我们面对的文学现状是文言诗与白话诗对举,中国诗与外国诗对举,兴象有理由也有可能成为文言诗甚至中国诗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兴象研究既可以继续在传统的诗学理论和历史情境中展开,又可以与当代诗歌创作实践及西方诗学理论资源联系起来,既树立自身的诗学品格,又可与西方诗学理论展开对话。进一步研究和阐释兴象理论,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自觉的中国诗学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