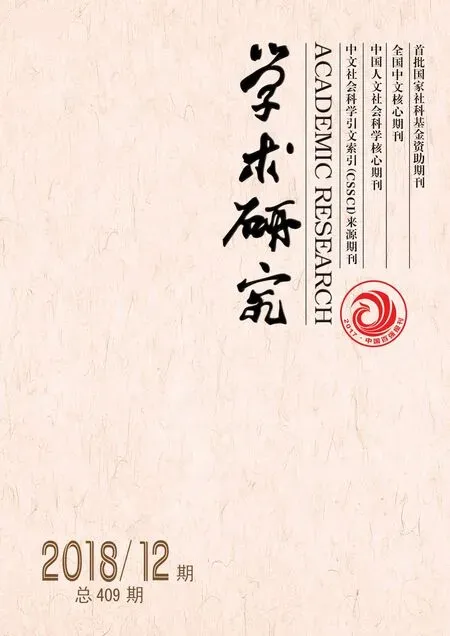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贾平凹小说的世界性和理论前瞻性*
王 宁
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到当今世界文学成为一门显学,世界文学作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已经历了一百九十多年的曲折历程。世界文学理念进入中国,也使得中国文学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发展到逐步开放,并成为全人类文学之一部分的阶段。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小说无疑有着最多的读者,而且小说也最容易经过翻译的中介成为另一国或另一种语言的读者阅读的文学文体。因此探讨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就及其世界性影响,我们应当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之下。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代的一些小说家不仅在中国有着众多的读者,而且在全世界也不乏知音。贾平凹就是其中的极少数佼佼者。本文在聚焦贾平凹小说的世界性特征之前,首先对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作一简略的概括。
一、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当代小说
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始终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当年,歌德之所以能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通过翻译的中介读到了中国小说《好逑传》等东方文学作品而突发奇想,预感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但这种构想在当时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假想。世界文学时代真正到来应是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事件,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人际的和文化的交流使之不再停留于一种乌托邦的假想,而是演变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审美现实。确实,中国现当代小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一种文体,因为在1919—1949年这段时期,所有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以及各种人文学术思想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理论话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世界文学的理念也因此进入了中国,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1949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们却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学几乎与外部世界又隔绝了多年,在时间上和文学质量上较之世界文学主流都有了不小的差距。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便开始意识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边缘位置,因而感到十分不安。为了再现往日的辉煌以便努力从边缘重返中心,中国文学一直在试图与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相认同。这也正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大面积地将西方文学翻译成中文的原因所在,他们也许认为,通过翻译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人文学术理论著作来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化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策略。而在各种西方文学文类中,他们翻译得最多的就是小说,以及各种现代文化学术思潮和理论,并将其视为一种摆脱孤立、走向世界的最佳途径。这些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尤其是译自西方、日本和俄苏的小说在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启迪了整整一代文化人。
既然“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受惠于中国小说,那么中国小说就理应对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但是中国现代小说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比重却远非尽如人意。在当今英语世界的各种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本中,也只有鲁迅、林语堂、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十多位中国小说家的作品被选入。而当代小说家中也只有莫言的《老枪》有幸入选2012年出版的《诺顿世界文学选》最新一版。由于绝大多数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受语言所限,因而在国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掌握话语权的主要还是西方的汉学家,中国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鲜有在国际学界发声者,即使偶尔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大多局限于同样在西方学界处于“边缘”地位的汉学圈内。这种批评和研究的缺席显然与中国现当代小说实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当然,除了翻译外,中国现代小说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批评性讨论和研究性著述的推进作用。当年,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的文学史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英语世界独树一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后经人翻译成中文后又在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界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甚至对中国几代文学史研究者和理论家重新书写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缺席也是阻碍中国现代小说走向世界的一大瓶颈。
我们在讨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当代小说时,应当首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断代应当始自1976年“文革”的结束,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我们通常说,从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全盘西化”的现象。而在1976年之后,尤其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坛再度出现了这样一个“全盘西化”的倾向。①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断代,参阅拙作《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断代》,《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越来越朝向世界开放以便得以跻身世界文学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可以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真正开始。但是莫言只是诸多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中的一员,而另一些同样优秀的作家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他,只是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翻译或批评性讨论而在异国他乡一度忍受着“边缘化”的境遇。下面我首先简略评述另几位有着世界性影响并最有希望获得下一届诺奖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的成就,然后着重聚焦讨论贾平凹的小说。
阎连科被认为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但他真正成为一位有着国际声誉的大作家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事。迄今他的小说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尤其在美国影响更大。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专门举办了讨论他的创作的学术会议,在批评界和学术界推广他的作品,这对于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来说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殊荣。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也运用西方的理论阐释他的作品并发表于国际学术刊物。①例如,在我应邀为国际比较文学的权威刊物Neohelicon主编的一组题为“Narrative and Stylis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中,就发表了两篇讨论阎连科小说的叙事和文体风格的论文:J. Wang,“‘Serve the People’from 1944 to 2005”,和 J. Yang,“Narrative Death in Yan Lianke’s Dream of Ding Village”,参阅 Neohelicon, Vol. 43,No. 1 (2016), pp. 45-57, pp.105-117。因此阎连科也和莫言一样,同时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但阎连科的理论意识更强,西方文学和理论造诣也更为深厚。在2018年3—4月间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阎连科应邀和另一位阿根廷作家与翻译家作了对话,引起了主流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②笔者应邀于2018年3月28日至4月1日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并作了专题报告。同时受到邀请与翻译家进行对话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就是阎连科,笔者亲自参与了这一活动并与阎连科作了短时间的交谈。会后阎连科在杜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罗鹏(Rojas Carlos)的引荐下在美国的几所大学演讲。这一切都说明,他在西方学界的知名度并不低于在国内学界的知名度,同时他的小说在西方世界也有着更多的知音。
余华也许是继莫言之后其作品在国外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被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而且也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关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刊物《疆界2》(boundary 2)和文学史学刊《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等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权威刊物都曾发表过论文专门讨论余华的作品或将其当作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来讨论。此外,余华的作品在国际学界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引起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关注,这说明他的影响已经走出了汉学家的小圈子,进入了比较文学和当代理论批评家的视野。随着余华更多的作品被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从比较文学和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他,从而加快他的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的步伐。
在当代优秀小说家中,刘震云的创作生涯一直是比较平稳发展的,但是近几年来在跻身于世界文学的进程中却有着后发的优势。他早年曾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而蜚声文坛,之后他虽然不断地在艺术手法和写作技巧上翻新求变,但几乎一直依循着这条路子稳步向前发展,最终成为一位就其国际声誉而言仅次于甚至与莫言旗鼓相当的实力派小说家。他的小说语言幽默诙谐,富有浓郁的人情味,丰富了当代汉语。因此毫不奇怪,迄今他的小说已被译成了三十多种语言,不仅囊括所有的主要西方语言,而且还在阿拉伯语文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说他的创作是世界文学并不为夸张。此外,他也在东西方文学界荣获各种大奖,同时得到翻译界和批评界的关注。这也正是他的小说同时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和国外汉学界及批评界受到欢迎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非近几年来也开始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吸引国际翻译界和文学评论界的瞩目,并开始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格非在坚守文学艺术的精英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同时,用厚重的笔触描述了自民国初年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力地回应了世界文坛上早已发出的“小说之死”或“长篇小说之死”的噪音。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角来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则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史诗”,可以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媲美。
当然,中国当代优秀的小说家绝不止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上述五位,若将他们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或更为具体地说来,世界小说的大语境下来考察和评价,我们也照样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国际影响与那些已获得诺奖的西方小说家相比并不逊色。因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国内读者而写,同时也为全世界爱好文学的广大读者而写。此外,他们的优秀作品也为文学理论批评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据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学文本。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作的,但在他们的作品中隐含着某种可译性和可阐释性,因此经过翻译的中介,它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作品主要是面向国内读者的,但是经过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理论阐释,他们的作品已经开始从本土走向全球,从具体走向普遍。但是据我所知,上述几位作家除了在普通读者中以及汉学界有着众多知音外,并未对更多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者产生启迪和影响。在一些讨论世界文学,或更具体一些,讨论世界小说的批评性或学术性著作和论文中,他们的作品也很少被主流批评家或研究者所引证。这就提醒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不仅要在国内批评界和学术界关注这些作家,及时地跟踪他们的创作,并运用理论批评的工具来阐释他们的作品,更要在国际学术界给他们以应有的批评性关注和讨论,从而实现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一方面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进入中国,另一方面,同样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可以走向世界。因为这些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杰作,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杰作。
本文所聚焦讨论的作家是贾平凹,因此我在接下来的两部分将着重讨论贾平凹小说的世界性及理论前瞻性,并以他的《怀念狼》作为分析阐释的重点。
二、贾平凹小说的世界性及理论前瞻性
如果我们说一位小说家的作品具有世界性特征,至少说明该作家的作品并不仅仅是为本国读者所写,而更是为全世界的读者所写,因为他的作品所探讨和描写的是全人类共同面对并予以关注的问题。因此,当他的作品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另一语境时便有可能受到该语境的读者的阅读和批评性讨论。而当我们说一位小说家的作品具有理论前瞻性时,则说明这样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该作家本身就是两栖写作者,既写作文学作品,又从事理论或批评论著的写作,例如意大利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翁伯托·艾柯就同时是一位著名的符号学家,他被公认为在这两个领域内都成就斐然,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另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就是英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戴维·洛奇,他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文论家,不仅在英语世界,而且在中国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显然,贾平凹是一位来自西北的中国乡土作家,他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理论家,他也很少从事文学批评。但是在他的创作意识或无意识中却有着某种理论的敏感性和前瞻性,他是我们所说的“小说家的作品具有理论前瞻性”的另一种类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小说《怀念狼》中。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贾平凹最具有乡土意识和民族特色,甚至他的语言都具有浓郁的西北乡土特色和浓重的乡音,这一点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一些方言和土语的运用中。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国外汉学家认为是“不可译”的,就连葛浩文这样的美国首席文学翻译家在开始问鼎贾作的翻译前还咨询过一些学者的意见。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就越是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好的翻译。这一点也体现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文学院院士、现任诺奖评委会主席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受到与会的中国作家的质询,他当时的回答十分巧妙,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长时期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缺少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是缺少优秀的(西文)译本。但是随即就有不少人问道,诺奖评委会究竟是评价作品的文学质量还是翻译质量,马悦然并未作答,因为他自己内心中也有不少令外人难以想到的苦衷。后来,在2004年的一篇访谈中,他再一次被问道:“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马悦然是这样回答的:“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直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①王洁明:《专访马悦然: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9日。这显然道出了诺奖的评奖原则和机制上的一个问题。它既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文学大奖,但长期以来却又仅仅在一个有限的小圈子里评选,由于评委本身的知识结构和所掌握的语言之局限,对西方世界以外的作家的评价不得不依赖翻译,这显然是一个悖论。我们可以从后来沈从文的案例中见出端倪。沈从文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他于1988年去世,按照诺奖的评奖原则,已故的作家是无缘获奖的,因而沈从文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①参见报道《沈从文如果活着就肯定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南方周末》2007年10月10日。马悦然曾几次试图改变这一原则均未果,当他最后一次使出全身解数试图劝说诺奖委员会改变这一原则时,依然无效。②曹乃谦:《马悦然喜欢“乡巴佬作家”》,《深圳商报》2008年10月7日。因此这就说明,即使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很有可能在另一语境或另一国度受到“冷遇”或“边缘化”或甚至是“死亡”的境遇。这就对我们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何在国际学界推出我们自己的作家和理论家?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贾平凹的作品如果早二十年或三十年由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翻译家翻译的话,如果我们在一切国际场合对他的创作及作品进行批评性阐释和讨论的话,他早就引起国际文学界的瞩目进而有可能问鼎诺奖了。
因此在我看来,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恰恰是贾平凹作品所具有的最大魅力和独特之处,尽管他的小说中有着上述不可译的因素以及种种缺陷,但这也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的流通,虽然他的作品没有余华和莫言的作品那样在海外有着那么大的影响和市场,但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了世界上二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众多的读者。他本人也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其中包括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浮躁》)、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废都》)、第一届红楼梦奖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等。这些都为未来的诺奖评委会认真考虑他的作品之价值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国内评论界一般认为,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这无疑是他的作品具有厚重的叙事艺术力量的原因所在。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视角尤为独特。他的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其间充满各种意象,但却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其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因此他的小说同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审美意象性。现在,优秀的英文翻译者葛浩文等人开始对贾平凹的作品感兴趣并问鼎贾作的翻译了,我们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也开始认真讨论他的创作成就了,因此可以预言,贾平凹的作品必将很快有效地走向世界。
尽管几乎贾平凹的所有主要作品都引起了国内批评界的重视,例如《商州》《浮躁》《废都》《秦腔》《古炉》《山本》等,有些作品甚至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但他的另一个特色也许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也即他在描写故乡的人和事的同时,也对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力图将其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作品隐匿着某种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并有着引发理论阐释和批评性讨论的价值。他虽然并不从事文学理论批评,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却对理论较为敏感并能“悟”出其在未来的发展走向,因此他的创作常常走在理论思潮的前面。比如说,我们一般在提及当代文学中的狼的形象时,总会想起姜戎的《狼图腾》,但那部十分畅销的小说却是在200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则出版于2000年,可以说,从当代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这可算是一部具有批评理论前瞻性的作品,并成为当代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难得的经典文本。
在总结《怀念狼》的写作时,贾平凹指出:“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日子一日复一日地过下去,顺利或困难都要过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把《怀念狼》终于写完的兴趣所在啊。”③贾平凹:《怀念狼·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出自本书,本文仅标明页码。这便十分清楚地道出了他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他所写的东西都是自己十分熟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写法却有所不同,平庸的作家只会专注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或寻找一些能够打动普通读者的事件大加渲染,而优秀的作家则善于提取具体实存的东西赋予其普遍的象征意义。《怀念狼》就是这样一部既具有象征意义同时又有着现实关怀的作品。由此可见,贾平凹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审美理想和理论抱负的作家。确实,他写的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但他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成规,而是虚实相间,以自己的感觉和体悟为主。因此,正如他所坦诚的:“《怀念狼》彻底不是了我以前写熟了的题材,写法上也有了改变。我估计它会让一些人读着不适应,或者说兴趣不大。可它必须是我要写的一部书。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而不是去迎合,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第271—272页)确实,《怀念狼》主要描写的并不是贾平凹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而是动物,或更具体地说是狼,因而很难吸引一般读者以及那些注重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但却对专事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学者意义重大。当我于本世纪初率先在中国的语境下引进西方的生态批评时,曾一度苦于找不到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文本,而《怀念狼》恰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诚然,正如他本人所意识到的,一般读者可能对之兴趣不大,因为它不同于贾平凹以往的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但我作为从事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的学者却对之异常感兴趣。因为在我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固然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是当代文学中也不应缺少这样的文学文本,因为中国当代的生态问题实在太紧迫了。此外,这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的作家和人文学者应该给与关注并提出自己的应对智慧和解决方案。
当一种理论思潮或批评风尚诞生时,具有理论前瞻性的作家实际上早已走在前头了,他们所创作出的文学文本就是我们从事理论批评阐释的极好文本。我们都知道,生态批评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之后风行于整个世界,而生态批评被引进中国批评界则是21世纪初的事。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者和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或人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很少有人去问津动物研究。即使是西方的生态批评家也只是到了新世纪初才开始关注自然界动物的状态并转而研究动物的。而《怀念狼》则写在这些理论思潮崛起之前,至少在中国批评界是如此,这实际上也预示了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他之所以选择狼为描写的对象,其一是他所关注或描写的对象是商州,那里也是遭受狼灾最严重的地区,其二便是狼的形象本身就具有二重性。狼一贯被人认为是人类的天然“敌人”,因此人类对狼是既怕又恨,这在中国尤其是如此。我们自幼便熟知的一则寓言故事《东郭先生和狼》就通过东郭先生对狼的怜悯而受到报应的不幸遭遇警醒我们,决不能怜惜像狼一样的恶人,否则我们就会失去生命。在中外文学史上,在描写人与狼的关系方面也不乏杰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狼总是一个反面的敌人的形象,虽然在一些作家的小说,例如杰克·伦敦的两部描写狼与狗的小说《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狼也被描写为通晓人性,并具有人的思维和行事能力。但狼的另一重形象则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它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物种,人类有时也会与狼共舞,与狼共存。一旦狼这一人类的天敌从我们的生活甚至视野中消失了,我们又不免会怀念它,并试图寻找他的足迹。《怀念狼》的主人公高子明就走上了寻找狼的征途,但在这一过程中却遭遇了种种曲折和磨难。
他来到商州的一个使命就是调查狼的生存和境遇,以保护这一濒临灭绝的动物。但是当他呼吁人们保护仅存的几只狼时,竟遭到人们的一顿暴打:
“打这狗日的城里人,城里人日子过得自自在在,只图着保护狼哩,谁保护咱呀?是这狗日的给傅山灌迷糊汤了,把他捆起来,捆起来!”
一阵如雨的拳脚,我被打倒了。我双手搂抱了头,蹲在地上,立即有人从后裆处再次将我扳翻,我的头发被揪起来,衣服也被撕破了,眼前晃动的是无数血红的眼睛、咬得咯吱咯吱响的牙齿,一口浓痰就落在了我的鼻子上。我最终是被用一条麻绳捆在了门前的柿树上。我大声地叫喊着我的舅舅,舅舅回头看了我一下,他没有来救我,连一句制止的话也没有。我还在叫:“狼只剩下三只了!”众人哈哈大笑。(第246—247页)
在人们的愤怒声和接踵而来的对狼的剿灭下,最后一只狼就这样从商州消失了。高子明为保护狼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但是作为一种报应,猎人们则因为再也见不到狼的踪影而变得虚弱和退化了,接下来的便是往日与狼战斗十分勇猛的猎人竟先后得了各种奇怪的疾病而死去。这就是人生的一大悖论。在姜戎的《狼图腾》中,牧民们最终结束了游牧生活,而草原上则大面积地沙化,人的生存环境也遭到了破坏。因此人有时不免也会对有狼的时代产生一丝的眷念。作者姜戎通过将狼写成草原上世世代代人们所崇拜的一种“图腾”,进而讴歌了一种一往无前的“狼的精神”,而贾平凹的《怀念狼》则把这一悖论写得十分出色,使之具有寓言的深刻意味。它不只是地球上的单一物种,而是象征着所有的动物。它的幸存也关乎着人类的未来命运。而一般的读者则看不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小说的题目看出贾平凹的匠心所在。当狼对人的生活构成威胁时,我们确实应该将其当作敌人来对待。由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人们赚钱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因此捕狼也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这方面贾平凹描述道:“地方政府从未投资给过捕狼队,捕狼队却有吃有喝,各个富有,且应运出现了许多熟皮货店,养活了众多的人,甚至于商州城里还开办了一家狼毫毛笔厂,别处的狼毫笔厂都用的是黄鼠狼的毛,而他们绝对是真正的狼毫,生意自然更为兴旺。”(第21页)但曾几何时,在对狼实施的全民围剿中,狼群渐渐地变得稀少甚至灭绝了。在偌大的一个商州,一度仅剩下“十五只狼”,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者所“听到的所有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来还没有哪位领导在介绍自己的家底时说到还有狼!”(同上)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在打完所有的狼以后,那些打狼的英雄又能去做什么呢?“捕狼队自然而然解散,据说狼毫笔厂也随之关门。”(第9页)昔日的捕狼队队长,“最后接受的任务是协助收缴散落在全商州的猎户的猎枪,普查全商州还存在的狼数”。(同上)此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没有了狼,猎人一个个都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怪病:人极快地衰老和虚弱,神情恍惚,先是精神萎靡、乏力无气,继而视力衰弱、手脚发麻,日渐枯瘦。这就是人在与狼为敌并剿灭狼之后所遭到的报复和报应。
诚然,贾平凹的小说所描述的不仅仅是狼的逐渐灭绝,他还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另一种珍稀动物大熊猫的生产过程,这不啻是一种生死煎熬,最后大熊猫“后”仍然在遭受剧烈的疼痛后死于产仔,接踵而来的便是幼仔也死了,“留下来的是一群研究大熊猫的专家”,他们中的一位——黄专家甚至变疯了,因为大熊猫的死也使他的晋升职称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来,动物的死亡和退化也带来了人的退化以及自然生态的失衡这一后果,同时还有商业化的文化生态的危机。在描述人与狼的敌对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时,贾平凹写道,狼在受到人的大规模捕杀后也变得乖巧了,见到活人也不扑将上去将其吞食,而是眼看着他从眼前存活下去,而出于良心发现的猎人则手拿着猎枪也没射向狼。人和狼往日的敌对关系逐渐变得缓和了,变成了一种“与狼共存”的关系。但这依然没有避免《怀念狼》最后的悲剧性结局。这并不是因为人与狼的那种平衡关系又恢复了,而更是因为那仅存的十五只狼的最终灭绝。这不仅是因为贾平凹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困难,同时也流露出了他本人对这种现象在未来的发展的悲观看法。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为什么叫“怀念狼”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狼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地球上这一单一的物种,而是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代表了整个地球上的动物。狼的灭绝同时也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灭绝,接踵而来的就是人类的不断遭受磨难甚至退化。假如这条生物链被割断了,人类也就会相应地遭受到报应,严重的自然灾害就会发生。因此,狼的灭绝对人来说并非好事,而是一件坏事,因为它破坏了地球上万物的平衡状态。既然狼作为地球上与人共存的一个物种,那么它也应当是整个生命链条中的一环,一旦地球上没有了狼,自然和人的这种平衡关系也就被破坏了,人也必将蒙受灾难。这样看来,怀念狼并不仅仅是怀念这一动物,而更多地是呼吁人类不仅要彼此关爱,而且还要关爱其他物种。这显然是一种生态世界主义的理想和情怀。
应该承认,贾平凹虽然不是一位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修养和对理论的敏感性却是当代其他作家难以比拟的。尽管一些抱有“理论之死”观点的人们对理论的未来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但我始终认为,理论依然存在,但是理论的功能却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一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甚至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理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但理论本身并没有死亡。大而无当的“文化理论”无所不在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来自文学的理论最终仍应返回文学,并用于文学现象的阐释。最近十多年里出现并风行于西方世界的“世界主义”“后人文主义”“性别研究”以及“动物研究”等理论思潮就表明了理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贾平凹的这部描写狼的小说可以说涉及了上述所有的理论思潮,我们完全可以从“后人文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动物研究”的视角来阅读和阐释这部小说,以发掘出隐匿在他的富有张力的文字背后的批评价值和理论意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对产生自西方的理论进行质疑甚至重构,这样才能达到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以及中西文学理论的双向阐发和对话。就此而言,《怀念狼》的出现应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大幸事。
三、“后人类时代”的动物意识:贾平凹的理论意识和无意识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过去经常由人所从事的工作现在经常为机器所取代,作为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以往的人文主义时代人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神”的位置逐渐下降为地球上万物的一种,人本身也成了一种“后人”,我们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后人类”的时代,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作为作家和人文学者对这种异化的现象率先作出了反应,生态批评、后人文主义和动物研究等“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也应运而生。诚然,我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响应,或者说我们与西方的乃至国际的理论同行都同时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2011年,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应我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主要高校作了一系列巡回演讲,他在演讲中描述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向,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六个方向:(1)叙事学的复兴;(2)更多地谈论德里达而较少谈论福柯和拉康;(3)伦理学的转向;(4)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5)后人文研究;(6)审美的回归。①参阅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 Today”,2011年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译文见《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生安锋译。细读贾平凹的这部小说,我们不禁惊异地发现,他的作品对当代理论不无某种预示,也即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中,他已经朦胧但却敏锐地感觉到某种理论事件正在或即将出现,而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理论家提供鲜活的文学文本,促使理论家从大而无当的(文化)“理论”中返回到文学理论本身,并专注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阐释。我认为这应是贾平凹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最大贡献,尽管这种贡献并非自觉地,但是制约作家创作的除了生活体验和以往所阅读的文学的积累外,无意识也是一个因素。也即作家并非理论家,他不可能像理论家那样有意识地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但是作家却在无意识中对自己所要创作的作品有着某种构想,而这种无意识的构想一旦进入意识的层面就有可能成为某种可供批评家破译进而阐释的密码。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在有意地拔高贾平凹的地位,或者说强制性地阐释他的作品,但我恰恰认为,正是作家向理论批评家提供了理论批评的文本,他们更应该受到理论批评家的尊重。批评家对作品的阐释只是提供给作者一种可能的解读,并非专断的甚至强制性的。因为是批评家在帮助作家完成他尚未完成的文字文本的写作,并帮助他发掘出他的作品的潜文本意义。
细读《怀念狼》这个文本,我们发现,小说中有好几处对狼的情感意识都有着细腻的描写,使之具有人性或与人性相通,如狼为死去的熊猫献花以表达哀思,为死去同伴而悲痛欲绝,并且集体对恩人表达悼念之情等。这些细节描写均体现了贾平凹对动物的特有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与尊重。它至少说明,在这个地球上,人并不是唯一的物种和价值主体,狼也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并不需要人来赋予,因为它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狼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因此它们也应该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意识和存在的权利。这无疑是一种生态世界主义的情怀。②关于世界主义与文学的关系,参阅我为国际权威刊物Telos编辑的主题专辑,Cosmopolitanism and China: Toward a Literary (Re) Construction, Telos, No.180 (Fall, 2017), 3-165;以及王宁《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前沿》第9辑(2012),第3-29页。而他对狼的地位的拔高并使之与人相平等的做法不仅是对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批判,同时也预示了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关怀。
所谓后人文主义又被译为“后人类主义”,它也是“后理论时代”的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思潮,最近几年里开始在中国风行,但这已经是《怀念狼》出版十多年后的事件了。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一“后人类”阶段,人类并非宇宙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甚至在地球上也不是各种物种之首领。只是人类的进化程度最高,因而带有最多的理性特征。此外,人类虽然最具有想象力,也可以创造出各种奇迹,甚至创造出连自己也无法驾驭的东西,但人类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后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加利·沃尔夫(Cary Wolfe)在其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09)中也作了阐释。按照沃尔夫的看法,“人类在宇宙中占据了一个新的位置,它已成了一个居住着我准备称之为‘非人类的居民’(nonhuman subjects)的场所”。①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47.也即在后人文主义者那里,人类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曾被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唯一有生命的物种,他和另一些有生命的动物和自然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而在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存的状态中,人类虽然地位显赫和特别,但并不一定永远是其他物种的主宰或主人,他有时也会受制于自然界其他物种或受到后者的挑战和威胁。例如人与狼的关系就是如此。贾平凹试图告诉人们,人与狼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当狼处于兽性发作时期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时,人固然应该奋起自卫反击狼的攻击,但是一旦狼处于劣势并开始与人共存时,我们则应该保护它,因为我们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后人文主义者也和动物研究者与生态批评家一样,实际上想告诫人们,不要忽视动物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人类所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生物链,一旦这个链子断了,人类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最近十多年里出现的风暴的频繁、草原的萎缩、部分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等现象就是一些不祥的预兆。对于自然和环境的危机状态,作家和人文学者是最为敏感的,他们试图呼吁人们保护自然,保护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也许这样的声音是微弱的,甚至被更多的人所忽视和误解,就像《怀念狼》的主人公高子明所遭遇的那样,但是作家和人文学者不断地呼吁终究会起到一些作用。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天灾人祸就是他对人们的警醒,而近几年来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恰恰证明了他写于近二十年前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了。这应该是这部小说的预示未来的寓言力量。
四、游离于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
我们曾一度认为,就文学作品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证明,这种已经持续了很久的观念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有时越是民族的反而越是难以走向世界,特别是在缺乏优秀的翻译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贾平凹的作品长期以来被一些人认为“不可译”,尤其是那些用乡间土语写的东西。但是他的作品仍然经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了世界。因此我们切莫忘记,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再创造,尤其是之于文学作品更是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优秀的翻译才能增色,否则一部优秀的作品很可能就葬送在拙劣的译者手中。中国的文学界和翻译界一向对世界文学采取一种拥抱和拿来的态度,一些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刚刚出版的文学作品,很快就有了中译本。自然我们也希望国外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像我们一样,能够及时地将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使之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但是事实总是与我们的一厢情愿相违背,当然少数幸运儿除外。就这一点而言,贾平凹算是比较幸运的,他的作品毕竟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国外也有了众多的读者。但是与他的那些西方同行相比,那就远远算不上是幸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观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不正确的导向所致。如果我们将《怀念狼》这部小说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它既是民族的,同时也更是世界的。说它是民族的是因为这一题材取自他所熟悉的商州这个地方;说它是世界的则因为他所描写的狼已经不只是一种动物,而是指代整个动物界和自然。
首先,《怀念狼》也和贾平凹的一些其他作品一样,写的是发生在商州的事和生长在商州的人,这些事,如狼灾、打狼和寻访狼的踪迹都是道道地地发生在商州这个地方的事,几乎所有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与商州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因此,这就是小说所立足于其中的民族的土壤和乡土特征。小说中所描写的狼也出自商州,也许它与姜戎笔下内蒙古的狼以及杰克·伦敦笔下的阿拉斯加的狼有着一些差别,但它们都属于一个大的狼科动物,或者说用来指代地球上一切不同于人的物种。就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和七情六欲而言,它们也和人一样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因此它们的命运和悲欢离合就具有某种普遍性和世界性。
其次,人总是怀旧的,即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商州的人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以往的那种以狩猎为生的生活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成了历史。但是生活得到改善后的人们却更加怀念以往的那种质朴和贴近自然的生活,这不仅是商州人的企望,同时也更是一切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地区的人们的共同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现代,希望告别原始的农耕和游牧生活,但另一方面,一旦失去了与之亦敌亦友的动物,他们就会感到极不适应,甚至染上各种奇怪的疾病,有的甚至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因此他们就开始怀念被自己灭绝的动物,怀念狼实际上就是怀念那些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动物。这也是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自然情怀和动物情怀。
再者,贾平凹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作家,同时也有着更为广大的自然关怀和动物关怀。贾平凹的生态关怀和动物关怀是明显的,但是他的这种生态关怀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疆界,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意义,并达到了生态世界主义的高度。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可以走出黄土地,进入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在谈到世界主义时,并非意味着某种趋同性,尤其是说到人文与文化时就更应该如此。世界主义并非意味着专断的普遍主义:前者指涉一种容忍度,而后者则诉诸一种共识。我们应该看到,任何貌似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都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任何物种,不管它是人类还是鸟类还是猫类,都是地球上的一员,不管它强大或弱小,都应该受到地球上其他成员同样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主义不应当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因为一个人可以在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也热爱整个世界,也即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他也应该热爱其他国家的人民。此外,作为一个地球公民,他不仅要热爱人类,而且还应当热爱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就这一点而言,贾平凹的作品就同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当下性和寓言性。经过翻译的中介和批评性讨论的推进,它们将载入未来的世界文学经典。作为批评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