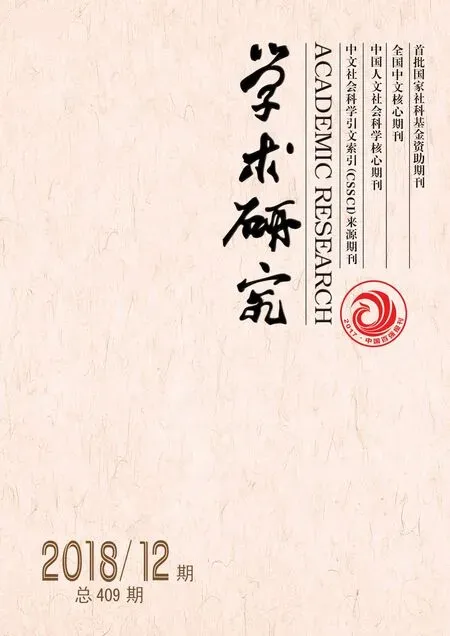从陈寅恪的“双俸”待遇看其崇高学术地位*
刘经富 卢冰冰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产生于清末民初,繁荣壮大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人才是办好大学与学术机构的重要环节,薪津待遇问题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政府适时制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薪津标准,各用人单位为引进人才适当破例浮动,放松教师进出流动的人事政策。良好的互动局面,培养打造了一大批顶尖的学者、教授,为我国学术由旧入新、跻身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贡献,陈寅恪即其中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1890—1969)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新中国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一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又在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和历史组主任(关于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关系,另文详论)。学术前沿的崇高地位,使他的薪俸待遇居于教育界薪津结构的顶端;多个工作单位的流动与各单位的人才竞争保护政策,又使他的薪津待遇复杂多样。他的高薪待遇与他的学术成就成正比,不仅成为观照其崇高学术地位的一个“缩影”,也折射出我国近现代学术、教育发展的面貌特征和礼敬学问、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本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材料(史语所档案目录摘由、傅斯年遗札、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和原有材料,以独特的视角,对陈寅恪一生位尊俸厚的背景、成因钩沈索隐,对其薪津待遇与学术成就、地位声望的相互关系予以阐发抉示。
一
上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的文化学术思潮中,崛起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等著名的学术机构,成为我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潮流接轨,学术现代化、科学化的标志。陈寅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的重要成员,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就是从这里开端的。
1925年2月,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时,经他留学哈佛时的同学好友吴宓推荐,清华学校聘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导师。2月27日,《清华周刊》登载《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
研究院主任讲师已聘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兹校中又函电往德国,聘请陈寅恪先生为主任讲师,连前共四位。陈先生幼承家学,故中国学问甚为渊博。自前清宣统元年迄今,留学欧美共已十余年。陈先生初治史学,继研究古今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及英、德、法文等。近七八年来,则攻读梵文、巴利文以及蒙文、藏文之类。其所用力者,为古代东方各国语言及历史,佛教发达传播之历史,中西交通史等……其人笃志用功,造诣宏深,诚留学生中特别首出之人才。①《清华周刊》第337期,第45页。
1926年2月,陈寅恪回国,7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上任。他在国学研究院三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样,享受月薪400银元的待遇。②《清华国学研究院民国十五十六年(1926—1927)预算表》,转引自陈明远:《那时的大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1926—1929年,尚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聘请陈寅恪为导师,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国学研究所聘请陈寅恪主持该所,讲授华梵比较课程,北平研究院聘陈寅恪为史学研究所主任,中研院史语所聘陈寅恪为兼职研究员,陈寅恪最终选择了史语所。
上述新式学术团体都是“海归”聚集的地方,从领导人到骨干成员,从筹建、管理工作到具体学术科研,归国留学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聘请陈寅恪,许以高薪,看重的正是他特殊的留学经历、丰富的域外语文知识和用新方法整理国故的能力。当时清华研究院招聘教师时,就制订了“受聘者必须精通国学,能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治学,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新成果”的基本标准。③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与经过》,载1925年9月18日《清华周刊》第351期,第2页。陈寅恪选择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史语所不动摇,从而奠定了他拥有两个顶级学术机构的学术资源和“双俸”待遇的基本格局。
1929年6月底,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被改制后的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文学院历史系、中文系合聘,哲学系也聘请他开课。④陈寅恪在哲学系开课至1932年止,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3、144页。
1931年12月,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制定了《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规定教授月薪一般为300—400元,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最高500元。每两年加薪一次,每次加20元,有特殊成就者,可加40元,基本遵循了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发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的规定。但由于清华经费来自庚子赔款退款,资金来源雄厚稳定,其教师平均薪津待遇要高于一般大学。⑤《国立清华大学专任教授休假条例·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档案,编号:1-2-1。在住房待遇上,清华的教授还可以独享一幢住宅。
根据清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度(1931—1937)教师一览表》,陈寅恪的月薪1931年为400元,1933年440元,1934、1935年460元,1937—1939年480元,1938年7—9月“国立西南联大员工薪俸表”记录了文学院17位教师的工资状况,其中陈寅恪月薪为480元,实发351元,为全院最高。⑥廖太燕:《陈寅恪与浦江清》,《书屋》2014年第9期。1938、1939年7月这两年清华发给陈寅恪的聘书第二款载明月薪“国币480元”。⑦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载周言编:《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6、9页。1940年西南联大薪俸表册中的一页列有清华、北大、南开三校66位教师工资,其中陈寅恪月薪500元,冯友兰、吴宓、金岳霖、吴有训、叶企孙450元,刘文典、闻一多、陈福田、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叶公超440元,朱自清、毛子水、郑天挺420元。①廖太燕博士提供的1940年西南联大薪俸表图片,仅拍摄有陈寅恪薪俸的这一页。陈寅恪在清华支领的薪金一直居于文学院之首,是不是全校最高,尚难考定。不过陈寅恪拥有“双俸”收入,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史语所研究员,为他本来很高的薪俸锦上添花。
1928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在广州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他决心率领史语所与法国、日本东方学争胜,确立了“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目标,认为“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自然会想到当时中国学人中最有条件和能力用欧洲东方学范式治学的陈寅恪。而陈寅恪对傅斯年发起“史学革命”的视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颇为欣赏,欣然加盟史语所。陈寅恪当时月薪400元,由于在清华、史语所两边兼职,有“合聘”性质,故两家商议各承担一半。②史语所1928年度经费概算、1929年聘员薪额表,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傅斯年遗札》第1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177、210页。
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平,对内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将原定八个组收缩改编为三个组,陈寅恪任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史语所迁北平后,傅斯年担心所里的重要成员因在大学任教而人才外流,决意取消兼职研究员的名义,请他们辞去所外的一切兼职,做专职研究员。如不同意,则将其改为特约研究员(特约研究员不支薪,只不固定地给予一定报酬)。陈寅恪不愿放弃清华教职,曾考虑辞去史语所职务。1930年3月15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提出不再领史语所薪金,在清华领全薪。③详见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页。
傅斯年也曾考虑过陈寅恪的要求,准备改聘陈寅恪为特约研究员。但此事后来并没有兑现,傅斯年不会轻易放弃一位史学掌门人,他要陈寅恪擎史语所历史学科这面大旗。作为史语所的领军人物,傅斯年非常清楚陈寅恪开拓史学新领域、新境界的价值与分量,极力留住陈寅恪。为使陈寅恪不脱离史语所,傅斯年只得为陈寅恪一人破例,允许他在清华兼职。只是陈寅恪在清华支领全薪的愿望得以实现,史语所不再发给他半薪,改为发给100元兼职研究员津贴。④具体起算月份不详,陈寅恪1931年5月6日致函傅斯年:“……五月份预支薪水百元已领,谢谢。”(史语所档案,元47-11)可证在1931年5月前已发。1931年,又破例给予专职研究员名义,以符合组主任必须由专职研究员担任的规定。
这样,陈寅恪的“双俸”月薪1931年就达到500元,1935年高达560元,加上稿酬收入,数额已非常可观,已跻身当时文人学者薪津收入最高者的行列。
1927—1937年,陈寅恪薪酬丰厚,生活稳定。他专心治学,勇猛精进学问的气象广博精严,是他学术成果的第一轮丰产期,不仅产生了一批关于西北史地之学的重要文章,还为40年代产生的成果在资料、记注、构思上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据苏云峰对清华文学院1937年前教师的科研成果统计,陈寅恪是文学院发表论文最多的教授,其次为赵元任、王力、朱自清、杨树达。⑤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3页。1937年5月,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扬陈寅恪能在清华关门闭户,不习惯人情往来,潜心著述,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史语所是最高的。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陈寅恪凭借广博的域外语文知识,新颖的西方学术理念,深厚的国学基础,继王国维、陈垣之后脱颖而出,显露出引领潮流的大师气象。这里仅以他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1930年,陈寅恪推出四篇研究《蒙古源流》的文章,即《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鄂尔多斯贵族萨囊彻辰所著的一部蒙古史书。陈寅恪以蒙文原本为主,用藏译、满译和汉译的异本互校、比勘《蒙古源流》同源异流版本。这批研究成果意义重大,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进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这四篇文章中,以《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价值最大。该文从《大藏经》中考证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著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取之于八思巴的《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这一结论对学界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①蔡美彪:《陈寅恪对蒙古学的贡献及其治学方法》,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9页。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亦被学界称道。该文考论综合藏文、蒙文、满文、德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长庆唐蕃会盟碑”这一珍贵的文物,考证《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即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对后世藏学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②王尧:《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84页。
1934年,陈寅恪又发表了《四声三问》这样极为专业的音韵学论文,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杨树达称赞该文“立论精凿不可易”。③杨树达:《积微居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7页。朱自清在日记中两次予以摘录该文的要点精义。④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7、269页。陈寅恪去世后,其弟子许世瑛在悼文中称颂“寅恪师并非语言学专家,但是他写的《四声三问》,确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论著,我每次讲‘四声’的时候,一定向同学介绍寅恪师这篇大著”。⑤俞大维等:《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47页。劳干亦在回忆文章中说:“至于《四声三问》那一篇,证明中国语言,虽然本有四声(但四声之中,还有变调,四声之分不易被发现)。而能以发现四声的,还是靠梵文的启示。此亦可以发千秋之秘。”⑥俞大维等:《谈陈寅恪》,第38页。
1937年抗战爆发前,陈寅恪获得一次大奖。获奖前(1936年11月),傅斯年联络胡适推荐陈寅恪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科学奖历史科候选人,推荐书云:
陈君研究范围甚广,中国文史学之各部多所精通。近年来专治晋六朝隋唐史,所成论文, 不特皆有独到,且皆以小见大,结论确不可易。陈君对于西洋文史学之素养在中国为第一人,又通习梵藏蒙诸语言,能兼用中西史学者之工具,并兼造其极也……中国之史学,虽考证上不乏精确工夫,而取材之范围甚狭。最近,研究范围颇能扩大,而方法不能精密。自与欧洲之正统之文史学接触,稍受影响,多以开风气为事,其有坚实之基础者,陈君为第一人。⑦中基会档案,见程巢父:《思想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中基会”自1928年设立以来,获得个人奖励的只有八人,文科的获选者始终只有陈寅恪。⑧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1年,第292页。1938年胡适向牛津大学推荐陈寅恪,即把他获得这一奖项作为推荐依据之一。
这一时期,陈寅恪除了具有清华和中研院两个顶级学术机构的重要成员身份外,还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基会”编译委员会委员,中研院评议员,以中研院评议员最为尊荣。中研院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组织,由当然评议员(院长、各研究所所长)和聘任研究员(中研院聘请的国内专家)组成。1935年6月选举聘任评议员30人,加上10个所长,共41人组成首届评议会,任期为五年。陈寅恪与胡适、陈垣当选历史组的首届聘任评议员。⑨张剑:《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研院评议会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6期。
二
1935年5月,牛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去世,牛津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的空缺。1938年10月,牛津作出聘请陈寅恪的决定。牛津大学聘任教授的荣誉,使陈寅恪一度成为文化学术界的话题人物。
但陈寅恪赴英执教却不顺利。他于1939年、1940年暑假两次准备从香港赴英伦都未成行。1941年12月下旬香港沦陷,陈寅恪被困在香港。
1942年5月,陈寅恪一家在傅斯年、朱家骅(时任中研院代院长)等人的大力营救下,撤离香港。5月12日,朱家骅致电陈寅恪,要求陈寅恪前往史语所驻地——四川宜宾南溪李庄,电文中有“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正加紧进行,务须即日首途来渝”之语。①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载《陈寅恪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第25页。此电是证据链中的关键材料,它使我们明了陈寅恪当时与中研院高层的关系,中研院、史语所上下一致希望陈寅恪归队的心情,陈寅恪以史语所研究员身份应聘燕大的背后原因。陈寅恪一家6月到达桂林后,遇到全家精疲力竭、自己病痛缠身的困境,遂请傅斯年转托杭立武以中英庚款会讲座形式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叶企孙担心西南联大召回陈寅恪,抢先给陈寅恪寄发了专任研究员聘书,发给全薪。傅斯年得知后坚持专任研究员必须到所坐班从事研究的规定,要求叶企孙改发给陈寅恪“专任研究员适用兼任研究员待遇”聘书,津贴由100元加到140元。②王汎森等:《傅斯年遗札》第3 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第1313页。
陈寅恪滞留桂林时,教育部开始实施第一批特聘教授计划,陈寅恪入选。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学术界有三大荣誉,即部聘教授、中研院评议员、中研院院士。“部聘教授”即国家级教授,不仅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在薪津待遇上也很优厚。1942年7月,28家国立院校和学术团体推荐121名候选人,直接由教育部提名者35人。8月,经会议表决,选举出第一批30人,③曹天忠:《档案中所见的部聘教授》,《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可见当选部聘教授颇不容易。④1943年6月西南联大向教育部呈报第二批推荐人选65人,有35人符合评选条件入围,而12月公布的第二批15位部聘教授,这35人中只有冯友兰一人当选。他当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地位较高,第二批才评上。
1942年9月5日,教育部颁发《部聘教授服务细则》,规定“部聘教授除规定薪给外,由教育部按月另发研究补助费400元(1946年增加到1000元)……部聘教授除不在所在学校支薪俸外,其余所在学校应予一般教授之权益均得享受”。⑤陈育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授薪俸及其生活状况考察——以国立西南联大为中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今存广西大学1943年3月发给陈寅恪薪金的封套,依次列项:本月薪金,无;本月生活辅助费120元;米贴400元;薪俸加成215元;实发735元。⑥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载《陈寅恪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第27页。这个数额是中英庚款会通过广西大学发给他的薪津,还是广西大学按“部聘教授除不在所在学校支薪俸外,其余所在学校应予一般教授之权益均得享受”的规定发给他的各项补贴,难得其详。可以确定的是,陈寅恪1943年由部聘教授1000元、广西大学或中英庚款会735元、史语所140元合成的薪金,勉强可以应付当时桂林月费约需2000元的用度。
陈寅恪当选第一批部聘教授后,迁徙到西南后方的各大学闻风而动,1942年8月间,先后有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给陈寄来聘书,浙大史地研究所主任张其昀致函陈寅恪,表示“待遇除部聘教授原薪外,另由研究所月送五百元”。⑦散木:《抗战期间陈寅恪与浙江大学失之交臂始末》,中华书局编《书品》2008年第6期。陈寅恪因已与燕大有聘约,他的部聘教授即由燕大提名,故谢绝了其他大学的聘请。他之所以选择燕大,是因为史语所驻地李庄与成都距离较近。他本拟直接到李庄,在1942年8月19、23日致刘永济函中辞谢武大聘请时说:“以人事关系言,若能入川,势亦不得不至李庄,此中委曲不能函尽”,“若此行遽入川而不至李庄,必召致人事上之纷纭。”⑧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43、244页。后来折衷改为到成都燕大。
1943年8月底陈寅恪携家入川,⑨吴宓1943年8月15日记事:“……接陈寅恪八月四日桂林函,将于八月中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吴宓日记》第9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7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拨给10000元差旅费,⑩贾鹏涛:《陈寅恪由桂赴燕京任教旅费出处》,《文汇报》2018 年6 月11 日第2 版。12月28日到成都燕大报到。现存燕大1943年8月发给陈寅恪的聘书,10月29日陈寅恪预支10000元国币薪津单,12月30日预借米四斗半便条等图片。①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载《陈寅恪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第36-38页。关于燕大1942年8月聘请陈寅恪的具体细节,目下尚不清楚。根据傅斯年1943年11月26日回复燕大代校长梅贻宝函,可知燕大就聘任陈寅恪事与傅斯年进行了沟通。此时傅斯年改变了对陈不来李庄不满的态度,认为李庄条件太差,陈未必能住下。又因公职人员生活水准大幅度下降,傅斯年不仅不再坚持所内人员不得兼职的规定,还主动为他们联系职位,留下了较好的口碑。②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台北:学生书局,2012年,第303、308页。故傅斯年同意燕大暂聘陈寅恪,但一俟抗战结束,史语所仍要将他召回,此权决不放弃。傅斯年该函后半部分谈史语所语言组重要成员李方桂也接受了燕大的聘任,将离开李庄。傅斯年在信中与梅贻宝约定,李方桂以史语所与燕大合作形式到燕大工作,其薪俸仍在史语所支领,燕大付给李方桂兼课报酬。③王汎森等:《傅斯年遗札》第3册,第1457-1459页。梅贻宝函复:“寅恪先生事蒙鼎力玉成,方桂兄屈驾来燕大讲学,欣喜曷可胜言。承示条件,当全部接受。”④史语所档案,李67-1-2,李67-3-1,李13-2-2,京25-2-5,杂4-1。据此推断陈寅恪到燕大兼课,也是经过傅斯年同意的与李方桂一样的合作形式。1943年12月下旬,史语所致函燕大:“部聘研究教授陈寅恪先生拟改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全部待遇,惟其既在贵校任课,仍可援引本院定章在贵校领取兼课四小时不兼行政职务之各项待遇。”⑤史语所档案,李67-1-2,李67-3-1,李13-2-2,京25-2-5,杂4-1。
至此,陈寅恪不按傅斯年的安排到李庄闹的一场不愉快,随着陈的入川而消弭,两人又恢复了原来的关系,并没有像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的两人关系因此出现危机那样严重。而且傅斯年突破了史语所研究员必须到所坐班才发给全薪的做法,发给陈寅恪全薪,不再坚持纠结专职、兼职的界限了。
研究员与教授可以兼课但不能超过4小时是当时在中研院系统、教育部门通行的一项规定。⑥详见《抗战期中清华教工的服务与待遇》,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西南联大教授校外兼课规则》,载《西南联大史料》第4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2页。而燕大给予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等几位特约教授是月薪450元的待遇,超过燕大本校教授月薪360元的标准。⑦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载台湾《传记文学》1984年2月第44卷第2期。燕大1943年发给陈寅恪的聘书言明“月薪国币360元”,这只是底薪,另外还有生活辅助津贴、薪资加成、米贴等,由哈佛燕京学社支付。今存从1943年8月起至1944年12月陈寅恪五个月的薪资单图片,⑧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载《陈寅恪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第36-40页。其中月薪360元,生活辅助津贴380元,薪资加成2664元,米贴261元,合计3665元。实际每月所得不仅比聘书高出许多,还高出梅贻宝说的450元的待遇。可见教会大学的财力远胜于国立大学。陈寅恪以“兼课四小时”的名义享受燕大的全部薪津待遇,反映出抗战时期各校在执行政策时的灵活性。
1945年4月,陈寅恪作《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诗,中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之句。在燕大、史语所资料没有出现之前,不少研究者把“双俸”理解为部聘教授的正薪加研究费两项。现在看来,所谓“双俸”,就是支领两个单位发给的薪金。1945年6月5日陈寅恪致史语所函说:“寅恪自三十三年一月起所得本所之待遇自系正薪,在燕大只领兼课之待遇”。⑨史语所档案,李67-1-2,李67-3-1,李13-2-2,京25-2-5,杂4-1。
抗战时期,公职人员、教师生活水准大幅度下降,陈寅恪虽然享受高薪待遇,但一样困顿无奈,他致贫的主要原因是重病。1944年12月,陈寅恪左眼又失明(右眼视网膜早在1937年脱落)。目盲体弱,使他的经济雪上加霜,不得不四处寻求救济援助。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连篇累牍谈钱米药费救济补助问题。这从陈寅恪1945年1月26日致傅斯年函可以窥知当时的救助详情。⑩详见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载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05页。
在艰难困苦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珍贵图书资料丢失、视力衰退等困难,1941年初写成两部不朽的传世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定了他在中古史领域的崇高地位。在学术研究上,迎来出成果的第二个高峰期。顾颉刚认为:“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隋唐五代史研究,亦以其贡献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9、90页。
陈寅恪抗战前在西北史地之学和抗战期间在中古史这两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上的学术声誉。1944年7月,陈寅恪继被牛津大学聘任为汉学教授之后,由英国学术院三位院士陶育礼、汤因比、库克联名推荐,当选该院通讯院士。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库克是剑桥大学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牛津、剑桥的两位钦定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推荐一位中国学者,确实非同一般。陈寅恪因该项荣誉又接着于1947年4月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员,5月当选1946年度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②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 101页。
抗战期间,陈寅恪又获得一次大奖。1943年,其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教育部第三届“著作发明、美术作品”奖社会科学类一等奖(奖金15000元)。③详见《竺可桢日记》第3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59页;刘明:《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审查与激励办法》,《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1期。
这一时期,陈寅恪的学术头衔与学术成果同步而至。1940年4月,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第二届评议员,陈寅恪在历史组33名候选人中以最高票数21票初选入围,决选以22票(低于胡适一票)当选。④郭金海:《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 4期。今存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具名颁发给他的第二届评议员聘书图片。
1943年1 月,撤退到昆明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聘陈寅恪为通信研究员,今存聘书图片。1943年7月,教育部聘陈寅恪为第四届“史地委员会”委员。⑤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陈寅恪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第35页。
由于陈寅恪在八年抗战中艰苦卓绝,成就卓越,他以史语所研究员的名义与史语所张政烺、梁思永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⑥史语所档案,李67-1-2,李67-3-1,李13-2-2,京25-2-5,杂4-1。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疏散到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大学先后迁回原来的校址。陈寅恪于上年9月赴英伦治疗眼疾,如手术效果好则留在牛津任教。终因手术不理想,双目失明已成定局,只得于年底辞去牛津聘约,1946年5月底回国,在南京住了几个月。陈寅恪还在英国将要回国时,史语所、清华、燕大都想留住他。最后清华胜出,陈寅恪最终决定回清华。这或许与梅贻琦校长6月到南京两次拜访陈寅恪有关。⑦黄延复整理:《梅贻琦日记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232页。
1947年7月24日,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常务会议,决议第一批部聘教授五年任期已到期,一律续聘五年。⑧《学审会通过硕士论文及续聘部聘教授》,《教育通讯》复刊第3卷第20期,第30页。
1948年6月,刚刚上任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北上,⑨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册,第510页。到南开、北大、清华、燕大游说动员著名教授到岭南大学任教,并给予丰厚报酬。当时战事主要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地区,处于华南的广州相对比较安定,对急于躲避战乱的教授有一定吸引力。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打响。傅斯年与朱家骅紧锣密鼓实施“抢救北平学人计划”,安排陈寅恪与胡适、梅贻琦等25人乘坐两架飞机,于12月15日飞离北平,当晚到达南京。傅、朱等人亲到机场迎接。陈寅恪一家当晚在南京住下,第二天晚上乘京沪夜车赴上海。16日,国民政府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当天即致函中研院总办事处:“拟恢复陈寅恪君专任薪俸,希转呈院长总干事核准。”①史语所档案,李67-1-2,李67-3-1,李13-2-2,京25-2-5,杂4-1。而陈寅恪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后,最终决定南下,于1949年1月19日抵达广州,受聘于岭南大学。
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里,陈寅恪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升。1947年中研院筹备院士评选,他提交了两部隋唐史专著和1943年前发表的29篇关于西北史地之学和中古史研究的论文。推荐人胡适对陈寅恪最初的评语是:“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决前人未曾想到的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②详见夏鼐1947年10月23日记事,《夏鼐日记》第4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次年3月下旬,中研院在南京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选举首届院士81名,陈寅恪当选。
1948年9月,北平研究院在北平召开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推荐首届会员90名(“会员”即“院士”的另一种称谓),③刘晓:《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及会员制度》,《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1期;张培富:《北平研究院第一届会员分析——兼与中研院首届院士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陈寅恪入选。“院士”与“会员”均为终身名誉。至此,陈寅恪集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中研院院士、北平研究院会员于一身,学术地位达到了顶点,走在学人队伍的前列。
三
陈寅恪于1949年1月19日挈家抵达广州后,第二天《岭南大学校报》登载了他应聘到校的消息和简介:
陈教授为名诗人陈散原先生之哲嗣,曾在巴黎柏林各大学研究,精通十余国文字,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壮年即享盛名。民十五年,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本校王力院长亦出其门下),迄今共任清华教授廿余年。1942年由牛津大学聘为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终以健康关系归国。陈先生以史学驰名海内外,尤精通隋唐史。同时以家学渊源,又精于唐诗。且以精通梵文之故,又常讲授佛典翻译文学。其博学为学术界所公认。去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陈先生荣膺院士。④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0、22页。
这份简介除增加了牛津大学聘任教授、中研院院士两项荣誉外,仍保留了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那份简介中的一些关键词,放洋留学多年的经历和掌握多种域外语言文字始终是陈寅恪的得分强项。
1951年前,陈寅恪为岭南大学中文系、历史政治系合聘教授。他支两份薪金,正薪为工薪分数1000分,折合人民币旧币27万元或新币270元,比校长陈序经工薪还高,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校方还每月固定补助他100元,一直领了两年多。岭南大学的历史专业一向很弱,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学生很少,有两个学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听课,被戏称为“最高价的学生”。⑤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8、272、274页。
1952年9月,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中山大学合并,中大迁入岭大校园,陈改任中大历史系教授。1954年,中大定期补贴他医药费60元,到1956年他获得一级教授止。⑥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第248、272页。
1954年夏秋之际,中国社科院筹备成立“学部”,⑦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03页;《竺可桢日记》第9册,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页。1955年6月3日国务院公布学部委员233人名单,社会科学部61人。陈寅恪当选,每月领取100元津贴。同一年,陈寅恪还当选中国史学会理事。⑧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1956年7月,国务院先后下达《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等文件,高教部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制定出高等院校工资改革方案,发出《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员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将教授分为四级,工资分别为345、287、241.5、207元。陈寅恪评为一级教授(中大核心小组初评意见为“特级”),按地区差,月薪381(一说385)元,加上学部委员每月津贴100元,月薪达481元。①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第248、272、274页。这在当时教授中,已经是高薪中的高薪了。
1956年的教授分级,虽然主要体现在工资上,但实际上是学术水平的分级。对于广大教授群体而言,这是一项事关其“名分”和“地位”的重要认定。尤其是一级教授的评定,几乎个个都是知名的学术大师。无论从学术传统上还是教育体制上,对后世均有重要影响。能够跻身“一级教授”之列,离不开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人格魅力。正因为一级教授与学术成就有着天然的关系,因此,有人把它形象地称之为“学术地位的最高标尺”。②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中国历史评论》第2辑,2014年。有没有一级教授,成为某省某校学术水平的标志。有的省或只有一个,或一个都没有。③关于全国一级教授的人数,有研究者根据一些一级教授的回忆,只有56名。另有研究者根据档案材料考证,得出200余人的结论,见徐彬:《1956年一级教授评定之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不过,这次工资评定标准也有不足之处,如标准中反复提到的“特级教授”,在具体操作中由于不好掌握,实际上没有产生,无人享受这种待遇。作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史学权威和在全国教育界负有极高威望的老教师,陈寅恪完全符合“特级教授”的条件。中大初评陈寅恪为“特级”,后改为一级,可能是受全国高校都没有产生“特级教授”的影响。
在住房上,陈寅恪也受到中大的礼遇。其住宅为中大校园东南区1号,该楼两层,为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于1911年所捐建,故名“麻金墨屋”,原是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葛佩之住宅。陈寅恪一家居于该楼的二楼。虽然比不上以前在清华一家独用一栋的住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中大最高的住房待遇。
从1949年到1964年,陈寅恪经济待遇优厚,生活环境尚属稳定,是他取得丰硕成果的第三阶段。在南下广州的初期,他仍然在中古隋唐的历史文化领域内耕耘。1950年,将两年前由助手协助整理成书的《元白诗笺证稿》正式出版,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略论稿》合称唐史研究三稿。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恒慕义认为该书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仅对诗歌本身内容提出许多见解,亦揭示了文化史上不为人知的事实。④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134、 101页。此外,从1949年到1958年,陈寅恪发表了16篇关于中古史的论文。这是他晚年又一轮学术生命力的勃发,为他的中古史研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4年后,陈寅恪的治学重心转到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研究,到1964年,他在目盲体弱的身体条件下,尽十年之功,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名作。《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最后一部考察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的史实和当时士大夫道德气节的学术著作。在方法上,继《元白诗笺证稿》后把“以诗文证史”发挥到极致。该书涉及文献资料几百种,其中关于“古典”、“今典”的考证诠释极多,全部通过指导助手查阅资料、口述写作内容而成。严耕望先生概叹“这绝非任何并世学人所能做得到”。⑤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01页。
四
通过梳理考证陈寅恪的薪津待遇、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陈寅恪对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都具有强大吸引力,特别是他1939年被牛津大学聘任和1942年成为部聘教授后,名声大振,中国的高校都向他敞开了大门。凡他专职、兼职工作过的单位都以此为荣,充分显示了其学问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清华校长梅贻琦在1946年复员的开学典礼上和在《清华校友通讯》刊出的关于复员的报告中,格外提到陈寅恪能够留校任教,是清华的荣幸。⑥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13页。而史语所、燕大、岭大、中大对陈寅恪的尊崇礼遇,同样令人感动。
192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的月俸,教授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1929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官官等薪俸表》规定部长级月薪800元,副部长级400—600元。因此当时教授月薪与国民政府副部长级薪俸相等。1956年调整的一级教授的工资标准,也大体等同于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的工资,有学部委员身份的一级教授则与正部级基本持平。陈寅恪与其他著名教授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的高薪待遇,从经济的角度维护了学者的地位和学术的尊严,使各色人等不得不对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产生深深的敬畏。包括那个据说出自刘文典之口的“陈寅恪每月拿400元,我只配拿40元”和中大的干部群众将陈寅恪一级教授月薪381元戏称为“381高地”的传闻,都是世道人心的一种反映。
陈寅恪生长于一个累世书香的文化世家,在家塾里打下了中国文史之学的根基,又留学东西洋十余年,掌握了多种域外语文工具和新方法、新学理。他在中西会通的治学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学术科研,所以能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三十不立”,却一鸣惊人,“厚积”之后的“薄发”,往往底蕴深厚,更能站得住脚。而且终其一生,几乎一直走在史学的前沿。①刘晓东:《陈寅恪——一个教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严耕望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先生为巨擘”。②严耕望:《治史三书》,第171、101页。朱维铮认为陈寅恪去世前,始终是中国史学界的头号泰斗。③朱维铮:《陈寅恪论韩愈前后》,载氏著《走出中世纪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作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史学首席,陈寅恪一生位尊俸厚,学术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