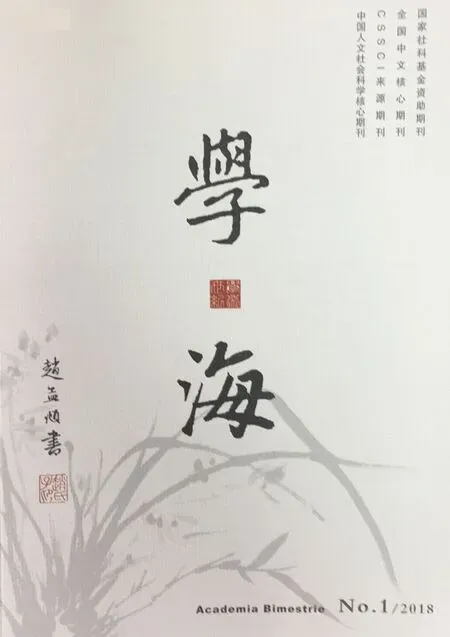迈向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
——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的若干争论及其超越
郭伟和
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进入了一个多元范式竞争的阶段(郭伟和,2014)。这种理论的争论一方面都借着实践有效性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却导致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实践专业日益脱离现实,难以回应社会问题,以至于美国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学会提出了需要面对12个巨大挑战(AASWSW,2016)。本文尝试总结出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的四对理论争执,分别是问题为本对优势视角的争论、技术性治疗策略对社会性干预策略的争论、实证主义对解释主义的争论、专业主义对本土经验的争论。本文认为这四对社会工作理论争论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工作学术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新问题。如何超越这些争论,真正面向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迈向实践导向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建设,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的若干争论
1.问题为本对优势视角的争论。2004年《社会中的家庭》(Family in Society)英文期刊刊登了一篇文章“结束社会工作的巨大争执:问题对优势”(Ending Social Work’s Grudge Match: Problems VS.Strengths)(McMillen, Morris and Sherraden, 2004)。作者认为,在过去15年内,美国社会工作界已经分化成一个人为划分的二分对立:一方面是优势为本、解决焦点、能力建设、资产创造、增强动机、增权等流派作为一个阵营;另一个阵营是问题为焦点的流派,包括证据为本的倡导者、实证主义者、健康产业(包括行为健康管理公司和第三方付费公司等)。这个二分对立模式,非常类似于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功能主义和诊断学派的争论,只不过伴随着社会工作的学术积累,当年功能主义和诊断学派的争论进化到问题为焦点和优势为本的争论。确实,当前北美社会工作理论界最大的争论就是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的争论。而这个争论主要是由优势视角学派发起的,因为问题视角本身是西方社会工作临床实践的主流,并不需要发起争论。按照优势视角的说法,问题为焦点的实践创造了一种不平等的专业关系,标识并责备当事人,强化了一种羞耻、罪责和牺牲者的思想;模糊了当事人的能力,制造了一种消极预期,忽视了案主系统的潜在资源,只注重个体问题,忽视了个体问题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只能提供临时的直接帮助,形成一种长期的依附关系等(Saleebey, 2006)。但是问题视角阵营对此并没有书面的反驳,只是在优势视角的人不在场时口头反驳,主要是认为优势视角的实践定义不清、和其他流派的差别并不那么明显,尤其是缺乏有效性证据(Staudt, Howard and Drake, 2001)。正如麦克米兰、莫里斯和谢若登等人所言,其实西方社会工作的传统和现实都需要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当事人,还是资助者都希望社会工作者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对问题的诊断和干预有着强大的社会背景和需求。而且社会工作专业一直就是强调人在情景中,强调案主本人及其周围世界存在潜能和资源,注重发挥案主的积极性,这一直都是临床社会工作的传统。所以,作者认为,这个二元对立状态是一个人为的区分,而且不利于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学习,让社会工作学生感到迷茫。实际上社会工作应该建立一个双重焦点的实践模式,以利于兼收并蓄,促进专业发展(McMillen, Morris and Sherraden,2004)。
2.技术性治疗策略对社会性干预策略的争论。在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中,美国两位社会工作学者形容美国的社会工作者已经是没有信仰的天使(unfaithful angles)(Specht and Courtney, 1994)。这本书中,作者敏锐地指出,最初社会工作无论是玛丽·瑞奇蒙德(Marry Richmond)开创的科学慈善组织运动,还是简·亚当斯(Jane Adams)开创的睦邻运动,都是注重社会改良,只不过一个偏重从家庭着手来改善穷人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方式;另一个从社区环境出发,来帮助穷人建立社区中心,培育基层组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但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工作对职业地位的追求,社会工作迅速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个人诊断和技术治疗,逐渐放弃了对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改良使命。幸亏二战后福利国家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社会福利系统,从而使其服务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之后,社会福利系统也开始一步一步地收缩和项目化运作,更加注重绩效评估和短期成效,而不重视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改良。这样,社会工作专业就更加放弃了其社会改良使命,埋头于向精神医学和心理辅导学习,成为一个次级临床辅导专业。但是,这个专业最初的起源带着社会改良和社会公正的使命,于是有人说这个追求社会改良的使命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活动一种说辞,并不落实在专业实践活动中(Olson, 2007)。
面对这种趋势,近年来许多人都提倡要恢复社会工作的社会面向,通过社会性干预来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公正的使命(Kam,2014)。当然如何恢复社会工作的社会面向,以及如何实施社会性干预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争议。西方社会工作对社会的理解向来偏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情景,它所用的一套分析框架基本上是一种微观互动理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关注比较少,只有少数社会工作流派强调社会倡导、社会增权、社会行动,推动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改革(Mullaly,1993)。香港学者甘炳光认为,社会工作应该通过六个S来恢复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首先要有社会关怀和社会意识;其次要把弱势人群放在首位;第三要把个人问题放在社会脉络里;第四是要进一步强调社会问题的社会建构属性,不要谴责案主个人;第五是要由微观的干预走向对社区环境、社会结构、社会政策和政治系统的干预;第六要始终把社会平等、正义、人权放在心中(Kam,2014)。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的社会性的理解也存在微观社会性和宏观社会性的分歧。陈锋和陈涛两位学者就比较强调社会工作的socialness(人际互动层面的社会交往),而不太强调社会工作的societalness(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认为如果过度看重社会结构和制度等抽象层面的社会分析和干预会导致社会性和专业性的冲突,他们试图用哈贝马斯的互为主体性这个概念来指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认为这个层面的社会干预本来就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陈锋、陈涛,2017)。但是郭伟和早期的研究则借鉴穆拉利的结构社会工作模式,强调把微观的增权、意识觉醒和组织化建设,与社会倡导行动链接起来,甚至可以和NGO组织结成联盟,来推动社会革新(郭伟和,2012)。总之,社会工作能否抵挡住市场化背景下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短期绩效考评压力,把眼光和精力由埋头于个人问题的技术性治疗上,抬头放眼一下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问题,似乎并不乐观。
3.实证主义对解释主义的争论。1915年,亚布拉汗·弗莱克斯纳在全美社会工作培训大会上发表主题发言——“社会工作是否一个专业?”(Flexner,1915),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激发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追求。从此,社会工作一直通过借鉴各类知识来发展自己的专业理论、建立专业方法技术、形成自己的专业组织和专业文化,寻求社会的认可(Greenwood,1957)。然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争议是,它到底是一种实证科学或理性技术,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或理解性能力?实际上,长期以来,社会工作内部的知识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如果硬要做出分类的话,才有了大卫·豪借鉴组织社会学家伯雷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社会理论划分框架,把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功能主义,对应的是修理工角色(The fixers);解释主义理论,对应的是意义寻找者角色(The Seekers after meaning);激进人文主义,对应的是意识提升者角色(The raisers of consciousness);激进结构主义,对应的是革命者角色(The Revolutionaries)(Howe,1992:50)。今天社会工作理论更加复杂多样,几乎所有社会理论和行为主义科学,包括哈贝马斯、吉登斯、布迪厄、福柯、巴特勒等人的前卫社会科学理论都已经进入了社会工作教科书(Gray and Webb,2013)。然而,当前在英美国家社会工作理论界争议的是,如此之多的理论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带来什么样实践效果呢?以及通过什么策略来证明社会工作有效呢?实证主义科学强调社会工作必须借鉴自然科学和循证医学,通过严格科学实验方法来检验其实践成效,用强硬的科学证据来指导其实践,发展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Gibbs & Gambrill,2002; Gambrill,2006; Macdonald,1998);而解释主义则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人文道德、政治实践,不能遵循自然科学的机械逻辑,把社会实践简化成一种技术治疗和行为改变,社会工作的实践证据应该更多地从实践过程中获得服务对象的主观表达,而不是进行外在客观指标测量(Humphries,2003; Webb,2001; Witkin and Harrison,2001)。
4.专业主义对本土经验的争论。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现代社会,并且秉持西方重要的基督教传统和乌托邦思想,强调通过助人自助来实现个人的福利改善和社会改良(Keith-Lucas,1972)。正如现代性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其他国家和社会扩散一样,后发现代化国家也面临着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相似问题,需要借鉴他们的现代专业方法和技术实现本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然而,社会工作专业内部的知识体系和方法技术充满了争议,它本来就是基于某个文化传统发展出来的一套社会问题干预策略,当然它也不断地吸纳现代实证科学知识来实现自身的转化和演变。当发展中国家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本国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时候,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并不能照搬一套实证主义的技术方法来产生神奇的效果(殷妙仲,2011)。而且,西方的职业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专业地位和专业自主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而是取决于和不同社会力量(主要是政府、学院和客户等几种力量)结盟的结果(刘思达,2006)。根据习近平2017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必须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结合中国的社会情景和社会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另一个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如何处理在服务对象、政府、资助方等几方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的专业自主性。正是因为社会工作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社会工作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不可能像精神医学和心理辅导一样是完全自治的专业,而是要在几方力量拉扯中建立一种准专业地位(郭伟和、郭丽强,2013)。
西方社会工作整合实践模式(通用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努力及其缺陷
面对社会工作领域的诸多分歧和争论,其实西方社会工作一直都在努力实现整合,以弥补裂缝,维持一个统一的专业形象。从20世纪40-50年代全国(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和全国(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以来,他们就力图把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发展整合起来,确定社会工作的共同基础。早在1945年,夏洛特·托儿就帮助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提出了人类共同需求的报告(Towle,1945),随后到1970年哈瑞特·巴特列特又提出社会工作实践的共同基础的报告(Bartlett,1970)。在20世纪60-80年代,系统理论(Hearn,1969)和生态理论(Germain and Gitterman,1980)进入社会工作,成为整合社会工作实践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教科书把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个折中的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作为通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Johnson,1998)。通过西方社会工作建立专业共同理论基础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社会工作专业必须保持两个焦点,把个人问题的解决和环境的改善作为共同基础,而不能仅仅根据个体心理学去发展对个人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技术,还要考虑社会环境问题以及相应的群体工作和社区组织发展的干预策略(Johnson,1998:84)。
第二,社会工作专业始终是实践导向和解决问题为本的,所以各种理论的借用都是为了确定如何对实践情景进行界定,以及如何发展出一套解决问题的过程模式。最初是从共同需求出发,包括物质需求、精神发展、社会交往关系和灵性需求等作为社会工作实践整合的基础(Towle,1945)。后来发现,社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简单地靠一种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就能解释清楚并加以解决,还有资源分配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所以系统理论就进来,试图通过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理论来解释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寻找干预的焦点(Hearn,1969)。于是,社会工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思路,用一种社会多元互动分析框架(transactions)作为通用社会工作分析问题和寻找干预焦点的理论基础(Johnson,1998)。
第三,为了强调其实践干预属性,社会工作理论又不能仅仅提供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还要发展出来一个行动过程模式,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工作理论一直注重提炼和概括专业实践行动的过程模式和干预手段的工具库(Compton and Galaway,1979)。现在基本上流行的主流模式是整合了海伦·珀尔曼(Helen Perlman)的问题解决模式和丹尼斯·萨利伯(Dennis Saleebey)等人的优势视角,作为一种流行的框架(Guo and Tsui,2010)。也就是沿着实践干预的步骤,先对案主进行接待,处理一下情绪焦虑等问题,然后和案主共同探讨问题的属性、成因和历史过程以及当事人的看法和反应策略等,再接下来就是共同约定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和计划,以及社作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角色分工。而在干预行动中通常的干预手段并不是社会工作者直接包办问题,而是促使案主发挥积极性来尝试探索不同的行动方式,打开问题的死结,包括改变当事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及干预当事人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和某些具体的政策制度,实现当事人和环境的功能适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结束的时候,评估一下整个解决问题的客观效果和当事人的成长改变,让当事人更加积极地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
然而,主流的西方社会工作通用实务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其价值使命一直都是二元焦点,既要关心个人功能性问题,又要关注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而其采用的核心分析框架却是一种保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虽然西方社会工作教科书并没有直接用这个词,而是采用生态系统理论的说法)。这势必导致其实际行动导向只能围绕着个体功能性问题进行改良和安抚,最多加上所谓的调动案主的潜能和优势,发挥其积极能动性,参与到个人功能问题的行动过程,很难真正改变社会环境和政策制度问题。这个整合通用模式显然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模式,难以整合起来微观治疗流派和宏观行动流派的分歧,只能任由两个社会工作实践流派各自发展各自的方向,相互打架。所以,到今天,国际社会工作理论界一方面试图通过临床干预的实证主义研究来证明其微观治疗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不断地有人从社会工作的原初使命和社会正义出发,质疑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从根本上来说,导致社会工作实践流派难以整合的原因是其使命、理论和实务模式三者关系的内在不一致。一个有着高尚理想情怀的专业,却配置了一个相对保守安全的理论内核,进而难以整合实践流派的分裂和冲突。当然如何解决这个内在分裂和冲突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听任社会工作理论的争论,丢掉那些遥远的和背景性的理论,集中在具体的行为决策模式上,一切靠证据说话,发展一种证据为本的实践策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思路,具体来说就是一种行为主义科学思路,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具体的行为问题,通过可行的操作化指标来检验哪种行为干预措施有效(Jaccard,2016);另一种是价值导向的解释主义专业实践,社会工作必须围绕着其价值使命,来发展相关理论和专业方法,因为如何定义证据、选择证据和使用证据,背后都充满了价值和理论争议,所以必须进行主观解释和对话(Humphries,2003)。
本文并不想在实证科学的专业实践模式和价值负载的解释主义专业实践模式之间分出高下对错,而是试图跳出这个争论,回到实践理论本身,借鉴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看看是否可以真正从实践出发,来解决客观的实证主义和价值负载的解释主义之间的争论?
找回实践理论
目前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在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和价值负载的解释主义之间争执,都忽视了对真正实践概念和实践理论传统的梳理和深入讨论。这个状况正在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并试图改变之。芬兰、丹麦、挪威、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家的一些社会工作学者发起了一个实践研究创新网络小组,他们在2008年的英国南安普顿的萨利斯伯瑞召开了一个论坛,形成一项有关实践研究的萨利斯伯瑞声明(Salisbury Statement),并在《社会工作与社会》英文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论文。尽管它声明并不存在实践研究的共识,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研究的方向,既不同于之前的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模式,也不同于之前的解释主义模式。萨利斯伯瑞声明中的实践研究强调,“实践研究包括对实践的好奇心。它是关于发现助人的好的有保证的方法的研究。它是通过对实践的批判性检验和在经验中发现新观念来挑战那些引起麻烦的实践。它是一种和实践者合作的研究,认为实践者和研究者一样可以向对方学习。它是一种包容性专业知识的发展策略,也就是关注理解实践的复杂性,并且认同增权以及通过实践来实现社会正义”(Salisbury,2011:5)。
我们发现萨利斯伯瑞声明对实践研究的定义其实是回到了实践过程本身的特征,那就是实践过程的复杂性、互动性、反思性和投入性。然而,实践过程其实是分层次的,首先是布尔迪尔所说的实践意识的即兴发挥特征;其次才是实践过程的反身觉识的可能性。正像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实践理解的原则不是一种认知的意识(一种超验的意识,如同在胡塞尔那里,甚或一种存在的此在,如同在海德格尔那里),而是习性的实践意识,这种实践意识建构世界并赋予世界以意义,习性被它居住的世界占据,被它在其中实施干预的世界预先—期待,习性在这个世界中通过一种介入、紧张和关注的直接关系积极地进行干预。”(布尔迪厄,2009:166)布尔迪厄对实践意识的定义是通过习性来说明的,而习性则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里通过塑造而形成的个人结构化的配置(disposition)(布尔迪厄,2009:162)。它会跟随实践进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这个世界,并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处于一种紧张和高度关注的状态,而不是经院哲学中的慢悠悠的思考,像放电影一样把整个实践过程全景式地反复轮回播放,发现一种最佳的策略,那就会失去行动的时机。因此,这样的实践是一种身体化的即兴发挥,它根据实践情景的任务要求,按照之前形塑的身体习性化配置做出及时反应,而且正常情况下应该能够恰当地反应,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phronetic),它并没有明确的系统逻辑,而是恰如其分地做事情的方式(亚里士多德,2007:246)。
实际上布尔迪厄的实践观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或者说默会知识,都把一种近似自动化而又恰如其分地“做好事情”当作研究的焦点。这既不是实证主义理性观所认为的理性逻辑,也不是价值负载的解释主义所说的意义之网的理解和融合。实证主义的理性逻辑必须要对整个情景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掌握足够的信息基础上,逐一通过控制参照系数,来检验哪个变量是最佳变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价值负载的解释主义所提倡的批判诠释,同样需要人们放弃日常生活的紧迫任务,在一种理想的沟通情景下进行协商谈判,达成共识;或者如早期文化解释主义者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把一种日常生活的斗鸡活动当成文本进行厚描,来发现文本的背景含义和符号意义。布尔迪厄认为,不管是实证主义理性思维,还是解释主义的人文情怀都是一种经院哲学,而经院哲学的认识论本身就是来自其特殊的社会位置和对应的个人配置。他们不需要投身紧张而迫切的日常生活,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来悠闲地发展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以经院学派的认识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俯瞰式的反思回观或者通过控制环境下的实验发现一些理性规律,然后把这个理性的逻辑强加给实践,而不是发现实践的逻辑(布尔迪厄,2009:53-54)。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实践模式,布尔迪厄也认为实践逻辑是一种模式转换基础上的类比实践。“这种模式转换是以一致确认的等价为基准实现的,为替换性和一种行为替换另一种行为提供了便利,并且有助于通过一种实践的普遍化,支配所有可能被形势提出的同样问题。这种对多义性、含混性、模糊性和近似性的妙用,以及这种使得由或多或少被证明的一种亲缘关系连在一起的各种实践具有连贯性的艺术。”(布尔迪厄,2009:58)
这样的一种实践意识和实践逻辑给人一种宿命论的感觉,个体习性(通过结构性空间制造的配置)和社会空间的位置结构是一致的,因此个体的实践行动就是一套近似自动化的即兴发挥,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把日常生活的常规情景要求的行动模式操演出来(performance),他的行动模式和他所在社会场域的结构位置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很少出错或者失效。除非面对社会转型或者个人的社会迁移,更改了自己熟悉的社会空间和结构位置,那么他/她原来积累的实践智慧就会失效或者作废,并发现自己无所适从,笨手笨脚,需要重新学习在新社会空间中的新结构位置上的行动配置。如此来看,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除了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空间结构下的行动习性的特征以及如何积累局部有效的实践智慧,进而洞察社会结构的支配模式之外,并不能为个体解放和社会转型提供什么指导。因为他过度看重个体身体化配置和符号体系运作的无意识操演的默契配合,被人批判根本无法再发现解放和改变社会结构的可能性(Burawoy,2011)。在布洛维看来,个体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默契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耦合性的社会情景,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借助于意识形态运作导致的一种神秘化机制(mystification),而不是借助于身体习性来运作的无意识的认可机制(misrecognition)。这种神秘化支配机制并不是不可以突破的,借助于反身批判和相互对话,人们可以突破社会结构通过符号体系制造的习以为常的支配关系(Burawoy,2011)。
反身性专业实践作为超越争论的可能性
实际上布尔迪厄的理论并不是像迈克尔·布洛维批判的那样不存在解放的可能性,他只不过是认为社会结构制造的身体化习性配置对社会结构的误识机制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反省觉悟就可以实现突破和解放。这就需要认真审视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关于反思性的双重观念。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着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认为所有的经院哲学思维模式,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解释主义,都是一种脱离日常生活实践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所追求的批判性理性思维或者反思性主体都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个体习性配置,这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习性配置存在着种属差异(华康德,1998:42),并不能给日常生活实践带来什么改变;另一方面他又提供了一种摆脱这种虚假的反思性主体的可能性,它只能依靠日常生活本身产生的客观社会结构提供的机遇和人们的主观希望之间不匹配,进而产生日益增多的社会紧张和沮丧,给客观社会结构带来一种不确定和危机的状态,那么就提供了产生颠覆性话语和行动的社会基础,这些颠覆性的象征性行动慢慢会导致个人批判性觉悟的发生(布尔迪厄,2009:279)。也就是在布尔迪厄的论述中,有两种反思性,一种是经院哲学知识活动中的纯粹思想主体的反思性,另一种是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空间及其塑造出来的主观思维模式之配合模式的批判反思(布尔迪厄,2009:136-139)。他甚至把这个基于社会实践空间结构和行动习性之匹配关系的反思性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提倡另一种反思性社会科学。根据他和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的对话,他所倡导的反思性社会科学,和其他经院哲学认识论提出的反思性不同,他的反思性社会科学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和特定方式的反思性观念,按照这一观念,反思性既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而且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反思性即是一种视知识分子为占据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纵者的理论”(华康德,1998:40-41)
布尔迪厄的这个区分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理论是有极大启示性意义的。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界存在的实证理性主义和主观解释主义,是一种超然于案主生活世界的专业场域中的专业人员知识创造之间争论,他们都共享着批判反思的理性主体习性(配置),也都共处在社会权威部门授权的专业人员所在的专业场域的社会位置(一种被支配地位的支配位置),从而使他们能够借着权威部门授权的助人专业身份,来全方位地研究案主的问题及其行动可能性。然而专业场域结构产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主体习性(配置)和案主的日常生活场域所产生的实践任务的紧迫性及其要求的行动反应并不一致。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基于实证主义实验研究的有效变量强加给案主,要求其理性行动;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其主观习性的反思性关注,概括出一些意义模式,仅仅理解生活的苦难。这些都不能帮助案主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每个案主都是一个理智的行动者,要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产生一套解决问题的行动智慧,只不过可能因为社会变迁或者个人流动,导致原来积累的实践智慧变得失效或者过时,需要学习新的应对策略。这需要对整个新的场域结构及其对应的行动模式的不断操演,但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足以对社会变迁以及对应的行动习性和时机把握都掌握吗?如何突破两种场域结构、两套主体配置之间的种属差异,真正让社会工作专业成为一种帮助他人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呢?
我们不妨也参考一下布尔迪厄对于学术研究场域和研究对象世界之间的差异如何消除的建议。他认为作为一种反思性社会科学要做到的“恰恰在对象构建工作中,所必须不断地予以详查探究和中立化的,正是深嵌在理论、问题和学术判断范畴之中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反思性的主体最终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华康德,1998:42-43)。也就是说,布尔迪厄认为,反思性不能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反身回观,作为获得主体性和客观意识的手段,而是要对产生这种高贵而悠闲的主体意识的社会科学场域实践模式给予反思,从而打破知识分子的超然地位和理智主义主体模式,真正进入研究对象的场域世界,从他们的位置出发,学习他们的行动策略和行动时机的把握,总结他们的实践逻辑。
实证主义和主观解释主义这两种认识论的分歧都以一种批判反思的主体性为前提,都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居高临下的系统控制实验或者全面经验反思,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种上帝式的普遍性知识或者普遍的意义之网,但是极少能够贴近案主的生活世界,给他们以实际帮助。所以社会工作专业要反思的不是案主的经验问题,而是自己如何操纵一套学院派的思维模式来支配案主的生活世界。只有放弃了学院派认识论的支配方式,才能进入日常生活场域,根据案主的生活实践场域结构特征,来协同他们反思自己的实践意识和实践逻辑的有效性。
这是不是说社会工作者要放弃自己的学术训练,变成一个普通人才能体会常人生活的逼仄和紧迫,寻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和办法呢?也不尽然,毕竟社会工作者在学院里的专业训练给他们提供了一套了解社会结构及其和主体行动习性之间结合关系的知识体系,而且实证主义研究虽然不能直接运用于某个具体场景,但是毕竟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条件下的变量之间的普遍逻辑关系证据。这些客观的抽象知识或者主观的意义理解技术都是进入专业实践的装备。重要的不是抛弃这些装备,而是抛弃一种学术场域塑造出来的无意识的专业支配关系。一旦进入实践情景里,就要本着一种谦逊的合作态度,跟随案主的生活世界事件之流,来一起探讨做出反应的策略,把一种本来是即兴发挥的身份化的行动策略,转化为可以进行选择和重组的另类可能性。尤其是在客观场域结构出现危机,原来构造的行动习性失效或者不匹配时,更要引导当事人来反思其行动习性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去学习新的行动模式,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暴力、破坏等负面行动来发泄愤怒。
幸好,沿着这种方向,有些学者提出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能力的知识问题,简·福等学者在继承了人工智能研究学者柯林斯(H.M.Collins)的知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处境依靠的专业知识发展理论。柯林斯提出一种知识论包括了四类知识:第一种是事实性知识,第二种是程序技术性知识,第三是常识性知识,第四是文化知识。柯林斯认为前两类知识都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自动化运用,但是后两类知识则需要通过实践体会慢慢成为一种默会的实践智慧,而不能全部的程序化(Collins,1990)。简·福等人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把普遍性的知识和启发性的技术,结合到具体的场景里,获得一种处境化应用和转换的能力,这样才能发展成为一个专家型人才(Fook, Ryan & Hawkins,2000)。对场景的敏感和熟悉需要慢慢来培养一种对特定处境的常识和文化的自觉能力,然后去和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对话,转换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结合到一种有着社会常识和文化背景的场景里去。这种处境化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机械地背诵知识和反复熟练地掌握一种技术就可以实现,那最多成为一个经验熟练的技术工,而是需要借助于唐纳德·肖恩的情景反思和框架实验方法,让学生增加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把握能力和转换能力(Schön,1983)。
1.陈锋、陈涛:《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2.郭伟和:《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觉醒与行动:公平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以建筑业农民工社会工作为例》,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郭伟和、郭丽强:《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广大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专业社会学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
6.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7.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王旭凤、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9.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Gr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Work: Ensure Heathy Development for all Youth [Web Page]. Retrieved from Http://aaseswsw.org/Grand-Challeges-Initiative/21-challenges/ Ensure Heathy development for all Youth, 2016.
10.H.Bartlett, “The Common Bas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70.
11.B.Burawoy, “The Roots of Domination: Beyond Bourdieu and Gramsci”,Sociology, Vol.46, No.2(2011), pp.187-206.
12.G.Burrell and G.Morgan,SociologicalParadigmsandOrganizational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1979.
13.H.M.Collins,ArtificialExperts:SocialKnowledgeandIntelligentMachin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14.B.R.Compton and B.Galaway,SocialWork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ress, 1979.
15.A.Flexner,IsSocialWorkaProfession?ProceedingsoftheNationalConferenceofCharitiesandCorrectionattheForty-secondAnnualSessionHeldinBaltimore, Maryland, Chicago: Hildmann, 1915, pp.576-590.
16.J.Fook, M.Ryan and L.Hwakins,ProfessionalExpertise:Practice,TheoryandEducationforWorkinginUncertainty, London: Whiting & Birch Ltd, 2000.
17.E.Freidso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rofessional Control”,AnnualReviewofSociology, Vol. 10, 1984, pp. 1-20.
18.GUO,Wei-he and Tsui, Ming-sum, From Resilience to Resistance: A Reconstruction of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InternationalSocialWork, Vol.53, No.2(2010), pp.233-245.
19.A.Keith-Lucus,TheGivingandTakingofHelp,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
20.Kam, Ping Kwong, “Back to the ‘Social’ of Social Work: Reviving the Social Work’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SocialWork, Vol.57, No.6(2014), pp.723-740.
21.E.Gambr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policy: choices ahead”,ResearchonSocialWorkPractice, Vol.16, No.3(2006), pp.338-357.
22.C.Germain and A.Gittman,TheLifeModelofSocialWork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L.Gibbs and E.Gambr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unterarguments to objections”,ResearchonSocialWorkPractice, Vol.12, No.3(2002), pp.452-476.
24.M.Gray and S.Webb,SocialWorkTheoriesandMethods, London: Sage, 2013.
25.E.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SocialWork, Vol.2, No.57(1957), pp. 45-55.
26.G.Hearn,TheGeneralSystemsApproach:ContributionsTowardanHolisticConceptionofSocialWork, New York: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69.
27.D.Howe,AnIntroductiontoSocialWorkTheory:MakingsenseinPractice, Aldershot: Ashgate, 1992.
28.B.Humphries, “What else counts as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SocialWorkEducation, Vol.22, No.1(2003), pp. 81-91.
29.J.Jaccard, “The Prevention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ofSocietyforSocialWorkandResearch, Vol.7, No.4(2016), pp.585-613.
30.L. G.Johnson,SocialWorkPractice:AGeneralist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31.G.Macdonald, “Promo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child protection”,ClinicalChildPsychologyandPsychiatry, Vol.3, No.1(1998), pp.71-85.
32.J. Curtis McMillen, Lisa Morris and Michael Sherraden, “Ending Social Work’s Grudge Match: Problems VS. Strengths”,FamilyinSociety:TheJournalofContemporarySocialService, Vol.85, No.3(2004), pp.317-325.
33.R.Mullaly,StructuralSocialWork:Ideology,Theory,andPractice,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3.
34.J.J.Olson, “Social Work’s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Justice Project: Discourses in Conflict”,JournalofProgressHumanService, Vol.18, No.1(2007), pp.45-69.
35.D.Saleebey, “Introduction: Power in the People”, in D. Saleebey (ed.),TheStrengthsPerspectiveinSocialWork, 3rd edn,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2006, pp.1-24.
36.Salisbury Statement,SocialWorkandSociety, Vol.9, No.1(2011), pp.4-9.
37.H.Specht and M. Courtney,UnfaithfulAngels:HowSocialWorkHasAbandoneditsMiss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38.D.Schön,TheReflectivePractitioner:HowProfessionalsThinkin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39.M.Staudt, M.O.Howard & B.Drake, “Operationaliz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trengths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JournalofSocialServiceReview, No.27(2001), pp.1-21.
40.C.Towle, “Common Human Need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45.
41.S.Webb,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validity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 Vol.31, No.1(2001), pp.57-79.
42.S.Witkin and W.Harrison, “Whose evidence and for what purpose”,SocialWork, Vol.46,No.4(2001),pp.293-299.
——认知行为治疗介入精神障碍康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