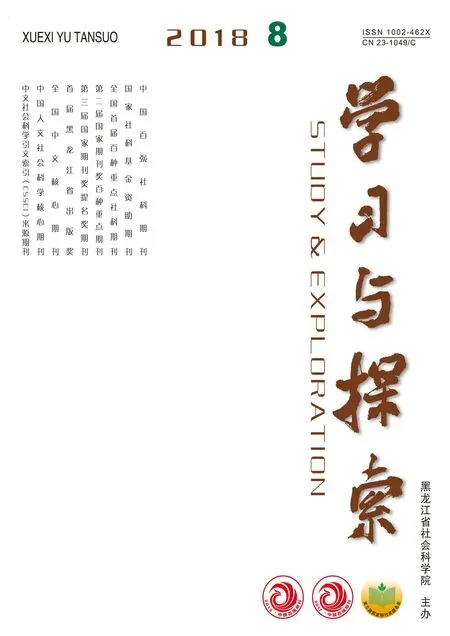都市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城市问题
车玉玲,宋 杰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在当代,全球“超大都市”不断涌现,城镇化浪潮也如火如荼,人类居住分布日益趋于城市化。世界城市居民在2008年首次超过农村居民,预计至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0%。据统计,至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过半,达到57.35%,城市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活空间,城市社会正在崛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城市从未像今天这样飞速地扩大为“超大都市”。列斐伏尔在1970年出版的《城市革命》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与延续的时代,即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他用“城市时代”来称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并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城市化。
那么,城市飞速发展的内驱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都市是现代性进展的成果,同时,现代性也是城市发展的内驱力。然而,仅仅从这一方面来解释近几十年来全球城市的疯狂增长并不够。为此,只有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才能更为深入地说明人类历史的这一深刻转变。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当代城市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共鸣,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剖析当代城市,才能更好地说明与抓住根本问题。可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以往的文化批判转向了都市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批判是以“城市空间生产”为基础展开的。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人为代表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者们,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把当代都市问题与资本积累直接因果关联。对此,哈维明确指出:“肆虐的资本主义开发已经摧毁了传统城市,过渡积累的资本不顾社会、环境和政治后果,无休止蔓延的城市增长。城市成为永无止境地消化过渡积累资本的受害者。”[1]前言ix概言之,城市问题的根本在于资本积累。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分析资本特性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运行逻辑,才能理解都市的增长与城市问题。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批判的最终目标就是寻找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本文探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在这一方面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了“城市权利”与“都市革命”,并力图构思与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城市日常生活。
一、过度积累与空间修复: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代途径
我们知道,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积累。过度积累一直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根源,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困扰资本主义。哈维直接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当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数量不断增加,却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时,危机就发生了。”[2]换言之,“资本剩余”如何被盈利性地吸收与转换,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在商品能够顺利流通与循环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的。当资本积累过度,剩余资本不能被有效吸收时,资本主义就会寻找新的出路来缓解这一矛盾。资本就会转向哈维称之为的次级循环,即投入到固定资本,包括生产与消费的建筑环境,如城市交通、住房等。“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认为,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力的关键手段。”[1]43固定资本的投入实际上是利用“时空上的转移”将资本积累寄托到未来的收益上。生产与消费的建筑环境投资较大,单个资本家将资本转向次级循环是较为困难的,所以常常是通过金融和国家机构及信用体系中的虚拟资本来完成的,即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
但是,通过未来时间的补救方法只能暂缓危机。固定资本投资也有自身矛盾,“为了克服空间障碍,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结构被创造出来,但它们自身却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3]具体而言,最初的城市建筑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剩余,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距离,加速了资本的有效循环。也就是说,通过改善交通环境,加快商品的运输,缩短了资本循环周期。然而,城市环境建筑不但建筑周期长,取得收益较慢,而且作为固定资本具有周期性贬值的特征。城市建筑空间具有非流动性,在某个特定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资本按照自身要求建筑了一个城市空间景观,又不得不在特定时刻摧毁它。例如,交通方式与商品形式的变化要求城市空间建筑重建。具体而言,在发展中逐渐出现了汽运、火车、空运和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商品形式与性质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商品适用不同的运输形式,在信息化的时代很多商品则无须运送。当主导性商品和运输方式变换时,比如说信息产品替代实物产品成为主导商品时,原有的城市交通与空间环境就不再有利于商品的流通。特定时刻城市建筑作为非流动性的固定资本,面临的是要么破坏性重建带来价值丧失,要么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
纵观资本自身的发展史,自1970年后,资本主义进入到空前稳定的阶段。资本主义的丧钟在鸣响了150多年后,反而进入了一个繁荣而稳定的时期,对此,如何进行解释呢?当代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认为,自1970年后资本找到了新的路径即“城市空间生产”,“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4]在当代,城市空间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把此称为“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他说:“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5]虽然空间修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剩余的问题,但却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具体而言,城市空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增值途径,并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一,空间商品化。城市空间建构不仅具有固定资本的性质,而且空间本身也成为商品,如房产炒作就是对城市空间的商品化。这一变化使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逐渐被交换价值掩盖代替。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以使用和使用价值为特征的古代传统城邑被瓦解了,城市由作品变成产品,交换价值成为主导。
第二,空间重组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城市空间的公共设施如机场、地铁、商场、学校、医院等的整合与规划,会提升作为商品空间的交换价值。在当代,我们不难发现,公共设施优质和完备的地方其空间产品价格要高些。如房产价格与周围的空间结构的变化存在莫大关联。
第三,通过空间生产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维持了资本主义秩序。城市空间的结构安排了人的生产、生活秩序,城市的物质建筑反映了城市中人的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政治性“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6]37。通过城市规划在空间上分离出等级来监管,如富人区与贫民窟、高档餐厅与平民餐馆等。不仅如此,城市的规划还重新分配了工人工作地点,工人变得更加离散和流动,削弱了具有反抗性的阶级力量。“政治力量从控制不安稳人群的角度出发,常常寻求重新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生活。”[1]43此外,城市空间生产中还出现房地产开发商等新富阶层与一批新的城市赤贫阶层。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生产不仅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且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秩序。
第四,“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由于交通和通讯等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的障碍基本消除,投资、生产、消费几乎可以在全球不同的空间内完成,哈维称之为“时空压缩”。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地理发展的不平衡,通过空间资本开拓了“殖民地”,从地理空间上扩充了资源、拓展了吸收剩余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与政治化的生产,为资本积累找到了新的途径,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社会秩序,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
二、远去的初衷与异化的城市
在城市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回望初衷,或者说,理论应该不断地追问“城市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提醒现实走在客观而冷静的道路上,不至于迷失方向。然而,在当代,当城市空间成为消解过渡积累的工具、成为资本增殖的载体之时,城市发展的初衷已经发生改变。城市本身作为可以被消费与买卖的商品生产者,“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7]这个城市的形象是以资本与商品的需要为尺度而建造出来的,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与空间存在的多种意蕴逐渐被平面化,生活于其中的都市人的生活必然也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都市中,看似一派繁荣,实际却蕴含着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危机。不仅城市中的文化与活力丧失,而且城市空间缓解过度积累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其也遭遇到自身的界限,并且带来一系列城市问题。
资本逻辑遵循利益最大化,资本控制下的城市规划常常经过理性化的精确计算,由此设计出来最符合收益的方案。城市空间的建筑是为了资本增殖以实现积累,并不是为了人的需求。可以说,城市空间在资本的控制下规定了人们的生存模式。城市空间对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娱乐和思想等几乎都给予了安排与规训。如城市空间中的交通方式,住宅、商业和办公建筑的格局,娱乐场所与娱乐方式,城市中的大小广告牌向我们传递的信息,等等。在资本控制的城市空间中,城市中的人被异化了,而城市本身也未能得到幸免,由以往的“意义”城市变为冰冷的庞大的“商品”城市。资本逐利的要求,使城市不断向外扩张,越来越多的大都市涌现出来。但是,这几乎没有带来城市的多样性。城市空间在资本的统一原则规划下,发展起来的城市千篇一律,如相似的交通、住宅、办公楼、商业圈和娱乐方式等。这种城市空间同质化发展吞噬了多样性的城市文化、地方习俗和价值观念。昔日具有向征意义与文化特色的建筑被大量破坏。城市展现的不再是人的意义活动,而是资本的逻辑。以往的“意义”城市逐渐被“商品”城市所代替,即城市由“作品”变成了“商品”,失去了“意义”变得冰冷。可以说,在资本控制的城市空间中,城市与城市中的人都是异化的。
这种资本控制下的“异化城市”产生了诸多问题,给人带来了新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市空间与人口膨胀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在资本逻辑原则下,城市空间最大化利用,不但使得高楼大厦四处林立,而且建筑高度不断增加。城市的发展不断向外扩张,人口的密度也不断增加。城市变得过于庞大,变得喧闹拥挤,造成了交通拥堵,教育、医疗资源短缺,引发了犯罪等社会问题。
第二,人与自然相分离,喧闹的城市隔断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人的全部活动与需求几乎都纳入到城市空间中,如办公室工作、去健身房锻炼、去电影院和游乐城娱乐、到商场与超市购物、去餐厅用餐,等等。人们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着,成为被城市圈养的动物,人与自然应有的有机联系被隔断了。
第三,人与人的交往空间缺失,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主导。资本化的空间侵占了大量的公共空间,人们失去了在公共场所休闲与交流的机会。休闲与交往方式常常变为在消费空间的交际。资本逻辑规划的生活让人们奔波于金钱和利益之中,人的交往变为物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更多地是冰冷的利益关系。
第四,人的精神焦虑。资本塑造同质性的城市空间导致了当代都市人的统一生活模式,人们虽身处不同的城市,却很少感觉到新奇与陌生。人生存空间的差异性逐渐被消除,在同一化的城市空间中,人变得片面化与单向度,失去了自身存在多样化的总体性。同质与单面的城市生活阻碍了人的创新与激情。正如哈维所说的,“旧巴黎不可能永远存在,而新巴黎似乎太可怕了,没有灵魂,也没有思想。”[1]前言ii在长期乏味单一的生活中,人的创造力无处释放,变得没有活力与生机。冰冷的金钱与建筑冲淡了人的情感,生活的意义变得匮乏。在创造力与情感的压抑下,人们倍感焦虑。
另外,资本主义虽然借助城市空间得到新的发展,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和矛盾,不可能无限地一直发展下去,其会引起新的危机。城市空间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有限性之间。列斐伏尔将城市定义为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没有中心,就不会有都市存在,这涉及商业中心、符号中心、信息中心、决策中心,等等。”[6]55构成性中心就是聚集、集中和共时代的形式。城市构成性中心常常是集中一切包括财富、权力、文化等于一体的中心,如法国巴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代表。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将城市等同于构成性中心,而构成性中心不可能一直无限发展下去,终于会走向自我瓦解。资本逻辑之下必然导致城市过度发展,发展过度就会导致匮乏,如优质的空气、水、石油、煤炭,方便的贸易环境等变得匮乏,这些都是构成中心衰亡的因素。在大都市中,历史好像魔术师一样,曾经极度匮乏的食物在今天极大丰富,而曾经廉价且极度丰富的自然、空间、水、阳光等在今天则成为新型的匮乏。这些生存必需品的匮乏与高成本,将导致大都市自身的衰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郊区化、老城的破败与瓦解等。资本主义通过城市空间维持经济与社会秩序,然而,随着城市中心的发展、饱和与瓦解引发了“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城市危机。“郊区繁荣,而内城却停滞或衰退。白色人种的工人阶级兴旺了,然而,受到影响的内城少数民族,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却没有兴旺起来。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内城动乱,包括底特律和沃茨。……最终积累成为美国40个城市自发暴动。成为有目共睹且不难给命名的‘城市危机’。”[1]52资本化的城市空间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等级关系,当城市空间瓦解、“赤贫”阶层被抛弃之时,反抗的声音就尤为响亮。
可见,城市空间的发展并不是无止境的,当它达到某个阶段时就会自行走向衰亡。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曾经预言了城市发展的历程,他使用“胀破的城市容器”来形容城市的这种状态,把这种城市的终极状态称为“废墟城市”。当城市达到饱和状态时,资本将会向其他新的空间转移,利用城市空间实现资本增殖就是依赖于空间的差异性,资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空间,进行城市的同质化发展与建设。但是,这种城市空间发展得越快,城市空间资本化的限度就越快地到来,当空间的差异化完全消失,城市空间资本化的道路就达到了它的限度。城市按这种资本逻辑发展下去,最终人类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座座庞大的废城,并且由于资源的耗尽引起生态性的灭亡。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观点,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相关,城市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引起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为达到增殖的目的,就要不断地重建与扩张城市空间。与此同时,城市建设与维持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排放大量的废弃物,如城市建设中需要的钢铁、木材等,维持城市生活的水、电等,毫无节制的城市化发展最终将这些资源消耗殆尽。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诸如废气、污水等的排放给自然造成了严重污染。过度的消耗与污染使地球难以负重。当前,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与资源之间始终无法克服的矛盾。
最后,城市空间与金融、信用制度等的联合发展,使贪婪的资本还未达到自身限度就提前产生了危机。2008年,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具体来说,城市空间作为资本增殖商品相对其他商品而言,它的生产周期比较长,迟缓的生产供应与需求很难同步。当需求上升时,很难产生相应的供应量,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刺激投机,信用制度与抵押贷款的产生则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投机之中。同时,空间产品的生产周期问题使部分资本投资转向抵押贷款,即一些投资者将钱借给那些无能力购买房产的人,从借款者那里来获益,而借款的购房者则期望房价上涨来获得赢利。也就是说,两者的收益是通过虚拟资本的持续增长与流通实现的。
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涌现,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了更多的份额,真实的供需关系已经不再重要,一切变得泡沫化。但是脱离实体泡沫化增长的经济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一旦泡沫破裂势必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从长期角度来看,创造和生产空间场所的活动显然是投机的,而且虽然这些活动的最初目的是消除过度积累,但通常会面临在今后出现更大规模过度积累的风险。所以,城市和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易发生危机的特征。”[1]4320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空间资本化的经济后果。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互依、生态上的共存越来越紧密,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的地理发展,将危机转嫁给全球,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态上的危机都具有全球化性质。资本主义通过城市空间的发展引发的危机很可能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后果也更为严重。
三、都市革命:当代主要的解放途径
不同样态的城市是不同时期文明的外化表现,因为城市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实践,就将建构什么样的城市。从根本上而言,当代城市问题的出现是人自身出现问题,在我们思考“要建构什么样的城市”时,首先应该考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这些依旧停留在理论的思考层面。如何按照人的需要和愿望建造城市,使城市属于人民、成为真正的家园却是一个现实问题,即城市空间的支配权归属于谁。正是在这一含义上,哈维提出了“城市权利”。他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另外,改变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力量的运用,所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1]52也就是说,改造和建设城市空间是一种人权,是该城市居民的集体人权。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于城市空间支配权与控制权的争夺,“谁的城市”这一问题摆在了都市人的面前。越是超大的都市,对于城市空间控制权的争夺就越是激烈,这种争夺形式多样,政治的、金融的、舆论的,等等,可能激进也可能温和,但都是残酷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就生产着空间不正义、创造着新的权贵与赤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于城市空间支配权的争夺是大都市中的主要问题,所有的一切问题都要在这里寻找答案。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革命”是当代的主要革命形态,也蕴含着新生的希望。
从当下的现实来看,“资本”占据着城市空间支配权,这背后当然有着政治的因素,因而从资本手中夺回城市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资本主义通过城市空间得到发展,生产了极大丰富的物质,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空间正义的缺失,产生了反抗的力量。虽然晚期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方式转向了城市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本质并没有变,只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城市空间商品化的过程存在着不平等的空间剥夺,通过强制、经济等各种方式,将许多人排除在城市之外。如对贫民窟进行强制拆除,驱逐居民,而房产开发商往往只需花费很少的费用甚至无须花费就可以得到开发权,在原有拆迁的土地上进行空间的重构和改造并出售,这是一种常见的资本增殖方式。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是那些投资者和开发商,而那些原居民和城市中的下层人——常常是城市建筑工人与维持城市生活的各种工人,由于被开发后的住宅大幅度增值而无力购买。许多拆迁居民、低收入者、失业者等群体就是这样通过空间的方式被剥削、排挤,成为被都市边缘化的城市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这些被城市边缘化的人将成为反抗城市空间资本化的主要力量,并应该通过争夺进入都市的“城市权利”来从资本手中拿回属于人们的城市。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认为城市权利是反抗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城市权利不仅仅是关乎个人权利的问题,更是反抗资本、变更资本主义的可能路径。列斐伏尔明确提出未来的社会形态是“都市社会”,在他看来,“都市革命”指的是划分当代社会阶段的那些转变。如同“工业革命”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通过“都市革命”,社会将进入以都市问题为主导的社会阶段,因而未来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将是以争取城市权利为目的的“都市革命”。城市空间资本化生产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城市权利是针对城市空间正义缺失而提出的,要求平等的空间权利,根本上就是要求政治权利平等,从而改变资本主义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权利本身就标示着一种处于首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在社会中有个性的权利,有居住地和主动去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同财产权有明晰的区别),是城市权利的内在要求。”[8]列斐伏尔旨在通过城市空间差异化和平等化抵抗城市空间同质化和对下层人的排斥。人的生存空间承载着人的生活方式,其不仅具有政治经济性质,也具有文化性质,反映着人的存在状况。空间差异化、多种样态是人的总体性存在的要求,同质化、单一化的生存空间只会产生单面化的人。因此,日常生活革命、对于差异化空间的需求,是人的权利。而城市权利则意味着城市空间摆脱资本的控制和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与总体性,人成为主体来塑造自己的城市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权利代表着对资本的超越与颠覆,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意义,也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改变城市空间的资本化。
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争夺城市权利?“主张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而实现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激进的方式。”[1]5在要求某种权利时,如果不能顺利得到满足,往往会通过激进的方式来获得,如走上城市街头巷尾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城市运动成为要求城市权利的主要表达方式。
当前城市作为人类的主要生存空间,新型的社会形态将完成于城市,因此,“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9]。人们通过城市权利从资本手中夺回城市空间,城市未来的发展应当按照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价值观和文明观来建设。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价值观下,不会生成新的城市空间。那么城市空间的发展应遵循怎样的尺度?如何建设理想的城市空间呢?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是遵循资本逻辑、以经济技术为中心、注重交换价值的生产,那么承载新文明与新社会形态的城市空间应当扬弃以经济为中心、遵循人本主义的价值逻辑,从交换价值回归到使用价值,从物回归到人本身。“在这个‘新社会’中,生产主义将被超越,增长也会受到控制和引导,对于技术的(信息的、电脑的、导弹和火箭等方面的)应用也是如此。”[6]70
未来的城市应当由资本回归到人与生活。那么,未来新城市空间具有哪些特征呢?虽然很多学者都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却存在着这样一个共识,即未来城市空间应当具有差异化与多元化的特征,它不同于同质的资本城市空间,是体现人总体性生成的空间。未来的城市应当是“有机”的系统。“有机”强调城市的整体性与生态性。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建筑物中应当蕴含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性,这样人才能实现居住的本质即“诗意栖居”。这强调了人与自然、神性、意义的联结,是当代人摆脱精神困境,回归信仰与意义生活的要求。日本学者黑川纪章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代的城市是法人城市,未来的城市是“个人(生活)的城市”,是一种遵循生命原理的城市。在他看来,当前城市遵循的机器原理是普遍性的霸权主义原理,它无视众文化的存在,将世界一元化作为目标。可以说,资本控制下的“法人城市”与霸权主义抹杀了差异与多元化。“生命原理的重要的关键词是新陈代谢、循环、突变、共生、信息和生态系统,这些全都是我迄今为止一贯追求的概念。”[10]城市的发展应当从机器时代迈向生命时代。
不可否认,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益处,极大地丰富了物质生活,城市成为人类主要生存空间,也说明了人类物质生活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面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如何在城镇化进程的道路上保持初衷,只有创造出一个多样化形态的、以人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才能为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提供条件。人之存在的完善与健全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