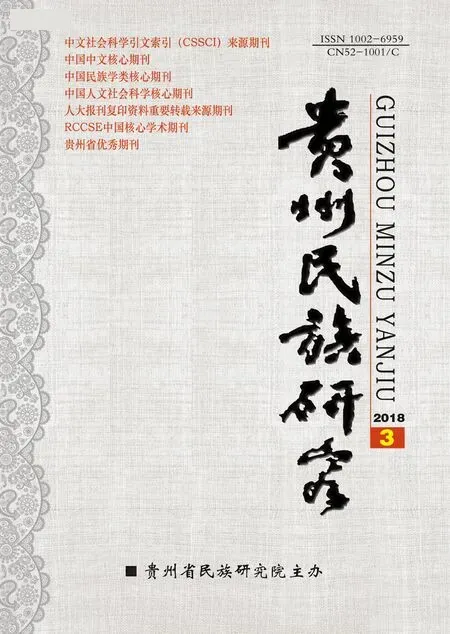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主体研究
刘弘阳
(西南财经大学 法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一、问题:藏区非遗的保护与救济困境
对于藏族地区而言,非遗的保护和救济形势十分严峻。当地藏民的保护意识不强;国家立法或者地方性法规适用程度低;再加上藏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宗教影响和历史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全球化影响等,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藏族非遗正在逐步消失。具体来说,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抢救总是赶不上消失的速度”。“在炉霍寨子里一些重要的庆典仪式早已无人问津了”。[1],作为四川省省级非遗项目的“藏族药泥面具”,就存在传承、保护与救济的问题。药泥面具,据松赞干布时期的《知识总汇》记载,起源于1300多年前。据《护法经文》记载:“药泥护法面具,不分教派放在家里,具有‘保佑全家、辟邪、吉祥如意、成就、福望、威得、知识得、消罪、长寿驱魔’等功效。”藏泥面具传承人四龙降泽说:“药泥面具减轻了佛教的神秘性,让佛教教义形象生动,这与佛教的‘造福众生’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关于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药泥面具有一整套严格的制作程序和规范,如果不严格执行,可能“药泥变成毒泥,与人无益”。如果不采取规范性的传承和保护措施,如立法、司法等制度性的规定,可能在不久将来我们将看不到这一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
另一方面,涉及藏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来看,主要有作为国家根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的具体规定。但是,从法条的梳理来看,我国目前并无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别法律。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角度来看,也较缺乏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另外,国际相关公约及法律救济规定的局限性较为明显,如我国签署但未正式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存在公约适用与救济的难题。如藏区非遗保护权利与救济范围的局限、实质性救济条款的缺乏以及救济内容难以达成等问题。
二、途径:藏区非遗保护应引入法律救济文化
作为权利的保护与实现机制,救济机制和救济文化理念的引入成为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救济是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没有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得以存续的依据。同样,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两面关系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了法治社会价值的两个要素。”[2]因此,根本的途径就是在法治社会的统领下,构建一种法律救济文化机制,用以保护非遗文化权利乃至生存权利等基本权利。而根据法律救济理论来推行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的也是构建适合藏区实际的法律救济文化,以主体的权利及权力视角和法律的文化理念来指导藏区非遗保护,也许这才是长远之计。
(一)法律救济文化的重要意义
把法律救济文化理念引入藏族非遗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救济作为一种权利保护或者纠正的方法,与藏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存在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更好地适应藏族人民的行为习惯,有利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效果。同时,这种救济方式的形成也有利于藏族人民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其二,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保护通常是刚性的,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属于民族事务的范畴”[3],可能产生法律规定理想与法律适用实践冲突的难题。引入法律救济文化理念可以避免法律保护的刚性要求,也可以体现民族地区的变通实践和柔性需求,从而实现非遗法律的真正适用,调整当地人民的行为习惯。
(二)以救济文化为中心的藏区非遗保护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证成藏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救济文化与主体。第一,法律救济文化属于法律文化,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属性。法律救济文化,是在特定地方、特定社会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保护机制在适用强度、理解力度、实施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别。藏民“全民信教”的特点,使得对于法律保护的适用在理解上有所偏差;法律保护是一种刚性实践,而法律救济理念则可通过藏族宗教习俗、藏族民间法文化等内化为藏民的法律信仰与心理状态,从而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非遗的保护。第二,这种法律救济文化的构建,不仅要充分发挥藏民等主体的作用,还要充分发掘藏民的“生存性智慧”。对于藏族非遗的保护,不仅要发挥当地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发挥当地藏民的主体作用。每一个藏民都不希望自己的文化逐步消失,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博弈的知识与观念”即藏民的“生存性智慧”,将成为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动力和源泉。第三,法律救济文化的影响和适用,取决于与当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的结合程度。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藏民族的文化变迁、生存方式、情感交流习惯等存在紧密联系。法律保护方式也许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法律救济文化却可以存在于藏民的独特文化体验之中,作为传统而继承和延续。第四,法律救济文化能够成为一种当地藏民法律意识和水平的内涵,也会成为藏民保护当地非遗的法律理念。同时这种救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会对其他民族地方乃至全国的非遗保护产生示范效应和借鉴价值。
三、出路:藏区非遗法律救济文化之主体理论及其要求
(一)藏区非遗法律救济文化的主体理论
关于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救济文化的探讨,要明确救济保护的主体理论。即依据前述的权利-保护-救济这一发展脉络,以权利的合理行使为手段、以权利保护为目标和以救济为主要措施来进行救济文化主体理论的构建。
1.个人权利保护与以人为本
从现实的藏区非遗保护来说,法律规定的文化权、国家法上的广义人权等,必须内化为公民的具体权利,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才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藏区法治发展的现实要义。在涉及藏区非遗的个人权利方面,可以初步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以突出在藏区非遗保护个人权利的类型归属和救济保护对象。其一,藏民个人意义上的“文化权利”。作为国际公约与法律中的重要人权概念,文化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文化权利的保护法律实践相对较少,在各国具体适用过程中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研究与表现。因而,对于藏区非遗的保护,必须首先要赋予当地公民个人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当其文化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由法律赋予其救济与保护机制,否则法律以及国际公约的制定会形同虚设。其二,藏民个人意义上的“生存权利”。生存权的权利内容,是强调在生存性法学范畴中对于个人的尊重,是一种权利本能与个人信仰的结合与协调。藏民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使得法律信仰与民族宗教文化相互交织。主体选择与权利构建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选择的存在与结果。最终,对于藏区非遗保护与救济的个人权利,在具体保护与救济过程中必须强调以人为本的救济原则。
2.集体性权利保护与救济需要
从藏区非遗的拥有者来说,不仅有着个人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利,还有着群体性的享有与所有。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存在国家意义上的所有,也有着藏民族群体意义上的关怀和保护责任。当地民众以及宗教等社会组织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和救济功能。藏族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集体型权利主体”,负有保护、传承与救济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这种集体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要求对于非遗进行文化方面的特殊保护与救济。因为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社会发展以及宗教信仰等相适应。
3.礼法之争下的国家权力保护与救济职责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从古至今都强调国家社会功能对于秩序以及私人主体的维护与保护作用。从古代的礼法相争等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侧面体现了国家在藏区非遗保护方面的作用和职责。儒家国家保护作用的发挥,其实也是借助作为文化层面的“礼”治;而法家则强调对于“法”的运用,强调客观意义上的保护与救济标准。[4]针对上述观点,鲍明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国家的危难在于国家无法提供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无法提供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救济机制。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宪法以及宪政的普遍实施。“欲解答上述诸根本的并其相关的问题,遂将本书分为两部:第一,叙述吾国最近历史及政治,冀得其历史背镜;若夫对于今年来诸纷扰情形——如内乱也,已往之种种教训也,临时约法之缺点也,督军制度也,宪法之制定也,种种危难之救济也——吾人更不能不有正确之了解。第二,研究宪政问题,察各国过去之经验,复审吾国现在之国情,冀得种种解决方法而纳之将来之宪法中。”[5]
因此,在我国宪法中,对于社会危机以及相关权利的具体规定,谓之救济之途径。从宪法等法律规范的角度对于国家保护义务之规定,有利于保护效果与救济机制的实现。在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救济过程中,要想通过法律救济文化的完善来促进非遗保护,必须通过法律乃至国家职权的行使才可能实现。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职权的行使等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藏区非遗保护与救济的职责要求。
(二)藏区非遗法律救济文化的主体要求
对于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主要包括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各级政府部门、具有公益作用的有关团体、组织和个人等。因此,笔者将从个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等主体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并评判。
1.重视藏区人民群众的呼声
在我国藏区,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使得他们真正成为权利主体和享有相应的法律地位。而且,藏区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和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是一样的:都不希望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属于全民族的公共财富,对于所有受益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与救济过程中。这如同我们早期的祖先一样,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所具有的团结力量。“显然,我们早期的、初有人性的祖先,不可能依据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来做事,而必定一直是被一种本能的机制所驱使,这是一种由部落里的友谊和对所有其他人的敌意组成的二元机制。”[6]
2.强调藏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作用
我国藏区有一定的自治权。因此,这种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构成了藏区非遗法律救济机制完善的法律渊源之一。“政府的主要目的,应该有三个:安全、公正和保护。这些都是对人类幸福至关重要的事情,也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更大程度的其他的善,每个人不得不做出一定的牺牲。”[7]对应于藏区非遗的法律保护,我们要求行政机关在维护“更大的善”的时候,适当避免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藏区行政机关,只能而且应该是为了保护属于全人类公共财富的藏区非遗而努力,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而市场的激励、个人的合理追求等只能回归那只“看不见的手”。
3.完善藏区司法机关的保护机制
从司法机关的政治背景和社会作用来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体现司法的被动型性格和国家法制的要求。“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者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碍难,也是很不妥当的,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8]一般认为,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藏族土壤中的活态文化,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不能进行凝固的“死”保护,必须进行活态的保护。而活态保护的关键在于对传承主体的保护。
从司法机关的藏区社会要求来说,就是要完善一系列相关程序性法律法规,对于侵犯藏区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乃至人身权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惩戒和司法规制。[9]这既包括实体法意义上的权利保护,也保护程序法意义上的救济途径构建和司法途径完善。从相关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藏区司法机关在进行非遗保护时,应当强调以下一些内容。其一,对于任何侵犯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行为,必须要求相关部门制止侵害行为,必要时可以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进行处理。其二,对于侵害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侵权行为,可以通过诉讼、仲裁等民事救济方式来进行解决,如赔偿相关权利人的损失,赔礼道歉以及消除影响等;如果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等,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进行主张权利。其三,如果侵害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涉及到刑事犯罪,则必须通过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等对于严重侵犯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事保护有所欠缺,尤其是对于侵权行为的刑事救济手段的规定与操作几乎为空白。因此,完善对于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事救济机制,显得格外重要。
参考文献:
[1]尼玛.抢救文化遗产是我的责任[N].甘孜日报(康巴周末,第2版),2013.
[2]程燎原,王人博.权利及其救济[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49.
[3]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13.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2.
[5]鲍明钤.中国民治论[M].周馥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
[6]Bertrand Russell.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A TOUCHSTONE Simon&Schuster (INC),1945:115.
[7](英) 伯特兰·罗素,储智勇译.权威与个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71-72.
[8]南怀瑾.周勋男整理.原本大学微言[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96.
[9]杨继文.“依法治藏”背景下的藏区草场纠纷治理[J].贵州民族研究,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