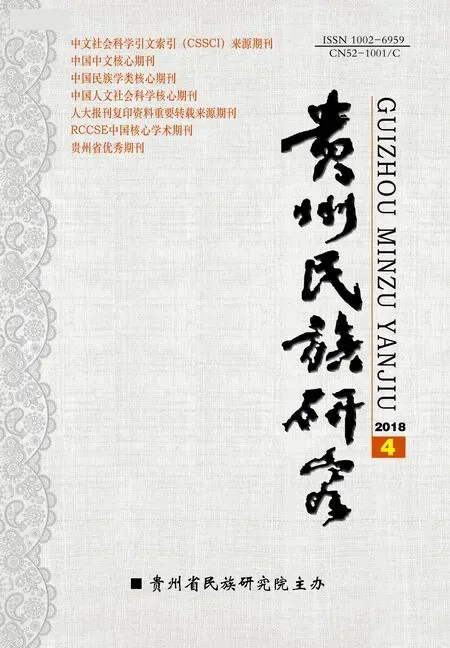一战后德国人民族心理对二战爆发的影响
周彰堃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一、德国人传统的民族性格影响民众战后心理
(一)长期分裂状态造成的不安全感被放大。德国西邻法国,东接波兰,北面是波罗的海,南面是意大利地区,处于整个欧洲的中心。17世纪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对德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信仰自由规定的结果却是使德意志人民分裂成了三百多个小诸侯国,从而使德国走上了漫长的统一道路,迟滞了德国近代化的进程。”因为缺失一个强大的中央集团的保护,容易成为周围国家的攻击目标,加之国内诸侯国之间也长期处于一个争斗的状态,这使得在德意志地区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一种极其不安定的状态之下,逐渐造成了德意志人的不安全感,并融入了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表现为严肃,谨慎;另一方面,表现为心胸狭窄,嫉妒心强而且报复心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这种不安全感空前的高涨。英法两国对于战败的德国十分苛刻,通过多项经济上、武器上的限制条款,企图让德国人无法再翻身与之抗衡。在失去了一个长久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德国的经济状况恶劣,通货膨胀严重,政府丧失威信,使得德国人陷入一种精神迷失[1],不安全感危机再次爆发并走向顶峰,对战胜国的嫉妒感,对不平等待遇的愤怒与随之而来的报复心理逐步放大。
(二)刚建立的民族自信心被击溃。德国人的统一较欧洲其他国家相对较晚,在十九世纪中叶才由普鲁士实现。反观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与法国,早在数百年前就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种对比之下,会给德国人带来一种较为强烈的自卑感和恐惧感。“他们一直担心被别人看不起,这种自卑与恐惧感使得他们不断的行动...;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目的,德国人并不因富裕和轻松而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所厌恶的生活方式。[2]”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德国经历了普奥、普法、普丹战争的胜利,并且担当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的角色,由自卑心理产生的渴望证明自己优秀的心理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民族自信心空前的高涨。但一战的失败,使德国人渐渐积累起来的民族自信心被打垮并跌入了新的低谷,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消除民族自卑感,就成为德国人必须共同完成的“民族任务”。
(三)渴望证明自己的进攻性被激发。早期的德国人生存条件相对较为恶劣,居住在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及较为贫瘠的土地上,难以有效进行农业耕作,使得德国人必须通过战争进行征服,来获得其生存繁衍所需要的资源。这激发了当地人尚武好斗的民族性格。塔西佗曾说:“德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潜在特点是对于弱小民族的进攻性。”这也是后来法西斯主义武力扩张的民族心理基础。这种好斗的民族性格在德国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强大的作用,一战战败的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军队被彻底打垮,也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一直渴望通过战争再次打败对手来重新证明自己,这种民族进攻性也导致德国人在战后仅仅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再一次发动战争。
(四)对上服从又希望驯服别人的双重性格被扩展。德国人的民族性中有一种服从性,人们愿意服从于强者。这来源于德意志地区条顿骑士团的历史传统以及后来普鲁士独特的军事训练体系。条顿骑士团作为一个教会军事组织十分讲求服从,而整个普鲁士的军事体制与“容克”阶层相挂钩,“容克”阶层为了方便军事管理,对士兵管理十分的严苛,使得普鲁士的士兵都讲求绝对服从。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各地都有一种带有雇佣兵性质的新部队体制即“改良团”,这种团建制部队在经过王室认可之后对其周边地区的人民有着一定的控制,并享有征兵的权力。这些团将德国的贵族阶层与下层平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分权的手段加强了对国家各个地区人民的统治,由此衍生了德国人服从的双重性格。一战失败后的种种困境,使得德国人对内服从统治,对外希望征服的双重性格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实现了“逆生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一直根植于德国人血脉中的民族性格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强烈刺激,逐步发挥它们的影响,在国家社会经济形势逐步恶化时,作为战败国国民的德国人的心理转变,直接带动德国社会中的“结构暴力”进一步发展,战争与复仇逐渐成为主旋律,直接导致了短短二十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凡尔赛和约》苛刻条款加剧了民族心理危机
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对战后德国的疆土领域进行了重新界定,对德国的军事力量进行了限制,同时要求德国人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这份和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消极和平”的手段,也是之后二十年德国人心理上巨大的负担,这份和约被德国人认为是羞耻、屈辱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二十一年中,德国人一直处于一个压抑心理的病态社会心理之中,德国人在战争中受挫的心理压力在和约的严苛要求之下得不到释放,越发地积蓄起来。
首先,《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德国人的土地被大量割让,每个国民的生活空间大大缩小,生产资源也大量减少。其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进行了军事限制,设立“莱茵兰非军事区”、废除传统的义务兵制、限制德国人的陆军规模、装备生产、不准设立空军等条款。这对于自普鲁士以来就有着极其悠久的军事传统的德国人是一次极大的羞辱,以“容克”为主的传统军人们对于此条约更是深恶痛绝。这意味着一旦周围对德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发起进攻,整个德国将会在巨大的装备差距以及军队差距中变得不堪一击。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德国人在这样的条款之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危机。再次,《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赔偿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并要求德国放弃对萨尔地区的煤矿产业的控制,最终所属15年后由当地人民公投决定。[3]在经历一战后,德国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对外要面临巨大的赔偿款的压力,对内主要的传统重工业损失惨重,作为经济压力的实际承担者,德国民众对此充满怨言。
《凡尔赛和约》签订时,西方对于和平的理念完完全全还停留在一种“个体主义阶段”。“在个体主义看来,有效地控制个体的动机和能力,对个体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对个体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就能够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对于结构暴力中提到的来自于社会更深层根源的“非和平”因素未能够进行控制。和约二十年间一再被违反,德国人再次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说明这些惩罚实际上是无效的。心理学上认为,“惩罚之所以无效,是因为惩罚容易导致个体去努力避免惩罚而不是停止其不良行为”。“惩罚会导致个体将惩罚与其实施者联系起来,而不是个体的行为本身。”《凡尔赛和约》并未使德国人认识到自身的战争责任,相反,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于英法等战胜国的仇视,并激发德国国民普遍性的复仇心理,希望能够对给他们制定这些惩罚的人以最残酷的报复,来达成心理满足,但却忽视了“和平的条件不能永久栖息于痛苦,憎恨和残酷的回忆上,因为后者好像流沙一样。”
三、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失败和经济危机挑动了“民族战争情绪”
在德国一战战败之后,魏玛共和国草草上台,就如同被赶鸭子上架一般,或者说是作为立宪君主制可悲的代替品一样。魏玛共和国本身机制不够健全,对内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新政府对于这些攻击,采取的办法是暴力镇压,这种单一的手段作用及其有限。对魏玛的宪法,“不论从字面上来看,还是就事实而言,他都是非常开明的,但是后来却受到了许多批判,称其一系列缺陷加速了民主制的瓦解。[4]”其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也使得德国议会中左右翼政党占比逐渐增加。加之之后法国对于德国的一系列行动,使魏玛共和国无能政府的形象在德国人心中牢牢树立。民主选出的政府,却无法保护国民,这更是在刚刚实行民主制度的德国人的心中,根植了对于“民主”的不信任。
在经济上,魏玛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919年1月,1美元可兑换8.9马克,而到了1923年11月15日,1美元所能兑换的马克已达到4200亿。通货膨胀使德国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是政府将他们带入了这样的困境之中,德国人的不安全感进一步的加重,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也日益增加。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依赖国外短期贷款,经济危机迅速摧垮了共和国极其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德国工业总产值比经济危机前最高点下降了40.6%,大量的产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倍增。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失业人数为132万,到了1933年则超过600万,占比接近10%,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恐慌日益加剧。
经济危机唯一的受益者,是垄断资产阶级。资本家们除了加紧剥削劳动者来转嫁危机之外,更是从政府拨款中侵吞巨款,几年内政府给垄断资产阶级的补助金总计在60亿马克以上[5]。就业者与失业者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而有权势者过得越来越好,对政府的厌恶以及仇富心理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滋生,德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小工商业者等下层人民需要一个更符合“民意”的掌权者。“民主政体确实与大范围的实施暴力相一致,不仅仅是有好战倾向,而且是相当好战。”[6]魏玛共和国为德国带来的民主,并未能给德国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比例代议制的民主使得其越发倾向于战争。
四、希特勒极端的“民族心理治疗”点燃了战争导火索
某种程度上,希特勒可以称之为“德国人的心理医生”,他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成功洞察了这一时期德国人的心理问题,并在政治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迎合了大部分德国人的需求。作为回报,德国人支持他走上权力巅峰。作为一战参战士兵,他很能与其他参战者们达成共情。利用这种共情,希特勒影响听众的情绪,操控他们的心理,逐步获得了右翼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如约瑟夫·戈培尔所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政府是一个人民政府的真理。它来自人民,永远执行人民的意志。[7]”纳粹宣传的角度几乎涵盖了能填补德国人心理创伤的方方面面,德国人长期以来积蓄的压抑心理在这种宣传中得到缓解。1933年底,纳粹上台仅仅几个月之后,德国民众中便流行起这样的观点:“人们越来越有信心和信念,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和德国一起发展向前。”
关于令德国人耻辱的《凡尔赛和约》,希特勒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从1933年之后,希特勒政府拒绝再赔偿战争赔款。1935年宣布德国重新恢复义务兵制,1936年驻军“莱茵兰非军事区”,1938年吞并奥地利,直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种种举动,将一战结束以来一直套在德国人头上的耻辱桎梏彻底甩开,这正是德国人内心所期望的。
希特勒政府还改善了税收制度,使得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及工人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在全国修建高速公路,解决失业人口的问题,使得整个德国经济有所复苏。“相比之前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在经济上的无力感而言,民众更愿意信任这个强有力的政府,最起码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的的确确在行动起来,改善我们的经济处境。[8]”希特勒在上台之后一直致力着填补德国人的不安全感,通过提倡集体主义的观点,来消除作为个体的不安。1938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为德国人重塑了民族自信。
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崛起正是由于“消极和平”期望的对于暴力行为的完全压制而带来的后果。局限的“消极和平”针对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应对措施强硬无比,但是却几乎是完全忽视了文化暴力,甚至可以说是对文化暴力的一种纵容。这使得希特勒通过大量的对于“歧视”和“偏见”的宣传,成功走上了德国政治巅峰,并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超人”形象。这种文化暴力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在德国肆意滋长,渐渐变成了一个结构暴力和直接暴力的集合体,从而使得这种和平手段完全失去了其效果。
结论
点燃民族情绪,煽动民众暴力,这种问题在各个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其直接后果便是残酷的战争。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化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必须真正认识到“结构暴力”对于和平的巨大的充满破坏性的影响,为实现真正的“积极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历史昭示我们,应该正确疏导民族心理,提倡相互尊重、消除偏见、避免歧视、解决争端,追求互利共赢。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各国人民应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德)埃里克·沃格林.希特勒与德国人[M].上海:三联书店,2015.
[2](德)埃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现代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英)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 (第三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英)迪克·吉里尔.希特勒和纳粹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6](挪威)约翰·加尔通.和平论[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7]JosephGoebbels:“”TwoSpeeches on the Tasks of the 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March 15/March 25,1933).
[8](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