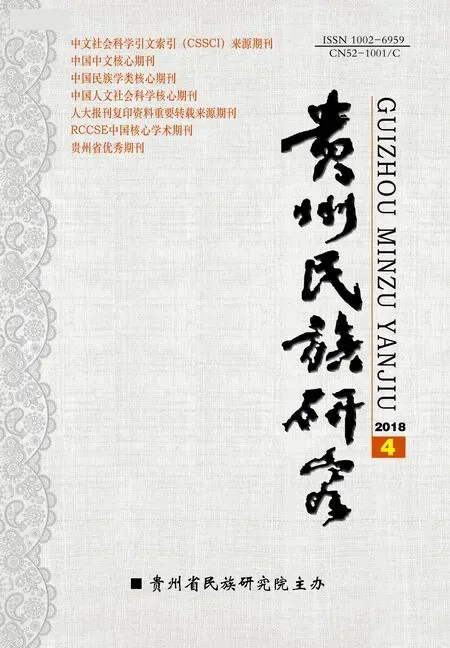契丹族墓室壁画中的儒家文化研究
李彩英 高永利
(太原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山西·晋中 030600)
公元4世纪,在我国北方草原,契丹建立了草原帝国——辽王朝。辽王朝经历了900多年的历史,直至13世纪西辽灭亡。公元10到12世纪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长期的民族融合使契丹族建立了强大的辽帝国并逐渐壮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传统和艺术风格,不但广泛地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还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具有了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流动性特征。并且作为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契丹积极、包容地接纳和传承了儒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使本民族文化获得了飞跃发展,积极地吸纳和传播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目前,有关辽代的史籍非常少,幸好辽代壁画出土数量非常丰富。为了还原辽王朝的历史风貌,学者们通过契丹族一些墓室壁画等考古资料,来洞悉契丹民族体现的儒学风华,并且大量的研究成果弥补了文字史料之阙遗。学者对辽代壁画研究方兴未艾,一幅幅的辽代壁画蕴含着许多似曾相识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契丹民族独特的文化。
一、儒家文化与契丹族文化的融合
(一)儒家文化在辽代的渗透历程
在没有建立辽国之前,契丹族没有文字和典籍,作为游牧民族,自身的文明还停留在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中。随后,中原汉族王朝利用千百年来积淀的高度文明征服了契丹族。正如马克思说的:“历史具有一条永恒的规律,就是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会征服那些野蛮的民族。”作为中原汉族王朝的征服者,契丹族也没有摆脱这一历史规律,在文化层面上,儒家文化征服了强大的契丹族精神。如:《辽史·义宗耶律倍传》中就有关于建孔子庙的记载,充分地证明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耶律阿保机认为孔子是“大圣”,是“万世所尊”,所以要建立孔子庙,“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典。”[1]这不但反映出耶律阿保机对汉族文化的熟悉程度和认同程度,也充分说明辽太祖从政令上提倡尊孔崇儒,成了契丹族接纳儒家文化最著名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契丹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提高了契丹族整体文化水平。首先,在对先进文化的认识方面,契丹人具有一种主动认同姿态和开放的心理;其次,儒家文化在当时社会中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力。因此,这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充分地体现了契丹族最先进最优秀的心理基质。契丹建国时,汉族文化处于文化霸权地位,已经发展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化,具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当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与契丹族在一个世纪的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阻止自己先进文化资源向异民族流失,如:严禁宋朝刊印的书传入辽国,违者斩等。而契丹族的心中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强弱之分,表现出一种面对先进文化的平静心态,面对保守封闭、处于绝对霸权地位的汉文化,他们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凡是对自己有用的,自己认为好的,都表现出一种完全开放和主动接受的文化观念。如:萧观音的《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中“文章通谷蠡”“应知无古今”等很好地体现出了契丹人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由此可见,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汉文化的影响下,契丹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儒家文化深入到了契丹上层统治者的意识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也正因为如此,儒家经典被定位太学、州学教材,并在北方草原扎下了根。如:辽圣宗“阅唐高宗、太宗、玄宗三纪”,并且还将其纳入契丹文化之中,通览《贞观政要》,并下旨将众多的儒学著作翻译成契丹文。澶渊之盟后,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程度进一步提高,宋辽进入了一个相对友好的时期,到辽道宗时期,儒学对契丹文化影响更加深入,如:辽道宗颁行了《史记》、《汉书》,令耶律俨进将《尚书·洪范》,令赵孝严等将《五经》大义,从而使契丹族掌握和接受了一整套先进的文化系统,提升了契丹民族文化水平。
(二)儒家文学对契丹族文化的影响
在史书中,关于契丹族儒家化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契丹民族正式儒家化起始于太宗时期,在辽景宗和辽圣宗时期才真正完成汉化和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而范寿琨先生则将其进程简单地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为了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地位,契丹族利用中原灿烂发达的文化统治异族,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接纳了儒家文化后,增进了境内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随着儒家文化在辽朝社会的传播,儒家文化迅速地渗透于辽朝社会各个方面,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首先,契丹统治者颁布的诏令、法律条文中有很多是根据儒家思想制定的,如:统和元年(1436年),为了将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现实化,圣宗下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旌其门闾”。再如:辽兴宗曾告诫族人:“不孝不义,虽小不可为”。并且,在契丹统治者的谥号与名字上,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五常”也有直观的体现,即:仁、义、礼、智、信,如:圣宗齐天皇后追尊号为“仁德皇后”;道宗谥号为“仁圣大孝文皇帝”;兴宗贞懿皇后追谥为“仁懿皇后”;萧义先也常常告诫族人:“不孝不义尤不可为”,由此可见,在契丹统治阶级的日常思维之中,儒家文化的“五常”“孝悌”观念已经渗透,成了上层阶级追求的政治理想,成为指导上层贵族思想行动的准绳。其次,辽代的科举之制,确立了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如:据有关学者考证,在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就有了由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科举制,契丹上层统治者对这样的科举制度非常重视。辽朝契丹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接纳,加快了辽朝的儒家化程度,其不只是简单地对先圣孔子表示尊重与推崇,还延伸到了社会各个方面,付诸于本朝的统治思想中,如:道宗时期就已经有了“行大圣之遗风”的赞誉。而壁画更是具象地表现出了契丹族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二、壁画对辽代民族融合研究的重要性
契丹源自东胡系统,自魏后游牧辽河流域,属于鲜卑族中类于原始者,以车帐为家,随水草就畋猎捕渔。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契丹族始终不认同自身为夷狄,身为少数民族政权,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族以“中国”自居,甚至认为辽与汉族同为炎黄子孙。这种观念充分地体现出了契丹族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吸收与运用。而辽代壁画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那汇集了岁月的丰盈与沧桑的坚实色彩,那沉重的尘土厚墙阴暗墓室中的完美线条,无时无刻不彰显着它的魅力。从本质上来说,壁画是一种艺术载体,具有直观且较为客观的形态,体现了墓主人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并且受当时社会的影响,这种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会直接作为壁画的内容,展现在辽代契丹族墓葬的壁画上。由此看来,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凭借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儒家文化受到了契丹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同时也深入到了每个契丹人的心中,使得在中原汉地流行千年的儒家文化大行其道,渗透到了辽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些意识形态被充分地展现在墓室壁画之中,使后人也能一窥儒家文化的痕迹。这一过程是契丹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历程,也是儒家文化融入契丹族民众思想意识中的过程。当然契丹墓室壁画还包含着佛家、道家甚至西域文化的痕迹,不只是反映了儒家文化。这些现象都是民族融合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水到渠成的产物,并不偶然。契丹族墓葬壁画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丰富了对辽史的研究,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的直接记录者。契丹族墓室壁画是辽代民族融合现象的有力见证,不仅仅是契丹族的一种丧葬艺术,其主题内容与史籍文字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辽代民族融合研究资料。[2]
三、契丹族墓室壁画中的儒家文化
(一)儒士文化
辽代墓室壁画绘于墓壁、石椁上,题材内容丰富,出土数量众多,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白音宝力格辽墓葬中的壁画,不但具有装饰层面的价值,还充分地反映出墓主人的意识形态,在骨灰盒的外壁上绘有一幅“散乐图”。由此可见,这些壁画无论绘在什么地方,都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并且,在儒学思想逐渐成为辽朝社会主流思想意识时,墓主人的意识形态被纳入到了壁画的创作中。[3]契丹墓室壁画多,不但皇帝、大臣的墓葬会绘制壁画,并且受唐朝贵族墓室壁画的影响,就连很多官吏也在墓室中绘制壁画。[4]而契丹民族接受汉族文化是从接纳汉人开始,一些饱读诗书的汉族人士将儒家文化传播到契丹民族中,如:以韩氏家族为首的“汉人四大家族”就是其中主要媒介。自辽朝设办国子监及州学以来,以儒生为代表的汉族饱学之士,受到了重用,契丹民族把他们当成了榜样,如:辽军俘获了原为宋朝国子博士的武白,在辽国教授契丹贵族学习儒家之士,将其“诏授上京国子博士”。契丹统治者非常重视对本族儒生的培养,积极吸纳汉族儒生,在汉族儒生的影响下,很多契丹人成了令人敬佩的大儒,被世人所知晓和敬佩。同时,随着辽朝儒家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契丹族墓室壁画上出现以儒生形象为蓝本的人物画。这充分地表明契丹上层统治者对儒生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入仕者。[5]从壁画分期上来看,辽庆陵墓室壁画属于辽代中期壁画。汉服人物像的出现也充分表明儒家思想在辽朝已经取得了正统地位,此时的辽朝汉化程度已经非常深。再如: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契丹族墓和内蒙古库伦旗辽代壁画墓的一号墓都绘有汉服人物图像。[5]
(二) 孝文化
儒家认为孝悌是人的本性,即使时代和地域发生了改变,孝悌也未发生改变,如:儒家经典《孝经》载有“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等,中原汉族中广为流传有“二十四孝图。”而在契丹族的墓室中,也有很多关于“孝悌”壁画,如:辽宁辽阳金厂画像石墓中,雕刻着孝悌义妇的“丁兰刻木奉亲”“王密舍子救弟”等孝子故事。再如:锦西大卧铺辽代契丹族墓中刻有儒家文化中经典的孝子故事,“郯子鹿乳奉亲”“茅蓉杀鸡奉母”“郭巨为母埋儿”等。在没有建国之前,契丹人对“孝”的意识是薄弱的,如:“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这段话出自契丹旧俗《旧唐书·契丹传》,表明契丹族具有“以不哭为壮”的落后习俗,但是书中还记载着:“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可以看出,契丹族已经告别了这种落后的习俗。而墓中出现的“二十孝图,”充分地表明了契丹族开始以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尽孝,直接反映出契丹族对儒家“孝文化”的重视。并且契丹民族中还出现了很多诸如萧蒲离不、萧乌野、萧阳阿等孝子。[6]
(三)花卉图案
在中原,荷花历代以来备受文人雅士喜爱,文人墨客赞美荷花的诗句不胜枚举,儒学经典《诗经·国风》中这样描写:“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而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最能体现儒生对荷花的喜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契丹人也逐渐喜欢上了荷花,如: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五号墓中有一幅“荷花图”绘制在东北壁上,图中四朵盛开的荷花,两片并仰的荷叶;再如: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中,东、东北、东南三壁上,绘制这一幅“荷花水禽图”,荷花之上蜻蜓飞舞,荷花、蒲草挺拔而立。[7]这两座辽代壁画墓中所绘荷花并不只是具有装饰的作用,而是直观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对荷花的喜爱。这说明,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契丹族人逐渐对荷花也产生了喜爱并且将其直接绘制于壁画墓中。另外,在契丹族墓室壁画中,也绘有这类花鸟图案,如:在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中,还有“梅兰竹菊”图案,这些都是汉族文人雅士所推崇的。再如:库伦1号辽墓的天井处绘有一幅“竹林仙鹤图”;敖汉旗七家村辽壁画墓中绘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在近尸床的红色床围栏外侧上绘有六幅竖轴条屏图,如:梅花、菊花以及月季等。这些契丹族墓室壁画中的花卉图案,充分地体现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契丹族人士已经形成了更加丰富的生活情趣,逐渐告别曾经单纯的对草原、牛羊的追求。而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代墓壁画内容则模仿了北宋流行的开芳宴题材,绘有墓主人宴饮、观看伎乐的场面。从理学上来讲,宋代墓葬壁画中的“开芳宴”题材在理学对个人行为、家庭关系及乡规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对家庭和宗族的秩序具有极为严格的原则规定。因此根据考证,这座辽墓的主人为契丹贵族,是辽代中期至辽道宗初年的墓葬。这深刻表明,理学形成之后,契丹上层统治者很快就认可和接纳了理学。
(四) “六艺”文化
在古代,儒家授学要求学生必须要掌握六种基本的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儒家提倡“六艺”,其中历来文人、贵族都比较喜爱“乐”,其是一种愉悦身心、修身养性的技能。孔子云:“先进礼乐,野人也,后进与礼乐,君子也。”“乐”是跨越文字、地域、民族的一种语言,《周易》中云:“君子以饮食宴乐”。而《辽史》中:“辽有国乐、有雅乐、大乐等”,“兴宗好儒术,通音律”。虽然今天我们从文字上很难看出辽代乐舞的兴盛,但是,契丹贵族对乐非常喜爱和熟稔,这可以从辽壁画墓中出土的多幅“散乐图”上看出。伴随着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融合,辽朝汉人墓中“散乐图”壁画众多,并且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辽代中、晚期的契丹族壁画墓中,也出现了很多“散乐图”,如:耶律羽之为辽代早期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人,在他的墓中就发现了“伎乐图”。再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契丹族壁画墓、库伦契丹族壁画墓等。这是由于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契丹人越来越重视“乐”所形成的,其不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礼乐”“尊卑”的重视,还彰显出墓主人高雅的情趣。
[1]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J].考古,1984,(2).
[2]赵建,华冰.儒学影响下宋代墓葬壁画主题探析[J].兰台世界,2013,(30).
[3]王未想.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代壁画墓[J].考古,1999,(8).
[4]范寿琨.敖汉旗七家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
[5]董新林,塔拉.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J].考古,2003,(1).
[6]雁羽.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象石墓[J].考古,1960,(2).
[7]项春松.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