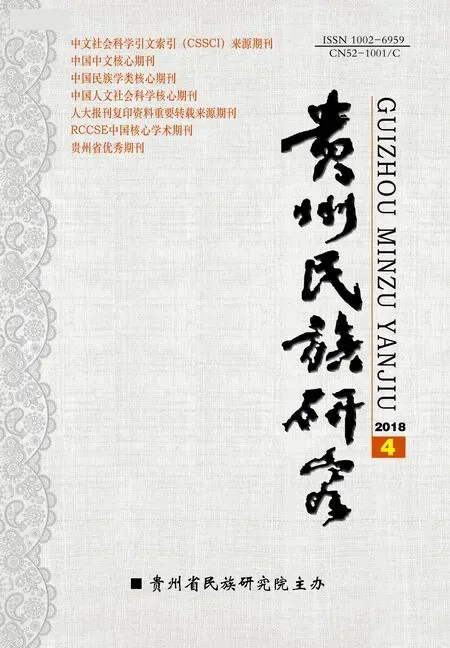推己及人:民族研究的一项传统思想资源
张少春
(中国社科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他的最后一篇长文《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对“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其基础是由“内”与“外”这两个维度建构而成的图景。所有的事物都处于“由内到外”或者“由表及里”的关系结构中,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认知结构上的“差序格局”。因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可以作为拓展传统社会学边界的方法。[1]本文将这一洞见引入民族研究领域,试图借用传统思想资源重申一种新的分析视野之意义。
一、学科传统的桎梏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指出社会学的某种传统,如科学主义可能正成为其发展的限制。而对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国家主义取向。麻国庆指出,近百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特色之一正是走过由家乡人类学到自身人类学,再到国家人类学的历程。[2]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所面对的种种压力,通过民族自觉和学术建设,形成了“国家建立型”(nation-building) 的人类学。[3]主要关注内部的“他者”如何达成一种认同的共识,以服务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这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必然在引入西方学科的同时加以话语性运用。[4]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自身独特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国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近代以来与外部的交流冲撞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需要它们来将原来纵向绵延不绝的文明传统和横向你来我往的复杂关系确定下来。具体来说,就是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树立新式的、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社会和认同边界。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不仅作为人们处理族群关系的外在象征,也具体地参与到这种关系的建构之中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系列政府主导下的研究活动进一步明晰了“少数民族”,并把他们与汉族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文化差异确定出来。与历史上“己”与“异己”共享中国文化,周边族群是儒家文化理想的候补人等认识不同,这实际上将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社会,乃至种族的差异定型下来。这个阶段的调查和研究强调收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材料,明确他们在国家历史上的地位。[5]通过统一制定的调查大纲,将不同民族置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时间线上。实际上将各民族置于断裂的点上,消解了不同人群之间流动与变化的可能性。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推动形成了一套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的族群分类知识体系。这套分类知识的意义之一就是,境内各民族不再依靠传统的文化机制,而是新的清晰的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实质边界来开展民族交往。这套民族框架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基础,甚至离开了这样的基本框架和概念,我们可能已经无法认识和表达自身社会。
在认识论之外,今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于民族的知识体系也是高度重合的。当时就有人指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项重要收获,就是为社会改革和学术研究收集了丰富的资料。[6]这些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在工作方法、指导理论等方面确定了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人类学(当时主要是民族学),并将这种特点和形式固定下来。在民族学学科体系建立的同时,知识和理论上的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后来,过度清晰化的民族话语体系通过高等教育、媒体宣传和政府政策又深入到当今社会大众的知识系统中,并为全社会所接受。最初具有客体性、出自于国家语境的“民族”也进入了地方语境,从而具有了主体性。[7]甚至关于民族知识的细节也是高度共享的。当时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所编订的《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成为后来一系列调查的指导纲要。在调查基础上编写的“三套丛书”和后来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则奠定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志书写的规范。不仅如此,这些工作的成果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入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地方社会的民众将这些被书写的历史作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结果就是,研究者在地方看到的东西可能与其在图书馆找到的材料相差不大。双方所掌握的基本概念、历史知识、文化细节都是高度文本化的。被研究者将早期的文本记录作为他们自身的“真实”传承下来,并以此规范当下社会的成员行为,或在各种仪式中不断展演。而研究者受到这些文本的限制,其思路和方法都具有早期研究的影子,有的研究甚至不过是在证实已有的文本记录。
近代以来,边疆及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持续开展,正是不断发掘、整理、建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与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上述活动有关,也同行政力量的深入、传播技术的发展、地方教育的普及等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传统上、某种意义上当下社会生活现实中仍然是模糊、混杂的知识体系衔接地带,逐步建立起坚硬的墙。早期学者的工作是将原先“松软”的“社会边界”加以“夯实”,[8]构成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个筑墙的过程既是对外建构一个国家对“他者”辨识和切割的过程,又是对内试图不断包容“他者”以建构国族的过程。[9]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积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界由“软”变“硬”,成为一道道坚实的界线。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些边界已然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
二、推己及人的思想资源
为了突破这样的限制,讨论如何扩展传统人类学的界限,首先就必须审视我们对学科的认识本身。今天我们熟悉的知识话语和学科架构,是百年前诸多学者按照他们理解的“西方科学”整理过的制度体系。[10]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搅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并存的状况,背后是中国、西方、乃至日本等多种知识体系的移植、调适和杂糅。使用这一套知识,我们不仅不能与所谓的“西方”进行对话,也失去了理解传统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能力。寻找中国人类学作为自身人类学的基础,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回归其生发的思想传统当中。
费孝通先生提出“推己及人”等传统思想可以作为拓展传统学科边界的方法,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同样具有意义。“推己及人”的方法反映的是一种类比和推论的思维。以已知的事物推论未知事物的“类比思维”是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11]“类”与“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概念,其背后的类比推论式思维方法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认识论资源。有学者指出这一思想源自《周易》“观物取象”与“取象比类”等论述。《墨子》对“推”进一步展开,提出“推类之难处,说在之大小”(《墨子·经下》),经由后世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说理方式。[12]这种思维方法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寻找两者之间属性上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从而在两者之间实现由此及彼,由事论道的逻辑方式。[13]这种论证方式在后世儒家思想家的推动之下,逐步转变为一种价值推理或伦理推理,成为建构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14]我们现在关于传统思想中类比推论的知识大都陷于“推己及人”等儒家伦理推广的话语。但如果拨开这些纷繁复杂的典籍,类比推论首先是一种逻辑方式。
潘光旦先生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出发,指出中国人将“伦”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就产生了“类别”和“关系”,“关系”就是“类别”的类比推论和相互震荡。[15]费孝通先生以此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认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6]简单来说,“类”是出发点,就要求首先必须对对象做清晰的判断和分类,在何为此何为彼之间形成明确的判断标准;“推”是目的,就是揭示同“类”之间的一致性,在其间建立关系。
这一认识论的特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类”的实践和复杂联系中,要严格把握“类”概念的确定性,不能做无限制的推演。二是“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关系和联系中,看到概念的联系性和不确定性,重视概念的转换和推移。换言之,首先必须要有清晰的分类标准,也就是将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中,或者说明确的互动关系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类别之间建立差异性。也只有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同一类别内部的一致性、联系性才能展现出来,掌握了这样的差异性和一致性,我们才能说我们认识了这一对象。而只有对象内部的同一性被揭示提炼出来,我们才能以此去认识新的事物。至此,才是完成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其核心就是以某类事物在某一性质上具有相似性或相同性,从而可以相互类推,这就是类推法的逻辑。[17]
在人类学研究中使用这一认识框架,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相似性,也就是某些事物何以成为一类。这种相似的标准有可能是宏大的想象,也有可能是具体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或行为方式。只有沿着这种同类内部的线索,其内部不同群体、社会、文化之间的往来互动,相互影响的过程才能展现出来,从而达成对于一致性、共同性因素的了解。而我们所期望的“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认识活动也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三、类比推论法作为认识论
类比推论法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早期的经典当中,而是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知识活动和行为实践。中国人在认识“四夷”“百越”过程中形成的区分中心与边缘,我群与他群,自我与异己的文化传统。这种认识论上的传统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同人类学研究中“己”与“异己”的区分联系起来,为自身人类学提供了基础。类别的划分和关系的建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而变化。台湾人类学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与中国文化对在国家范围内“己”与“异己”同质但有等级区别的认定有关。这种认识论包含两方面,一是“己”与“异己”之间是有连续性而且基本同质,并可放置在一个水平上进行比较,但同时承认“己”与“异己”之间还存在有等级的差别。[18]
因为儒家强调由内而外的伦理本位决定社会关系的远近,所以这就决定了认识论上“中心与周边”的类推框架,“己”永远处于认识世界的中心地位,一切“异己”的地位都是由它与中心的关系紧密程度而定。到汉代“中国”这个词汇本身就已不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成为儒家文化以四周蛮夷降服归化的程度而排成的等级化序列。周边民族被作为“中国文化的候补人”,并以此来确定应对策略。[19]
但“己”与“异己”不是绝对的,“异己”可以通过学习“己”的文化、习惯、制度来成为“己”的一部分。采用这一框架,许倬云以“我者”与“他者”的关系,将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分成中国与他国、本部与边陲、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正统与异端来考察。指出这几者之间的变动与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体系。[20]中国历史上的“我者”与“他者”从来就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中的族群关系和文化交流表现出迥异的面貌,这构成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因而今天研究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就不能以当前的框架去割裂这一整体内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的共享和转化,构成以小见大类推理解“中国”这一概念下各种现象的基础。
“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与“四夷”“夷狄”相对而称的,两者的区别与转化构成了“天下”。[21]历史上周边的民族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中国”,实现了“四夷的中原化”与“蛮夷戎狄的华夏化”。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重视的既不是人种,也不是地域,而是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价值观念为代表的文明方式。[22]因而民族的属性是以文明差异来进行区分的,是一种可以后天转变的属性。“蛮夷戎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的文明方式就是“华夏”,“华夏”如果接受了“蛮夷戎狄”的文明方式就是“蛮夷戎狄”。[22]与被历史滚雪球融入汉人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一样,我国的少数民族也大多具有“汉人成分”[23]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分。而之所以会在“中国人”这个称谓中派生出“汉人”的族称,是因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下,边疆民族,特别是新加入的民族要求共享“中国”称号的结果。将原来的“中国人”改称为“汉人”从而便于将边疆民族吸纳进来。[21]历史上中央王朝政权不断转手,在“中国”这个“己”内部日益容纳进了丰富的“异己”原素。
在这样的历史实践所塑造的认识论中,“己”与“异己”之间是密切联系但有差异的关系。因而“己”也可以通过具体的细分,而进一步析出某种“异己”的因素,如汉民族可以分为多个支系。在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一部分留在旧居地,一部分向南迁徙,形成了“北人”和“南人”两支;而南系汉人因为迁移路线、自然环境与民族交往的差异,到唐末五代,又分化为越海系、湘赣系、南汉系、闽海系、闽赣系等五支。[24]
认识到这样的历史,“己”与“异己”就可以不断地转换。一种情况下是“己”,因而可以提出主位的体验,做自身人类学的研究;另一种情况下,研究者可以跳离出来,对“异己”做异文化的考察,就是研究者的自我他者化。正是因为中国研究的这种特殊性,其内部存在纷繁复杂的地区文明和民族文化,以及这些文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互动和衔接,使得其研究远比某个封闭的太平洋小岛来得复杂。国内人类学界一直强调要以民族志阅读、文献梳理、陌生化等方法来调整研究者,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的弊端,却没有提出一个方法论的路径。针对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以“旧知识”和“新经验”的推演,来克服中国学者所面对的“己”与“异己”杂糅的困境。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以我以上的思路来说,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25]实现这样的目的,我们首先需要使用类比推论的方法来突破“旧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
四、一种分析框架的可能
要突破学科传统对现实社会文化特征的遮蔽,就必须打破国家与地方两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虽然这种类似于“大传统-小传统”的框架有效地揭示了复杂社会内部的文化等级。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是简单的上下层关系,而是一个三角形的模型。历史上中国的任何民族都不是封闭在一个岛屿上,人群之间的互动才是历史的主流。这种互动使得他们各自形成了对自身的一套知识传统,同时也为双方的互动积累了一整套知识。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学研究中存在两套知识:一套是“观察者知识”(observers models),一套是“本土知识”(home-made models)。[26]如果将研究者与地方土著置换成一个地域范围内的两个族群,这就揭示出所谓的“地方知识”同样是一个“人看我,我看人”的认知过程。换句话说,“小传统”本身可能不是一套传统,而是一个互动的传统,即本群知识与他者知识持续交流的结果。但任何族群都不能脱离整体社会的历史进程,不同族群在互动过程中也时刻伴随着他们对于同一性的认识,他们共享着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纽带。所以在上述两种知识之外,还存在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认知这一套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是两套传统,而是三套传统在同时并存。自身、他者与国家构成我们认识族群活动的立足点。国家所代表的共享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制约着双方的互动,但同时构成相互转化的基础。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事物,已有学者以此框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华德英教授在对香港滘西洲渔民的研究中指出,这个群体与周围的陆上居民在交往中形成一种三角形的认知模式。他甚至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思维,并以此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能够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上保持连续性。其中直接模式(immediate model)是指他们对于自身水上人家传统的领悟和潜移默化;观察者模式(observers'models) 是指以观察者的视角对周边族群进行认识,成为展开互动的基础;意识形态模式(ideological model)是指自身与他者共享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双方联系起来,并为相互的转化提供可能。这三种认知模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关系,对渔民与周边居民的族群认同、生计变迁乃至空间知识都产生了影响。[27]
这种结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认知模型,更直接地展现为人们的行为策略。与香港一水之隔的珠三角地区,在流民向居民,疍民向汉人转化的过程中,国家为规范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的祖先与继嗣的伦理体系被用来作为适应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工具。[28]这里的类推主要表现在双方如何以宗族为共享的意识形态,以此去认识对方,并指导双方的行动。珠三角的宗族大多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这种文化手段赋予他们合法的成员身份,并把此外的疍民和流民视为不合乎礼法。另一方则为了巩固土地权利,通过合族聚宗、编写族谱、建立祠堂等手段向“汉人”身份靠拢。在这样的推拉过程中,创造出了一套最后为本地所有族群共同使用的宗族文化。其中基本的运行逻辑仍是“类别中的关系”,“类”以家为轴心,存在于“推”的过程当中;“推”的基本关系就是“礼”,因而产生以辈分为内容的“序”。[29]
如果以上述自身、他者与意识形态构成的三角模式来分析,彝族就是由三套知识混合界定的产物。族群成员自身、邻近族群和国家共同界定了什么是“彝族”。[7]其中国家掌握着民族识别以及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地方社会的族群间就以此来调整他们的历史,指导现实中的互动交流,以竞争类似“真正的彝族”这样的正统地位。还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市场力量的兴起推动少数民族重新“规范”他们的民族文化特征。人们往往以国家民族理论政策赋予的民族文化特征来进行展演,以满足游客对于少数民族的想象。民族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复杂性和变动性才是民族文化的本来面目。
五、走向模糊地带
人类学研究中的“推己及人”,就是从自身、他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异己”来理解“己”,通过“己”来认识“异己”。历史时期由“己”到“异己”的类推首先是承认有共同的文化理想存在,并且意识到双方都不完全符合这个理想,因而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但当下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所包含的变动不居与连续性,已经被固定为清晰的条目,大大削减了类比推论的空间。
因而,要发挥类比推论法的解释力,就必须破除上述的确定性和一致性,深入社会生活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中去。只有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才能生长出此类向彼类转化的过程,而变化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进一步来讲,也只有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对于某个民族或文化的研究才能类推到与他相联系的民族与文化。或者说,对于某个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其互动交流中,才能成为理解其他文化的基础,这样的人类学才具有扩展性。
首先,民族本身也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现象,而不是对象。费先生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曾说,“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有它的稳定性,但也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有些互相融合了,有些又发生了分化。所以民族这张名单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30]这就将民族识别过程中固定下来的“民族”看成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交往互动的连续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1]
其次,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和融合是构成民族现象的基本条件。我国境内的各民族从来都不是独立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民族都不会单独存在,它存在于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关系当中。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心”。[32]现有的民族知识明确并固定了民族交往的边界,这里的边界更应该是“边缘”。它不是单一的、清晰的界线,而是社会、文化和历史互动的边缘地带。这里存在的不是“单线历史”,而是“复线历史”。[33]我国民族发展的一个特征即是“变”。在几千年历史中,不同民族在交往、流动过程中有的分散了,有的融合了,有的嵌入了,有的迁出了。历史脉络中的分分合合与空间上的你来我往奠定了今天各民族交杂分布的格局。具体来说,民族交错地带在历史上就存在复杂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今日多元文化共生却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在民族结合区域的社会交往中,民族人口之间的流动、交往和互动,以及民族聚居区之间的影响与渗透,是与民族的存在同样重要的命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原来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日益频繁的族际人口互动现象,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流动的现象也日益突出。这就对于突破现有话语下空间固定、边界清晰、文化明确的“少数民族”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再者,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不存在清晰的边界。民族国家书写的文化交流史把一个“与他者的邂逅”简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条块化的内容。如果回顾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并不是内部中国人自身的自我审视,或者外部压力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这两者的关联方式,通过“外”来发现“内”,通过“内”来理解“外”才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34]“内”与“外”都不是一致的整体,而是包含着若干“他者”与“自我”的复杂结构。这个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情境性,双方伴随具体的政治与文化情境而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其中不论是哪个方向,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外部的。[35]但是遗憾的是,较少研究从此出发反思僵化的一致性话语,以“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和地方性来讨论国家话语、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多种可能。
立足当下,中国社会经过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然打乱了原有的文化和空间格局,大量的人口亲身参与到各种洪流之中。当流动成为历史的情境,人类学研究者所面对的每一个社区,都既是本地的,又内涵整个宏大体系。“自我”不再是原来的自我,“他者”不再是原来的他者,“国家”也不再是原来的国家。当流动成为这个时代的现代性之后,它们都具有弹性,每个身处其中的单位都具有“推己及人”的伸缩性。这对于人类学而言是相当幸运的,传统上需要“跨文化并置”才能获得的跨文化理解,现在就存在于“己”与“异己”在空间、时间和文化上形成的连续体之中。这种对于本文化的自觉和跨文化的理解,并不是人类学研究者所揭示出来的,而是作为洪流中参与者的“己”在各种关系中“推己及人”的领悟和感受。人类学者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梳理“己”与“异己”之间的类推过程,来寻找共享的文化理想,进而找到跨文化交流的基础。
结语
传统人类学强调建构一个异质的“他者”,这种认识论不仅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并且难免会建构出一种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而就我国的实践来看,人类学学科的特殊发展历史进一步导致了概念的固化,将“他者”这一多层级、多面向、多时空的概念体系固化为“少数民族”,确定地指向“落后的”、“待拯救的”、“需要帮助的”群体或文化。而“推己及人”等传统思想强调文化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重视“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互动转化。事实上前辈学者已经在扩展民族边界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潘光旦先生对于土家族历史的研究从时间纬度,费孝通先生对于民族走廊的讨论从空间纬度,都突破了民族调查与识别所带来的知识限制。以此来理解“他者”或“异己”的多维性,会发现村寨层面上的“异己”在地域可能就成为“己”;地理空间上的“异己”可能正是文化传统上的“己”;而当前的“己”可能在另一个时间点上就是“异己”。这种多维性带来的变动不居、模棱两可构成了类比转化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深入发掘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背景下的自身人类学传统,有助于我们突破西方赋予这门学科的认识论限制,从而形成新的学术气象。
[1]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2003,(3).
[2]麻国庆.从自身人类学到国家主义人类学:中国人类学学术取向的演变[J].清华大学学报,2018,(1).
[3]George W.Stocking.Jr.Afterward:A View from the Center.Ethnos.47:172-186.
[4]Frank Dik?tter.Global Science,National Politics and Assimilationis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Chang,B.and He,T.(eds.),State,market and ethnic groups contextualized.Taipei:Academia Sinica.
[5]费孝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A].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6]谢扶民.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总结[J].民族研究,1958,(1).
[7](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8]范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J].世界民族,2008,(6).
[9]陈建樾.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国族的整合历程——基于美国的考察[J].世界民族,2015,(1).
[10]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11](日)中村元.東洋人の思維方式[M].東京:株式會社春秋社,1988.
[12]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1980,(2).
[13]陈孟麟.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J].中国社会科学,1985,(4).
[14]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15]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0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17]张晓芒.中国古代从“类”范畴到“类”法式的发展演进过程[J].逻辑学研究,2010,(1).
[18]何翠萍.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几个个案谈“己”与“异己”的关系[A].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C].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
[19] Yu Ying-shih.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Sino-Barbarian EconomicRel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20]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北京:三联书店,2010.
[21]陈连开.中国 华夷 蕃汉 中华 中华民族[A].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2]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3]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A].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4]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台北:集文书局, 1975.
[25]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A].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26] Levi-Strauss,C. Social structure.A.L.Kroeber(ed.)Anthropology Today.Chicago:Chicago U.P.I953.
[27]Barbara E.Ward.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Man.1966,(No.2)p.201-215.
[28]刘志伟.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社区[A].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C].2003.
[29]麻国庆.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J].文史哲,2008,(4).
[3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七卷) [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A].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1997.
[33]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4](日)村田雄二郎.連續與變化的世界以及與他者的邂逅[J].朱琳,译.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シリーズ20世紀中國史』第1卷,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
[385(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