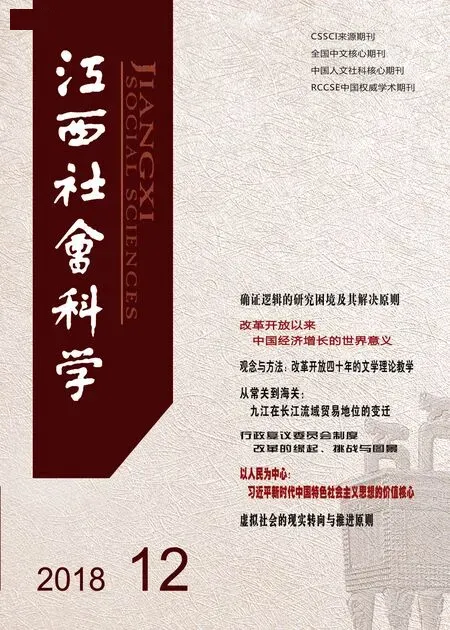大众媒介与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
——以《申报》政府公告为例
《申报》是上海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之一,在承载和传递信息方面对市民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素质的培养和塑造起着重要作用,能够整合市民意识。工部局利用报纸这一传播功能,将政府当局有关公共租界市政管理的有关公告刊登于 《申报》之上,借此宣传西方的近代城市管理理念,警告并争取界内居民配合,提升居民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工部局正是利用这一传播媒介构建和扩展了界内市民公共文化空间。
公共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的公共问题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定,而公共政策的实现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介实现其与公众的联系。大众媒介也就成了政府当局告知、宣传市政政策及沟通并取得公众支持的最佳渠道。由于大众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引导和培养公众规范地适应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实又有着教育公众的功能。近代上海租界工部局正是利用了大众媒介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对公众进行劝服,争取民众的同意和支持,从而使公共租界的市政建设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工部局研究一直是上海学研究的热点,成果颇丰①,但相关研究几乎都借助工部局会议记录档案及工部局《公报》和《年报》等官方资料为切入点,本文另辟蹊径,以《申报》所刊工部局颁发的政府公告为切入点,从传播学、历史学角度探讨工部局在城市公共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工部局与大众传媒在上海近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
一、工部局对大众媒介的重视
上海工部局成立于1854年,根据《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第二次土地章程》),英美法三租界合并,工部局为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之后由于英法矛盾加剧,法国于1862年退出合作,自立上海法租界。英美两租界则于1863年9月21日正式合并,合并后的英美租界被外国人称作 “外人租界”(Foreign Settlement) 或 “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Foreign Settlement North of Yang-Kinp-pang Greek),中国人则称之为上海英美租界。之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1899年又改称“国际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或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简称公共租界②。自此工部局便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界内一切市政事务。工部局作为公共租界唯一的市政管理机关,几乎由西人独立把持,必然在市政公共建设与管理中渗透着西方近代城市管理的先进经验与科学理念。
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传递的直接性和迅速性,它能快速地把工部局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便最短时间内争取界内更多居民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政府运用大众媒介能够广为告知民众市政信息,从而引导民众参与,最终使工部局的市政管理理念得以实行。因此工部局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尤其是善于利用大众传媒在发布政令、塑造政府形象、培养公民意识等方面所发挥的舆论影响。工部局通常采用张贴告示、通知及散发传单等方式向界内居民传达政府之政令、通告,但收效甚微。于是租界当局便承办自己的机关报刊,并栽培半官方的报刊,运用报纸传媒来推广并贯彻政府的施政举措。“从1861年至194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公董局主办的各种机关报刊至少有十余种”[1](P163),其中发行量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工部局公报》和《工部局年报》。但《公报》和《年报》大都为英文版,主要面向外侨,且出版周期颇久,因此限制了传播的广泛性与时效性。此外,租界当局还通过半官方性质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850—1866)、《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1866—1951年)来发布政令及各种信息。《北华捷报》素有“英国官报”之称。同理,《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亦为西文报纸,仅供界内外侨阅览,受众范围狭窄。
鉴于公共租界华人居民居多的人口现状,以及中文报刊的迅猛发展,租界当局便在华文报纸上登载广告,也向华人居民发布政令。具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申报》赢得了工部局的青睐。“《申报》既刊经国大事,也刊闾阎所闻;既有生意行情,又有吃喝玩乐。特别是《申报》发刊时连续惹起两场新闻竞争和若干则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2](P57)(如 “杨月楼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郭嵩涛画像案”等),引起社会广泛注意。而且当时《上海新报》《字林西报》与《申报》竞争激烈,两报对《申报》在报道中时时为中国人说话的情况进行指责,反而更使得《申报》受到上海市民信任。时人用“申报纸”来指所有的新闻纸,可见《申报》影响之大。因此工部局在《申报》上刊登政府公告,扩大其在华人中的影响,以此来形塑和培养居民的现代意识,并运用大众传媒对社会进行整合,共同致力于公共租界的市政建设。
二、《申报》所刊工部局市政举措
大众媒介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公众报告重要的政治信息,工部局制定的政策通过大众媒介传达到它的目标对象后,借助媒介的宣传效能,工部局市政管理公告之内容、重要性、便利性及违反政策应受到的惩罚等,皆能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与宣传。宣传的过程也是教育劝服的过程,政策的执行有赖于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培养,大众媒介通过登载政府公告的形态倡导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介绍西方先进的市政理念,批评并纠正民众(主要是华人)的传统观念和行为偏差,能够引导民众培养卫生意识与环境意识,培养和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工部局在《申报》上登载政府公告,利用媒体搭建互通平台,既是大众媒介实现其功能的过程,也是政府对公众进行劝服的过程,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一)公共交通
“城市交通管理是近代城市基础性管理和社会公共秩序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维系都市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近代都市居民法制意识的启蒙课堂。”[3](P137)传统中国由于生活节奏慢,交通工具落后,车、轿、人的矛盾不突出,导致人们随意行路,没有所谓的交通规则概念。但日益发展的上海租界却是一个别样的世界,“上海出现了与世界其他大都市截然不同的一种独特现象:速度最快的汽车和速度最慢的手推车同时大幅度增加,一起拥挤在狭窄的马路上,从而出现了人与车争道,车与车争跑之独特的交通状况”[3](P166)。车多加上行人不懂行路规则,交通状况的恶劣可想而知。为了确保行人安全及道路通畅有序,工部局于《申报》上相继刊登有关交通规则的政府公告,面向大众,扩大传播影响,从而提高居民的交通和法制意识。如其1872年6月26日告示:
一、凡马车及轿子必于路上左旁行走,或马车及轿子于路上行走后,又有马车或轿子行走,如前之车轿走快则后跟之马车必须赶从右边过去。一、凡轿子往来必由大路,不许从旁路行走。一、凡小车必由路左边往来,惟不许走旁路,即由大路与旁路相近之路行走。一、凡小车必在定规之处,毋得于路上往来逗遛。一、凡马车自日落一点钟之后至日出一点钟之先必得点灯,如违章程,每车罚洋五元。一、凡马车于十字路来必得走慢,譬如地界内西至东为马路,北至南为岔路,如车由岔路上来,必得谨防马路之来车碰撞。一、凡街道上跑马以及马车往来,巡捕人必得照应不准过速。
公告明确规定了车、轿、人的行走规则,且就马车和汽车又做了具体划分,强调“汽车左行,轿子中行,行人傍走”,同时还强调汽车专区停靠,马车按时点灯,会车时减速让道及交通限速等问题,并附有违规处罚规定,要求“巡捕必须依此办理”,使该《章程》具有法律强制性质。而“车人分道”的交通举措,既可加快车辆行驶的速度,保障交通顺畅,也可确保行人安全,对公共租界交通的改善大有益处,理应得到人们(华人)的热烈响应。但囿于传统积习,行路规则公布后,一时之间,华人难以适应,纷纷反对,并发出“马车可行,人岂不能行”的诘问。传统社会使用的大都是人力或畜力的慢速交通工具,叫停及时,故发生碰撞事故时危害不甚大,更何况过去的城镇道路狭窄,筑路条件又不成熟,行人在路边行走反倒不安全,这与西方近代城市恰好相反。
近代新式交通工具迅猛发展,上海车辆“从1901年至1912年相距不过11年,其数已达294辆。平均每年增多27辆,其增加不可谓不速。自1913年起至1922年,10年之内之增加更形显著,每年平均竟增352辆,较前11年平均增加之数高出13倍,若以最近4年(1919年至1922年)观之,则每年平均之增加达500辆。此诚上海汽车事业之速力。今若以此类推,再隔10年,则其数目之巨更有客观也”③。车辆的持续增长及人口的不断膨胀,加重了交通负担。为缓解交通压力,工部局实行“限制行车”,规定具体路段在规定时间内单向行驶,与现代交通之“限时”“限号”等有异曲同工之处。如《申报》1919年5月1日公告:
工部局布吿,实行限制行车:工部局布吿云,案查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本局布吿,自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为始北京路与爱多亚路间之江西路及四川路,各项车辆在午前八时至午后八时间,仅许向一方向驶行。至将来通吿时再行变更其方向,如左江西路车辆由南而北,四川路车辆由北而南。
正是基于车辆增多、行人交通理念缺失、交通事故多发等现状,工部局不断改进和完善租界内的城市交通管理规则,“从1872年工部局制定行路章程到1903年《上海工部局治安章程》中的《马路章程》,再到1921年1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交通规则》。此外,为了弥补《交通规则》的不足,工部局还适时补充一些专项法规。如1922年颁布了《新单行道规则》、1935年通过了《取缔汽车滥揿喇叭》以及其他针对各类交通工具的管理规定等等,这些规则对于规范、监督车辆和行人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交通事故隐患至关重要”[3](P188)。工部局发布之交通公告借助于《申报》的社会影响力传达到市民生活中,通过广告传播的重复性和广泛性,加深了交通规则在市民头脑中的印象,从而宣传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交通管理理念。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众尤其是华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参与意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营造相对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如“1933年至1941年间,不仅公共租界辖区内华人交通违章被起诉者比例逐年下降,捕房报告的交通违章案件涉及者从53054人减少到27505人,在1938年一度只有17632人”[3](P198),这一数据变化可谓民众(主要是华人)交通理念提高及工部局交通管理成绩有效的佐证。此外,工部局的交通举措也对华界及中国其他城市交通管理的近代化起了示范作用。如上海县城或华界路政的兴起即是租界的示范推广,其颁布的《沪南新筑马路善后章程》涉及车辆捐照、行车点灯、禁止驰骤、不准堆物碍路、店铺招牌需高悬至少离地七尺等24款④,“均系效仿租界章程,次第妥为举办”。所以时人评价“上海各路政,占全国之冠,又阔又平。假使走惯了上海的马路,再走内地的石子街,不但要嫌地高低不平,更其要觉得地狭得无从投足”[4](P56)。
(二)公共环境
上海租界早期公共环境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道路清洁、垃圾粪便清除等基础性环境卫生,且这一基础性环境管理早在1845年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第18条中已提出,具体如下:
界内不许架造易燃之房屋,如草寮、竹舍、木房之属,所有可危害人民之商品,均不得贮藏,如火药、硝石、硫磺及多量酒精之属。公路不得侵占,如屋檐耸出,及堆积物件等事,又不得堆积垃圾,及疏泄沟洫与街上,亦不得当衢叫嚣滋扰,以免妨害他人。凡此限制,无非为求商人房舍财产之安全,与社会之安宁。[5](P49)
《第一次土地章程》以条约的形式粗略规定:公路上“不得堆积垃圾”,不得“疏泄沟洫与街上”,以此保卫“人之安全”和“社会之安宁”。但受制于“华洋分治”,该项有关公共环境管理的规定主要面向外侨,因此其社会影响相对比较狭小。之后随着公共租界的建立及“华洋杂处”的不断扩展,华人成为公共租界的主要人口构成部分。工部局为了改善和维护租界的公共环境,提高居民(主要是华人)的环境和卫生意识,于《申报》上也登载政府相关公告,就道路清洁和垃圾粪便清除提供具体管理措施,希望“各居民人等一礼遵照毋违”。告示如下:
为再行明白晓谕事照得《租界章程·第十四条》,开栈各屋须设篷漏,俾便行人。为此明白钞录该章程,仰各居民人等一例遵照,毋违特示。《十四条》:凡遇街道接连或近路各居民既得工部局发去之文,令限十四日装设檐漏,与房屋之面同长。或从邻房接连或用水管从檐至地,俾水流下,以至水从房屋檐,或从门头檐俾下流,而不至流着行客,亦不准流在边路之上,如限内不听令承办,即可罚银。以逾限每日洋十一元为限。⑤
该告示在登载《申报》之前,已经发文到各街道及近路居民,且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十四日)内必须“装设檐漏”,且“与房屋之面同长”,保证雨水、污水的排放,“以至水从房屋檐或从门头檐俾下流,而不至流着行客,亦不准流在边路之上”,既便于行人,也有助于道路的维护,从而保证马路环境的清洁,减免道路的泥泞肮脏。同时为保证执行效力,强制实行“罚银”,“逾限每日洋十一元为限”,将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捆绑到一起,督促居民执行政府的管理措施。
工部局谕英美租界居民、铺户人等知悉。凡本局每日各路打扫洁净之后,一概垃圾不得再在大街小巷随意倾倒,再有《倒粪章程》亦开明于后。一概挑夫人等所挑粪担,须要用木盖将桶盖紧,倒粪时候,夏天即英三月十五号起至英十一月十五号为止,每晨八点钟为止,一律挑尽。除山东路之西一带,许迟至九点钟为止。冬天于英十一月十六号起至英三月十四号为止,以上午九点钟为止,一律挑尽。除山东路西一带即迟至十点半钟为止。惟独南京路于夏天早上八点钟为止,冬天九点钟为止一律挑尽。⑥
道路清洁不仅关系到市容,且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出行。工部局雇人每日清扫街道以确保道路的干净整洁,但道路的维护还需居民的配合,因此告示警告居民不得“随意倾倒垃圾”,“倾倒垃圾必须在早晨9点之前,违者将要受到告发,被告者将受到警告、居留或经济罚款等处罚”[16](P141)。《倒粪章程》更是详细陈列挑夫人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责任,从而保证粪便的清除。为保证空气质量,减少环境污染,特意“用木盖将桶盖紧”。通过对垃圾、粪便等污物的处理,工部局为租界营造了一个相对洁净的环境,以致租界与华界环境卫生状况产生了巨大差异:“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6](P68)郑观应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7](P663)此外,1872年5月18日《申报》刊登之竹枝词亦有此论:“双马轮车夹马车,钟潮辘辘起尘沙,却劳工部经营好,洒扫街前十万家。”“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
(三)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卫生防疫,即传染病防治。上海公共租界由公共卫生处负责具体卫生事务,其工作人员大都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各工作部门(5大部门)又能互补协作,因此当传染病来袭时,工部局能够及时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兹以霍乱防治为例。1873年8月,外国驻沪诸领事照会工部局,曼谷、新加坡两地发现霍乱。有鉴于此,工部局立即采取相应卫生预防措施,并广发告示,呼吁居民高度重视,8月8日《申报》亦刊登相关条例,具体如下:
一、凡居屋或租屋于他人者,须逐时巡查。将所有泄水引沟、积秽池坑等处,皆行修整,不使秽物堆积,以十二时为率,不可多延留。或于臭气熏蒸处,仍用解臭药以除毒害云。一、凡目睹何事有碍于除病之道者,或于公路,或于人家人地,仰均来局通知,以便即行移除。一、本局向定例章二十九及三十条者,系干禁积壅粪土与各等秽物,并房屋,须清洁沟厕池坑,务必留心。今该例更加从严施行,其各凛遵以扫除秽气,免致疠疫感召,和平是本局之所厚望也。
工部局为了预防霍乱,采取以消毒和隔离为主的防疫措施,增大巡查力度,注意保持公共环境的干净,尤其加强对容易滋生病菌的“泄水引沟、积秽池坑”等地的修整与消毒,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传染病预防工作,“目睹告知”,“即行移除”,使霍乱预防成为界内全体居民之共同责任,而非只是政府的公共职责。而当霍乱发生后,工部局又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给予无偿治疗,免费防疫注射、隔离医院互相配合,最大力度地控制疫病蔓延,以确保界内“和平”:
照得本局现将举行预防霍乱之免费注射。望华籍居民一体注意。凡欲免费注射,而欲知其详情者,须直接向距离最近之卫生分处询问。或直接与往来界内各处注射汽车队之主任医师接洽。各雇主之欲为其所属工人注射者,亦可商请办理。(电话一三○六八号)⑦
更为重要的是,工部局还注重通过公共媒介的传播与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开展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1916年《卫生处年报》认为“中文版公共卫生通告的发行已被视为普及卫生常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工部局广泛散发了“日常公共卫生通告,结核病、天花、霍乱、传染病预防及灭蚊通告”。到1923年,各项卫生通告已分别有中文、日文、俄文版本。这些传单和布告,在卫生处专设的“宣传橱窗里,各卫生分处边的水泥墙上、卫生处告示牌上、工部局所建厕所边的水泥墙上张贴。并经许可张贴在电线杆上”,同时还“张贴在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8]《申报》所刊登的相关防疫告示,只是当局公共宣传的缩影,通过报纸广告灌输工部局有关公共卫生的理念,以便增强居民对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视,尤其是对肉类卫生的检查,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降低诱发疫病的风险,从思想观念上提高居民的警惕心,为疫病的防治做了思想上的宣传动员。
当然也不可否认,租界、西人与华界、华人的卫生理念有着相当差别,这势必导致工部局在推行相关公共卫生管理措施时引发矛盾甚至冲突,如1910年发生的“鼠疫风潮”⑧即为典型案例,这场冲突“既反映了西人凭借公共卫生的先进理念与技术为所欲为的一面,也表明了华人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无知的一面。屈辱、愤恨、抗争与惊羡、懵懂、犹疑等各种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大部分民众对传染病表现出恐惧心理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3](P141)。正是在这样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民众逐渐克服对传染病的恐惧排拒,疫病防治也由迷信无知走向科学理性,实现了中西卫生理念的调适与融合。
(四)公共治安
维护界内社会治安稳定是租界当局进行“国中之国”统治的前提,也是其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与归宿。尤其对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不稳定因子,如不法分子、过激行为、非法言论等,当局严格执行《治安管理章程》,防微杜渐也好,以绝后患也罢,总之工部局对界内社会秩序的安定团结做出了相当的努力。
为了“维持公共租界内之治安及良好秩序,并保护所有安分住户”,工部局通过《申报》登载的相关告示,不仅在于打击不法行为和不法分子,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和宣传方式,向居民灌输监督、举报不法行为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近代市民。确切地说,《申报》是转载工部局告示的社会舆论平台,一是警告居民及不法分子,敲山震虎;二是鼓励居民监督、举报不法分子,防微杜渐;三是扩大工部局的社会影响力,运筹帷幄。如对“不安分之徒以及无赖土棍勒钱吵闹”,一经举报,“提拿不贷”⑨;对“冒充暗捕,倚藉势力假公济私向平民索诈”⑩等不法行为和非法举动,当局鼓励居民控告、举报,并承诺“事若有凭,即当尽法惩办不贷”。对“囤积垄断投机渔利”者“依法起诉”[11];对“有人前来恐吓勒逼关闭店门者”,“散发煽惑人心之传单及悬挂旗帜,有直接激动扰乱公安者”,“造谣或散布谣言者”及“故违本局布告”者,皆“严行惩办不贷”[12]。更有甚者,“凡在界内街衢成群结队,一概不准”,“如无合法之事,不得在道路闲游”,“合行警告一切界内居民,自夜间十时至次晨五时止,概须留居户内不得外出”。[13]从其规范、实施的范围及力度来说,工部局有关社会治安的管理趋于越来越严密,客观上有助于界内社会治安的稳定,但也加大了居民控制,使其处于工部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丧失了人格和国格。尤其对抵制日货的行为,工部局采用“一刀切”方式,妨碍甚至企图消灭界内华人的爱国情绪,客观上包庇纵容了日人,如《申报》1919年5月20日公告:
照得本局现闻有一种人,印发传单,煽惑恐吓违法强迫界内华商及居户,不购日货,扰乱治安。尔等须知,此种行为有违法律,如有人强迫干涉华商及居户买卖购用各货之自由权,一经查出,照违法例拘拿罚办。尔众商民人等,如遇有人前来骚扰,应即报告,就近捕房。即由捕房将扰害人拘拿解送会审公堂,或其他该管公署。照律严办决不姑宽,其各遵照母违。特此布告。
此则公告看似客观公允,旨在维护“华商及居户买卖购用各货之自由权”,实则重在控制、打击甚至取缔界内激进爱国团体(及个人),抑制华人的爱国热情,防止华人受“蛊惑”由“不购日货”最后发展到“不购”或“抵制”英货、美货,从而殃及自身利益,因此概以“扰乱治安”之名“照律严办决不姑宽”。当然并不排除有不法分子趁机故意扰乱社会秩序,恶意竞争,打压商贸对手,但工部局仅简单粗暴地以“扰乱治安”“煽惑恐吓”加于“发传单之人”,并鼓励华人互相检举告发,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综上,工部局为了维持公共租界的稳定和发展,改善交通、卫生、治安等公共环境,于《申报》上刊登工部局有关市政建设的政府公告,宣传当局的市政举措,号召并呼吁居民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同时予以警告。借助传媒力量将政府当局的市政建设理念传达并渗透到居民中间,既扩大了当局的政治影响力,也培养了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为公共租界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上海的城市化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结 语
上海公共租界的发展与上海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而城市化的基石则来源于近代化的市政管理。租界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特殊存在,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也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先驱,是西方近代城市管理理念、经验在中国的最先移植。“在近代中国众多租界中,上海租界是殖民地色彩最强,形态最完备,结构最为系统的一个。”[9](P1)仅仅在100多年的时间之内,上海便轻易地走完了西方城市的近代化历程,这与租界的设立及城市管理模式的先进性不无关系。
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民众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重复放映,形成对市民意识的整合。工部局通过《申报》这一新闻传播媒介,将政府公告广而告之,通过传媒向居民灌输了诸如公共卫生意识、现代交通意识、社会公德意识以及现代法治意识等现代意识,这些观念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型塑着上海民众,使其所接受的现代公共意识逐渐变化为生活习惯,继而提高居民(主要是华人)的参与意识,所以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共意识远胜于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乡村地区。城市居民整体公共意识的提高,反过来也减少了城市管理的阻力,降低了管理成本,从而更进一步加速了上海租界的发展完善。
同时也应看到,工部局利用广告效应传递近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时,也会引发一些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1911年工部局为防止鼠疫传播,在疫情非常严重的虹口一带(租界和华界交界区)实行消毒检疫,引发了华界市民的抗议和冲突,最终酿成“清末检疫风潮”。又如19世纪末工部局以加增执照费的方式调控租界内手推车日益膨胀的局面而引发“小车夫抗捐事件”等。这类由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所引起的冲突事件,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调适的过程,它暴露了民众对公共卫生、交通等现代市政管理的不解,以及对工部局雇员巡捕蛮横粗野行为的反抗,更是对以租界当局所代表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实行“国中之国”统辖的一种民族抗争。但是由于工部局在租界所实行的市政管理在总体上有益于城市良好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建立,且使租界城市环境远远优越传统华界,两者形成巨大反差,即所谓“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同时也便于上海民众的衣食住行,有利于城市民众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能够被多数上海民众所接受。
注释:
①与本文论述相关之研究如下:樊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力监管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刘文楠《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焦存超、陈业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新式粪秽处置系统的原因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罗振宇《私营到公用:工部局对上海公济医院的管理》(《史林》,2015年第4期),罗振宇《“救己”到“救人”:工部局早期医疗服务与城市公共医疗的起源(1854—1898)》(《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等等。
②吴志伟在《上海租界研究》一书中认为,“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总共28册中,中文名称为西人租界、公共租界、外国租界的词语反过来查找相对应的英文,总记录得916条。则the Foreign Settlement始自于工部局建立的1854年7月,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the Foreign Settlement North of Yang-King-Pang)这个名称最早使用是在1867年2月11日,该词约在1894年后基本就不用了。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称呼,从《会议录》上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取代the Foreign Settlement”(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2页)。
③见《申报》1923年7月28日工部局公告。
④见《申报》1897年1月20日工部局公告。
⑤见《申报》1880年7月20日工部局公告。
⑥见《申报》1886年4月27日工部局公告。
⑦见《申报》1932年6月1日工部局公告。
⑧《东方杂志》1910年第11期《上海验疫风潮始末记》详细记录了“鼠疫风潮”。
⑨见《申报》1878年1月14日工部局公告。
⑩见《申报》1909年12月16日工部局公告。
[11]见《申报》1940年3月14日工部局公告。
[12]见《申报》1919年6月7日工部局公告。
[13]见《申报》1937年8月16日工部局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