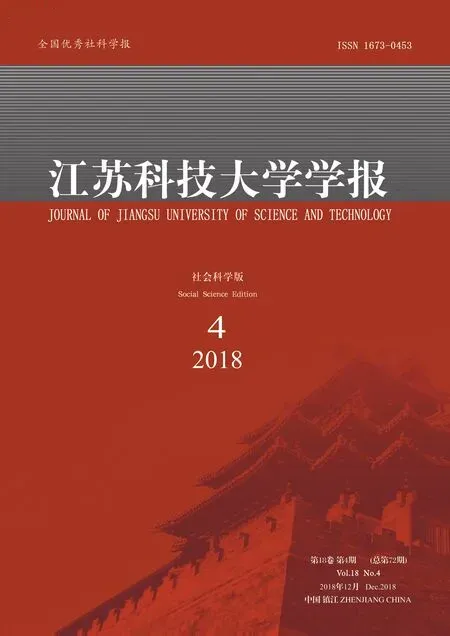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庙堂指向
金周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1600)
晚清民初,在新小说方兴未艾时,作为古典小说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逆势而起,红极一时。胡适就曾言明:“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等等续编。”[1]可见其影响超过同一时期其他较高水平的小说,占据文坛中心,影响颇大。
但后世学者站在新文学立场上多持贬斥态度。除了对其迷信宣传、模式化结构进行批评外,最主要的还是集中于批判此类侠义公案小说的价值倾向。在当时新文化人看来,侠客归顺朝廷,是对本应行走民间守护世间公平正义侠客精神的背叛。鲁迅的批评奠定后世基调:“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2]之后的学者也多持否定态度:“这样一种文化追求在清代已完全变质,以塑造为一大僚隶卒的鹰犬式侠客的侠义小说,标志着这一时代的大众的文化境界并没有随着时代进入近代。”[3]“侠客不再反抗官府,而是归顺大清王朝,帮助统治阶级去捉拿、剿灭所谓‘强人’、‘恶霸’,基本倾向是反动的。”[4]这些评价主要是对本应重气轻死、义气相兼的侠客与权力合谋持否定态度。
实际上鲁迅等人潜意识里真正否定的却是侠义公案小说中逆时代潮流的儒家陈旧理念。这种陈旧理念以“三纲五常”为代表,尤以忠君思想为核心。对于传统庙堂指向两个关键问题——途径和目标,虽根据时代替换了部分内容,却做了实质保留。后世因侠客刚毅自由的英雄主义人格被权力规训而集中批评侠义公案的庙堂指向,这有失公允。因此,向前看,侠义公案小说这种庙堂倾向并不是一种“突变”,也不是对历史上侠文学乃至侠文化精神的一种背离,实际上还是一脉相传地承继着侠客历史及其侠文学传统的特点;向后看,当忠君思想被剥离后,这种在侠义公案小说中存在的庙堂指向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程度地彰显。启蒙者对庙堂指向的默认态度也多见于此。从晚清尚武任侠思潮中梁启超等人“侠客救国”的主张,到民国武侠小说中对现代 “侠忠”的演绎以及新文学中郭沫若对侠客历史戏剧的再改编都是明证。审视五四新青年一代命运的轨迹,也可提供佐证。造成启蒙者批评偏移的原因,在于将思想进步性作为批评标准。对于侠义公案庙堂指向的批评,问题虽小,背后却牵扯了现代文学几个重要问题。文学的主体性、人民性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纠葛以及亚文化的健康发展,这些恰恰是这种批评偏移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 关于传统儒家的庙堂指向
儒家的学说浩瀚复杂,究其本义来说是一种尚群文化。它讲究群体意识,着眼于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关注个人本身自由独立的发展,拒斥个人中心主义。这些均是它持群体本位主义观点的体现。将这些学说按方向分,主要是“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内圣”讲究对个人修养、道德的培养,“外王”则指的是注重经纶天下的外在事功。这两者也就是钱穆概括的“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历史上两者发展并不平衡,宋明理学一度将儒学演化为“心性之学”,出现单骑突进现象。直到清代“经世致用”思潮推动下,儒家重新将目光更多投射于现实社会,如何构建和实现理想的现世秩序成为儒家的重心。这也符合孔孟时期儒家初衷,否则也就不会有孔子周游天下十三载以求安邦定天下的事迹传于后世。在此问题上,儒家以群体意识为导向,提出了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将个人置于家庭之“孝”和君王之“忠”的依附中,构成“家国一体”格局。这种群体意识究其本质是凸显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秩序的建设,“心性之学”价值凸显。它是实现“外王”的基础,通过心性修养的追求将其内化为价值目标,并落实在日常实践中。
但对知识分子而言,在“心性之学”基础上还有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得道”之后更要“弘道”。弘道途径在于庙堂指向。的确,“弘道”的途径一般来说有很多。著书立说、讲学育人都是很好的方法。这也就是陈思和教授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背景,总结现代文学经验教训时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民间的岗位上依然可以坚持理想、传承道义。但是实际上,包括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内,传统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独善其身是世道不显的无奈之举。他们更渴望的是居庙堂中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因此,庙堂指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实现儒家理想的唯一正统的途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儒家理想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它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巩固统治的基础上。比如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受后世称道,但他的论证思路却是从庶民的生产力以及在争霸中的生力军角度予以阐释。他劝诫君王,直言利弊也并不是反现世的君王而是着眼于后世的统治。一代明臣海瑞直言天下乃帝王之家,就完全站在家天下的立场,乃至嘉靖去世痛苦不已。可见儒家是帮助君王构建合理现世秩序。当然有些人“仕以行道”,会有功名追求,这虽不是儒家本义,但与“弘道”并不必然冲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既能占据社会中心,备享尊荣又能为兼济天下寻找一个良好机会,何乐不为。
根据以上内容,简单归纳古代儒家中的庙堂指向含义,就是儒家希望士人能居庙堂中心,“得君行道”,借助“势”的力量,兼济天下,构建理想的现世秩序。将其拆分,就牵扯到几个重要问题。它的途径是借助君王之势占据社会中心,以此影响天下决策。它的目标是实现儒家理想也就是构建理想的现世秩序。这种现世秩序是为君王服务,以群体意识作为它的价值导向的。侠义公案小说的庙堂指向被否定,总的来说是以忠君为代表的儒家陈旧理念被否定。但若仔细分析,它否定的庙堂指向中有两点。一是途径上,它否定了弘道要“得君”的观念。二是目标上,否定了儒家构建理想现实秩序的具体模式——“君臣父子”,因为这种现实秩序是为君王服务的理念。但是庙堂指向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却做了保留。首先,从途径角度看,后世启蒙者认可了要弘道必须占据社会中心的理念,而不是坚持退守书斋、治学育人的岗位意识。从目标角度看,启蒙者首要目标不是在于文学上的建树,而仍在于构建合理的现世秩序,具体反映于那个时代的就是如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
二、 侠客庙堂指向的历史传统
侠客庙堂指向既融于儒家理念而被实践,它代表一种传承。在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是核心观念,文并不具有独立地位,它的地位取决于道。就像袁进分析那样,越贴近于道的,特别是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文的地位越高。文人真正推崇的都是“文道合一”之文,都把文、道、学、教视为一体。处于文学中心地带的虽然地位高,但是受到束缚也越大。而侠文学虽然处于边缘地带,重市民意趣,但并不代表不受到“载道”压力,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
(一) 侠客传统
从整个侠客史看,侠客或受客观环境影响,或受功名之心驱动,乃至报恩之心的感召。他们在不少时期都与庙堂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大变动时代的风标”[5]28。和平年代,侠客秉持的价值观及其不受拘束的行为会对传统道德规范、朝廷的统治秩序有消解冲击的作用。因此自西汉以后,每于王朝兴盛,侠客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排挤。但是每于乱世,侠客都会不同程度参与到庙堂纷争中。先秦游侠就是在乱世横流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战国时代,很多公侯之家养门客风气盛行。其中多为有名侠士,他们报恩情纾国难,上演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大剧。比如聂政受严仲子礼遇刺杀韩相侠累,虽成功但因寡不敌众自杀而亡。类似还有魏子、冯媛、豫让等亦名垂青史。在后世,此种情形不断上演。东汉末年,豪雄角逐,中央权力分崩离析。众多侠客“既度其势之广狭,又量其德之厚薄”[6]76,选择明主建功立业。典韦、甘宁、徐庶虽名将传世,但也实以布衣侠客进位。这种进位方式,也是许多侠客的人生发展轨迹。李世民招贤纳士,广纳英豪建成帝业。后世唐代名臣多侠客出身,比如刘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生产”[6]95。类似还有在北宋靖康之役的李彦仙、孙益等,素豪侠,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可见侠客虽所持价值观与正统儒家文化有冲突的一面,其行为亦乖张不为法律所容,但在乱世中,侠客与庙堂多保持千丝万缕联系。君王多器重其勇毅,招贤纳士,使其逐鹿乱世,并出现两种轨迹。一是慷慨赴国难,以死殉国;一是从龙跟明主成为开国元勋。
(二) 文学传统
文学作为现实的反映,从整个侠义文学史看,侠客与庙堂的纠葛亦是重要题材。汉代《史记》虽是史书,却是最早较完整记载侠客事迹的文学体裁,对侠文学有深刻影响。上文所述的诸多历史侠客群体,荆轲、专诸、郭解在战国风云中的事迹都被收录,对人物描绘亦有小说风韵。到了唐代,唐传奇一直被视为武侠小说的萌芽,出现了许多类武侠小说。从侠客与庙堂的关系考量,有《聂隐娘》《红线》等诸篇写侠客效力藩镇卷入唐代乱局中。这实际是唐代繁镇割据、刺杀之风盛行的表现。侠客虽有“私剑”的成分,却不违背侠义之道,比如《聂隐娘》中的聂隐娘奉魏帅命令刺杀节度使刘昌裔,但看到刘氏贤明能干,不仅放弃刺杀还保护刘氏。刘氏进京,聂隐娘婉谢刘氏,选择寄情山水。而刘氏死时,她则大哭拜祭。从她身上可以看到侠客慕义感恩、临难不苟的品质。同时代的唐代诗歌更加值得品味。边塞诗在盛唐兴起,蔚为壮观。如杨炯在《紫骝马》中云:“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秋。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来灭,画地取封侯。”又如王维《少年行》将侠客义薄云天、重气轻死、沙场报国形象写得惟妙惟肖。从游侠诗的创作风貌可以看到侠义公案小说的轨迹。陈平原从一般的边塞游侠诗中归纳出了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步行侠,第二步报国,第三步就是封侯拜相,扬名立万。而这三步曲不正好与侠义公案侠士的人生轨迹同步吗?只不过立功方式从沙场建功转移到了扫除劣绅豪强、平息藩王叛乱罢了。但可惜历史上对两者的评价截然相反,或许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到了宋代,宋话本的诸多侠义小说虽描写更加精细,但是更令后世注目的是其侠义内涵出现了嬗变,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儒家倡导的“忠” “孝” “贞” “节”等伦理规范逐渐渗进原侠精神,甚至占据于“信” “义”精神之上。西湖二集中的《侠女散财殉节》,重气而不重武。但描绘的都是丫鬟女子以死护主、以死守节、割肉喂主母等种种情节。冠之以侠女名,但更多却是演绎儒家精神。明代的《水浒传》,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的旗帜,不仅是义的感召更是忠的演绎。天的指向性不在于民心而在于君道。他们杀贪官除豪强却从未反君主,在第19回阮氏三雄高唱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7]就是生动写照。
不论从侠客史还是侠文学史都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历史上,每当乱世侠客多参与庙堂纷争,亦有捐躯赴国难之传统。反映到侠义公案小说,与其兴盛背景分不开。晚清乱世中,清廷岌岌可危已经无力巩固统治,客观条件已经无法阻止侠客崛起。主观上,跟历朝君王一样腐朽没落的官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于危局,他们不得不假借庙堂之外侠客之手为其平息动乱。在作品中呈现的则是侠客扫奸除恶、匡人间正义。比如《三侠五义》中斗恶霸马强、花蝴蝶,除作乱水怪,治奸臣庞太师马朝贤;《施公案》中,施世纶在黄天霸等帮助下破霸王庄、殷家堡、东昌府、落马湖等。基本情节仍不脱于《水浒传》,但却反映民心,应和时代背景,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侠客能继承古有之传统,铁肩担道义,热血为苍生。二是在侠义文学史上,侠与庙堂纠葛亦是重要题材。但自宋以后,侠的德行被儒家道德规范所束缚,愈来愈有儒化倾向。发展到侠义公案小说,儒家的忠君报国已经占据侠义精神的核心。《小五义》中智化遭擒时慷慨陈词很有代表性。这基本就是儒家忠孝节义的再阐释。像《续侠义传》的展昭沙场峥嵘,秉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后于平叛后辅佐范仲淹,最终“守边十余年,终于任所”[8]。自汉至清,儒家正统文化与作为亚文化的侠文化长期碰撞融合,最终以侠义公案小说中侠客变儒将方式暗示了这场博弈结果。
三、 侠客庙堂指向的时代新解
传统的侠义精神除了侠客本身的任张个性、豪宕不惧、崇尚绝对个人意志和自由之外,更多呈现一种民间指向。这就是行侠仗义,执义不苟,往往于人困顿时施以援手而不留名不记事,作为守护民间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而存在。但侠义公案小说的忠君提倡,实质是将侠义精神由民间转向庙堂,由“侠义”转化为“侠忠”。这种转向除了上文提到的历史事实、正统文化影响之外,更与侠义公案小说出现时的社会风尚有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让晚清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们觉得日本之强盛在于尚武,中国因尚文而积弱,以致被冠以东亚病夫恶名。“病夫”的后果就是“病国”。当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解读侠义精神,将其作为重塑国民性的重要精神源泉。这种精神资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侠客固有的品质,比如刚健勇武、锐意进取、激烈伉直,有时更接近生命的原生状态,可冲刷儒家承压下的中庸、懦弱、麻木、逆来顺受等孱弱国民性,能使久已失落它们的人得到一种坚强的信仰支撑。二是对儒家改造下的侠文化作了崭新的解读,突出侠客的爱国指向。后者是关键,前者为后者服务。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武士道自古有之,“起孔子而迄郭解”,称孔子为“天下大勇”[10]25。而后世尚武风气的湮没是因为儒道不兴与玄黄之道盛行。这为武侠合法的社会地位找到思想依据。这种托古改制策略实质是将侠纳入儒学范畴。他在理论上对历史上的侠儒融汇进行梳理,将“忠” “孝”等儒家理论移植到了武侠身上。更关键的是侠客以往以武犯禁的特点往往最不容于正统者。梁启超从国家大义的角度,为侠客辩解。“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所必禁者,有不谦于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谦于天下之人心也。”[10]13他认为禁者本就有不容于人的私心,而为天下的“公义”犯禁是情有可原的。这种结果导向的论断其实可以移用于侠义公案小说,只要不违本心,只要能平世间不平、维护世间正义公平,是“犯禁”还是与清官合作,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梁启超把“爱国之义”为国家而死作为中国武士(侠客)的首要标准。他认为侠客武艺不能好勇斗狠,甚至不能“私人报恩仇”,而应该“苟杀生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10]44。因此,梁启超对于同入《刺客列传》的曹沫极尽颂扬而轻视聂政。因为曹沫为的是国家社稷而不顾生死,聂政只是为了报个人之恩仇,不能相提并论。他创造性地将春秋战国的“君主”替换为“国家”。如弘演的“杀身出生以殉其君”本为宣传儒家忠孝节义的传统内容,谓弘演“以一死动强邻, 使国家亡而不亡,是则非为独夫死,为国民死也”[10]121,将侠客的死解读为为国为民,死得壮烈。从以上可以看出,晚清的尚侠风气虽然看重了侠客固有品质,但梁启超等人主张的核心却是爱国情怀。这本应不是侠客精神最重要的部分,却被当做侠客精神的旗帜,尚武等精神都是围绕其服务。
当然梁启超的主张和侠义公案小说的侠客倾向是有不同的,前者看重的是侠客对国家民族的价值,使侠客适应时代新发展,焕发国民新活力。而后者是儒家忠君思想的演绎,强调侠客不应以武犯禁而应以武为君。但实质上,两者倾向还是一致的。梁启超规训侠客的放任而提倡侠客“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的国家情怀。这些将“侠”与“国家”“公义”联系在一起的解读,其实质仍是将侠客精神的民间指向改造为庙堂指向。武侠小说基本代表了侠客精神嬗变的发展方向,只是梁氏等人迈的步子更大一点罢了。考虑到侠义公案小说脱胎于北京的说唱艺术,流传于茶馆坊间,在政治中心、舆论思潮此起彼伏的北京,它不能不受到同一时期尚武任侠思潮的影响。《续小五义》序言:“传中所载,人尽忠烈侠义之人,事尽忠烈侠义之事,非若他书之风花雪月,仅足供人消遣者比。”[11]这至少表现出作者是考虑到了侠义公案小说的社会意义,看到了侠客精神的社会作用。在消遣之余,通过展现展昭、黄天霸、南霸天侠义事迹,将侠客个人英雄主义上升为民族英雄主义,将守护社会正义转变为守土护国的民族大义。希望能有更多人受此忠义精神感召,展现出一种使命的担当。
四、 侠客庙堂指向的后世演绎
新文学家贬斥侠义公案小说中忠君等儒家理念,而不否定庙堂指向,除了晚清梁启超尚武任侠的理论支点,也可窥见后世雅俗文学的发展趋势,乃至“五四”一代人的命运实践。他们都对侠客的放任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训,突出侠客精神中的国家情怀、民族利益。所不同的是对国家、民族的内涵把握有了质的变化,对侠客作用也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 民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忠”演绎
最明显有侠义公案痕迹的是文公直的《碧血丹心》三部曲和赵焕亭的《奇侠精忠全传》。小说中于谦在三军拥戴下,特别是在侠客帮助下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同样是取自历史人物加以想象虚构,同样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同样是清官带着侠客平叛乱,这与《三侠五义》何其相似。但文公直的突破点在于,在忠君内涵中更突出爱民的内涵。作者借用于谦的话说:“官不爱民忠国就是贼,反过来说,贼就是害民的奸徒。要是开山立寨的朋友能够保爱百姓,就是古来的侠士所为。”[12]132他厘清并摆正了忠和爱民的关系,对爱民概念的强调,消除了人们对侠义公案小说中因为忠君而可能导致侠客精神消解的质疑。“贼”的界定非在朝或在野,关键看心中是否有国是否有民,若能做到忠国爱民,侠客落草也是英雄。相比侠义公案的暧昧不清,文公直把“忠君” “忠国” “爱民”作了有机联系,予以平白无误的阐释,并由此肯定了侠客的地位。对忠这一概念的解释是质的突破,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文公直写于谦就曾在《序》中直言:“吾人今日,为我民族求生存计,为救世界弱小民族计,为求达全人类平等之日计,公直急谋恢宏我民族之忠侠性,发扬而光大之。”[12]4他对于武侠小说侠、武两者都有开拓性认识,希望能做到“以侠改心”“以武强身”。平江不肖生作品采用了民间立场,侠义内涵上也有突变。小说以大刀王五和霍元甲作为中心人物贯穿全篇。围绕他们出现了杨班侯、孙福全、罗大鹤等一位位侠肝义胆、热血赤城的侠客。全文以“武术救国”立意,将侠者风范、民族正气融入于武道中,使“侠”与“武”达到高度统一。小说以反“朝廷”忠“国家”的面貌展现,最经典部分是霍元甲的三次比武。借用农劲荪对比武的解释:“霍先生的性情,从来是爱国若命的。轻视他个人,他倒不在意。他一遇见这样轻视中国的外国人,他的性命可以不要,非得这外国人伏罪不休。”[13]他彰显国魂,为的是不甘国家尊严受辱,他挺身而出打击外族气焰,是要洗掉“东亚病夫”的污名。不论平江不肖生还是文公直,这类英雄侠义小说重心不像唐传奇那样赞扬侠客古道热肠、义薄云天一面,而是认为侠之精髓在于其忠侠精神。作者通过相应事迹唤起民众报国热情,提升民族凝聚力,革除了国民性中冷漠懦弱的痼疾。从以武行侠上升为以武报国,倡尚武风气,扬自强精神。
(二) 新文学作品中的再继承
在新文学中也有类似作品。影响较大的当属自称“学匪”的郭沫若创作的抗战史剧《屈原》《南冠草》《虎符》等。郭沫若取材历史上侠义事迹,牢牢抓住抗战救国的时代主题和当时微妙的时局,颂扬侠客身上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时代担当。这就使现实环境与剧中人物斗争相似、处境相似的人民群众从侠客身上愿舍己身、矢志报国的精神中获得鼓舞,坚定抗战信心。前文曾论述,梁启超赞曹沫而轻聂政,因曹沫挟持齐王为的是江山社稷,聂政刺韩王只为个人恩仇。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聂政刺韩王的原因是韩哀侯等因私利企图三家分晋,给秦国吞并可乘之机。为纾国难他不顾个人安危,侠肝义胆做出刺杀义举,后怕连累亲人而毁容自尽。类似还有《虎符》,战国门客多无国家归属感,他们奔走各国只为自己才华得到施展。诸侯养士多平等相待,门客相报多为知遇之恩。但剧中的侯瀛认为唇亡齿寒,亡赵危魏,力荐侠客朱亥,筹划盗虎符,助信陵君提兵退秦。从以上看出,郭沫若更看重的侠客精忠报国的国家情怀,也就是“侠忠”的品质。他的价值取向与侠义公案的整体倾向是一致的,赞扬侠客的因义立节、依节而行、百折不挠、坚韧自强,为达到目标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但是在保留侠客一部分优良精神同时,试图对其恃武过人、纵横行事的个人主义倾向进行规训,将之从个人狭隘天地引向更广阔的时代中心。同样的封建历史题材,同样的庙堂倾向,郭沫若作品能经得起时代考验是因为他淡化忠君印记,高扬国家利益,也就是将个人之义上升为民族大义。但如不考虑意识形态的价值倾向,究其本质两者是一样的。
(三) “五四”新文人的命运实践
王德威曾经评价现代历史中集体主义倾向就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与现实中,有多少叛逆的‘新青年’曾以激进的个人主义起家,却臣服于集体乌托邦的号召下。他们奉献一己的资质勇气,以赢得民族和政党的胜利,这些倾向,其实与晚清男女侠客向(君主)极权顶礼膜拜的去向,有了诡谲的照映。”[14]144王德威的价值倾向有待商榷,但他的确看出了革命青年命运与晚清小说中侠客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这些“五四”青年乃至一些新文化运动元老,他们既秉持“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古训,又“成为侠义公案精神不可思议的继承者”[14]144。庙堂崩塌,在重重包围下他们站在广场传道布讲,以笔代剑,毅然谴责社会不公,痛斥军阀的无道,誓要以己之身换民族之未来。激进者以儒侠风范,游走于暴力与正义之间,虽九死而不悔。最后因为信仰的相通、理想的共鸣和现实环境共同影响,他们围绕在革命旗帜之下。“左联”的成立其实标志着个人主义的话语最终和民族建构的当务之急产生了分歧。丁玲、夏衍、胡风、胡也频、艾芜等都是沿着如此轨迹,乃至曾经颂扬《女神》生命力的郭沫若,曾经幻灭、动摇的茅盾亦不能避免。所不同的是,关于如何弥合个人与国家冲突、文学与政治分歧,每个人进度不一。郭沫若很快转变了角色,丁玲、蒋光慈等人苦苦挣扎,鲁迅的“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都显示强大的集体主义对个人身体心灵造成的负荷。“鲁迅一代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扮演英雄人物的角色,一方面又谴责侠义公案小说为反动文学。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自身角色的真谛,因为他们未能体会他们所师承的晚清侠义论述中的暧昧性”[14]144,而对这种暧昧性的忽视恰恰显示了启蒙的不足。
五、 误读背后的原因分析以及带来的危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启蒙者表面上似乎否定了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庙堂指向,但实际仍然受儒家的隐性影响,肯定了庙堂指向中的基本含义,对其中的关键途径、目标问题,只是换了部分内容。具体来说,启蒙者认可了传统庙堂指向中要弘道必须占据社会中心这一思路。“五四”时期,占据社会中心是通过文化运动占据广场,试图反思传统启蒙大众,表现出鲜明的广场意识。这是从途径角度来说。从目标角度来说,启蒙者首要目标不在于文学建树而在于构建合理的现世秩序,所不同的他们不是为君王构建的而是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服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通过新文学的“新思想”来立“新人”,从而立“新国”。可见,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中国启蒙主义以群体意识为导向,它的落脚点是国家本位主义而不是个人本位主义。在这里,群体意识剥离了忠君内涵,突出的是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所负的责任和意义,个人如何为现代国家、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要想占据社会中心的位置,在“五四”特殊阶段可以单纯依靠文学力量在广场启蒙民众,影响社会进程。但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五四”退潮后,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凸显。不论是为了加快推进社会改革的进程,还是为了保持其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一些启蒙者不得不接近权力,又走回了传统的老路。因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文人卷入政治风云之中。二是启蒙者将构建合理的现世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在“五四”时期,立人被认为对于立国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张扬人的主体性和建立现代国家就具有同一性,因而保持着很好的张力,文学的独立性也能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是在群体意识的价值导向不变情况下,对立人的工具性认识也就无法改变。立人只是被当做立国的一种途径,这就导致一旦这种途径或效果不明显或受时局影响很可能会发生偏移甚至被抛弃,而采取其他方式来实现立国的目标。上述两种情况的结果就是:要通过接触权力占据社会中心,就不得不面对权力的规制,这是传统庙堂指向中势与道的矛盾冲突在现代的再延续。而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又受到自己所持群体价值目标的影响,很难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个人性,两相作用下很多人最终仍然难脱集体主义桎梏。“以激进的个人主义起家,却臣服于集体乌托邦的号召下。”[14]144
具体来说,文学是人学,当集体性凌驾于个人性之上时,一开始就有让文学健康发展发生偏移的隐患。这种隐患表现之一就是对侠义公案小说所持的批评标准。对于侠义公案小说展开批评,只是当时对传统小说评价的一个缩影。近代以来,受进化论影响,知识分子普遍秉持着线性历史观。“新小说” “新文学”就是鲜明的体现。鲁迅、茅盾等人坚信“新”的远胜于“旧”的,要树立“新”的权威,就必须对“旧”的进行全面清算。关于评判“新”与“旧”的首要标准,就是“思想”的“进步”。这种进步性具体体现于是否为人的文学。这被当做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区别。以此标准作评判,作为晚清通俗小说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显然也是“非人性”的。因为原本刚毅自由、重气轻死、张扬个性的侠客摇身一变成为依附朝廷的官僚。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就是作为旧思想代表的儒家忠君理念,以及背后作为旧政治代表的封建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侠义公案小说,在当时出于主义需要,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优秀传统都进行否定。比如“迷信的鬼神书类”的《西游记》《封神传》,“妖怪书类”的《聊斋志异》,“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15]160。这一标志性主张得到了新文学家的广泛认同,即使对侠义公案持为数不多肯定意见的胡适也曾指出:“在周作人先生所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之中,有《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这是很可能注意的。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15]160也许这里面有权宜之计,为了打破与传统政治模式相表里的封建文化意识形态,在强敌环伺下站稳脚跟,新文学家不得不用“一些启蒙所倡导的抽象概念同封建传统文化观念杀伐攻打时,过于迷恋它表面上的优势”[16]6,只求能迅速打开局面,打出气势。在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那里,它所透露出的是对传统文学的轻视,没有很好继承和发扬,而把学习目光放于西方。这种以“主义”来排斥包括侠义公案小说在内的一切古代小说传统,明显是有失偏颇的。对《西游记》《水浒》等造成误读的成分更多,对《三侠五义》等稍小罢了。但这不能掩盖“五四”启蒙时期启蒙家对文学艺术性有意无意的忽视,文学的本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蔡元培就指出:“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扯到文学?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15]158这种工具论使新文学一开始就有走向歧途的危险。思想和文字结合不一定就是文学。思想的进步性并不能代表文学本身的审美艺术性质,也不能说明思想本身的“丰富性”以及“深刻性”。具体于侠义公案小说,它的人物设置塑造等并非一无是处。在之后的英雄传奇小说中,这些特点都被不同程度继承。比如将人物置于奇险环境来突出主人公的超能力。比如在人物设置上,沿用了《三侠五义》等类似“五虎将”模式。《林海雪原》有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等五人。而章回结构下“集锦式”的缀段结构、“珠花式”结构也可窥见于《吕梁英雄传》。这些英雄传奇小说都是汲取了古代小说优秀资源,并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大放异彩。至于思想性上,思想丰富性既可以指优秀深刻的思想可以衍生出多样的解读角度,同时也可以指它本身驳杂。侠义公案小说属于后者。启蒙者将其思想笼统归纳为落后的儒家忠君理念,痛斥其与权力的合谋,却没有仔细辨析庙堂指向框架中包含着“途径”和“目标”这两个关键问题。弘道是否一定要占据社会的中心,构建理想的现世秩序是否就是知识分子唯一的重要责任。这两个问题看似小问题,却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走向和人物的命运。这也是辨析侠义公案中庙堂指向的意义所在。
首先,知识分子占据社会中心启蒙众人,他们的广场意识实际上与士大夫庙堂情怀一脉相承。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既然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也有这种能力,那么就必须占据社会中心,讲经布道为国家未来摇旗呐喊。陈思和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有一个形象论述:“如果你中举了似乎审案破案也能做,经济建设也能管,水利也能修,杭州的白堤苏堤不就是那些当官的士大夫主持修筑的吗?”[17]62“五四”时期启蒙者也是如此,“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拥有真理在握的绝对自信,坚信他们在批判对象面前进行的是一种布道者理所当然的‘解放叙事’和‘真理叙事’”[16]8。他们往往对西方学说一知半解还未完全吸收,就将其当做解决现代中国道路问题的真理来传播。光说还不满足,后来干脆“胡适去鼓吹好人政府,陈独秀去组建政党闹革命,一个个分化了,天下兴亡仿佛在他们身上”[17]67。这种要占据社会中心的倾向就出现两个很大问题。一是他们占据社会中心的精英意识让他们以俯视态度看待民间,导致他们的学说与民众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感,缺乏必要的民间基础。他们自信他们的口号术语能够拯救民众,但在民众看来这只是在台上“画鬼符”自娱自乐罢了。这直接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实际作用,以致引发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讨论知识分子的人民性问题。二是启蒙者拥有绝对自信,认为无所不能。但是当“五四”退潮,他们发现自己的学说理念与时代有距离时,就容易陷入被遗弃的恐慌。当时国共纷争已经是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问题。在焦躁恐慌下,为了能继续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他们往往以激进方式去发展。
其次,庙堂指向中的目标是构建理想的现世秩序。当启蒙者对自己能力认识过分膨胀,认为自己能拯救中国时,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忘记了自己关键的身份是文学家。这也是传统庙堂指向带来的弊病。自古以来,“文”很难挣得独立地位。“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8],在弘道的目标下,文是用来载道的,“文”只是被当做表达“道”的语言手段,只是附庸。历史上的文学名篇如《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等,作者关注点在于扬道而不是表现人生、表现个性的审美考量。传统儒家是如此,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乃至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的倡导等等也是如此,在群体意识支配下只是所载的道不同罢了。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等人注重意趣的雅文因为远离社会问题,容易产生麻痹心灵的负面作用,因而饱受指摘。这与对侠义公案的批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注重思想倾向性而不是文学性。这使得文学的主体地位十分脆弱。
再者,由于对群体指向的目标过于推崇,这会导致他们会不自觉的压制人的个性,以及以个性为核心的亚文化的健康发展。这种亚文化在侠义公案中是侠文化,在现代则是“五四”的个性主义。千百年来,正统文化与亚文化之间既交流融合又激烈碰撞。如上文提到侠文化与正统文化间的交锋在宋代发生明显变化,儒家的忠孝等理念开始侵蚀侠的唯个人主义特性。但这个过程延绵千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缓慢进程。侠义公案小说受人关注在于它的庙堂倾向,儒家的“忠”已经让侠精神完成了“质变”,从曾经是侠精神中的重要部分变成了核心。批评家猛烈抨击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其潜意识里并非是希望传统侠文化能站上舞台中心,而是希望对原来正统意识形态能取而代之。当然他们坚信新的正统理念与思想将会具有更大包容性与活力。这在“五四”的一定历史阶段两者可以达到高度融合。但仅仅不到十年,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使启蒙思潮陷入低潮。到20世纪三十年代,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时候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两者一度被弥合的缝隙豁然裂开。个性主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将原本的封建文化意识赶下了意识形态的中心舞台。但正统的群体意识在时代战火的助燃下卷土反扑,相比之前对侠文化的漫长侵蚀,它和个性主义形成了最激烈的碰撞。我们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革命加恋爱文学窥见一面。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施蛰存《追》、丁玲《一九三O年春上海》等主人公,基本都遵循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他们都是“五四”思潮洗礼下成长的新一代。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不满于现状又对未来迷茫,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最终遇到革命引路人,走上革命道路,并严格按照革命要求改造自己成为一名合格战士。在将“五四”的个人话语向革命的集体话语转化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个人与国家、爱情与革命的激烈碰撞,他们是“五四”一代命运写照,实质和侠义公案小说相似,显示出集体的正统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义文化带来的压力。如果仔细对比,王曼英等人身上都有白玉堂等侠士的影子。少时出游,持世道公心行侠仗义,路遇包拯等恩主感其正气,念知遇之恩转身投靠,最终杀劣绅豪强,平叛乱,乃至像黄天霸杀兄逼嫂经过种种考验,最终才受赏封爵。这种历史轨迹出现惊人重合并不是完全巧合。这也看出批评家看似跳出了儒家理念圈子,但新文学乃至新文人仍受集体主义桎梏。这一切没有像文学家想象得那么简单,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最终还是以对立姿态出现,“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19],文学性、人性的坚守从此愈发艰难。不过就侠义公案小说而言,“侠忠”结合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由个人之义上升为民族大义,焕发出适时的生机。它也终于为晚清小说中侠客找到了与时代相融的一条通向“庙堂”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