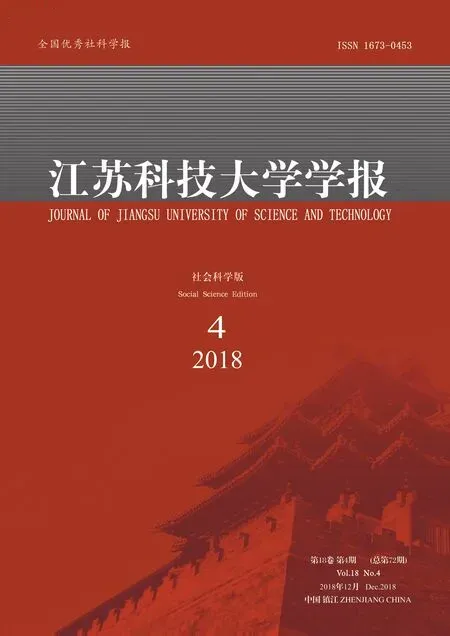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研究述评
梅阳春 , 汤金霞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伦理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1]。 “只要有人,有了人的活动与生活,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就会发生作用。”[2]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人际活动。该活动牵涉到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译者、翻译活动的发起者等多个行为主体,不可避免地要同伦理产生关联。如何协调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冲突,如何给译者的行为设定合理的界限,如何平衡与翻译活动相关的各个主体(包括直接参与翻译的主体和间接参与翻译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翻译对跨文化交际的正面作用,同时将翻译对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伦理的指引。事实上,译者践行什么样的翻译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翻译的成败。自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为了对抗翻译中“用本族语言文化归化原文的译法”[3]而提出“翻译伦理”以来,翻译伦理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翻译伦理研究不仅指向文学翻译,也指向科技翻译。自2009年论文《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发表以来,学界多位学者先后从不同维度对文学翻译伦理进行了梳理、总结与反思,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科技翻译伦理开展述评类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对现有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进行梳理,明晰该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指出该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并尝试提出对策,以期抛砖引玉,与译界同仁探讨。
一、 科技典籍翻译伦理研究范式纵览
尽管科技翻译伦理研究成果不及文学翻译伦理研究成果那般丰富,但也在字词层面的翻译伦理、句子层面的翻译伦理、篇章层面的翻译伦理以及宏观科技翻译伦理四个层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 字词层面的翻译伦理
在四种范式的翻译伦理研究当中,字词层面的翻译伦理研究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在这个领域当中,蔡耿超、李曙光、陈苑以及周薇四位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蔡耿朝的论文《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考量》以医学术语的翻译为例,论述了将伦理研究与科技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该作者在剖析医学词汇的特征之后指出,“医学翻译涉及的远远不只是语言,更牵涉到源语与译入语背后的文化……因此,医学翻译伦理应跳出语言层面,着眼于更大的文化层面,才能成就更丰满的译文”[4]。该作者进一步指出,“伦理可谓医学中的永恒话题,而在以医学科学的传播和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医学翻译中,医学伦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要素。简而言之,医学译者要考量的,不仅是如何忠实而通顺地传达医学信息,还包括如何适当地传递具有普世意义的医学伦理”[4]。
论文《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考量》明晰了伦理是科技翻译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不过这篇论文作者并没有论证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需要或者说可以遵循什么样的翻译伦理,这虽然是该论文作者的一大遗憾,但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契机。论文《医学术语翻译中的伦理问题——以autism的汉译为例》就尝试阐明科技翻译工作者需要遵循什么样的翻译伦理。该论文作者指出,作为科技翻译的一种,医学翻译自然需要坚守“求真”的原则,但“伦理是确保人类行为向善的准则规范及价值取向。医学与翻译虽分属不同领域,但在‘求善’这一伦理追求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5]。该论文作者以医学术语“autism”的翻译为例论证了科技翻译工作者如何既“求真”又“求善”。论文作者指出,医学术语“autism”的两个汉语译文“孤独症”和“自闭症”都没能实现“真”与“善”的统一。因为将“autism”译为“孤独症”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求真”的伦理要求,但若将该术语译成“自闭症”又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求善”的伦理要求。因此,笔者建议采用音义相结合的策略,将“autism”译为“奥蒂森症”,以实现“求真”与“求善”的统一。
李曙光借鉴了西方基督教中的“真”与“善”理念,建议以“真善合一”作为科技翻译的指导伦理。他的建议只能说给科技翻译提供了一个粗略的伦理指引。他仅以“autism”一个术语的翻译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科技翻译工作者在具体翻译中面临的问题何其复杂,一个“真善合一”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他们的伦理困惑?科技翻译工作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提纲挈领式的翻译伦理,还需要能够协助他们应对具体翻译问题的更为细致的翻译伦理。陈苑的研究则让科技翻译工作者们看到了希望。在论文《科技翻译译员的专业伦理——以三一重工产品介绍英译为例》中,陈苑首先指出译者在科技翻译中会面对大量的技术词汇和专业术语[6],译者一方面要熟谙相关翻译涉及到的两种语言,另一方面还要熟悉原文中相关的科技知识;此外,译者还需要践行合适的翻译伦理。陈苑接着论证并指出,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勾勒的五种模式的翻译伦理,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以及承诺伦理可以很好地为科技翻译工作者提供伦理指引。她随后以三一重工产品介绍的英译为例解析了译者在何种情形下可以遵循何种模式的翻译伦理,同时还论证了译者在何种模式的伦理的指引下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这就为科技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具体的伦理参照。
切斯特曼建构的五种模式的翻译伦理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7]的翻译伦理理论。但这五种翻译伦理是基于五个不同的立论点对翻译伦理展开论述的。五种伦理尤其是前四种伦理之间“互不兼容,矛盾冲突时有发生”[8]。这种潜在的冲突也会给科技翻译工作者造成困惑。如果科技翻译工作者在应对同一性质的翻译问题时一会儿践行这种翻译伦理,一会儿践行那种翻译伦理,这必然有损译文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周薇的论文《翻译伦理与中医术语翻译》则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周薇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论证了中医术语翻译与翻译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随后论证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借鉴意义。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周薇觉察到了五种翻译伦理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的不利影响。因此,她主张“译者应区分不同的翻译任务,将中医术语分类,选择遵从再现伦理、交际伦理、服务伦理、规范伦理中的一种翻译伦理,统一翻译思路,从而避免中医术语翻译中所产生的问题”[9]。
(二) 句子层面的翻译伦理
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术语层面上,也体现在句式层面上。因此,科技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不仅需要应对大量的专业术语,还需要应对特殊的句式。王志晨等的论文《从翻译标准和医学英语特点的角度论述医学英语翻译》开创了从句式层面研究科技翻译伦理的先河。在这篇论文中,王志晨等先以医学英语为例分析了科技英语句式的两大特征,即句子复杂冗长、被动句式较多。他们随后论证并指出,在翻译科技英语的特殊句式时,译者需要视翻译情境灵活遵循翻译的再现伦理和规范伦理。该论文作者强调“翻译时应该把‘忠实’和‘通顺’作为基本的标准”[10]798,从而实现译文一方面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另一方面也能满足目标读者对译文可读性的要求。方春艳的论文《科技英语句式陈述的客观性的翻译策略——以〈编程语言与λ演算〉(第1—4章)的翻译为例》也是从句式层面探讨科技翻译伦理的[11]。方春艳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论证了客观性是科技英语最为典型的特征,随后从时态、语态、情态和语气四个方面论述了科技英语如何在句式层面实现文本的客观性。方春艳最后以再现伦理为指引,以《编程语言与λ演算》(第1—4章)的翻译为例论述了译者如何在上述四个层面最大程度地尊重原文的客观性。
中国的翻译伦理学研究起步比西方晚,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翻译伦理学研究的影响。这导致了国内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味借鉴西方学者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但李伟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研究模式。她敏锐地觉察到,不仅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国内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国内学者建构的翻译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在论文《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中,李伟兰借鉴了国内学者吴志杰建构的和合翻译理论。李伟兰首先论证了以和合翻译观为视阈研究科技翻译伦理的可行性。她指出,科技英语在句式层面既有模式化的一面,又有灵活性的一面;既具备科学性,又具备文学性。因此,译者可以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12]。除了可行性研究之外,李伟兰还借鉴翻译的和合理论,尝试从“诚于内外兼修”“诚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之融和”以及“诚于科技翻译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之融和”三个维度建构科技翻译句式层面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
(三) 篇章层面的翻译伦理
与文学文本相比,科技文本除了专业术语多、句式复杂之外,在篇章层面上也具有一定的区别性特征。科技英语“一般不使用诸如隐喻、夸张、拟人、反语等修辞手段”[13],并且文本“严谨周密,概念准确,逻辑性强,行文简练,重点突出”[13]。此外,科技英语在语场维度上具有层级性,即“按照精密度阶的要求分成若干小语域,或小语域的小语域”[14]。上述特征都需要译者给予恰当的伦理考量。在论文《翻译职业伦理视角下科技翻译规范性研究》中,李淑杰首先剖析了伦理和科技英语翻译之间的潜在关联,随后指出目前科技翻译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是译者没有在语篇层面履行合适的翻译伦理。随后,他援引译者职业道德伦理论证了科技翻译在语篇层面上“应该遵循单义性、简洁性、规范性这三个原则”[15]。
李淑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只是从宽泛的译者职业伦理维度探讨科技翻译伦理。此外,他在研究中并没有结合实例论述译者应如何在职业道德伦理的指引下实现他所强调的科技翻译语篇三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研究的说服力。李先玉的研究则较好地避免了这一缺憾。在论文《翻译伦理视角下的科技翻译——以〈时间简史〉和〈万物理论〉为例》中,李先玉论证指出,科技文本从总体上看属于信息类文本,“具有准确美、简洁美、逻辑美的特点”[16],但科技文本尤其是通俗类科技文本,“虽有术语性特点,但往往还对术语或其理论做出一些通俗活泼的解说,句式活泼多变,也运用修辞格,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16],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科技文本增添了一些文学文本的特征。因此,科技翻译工作者不应该忽略科技文本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在文体维度上的区别,不可以奉行单一的再现伦理,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译文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还应该以交际伦理为指引,竭力呈现科技文本中的文学性元素,最大限度地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她随后以科学著作《时间简史》和科普电影《万物理论》的翻译为例论证了译者如何在再现伦理和交际伦理的指引下实现译文的忠实、通达以及文雅。
(四) 宏观科技翻译伦理
翻译伦理五模式理论的提出者切斯特曼指出,翻译伦理涵盖两个层面:一个是微观层面,另一个是宏观层面。微观层面“指涉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17],如“译者如何从总体上设定译文的框架,章节,段落等”[18],以及“译者如何遣词造句,实施强调”等;宏观层面“指涉译者和翻译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17],如翻译如何促进全球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翻译如何应对各种权力话语的左右和操控等。
如前所述,学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微观层面研究科技翻译伦理的,很少有人从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这一点直到论文《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科学伦理思想》的刊发才开始逐渐改变。该论文的作者杨韬指出,国内学界在探讨科技翻译伦理时往往聚焦于文本内部各层级元素的翻译伦理,时常忽视文本外部的翻译伦理[19]。而译者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为的后果,但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取决于译者实施该行为的动机。作者随后以中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对《几何原理》的翻译为例,从科学学术伦理和科学社会伦理两个维度探讨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伦理。论文作者指出,徐光启的科学学术伦理体现在“疑古求是”的学术观、“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数学思想以及“几何之学,深有益于致知”的科学强调三个层面;徐光启的科学社会伦理体现在“会通中西科学的超胜思想”“敢为民族先的创新精神”以及“服务国家、民族的爱国情感”三个层面。
二、 科技翻译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 理论研究针对性不足
无论是字词层面的翻译伦理研究,还是句段篇章层面的翻译伦理研究,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的研究者们很少立足于科技翻译的典型特征去建构科技翻译伦理,他们基本上都是沿用甚至简单套用文学翻译伦理的研究成果。虽然有的学者借鉴的是西方文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有的借鉴的是国内文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成果。科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固然存在很多共性,文学翻译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可以为科技翻译提供一定的伦理指引,但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确实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科技翻译在很多时候需要的不是文学翻译伦理,而是能针对其典型特征而为之的科技翻译伦理。然而截至目前,国内尚未有学者立足于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差异性开启科技翻译专属的翻译伦理研究。
(二) 研究语料不足
除了术语层面的翻译伦理研究之外,其余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所用语料全部来源于现代英语或现代汉语建构的科技文本。自21世纪初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国家各级部门先后实施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工程(199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以及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2013)等工程,已经将一批优秀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至西方世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文本是由文言文建构的,译者在翻译这类科技文本时所需要的翻译伦理与其在翻译现代语言建构的科技文本时所需要的翻译伦理肯定会有所不同。首先,译者在翻译现代语言建构的科技文本时只需经历语际翻译这一个过程,但在翻译文言文建构的科技文本时则先要经过语内翻译,然后才经历语际翻译。翻译过程的差异必然会引发翻译伦理的差异。其次,以现代语言建构的科技文本主题突出,架构明朗,“行文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由中心议题统领与该议题相关的诸多信息,由逻辑连词显示各信息模块之间的层级关系”[20];而由文言文建构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结构较为松散,存在科技信息不够详实、行文逻辑不够连贯以及信息陈述客观性不足等问题。文本架构和文本行文的差异也必然会引发翻译伦理的差异。再者,现代科技文本是典型的信息类文本,科技信息在文本内容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文本类型较为复杂,既包括以科技信息为核心的典型科技文本,也包括大量的与典籍所论述的科技主题关系不大的非典型科技文本。这一切使得译者在翻译此类文本时所遇到的伦理困扰远远超过翻译由现代语言建构的科技文本。
(三) 论述的伦理维度偏少
国内现有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基本都是微观层面的伦理研究,宏观伦理层面的研究不足。字、词、句、段等微观层面的伦理研究固然是科技翻译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仅仅局限于该层面的研究,很容易使科技翻译伦理研究陷入一种天真的假设,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21]。而实际上,翻译一直以来都受到各种外界条件的影响与操控,与翻译相关的两种文化也很难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译者的翻译也往往带有特定的时代使命。如何应对与科技翻译活动息息相关的各种外部影响?这需要学者从宏观层面给予译者以伦理指引。
三、 对策
针对国内科技翻译伦理研究业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憾,笔者认为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可以按照下面的路线图进一步开展,见图1。

图1 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研究路线图
如图1所示,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应当涵盖微观翻译伦理和宏观翻译伦理两个模块。
(一)微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
微观翻译伦理研究应当涵盖如下两个层面(上图左侧椭圆区域):
1. 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差异性以及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差异性比读研究
长久以来,学界想当然地认为科技文本除了专业术语多一些、长句子多一些之外,与文学文本并无二异。这种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界重文学翻译、轻科技翻译,重文学翻译伦理研究、轻科技翻译伦理研究。而事实上,科技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除了上述区别之外,在话语构成、文本结构、体裁规约以及隐藏在三者之后的语言哲学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中国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如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研究者们就必须全面探究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在上述多个维度上的典型区别。只有这样,方能成功建构出最能反映科技翻译本质特征的翻译伦理。
2. 语内翻译伦理与语际翻译伦理研究
无论是明朝中后期徐光启等开展的科技翻译运动,还是清朝末年“西学东渐”运动中的科技翻译运动,抑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1世纪初的历次科技翻译高潮,中国的科技翻译基本上都是“外译中”,科技翻译伦理研究基本都是以语际翻译文本为语料。但21世纪初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并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科技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言文科技典籍被翻译成他国语言。文言科技典籍的译者往往不是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是古文专家,所以这些典籍往往先由古文专家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翻译成白话文,再由外文专家翻译成外文(如《黄帝内经》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本)。最终的外文译本科技信息是否准确,文内逻辑是否连贯,文本陈述是否符合规范,都跟相关典籍语内翻译的译者遵循何种翻译伦理有着重要关联。
当然,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差异性比读、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比读、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比读都必须包括字词层面、句段层面以及篇章层面(上图左侧椭圆下的三个方框区域)等维度的研究。各个研究模块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彼此之间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存在交集(如图左侧各箭头线所示)。
(二) 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
图1还显示,科技翻译伦理研究绝不仅限于字、词、句、篇等文本架构层面的微观翻译伦理研究,还应当包括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前者的研究为后者提供文本语料支撑,后者的研究为前者提供方向指引。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涵盖科技翻译与国家战略、科技翻译与译者使命以及科技翻译与目标语期待等领域。
1. 科技翻译与国家战略
中国科技翻译尤其是中国科技典籍翻译是实现中国科技话语传播,塑造中国科技大国、科技强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目前,科技典籍翻译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战略议题的一部分。科技翻译的工作者和研究者应当以国家科技文化“走出去”战略为指引,研究相关科技典籍的诞生背景、国家对相关典籍的定位等,选择最符合相关战略的科技文本进行研究和翻译。如此方能对国家科技文化“走出去”战略有所助益。
2. 科技翻译与译者使命
科技翻译从来都不是译者的一种自我消遣和娱乐行为,译者的工作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目标感和使命感。造就优秀科技文本译文的译者(如上文提到的徐光启)往往都带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从事翻译。背负特定的使命感且创造了优秀译文的科技翻译者在翻译时践行什么样的翻译伦理,什么样的翻译伦理使得译者选择了相关科技文本,什么样的翻译伦理使译者的译文凸显了相关翻译取向,什么样的翻译伦理又使得译者采取了特定的宏观翻译策略和微观翻译策略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的课题。
3. 科技翻译与目标语期待
译文只有为目标语读者接受且在目标语世界取得了既定的传播效果才能被称为成功的译文。因此,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的研究者们需要遴选在目标语世界接受度高的科技文本的译文。研究造就了相关接受度的译者践行的科技翻译伦理。研究相关翻译伦理与目标语世界盛行的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该哲学支配的目标语世界对科技文本在学科领域、文本主题、文本架构以及文本行文等层面的特定认知,可以为国内科技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文言科技典籍翻译工作者提供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科技翻译伦理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研究者们需要将宏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与微观科技翻译伦理研究结合起来,以国家科技文化“走出去”战略为指引,明确译者的时代使命,探究目标语世界对科技翻译的多维度期待,从字词层面、句段层面、篇章层面研究科技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差异性、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差异性以及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差异性,如此方能建构体系完备的中国科技翻译伦理,为科技翻译工作者提供伦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