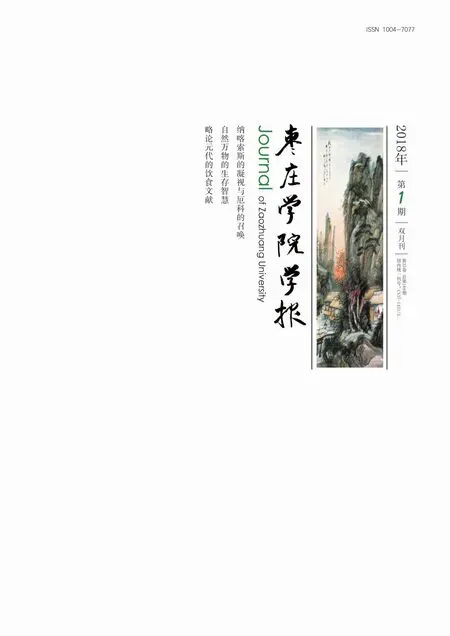贝克特的戈多来源于巴尔扎克的《投机商》
杨德煜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戈多到底是谁?关于这个问题有人问过贝克特,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的这种故弄玄虚却把问题留给了后人。
一、同样的等待
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戈多与奥诺雷·巴尔扎克的《投机商》中的戈多一样地被等待,一样地被当作是一种挽救的力量而被剧中人所关注。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一部远离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这部剧共分两幕,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简称戈戈和狄狄),在路上等待戈多。在等待中这对难兄难弟在毫无意义地闲聊,做些动作以打发时间。奴隶主波卓和奴隶幸运儿从这里路过,帮他们打发掉一些时光。第一幕结束时,一个男孩来报信,戈多先生今天不来了,明天准来。第二幕表现的是第二天的继续等待,几乎是第一幕的完全重复。只不过,一天之间,波卓已成了瞎子,幸运儿已成了哑巴,枯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戈多一直不来,戈戈和狄狄就一直等待。接下来的日子,两个流浪汉还将重复着这样的活动,等待是这部剧的主旋律,而等待毫无希望。
贝克特的远离现实主义传统的戏剧是否脱胎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呢?这是确定无疑的。巴尔扎克的剧本《投机商》就是这样的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这部五幕剧剧情开始于1839年,地点是主人公麦卡代家的大客厅。剧本一开始,就揭示了麦卡代的窘境,虽然革命后房租已经很低,但股票投机商麦卡代还是拖欠了六个季度的房租,他的家具被扣押了,面临着要被房东布雷迪弗拍卖的危险。麦卡代说:“我租您的房子住了十一年,现在您要把我赶走?……您知道我过于轻信,吃了大亏。戈多他……”[1](P491)这里首次提到了戈多,这是麦卡代的经济合伙人,卷款私逃了,使麦卡代陷入了接近破产的境地。而据布雷迪弗描述,“戈多精力异常充沛,为人随和,知足常乐!……他同一位秀色可餐的……小女子一起生活……”(同上)戈多卷走了十五万法郎,麦卡代靠戈多留下的清理证券继续勉强做了八年生意,结果负债累累。戈多若是意外携带财富归来,麦卡代将获得拯救,但八年的苦苦等待,麦卡代对此已经不抱希望。麦卡代的等待与戈戈和狄狄的等待具有相同的绝望属性,他一直只是以戈多要回来了为借口在拖延债权人,最后在破产的前夜,被逼无奈之下他让德·拉布里夫假扮回来的戈多,以此继续欺瞒债权人。
二、同样的虚出
贝克特笔下的戈多与巴尔扎克笔下的戈多,最后的结果又都是虚出——没有真正地登台的在场。这就像莫里哀《伪君子》的前两幕,答尔丢夫虽然没出场,却一直是人们谈论的中心,我们称这种没有实际出现的在场为“虚出”。好在答尔丢夫在第三幕出场了,可《等待戈多》和《投机商》中的戈多却始终没有登场。
《等待戈多》中的戈多一直没有出场,人们却都在谈论他,这就是一种虚出的状态。登场的角色一共有五个,主要的是其中的两对,戈戈和狄狄,波卓和幸运儿,还有报信的小男孩。 第六个角色没有出场,却是全剧的中心,那就是戈多。他通过登场人物的对话而存在,报信的小男孩被认为来自于戈多那里。
在《投机商》中,由于给不起嫁妆,麦卡代的女儿朱莉也很难出嫁。整部剧以戈多卷款私逃后造成的窘境开始,以戈多回来为麦卡代料清了债务结束,麦卡代的债权人们说他们的债务都被戈多偿还了,剧本的最后一句台词是麦卡代说的话:“我一再让人看戈多,自己总有权瞧瞧他吧。去看望戈多!”[2](P389)戈多回来是回来了,巴尔扎克却没有让他登场,这同样是一种虚出的状态。
使用核心人物虚出这种手法需要剧作家具有足够的魄力,否则这种尝试很容易失败。如何让这个人物一直不出场,又一直处在人们关注的中心,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主要人物一直没有登场,却在结尾突然出现,这就会显得很突兀,而且落入了俗套,这样的剧本难免要受到欧里庇得斯戏剧最后请神下来一样的指责。莫里哀对人物虚出进行了部分尝试,巴尔扎克和贝克特却做得十分彻底,他们干脆让主要人物自始至终完全虚出。这样的做法不只大胆,而且相当高妙。
三、同样的主题
《等待戈多》与《投机商》主题相同,反映的都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戈戈和狄狄与麦卡代一样都是在苟延残喘,回避现实,虽生犹死,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窘境。
戈戈和狄狄在等待中害怕孤独,害怕分离,但又无法互相沟通和了解。他们不停地用可有可无的毫无意义的谈话来打破沉寂,同时又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动作。戏剧的第一句台词是“毫无办法”,这句话之后又被多次重复。两个流浪汉对戈多一无所知,却又无可奈何地把戈多看做是能使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无奈地继续等下去,而等待又遥遥无期,他们苦闷得直想上吊。《等待戈多》确立了贝克特成为“荒诞派”戏剧家代表的地位。这部剧就是人类在这个荒诞世界中的尴尬处境的反映。其中情节严重弱化,动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它的意义在于,贝克特表现了当代人与自己生活环境的格格不入,并由此而产生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绝望情绪。“作者看到了社会的混乱与荒谬,更感受到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既弄不清自己的生活处境,也无法知道自己行动的意义和存在价值,孤苦无告,被动可怜,只有靠可望而不可即、飘忽不定的希望来聊以自慰。”[3](P331)在可望而不可及这个意义上,戈多有点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贝克特用荒诞的形式表现荒诞的内容,他“极为夸张地强调了这个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了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人变得日益渺小,渐趋萎缩,仅能说一些相同的无聊话语,做一些同样的滑稽动作。”[3](P334)而这种无聊的荒诞就是常态的人生,这是人们难以挣脱的厄运。
这种生存窘境,也就是戈戈所说的“奋斗没有用”,“挣扎没有用”,我们在《投机商》中感受到的更为具体而丰富。面对极端的生活困境,麦卡代感慨到:“一个遭难的人,如同扔在养鱼塘里的一块面包,每条鱼都来吃一口。债主都是凶恶的白斑狗鱼!……直到债务人——就是这块面包——被吃光了,他们才住口!”[1](P493)在被房东逼迫之下,麦卡代只好以放弃转租权为代价,希望能再拖上三个月。但三个月之后呢?他是看不到希望的,能坚持下去的,只有依靠顽强的生命力。麦卡代已经拖欠仆人们一年的工资,而仆人们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都以各自的手段在啃咬主人这块面包。麦卡代怎么拚命做生意都是徒劳,总是负债,他每天都要费力地去应付上门讨债的债主。所以麦卡代痛苦地对妻子说:“今天,夫人,所有的感情都在消退,让金钱给赶跑了。现在人们只讲利益,因为家庭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个人!”[1](P506)麦卡代已经被逼迫得想要不择手段了,他玩世不恭地说道:“只要能救自己,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您拿石膏假冒白糖出售,从而发了财,只要没有引起官司,就能当上议会议员、贵族院议员或大臣!……说到底,欠债有什么不光彩的?欧洲哪个国家不欠债?……生活,夫人,是永无止境的借贷。……无债一身轻,可也无人想着你;而我的债主们,却处处关心我!”[1](P507)这是一个人要狗急跳墙时说的非常泄气的话,也是对荒谬现实的一种有力揭露。麦卡代又说:“我要在投机的大赌桌上保住一席之位,使人相信我的资金实力,究竟采用什么手法,您就不要责备了。……您应当协助我,用表面的豪华掩饰我们的穷困。勋章离不开武器,而武器是不干净的!……不止一个比我的手段还恶劣。”[1](P508)幸亏有妻子和女儿的全力阻拦,他才没有最终做出有损名誉的事。巴尔扎克是让麦卡代一直保持住了自己的荣誉,但剧中也客观地写到了他谎话连篇,欺骗成性,这本来就是投机商的一种职业特征,可谓是无奸不商。同时,麦卡代这个形象身上有着终生负债的巴尔扎克自传的性质。
麦卡代的女儿朱莉完全了解父母的处境,因此学会了陶瓷彩绘技艺,以便不再依赖父母。朱莉还是有人向她求婚的,有小会计米纳尔和富家子弟德·拉布里夫。但米纳尔工资只有一千八百法郎,并不能令麦卡代满意。米纳尔是戈多的私生子。他本来指望能靠朱莉的嫁妆作为发家的资本,可知道了麦卡代的穷困处境后他决定放弃求婚。麦卡代把希望放在了德·拉布里夫的身上:“要一个其貌不扬、所带嫁妆惟有品德的姑娘出嫁,我倒要请教最有手腕的母亲,这难道不是一件魔鬼的差使吗?……至于德·拉布里夫先生,只要看他那套马车,看他在香榭丽舍大街挥鞭抽马的气派、他在歌剧院里的轩昂神态,最挑剔的父亲也会感到满意。我在他那儿吃过饭:房间雅致,漂亮的银餐具、上点心用的镀金盘,都有他的族徽,绝不是借来的。……也许他厌倦了风流艳遇……还有,据梅里库尔讲,他在杜瓦尔府上,听见了朱莉那美妙的歌声……”[1](P515~516)麦卡代在自己家里与德·拉布里夫见面之后才知道,他也是一个负债在逃的浪荡子弟,他使用化名米肖南,他也希望通过娶朱莉获得一笔嫁妆来摆脱窘境。麦卡代知道了真相后见他衣冠楚楚,就让他假扮戈多,以蒙骗讨债的债权人,因为麦卡代这时已真正遇到了绝境,第二天就要被迫宣布破产,他已准备好剃须刀,随时准备自杀。
对于《投机商》,艾珉在题解中说到:“本剧的最大特色,在于以强烈的色彩刻画了破产人垂死挣扎的心态和交易所投机事业的风云变幻。入木三分的心理分析,具有广泛现实意义的题材,加上安排得相当紧凑的情节和尖锐的冲突,使全剧自始至终扣人心弦。”[4](P767)而麦卡代所遭逢的窘境,《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在更深的层次上体味着,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指望《投机商》中戈多从天而降式的意外归来那种结尾。贝克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生活在死亡与疯狂的阴影中,受尽了痛苦与折磨,却得不到丝毫的报偿。”[5](P238)
四、悲喜之间
贝克特虽是爱尔兰人,却长期生活在巴黎。1906年,贝克特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母亲是法国人。上中学时,校长又是法国人,而且他当时的学业中法文最优,这对他后来长期生活在法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27年,贝克特获得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1928年,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教授英文。1937年或1938年,他因为厌恶爱尔兰的神权政治和书籍检查制度而定居巴黎。1945年开始在巴黎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先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在小说中,贝克特“所揭示的是人类生存的困惑、焦虑、孤独,人的精神同肉体的分离,人对自身的无法把握,人的自主意识丧失之后的无尽悲哀和惨状。……当人们读过贝克特的小说之后,得到的……是一种在浓云密雾中穿行和在荒凉世界中受困的体验。”[6](P164)而我们看到,这种主题在他创作的戏剧中得到了延续,使他名噪世界的,正是他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1969年,贝克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7](P146)我认为“得到振奋”属于溢美之词,贝克特的创作整体上是关注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荒诞,而他的戏剧创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创作于1948年,1952年出版,由罗歇·布兰导演,于1953年在巴黎巴比伦剧院上演。而巴尔扎克的《投机商》,又名《麦卡代》,开始时叫做《好吹牛的人》或《自命不凡的人》,于1848年创作完成,于1851年8月25日在巴黎竞技剧场首演,连演七十三场,被认为是作家最好的剧作。1868年,这部剧又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并成为这座剧院的保留剧目。1935年、1936年和1948年,这部剧被杜兰改成“三幕四景,重新搬上舞台,直至近四十年,此剧仍不时有演出机会”[4](P767)。所以,贝克特不知道巴尔扎克这部剧是不可能的,他的《等待戈多》虽然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的表演方式,但里面的深层的相似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我们认为,贝克特的戈多(Godot),就来源于巴尔扎克的发音接近的戈多(Godeau)。这一点早已有人注意到:“戈多这一人物的由来同巴尔扎克的一个喜剧剧本《自命不凡的人》有关,该剧中就有一个众人都在谈论又始终不曾露面的神秘人物戈杜”。[6](P167)“戈杜”直接被李玉民翻译成“戈多”,应该是有意指出二者之间的明显的联系。
巴尔扎克的《投机商》,本来演绎的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破产的悲剧,却因为作者加上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结尾而使悲剧变成了喜剧,戈多携带着财富从加尔各达归来,他已经与米纳尔的母亲结了婚,并还清了麦卡代的所有债务。米纳尔再次向朱莉求婚,获得了应允。整个故事有惊无险,但这样的结局也降低了主题表现的深度。田红卫在《寻找戈多——论寒(塞)缪尔· 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一文中说:“默卡迪特(即麦卡代)利用假戈丁(多)的出现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投机。但这一欺骗行为被发现了, 默卡迪特破产了, 戈丁的最后归来成为泡影。”[8](P87)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却还原了人类命运悲剧的常见面目,戈戈和狄狄凄凄惨惨,痛苦地强捱时日,而这种痛苦又是遥遥无期的,这就显现了这类题材所该有的深度。“贝克特从形式上说是在戏仿,但他表现得更为抽象,也就更为概括,含义更广。”[9](P244)在《等待戈多》初演的“幕间,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在休息厅里大打出手。”但它很快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不多几年里,《等待戈多》被译成数十种文字。”[7](P144)贝克特笔下的戈多明显地来源于巴尔扎克的《投机商》,但《投机商》是以悲剧形式上演的喜剧,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以喜剧形式上演的悲剧,二者的差别虽在微秒之间,但因《等待戈多》没有一个狗尾续貂式的结局而显得更胜一筹。
[1]巴尔扎克著,李玉民译.投机商[A].巴尔扎克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巴尔扎克等著,李玉民译.法国戏剧经典(19世纪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项晓敏主编.外国文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艾珉.投机商题解[A].巴尔扎克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陈惇主编.西方文学史(第3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6]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张英伦.贝凯特[A].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等主编.外国名作家传(上)[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8]田红卫.寻找戈多:论寒缪尔· 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J].北京: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9]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