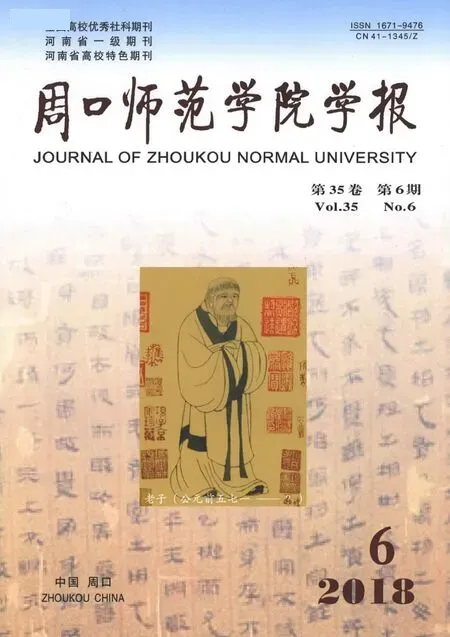试析《米格尔街》中底层人的价值观
李明珠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公外部,河南 郑州 450053)
维·苏·奈保尔(Vidiadhar Suraiprasad Naipaul,1932-)出生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后获得奖学金去英国留学,学成辗转于第三世界国家,书写各国游记,把获得民族独立后的国家的真实状况展示在世人眼前。他本人经历过特立尼达、印度、英国三种不同文化的熏陶,有过精神困惑也有过精神回归。奈保尔的文学作品屡获大奖,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很多文学批评者称他为“浪子”“无根者”。实际上,这只是他复杂的成长背景和冷静的叙述口吻造成的。作为文学创作者、舆情观察者和研究思考者的奈保尔,他要对自己的创作负责,这些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挣扎与矛盾之处。他很想要殖民地的“真实”,苦苦寻求殖民地的“本原”,多少削弱了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在作品里的体现。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牛津大学毕业后创作的处女作,行文简单流畅,文笔风趣,可读性很强。这部作品为他斩获1959年的毛姆短篇小说奖,带有“伪自传”的性质。这部集子由17个平行展开的短篇构成,由一位男孩把这17个故事串起来讲述。每个故事中除了主人公以外,出现的人物会在其他故事里以主角的形象再出现。这位串起全篇的男孩也是这条街上的一分子,在他眼里这里的人民既质朴又愚昧无能,“他”只想逃离这个“贫民窟”,离开这个没有存在感的殖民地——特立尼达。
价值观,是人基于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观体系中,有两个核心价值观念,分别是“关于生产劳动的价值观念和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1]89-90。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包括集体人格和精神价值。价值具有文化赋予的性质,很多事情在特定文化中有其特定的价值,脱离这个文化背景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反观《米格尔街》这部小说集,里面充满对上述概念的印证。笔者接下来从男性角色的价值取向及女性角色的价值取向两个方面进行文本细读。
一、男性角色眼中的世界及价值观念
小说集里17个故事有15个都是写男性的。这些男性里有孩子有成人,作者在单个的故事里展现殖民地男性对殖民地现状、人生、择业和婚姻方面的价值取向,从而让读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整体的把握。首先来看当地居民对自己现状的理解。在短篇《曼门》中,曼门看上去似乎疯疯癫癫,模仿耶稣受难让其他人向自己砸石头。等到其他人真把他砸到流血,他又开始大声咒骂。这个情节初读有点莫名其妙与忍俊不禁。但是往前翻看你就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有人自认为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发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曼门之前在选举中积极参与,自投一票却总是能得到加他自己在内的三张选票。他还热衷于“书法”,只是这书法是英文单词。“曼门的口音也令人捉摸不透,他说话时,如果你闭上眼,就好像在跟一个不太注意语法的英国绅士谈话”[2]39,“我们米格尔街上的哥们儿,对街上有这么一个人,颇有些得意”[2]42,原文中的这两句话意味深长。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特立尼达岛上的人来说,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说英语?据资料记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被殖民史源于1530年,其间多次易主,有“欧洲殖民者棋盘上典当最多的地方”之称。在1814年划给英国前易主31次,1957年加入西印度联邦,1962年独立。该地区石油储量丰富,人口以黑色人种为主。官方语言为克里奥英语,是一种英语方言。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殖民地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基调。“当经济长期强劲发展的地区或者国家,它的地域文化就有变成国家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趋势。反之,当你长期不行的时候,一部分原来是由你上升为世界文化的也要回归为地域文化。”[3]小国弱民,积贫积弱。国民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长期没有主导权,因此,像曼门这样的人尽管看上去疯癫、愤懑、乖张,实际上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及殖民地人民的抑郁迷茫。有人放荡不羁行为怪僻,也有人以流利掌握宗主国的语言为豪。其背后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国家寄人篱下状况的心知肚明却无力反抗的可悲心理。表面上的傻并非真傻,实力悬殊的痛才是最痛。在短篇《布莱克·沃兹沃斯》里,流浪诗人沃兹沃斯先生追求诗意,追求纯美的生活,最后潦倒至死。主人公可能真实存在,也可能只是一个寄托作者的理想与价值信念的形象。在作者那里,流浪诗人才是真正人生的代表,是精神世界的旗帜。而诗人院子里的杧果树、可可树、李子树是真善美的化身,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水泥砖铺成的地面”,“一切都好像表明B.沃兹沃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2]57。特立尼达在很久以前也是个充满真善美的地方,可是后来殖民者的到来与覆盖全球的现代化,让这个地方失去了特色和繁荣的精神文化。
短篇《择业》中,伊莱亚斯第一次考剑桥高中文凭时,老师预言他会高分通过,实际上并没有。有人就说了,“你指望他们让伊莱亚斯及格?”[2]32后来第二次考试他通过了,获得了三等文凭。第三次当他想要考取二等文凭时却没有通过。又有人说了,“咱们哪能去和人家英国人比,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说这孩子通不过考试,可那些人会让他取得更高等级的文凭吗?”[2]35寥寥数语,便能让人明白当地人不是没有志气甘受剥削,而是有志气没运气没钱也无法抗衡殖民统治。短篇《懦夫》里的大脚明明看上去孔武有力,在当地也是威名赫赫,却在和一个来自英国的毫无名气的拳击手比画时落荒而逃。英国是特立尼达的宗主国,被殖民心态让殖民地人民面对殖民者有心无力,自我贬低。精神殖民加资源剥削,特立尼达的繁荣也是徒有其表。更加滑稽的是,殖民地的人民既被殖民者塑造了世界观,同时心里也非常清楚这种塑造的来龙去脉。
二、男性角色眼中的人生观与择业
在小说集第一篇故事《博加特》里,主人公博加特平时无所事事,晃晃悠悠,装模样地做着“高级裁缝”的工作,随心所欲放荡不羁。后来他又从米格尔街出走,结婚生子,为了生计也干些非法的勾当。在这背后是他漂泊无依的心,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博加特类似,米格尔街上的波普身为木匠不务正业,光靠妻子在外务工养家,后来老婆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他又竭力想要挽回。再后来波普靠偷来的材料翻新了房子接回了老婆,却好景不长又蹲了班房。这串滑稽戏背后暗藏着苦涩。大字不识的人想要思考人生,不为生计发愁是不可能的。做流浪汉倒是够格,可波普又看不起连老婆都娶不起的闲汉们。“街上没有一个人为波普蒙受蹲监狱的耻辱而难过,因为这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可能遇到”,“他像个英雄似的回来了,他成了这帮哥们心中的一员,一个比海特和博加特更冲的硬汉子”[2]17。在短篇《母亲的天性》中,劳拉有8个不同父亲的孩子。米格尔街上的人并不歧视她,反而理解同情她的辛苦。尤其是在其大女儿未婚先孕走上劳拉的老路时,男人们也没有表达出恶意。米格尔街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人,就是博勒。他由于受过骗和对殖民地政府极大的不信任,就发现了一条真理,即“决不能相信报纸上讲的事”[2]159,这是博勒全部的人生哲学。再后来,博勒觉得自己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活着没啥盼头,就想赌一把,买张彩票。后来中奖了博勒却不肯相信,愣是撕掉了价值300块的彩票。这究竟是生活捉弄人,还是人自己作的?背后原因大概是这个怪相频出的殖民社会。值得一提的还有贯穿全文的人物海特的人生。海特对孩子们很大方很负责,为人洒脱,是“我”的偶像。海特身上部分折射出了“我”的人生观。等到“我”长大成人,我不再希望成为垃圾车司机埃多斯那样的人,以前的老师也是那么愚蠢和乏味,不是“我”想要的。由以上这些典型的殖民地人生活模式可以看到,当地人实际上并不以宗主国的道德教化为准绳,由于贫穷和自身素养的低下,很多人都是怀揣梦想却难以实现,这种受限的和混乱的社会管理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人生观又反过来指导着他们的行为。
小说集里有一篇《择业》,讲的是米格尔街上孩子里面的佼佼者伊莱亚斯的故事。前文已提到,他一次次想要通过英国人组织的剑桥高中文凭考试,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脱离乱糟糟的家庭。全凭一己之力从潦倒暴力的原生家庭脱颖而出已实属不易,可是由于没有贿赂当权者,伊莱亚斯还是没能通过考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最后,没背景没门路的伊莱亚斯只能去开垃圾车,当起了街头贵族,一肚子学问也只能自己消化。也许当初的教养和忍让在理想无法施展和琐碎的清垃圾工作中消磨殆尽,伊莱亚斯会成为和他父亲一样酗酒暴力的人。在《择业》这个故事中出现了后面《蓝色卡车》里的主人公埃多斯。这个人来自印度社会中的下等种姓,却是米格尔街上的“上流人物之一”。可见远离印度本土,殖民地的文化融合可能削弱了当地印度传统等级观念。埃多斯的工作收入稳定又有外快,所以人人羡慕。有很多女人为了生存打他的主意,最后他挑了一个西班牙美女并为其养孩子,也是各取所需。尽管大家身处殖民地,身处底层社会,却没有互相践踏,互相坑害,相反是互相扶助,互相理解。从大家对单亲妈妈劳拉的同情,到埃多斯设法把老博勒卖掉的手推车弄回来,再到街上的女人们合力帮埃多斯带孩子,等等,底层人内心深处的善意和他们身上的劣根性一样闪闪发光。他们也因此选择了特有的人生道路,构成了与宗主国完全不同的国情。
三、女性角色眼中的婚姻与处世观
《米格尔街》对于女性的描写不是重点,单独讲女性的章节也就2篇,分别是《母亲的天性》和《爱,爱,爱,孤独》。其他的女性角色零星穿插在个别篇章中,比如《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焰火师》《机械天才》等。在奈保尔笔下,男人的故事里自然少不了女人。从男性对待他们伴侣的态度上可以看到真实的人性——尽管是侧面的。而女性的态度和观念就要多变一些。在殖民地大环境中生活,女性处于底层的底层:既要挣钱养家做家务,又要忍受丈夫拳脚暴力。如此恶劣的社会风气发展出她们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在《叫不出名堂的事》里,木匠的老婆待人诚心,却因为丈夫不作为而与园丁私奔,后来丈夫偷材料盖了新房子,她又回家并等着木匠狱中归来。另外有一位反复出现的女性,就是每个故事的叙述者 “我”——的母亲。这位母亲坚强、精明、节俭。有文章分析称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出身印度的高等种姓,所以这位叙述者的母亲很可能就是以作者母亲为原型,结合了殖民地典型的母亲形象创作的。母亲是位严母,经常殴打“我”,训斥“我”。同时充满了生活智慧,拥有面对现实清醒沉稳的头脑。比如她劝海瑞拉夫人:“你知道,海瑞拉夫人,我真希望你能像我,如果一个人在你十五岁时娶了你,我们就不应再听那些无聊的事,更不会有什么心啊、爱啦乌七八糟的事儿了。”[2]136再比如,当“我”离开米格尔街外出求学时,母亲因为迷信还特地在行车道旁放一罐牛奶。当我走过时踢翻了它,母亲脸色一沉。这些生动的小细节勾勒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也从侧面显现出人物的内心和观念。另外这些作品中有两位作者轻描淡写的女性。一个是埃多斯的女朋友,一个是《直到大兵来临》里爱德华的老婆。这两个女人一个是西班牙女郎,一个是白人妇女。面对艰难的生活,有的女性并不是想要婚姻,而是想找个男人做“长期饭票”。埃多斯的女朋友把血缘可疑的乐乐交给埃多斯抚养就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生存方法。她手中有埃多斯的把柄,又有埃多斯想要的美色,所以成功甩掉了孩子这个包袱。爱德华的老婆也是名投机者,因为各种原因和爱德华在一起,又因为浪漫主义而移情他人。《焰火师》里墨尔根的妻子、《机械天才》里比哈库的老婆都对这个女人有成见,因为她俩是米格尔街上传统贤妻的代表。就像比哈库太太评价爱德华的老婆:“她可是个现代派,她们这种人需要丈夫在外工作一天,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她们就知道往脸上擦胭脂抹粉,走到大街上扭屁股。”[2]187-186这些话里的婚姻观念一目了然。爱德华不打老婆,比哈库太太们就要嫉妒他老婆的能耐。她们对丈夫忠心耿耿,真心可鉴日月,却换来拳打脚踢或是背叛。爱德华的老婆不会生孩子还备受宠爱,当然令她们看不惯。除去这些“正统”女性,奈保尔还描写了一些妓女,都是扁平化和脸谱化的。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是她们的信条。
在奈保尔笔下,女性是可怜的、坚韧的、多情的、拖累好男人的。然而在殖民地复杂的社会境况里,本质不坏但是颇有个性的男性只有遇到技高一筹的女性才能被驯服。这个两性关系的事实,通过奈保尔的描写十分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下面来谈谈其他比较重要的女性角色。先说上文提到的伊莱亚斯的母亲、粉红房子的女主人。这是一位卑微到名字都没有的女性,她要每天忙碌不停,而且病病歪歪的。她的丈夫乔治拿家人当沙包,发泄自己身为男人却潦倒不如意的愤懑。儿子比较争气,长大后乔治不再打他,而是拿妻子和女儿出气。后来妻子被生活和丈夫的拳脚拖垮,魂归西天。在这个过程中,她连句话都没有,留下的只有挨打时的惨叫。如同牲口一样,没有人权没有话语权。她的人生哲学应该就是沉默与忍受。再者就是乔治的女儿多利。她有了名字,也有了声音——咯咯的傻笑声。只有在婚礼上,她才有所反抗,爆发出大哭。哭声招来的只有欢笑。多利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婚姻只是下一个火坑罢了。其次特别提到的就是劳拉——8个孩子的母亲。生活不易、无依无靠都压不垮她,反而让她活泼快乐,光彩照人。唯有大女儿走上她的老路让她一夜之间老了一大截。她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用最恶毒的话谩骂儿女,殴打吃软饭的伴侣。但是她没忘让孩子接受教育:“受教育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事。我可不想让孩子们像我这样过一辈子。”[2]108-109劳拉既泼辣又有反抗精神,同时对身为女性感到憎恶。因为在第7个女儿出生后,她感到自己很没福气,女儿多了是件晦气的事。为什么?因为在殖民地,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她感同身受,却只能向命运屈服。最后大女儿投海自尽,劳拉只说了几个字——“这好,这好,这样更好”[2]110。这几个字也是其对生活的妥协和对人生的绝望与抗议。最后说一说《爱,爱,爱,孤独》里的海瑞拉夫人。她离开自己的医生丈夫并和丈夫的病人私奔到米格尔街。她或许是一个像娜拉一般觉醒的妻子:“我并不讨厌他,只是无法忍受他身上那种医生的气味,简直要憋死我了。”[2]135但是这位金丝雀一样优雅美丽的富太太并不属于这里,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继续过她优渥的生活。这种视生活同儿戏,任性妄为的女性并不常见,但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让米格尔街上的女性群像更多姿多彩。同在特立尼达,身处不同的阶层,女性持有不同的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
《米格尔街》中的那些小故事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味道,米格尔街也是整个殖民地的缩影。特立尼达有很多条米格尔街,一条大街就是一个世界。外人眼中的贫民窟,在奈保尔笔下充满勃勃生机。来自外界的经济剥削、政治包围和精神殖民并不能摧毁当地人的心灵,反而让他们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通过有差异的个体间观念的比照,读者可以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二战后殖民地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