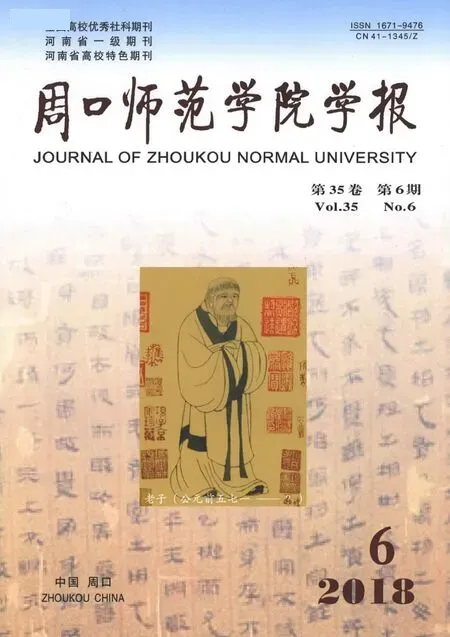以影载道:《百鸟朝凤》的民族寓言与时代焦虑
孙孟猛
(宜宾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第四代电影艺术家登场于新时期大幕将启的年代,“他们贡献于影坛的是一种艺术氛围,忧伤而又欣悦”[1]。戴锦华将其称为“在倾斜的塔上瞭望”,一方面,他们想要讲述自己的历史,结果讲述的却是自己生活的年代;另一方面,他们希望用影像记录独特而又畸形的个人命运,却只能诗化地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畸形的历史。第四代导演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登上历史舞台,以一种忧患意识审视着个人与国家,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联系起来,放置在整个历史图景中进行个人化的解构与重建。《百鸟朝凤》既是吴天明导演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同时也为第四代导演画上了句号。影片通过讲述焦三爷与游天鸣之间唢呐技艺的传承与坚守,反映了在西方文化观念的渗入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下民族文化逐渐式微的窘境,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审视个体轨迹下的民族命运;吴天明在关注乡村、反思民族文化的同时,既有面对社会发展必然的无可奈何,又饱含着对民族文化渐行渐远的迷恋与不舍,在创伤和犹疑中完成了民族影像的个性化言说。
一、个人叙事与民族寓言:丧曲为谁鸣
在吴天明导演的影片中,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炽烈而醇厚,对乡土中国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迷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第四代导演所集体拥有的民族情怀。比如影片《老井》那苍凉的背景下,村民为生存顽强抗争的图景扣人心弦,为民族疾苦而激动,为民族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感怀,创作者的所思所想通过影像世界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电影《百鸟朝凤》一以贯之地延续了导演的民族情怀,以一种忧患意识反思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国家。影片结尾,游天鸣独自站在唢呐王焦师傅坟前,吹奏百鸟朝凤为师父送行,画面给人一种悲凉之感,这既是游天鸣表达对已故师父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也寄托了导演在时代浪潮风云变幻中对传统文化逐渐凋零乃至消逝的过程中深感无可挽回的无奈叹息。
(一)唢呐传承
寓言是一种运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从而给人以启示性的文学体裁。《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寓言是使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性质。它以文本内的叙事关系喻指文本外的叙事关系,因此它便在表层文本和深层文本之间建构起了丰富的联系。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Jameson)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的文本,总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受到冲击的寓言。”[2]在他看来,第一世界的存在使得第三世界的个人与民族普遍存在着难以确定的人生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感和焦虑感是第三世界民族与个体的共同命运,而作为个体的困惑与焦虑折射出的即是整个民族文化自身的困境。
“同样是乡村叙事,有宽度更有长度的《白鹿原》写的是家族的时代变迁”[3],而吴天明却将目光聚焦于唢呐匠两代人的坚守,反映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的尴尬境地。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唢呐只有在处理红白喜事时才使用,而《百鸟朝凤》只有德高望重,为百姓、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逝世后才能享用,这一原则不仅为焦三爷一直坚持,同样也是第四代导演所持有的艺术理念与历史使命一贯追求的喻指。传统文化在走向现代性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现代潮流的冲击与挑战,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过程中实现发展与创新的内在要求,这个过程必然会带来阵阵伤痛,甚至流血牺牲。在祝寿宴上,游天鸣的唢呐队不得不面对西洋乐队的冲击,这段演奏对斗热血而悲壮,充满了英雄迟暮的苍凉之感。我们那个年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以一种西西弗斯似的行为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建构,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乐器被毁,头破血流。我们在叹息传统文化逐渐消失的同时,一面又鄙夷固执老派的文化传统仍在因循守旧,以至于生存艰难,蹒跚前行。我们在反思传统的同时,更应该反思自己,虽然打倒了“孔家店”,却也因此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自我的信仰也迷失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不仅是影片中游天鸣对唢呐技艺逐渐没落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丧曲为谁而鸣,不只是吴天明导演对唢呐文化传承的思考,也是一种对民族现实的真实观照。
(二)置换的想象
《百鸟朝凤》是导演吴天明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托物言志的作品,影片通过讲述唢呐艺人游天鸣从师学艺的成长经历,表现了民间传统艺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精神气节。正如黄建新导演所评价的:“吴天明用一个‘年轻生命的成长’与一个‘生命的消亡’来交叉表现了一种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他的,也是全人类的。”[4]吴天明以一种匠人精神观察和反思民族文化,运用置换的影像策略,建构起唢呐与民族文化、影像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参照体系,以影像世界投射现实社会,在想象与重构之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带有寓言性质的乡村图景。
影片中置换手法的使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唢呐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在电影《百鸟朝凤》中,唢呐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族传统文化被冲击、被边缘化、被一些年轻人排斥的尴尬境地。影片讲述的不仅仅是关于唢呐技艺的传承问题,在西方文明和城市化的冲击下,唢呐所面临的困境同样是许多民族文化技艺传承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唢呐仅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之一,唢呐艺术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命运的未来写照。其次,影片塑造的焦三爷这个人物形象与导演吴天明也存在着许多共性之处,如对民族文化的坚守、艺术追求的执着等,他们两者都体现出一种匠人精神。影片中有许多细节可以看出焦三爷和吴天明身上存在的共同之处,具有明显的喻指意义。陶泽如饰演的“唢呐王”焦三爷将唢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年老体衰时,他为无双镇的唢呐不能演奏而四处奔走;生命垂危时,他时刻惦记的不是拿卖牛的钱为自己治病,而是想为徒弟置办一套新的唢呐。而电影《百鸟朝凤》也是在吴天明逝世一个月之后才得以制作完成,他用生命演绎了对艺术的坚守与追求,对匠人精神的现实诠释。影片中焦三爷对游天鸣的要求亦是吴天明对匠人精神最好的注解。最后,焦三爷将自己第一次学习唢呐时师父送给的唢呐,又再次传给了天鸣,并告诉他别看它个儿小,调儿可高,调儿越高唢呐就越小,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不管做人做事都要戒骄戒躁,保持一颗谦虚之心;还有时刻叮嘱徒弟唢呐离口不离手,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而是吹给自己听的,要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这是师父对徒弟的要求;无双镇不能没有唢呐,这是匠人对艺术的守护,也是吴天明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殷切期盼,民族文化必须得到重视,一代代传承下去;每代弟子只传一人,这个人必须是天分高、德行好的人,这是匠人对德行的坚守;等等。这些细节不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严谨、执着、坚守的匠人形象,同时也是导演吴天明最好的自我写照。通过置换的想象,导演完成了理想的现实与现实的理想之间的影像建构。
二、时代焦虑:伦理秩序的颠覆与陷落
吴天明导演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一员,同样经历了社会的激烈变革。一方面,面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纪实美学的冲击,进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另一方面,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深沉的道德关怀与家国情怀背景下进行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反思。从影片《老井》《人生》《变脸》到《首席执行官》《百鸟朝凤》,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通过独特的电影表现手法记录乡土中国的图景,审视和反思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影像世界中建构起关于个体和国家的时代记忆。
(一)乡村叙事:民族记忆最后的瞭望
电影《百鸟朝凤》以一种“乡野世界挽歌般的文化哀悼成为浮躁现世与世道人心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和宗法伦常的瓦解与崩塌”[5]。在他的影片中几乎都设置了一个有关“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在城市文明(西方文明)对乡村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压迫焦虑中,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影像书写。因为他选择的立足点不在城市(西方文明)而在于乡村(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讲述便成为一种美丽而凄美的悲剧性言说。“在一种怀旧式的、美丽的诗意氛围中,一步三叹地将中国民族形象和民族文化送上了人类城市化(西方化)历史的祭坛。”[6]影片中,面对时代的变化与现代性的冲击,传统文化渐渐走向没落,无论是电影中的焦三爷和游天鸣,还是作为导演的吴天明,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影片中表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片段尤为明显,作为唢呐班的新一代班主第一次出班接活儿,遭遇到西洋乐队的挑战,进而引发了一场乐器大战,虽未说明结果,却早已不言而喻。不仅仅被视为自己生命的唢呐被毁,作为唢呐匠最基本的尊重与尊严也被无情践踏。影片中有两处细节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和伦理秩序的崩塌:一处是徒弟在师父面前的落寞直言,“如今庄里操办红白喜事,都请洋乐队了……”;另一处就是,焦三爷阻止徒弟离家外出打工,一脚踩住行李袋,却被徒弟无声夺去,只剩徒劳。可以看出,导演借此表现出自己面对传统文化的消亡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如影片中所言,“接师礼没了,规矩没了”。
乡村是吴天明电影中的重要意象,并不仅仅是作为地理区划存在的,而是有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和指称作用。从他早期的作品《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到后来的《老井》《变脸》,再到最近的《百鸟朝凤》以及未完成的遗作《农民日记》,这些影片的故事背景都发生在乡村。在吴天明的世界中,乡村并不完全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常常寄托着时代记忆,充满着作者丰厚的感情意蕴。乡村代表的更是一种民族文化聚合地,是民族文化的根,吴天明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对民族文化的根的坚守与传承,而这种坚守也是带有想象性的、诗意化的。在乡村想象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通过这种手段试图缝合想象乡村与现实乡村之间的差异性。《百鸟朝凤》中的乡村是建立在古老中国的农耕文明基础上,唢呐技艺的传承与流行更具有历史感与仪式感,唢呐人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个封闭的文化空间内,吴天明通过乡村书写历史、记录历史,以乡村的变化审视历史,思考未来,反思民族文化的发展命运。
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冲击,西方文化观念的渗入,已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不得已或走向没落或重新解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也不得不走向陷落的尴尬境地。影片中,唢呐匠本应是一个受人尊重、体面的职业,最后不但接师礼没有了,最起码的尊重与尊严也没有了,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将要被剥夺,只能沦为沿街乞讨的工具,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悲剧。
(二)主体的焦虑性
如同第四代其他导演一样,时代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政治语境还是社会语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电影艺术本身也产生一种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要求改变当时影坛中呆板僵化的电影表现形式,重新回归“十七年电影”时期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使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纪实美学的引入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西方文明的侵入,对几千年形成的东方文化传统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东西方文明的文化碰撞中,农耕文明/东方文明在阵痛与犹疑中完成了现代性的书写。第四代导演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语境下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肩负着革新电影语言的历史使命,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向往与追求;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与不舍。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求与东方农耕文明的迷恋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冲突,当这种矛盾冲突并置在同一主体即第四代导演中时,就会产生理性追求与感性留恋之间的选择悖论,而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也就会显现出一种犹疑的叙事基调。这种叙事的犹疑性是时代焦虑感的内心投射,而这种迷惘的风格乃是“中国当代最初的城市性的表达”[7]。
吴天明有着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艺术自觉,而这种自觉性也投射到他的电影作品中,使得他的影片始终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思维。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促使他去反思和审视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在对民族文化悲剧性影像建构的过程中,完成现代性的书写,从而观照自身现代性演进的合理性。在吴天明的电影中,这种现代性的演进常常伴有主体焦虑感的出现,这种焦虑使他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不断徘徊,最终使他的电影呈现出一种悲剧意味。吴天明的早期作品《没有航变的河流》中,静静流动的河水,在水中飘荡的排船都具有明显的指代意义:排船是家的喻指,河水的流动性打破了家的固定性,也暗示了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对自身命运的焦虑在时代的压迫中使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导致了一种诗意的悲剧。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这种焦虑感的体现更为直接和明显,出身于农村的高加林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与渴望,而农村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两种职业的选择——进城工作和回农村种地——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两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这种对乡村的逃离与对城市的向往成为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的现实投影,这也直接导致了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百鸟朝凤》中,吴天明将这种焦虑感表达到了极致,漂泊异乡的经历使他对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与思考。新世纪以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民族文化受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吴天明以一种挽歌式的语调将唢呐技艺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命运联系起来,在悲剧性的影像建构中完成了现代性的书写。
三、以影载道:一场无望的自我救赎
与第三代导演相比,第四代导演以一种痛苦审视与自我拷问的方式在历史中艰难前行,他们常常辗转于时代的重荷之中,一方面是对传统的不忍舍弃,一方面又是对传统枷锁的不懈突围,在批判的理智和批判的勇气之间不断犹疑,使他们的作品也产生丰厚的意味,成为这一代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现实投影。
在传统伦理文化中,讲求天地君亲师,虽然师徒关系仅排末位,但却说明师徒关系是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宗法血缘之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就是这个道理。唢呐王焦三爷表面上虽然对徒弟严厉甚至苛责,但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内心因重视爱护徒弟才会满腔热情,才会严厉要求。这是对传统技艺的严谨追求,也是一种对徒弟将唢呐发扬光大或者不至于埋没的殷切期望。徒弟游天鸣出师后回来探望师父,焦三爷打开了一坛封存了20多年的好酒,一醉方休,一种透着悲凉的幸福感,让人心酸又心疼。徒弟游天鸣对师父的敬畏和爱戴,以及后来对唢呐传承的执着和坚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师父对徒弟的影响不仅是授业更是传道解惑。在影片结尾,只剩一座坟、一个人和一条狗,徒弟在师父坟前含泪吹奏“百鸟朝凤”,把这份师徒的情谊推向顶点。传统师徒关系在如今这个价值多元、个性解放的社会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却能把匠人精神衣钵相传。在吴天明的心里,“我们看到了他那种文化之于心底的坚持,誓死不服输的倔强”[8]。影片的结尾耐人寻味,对唢呐能否传承延续以及游天鸣的命运,导演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留下了足够思考的空间。一种可能是如影片中街头乞讨的老人一样,唢呐只能沦落为街头行乞的工具,唢呐艺人的生存空间愈加逼仄,也可以说是苟延残喘;另一种可能是社会外在环境的改变,由政府机构出面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如影片中文化部门的出面,政府部门作为国家机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府支持与帮助可能成为唢呐技艺传承的希望,但此时的唢呐传承却只能束之高阁,成为某个展览会或博物馆中的表演形式,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本身的艺术魅力也黯然失色。不管最终出现哪种可能,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唢呐的命运仍然是日薄西山,离我们渐行渐远,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只能在历史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中体验一番。唢呐王焦三爷带着不甘与无奈,也似坚守与鼓励转身离去,他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来临。游天鸣站在孤零零的坟前,面对一抔黄土以一曲“百鸟朝凤”为师父送行,也为唢呐艺术兴盛的“黄金时代”送行,有痛苦和不舍,有坚守和自信。虽时过境迁,但唢呐传承不会断,民族文化不会湮灭。
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百鸟朝凤》讲述的就是一个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把我们本该倍加珍惜和尊重的民族文化血淋淋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影片更多的是通过民俗呈现来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挖掘民族自身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投射出时代变迁的历史印记。影片透过焦三爷和游天鸣师徒对唢呐技艺的传承与坚守,折射出现实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冷漠,在传统文化逐渐凋零与消失的同时,社会呈现的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唢呐艺术的传承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秉持的文化态度是一味地保守,故步自封,坚持个人中心主义,全盘否决,还是主张历史虚无主义,全面西化?历史与现实证明,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传统文化应该扎根于生活这层土壤,深入群众中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传统文化才能迸发出勃勃生机。导演吴天明通过影片塑造了焦三爷和游天鸣两个人物形象,反思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将一段即将湮灭的历史影像化搬上银幕,以一种文化自觉和民族情怀叙述历史,观照现实。
四、结语
作为第四代导演中一员的吴天明,他既没有像第三代导演那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明显的教化意图以及拯救倾向,也没有同时代的其他导演那样对电影语言的种种实验革命,更不可能像第五代导演那样以一种俯视的视角剖析国民的劣根性,并能够毅然决然地投入商业片浪潮中。他始终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始终关注着个体与民族的命运,以自身的文化自觉性希望通过影像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说是一种忧思: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是不是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并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是不是可以和谐共生。老一代唢呐匠在与时代洪流的搏斗中被无情吞噬,而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捍卫了自身的尊严,以此希望唤醒大众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觉醒,但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救赎,带有一点点心酸,一点点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