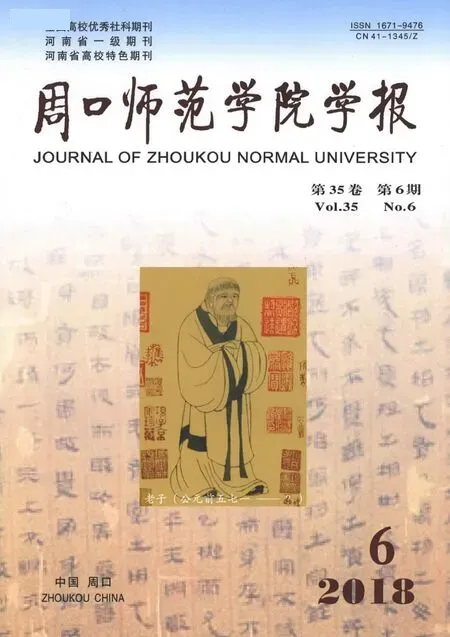虚静与情动:苏轼对韩愈的回应
何安平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韩愈和苏轼是唐宋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共同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对韩愈评价甚高,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言:“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1]509特别是“文起八代之衰”成为后人论韩的主要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韩愈完全认同,仅就两人文艺思想而言就有很大差异,突出表现在《送参寥师》中,其针对的是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如此针锋相对,对于我们了解韩愈和苏轼文艺思想的分歧和差异极有助益。
一、韩愈质疑
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是古文名篇。关于写作时间,有学者认为是韩愈生平前期之作,可能作于在长安任四门博士时期[2];也有学者以为当作于韩愈晚年[3]。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都只是推测,难以断定。这篇文章古往今来受到诸多关注,除文章本身的写作艺术之外,其中关于书法创作和艺术心理的描述也引人注目,常被作为分析韩愈文艺思想的重要理论文献,在书法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文中韩愈论书法强调专一其心,并以“不治他技”、擅长草书的张旭为例,认为写作草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情感在心中激荡不平,“有动于心”;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天地万物变化无穷的感染,有了“可喜可愕”的感情,才“一寓于书”。张旭正是如此,所以,他的书法才能“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如何做到张旭这样呢?韩愈明确指出:
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4]271。
核心就在于要“情炎于中”,让感情激荡,喷薄而出,因此对于利害欲念就不能不置之不顾或淡然处之。然而高闲是僧人,与此要求颇相矛盾,他们“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如此的心境与处世理念与“情炎于中”完全相悖,所以,韩愈得出结论:“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很明显,韩愈对高闲的书法造诣实有所质疑。虽然文末以“浮屠人善幻多技能”为由来解释,但只不过是在送序中的一种缓和之词。本序的思想与韩愈一贯的文艺观念相一致,如《送孟东野序》特别提出“不平则鸣”:“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也。”[4]233无论是国家之兴盛还是个人之不幸,只要心中有所感发,就以文学表达之,《闵己赋》“余悲不及古之人兮, 伊时势而则然;独闵闵其曷已兮, 凭文章以自宣”[4]9也是同样的意思。对于如何表达,韩愈则指出“气盛言宜”,《答李翊书》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171因此,韩文气势磅礴,富于力量感,后人评价韩文如海。
张旭被称为“草圣”,书法出神入化,为人狂放不羁,是一尽情尽性之人。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5]84李颀在《赠张旭》中道:“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6]1340韩愈文中对张旭的评述基本恰当,和作为僧人的高闲对照,确实反差极大,难免引起质疑;但并非僧人就不可为草书,书僧怀素就是草书高手,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评价为“纵横不群,迅疾骇人”[7]3416。两相对照,韩愈的疑问还能成立吗?
二、苏轼回应
到宋代,苏轼在《送参寥师》中对韩愈的看法给予回应: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8]905-907。
苏轼写作此诗是有意针对韩愈,对于韩退之之论“细思乃不然”,认为上人擅长草书“非幻影”,转到论诗上,言“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诗书相通,同为艺术创作,“欲令”四句可看做是苏轼对艺术创作的意见。这种思想在苏轼其他文章中也有反映,如《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1]《上曾丞相书》:“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1]
这一问题其实是对作者创作时心境状态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韩愈之所以质疑上人的草书,是因为他认为浮屠氏的心境平静如水,难以有情感的波澜动荡,而草书要达到张旭的境界,又必须“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创作心境差别如此之大,则上人的草书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同一问题,苏轼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赞成“空且静”,而且赋予空静更为重要的意义,但受诗体所限,苏轼没有详细分析空静的地位,也没有确切说明空静与情感的关系。以此来回答韩愈的疑问,或许还不是很充分。
空与静是佛教的观念,苏轼受佛教影响很深,这首诗的写作对象又是僧人,借助佛学,以禅论诗,自在情理之中。孙昌武先生指出:“苏轼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就是他认为诗的韵味可以得自内心的闲静。这与禅宗的心性观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他不强调以热烈的主观感情去回应外境,而认为心如止水才能更好地反照外物。”[9]442当然,苏轼的思想世界是极为复杂的,绝不会束缚于佛教的“空且静”。相反,他对于诗歌中的感情非常重视,在他的各体作品中也有充分的情感表露,即“情动”也存在于苏轼的观念与创作中。《南行前集序》:“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1]323可见,在苏轼的观念中文章的写作是作者受到自然万物的感发,心有所感而不得不表现于文字,情动于中而言于外,并非为作文而作文,此次行旅作品的结集《南行集》即是在这一观念下产生的,所谓“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自然事物如此,社会政事亦如此,《乞郡札子》:“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1]829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持反对意见,被贬出朝廷,变法失败,旧党当政,他又对变法中的合理措施建议保留,因此再受排挤。苏轼“遇事即言”“不合时宜”的作风和个性,决定他不可能只是个“空且静”的人,更多的则是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典型士大夫,所作诗文如他自述是“寓物托讽”“诗笔离骚亦时用”(《次子由诗相庆》)。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也认为:“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10]306“多怨刺”就是为情造文,有为而作,非无病呻吟,晚年学浪漫高华的李白,诗歌中浓郁的情思也是必不可少。所以,无论为人为文都有“情动”的一面。只不过《送参寥师》限于特定的写作对象和场合只强调了空静。我们追溯他文艺思想的源头,在禅宗之外,还应该注意道家思想以及传统文论对苏轼空静文艺观的影响。
三、虚静与情动
空静与虚静大意相同,使之与创作相关联。刘勰就已提出,《文心雕龙·神思》:“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11]245就虚静本身而言,较早且充分讨论的是庄子。《庄子》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心斋”。《人间世》:“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2]147[注]后文《庄子》原文与注释均出《庄子集释》,不再注出。又有“坐忘”,《大宗师》:“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道),此谓坐忘。’”成玄英疏:“虚心无著,故能端坐而忘。”“心斋”“坐忘”都集中到“虚”,除这两个特别概念之外,还有“虚”的表述。《人间世》:“颜回曰:‘回之未使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使有回也,可谓虚乎?’”成玄英疏:“未秉心斋之教,犹怀封滞之心,既不能隳体以忘身,尚谓颜回之实有也。”又言“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集释》引司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心斋”与“坐忘”意义相近,主要指心不受外物的干扰,与天相行,忘却身体、知识,与“道”合一,达到一种心灵的虚空、平静、明净的状态。如果心不能“止”,则谓之“坐驰”,所以“心斋”“坐忘”的核心即为“虚静”。庄子“虚静”与文艺创作没有关系,但却深刻影响了后代的艺术家,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宝贵资源。
但这种“虚静”能够直接产生诗、书等艺术作品吗?显然不能,即使如苏轼所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也仅仅是创作开始的一种可能。真正的创作必然是由于情感的推动。《毛诗序》即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3]6钟嵘《诗品序》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可见,诗之形成必须有内心情感的激荡,“情动”之后才有诗。诗歌如此,绘画亦然,北宋李公麟说:“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情性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焉。”(《宣和画谱》卷七)清恽寿平:“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无情。作画贵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瓯香馆集》卷一)所以,无论诗、画,都十分强调“情”对于艺术的重要意义。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里就持类似的观点,所以特别重视情感的郁勃动荡,激扬喷发。因此,可以说有“情”才有艺术。由此来看,韩愈在文中提出疑问确实是有道理的,“虚静”与“情动”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但若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二者其实并不矛盾,而且都是艺术作品产生的必要条件,只不过不是处于同一个层次,将二者分开观察,则问题就会得到较好的说明。
虚静是一种心境状态,强调的是内心纯净。《庄子·田子方》就描绘了一位拥有“虚静”之心的真画家。“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众史”心存名利,即使技艺高超,也是“技”,而非“道”,所作的画品格自然不高,而后来的画者不为利禄所动,摆脱一切束缚,不似众史之趋竞,心内虚静无所求,故为真画者也。宋代朱熹也认为:“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事物。”(《清邃阁论诗》)王国维以为:“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文学小言》)[14]4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论类似:“回黄转绿,看朱成碧,良以心不虚静,挟私蔽欲……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沦于幻觉。”[15]56诸家都看到虚静在认识事物时的重要作用,本此虚静之心才能祛除遮蔽,认识事物的本原。所以,以“虚静”为艺术心灵之基底,有此基底,才有可能识物之真,艺术才有产生的可能。但并不绝对,刘勰就已经有所补充,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然此基础必须存在,因为心灵在虚静下,摒除了私欲杂念,清净无著,心灵才处于一种开放澄明的状态,为与万物相感提供了前提。
“情动”则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没有情感的波澜动荡,作品就会没有生气,纵使已有虚静之心,也不能“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勉强为之,只会是“为文造情”。要使作为艺术心灵基底的“虚静”与“情动”连为一体,产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就必须要有“通感”(不是修辞上的通感),即人与自然之间取消对立与隔阂,物我无碍,相通相感。古人已多有论述,庄子就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而“庄周梦蝶”也形象说明了人与物并不是完全对立,而是能够彼此感知,“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庄周与蝴蝶区别明显,但却可以“物化”,从而取消了区别,物与我为一。“濠上之辩”中,庄周能于濠上知鱼之乐,也是因为他能破除人物之间的界限,而不是像惠施一样只看人和鱼之间的差异。这种思想并不是庄子一人之言,而是中国古代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普遍看法。《诗》之“兴”也与此种思想相关。起兴的一般是物,如花、鸟等,它们和全诗所要表达的情意密切相关。《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就是以桃花的美引出“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人是快乐的,而桃花也“乐”在其中。陆机的《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即是说人感受自然万物之变化而一己之情亦随之而变;当秋季落叶纷飞之时,萧瑟肃杀之际,人情即悲;而当寒冬退去,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枯枝转绿,人情也随其而喜。钟嵘《诗品序》也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16]47。所谓“感诸诗”当然首先是人受其感,然后作诗以达情。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是“通感”的展示。诗歌创作如此,绘画也是,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17]26郭熙所言几与陆机相同,都是天人一体,人物相通,也就是郭氏所谓“身即山川而取之”,明此,才能理解山之四季何以会对应人的四种情感。总之,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生命相通,物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人可以感受到自然的律动与情感,使之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相通相感。由此通感而产生情感。
现在,可以就虚静与情动的关系做一简单概括:“虚静”做艺术心灵的基底,是必不可少的,“虚静”就是要排除内心的利欲之念,保持一种澄明自在的心境。“情动”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虚静”与“情动”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虚静其心,才能真切认识事物,然后由于“通感”,物以感人,情动于中,而发之于书法或诗歌等艺术创作。韩愈的疑问其实是以“情动”来质疑“虚静”,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了“情动”的重要,而有意无意之间忽视了“虚静”之心。这首先是由于韩愈排斥佛教,将辟佛之旨贯穿其中,所以,《送高闲上人序》虽主要论书法,但没有正面评价,而是从根本上怀疑高闲书法已达妙境的可能性;其次,韩愈的文艺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尽管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在思维方式上还是一致的。苏轼对于佛教不仅不排斥,还很亲近,他的思想由于融合了儒释道,对于庄禅深有理解,又是艺术全才,所以指出了空静的重要性,认识比韩愈更为全面。苏轼一方面认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另一方面,他也认可“情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虚静”与“情动”在苏轼的思想中和谐并存,使他的文学世界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