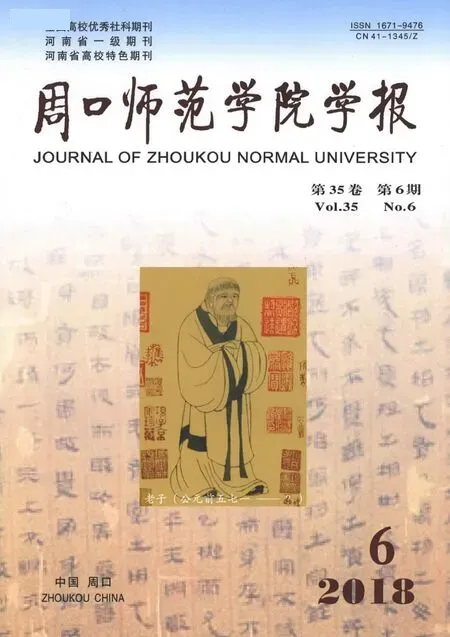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库娜尔都》的“他者”身份解读
陈丽君
(安徽新闻出版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601)
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1883-1969),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澳大利亚文坛中心人物之一,曾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小说《库娜尔都》创作于1929年,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该小说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澳洲早期殖民时期的乡村生活画卷。作品主题丰富,内容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白人与土著之间难以跨越种族藩篱的爱情故事以及维塔利班牧场的兴衰沉浮。小说于1928年在澳洲颇具盛名的杂志《公报》上连载发表,因内容涉及白人与土著人的性关系在澳大利亚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因此铸就了这部小说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时至今日,《库纳尔都》仍是澳大利亚文学中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其核心是把女性问题与环境问题相结合,反对二元式思维方式和父权制世界观统治下的对女性和自然界的压迫,把反对性别歧视、追求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终极奋斗的目标,主张建立一种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平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用“整体性”取代了 “二元论”, 解构了传统西方国家在两性问题上一贯提倡的主客二分原则,认可“性别、种族、阶级等种种不公正行为的意识形态与纵容对剥削、恶化环境等意识形态的关联性”[1]。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魅力在于,它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中心文化以及白人帝国心态的殖民情节在环境和性别上给人们造成的病态思维。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阐释经典文学作品,为探讨女性与环境问题拓展了新视野。
一、小说《库娜尔都》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
笔者认为,女权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使普里查德在小说《库娜尔都》中有意或无意地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流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元素。
首先,小说背景设定为澳洲早期殖民时期,殖民者大力发展畜牧业造成了以狩猎和采集为基础的土著经济土崩瓦解,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天地人共处的精神信仰分崩离析;作者笔下的维塔利班牧场因过度放牧从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乐园最终沦为废墟,揭示了早期殖民者在不断扩张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次,作者对女主人公名设极具深意,库娜尔都在土著语中意为“深井”。水对于地处澳洲西北腹地、连年干旱的维塔利班牧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伊始,女主人公便被赋予水的形象,承载着跨越种族的重任,然而流淌着土著人血液的库娜尔都,在一个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里终将无法完成使命,而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此外,作者着力描写了女主人公库娜尔都与维塔利班牧场主母子贝茨夫人与休的关系。无论是一手把库娜尔都培养为光彩夺目的“艾丝美拉达”的贝茨夫人,还是视库娜尔都为精神支柱的男主人公休,他们都无法跨越自己白人身份的屏障,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库娜尔都的毁灭。
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作者塑造了一个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发出声音的女主人公库娜尔都。然而无声胜有声,女主人悲惨的命运向世人揭示了西方殖民环境下,人类中心主义、白人帝国心态以及父权制中心文化在环境和性别上给土著居民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罪行。作品对土著女性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环境变迁的忠实描述,在充满生态危机的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二、被放逐的“他者”库娜尔都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论断明确提出,一切认可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者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小说《库娜尔都》中,白人对澳洲土著地区的早期殖民开拓这一背景对应了生态女性主义中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白人以过度放牧、机械挖井等手段不断地对土地进行开采来实现经济利益,最终导致土地的荒芜。在这一前提下,维塔利班牧场中白人对土著人的驯化与利用,男人对女人的物化与爱情交织其中。通过文本分析,能够准确捕捉到作者极力批判的是凌驾于自然与女性之上的目空一切的种族主义思想与男性价值观。白人统治者凌驾于自然,并通过对代表自然的土著居民 “他者化”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本文仅以小说女主人公库娜尔都为代表展开论述。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他者”与“自我意识”概念,认为只有“他者”存在,主体的意识和权威才得以确立。这一概念隐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白人以黑人为他者,通过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得出白人必然是更文明、更具智慧的结论。这种认知行为的弊端在于:一个主体若没有他者的对比,将完全不能认识和确定自我。小说《库娜尔都》中,白人首先通过征服自然获得相对于“物”的至高无上的“人的优越感”,进而对与自然同一阵营的弱势群体的人进行“物化”。通过对以库娜尔都及其族人为代表的土著居民的“他者化”,白人殖民者具有了相对的身份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使他们在土著的土地上把种族主义与父权制发挥到极致。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库娜尔都”跌宕命运的叙述,表达了对戕害包括“自然”与“女性”在内一切弱势群体的“人类中心主义”“白人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强烈控诉。
(一)“他者”库娜尔都与女性家长贝茨夫人的对立
贝茨夫人在小说中被描绘为一位被土著人称作“Mumae”(土著语父亲意)的女强人,作为早期殖民开拓者和维塔利班农场的女性家长,孀居的贝茨夫人一手使“延绵几百里都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岩蕨都不复生命”[2]9的几近破产的牧场日渐恢复生机,成为“牧草和灌木丛的海洋”[2]9。牧场的管理和运作都离不开当地的土著居民,贝茨夫人不得不面对与黑人共处的事实,她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控制着以库娜尔都为代表的土著居民来实现自己牧场复兴的梦想。
小说伊始,库娜尔都与小说男主人公,即贝茨夫人的儿子休尚处在幼年时期,两人是两小无猜的玩伴。休在母亲的安排下到城里求学,面对小伙伴的离去,库娜尔都“眼睛里充满了荫翳,像一头被遗弃的小野兽”[2]7。精明的贝茨夫人意识到小女孩“所遭受的痛苦不比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少”[2]7,一番深思之后把她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不仅教会她白人的生活方式,还让她帮助自己打理牧场的各项事务。在这种不同于周围土著女孩的成长环境中,库娜尔都从儿时那个满脸困倦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位“古铜色的女神”。然而对文本进行深层分析,会发现贝茨夫人的善举之后隐含着自己精巧的打算。一方面库娜尔都可以弥补她儿子离家后心中时时泛起的“孤独的疼痛感”,另一方面还能够满足她作为主人的身份优越感。当库娜尔都终于被她培养成一名将来能够服务于自己儿子的能干、高贵的土著女子,而且只听命于自己时,贝茨夫人心里充满“感激”。虽然她无法预知自己死后的情境,但是她坚信库娜尔都会一直陪伴在休左右。为了加强这种信念,她临终前留下遗言:“你若对休有丝毫懈怠,我就会化作白色的雉鸡,给你们带来噩梦,带来疼痛,吃掉你们的内脏……”[2]73作者笔下贝茨夫人对待土著人友好的假象下隐藏着她白人身份的倨傲。她一直生活在土著居民之中,然而土著人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工具,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保持着与他们的距离。
除了“将来可以陪伴休的人” 这一身份,库娜尔都还是白人与土著人的纽带。贝茨夫人通过库娜尔都向土著人传达自己“善待”对方的信息,因为她知道只要控制了库娜尔都,以库娜尔都丈夫为首的族人就会团结在周围为维塔利班牧场卖命,而她只需要付出“几匹马加上一张毯子”的代价。然而隐藏在贝茨夫人内心深处的却是她对土著文化的极度藐视。小说第三章,作者着力描写了类似于基督教文化中圣诞节的土著节日“红眼节”(pink-eye)的风俗仪式,贝茨夫人认为土著文化中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仪式是野蛮行为。当目睹库娜尔都陶醉于自己族人的仪式时,贝茨夫人甚至“想除去库娜尔都身上存在的土著元素”[2]24,她以自己的白人基督教文化为尺度来衡量一切“他者”文化,不允许任何白人向维塔利班牧场的土著人灌输基督教思想,因为基督教在她心目中代表着“文明”,而土著人的信仰代表“落后”与“未开化”。只要土著人不接受外来文明,一直维持未开化状态,那么“文明”就可以一直统治“落后”。一方面,白人牧场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为牧场谋取暴利;另一方面,相对于自己的白人身份,通过驯化和利用被视为“他者” 的黑人土著,其身份的优越性得以彰显,其人生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说,以库娜尔都为代表的土著人无论在肤色上还是在文化信仰上始终都是白人统治者伪善外表下借以彰显“自我”的“他者”。
(二)“他者”库娜尔都与男主人公休的对立
与贝茨夫人相比,小说的男主人公休并没有因为对库娜尔都的爱情而走出自己身份的困惑。白人身份使他无法跨越种族的藩篱而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无法接受库娜尔都土著女子的“他者”身份。作者笔下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占据巨大篇幅,但是他对库娜尔都始终保持缄默;至高无上的父权制使得他在库娜尔都受辱后“勃然大怒”,为挽回尊严,对她施以火刑后逐出自己的家园,直接导致了库娜尔都的悲惨结局。儿时玩伴与成人后相守的情分都在身份羁绊与男权至上的烈焰中焚毁,休的行为践踏了他与库娜尔都多年来的感情以及库娜尔都对他的信任与忠诚。“他自身的欲望就是衡量一切‘他者’,一切他自身以外的生命价值的尺度。”[3]
求学归来的休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丧母之痛使他奔走于丛林直到迷路失去意识。而库娜尔都一直暗中伴随左右,休醒来后发现库娜尔都一直在黑暗中守候的身影,便在这样一个情境中与库娜尔都有了一次身心交合的经历,他觉得“在这个空荡而荒凉的世界上,库娜尔都像是他自己的灵魂,是唯一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人”[2]61。男主人公的感触源于丧母后的无助与迷茫,他急需寻找一个能够代替自己母亲角色的人来弥补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缺失,而“库娜尔都一直都在那里”[2]109。然而爱情在身份与种族的枷锁下显得苍白无力,休很快迎娶了同样是白人的女子莫莉。牧场的荒凉与无趣终究无法挽留一个爱慕虚荣的白人女子,休很快面临被莫莉抛弃的命运,作为彰显白人尊严的道具,莫莉的离去并未对休造成精神上的折磨。随着情节发展,休在库娜尔都的丈夫暴病而亡后,为了不使库娜尔都落入他人之手,按照土著人的习俗,将库娜尔都收于自己屋檐之下,然而从灌木丛中的身心交合之后,“休再也没有像一个男人对待女人那样对待过库娜尔都”[2]125。休降低白人身份宣布库娜尔都是自己的女人,却不把她当做妻子一样对待,他急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白人的道德正义感,“尽管他的眼中都是对库娜尔都的渴望,却从来不碰她”[2]125。他的善举实际上是把自己“生命的中坚力量”完全物化占有,出于白人的尊严不能像土著人那样从身体上占有她,却把她当作物品一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他者”与“自我”剑拔弩张的矛盾爆发于一次暴雨后休外出放牧,一直觊觎库娜尔都的另一个白人牧场主盖瑞来到维塔利班牧场,男主人不在家的消息让他狂喜,酩酊大醉之后占有了无力抵抗的库娜尔都。放牧归来的休对库娜尔都进行了“谋杀般”的惩罚,他内心深处对库娜尔都的物化使得他不是寻找盖瑞复仇,而是通过羞辱和惩罚她来获得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安慰。被赶出家园的库娜尔都落入珍珠捕捞船员之手,“她从曾经骄傲、优雅而充满尊严的艾丝美拉达沦落为备受摧残、疾病缠身、面目全非的黑珍珠”[2]204。库娜尔都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休为什么如此待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改变了休……”[2]205休在库娜尔都离去之后意识到自己对她精神上的依恋与牵挂,但是白人的尊严不允许他像她的族人一样出去寻找她,而是陷入不断自问:“有人能相信吗?一个白人居然会对一个土著女人有这样的情愫!”[2]190他的自问愈加醒目地划清了白人与黑人的界线,把库娜尔都“他者”的身份推到界线以外。
三、结语
通过对女主人公库娜尔都的“他者”身份解读,不难发现小说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美丽土著女孩的悲剧故事。作者通过对女主人公与牧场母子关系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澳洲早期殖民时期畜牧业扩张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白人与土著的关系以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不断向自然发出挑战,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为解决饮水问题而不断利用现代机械在原始的土地上挖井,最终导致土地荒芜、沦为废墟的结局;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建立起种族的藩篱,即使是纯真的爱情也难以逾越。白人的过度放牧使土著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失去了自己的原始经济支柱和种族信仰,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二元思想主宰下的父权制剥夺了女性的身体、财产和话语权,以库娜尔都为代表的女性被极度“物化”“他者化”,在男性家长制的洪流中淹没,沦为牺牲者。对小说女主人公的“他者”身份解读,有助于读者通过作者的笔触去追寻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进一步挖掘小说的思想内涵;通过回顾一百年前的殖民历史画卷,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思索我们今天的世界所面临的相同问题;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对小说的解读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纵向的思考维度,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普世价值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