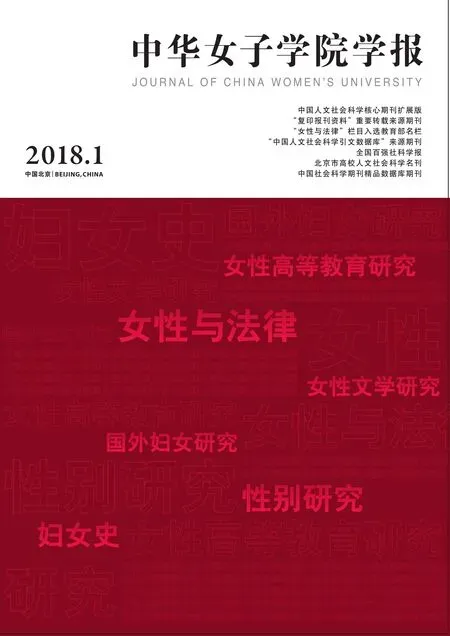贴切自然 神与物游
——略论《庄子》散文创作的艺术构思
梁克隆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当刘勰把这句话用来形容“神思”即想象的时候,“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艺术构思,则也就以“神与物游”[1]295的形式出现了。在整个构思过程中,作家要努力在“虚静”的状态下,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纵横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把平素所学习积累下的全部知识、感悟都调动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绝妙“思理”;在此基础上,作家还必须使自己绝妙“思理”完全地与经过选择的客观“物象”相沟通、相融合,赋之于新的生命逻辑,从而使“神与物游”成为现实可能。因此,“神与物游”的艺术构思是所有优秀艺术构思的重要标准与显著特征。
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庄子,正是凭借了其天才热情、渊博知识与深厚的人文修养,以及创造艺术境界与艺术构思方面的巨大才能,使神秘而智慧的《庄子》散文,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哲学。而整部《庄子》散文所创造出的艺术世界,应当说都是庄子非凡艺术构思——“神与物游”的完美体现。
一
《庄子》散文中的“神”,无疑是庄子雄辩的思想与高度智慧的产物,也是“其学无所不窥”的结晶,而且更带有他对世间万物深刻的认识与无限的想象力。所以,庄子在选择与其“神”相游的所有“物象”上,都把与其“神”相一致,并忠实地为其“神”服务放在第一位。
如果说《庄子·逍遥游》的思想“主旨是说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1的话,那么显然庄子所选择和使用的一系列“物象”,都是异常精心的。特别是《逍遥游》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既彼此关联,又有所分别,既集中论述,又独立成章;既有统一的“鲲变”“鹏飞”的大背景,又有精雕细刻“越人断发文身”的小篇幅,既有“水击三千里”的雄伟壮阔,又有“之二虫又何知”的狭小偏执;既有“藐姑射之山”的神仙世界,又有“知孝一官”的现实社会生活,既有“御风而行”的潇洒不羁,又有“爝火不息”的深切著明;既有“树之于无何有之乡”的从容自在,又有“拙于用大”的固执拘泥,既有“无用之用”的大美观念,又有“鹪鹩”一枝、“偃鼠”满腹的哲理思辨。总之,均体现出贴切自然的与“神”相“游”。
以《逍遥游》的第一部分而言,开篇就描绘出一个广大无穷的世界,即大鹏展翅的万里天空;接下又写出“小知不及大知”的根由,引出著名的“小大之辩”;然后再以“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而点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表现出庄子所特有的“神与物游”。第二部分,则先以“让天下”而描写去名、去功,接着再借助“肩吾”来写圣人的精神境界。第三部分,则紧紧围绕庄子与惠施的对话展开,表现出如何才能“用大”以及“无用之用”的意义。三个部分同样都是沿着“神与物游”而进行、发展的,正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在第一部分当中,为了清楚地表达其主旨之“神”,庄子先使用了“鲲鹏”的寓言及“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的明白说理,接着再叙述“蜩与学鸠”的见解认识,又以“汤之问棘”而重申鲲鹏的绝大意义,最后才概括出得道者的突出特点,即“无己”“无功”“无名”,并紧扣于“至人”“神人”“圣人”身上。细检而来,仅在这一部分就出现了数十种的“物象”,如鲲鹏展翅,乘风直上,扶摇高天,万里图南;如《齐谐》所言,尘埃野马,天之苍苍,视下若是;以及坳堂复水,芥之为舟,二虫置辞,小大之辩,八千春秋,彭祖人寿,汤之问棘,荣子犹然,列子御风等等,用来展示和说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必然。在这里,由于“神”的精湛渊深则要求与之相游的“物”亦万千纷纭,蔚为大观,达到“物”与“神”游。
不仅《逍遥游》的开篇里有如此异彩纷呈的表现,整个《逍遥游》及《庄子》散文中相当多的篇章,都是如此这般进行构思的,因而显得气象万千,精彩绝伦。如果没有与“神”强烈而一致的“物”,则难以与其“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无法完美地体现庄子的“神与物游”。
二
《庄子》中所呈现出的“物”都带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小若触蛮之国,大到任公子钓鱼;短若蟪蛄朝菌,长到千年大椿树;怪若畸人美德,美到藐姑山女神;窘若邯郸学步,奇到鲲鹏之变幻;甚至于吕梁蹈水、庖丁解牛、浑沌凿穴、庄子化蝶、洞庭之曲、天籁之音、运斤成风、杀龙妙技等等,都充溢着神奇的色彩,表现出远非寻常的风姿。而所有这些,乃是庄子独特的思想与学说的体现。
本来“鲲”是所谓的“鱼子”(《尔雅·释鱼》),或者是“小鱼之名”,但庄子偏用它来命名“大鱼”,而且还要说“不知其几千里也”,即前所未有的巨大。不仅如此,庄子笔下的“鲲”还能够神奇地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当它横空出世的时候,所谓“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如此贴切“奇幻”之“物”,表现了庄子其“神”的力量。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齐物论》[3]110
“景”即影子,“罔两”即影外之微阴,它与影子的对话,则是继续申说《逍遥游》中的“无待”之议。庄子所谓的“无待”,就是他强调的摈弃一切,使自己的精神能够达到自由飞翔的目的,并像那些“至人”“神人”“圣人”一样地超凡脱俗,卓然独立。当然,庄子知道要达到如此的境态,根本不是普通世俗之人所能够认同与想象的。然唯其如此,或许才能更表现出得道者完美的灵魂与境界,也才能更给予追求者以绝大的精神魅力。因此,庄子选择“影外之微阴与影子的对话”这样一种特殊的“物象”,就是为了把所要表达的“神”忠实而完美地表现出来。
为了使“神”能够同与众不同的“物”游动起来,有时庄子的选择出人意料。例如,他把可供为“师表”的完美孔子,与杀人越货、横行天下的盗贼首领“盗跖”,放到一起描写和比较。在他们逼真的“表演”当中,反映出“物象”的力量,既淋漓酣畅地表现出孔子与盗跖的思想观点、感情色彩与形象特征,又闪烁出异样的光辉。就像里尔克所说的那样,在这里“美”不过是酷似的“物”,“人们可以在那里面认出他们所爱的,他们所畏惧的,和这一切中所有不可思议的。”[4]51
庄子常常通过具有独特的“物”之选择,把本来抽象、模糊的情感与思想,改变成清晰而理性,为人所能够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情感思想,在实现思辨与感性的统一中,达到“神与物游”。
三
在《庄子》散文的构思过程中,非常讲究“虚”与“实”的交叉融合,从而使“神与物游”带有飘忽不定的色彩。这里所谓的“实”,就是庄子通过文字所创造出的艺术“境界”,或者带有生动而具体的“人”与“物象”以及他们自身的意义;而所谓的“虚”则是超乎具体的“境界”与“人”“物象”之表以外的内容,即可以咀嚼、寻味,并且可以沿其思路领会的东西。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逍遥游》[3]28
通过肩吾的叙述,“藐姑山之神”的形象已经非常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她是如此的宁静端庄,不仅集窈窕的身材与美丽的容貌于一身,而且内心还那么纯洁净朗。她典雅高贵,带着永恒的微笑,面部表情又显得那么深刻。她不仅灵秀,婀娜多姿,还韵味深长,带着神秘气息,与飘忽不定的明暗变化,呈现出缥缈而奇异的美。
“藐姑山之神”所具有的美德与飘逸的风致,更是人们应当追求的理想性格。特别是“之人也,之德也”所昭示出的“旁礴万物以为一”与“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世界,该是怎样的一种境界!而这种对“虚”境界的想象与把握,正是通过对“神人”美德及其世界的美好之“实”来实现的。
徐复观先生说,“当庄子从观念上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辩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5]30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养生主》[3]117
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过程及感悟,一方面真实地表现出“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见解认识;另一方面又让文惠君明白“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认识得到启示与升华。这里庖丁的形象,特别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风采神姿,无疑属于“实”的范畴;但由此而
对“道”的深入认识,对“养生”原则的理解与把握,以及由牛的脉络筋骨而比喻出的社会人间的错综复杂、千奇百怪,即“虚”的部分也表现了出来,并且还为之准备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即由“实”而理解“虚”的一种方式。
庄子作为“完美之美”的坚定崇尚者,他相信除去自然“天籁”之外,没有任何一种人为的行为与结果,能够穷尽自然的全部之美。所谓“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正是他对于“虽有繁手,遗声多矣”(郭象注)的感慨。这也就是庄子高扬“大音希声”旗帜的缘由!但是庄子把对“有”与“无”的认识,转化为“虚”与“实”的把握,并且还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构思当中,这倒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当然,庄子笔下的“虚”与“实”,都具有整体的意义,只不过是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而已。
四
《庄子》散文“三言”表现手法的使用,特别是“寓言”使用与编排的方式,也使“神与物游”能够更为恰当地表现出来。《庄子·天下篇》中说庄子试图通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倘,不以畸见之也”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认识,因此,他选择了“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三言”。所以,庄子使用“寓言”“重言”和“卮言”,是为了说明道理而选择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寓言”可以通过采取“藉外论之”的手段,免去“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之罪也,人之罪”的尴尬,使问题的讨论与理念的表达,更为深入与切合实际。通过“寓言”这种表现手法所形成的文字内容,因其言简意赅,以小喻大,语义双关,以形见理,言在此而意在彼,这些是容易成为维系整篇文章,并使之达到“神与物游”的特殊结点。
庄子为了真切地表达其“全生”的思想,在《人间世》中连续使用了“栎社树”与“不材之木”两则几乎相同的寓言,并把它们平列开来,说明“大木”的长寿之道是“无所可用”与“不材之木”。
庄子以为,如果一个人具有某种才能,往往可能因此而招来杀身之祸,“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而当“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往往可以使人脱离危险。所以,一个人要想方设法远离灾难,首先要确保自己的个体生命,才能进而争取达到思想与精神的自由境界。
庄子之所以注重自己强调的“无用之用”,并希望始终能够“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用以保全生命,是因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所以,人的一切都应当自然而然,循其自身的变化而完成自然的生命过程。尤其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一定要尽量避免遭受残暴统治者的屠戮、迫害,以及其他的种种干扰和破坏,免除不该有的痛苦与灾难。
庄子使用这样的两个以上的同类寓言,即所谓平列式的寓言,就是为了说明自己所强调的道理,从而强化自己的思想主张。有时,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庄子甚至在使用“寓言”的同时,还使用平列的“重言”及“卮言”的方式,充分发挥“三言”的作用。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齐物论》[3]79
当“卮言”的使用,让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观点和盘托出之后,为了在以后的部分,能够继续申说这一观点,他便平列出“昔者尧问于舜”“齧缺问乎王倪”“瞿鹊子问乎长梧子”三个“寓言”。
三段平列的“寓言”,通过尧舜的见解,“物之所同”的观点与体道之士的精神境界,进一步深化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认识,从而使“神与物游”实现得更加微妙。
在《徐无鬼》的开头部分,将人的真情实感的可贵之处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当徐无鬼直接大谈狗马时,竟使得“武侯大悦而笑”。如此描写,就是要揭示出“人与人相亲”的道理。及至当黄帝问小童,并得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回答之后,“卮言”便油然而生了。
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淩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教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易于物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
——《徐无鬼》[3]838
三个排比句式,结穴于“皆囿于物者也”;而连续的九个排比句,更是将“囿于物者也”的弊病详细指证出来。“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事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则进一步对照分析,将“不易于物”的症结继续陈述下去,并得出“悲夫”的结论,使“卮言”的论述掀起新的波澜。
《齐物论》中的三个寓言,多为陈述,侧重于叙述中见人物形象;《徐无鬼》这个段落则注重议论,使情感的抒发显得急切,富于气势。
庄子的“寓言”当中,有时候是包含着“重言”与“卮言”;而“重言”与“卮言”当中,也有“寓言”的存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转换,使文章显出变化,也使“神与物游”得到彰显。
五
《庄子》散文特别注意把叙述(包括议论)的文字同抒情的文字结合起来,既表现出整齐划一的宏大叙事,也把抑扬起伏的诗情画意贯穿其中,使“神与物游”显得摇曳生风。
《逍遥游》的开头,叙述了鲲鹏变化、飞腾的奇迹,及至飞到九万里高天的时候,“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则从前边的自然叙述,转入从容的抒情,境界宽广,展示出非凡的意义。就像一首起伏跌宕的交响乐,经过若干的叙述乐句,进入到富于抒情色彩的段落,音域显得更加宽阔,呈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而整个的《逍遥游》就像完整而规模宏大的乐曲,在完成了自己的叙述说理之后,以富于抒情的“无用之大用”结束了文章,并留下启迪人们想象的无限空间。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遥游》[3]40
所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逍遥游》抒情性的结尾,展示出浑茫无限的天地,也体现出了庄子对“大美”的追求。
同《逍遥游》一样,《齐物论》与《秋水》等篇,也是在雄伟与宏大叙事之后,用优美而别致的抒情作为结束:前者是在完成了洋洋大观的“齐”“物论”与“齐物”“论”等论述之后,以揭示“物化”之旨的“庄子化蝶”而展示出新的境界;后者则是通过河伯与海神的“七问七答”,在阐释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之后,以极富观赏性的“濠梁之辩”,描绘出不同的色彩与情怀。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齐物论》[3]112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3]606
此段叙述自然流畅,气势恢宏,使用的语言又显得精致高雅:前一个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更为深入的、神秘的境界,后一个则不拘礼数,把论争变成慎言明辨的交流彼此心得的场合。而雕琢精工的字句,充满奇思幻想的光彩则又是兼而有之。
庄子是“伟大的诗人”,他所创作的“时代的丰碑”——《庄子》散文,给予后世以无穷无尽的影响与滋养。而其创作过程与使用的各种表现手法,更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庄子无与伦比的创作艺术构思,或许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从而成为阅读与研究《庄子》散文的一种方式。
[1]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奥地利)里尔克.罗丹论[M].梁宗岱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