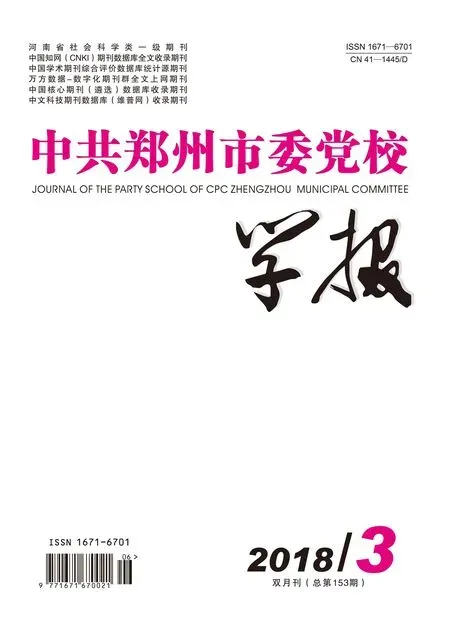佛教信仰的民间异化
——以洛阳禅虚寺为中心的考察
金勇强
(洛阳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传播过程往往伴随着民间信仰的渗透与侵入,并由此改变了传统佛教的信仰形态与信仰空间。在学术界,无论是佛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佛教化,都是中国佛教史与民间信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严耀中认为,佛教“参与民众祠神信仰,不仅可以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利用民间信仰扩大其影响,包括观念上的渗透,从而主导地方民众信仰世界”[1]。贾二强、张国刚、韩森等指出,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杂神淫祠是必须着重应对的一大问题[2][3][4]。曹刚华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5]。程宇昌基于对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考察,发现明清以来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民间信仰的佛教化日趋显著[6]。王文旭通过对民间普遍存在的河神信仰的考察,分析了佛教河神信仰的中国化过程[7]。总的来说,研究者们探讨了汉魏以来,隋唐、宋代、明清等不同时期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并从民间士绅、官僚阶层、世俗民众等方面,对佛教信仰在民间的变迁融合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然而,很少有学者基于微观地域,通过单个寺院的演化,对佛教的民间化过程进行历时态的系统考察。在佛教变迁历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佛教信仰民间异化的过程和影响因子存在着显著差别。洛阳作为汉传佛教传播发端之地,现存古寺院众多,但经过近2000多年的发展,在民间信仰的渗透与侵入下,多数寺院的信仰空间和信仰形态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以始建于北魏时期的洛阳禅虚寺为中心,探讨北魏至今,佛教信仰在当地民间的异化过程、地方佛教信仰历史流变的背景及其与民间信仰融合的内在原因。
一、北魏至宋代的禅虚寺:从皇家寺庙到乡村佛堂的变迁
东汉明帝时,洛阳诞生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自此,佛教信仰开始在中原大地广为传播,而作为都城的洛阳,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昌盛,大批官办或民办的佛教寺院在洛阳涌现,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洛阳佛教更是达到鼎盛。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由于北魏皇室的提倡,奉佛之举,朝野风从,其中皇室造寺47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到了北魏末期,洛阳寺庙已然多达1367所,僧尼200万众,人称洛阳为“佛国”[8]。禅虚寺是北魏佛教极盛时期,由北魏皇室捐建的一座皇家寺庙,其始建时间不可考,位置在汉魏洛阳城北的卫邑金墉城,大夏门御道西,占地数十亩,僧众上百人。禅虚寺并非一般讲经念佛的皇家寺庙,与北魏军方有着密切关系,“其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一习一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不少羽林武士亦信奉佛教,因此禅虚寺有着相当浓郁的武术氛围,这也为后来佛教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时的禅虚寺不仅承担了宗教功能,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娱乐功能,当时的皇家戏场即设于禅虚寺,其寺院僧人不仅工于佛事,亦善百戏。“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9]。这一切都说明禅虚寺并非超然世外的寺院,其与当时的上层世俗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接触。北魏末年,由于边镇起义和统治集团的内讧,洛阳大多寺院或毁于战火,或毁于天灾。尚存的寺院其建筑与规模已大不如前,作为皇家寺院的禅虚寺也大受影响,演武场与戏场亦不复存在。《洛阳伽蓝记》云:“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10]失去了上层世俗政权的支持,禅虚寺也开始走向衰败,而真正导致禅虚寺衰落的乃是洛阳城址的迁移。
汉魏时期,洛阳城北倚邙山,南临洛河,但到了隋唐时期,洛阳城迁至汉魏洛阳城西边的洛河、伊河汇合地带,西移了近30公里。唐朝初年,洛阳县治仍设在金墉城,至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洛阳县治迁到了东都毓德坊,自此以后汉魏洛阳城的卫邑金墉城逐渐废弃[11]。伴随行政中心西移,大量的官僚阶层与市民也随之西迁,这使得金镛城及其附近接受官僚与市民供养的佛教寺院受到了很大影响。如白马寺由东汉洛阳城西,变成唐代洛阳城东后,其离城区最近距离也有10多里,离皇家中心区宫城则有30余里。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唐代,城内的寺院比城郊的寺院有着更为显著的空间优势,它们比城郊的寺院更容易汲取皇城丰富的政治资源,从而壮大自己的寺院。如城内天宫寺,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9月,高宗巡幸该寺,“周历殿宇,感怆久之,度僧二十人”[12],后禅宗北宗神秀又在此出家。城内大福先寺,寺内建筑有1200百间房屋,寺塔高16丈;高僧义净、志辩等人曾在此从事翻译佛经、弘阐律学的活动。而位于城东郊的白马寺,初唐、中唐时均少有修缮,破败不堪,寺内有数十余僧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城内寺院相差甚远。直至武则天末年,白马寺才由薛怀义重修。1977年出土于河南伊川的《张庭珪墓志铭》记载,“薛怀义建伪阁(白马寺),殚万家之产”。白马寺尚且如此,距离洛阳城区更远的禅虚寺更是日趋被边缘化。清乾隆五十三年刻制的“重修金村镇石佛堂碑记”记载了禅虚寺自北魏毁弃之后到唐武后时曾重修禅虚寺的历程,“佛何以石,盖创于北魏之胡后,再钟于唐之武氏……”此后禅虚寺再无重建之记载,北宋之后,禅虚寺外围建筑已经毁弃殆尽,仅余石佛堂[13]。在笔者的访谈中,当地村民称村内有石佛寺,自宋代始有其名,其内石佛原为禅虚寺所有,通高2.45米。宋代之后,石佛一直供奉在金村中街的石佛堂中,成为禅虚寺仅存的佛教信仰之物。
二、明清时代的禅虚寺:龙王庙的建造与民间信仰的渗透
宋代之后,禅虚寺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都已经与北魏时不能同日而语,尽管石佛堂依然保留,但禅虚寺的其他建筑也已经损毁废弃,禅虚寺所在的金墉城变成了洛阳县金村镇,汉魏洛阳故城变成了农田和土丘。在古代中国,农耕是重要的经济活动,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而古人多认为水旱灾害是上天对世人的惩罚,所以,祭祀禳灾在封建时代有着很大市场。但是,古人对于神灵的祭拜并不随意。受祭的神灵既要“术业有专攻”,能够承担起消弭灾祸的重任,又要足够灵验,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在访谈中,村民张某叙述了金村在明弘治年间遭逢大旱祭祀四龙王禳灾的传说:“据长辈们讲,大概明朝弘治时,洛阳大旱,家家户户都是颗粒无收。村里人先是在石佛堂拜了菩萨和佛祖没有用,后来又到洛河边祭拜洛河龙王也没效果,大家都着急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老一辈祖上是山西来的,老辈人说,山西的四龙王求雨特别的灵,但神仙是借不来的,只能偷。于是,村里就找人跑到山西偷四龙王。古时候偷东西是大罪,但偷神仙不算偷,就算知道你偷了,人家也不会说啥。偷来四龙王之后,村里人在村西头搭了一座大台,台上放了个大轿子,将四龙王像放于其中,然后杀猪宰羊,每日祭拜,果然不久就下起雨来。大家伙感四龙王的恩,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建了一座供奉四龙王的庙,把偷来的四龙王像供到里面。为了表心诚,造的龙王殿规模很大,建造的时候还挖出了老洛阳城(汉魏洛阳故城)皇帝金銮殿上使用过的麒麟兽,大家把麒麟兽放到了庙门口,为龙王护法。庙里东西两边还塑了龙王四太子金身,代表风、雷、雨、电。此后每当天旱或涝时,村民就拜四龙王,特别灵。”
金村村民祭祀的主要对象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主司行云布雨。对于龙的崇拜大约始于东汉,“夫五龙之说,始于东汉,记曰:济源县东北二十里枋口山有五龙之祠焉,或遇岁旱,设五方龙象以祈之,故曰五龙。春以甲乙日,夏以丙丁日,季夏以戊己日,秋以庚辛日,冬以壬癸日,各为之塑(句),绘之以方色,俾童子衣方色之衣以舞之,牲用鸡豚,杂以酒醴时物祭之,效古之雩也,往往获其灵应”[14]。这段记述不仅说明了龙王信仰的来源,还明确了龙王之职就是行云布雨。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对于村民来说,只有真正灵验的龙王才值得祭拜,于是灵验的山西四龙王就成了金村村民祭拜的对象。当然,村民在叙述祭祀龙王过程时,对于龙王的神力显然过于夸张,而且年代久远,后人的转述必然也有失实之处,所谓的四龙王行雨只是巧合。然而,这里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金村人祈雨时曾在石佛堂拜过菩萨佛祖,也曾经在洛水边祭祀过洛河龙王,但都没有下雨,而拜四龙王时恰巧下了雨,于是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拜四龙王比拜菩萨什么的更加灵验。也因此,来自山西的四龙王信仰就成为金村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
可见,民间信仰在信仰对象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佛教这种相对固化的信仰在无法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灵活的民间信仰所取代。而且,龙王信仰不仅限于祈雨,“道言:告诸众生,吾所说诸天龙王神呪妙经,皆当三日三夜,烧香诵念,普召天龙,时旱即雨,虽有雷电,终无损害。其龙来降,随意所愿。所求福德长生,男女官职,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怨家及诸官事,无有不吉。如有国土、城邑、村乡,频遭天火烧失者,但家家先书四海龙王名字,安着住宅四角,然后焚香受持,水龙来护”[15]。访谈中张某还告诉笔者:“后来大家家里有啥大灾小灾的也都去龙王庙拜,龙王都是有求必应。去石佛寺(禅虚寺)求的却是少得很,一般家里有谁出个远门会去拜拜,求个平安,平常去的可少。”显而易见,龙王信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祈雨,还扩展到了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村民日常信仰的核心,与之相反,佛教信仰的空间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之后,明清以来一直到民国的几百年间,金村龙王庙虽然历经战火,却又几经重修,香火旺盛。而石佛堂自乾隆之后,再未重修过,民国时期又遭遇大火,显得愈加破败荒废。
龙王庙的兴起与禅虚寺的衰败,反映的不仅仅是信仰的更替,更折射出信仰背后的阶层变化与人口迁移。明清以来,禅虚寺所处的地方由都城退化为村镇,供养阶层由官僚、市民转变为农民,这是导致信仰更替的关键原因。北宋之后,随着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洛阳不再作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其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也荡然无存。原来规模庞大的隋唐洛阳城与汉魏洛阳城,大部分废弃并退化为农田,禅虚寺所在的金墉古城在宋代即已经彻底地乡村化,而农民对相对艰深的佛教理念并无直接兴趣,佛教的吃斋念佛对于农民的祈雨防灾也并没有直接帮助,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就逐渐把信仰中心转移到更加灵活变通的民间信仰上。与佛教教义的系统表述相比,民间信仰的突出特点就是其表述的非系统性与随意性,崇奉对象与祈愿间往往缺乏教义上的内在联系,而这又主要与自身的需求相关,于是诸宗杂糅、诸佛并拜者屡见不鲜。
不过,龙王信仰虽然在民间普遍流行,各地龙王庙的功能格局甚至都大体一致,但因各地区环境差异,其信仰的龙王却有着很大不同,甚至同一个府、同一个县其龙王信仰的供奉对象也是大相径庭。如洛阳偃师草坡村的龙王庙是白龙王庙,信奉的乃是本地水神许三多,因其祈雨必应,乾隆时朝廷封其为白龙王都督[16]。而金村的龙王庙是四龙王庙,人口迁移流动是金村产生四龙王信仰的关键原因。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使洛阳所处的伊洛平原逐渐变得人烟稀少,经济颓废。明初之时,河南府13县总共才74168户,与汉唐极盛时相去甚远。而明洪武年间,官方组织的大槐树移民活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河南的人口空白。曹树基认为整个河南府由山西迁来移民大约7万人[17],而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金村人口有42%的祖籍都是山西。自明初由山西迁入之后,这些人除了带来大量的农耕劳动力之外,也将山西流行的祭拜四龙王的传统带入此地,并使之逐渐演变为当地的主流信仰。
三、当代禅虚寺:旅游业驱动下的寺院重建与信仰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经“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风潮,金村的龙王庙虽得以保存,但也遭受了较大的冲击,寺庙建筑损毁严重。1988年,金村投资300万元,在禅虚寺的旧址四龙沟复建了北魏禅虚寺,并将村中的龙王庙和石佛堂迁入其中。由于该寺地处古代金墉城遗址上,又有村中的龙王殿迁入其内,故又名金龙寺。在重建过程中,基于旅游与社区村民的双重影响,禅虚寺呈现出诸多信仰交错融合的发展趋势。
1.旅游驱动与禅虚寺重建意愿的产生。禅虚寺的重建有着强烈的旅游动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省境内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佛教寺院,如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相继对外开放,逐渐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并获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一些相对偏僻的地区利用寺院发展旅游的动机。禅虚寺所在的洛阳孟津县金村距离著名的佛教祖庭白马寺不足4公里,白马寺镇因白马寺旅游的发展日渐富裕起来,这对于与白马寺相邻但又相对贫穷的金村村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1986年,金村村委会决定通过恢复北魏禅虚寺的原貌来发展旅游,改变金村的落后面貌。禅虚寺在1996年完工之后,1997年就被县、市旅游部门批准正式对外开放。
2.旅游驱动表象下社区主导的寺院重建。尽管禅虚寺的重建来自于旅游业的驱动,以吸引游客为目的,但宗教旅游涉及较多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游客、投资商,也包括本地村民、政府和僧侣。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寺院重建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旅游活动的特点使得游客在传统社区中并不直接参与社区生产活动。因此,对于信仰空间的构建并没有决定作用。第二,禅虚寺是村委会发动村民集资修建的,县市宗教局给予了一定的拨款,一般投资商并未直接参与其中。第三,禅虚寺中的驻寺僧侣是在寺院重建成功后才引入的,对于禅虚寺的规划建设也没有直接参与,因而真正决定禅虚寺重建的是村民和宗教局。由于宗教局主要通过政策和法规对寺院加以引导控制,并不参与寺院的直接经营管理与建筑规划,于是金村的村民便成为了寺院唯一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禅虚寺并没有像多数寺院那样由僧侣主导或者投资商主导,而是社区主导,村民决定了寺院重建的规模、形制和内容。不仅如此,禅虚寺的遗产,金村原有的龙王庙和石佛堂都属于村民共有的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属于村民的共有财产,在金村,任何对龙王庙和石佛堂的改变都需要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问卷调查显示,91%的村民表示参加了禅虚寺的营建,36%的村民参加了规划讨论。
3.佛教寺院外壳下多元信仰的杂糅。作为禅虚寺重建的主导者,村民希望禅虚寺不要建设成为类似白马寺那种单纯观光性的佛教寺庙,应该满足社区自身的信仰需求。民众对各种神灵的信仰都有着功利化的动机,他们往往以最实际的功利要求为尺度来调节人神关系,其神灵崇拜与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要求和利益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新事物的涌入导致农民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也使得传统的龙王信仰遭到了很大的削弱。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求子治病,挣钱、盖房、教育等也都成为农民追求的主要目标。村民希望这些诉求都能够在重建后的禅虚寺中得以体现。所以,重建的禅虚寺与北魏的皇家寺院以及明清时期的龙王庙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汉传佛寺中,其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往北,一般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天王殿前的东西有钟楼、鼓楼对峙,大雄宝殿前的左右是伽蓝堂和祖师殿相对,法堂前左右为斋堂和禅堂。但重建后的禅虚寺放弃了汉传佛教的传统规制,改设佛祖殿、观音殿、千佛坊、石佛殿,又迁入了龙王庙,除此之外,禅虚寺又相继增设了玉皇阁、云台阁、包公祠、三教堂(堂中有佛教、道教、儒教祖师的塑像)、九天玄女庙,而在寺内两侧的窑洞内还塑有都洛十三朝代的帝王像以及历史名人张衡、蔡伦、孙思邈、李白、杜甫、白居易、狄仁杰等塑像。由此可见,在村民主导下,禅虚寺不仅具备佛教信仰的空间,更杂糅了包括龙王信仰在内诸多民间信仰的成分。
4.驻寺僧侣的介入。尽管是出于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但禅虚寺建成初期客流量并不乐观。村民认为,禅虚寺既缺乏足够吸引力的体验活动,也没有驻寺僧侣进行管理,极大地影响了寺院的发展。2001年,经过洛阳市宗教局的批准,一些来自白马寺的僧人开始进驻禅虚寺,禅虚寺的佛教信仰开始渐趋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入住禅虚寺的僧侣不仅主掌佛堂,亦主事如龙王庙、包公祠这些民间信仰的祠堂。这样一来,僧人不仅成为佛教的守护者,更是民间信仰的守护者,其宗教角色日趋混杂模糊。僧人入主世俗祠庙,其实在明清以来已经普遍存在。佛制规定,僧人为了住持正法、教化众生、应住寺院、精舍,但有时为了个人精进修持,个别也可住在林下岩间。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宋代以来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僧人在政策驱动和民众影响下,以积极入世的姿态介入各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如住持政府开办的庵驿、养济院、安乐庐、漏泽园等。另一方面,也与寺院经济的崩溃有关,明代佛教寺院大规模合并,不少僧人流离失所,有一些便进入了民间庙宇。由于禅虚寺不同信仰的杂糅,使得这里主事祠堂的僧人,要面临各种不同民间信仰的冲击与影响,也使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融合更为突出。在佛教节日的庆祝上,这种情形表现得更为显著。作为佛教寺院,禅虚寺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要举办释迦牟尼佛出家日、二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圣诞日、四月初八举办浴佛节、六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出家日、十二月初八举办释迦牟尼佛成道日等,伴随着这些佛寺重大节日的还有盛大的庙会。每到这个时候,去禅虚寺的人不仅有很多求佛拜佛的,而且还有很多拜祭包公祠、玉皇阁、九天玄女的。他们到佛寺只是为了求得一些世俗的利益,如平安、发财、排忧解难、心想事成等,佛教节日跟民间信仰的节日在这里彻底融合为一。
总之,由于佛教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容易招徕游客,引起外来人的兴趣,但民间信仰在本地村民中更有市场,深深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由此,佛教与民间信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了互动,呈现出了新的交融,如佛教信仰宣传的方式趋近于民间信仰并对民间信仰活动实现了广泛的容纳和参与。为了进一步发展禅虚寺的旅游业,2015年,金村引入了战略投资商对禅虚寺景区进行了新一轮的开发,规划有梅园、十方莲池和土地宫等,并计划复建北魏永宁寺塔。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将对禅虚寺产生更深刻的影响,佛教与其他信仰的融合也将更加显著。
[1]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7.
[2]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9.
[3]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98.
[4][美]韩森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6.
[5]曹刚华.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J].世界宗教研究,2011,(4).
[6]程宇昌.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J].江西社会科学,2015,(10).
[7]王文旭.佛教河神信仰及其中国化[J].青海社会科学,2014,(2).
[8][9][10][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校释[M].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2,179,180.
[11][1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2,82.
[13]桑永夫编.洛阳明清碑志(孟津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100.
[14]陈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5.
[15]张继禹.中华道藏(第6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8.
[16]乔竹坡.偃师县风土志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34.
[17]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明时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