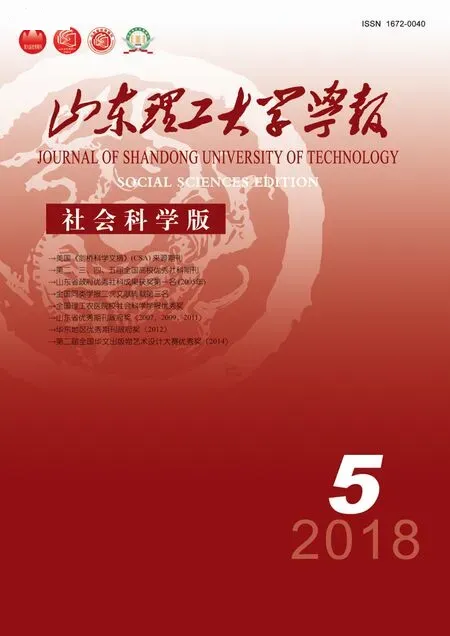消费文化语境下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研究
陈 维 超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表情包是指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图片与文字嫁接后进行重新赋意的一种视觉传播形态。网络表情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经历了从颜文字、绘文字到表情包的流变。由于互联网技术和视像技术下的世界呈现为符号化形态,符号以代码的形式无限扩张,因而当下表情包在内核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表情包在各种语言文字和图像随意错乱拼接、相互碰撞、吞噬和嫁接中被生产和传播出来,过去符号强调的完整叙事在互文链接下被割裂,形式上的新颖和“刻奇”(Kitsch)才是最重要的。根据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符号内爆下的意义错乱成为一种症候,网络符号使用者被慢慢浸染,直到对符号意义的错误无意识、被动适应直至享受其中[1]103-104。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表情包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形态,因此本文将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的着力点聚焦在青年群体。消费主义语境下,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深层次渗透,青年群体越来越通过消费和市场层面发现他们的身份和价值,因为消费这种手段最直观、最快捷[2]29。表情包作为一种视觉内容,其图像与文字的随意拼接建构了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形态,成为青年网络集体狂欢的交流符号。借助表情包进行品牌营销,是社会化媒体时代极具创意的、契合青年感性趣味、引发青年共情的一种新型营销方式。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不仅可以使广告创意呈现出张力和生命力,还可以快速增强品牌曝光度,实现品牌理念与消费者的互动,最终带动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一、消费文化语境下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的内在机理
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形态,表情包的生产和传播背后潜藏着某种青年群体的文化取向。技术-社会交互影响下,当下传播格局表现出情感传播的机构转向,表情包内核的抵抗、消解、压抑、狂欢特质契合了当下的情感传播模式。表情包使用者通过制作、转发表情包形成了在网络空间中相互指认的共同体,其中,“想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趣缘”结成的表情包文化共同体,充当了个人与社会的连接媒介,是青年群体消解焦虑和找寻情感归属的主要路径。与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基于“想象”的表情包“斗图”景观,形成了一种成员互动的第二媒介景观[注]第二媒介景观即观点与观点构建出一个区隔于综艺内容本身的新的社交场景。参见毕啸南:《直播综艺节目的冷思考》, 《中国电视》,2017年第8期,58页.,强化了同在感和共同感,使得狂欢表现出极化的表征形态。“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3]18。
(一)消费文化语境下消费者的情感消费转向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再造和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方式,“引发了一场正由互联网亚文化所承担的日常生活革命”[4]429,在多元化、媒介化、消费化、碎片化的网络文化风格下,经典美学所推崇的理性思辨和意义生成转向世俗化的感官愉悦、快感体验的审美理念,审美越来越带有世俗化的表征,人们的审美趋向表现出非中心、经典解构、感官体验等特性。其中,情感需求成为当下青年群体最主要的意义取向和关切,青年关注的是“是否与我有关、是否能满足我的情感需求”,意义本身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根据企鹅智酷持续四年的数据统计,当下“95后”群体为未来消费主力,具有“偏爱直播、短视频,内容消费更加碎片化和视觉化”的典型特质[5]23-30。在此背景下,以“去中心化、解构权威、戏谑拼接”为特征的表情包成为当下青年群体进行情感宣泄和集体狂欢的重要文化形态。针对当前传媒场域表现出的注重情感体验、娱乐化、意义虚无等特征,喻国明教授甚至认为当下的传媒领域正从传统的信息范式转向斯蒂芬森的游戏范式[注]斯蒂芬森的游戏范式指的是从人类心理机制的角度来讨论游戏与传播的关系,注重传播活动本身带来的快乐,而非信息传播范式的传播效果。[6]16-22,感性审美、沉浸体验成为至关重要的主宰逻辑。
(二)青年群体从情感消费中获取身份表征
从符号学视角来看,任何表意行为均离不开符号的参与,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7]1-8。表情包作为一种符号,青年群体对其消费的背后彰显的是身份区隔与认同。青年人的自我身份和群体身份都有被认同的强烈需要。消费社会语境下,消费过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让渡给象征价值。通过使用特定的表情包符号,青年群体得以建构自身的自我认同。
此外,人类具有类本质和凝聚的本能需求。根据社群认同理论,青年群体基于表情包符号会形成一个“脱域”的网络趣缘社群,通过制作、传播表情包,青年群体实现了一次连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网络狂欢,并最终实现了短暂性的自我身份的构建,“共同体营构的集体围观的仪式感,赋予了个体自我身份的进一步认同”[8]88。值得注意的是,成员为了强化社群认同,往往会建构一个能够区隔的“他者”社群。如“中老年表情包的图案形式方正、整齐划一,字体偏大、色彩艳丽夸张(大红大绿),内容多为风景静物或是玫瑰花、婴孩、举杯等营造幸福美好、喜庆热闹之感的表情包图片”[9]97。 相形之下,青年群体使用的表情包则极尽丑化人物形象之能事,越是粗糙的图像符号越能够得到追捧。表情包符号使用的对立分化,彰显青年群体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对中老年表情包使用群体的身份区隔。
(三)表情包营销契合当下青年群体的符号狂欢诉求
表情包文化与当下的社会文化休戚与共并深受其影响,特别是以“非中心性”“反思”“解构”“多元”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表情包深层的符号内核与后现代文化表现出高度契合。视觉文化转向背景下,视觉符号的泛滥使得符号取代现实,即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符号世界,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本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景观体系中,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10]38-40。新兴媒介技术为青年群体的情感宣泄提供了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平台,青年群体借由媒介影像符号完成自己的感官刺激、情感狂欢和游戏消遣偏好。
在这个符号不断建构“真实”的过程中,符号“内爆”成为网络流动空间的内在逻辑,表情包的内爆主要指的是意义的消失与游移,纵观当下传播火热的表情包,无不表现出与主流审美价值相对立的审丑趋向,“简单粗暴”的修图加上极具视觉冲击性的粗号字体,营造出刻奇化的媚俗效果。鲍德里亚认为,“媒介自身形成了‘内爆链’,媒介的符号脱离了所指涉的现实世界,为媒介的自主逻辑所操纵,符号的意义在能指链条的滑动中被消耗和分解”[11]31。因此,意义在审美与审丑之间游移,“经验、意义、价值、权力关系脱离了物理的时空束缚,成为人在媒介世界中定义自我的尺度”[12]48。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品牌借表情包营销的优势
根据创意传播营销的过程,段淳林将创意传播营销的核心内涵归为三个方面:接触创意点、沟通创意点、核心创意点[注]参见段淳林、林伟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品牌传播创意研究》,《编辑学刊》,2014年第1期,102页。。从营销角度来看,表情包是一种传播品牌价值的内容符号,表情包营销是一种内容营销。作为青年群体产制的表情包文化,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具有重要的传播优势:受众基于趣缘集聚的网络小世界,有助于实现品牌的精准营销;利用表情包的社群间传播属性,可以解决受众圈层分布造成信息整合和品牌接触困难等问题;最后,表情包契合消费者的情感消费特征,有助于传达品牌价值。
(一)接触创意点:表情包有助于扩大品牌接触点
接触创意点是传播创意的第一环节,纵向在于传播的精准性;横向在于驱动消费者的兴趣。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内容营销目的并不仅在于扩大传播范围,更重要的是增加传播的深度,如培养品牌意识、提高顾客品牌忠诚度等[13]68。
首先,表情包营销是一种精准营销。表情包是一种小众文化,其消费群体天然就是某一类细分群体,品牌商可以根据亚文化群体特性进行精准营销,如在阿里建立的“OneData”数据体系中,根据用户行为和内容偏好打上了诸如“日剧爱好者”“来自星星的你忠实粉丝”“文艺青年”等标签。同样地,表情包也成为不同群体的符号标签,表情包的使用类型彰显着使用者不同的性格、年龄和社会阶层,如追星群内的“明星”表情包;热衷于动漫群体的 “二次元”表情包;集结60后、70后等中老年一辈群体的“中老年”表情包等[14]11。此外,内容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其背后蕴藏着消费者的情感、调性、兴趣和价值观等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深入洞察消费者的心理活动和消费需求。
其次,视觉文化转向下,表情包已成为网民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借助表情包的创意传播,有助于扩大品牌创意的接触点。读图、视像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身处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表情包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形态,通过图像与文化的随意拼接营造的狂欢体验,有助于将品牌创意进行最大范围的传播。有学者认为视觉文化容易成为“一种特殊的交往,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广场式交往”[15]242。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约90%的大学生使用微信商店的表情,超过95%的被调查者使用微信收藏表情功能,可以初步推断,表情包使用行为在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微信交流中非常普遍[16]128。
(二)沟通创意点:“圈层”传播下的口碑营销
沟通创意点的目的在于沟通和分享,是接触创意点和核心创意点的连接桥梁,通过对热点话题、消费者兴趣的整合,最终将消费者引向品牌核心价值。传统营销是一种基于人口特征属性进行人群细分的方法,社会化媒体时代,消费者小众化及圈层化趋势明显,传统营销已经很难精准识别和触达目标消费者。IP热背景下,优质内容资源成为集聚用户进而实现流量价值变现的重要切入点和价值要素。
表情包营销可以建构一种基于“强关系”连接的口碑营销。互联网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兴趣爱好相近的群体分类聚化成少数人的群体,在这种群体中,成员通过一套只有群体内部才懂、约定俗成的符号代码进行交流,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关系连接”。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弱连接传递信息,强连接引发行为”[17]1361。社群成员的“强关系”连接成为口碑营销的内在逻辑,成员之间通过互动形成对品牌价值理念的理性认知,一旦品牌形象遭遇危机,成员会自觉维护品牌形象。只要运用得当,表情包营销能够强化品牌核心价值的传达。
此外,社群推动成员形成自我网络,并对社群其他成员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网络社会中,成员间的行为和情绪能够相互“感染”。当下,社交已成为当前媒介领域商业变现模式的内在逻辑。正如胡泳所言:“互联网环境下,超强的传播效应和社群本身超低的边际成本使得社群的拓展具备更大的经济价值。”[18]13
(三)核心创意点:通过诉求青年情感价值完成品牌核心价值构建
品牌借势表情包营销可以通过诉诸受众情感体验实现品牌核心价值的构建。我国著名学者段淳林指出,“源于产品功能和属性的传播创意只能与消费者建立利益关系,只有基于品牌核心价值的价值关系才能实现品牌忠诚”[19]101。核心价值的构建在于引起消费者的价值认同,随着情感消费成为受众的主导消费趋向,从情感切入是引发当下青年群体价值认同的重要取径。“从用户的情感需求结构和情绪依赖入手,通过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共鸣已经成为内容生产的标尺”[20]41。
技术—社会交互影响下,受众的消费行为开始向感性消费、个性化、碎片化等转变。“非使用价值正在成为品牌价值的核心构成要素,趣味感性的、软性植入的、能够激发消费者共情的优质内容,正逐渐成为营销行业追捧的新模式”[21]43。因此,借助表情包这种备受青年群体喜爱的交流符号进行营销,能够强化营销的趣味和感性特质,降解传统硬广的商业属性,让消费者在创意传播与感性趣味的内容享受中接受品牌的营销信息。由于充满了幽默、反讽、自嘲的元素,表情包成为一种游戏式、集体狂欢的话语结构,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契合了青年群体个性化、迭代更新的文化需求。
对于表情包使用者而言,品牌借助表情包进行创意传播和营销,易于让表情包使用者对品牌产生一种“自己人”的延伸性认同。“消费社会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消费行为进行社会关系建构的时候,并非关注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号意义”[22]85。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表情包营销的问题与优化空间
表情包虽然在品牌传播与营销上有着诸多优势,然后,作为一种由青年群体生产传播的亚文化形态,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表情包营销过程中存在图像能指模糊不利于品牌价值传达;表情包生命周期短,使得营销缺乏连贯性与体系性;表情包传播盖过营销活动本身,造成营销上的失焦等问题。对此,选择契合品牌理念的表情包进行传播、树立“先传播后营销”的理念对于最大化营销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一)针对表情包能指模糊缺陷,选取契合品牌理念的表情包进行传播
消费社会语境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往往不是为了其使用价值,而且商品背后所表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如购买iphone手机的用户,看中的是手机背后蕴藏的青春时尚、个性魅力等象征价值。同样地,用户对表情包的传播和接受行为,实质是一种对表情包背后价值的选择行为。鲍德里亚甚至指出,“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23]21。
从传播感染力上来看,通常越使用丑化图像、粗号字体、表情夸张等极具视觉冲击性的元素和戏谑内核的表情包,越能够得到追捧。表情包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本质是通过对日常和严肃性语境的消解获取精神狂欢。选取和品牌本身并不贴合的表情包内容,这样虽然赢得了曝光率,但却可能应该因此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品牌在进行营销时,应该选择与品牌资产和底蕴相契合的表情包进行营销。
(二)针对表情包生命周期短问题,打造自带长效营销优势的IP表情包
表情包一般由“文字+表情”构成,导致品牌信息或者是植入在视觉内容点上,或是植入在文字内容点上,品牌的植入方式单一给表情包营销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此外,表情包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更新频繁、生命周期短,致使表情包营销呈现出精神内核不够聚焦、缺乏连贯性和体系性等诸多弊端。
表情包传播度就等于品牌传播度,如果传播度总量很弱,就代表品牌的传播也会很弱。我国很多品牌的表情包多是在品牌内部使用,沦为自嗨符号,无法成为爆款表情包。因而,不论是自制表情包还是借势营销的表情包,都必须首先考虑传播力和感染力的问题。对此,可以借助自带长效营销优势的IP 表情包,IP这个概念背后逻辑起点即是将用户的情感纳入创作与生产活动。以社交平台LINE的表情包开发模式为例,通过广泛吸纳自媒体等社会化创作主体进行表情包创作(UGC),LINE对表情包质量把关(PGC),使得表情包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此外,由于受众共通空间的差异,网络表情符号带来的认知障碍和认知偏差不可避免。一方面,微信用户用网络表情符号表达时,有着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人群对于网络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认知也会不同,对同一种网络表情符号,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解读。这种解读很有可能和表情符号的使用者的本意大相径庭。这些都是在进行品牌营销时所需要避免的。
四、结语
表情包图像、文字与语境的随意错乱配置契合青年群体的情感消费趋向,因而成为一种备受青年群体青睐的图像符号。品牌通过借势表情包超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有助于扩大营销品牌理念的接触面。其次,表情包作为一种亚文化集聚社群,在亚文化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圈层团体,这有助于品牌营销借助表情包实现基于“强连接”的精准营销,促使消费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通过“人”背后所归属的多元社群实现基于“弱连接”关系的泛社群传播,最大化品牌信息的传播。此外,借助青年群体喜爱的文化形式进行营销,有助于在感性趣味诉求下激发青年群体“共情”,促成青年群体对品牌价值的“延伸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