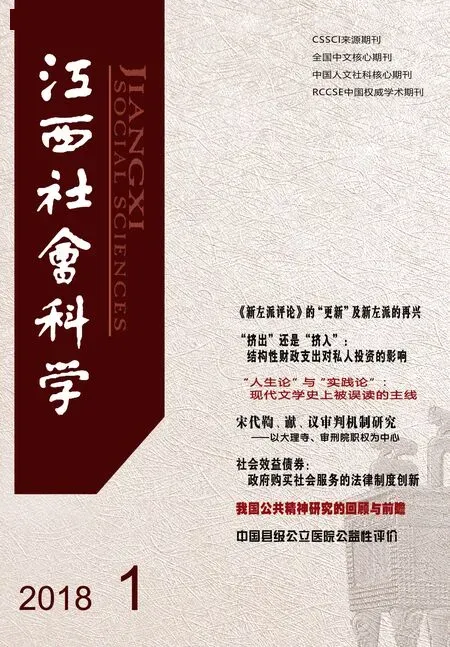18世纪欧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解读
——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在近代学术研究中,王安石及其变法是一个极具牵动力的核心议题,严复说:“以余观之,吾国史书之中,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商君、王莽之所当,其致力之难,得效之不期,不如是之甚矣。”[1](P1150)经过长期的积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在中外学界都已取得丰硕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适时的总结和反思,是推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迄今为止,国内学界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已建构起比较完备的学术史,但国外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的成果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18世纪上半叶,法国神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了四卷本巨著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以下简称《全志》),把王安石及其变法介绍给欧洲学界,奠定了此后近两个世纪内欧洲学者论述这一问题的基调。本文拟就杜赫德《全志》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记述进行讨论,进而尝试在18世纪欧洲的知识语境中,探究欧洲早期汉学对中国古代史的解读方式。
一、杜赫德与《中华帝国全志》
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在中国和欧洲同时进行着两种思想运动:在中国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碰撞,在欧洲是对有关中国信息的吸收[2](导言,P2-4),而于其间充当媒介的便是来华耶稣会士。从罗明坚(Michel Ruggier)、利玛窦(Matteo Ricci)开始,耶稣会传教士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他们收集有关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加以诠释,以书信、报道、著作等形式传回欧洲。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他们的参与和引导下,欧洲不断完善着有关中国的知识。
在由耶稣会士启发和帮助产生的众多中国研究著作中,杜赫德编纂的《全志》是一部扛鼎之作,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er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和《中国杂纂》(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c.des Chinois)一起被视为欧洲早期汉学三大名著。《全志》收录了百余年间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告、信札,综合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成为18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甫一问世便轰动了欧洲,短短数年就有三个法文版本和两个英文版本发行。①
《全志》第一次系统地向欧洲展示了宋代中国的面貌,其记述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宋代历史的概述。《全志》第一卷“中华帝国君主史纲”的“宋代”部分,列举了自宋太祖至宋帝昺的十八位皇帝,并对每位皇帝在位期间的主要言行、事件予以描述。二是分门别类收录了为数众多的宋人文章、奏疏的译文。这些译文系从明代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稗编》和清代徐乾学等编的《古文渊鉴》等书中选译[3](P187-261),被杜赫德视为支撑其对宋代中国文明诠释的证据。杜赫德在《全志》序言中写道,几位入华耶稣会士“出于好意,精心翻译了一些中国文人的著作,本书收录了这些译文,它们将会为我所陈述的事实作证”[4](TheAuthor’sPreface,Pⅲ)。这些译文的存在,使《全志》成为当时欧洲范围内收录中国文献最丰富的文集,“在18世纪初叶,人们尚丝毫不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唯有由杜赫德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提供的那些非常简短而又含糊的摘译文”[5](P159)②。
二、“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杜赫德笔下王安石的角色
杜赫德对王安石的讨论是在宗教辩论的背景下展开的。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一直尝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基督教教义吻合或相近的因素,当利玛窦在儒家经典中发现“上帝”“敬天”等说法时,就把“上帝”和“天”与基督教的“天主”等同起来,“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6](P100-101)此后,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崇拜过唯一的神,即“天”或“上帝”,这种信仰就是原始的基督教信仰。③
但耶稣会士仍需面对一个挑战,即在中国盛行的“新儒学”所具有的无神论性质,他们的策略就是把古儒与新儒学区别开来,宣称无神论是后起的理论。杜赫德在《全志》中指出,新儒学形成于“偶像崇拜(指佛教)传入中国一千余年后的宋朝”[4](Vol.1,P657),宋神宗时期,“一个新的哲学学派开始活跃,他们着手重新解释经典,其代表人物是周敦颐(Chew)、程颐(Ching)、张载(Chang)、邵雍(Shau)”[4](Vol.1,P209)。
杜赫德批评新儒学是对古代儒学的污染,但对这种“疯狂的学说”(mad notions)[4](Vol.1,P659)兴起的过程,尚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杜赫德并没有将之归咎于二程、朱熹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朱子学说在康熙朝被确立为国家正统,对他们的批判显然会不利于在中国的传教,王安石便取而代之,被当作无神论的始作俑者:
神宗统治期间,一个新的哲学学派开始活跃,他们着手重新解释经典,其代表人物是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他们生前和殁后,神宗加封荣誉官职,使他们显贵。他们之后,新哲学学派的成员之一王安石(Van-ngan-she)开始提出无神论(Atheism)。他看到皇帝面对干旱非常悲伤,努力通过禁食和祈祷缓和上天的愤怒,于是说:“您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为什么如此畏惧上天(Heaven)?陛下,要知道所有事情都是偶然的,您的努力是徒劳的。”卓越的“阁老”(Ko-lau)富弼(Fu-pye)对这些话忍无可忍,愤怒地说:“你怎么敢传播这种学说(doctrine)?如果皇帝失去对天的敬畏,还有什么罪恶他做不出来?”[4](Vol.1,P209-210)
《全志》的这段叙述改编自《历史大方纲鉴补》(以下简称《纲鉴补》)如下记载: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撤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7](卷三十《宋纪·神宗皇帝》,第68册,P132)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8](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P10550),所谓的“三不足”说一直被认为是王安石变法的口号,《纲鉴补》和《全志》引述的,正是其中“天变不足畏”的内容。但问题在于,“三不足”说很可能并非王安石自己提出,而是反对变法派对王安石观点的转述和总结,其中难免有断章取义的成分④。“天变不足畏”的说法,便与王安石一贯的主张不相符合。王安石在《洪范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天人观: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征”之意也。[9](卷六十五《洪范传》,P695)
据上可知,王安石并不否定天变,也不认为天变与人事无关,他只是反对将天变与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他曾对宋神宗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10](卷五十九《王安石事迹上》,熙宁三年三月己未条,P495)在他看来,畏天变并不表现在因特定的灾异而生畏惧,而在于持之以恒地修德修政。王安石的天人观是以“以天变为己惧”为前提的,并以统治者的“内圣”之学为基础,而反对变法者的转述则割裂了这个前提和基础,推导出“天变不足畏”的口号,这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⑤
王安石及其反对者围绕着天变的论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灾异论原本是约束人君的工具,当王安石的政治理论从各个角度挑战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站到了祖宗法度的对立面时,所谓的 “天变”就成为朝中大臣攻击新法的旗号和武器。《全志》提及的旱灾发生于熙宁二年(1069),苏轼撰《富郑公神道碑》记道:
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诤之臣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11](卷八《策》,P534)
富弼的意图是借助灾异论的约束力和“天”的外在权威,强调天变与变法之间的联系,阻止新法的推行;而王安石意在宽慰神宗,天变与人事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灾荒变异与政事德行之间存在着偶然性,由此否定当时出现的灾民与变法有关。二人的言论都是因应当时的政治局势而发,其中蕴含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并不是围绕“天变”问题的纯粹的学理性讨论。但杜赫德显然对变法引发的政治纷争并不感兴趣,他的目的不是揭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特质,而是为耶稣会士提供支持,因此,他将二人论战的政治背景虚化,将二人有关天变的言论孤立出来并推向前台,已经歪曲了王安石本意的“天变不足畏”的政治口号,在杜赫德的重新诠释下,又成为否定“天主”存在的无神论宣言。这样,《全志》虽然转述了事件的梗概轮廓,但却完全改变了其内涵,事件被解读为宋人围绕无神论而展开的宗教争论,王安石成为“新注释家”的代表,是无神论的始作俑者,富弼则作为能够理解“上帝”和“天”的含义的“真正的学者”,抵制王安石的“无神论”,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消弭殆尽。
三、“新注释家”与“真正的学者”的对立:杜赫德对新、旧党争的借用
杜赫德将新儒学兴起以后的文人分为“新注释家”和“真正的学者”两类,进而提出了一种理论:尽管无神论的兴起玷污了中国人的原始信仰,但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种抑制力量,“真正的学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疯狂的学说”。北宋中后期围绕新法而兴起的变法派与反对变法派之间的论战,为杜赫德的理论提供了思想凭籍。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引发了贯穿北宋后四朝的“朋党之争”,对立的双方互相倾轧,君子、小人之辩成为双方论战的武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派占据了道德的高地,王安石及其新党则被视为“奸党”。熙宁九年,富弼上书攻击新法云:“缘误用一二奸人,则展转援致,连茹而进,分布中外,大为朝廷之害,卒难救整。”[12](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P6757)降至南宋,统治者更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指责王安石任用奸人,变乱祖宗法度,最终招致“靖康之祸”。这种看法主导了宋朝以后的历史书写,明清时期的士人学者大多对王安石及其新法予以全盘否定。大儒王夫之便称,“苛政”虽病国虐民,但尚未足以亡国,而王安石任用宵小,“群小乃起而应之”,“于是汎滥波腾,以导谀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类一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衅乃倏生,败亡沓至而不可御”。“其亡也,则惟通国之皆小人。通国之皆小人,通国之无君子,而亡必矣。”“然则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无人者,无大臣也。”[13](卷六《神宗》,P129-131)
《全志》有关宋代历史的叙述系据明代袁黄的《历史大方纲鉴补》编纂,这部书在内容上由几部著作拼凑而成,周代以前“合编、纪而采其粹”,改编自金履祥《通鉴前编》和刘恕《通鉴外纪》;宋元以后“参商、陈而纂其全”,参考了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和陈桱《通鉴续编》。[7](第67册,P100)在编纂思想上,则秉持自朱熹《通鉴纲目》以后以褒贬义理为要的主张⑥,承袭元祐诸臣和南宋以降的主导性史观,“述而不作”[7](第67册,P103),对王安石及其新法极尽贬斥。
杜赫德对中文史料中蕴含的史观并没有自觉的警惕,也不可能如当今的历史学家一样,对史料持一种谨慎的怀疑、批判态度,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确凿无疑的“知识”,从中寻找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这就使《历史大方纲鉴补》中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得以渗透到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中,《全志》对王安石新法和以反对新法为旨归的“元祐更化”的评价即证明了这一点。杜赫德写道:“宋哲宗即位时只有十岁,由祖母高太后听政。高太后在位八年间深谋远虑、处事审慎,临去世前,她命令‘阁老’驱逐朝中无用大臣,因为他们只会带坏年轻的皇帝。”[4](Vol.1,P210)南宋以降至明清的史书中,元祐诸贤和元祐更化几乎得到一致褒扬,《全志》显然受到了影响,高太后“深谋远虑、处事审慎”,参与变法的“无用大臣”则“只能带坏年轻的皇帝”。力图恢复新法的宋哲宗也未能逃脱谴责,被勾绘成一个道德低下的形象,“当他以遵循祖宗故事为借口废后时,大臣回答他说:‘你应该学习祖宗的美德,而非他们的错误。’哲宗被这一回答激怒,将奏章扔在地上践踏,并免除了这位官员的职务”[4](Vol.1,P210)。
杜赫德将北宋时期新、旧两党之争重新诠释,移植到“新注释家”与“真正的学者”对立的理论框架内:王安石作为“新注释家”的代表,倡导并传播着无神论;以司马光为首的“真正的学者”,则极力抵制着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还努力引入其他‘新说’(novelties),但声誉卓著、备受尊敬的司马光强烈反对这位鲁莽、狡猾的天才(rash and subtile genius)的所有举措。”[4](Vol.1,P210)
借用中文史料中君子、小人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判断,《全志》为欧洲学者勾勒出强烈的形象对比。司马光于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时期大放异彩,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4](Vol.1,P209)《全志》收录了司马光的三篇奏章,分别是《论治身先孝治国先公疏》《上英宗言时政阙失疏》和《乞改求谏诏书札子》。前两篇上书给英宗,针对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进行劝诫,“谈论孝道和公正”[4](Vol.1,P543);后一篇系元丰八年(1085)上书给哲宗,为废除新法要求广开言路[4](Vol.1,P548)。三篇文章一起,呈现出一个道德高尚、公正忠直的大臣形象。译文之后,杜赫德又引用《古文渊鉴》的介绍称赞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历相四朝,忠直如一。”[14](卷四四,P922)
相比之下,王安石则被认为是鲁莽、虚伪和诡诈的。《全志》虽然收录了王安石的两篇文章[4](Vol.1,P558-559),但从篇章安排顺序来看,却对之采取了孤立和谴责的态度[3](P283),两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就是苏洵的《辨奸论》,随后连续收录郑侠《论新法进流民图》以及苏轼的一系列文章,对王安石及其新法进行批驳。苏洵《辨奸论》是一篇著名的批评王安石的文章⑦,文中指责王安石“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认为王安石行事不近人情、欺世盗名,如果得到重用,必然会为天下大患。[14](卷四十七《辨奸》,P1031-1032)《全志》全文收录了这篇文章的译文,并将题目改为“王安石肖像”(A Picture of Wang Ngan She)[4](Vol.1,P559)。杜赫德介绍这篇文章的背景说:“思想堕落的王安石在朝中得到晋升,即将官至宰相,苏洵描述了王安石的形象,将文章直接呈递给张安道,提醒他王安石不应再被擢用,更不应被任命为宰相。”[4](Vol.1,P559)在译文之后,他又评论道:“在《古文渊鉴》中,还有很多对王安石倡导的祸国殃民(ruin the people)的‘新法’(Regultion)的抗议,新法至今仍被诅咒,因此苏洵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4](Vol.1,P560)杜赫德显然赞同苏洵对王安石的评价,借由这篇文章,苏洵对王安石的批评被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欧洲读者,建构起王安石虚伪阴险的邪恶形象。
熙宁七年春,旱灾严重,神宗下诏许吏民直言得失,郑侠绘《流民图》以进,对新法提出强烈批评。郑侠将当时的旱灾以及由此引发的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乃至蛮夷轻肆都归咎于“中外之臣辅相陛下不以道”,指责在位大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视生民之死而不恤”[14](卷四十八《论新法进流民图》,P1058-1059),将矛头直指王安石。宋神宗受到郑侠《流民图》及奏疏的触动,一度暂停了新法的实施,所以郑侠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评价:“宋自开国以来,大臣上书言事,未有如郑侠能尽其忠也”,“可谓一言能正君臣之失而有回天之力矣”。[14](卷四十八《论新法进流民图》,P1059)通过这篇译文中对灾情的描述[4](Vol.1,P561-563),杜赫德试图证明《全志》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批评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在郑侠奏疏后,杜赫德写道:“在这部文集(指《古文渊鉴》)中,郑侠文后是一篇由苏轼撰写的同样上奏给宋神宗的奏章,其内容比郑文更全面。”[4](Vol.1,P563)《全志》收录了多篇由苏轼撰写的策论[4](Vol.1,P567-573),杜赫德把这些策论视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抵制,将其内容总结为三点:
首先,苏轼证明皇帝可以没有权势,但要取得臣民的爱戴,他劝皇帝尽力争取民心。所有这些都与郑侠所言一样,系针对王安石创立的新税种(new imposts)和“新法”(new regulations)而言。
其次,苏轼劝神宗在国内培育良好的道德规范,提升美德,他认为皇帝的权力和皇位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而非财富。苏轼以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的一个办法是罢黜那些虽有才能但道德低下的官员。这同样是针对王安石及其同党的。
第三,维持法制。苏轼谈及台谏的效用(usefulness of remonstrance),感叹经过很长时期才确立起来的台谏机构现在变得沉默无言,他提醒神宗,还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在虎视眈眈。这一点也是针对宰相而言,特别是王安石。苏轼劝神宗支持台谏的权威和自由,任用重要并有权威的大臣担任此职,他们的认识有益于皇帝,其不可动摇的坚定会使宰相敬畏。[4](Vol.1,P563)
但实际上,这些策论本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参加制科考试时所撰[15](卷十一《嘉祐六年》,P330-337),苏轼自言:“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11](卷二十七《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又》,P790)文章本系针对仁宗朝晚期的弊政而发,与王安石变法不但并无关联,还因为文中倡导人主自断,破庸人之论、奋发有为,在某种程度上于熙宁之政有“以水济水”之嫌[14](卷五十《策略三》,P1086)。但在杜赫德笔下,原本在仁宗时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被解读为呈递给神宗的奏章,对仁宗的劝诫被曲解为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讽谏。
《全志》在译文的顺序安排上饱含深意,王安石的文章之后,紧跟苏洵、郑侠等人的批评,苏轼的策论虽然成文年代远早于王安石变法,但也被杜赫德有意曲解为对王安石的战斗檄文。这样的安排等于将王安石置于被众人围攻的位置,借由当时反对变法派对王安石的批评,衬托出王安石“阴险邪恶”的形象以及新法“病民害国”的本质。凡此种种,意在向欧洲读者表明,尽管宋朝出现了无神论,但只是由一些道德低下的文人所倡导,当时的道德并没有完全沦丧,一些贤士大夫仍然坚持着对真理和美德的信守,抵制着无神论的影响。中国传统史书中对新、旧两党的君子、小人之别,被杜赫德成功地移植,建立起“新注释家”与“真正的学者”对立的框架,史料背后蕴藏的主观价值判断,也随之渗透到杜赫德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中。
四、如何解读中国古代史:宗教色彩与中国传统史观的结合
17、18世纪,欧洲陷入沸沸扬扬的“中国礼仪之争”⑧,《全志》出版时恰逢这场争论走向尾声。“礼仪之争”中,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的“适应政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引起其他教派的反对,耶稣会士则以大量的著述进行抗争,通过发表著作来传播并证明他们的观点。杜赫德在《全志》中声称,他在书中只扮演一位“历史学家”的角色,叙述基本史实,以规避“给基督教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进行传布带来致命结果”的争论。[4](Vol.1,P639)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全志》中的很多作品都出自礼仪之争中的耶稣会重要人物之手,毫无疑问,这次争论对激励这部文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3](P123-124)“尽管这些出版物貌似公允,甚至有时候还表现天真的纯朴,但在装作仅提供真实情况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堆砌了大量支持耶稣会士理论的证据。”[5](P151,P155-156)人们轻易便可看出,“这套文集过分向耶稣会士们的论点方向倾斜了”[16](P15)。
“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与对手们就中国人的信仰展开激烈争论,耶稣会士的对手们极力证明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指责耶稣会士既然认可中国哲学,就等同于在散布无神论无害的主张。耶稣会士的回应,就是把古儒和近儒区别开来,认为孔子承认真神信仰,而近儒倡导的新儒学则宣扬无神论,是对孔子教理的误解、对原始信仰的玷污;但即使是在无神论兴起以后,“真正的学者”仍然保持着纯洁的原始信仰,自觉抵制无神论的污染。
杜赫德所要做的,就是为无神论的兴起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框架。新儒学兴起于宋代,二程、朱熹是其代表人物,但显然不能让他们承担无神论兴起的“罪责”,朱子学术在康熙朝被奉为官方正统,对他们的批评会不利于当时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因此,杜赫德需要寻找一个替罪羊,王安石便成了理想的人选。在围绕新法的政治斗争中,王安石试图强调天变与具体的人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回应反对变法派的攻击,他的主张经过反对变法派有意地曲解和转述,推导出“天变不足畏”的口号,这已经背离了王安石的本意。而经过杜赫德的诠释,这种纯粹在政治领域展开的斗争又被发掘出另一种解释路径。在杜赫德看来,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主张,潜台词是对“天”亦即“天主”的否定,显然是对古代信仰的一种反叛,是一种无神论;时人掀起的反对新法的浪潮,君子、小人二元对立的政治话语体系下对王安石及新党成员的谴责,都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学者”对无神论的抵制。时空错位之下,北宋时期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朋党之争,阴差阳错地为杜赫德构建无神论兴起的解释框架提供了完美的史料支撑。这也就是说,王安石及其变法最早为欧洲学界所认识,是由宗教辩论的背景所引发的,而贯穿北宋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和中国传统史学中起主导作用的元祐诸臣的历史观,为欧洲学界解释无神论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凭籍。作为一个个案,它清楚地表明,欧洲早期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是在宗教因素的宰制下完成的。
《全志》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蕴含着浓烈的宗教色彩,杜赫德对史料的取舍和诠释方式,都由其主观思想倾向决定,他显然并未止步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角色,其对史料有意地改写与附会,已经严重背离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正当责任。但这并不能否定《全志》在18、19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巨大影响,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神父就曾这样评价杜赫德:
在所有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杜赫德是无可争议的,他精心编辑了一些回忆录,使其内容更丰富、更可靠。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只是在书斋里观察中国,但却无碍其看法的准确性,仿佛他并不是从传教士的回忆录中得到的这些知识,他的思想不是形成于这样的环境。他给读者带来准确的知识,消除了一些虚假的偏见。因此,他的著作历时愈久,声誉愈隆。因为他将证明自己,甚至使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当代作家们惊讶不已,使他们不敢轻视中国,他们反对杜赫德有关中国的看法,就等于企图让人相信幻想和谎言。[17](Vol.2,P564-565)
钱德明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杜赫德及《全志》在18世纪的崇高声誉,对于当时的欧洲读者而言,他们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非常有限,耶稣会士的作品是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在他们眼中,杜赫德是一位“在忠实程度上可以和一切古今的世俗历史学家相媲美的作家”[18](P60)。安田朴(René Etiemble)形象地比喻,在18世纪40年代左右,“杜赫德神父在中国问题上所具有的权威就如同过去的博瓦尔圣母院一样”[19](P577)。《全志》也得到高度评价,直到20世纪初仍被很多学者视为了解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著作,阎宗临完成于1936年的博士论文中就称:“这部著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科学价值。直到今天杜赫德的这部著作仍值得参考。不求助于这部著作,人们就很难得体地谈论中国。”[18](P57)
《全志》刻画了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欧洲汉学史上的最初形象,正因为杜赫德和《全志》享有的崇高声誉,这种形象长期影响着欧洲学界对该问题的认知。在杜赫德以后,无神论于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倡导下兴起在西方学界成为一种共识,1834年,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在《中国简史》中就写道,宋神宗在位期间,唯物主义(Materialism)成为盛行的哲学,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20](P223)
更重要的是,《全志》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宋代文献介绍给欧洲知识界,奠定了欧洲学界认识、探究宋代历史的文献基础,在此过程中,文献背后蕴寓的主导性史观也潜移默化地为欧洲学者所感知和接受。魁奈(François Quesnay)曾说:“杜阿尔德神父曾经专心收集了这些报告并将它们编辑成内容相互关联的一个专集。他的这部著作所具有的一般长处为人们所公认。我们研究中华帝国,即以这位作者编辑的史料作为依据;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查考他曾经用过的那些原始资料。”[21](P26)
魁奈的话揭示,杜赫德对史料的取舍和诠释方式,为当时欧洲学界所广泛依据,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优秀的学者如魁奈已经意识到杜赫德提供的“二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危险,转而亲自查考“原始资料”,但他们却忽略了这些“原始资料”仍然是由某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文献中蕴含的主观价值判断仍然会发挥潜在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很多西方学者仍然未能摆脱这种影响。1873年,英国人葛显礼(H.Kopsch)在《中国评论》发表了《“改革家”王安石》一文,文章完全承袭了南宋以降至明清中国史书的主流观点,对变法派和元祐党人作二元论的区分:王安石是“手段高明的阴谋家”(consummate schemer),他所倡导的新法给国家带来数不清的伤害,并且他“贪得无厌”,无疑曾通过新法中饱私囊[22](Vol.2,No.1,P29-33);司马光则代表百姓的利益竭力抵制王安石[22](Vol.2,No.2,P74-79)。1898年,蒲尔杰(Demetius Charles Boulger)的《中国历史》在论及王安石时也写道:“他颁布的新法激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和宫廷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被废除。……这位精明而没有节操的大臣或骗子(charlatan)就是王安石。”[23](P258-259)而对于司马光,蒲尔杰同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与王安石相比,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展现出更明智的判断,以及对人性更精确的估计,他批评这些观点(指新法措施)是荒诞的”[23](P260)。葛显礼和蒲尔杰的研究在质量和深度上都较《全志》有了大幅提升,蒲尔杰甚至开始运用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王安石的新法展开分析,但就文章的核心史观而言,二者仍然受到《全志》的影响,承袭着自“元祐诸贤”以后的中国传统史家的主流看法。
从《全志》开始,直到近代学术兴起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欧洲学界饱受批评,当《全志》中弥漫的强烈的宗教因素逐渐褪去后,杜赫德出于宗教目的而引入的史观、援引的史料却依然持续地影响着后代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提醒我们,所谓的“西方汉学”,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异域的想象”,其知识体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学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学界已经就西方汉学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多有论述,可当我们汲汲于寻求“他山之石”,以作为反观自身的镜鉴时,也不应该忘记首先检视“石头”的由来。
注释:
①《中华帝国全志》有两个英文版本,一是由出版商瓦茨(J.Watts)于1736年12月在伦敦出版,书名为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是一个节译本。另一个是由出版商凯夫(Edward Cave)推出的全译本,于1738—1741年陆续出版,书名是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本文以凯夫本为据。
②法国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教授考证,“中华帝国君主史纲”所据书目为朱熹《通鉴纲目》和袁黄《历史大方纲鉴补》(参见蓝莉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2、182页),本文中的引文也尽可能从上述史书中摘引,特此说明。
③耶稣会内部对利玛窦的提法存在争议,龙华民(Nicoolò Longobardo)就批评利玛窦的解释是迎合儒家,反对将儒家经典里的“天”和“上帝”等同于“天主”。
④学界就“三不足”说是否由王安石本人提出还存在争议,以邓广铭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持肯定意见(参见邓广铭:《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而以漆侠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不足”说是由反对变法派捏造(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0-98页;顾吉辰:《王安石“三不足”说质疑》,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102-104页;王荣科:《王安石提出“三不足”之说质疑》,载《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第47-55页)。
⑤以上关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论述,参考了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271页),特此说明。
⑥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出版后,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衍生出众多支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考究义理、严辨正闰的“纲目体”的出现,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代表。《纲目》与《通鉴》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思想的背离,《通鉴》“事备而义少”,重事实、严考辨;而《纲目》则把褒贬义理放在首位,摒弃了历史学尊重历史事实的基本要求,于文字叙述之间表现予夺,寄托某种政治理想(参见葛兆光:《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154-171页)。
⑦有关《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学界还存在争议,曾枣庄(《〈辨奸论〉真伪考》,《古典文学论丛》第十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章培恒(《〈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氏著《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等学者认为该文为苏洵所作无疑,而以邓广铭先生(《〈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该文系邵伯温伪作。
⑧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Benoit XⅣ)发表“自上主圣意谕”,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天主”,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孔或祭祖活动,对中国礼仪问题做出最终裁决,很多学者以此作为“中国礼仪之争”的结点(参见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147、154-155页;蓝莉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9页)。但实际上,礼仪之争在此后又有多次反复,直到1939年罗马传信部颁布法令《众所周知》,取消了1742年谕令,礼仪之争才告终结(参见(比)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复旦学报》2016年第1期,第97页)。本文在此仍以1742年为一阶段性终点。
[1]严复.王荆公诗评语[A].严复集: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M].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3](法)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Du Halde,J.B.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London:PrintedbyEdwardCave,atStJohn’Gate,1738-1741.
[5](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M].(法)梅谦立,注.谭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明)袁黄.历史大方纲鉴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8](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宋)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续修四库全书本.
[11](宋)苏轼.苏轼文集[C].(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3](明)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古文渊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15]孔凡礼.三苏年谱[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16](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A].法国当代中国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Amiot,J.J.M.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c.desChinois.Paris:Nyon,1776-1814.
[18]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阎守诚,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9](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0]Gutzlaff,C.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Ancient and Modern: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New York:By John P.Haven,1834.
[21](法)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M].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2]Kopsch,H.Wang An-Shih,The “Innovator”.In Dennys,N.B.and Eitel,E.J.(eds.).The China Review:OrNotesandQueriesontheFarEast,1872-190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23]Boulger,D.C.The History of China.London:W.Thacker&CO.,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