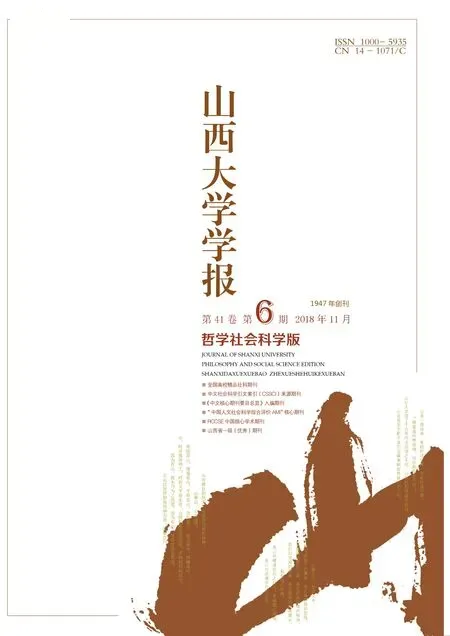身体的武器: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赛场暴力
李金龙,葛 辉
(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从中外体育运动发展历史来看,暴力行为始终困扰着体育运动的和谐发展,在付诸诸多干预和控制措施的情况下,体育暴力仍然充斥于国内外的各类体育赛事之中,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困境,“体育暴力”成了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学问题。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在体育暴力议题上通常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界定体育暴力的概念,以及如何区分赛场攻击性与暴力、合法暴力和违规暴力之间的差异;第二,作为有组织的体育赛事,是否为运动员提供了一种Moore(1966)认为的表达攻击性态度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体育暴力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构建和学习的行为,体育通过设置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本身具有违规或违法性质的暴力行为合理化[1]。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需要基于一个理论分析前提:以何种方法和视角能够对体育暴力行为进行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就国外学者而言,功能主义理论、冲突论、互动论、后现代主义都对体育暴力的概念界定进行了尝试;我国学者则更多的借助于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将体育暴力与法律和道德的社会约束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理论视角的单一也造成了目前我国在体育暴力研究中的一种窘境: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结论重复空泛,教育、道德、规制、法律成为解释体育暴力的固定框架[2,3,4]。
在法学和心理学领域,对于攻击性行为和暴力都进行了准确定义,但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角度而言,需要给予体育暴力以社会学的意义,这也就决定了体育暴力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唯一的定义来解释。甚至在足球、篮球、冰球、橄榄球等项目中,实现赛事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使用暴力,暴力在上述项目的赛事中被看作是一种武器来对抗对方的身体[5]。由此可见,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赋予体育暴力一定的社会意义,能够进一步洞察和解析暴力行为在体育运动中的内涵。就体育运动而言,暴力行为更多的产生于男性运动员群体中,在常规的道德、法律、教育、社会化等分析视角之外,体育运动中的男性性别认同和“男性霸权主义”对于运动员的暴力行为会产生何种意义的作用,这是值得学者思考和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和批判社会学理论,结合对一些男性运动员的访谈,从男性性别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运动员在规则约束下的赛场中通过暴力所构建的社会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运动员男性化的社会建构所产生的影响。
一 体育赛场暴力对男性群体的社会意义建构
(一)女性性别权利的崛起与男性的应对
除去原始社会时期短暂的母系氏族社会,世界大多数地区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阶段都是以父权社会为基本特点。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及中国的殷商时期,父权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早期的性别平等逐渐转变为“男尊女卑”的性别压迫。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赛会以及中国古代的体育赛事中,女性被完全剥夺了参与甚至观看的权利。尤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强化了男尊女卑、夫为妇纲的家庭观念,程朱理学的兴起进一步将这种封建性别观念制度化、极端化。可以说,中西方传统性别观念下的男女差异影响到了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体育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也自然难以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就现代体育运动而言,其是以一种男性身份出现的,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到现代社会的各项赛事,男性身份的强势几乎体现在各个层面。
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东西方各国的发展,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所构建的传统性别观念遭到了强烈挑战,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女性自觉能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传统性别观念下男性群体的优越意识逐渐被削弱,男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同样表现出了一种“男权危机”。例如我国,以男性身份出现的现代体育运动反而体现出了一种“性别倒置”,在足球、排球、田径等项目上,女性运动员的成绩要明显优于男性运动员。在这样一种潜在的“男权危机”下,男性运动员群体眼中的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就更加重要,因为体育运动为男性运动员提供了一个性别认同强化的理想场所,即在体育运动中,男性理应比女性更加优越。与此同时,相对于其他社会活动来说,体育运动的开展更加依赖于身体,而身体在性别观念中的作用尤为突出。Crossett(1990)指出:男性性别意识的优越感在体育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有助于男性对女性权力的控制和剥夺,因此女性会被不同方式排斥于体育运动之外,这是男性社会权力自我强化的途径之一[6]。Crossett的观点在我国体现得更为明显,从社会到家庭、从家庭到父母,几乎对于女性从事体育保有一种抵制和排斥的态度,女性身体应该被弱化,而不是通过体育运动得到强化。
自女权主义理论兴起以来,许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都认为男性是通过运用身体上的优势来提升自身对女性的控制力(Brownmiller,1975)。虽然男性对于女性控制的尝试涉及了心理、经济、教育、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但是最终都会借助身体优势,这种身体优势的重要表达方式就是暴力行为。根据美国体育社会学家Eric Dunning(1986)的研究[7]可以看出,古代社会中,战争和暴力行为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权力的平衡更加倾斜于拥有强壮身体的男性,但是随着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文明,社会对于暴力行为实施了更多的控制,权利的平衡就逐渐地靠近女性,男性对这种性别秩序更迭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参加对抗色彩浓厚的体育运动。但是随着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这是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直观体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以身体对抗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运动中,在身体层面存在劣势的女性群体同样可以获得优异成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体育运动力图通过排斥女性达到提升男性权利的意义逐渐淡化,因此为了保证男性在体育运动中的权利主导性,将男性价值技能进行强化就成为更加可行的途径。
(二)男性群体暴力规则的构建场域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将男性气质和女权主义理论融入体育暴力研究正在逐渐的普遍化,但是简单地将体育暴力等同于男性气质则缺乏一种科学性和可验证性。首先,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目前为止还尚未有任何研究能够从实验和数据的角度来证明暴力行为与男性遗传荷尔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甚至Scher和Stevens的研究证明男性并不喜欢从事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是男性后天习得的结果[8]。因此,以男权主义作为分析体育暴力的基础概念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性别在体育暴力中的意义,其难以有效的分析历史过程中性别观念的动态变化在体育暴力中的作用。其次,作为一种性别群体,在我国封建社会及西方的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确以牺牲女性群体为代价获得一种“男性特权”,但是这种男性特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和毫无争议的,以女性的从属地位来定义男性特权在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中难以起到科学的分析效果。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Connell建议使用性别秩序的概念接入到体育暴力行为的研究之中,将性别权利的动态变化与体育暴力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首要对象。Connell(1987)认为在男权主义下分析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群体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因此男权主义下的暴力应该针对女性群体,但是体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几乎都是男性之间的暴力行为,女性并未在体育暴力过程中受到实质性的伤害[9]。在体育运动中,赛场暴力的实施者和受害者多数为男性群体,因此借助于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体育赛场暴力的社会构建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男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如何影响到男女性别的社会建构。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要基于下述几个问题的思考:(1)一些男性运动员为何会产生暴力倾向,这些运动员对他人的暴力如何影响自身社会意义的建构?(2)男性运动员对他人的暴力行为是否仅限于赛场这一特定的情境之中?(3)男性运动员的赛场暴力行为是否对现有的社会性别秩序产生一定的意义?将体育赛场作为分析男性暴力行为的场域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首先,体育赛场中的男性群体可以自己构建暴力的策略和行为方式,男性运动员对于暴力行为的实施有着明确的规则和“战术”;其次,体育赛场是一种具有社会公开性的特殊场域,男性运动员的暴力行为能够被其他观众直观地观察到,这是赛场暴力对于男性社会意义建构进行影响的必要途径。
二 赛场暴力的特殊意义
除去拳击、散打、柔道等以暴力攻击作为基本运动形式的格斗对抗项目之外,足球、篮球和橄榄球项目比赛中的赛场暴力要显著多于其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运动员在整个比赛过程之中除了精彩的盘带、射门、投篮之外,还充斥着以咆哮、谩骂和推搡为主要形式的高强度对抗,同时在高强度对抗之下的身体伤病也较为频繁。但是相对于恐惧而言,似乎男性运动员更加乐于接受这样一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对抗,笔者曾经访问过一名参加CUBA赛事的高校篮球队队员A时,有这样一段谈话:
“我们队友不停地对我吼:你弄他呀,你那么大块,你卡死他他肯定过不去。教练员也不停让我加强身体对抗,让我通过强硬的身体碰撞来威慑对手。我一想想也是,我这么重不怕他们,我受伤了他们也够呛。”
A的谈话体现出男性运动员在高强度比赛中有关身体的一种态度,即除了基本的技术和战术之外,身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加入到与对手之间的对抗之中。在访谈的一些其他运动员中,大多数男性运动员都将身体暴力作为一种比赛对抗的重要形式,都在比赛过程中力图将暴力行为由规则约束下的非法化转化为比赛允许的合法化行为。在这些运动员眼中,强壮的身体就是先天所赋予的有力武器,日常所参与的力量训练就是为了高强度对抗所需要的强壮身体进行针对性的培养。美国橄榄球明星Macarthur Lane曾指出“作为一个职业橄榄球明星,吃饭和睡觉都是在浪费时间,真正的运动员应该无时无刻地培养和强化自己的身体”。男性运动员在比赛中对于强壮身体的崇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暴力在体育比赛中不仅仅是一种不合理的场外因素,反而是一种比赛的组成部分。运动员对于暴力的意义也不仅仅建构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相反,许多运动员都将暴力对抗看作是运动员努力比赛的标签。运动员J是一位参加过三届CUBA赛事的老队员,其在描述自己的身体对抗时有这样两段谈话:
“在第一次参加CUBA赛事时,暴力对抗始终困扰着我,有时候我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可能会伤着对手,他躺在地上打滚的样子我看了也很内疚。但是在后面的比赛中,我反而觉着如果整场比赛都没有一次强硬对抗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失败。而且我作为内线球员,一旦产生强有力的身体接触,甚至有时候就是故意攻击对方的时候,教练员和其他队友反而很认可。”
“我觉着暴力本身就是篮球的一部分,肯定有人受伤,这可能就是游戏规则吧。反正我觉着必须得暴力点,不是他倒,就是我倒。”
从这一段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体育暴力并非是运动员先天具备的,而是一种带有学习倾向的习得性行为。Smith(1974)在20世纪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对于橄榄球运动员暴力行为的研究就指出,在比赛中容易使用暴力行为的运动员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一般比较高,同时这种暴力行为也会被其他队友和教练员看作是一种男子气概而受到鼓励和支持[10]。同Smith的研究一样,许多经常出现恶意犯规或者赛场暴力行为的运动员并没有受到同伴和教练员的鄙夷和排斥,反而在运动队中扮演着一种相对重要甚至无法替代的角色。
L是山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长治大力水手的一名业余球员,其在多场比赛中出现了恶意犯规和场外辱骂斗殴的行为,但是这位极具攻击性的业余足球运动员,几乎已经成为整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2017年山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决赛中,L因为受伤早早下场,长治大力水手也在决赛中4球惨败,痛失冠军。赛后L的一段话从另一个层面论述了赛场暴力行为对他的特殊意义:
“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的下场让球队输掉了比赛,但是我不在,整支球队在对手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威胁,感觉对手就像在和小学生踢比赛,轻松随意。我知道我对于球队的意义,教练员和队员让我上场就是增加球队的硬度,只要我在,绝不让他们为所欲为,想干啥干啥。”
L的这段话说明攻击性暴力行为在他眼中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型行为,更类似于是一种战术风格,或者说是个人技术特点。而且对于L的暴力行为,球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依赖的。2011-2012赛季CBA总决赛广东宏远与北京首钢的比赛中,广东队教练在暂停布置战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犯规狠一点,狠一点也吹,不狠也吹,为什么不狠一点,马布里再上腿就掀翻他”!这种战术布置和L所经历的比赛比较类似,在大多数教练员和运动员看来,体育比赛就是身体对抗。在男子体育比赛中,整个比赛就是激烈的战斗,所以作为运动员而言,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许多人将其称作为“赛场强硬”。而且对于比赛而言,在对抗的情况下展示出侵略性更加符合“战士”的特质以及男人的性别特征,这是许多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极为重视的。NBA著名运动员Metta World Peace以暴力行为而著称,但是在场下却是彬彬有礼的绅士。这一系列案例可以看出,如果将赛场暴力行为仅仅局限于道德、法律和社会教化层面来讨论,就会将赛场暴力与传统的暴力行为进行等同,割裂体育赛场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体育赛场中,暴力行为可以是一种情绪宣泄,可以是一种战术安排,可以是一种个人特质,也可以是一种球队风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赛场暴力对于运动员而言,一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男性气质、比赛规则与体育暴力行为
(一)男性气质:对赛场“亲密感”的控制
男性气质与体育运动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与其说体育运动培养了参与者的男性气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具有男性气质的人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也就是说男性群体并不是在体育运动中完成了男性气质的社会化学习。相反,Messner指出大多数年轻男性在第一次参加正式体育比赛时就已经对自己性别特征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明确且强烈的认知[11]。心理学家Chodorow认为男性在早期的发育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性别认知的差异,由于母亲为女性,因此男性在幼年时期会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形成一种认知差异,即会主动地规避女性的性别身份,转而强化自身男性的性别身份[12]。这种结果在体育运动中往往会造成青年男性会主动选择一些与女性不同的体育运动(例如篮球、足球与健美操、瑜伽),但是当一部分女性也参与到这项运动中的话,男性就会进一步选择一些有助于区分性别身份的行为,例如恶意犯规和赛场暴力。在笔者访问的多名职业和业余男性运动员中,强烈的身体碰撞不仅仅是体育所应该包含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为证明体育之所以是体育的关键标识,以身体作为武器进行高强度对抗被看作是合理的和安全的。
无论是从历史研究的梳理还是实践工作的开展来看,从性别认同的角度来分析体育赛场暴力都是有据可循的,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性别认同不能看作是一个局限于某个时段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研究过程。Rubin通过研究发现男性最主要的情感发展主题就是对“亲密”所产生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男性渴望与他人产生亲密感,另一方面亲密又会影响到男性的性别认同,因为从性别差异而言,亲密更加适合形容女性[13]。从性别认同的角度而言,男性对于“亲密”的矛盾心理会影响到其作为男性大多数的社会活动,其中也包含其参与的体育运动。认知心理学家Jean Piaget通过观察儿童体育参与指出:女孩对于游戏和比赛规则的遵守更加灵活,其往往能够在游戏和比赛中做出一些带有创新性的调整,以保证游戏和比赛更为公平;男孩对于游戏和比赛规则的遵守则岗位保守和死板,对于男孩而言,清晰固定的游戏规则是保证公平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正式的体育比赛中,规则的固定化和系统化有助于为男性创造一种较为安全的心理适应环境,比赛中的明确规则会为男性产生矛盾心理的“亲密”划定一种界限,男性与对手之间的关系在规则的约束下非常明确。一方面,男性在比赛中无论是与对手还是己方队员之间都能够保持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亲密”关系(即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进行配合、对抗),另一方面会严格按照比赛规则来进行带有强烈对抗性质的比赛,从而避免改变之前的“亲密”。
由此看来,男性与女性在体育运动中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态度是存在差异的。在女孩看来,比赛公平意味着大家对于所有比赛规则的认可,因此女孩会主动地调整和优化游戏比赛的规则来保证大家能够对这种规则进一步的认可,从而强化己方之间甚至与对方之间的亲密关系。简而言之,女性在体育运动中更倾向于实施有助于强化“亲密”心理的互动行为。但是就男性而言,其普遍存在对于“亲密”的矛盾心理,因此其在体育运动中更倾向于对“亲密”关系的控制,以避免由过于“亲密”所带来的男性身份认同的削弱。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因素,男性在体育比赛中不会主动的通过一系列互动行为去使原本与对手之间的对抗关系逐渐转换为“亲密”关系,甚至更倾向于采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的身体对抗来实现对“亲密”关系的规避和控制。
(二)比赛规则:正式约束下体育赛场暴力的诱因
在体育运动中,个体角色以及在运动群体中的特殊位置是由在完善规则系统约束内的竞争所决定的,这种规则系统决定和控制着参与者在体育运动中的大多数社会互动行为。虽然在正式的体育比赛中,许多运动员都会通过分析规则来尽可能获得比赛优势,但是大多数运动员都会尊重规则。甚至对于一些经常发生暴力行为的运动员而言比赛规则也同样重要,比赛规则能够为运动员之间的攻击性行为设置“安全阀”。就体育运动而言,尤其是正式的体育比赛,规则保证其能够在一种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运行,如果失去规则的约束,男性运动员就需要不断与对手进行协商和谈判以保证比赛能够在双方认可和接受的情况下进行,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无论在身体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会在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遇到更大困难。因此对于上文提到的运动员J和L而言,频繁发生的身体接触和攻击性行为反而在男性赛事中显得更为自然,相对于谈判和协商来说,身体对抗和接触更能够在男性运动员之间建立和强化人际关系。
在访谈的多位运动员中,规则范围内的竞争是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态度,因此能否在规则约束内来实施自身的社会行为,也成为运动员群体的身份标识之一。与之相类似的是,在被访谈的运动员中,即使是规则范围内的犯规和暴力行为也被看作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只要没有受到裁判的判罚,既可以被看作是规则允许下的正常竞争行为。但是,在关注体育赛场暴力时需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在男性运动员中,暴力行为的发生频率相对比较高,但是主要去攻击对手的情况则相对较少,更多的暴力行为基于一种规则允许的动作基础之上,但是给被侵犯的运动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害,这种情况如何来分析?是基于一种赛场行为还是暴力行为?在篮球和足球比赛中,某些导致运动员受伤的犯规行为并未得到裁判的处罚,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争论,这些犯规行为是规则允许下的合理比赛行为还是赛场暴力行为成为争论的焦点。因此,对于赛场暴力行为而言,一方面需要分析运动员的个体参与经验及规则意识如何与赛场暴力之间产生联系,另一方面则需要分析暴力行为在赛场之外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在对抗激烈的体育赛事中,频频发生恶意犯规的运动员可能不会遭到教练员和其他队员的排斥,甚至成为比赛战术设计的重要环节。对于这些运动员本人而言,所产生的恶意犯规和暴力行为可能也不会影响到运动员对自身的价值判断。但是对于每一位体育比赛的关注者来说,这些恶意犯规和暴力行为是否会改变体育运动的性质,影响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则是一个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2015年的中超联赛中,天津泰达队球员郭浩对上海上港球员孔卡实施了恶意犯规,导致孔卡腿部被拉出15厘米的伤口受伤离场,这名1993年出生的球员突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被社会大众称作“一犯成名”。但是对于这种因暴力行为引起的关注,郭皓本人并不完全认同,其在赛后说道:“我觉得作为防守型后腰,就应该踢出自己的风格,自己动作有点用力过猛,不合理,才对他造成这么大伤害”[14]。在郭皓看来,对孔卡造成的伤害只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这种不合理并非基于道德和公平观念,而是基于比赛位置的战术要求和自身对于比赛的认真态度,也就是说郭皓实施的恶意犯规是在对比赛规则和体育精神的尊重下发生的,这是运动员自身同媒体公众看待这一问题的最大差异。
类似于访谈的篮球运动员J和L,以及“一犯成名”的足球运动员郭皓,其所发生的一系列案例可以用Bredemeier和Shields“语境道德”来分析。语境道德最核心的观点就在于对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设置了不同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于道德的判断和分析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标准。体育赛场相对于其他社会活动场域而言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这一特殊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道德和价值判断标准都有着特殊的标准,体育赛场即是一种特殊语境。在这几位运动员看来,体育赛场最重要的语境道德标准就是遵守规则,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不需要再重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约束。在体育赛场中,故意违反规则所引起的伤害行为应该属于暴力行为,应该受到严厉制裁。但是在比赛中出于竞争目的而造成的伤害只能是一种积极参赛的表现,反而应该获得社会的认可。但是出于社会道德约束的影响,这种观点受到了众多质疑,规则是在约束暴力还是为暴力行为做出铺垫,运动员和社会大众的态度显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四 男性运动员的身份标识
在拳击、柔道、摔跤等格斗对抗类运动项目中,运动员被看作是拥有强健身体和完美体魄的优秀人群,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格斗类项目运动员的伤病情况也更为恶劣,几乎每一位格斗类运动员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永久性身体损伤。批判理论中的工具理性让运动员将自己的身体看作是获得比赛胜利的机器和武器,用来战胜一个被客观化和程式化的比赛对手。在足球、篮球、冰球等通常对抗性项目中,更能够体现出以身体作为武器的重要作用,不停地卡位、碰撞、推搡等使得运动员能够在激烈的比赛中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优势,但是这种以身体作为武器的对抗极容易导致赛场暴力。从目前来看,运动员的伤病随着现代竞技体育激烈程度的增加而变得更为普遍,例如2017年NBA所发生的伤病潮,仅仅开赛一月左右,因比赛受伤而停赛的首发球员高达12人,替补球员为38人,远远超过之前几个赛季;在我国运动员中,被访谈的所有运动员均发生至少一次伤病,这种情况涉及了国家队、省市体工队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运动员。几乎所有的职业或专业运动员都产生过运动伤病,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并未对伤病产生消极情绪,反而将伤病看作是男性运动员的身份象征。在其看来,运动伤病是男性运动员应该有的身份标识,以身体作为武器获得胜利是男人的义务。
虽然由于犯规引起的伤病对运动员的身体造成了明显损伤,但是从群体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种伤病却为男性运动员群体构建了群体关系和群体认同感的基本体系。犯规所带来的伤病为运动员带来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恰恰被其看作是比赛的一部分,这是其由“男孩”向“男人”转变的重要途径,是赢得尊重的基本方法。Salvini和Souza的研究指出:“运动员在正式体育比赛中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提高自我能力,同时强化和发展自身与对手之间极端的工具性关系,各种自我能力的提升和工具性关系的发展极容易导致运动员的愤怒情绪”[15]。也就是说,在体育比赛中,男性将身体作为对抗的工具和武器首先在个人层面是得到较大程度认同的,但是一旦将工具性关系进行强化,运动员在身体层面和人际交往层面都会由于这种极端关系和暴力行为的产生而付出代价。
将身体武器作为男性身份标识来强化自身的性别认同,在一些特殊的运动员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就我国来说,从事正式体育比赛的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起步较早,同时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职业可选择范围上同其他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从男性性别认同的角度而言,运动员群体由于时间、能力、职业范围等方面的原因,很难通过其他渠道来实现对“男子汉”气质的认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家庭地位、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青年男性在短时间内实现自身的男性地位,但是运动员大多数为未婚男性,且职业收入的有限性也限制了其经济地位的提升,因此从职业地位的角度而言,以更加积极和认真的角度来实现男性身份标识是更为理想的途径。体育运动为这些较早进入固定职业且年龄较小的男性群体提供了一个证明自身男子气质的理想途径,一方面体育运动所带来的胜利也极大满足年轻男性的男性认同期待,另一方面运动员可以通过身体的对抗更为直接的获得男性身份地位的标识。
五 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新建构
就体育运动而言,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多层面的,爱国主义、道德约束、精英文化都能够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得到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性别严格而言不能看作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象征意义,但是体育运动与性别的关系是认识体育的重要途径。虽然从目前来看,世界体育的发展方向趋于性别平等,但是男性与女性在体育中的身份认同差异依旧十分明显。在访谈一位山西省古典式摔跤运动员Z时,他对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更为简洁和直观的表述:
“女人可以从事体育运动,甚至能够成为我的教练和领导,但是你要让她和我一样扛住对方一个滚桥抱摔,哈哈,肯定住医院了。”
之所以简短的附上这位摔跤运动员的观点,目的就是说明体育赛场暴力同社会性别秩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男性运动员和男性观众在对待性别差异上的态度十分明显,男性更加适合暴力的身体对抗,而女性则适合于暴力之外的任何其他活动。从摔跤运动员Z的这一段话来看,体育运动被看作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游戏,而判断是否能够参与这一游戏的标准仅仅是能够拥有对抗击打的身体。在篮球运动中,男篮无论是在开展规模还是参与人数上都要远远大于女性,在许多男性篮球运动员看来,篮球的基础就是身体,肌肉发达、身材高大被看作是最适合篮球运动的身体。但是女性在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同男性相比十分明显,因此女性更多地在篮球运动中充当着啦啦队和观众的角色,为男性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加油。与女性拉拉队员和女性观众“矮小脆弱”的身体相比,男性运动员的身体被提升到了一个接近于神话的地位,例如许多NBA运动员的夸张绰号都来自于其身体及身体基础上的对抗能力。(“大鲨鱼”奥尼尔、“小霸王”斯塔德迈尔、“半兽人”法里埃德)。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目前社会性别秩序的一个特殊性:至少在体育运动领域,男性表现要优于女性。
随着社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身体在工作中所起到的重要性不断降低,同时和平时期内战争数量的下降也降低了身体在国家对抗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社会性别秩序中,强壮的身体和对抗能力就成为凸显男性性别特征的重要标志。身体作为自然天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构建现代社会性别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trelanH和Hargreaves指出:在体育运动中,身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就运动员而言,拥有足以改变性别秩序的强健身体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其需要长时间的实践、锻炼、营养补充甚至服用一些激素药物[16]。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虽然身体来自于先天遗传,但是能够在社会性别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身体更多地需要来自于社会实践。
男性主义中所蕴含的阳刚之气是赋予了男性在对抗中所需要的力量和技能,这就导致社会性别中女性对于男性的规划和服从,这种性别秩序也影响到了社会的暴力分布,男性群体的暴力发生率要明显高于女性群体。同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相比,体育更是一种彰显男性气质的理想场所,作为一种改造身体的实践,体育进一步削弱了身体遗传所表现出的相似性,构建和强化了身体通过后天改造所带来的差异性。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被观众和媒体通过不同形式的观察、报道、记录而形成一种社会“符号”,使其逐渐的自然化与合理化。但是最近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学者指出体育在强化男性性别认同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的原因可能并不在于暴力,而是在于有机会观看并认同肌肉发达的男性身体的男性观众。例如目前流行的动作电影,电影演员在影片中更加直接和连贯的将男性强壮的身体与暴力行为进行紧密结合,但是男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认同更多的不是来自于暴力,而是来自于对男性身体的欣赏甚至自恋情节。Morse在一篇关于足球中使用慢动作即时回放的研究中指出:足球比赛中的慢动作回放让暴力动作的激烈和血腥程度大大降低,因此观众通过慢镜头回放来观看赛场暴力行为并不是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其提高自身男性性别意识的重要方面还是在于欣赏运动员强壮优美的身体。
就赛场暴力而言,其也可能起到另一个较为明显的作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前文说道,运动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者,过早的投入到了职业工作之中,难以通过学历、经济、家庭等其他方面来实现社会地位和男性地位的提升。相对于运动员而言,男性公务员、企业家、教师等在其参与的多数男性活动之中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少之又少,这主要是因为上述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暴力之外的途径来实现和强化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认同。对于男性观众而言,也能够通过对于暴力行为的观察满足自身的社会差异感。尤其是对于一些中等以下收入阶层的男性观众而言,他们眼中发生暴力行为的运动员体现出的是一种“硬汉形象”,这些运动员证明了男性要比女性优越,身体强壮要比身体瘦弱优越,这就满足了男性观众的性别秩序的认同感。从球迷的角度而言,这些发生暴力行为的运动员是当代的“希腊角斗士”,让男性观众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社会性别秩序中所占据的主导位置,这种认同感和主导意识的获得是建立在赛场暴力行为者在身体和心理双重牺牲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暴力行为的运动员在某些情况下被看作是“英雄”和“男子汉”。就大多数没有获得过高水平赛事冠军的青年男性运动员而言,教育经历和经济实力的差距使得其在整个社会男性群体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但是男性气质的培养以及男性性别认同的提升同样也是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可能会倾向于选择赛场暴力行为来构建真正的“男子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