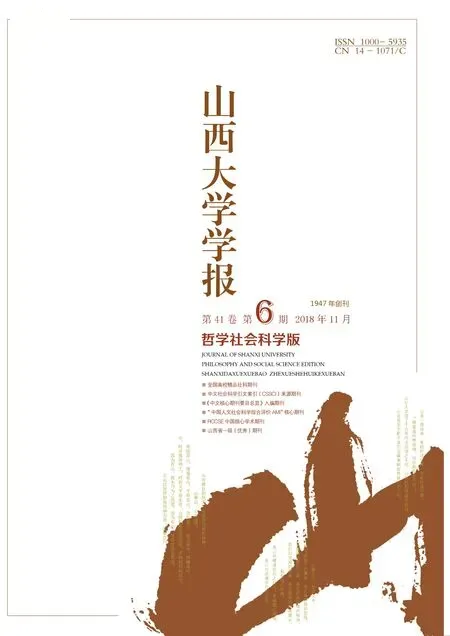《红楼梦》哲学性质考辨
——红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对象的反思
高 源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珠海 519082)
近年来,关于《红楼梦》哲学思想的研究日趋增长,一系列著作如《红楼梦哲学精神》《红楼梦哲学笔记》《<红楼梦>哲学论纲》《红楼梦悟》《<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等专著或论文的出现,将《红楼梦》能否作为中国哲学有机部分的问题提上日程*参见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再复红楼四书,如《红楼哲学笔记》《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此四书均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以及刘再复论文《<红楼梦>哲学论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4):5-16;《<红楼梦>与中国哲学——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渤海大学学报,2010(2):5-18。其中,《红楼梦悟》的英文版,见Liu Zaifu,Reflection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rans. by Shu Yunzhong (New York: Cambria Press,2008)。此外,关于红学的哲学与文化学向度的研究,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梁归智:《禅在红楼第几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红学的哲学与宗教学维度的研究也力图拓展自20世纪初新红学所开辟的考据学路径,即超越出“探佚学”“版本学”“曹学”“脂学”等传统范式和范围来寻找《红楼梦》与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的内在精神关联*重要的代表性研究包括Zuyan Zhou,Daoist Philosophy and Literati Writings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Hong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3); Anthony C. Yu,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Jeannie Jinsheng Yi,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 Allegory of Love (New Jersey: Homa & Sekey Books,2004); Dore J. Levy,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Li Wai-yee,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等。此外,自2010年始的欧洲汉学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Sinology也反映了部分最新欧洲红学研究的动态,其中哲学路径的研究值得关注,比如Karl-Heinz Pohl,“The Role of the Heart Sutra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in European Journal of Sinology 2014(5): 9-20等。。然而,《红楼梦》能否进入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话语系统内加以讨论,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论。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红楼梦》哲学”并非是通过材料校勘的方法去厘清作者、版本等史实问题,其范围和研究对象模糊而不确定[注]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价值诠释的读法相较于新红学来说,过于自由和不确定,所以是“不科学的讨论”。如汉·索斯(Haun Saussy)批评这样的哲学读法是主观选择的结果。[1]123。
二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小说并非严谨的哲学表述方式,在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小说一般被纳入文学评论的范围而不是哲学的研究视阈,因此将红学置入中国哲学范围内讨论是不严谨的[注]在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小说被认为是不入流的“小道”而被排除于传统哲学话语系统之外。小说是否是一种哲学表达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至少在现行的诸多中国哲学教材中尚未将红学纳入哲学的讨论范围。关于《红楼梦》哲学研究的争论,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1(2): 20-46。。
针对这两方面的挑战,我们首先考察“《红楼梦》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一 “《红楼梦》哲学”的合法性
(一)新红学与《红楼梦》哲学价值批判
在20世纪的新红学研究中,《红楼梦》一般被作为史学与考据学的材料加以考证[注]新红学一般以胡适《红楼梦考证》(1921年)的出版为标志。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作序时称胡适以实证和实验主义为指向的红学为“新红学”。见顾颉刚:《顾序》,载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在陈维昭看来,无论是否在理论上追随胡适,只要研究出现“实证与实录合一”特征的,即可归为“新红学派”。关于新旧红学的划分和本质的分析,见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147页。,其思想价值时常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批评《红楼梦》的哲学与思想价值已成为20世纪新红学发展中的重要公案。比如胡适在《与高阳书》(1960年11月24日)中这样评论: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更试读同一回里贾雨村‘罕(悍)然厉色’的长篇高论,更可以评量作者的思想境界不过如此。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注]在之前《答苏雪林书》信(1960年11月20日)中,胡适亦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总体印象:“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 胡适:《胡适论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2]253-254
胡适晚年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评论亦为郭豫适、李辰冬、周策纵等后来学者所证实。如郭豫适在其《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引述李辰冬的序文曰:
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广播公司为广播全部红楼梦,整整准备了一年,在正式广播的前夕(按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底),约胡适、李玄伯两位先生以及兄弟我…胡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红楼梦毫无价值”…这是我第一次从胡先生口里听到…但后来打听,晓知道胡先生讲这种话的不止这一次。[注]周策纵指出:“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对唐德刚也说过《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plot)。” 周策纵:《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页。亦参见南佳人:《红楼梦真相大发现:石头记的真相》,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年,第104页。[3]61-62
不止胡适,苏雪林在《由红楼梦谈到偶像崇拜》中评论说:“曹雪芹只是一个仅有歪才并无实学的纨绔子,红楼梦也只是一部未成熟的作品。”[4]103在《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中,苏雪林以更严厉的口吻批评说:
原本《红楼梦》之恶劣,出人想像之外…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还说不上一个‘通’字。全书遣词造句,拖泥带水,粘皮搭骨,很少有几句话说得干净利落的…因为作者曹雪芹实在不通,故此他毫无驾驭文字的力量,如我前文所举‘造句不自然’,‘遣词轻重失当’全书指不胜屈…我以为《红楼梦》好似《聊斋志异》上的‘画皮’…应该说只是一个全身溃烂,浓血交流,见之令人格格作呕的癞病患者![注]此文原载《作品》,1960年10月第1卷,第10期。[5]1272
虽然胡适不同意苏雪林《作品》中夸大其辞的批评(认为“未免太过火”),但“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的观点还是赞同的。[2] 244-245之所以“过火”,在胡适看来,即在于雪林用的是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本[注]“雪林依据那部赶忙钞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都是最不幸的事。”见《与苏雪林、高阳书》(1961年1月17日),载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2]256,而非胡适本人所发现的“十六回”甲戌本[注]据胡适透露,其甲戌本(只有十六回)是与徐志摩一起在上海办新月书店期间从一收藏者手中获得。[2]226-227。与胡、苏相一致,俞平伯对《红楼梦》思想的评论也不高: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我极喜欢读《红楼梦》,更极佩服曹雪芹,但《红楼梦》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的书。[6]225-226
值得关注的是,陈寅恪对《红楼梦》看法也不甚高,认为“其结构还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其结构皆甚可议。”[7]93-94这些文史大师在《红楼梦》获得众口颂赞之时给出刺耳的评价,认为《石头记》“见解平淡无奇、毫无价值”(胡适)、“结构松散、散漫”(苏雪林)、“结构皆甚可议”(陈寅恪)[4]106,着实令人疑惑。然而,对《石头记》的异评早在嘉庆年间即已有之,比如嘉庆十年(1805)的周永保说:“最可厌者,莫如近世之《红楼梦》,蝇鸣蚓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蜡。”[8]61同治五年(1866),梁恭辰之《北东园笔录》刊行,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曹雪芹身后萧条乃编造淫书之显报也。”[9]64光绪年间(1891),毛庆臻等认为《红楼梦》“启人淫窦,导人邪机”,“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9]74-75。
以上诸家对《红楼梦》的思想见地和精神价值提出了尖锐质疑,成为20世纪新红学研究中的历史公案。以此为背景,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红楼梦》的性质并考察“《红楼梦》哲学”概念何以可能。
(二)作为“悟书”的《红楼梦》及其哲学价值
“《红楼梦》哲学”这一术语虽然很晚才有,但把《红楼梦》作为“悟书”来进行诠释和评价的做法在它形成和早期流传时即已有之。如清咸丰时期的“鸳湖月痴子”在《妙复轩石头记序》说:“似作者无心于《大学》,而毅然以一部《大学》为作者之旨归;作者无心于《周易》,而隐然以一部《周易》为作者之印证。”[10]37光绪年间,张新之在《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卷首上谈及“红楼梦的读法”,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11]700-701同治初前后的江顺怡在《读红楼梦杂记》中认为:“《红楼梦》,悟书也…谓之梦,即一切有为法作如是观也。非悟而能解脱如是乎?”[10]205但是清人将《红楼梦》视为“悟书”的评点做法在新文化运动和民国时期渐趋消匿,代之而起的是对其哲学思想和价值的评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精神亦即存乎此。”[12]13这里“哲学-宇宙-文学”的排列顺序明显地凸出了《红楼梦》的哲学价值。王国维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红楼梦》高于《桃花扇》《西厢记》等其他文化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独特的宇宙视角以及具有的一种证悟人生宇宙本质的自觉。因此,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被认为是《红楼梦》哲学研究的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实际上,看到《红楼梦》的哲学价值并建议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人并非王国维一人。辛亥年间的陈悦也说:“《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涵义,乃具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和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10]269他认为应把《红楼梦》列入经史子集中的《子部》,其思想当与西方近代哲学相媲美。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也都试图从儒家或佛教的角度看《红楼梦》的哲学思想。如牟宗三在其《<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中认为《红楼梦》之过人与感人,决不在描写之技术,而在其悲剧思想之大乘[13]。此外,周汝昌关于《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化小说”[14]之论,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为我们将红学纳入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互动视阈下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
从上面旧评点派以及后来研究者的评述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在流传早期就被许多评点家视为“悟书”而与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联系起来。它并非是离开中国传统哲学而存在的孤立的文本形式,恰恰相反,中国哲学的许多范畴、命题、价值判断都深入到这本所谓的“悟书”中并融构出它自身的主题与主旨。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红楼梦》是借用小说的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所悟之道和哲学思想的。这一点在甲戌第一回曹雪芹已经讲明原因,“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曹雪芹用小说这种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展现其哲学思想实际上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应。因此,同样是“立言”,借小说之名而传悟道之实是《红楼梦》作者不同于以往理学家的地方。从“悟书”角度看,“文以载道”是明清小说哲学中的重要特质,也是将《红楼梦》纳入中国哲学体系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红楼梦》哲学思想的独特性
既然“悟书”的性质是《红楼梦》进入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那么,相较于其他明清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红楼梦》是否有独特的哲学价值?
在清代评点派中即有将《石头记》置于小说比较以及古典哲学语境加以判断的理论。如道光时期张新之说:“《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石头记》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11]700-701同时,张新之又将《石头记》与《周易》《大学》《中庸》甚至《春秋》《礼经》《乐记》《战国策》《史记》等传统经典作以比较,认为《石头记》是一部以小说形式来诠释儒家性理的作品[15]58: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10]153-154
相类似的评点亦见嘉道年间甲戌本的收藏者刘铨福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题跋曰:“《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书》,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16]317清人濮文暹、濮文昶亦有跋文:“《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16]318而脂砚斋的评阅也屡屡谈到《石头记》的文笔思想与同时代小说的不同处,如第三回甲戌脂批曰:“奇奇怪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名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
在清人评点派这里,亦将《红楼梦》置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加以考量,并认为有不同于《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其他明清小说的独特哲学价值[注]关于《红楼梦》与其他同时代明清小说比较中的独特性,参见Jeannie Jin Sheng Yi,“Honglou meng and Its Literary Predecessors”,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 Allegory of Love (New Jersey: Homa & Sekey Books,2004),88-93.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4-545页。。“《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集中展现了《红楼梦》植根于中国古典哲学精神而融构自身哲学主题的特质。
当我们考察《红楼梦》作为“悟书”而区别于其他明清小说的时候,就不能不注意新红学兴起之际《红楼梦》哲学的研究与之前“悟书”的品评之间的联系。从“悟书”到“《红楼梦》哲学”的演变过程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在探索《红楼梦》哲学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可以进一步明晰其性质和价值。《红楼梦》哲学形成的背景因素: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作为流行的思维模式刺激了《红楼梦》创作形式的成功,《红楼梦》特立独行的行文风格和哲学思想是对这一时期小说形式的吸收和超越[注]参见陈敏子:《论<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借鉴与超越》,武汉: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亦见Jeannie Jin Sheng Yi,“Cao’s Transformation of Xixiangji and Mudanting”,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 Allegory of Love (New Jersey: Homa & Sekey Books,2004),102-112.。《红楼梦》是在明清之际情思潮的涌动时期形成的。曹雪芹与戴震同属雍乾时代并处于乾嘉学统背景中,他们继承了明清之际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哲学家的传统,对于程朱理学末流之工具化转向和“以理杀人”的社会伦理异化有较深刻的反思,同时也结合市民阶层高涨的情思潮来对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理”“情”“欲”“性”等进行重新思考[注]关于情思潮和明清之际反思宋明理学异化的哲学转向,参见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191页。。在脂评本系统中,甲戌本是保持曹雪芹原著原貌程度最高的本子,而其中脂批在透露《红楼梦》创作背景、揭示儒佛道思想和“悟”的阅读方法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故脂批本身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也是《红楼梦》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根本不同于同时期其他的小说评点批注。
因此,《红楼梦》以小说的方式来反映明清之际所形成的情哲学思潮并对程朱理学末流进行反思[注]以贾宝玉为例。其“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第三回《西江月》)的人物性格反映了对理学末流的反叛。,同时也以“悟书”的形式来融摄古典哲学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融构出自身的哲学视阈和理论主题,展现出《红楼梦》作为“悟书”的独特哲学精神。所以,《红楼梦》哲学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其“悟书”性质的认定上,而从清代“悟书”的评点到近代“《红楼梦》哲学”的研究[注]《红楼梦》美学与哲学价值的研究往往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标志。参见《王国维与哲学、美学诠释》,载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116页。则呈现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
二 《红楼梦》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所处的时代思潮
《甲戌本凡例》[注]甲戌本是目前进行《红楼梦》哲学研究较为可靠的版本,而甲戌脂砚斋批语是体现《红楼梦》哲学思想较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处处点出《红楼梦》的旨义、笔法、史实、哲学思想与关键术语。作为曹雪芹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亲密助手,脂砚斋所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可信度较高的。关于脂砚斋与甲戌本的关系,参见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一开始就点明《红楼梦》的旨义和书名的源流,并认为“情”“梦”“鉴”“空”是曹雪芹这本书的点睛。而在第一回开卷不久之“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处,又有脂批曰:“四句乃一部书之总纲”。依照脂砚斋的观点,“梦”“鉴”“空”“情”这几个字眼不仅涵摄了《红楼梦》的全部书名,也揭示了《红楼梦》的旨义和理论基础。这些关键范畴表明,《红楼梦》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中国古代寓言神话以及儒佛道三教理论的基石上形成的:
(1)中国古代梦的寓言神话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而从另一角度看,小说的“梦”的主题也说明道家道教对它的影响。“梦”的写法和结构能同时杂糅中国文化的许多“套式”和“母题”。首先,小说从梦的神话中开始,体现了远古洪水神话、补天创世、抟土造人在梦的话语系统中的重构。[17]12-24其次,《红楼梦》梦中有梦、梦的回环的写法受到“庄周梦蝶”的影响,梦中有梦、幻中有幻、梦是梦、醒亦梦的思想是对庄子“梦”的观点的借鉴,这种联系在脂砚斋的批语中多次被明确点出(见甲戌本第一回)。再次,“梦”的主题也反映了《红楼梦》背后的道教的理论基石。关于《红楼梦》的道教思想来源,见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第四章。[17]170-268
(2)“梦”在小说中以“假语村言”的形式同时展示了佛教对《红楼梦》的影响。将“梦” 和“幻”联系起来进而展现“万境归空”以及“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思想受到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而《金刚经》的“梦幻泡影”说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的章法、修辞,并引发了梦幻情境中的真假的辨释[18]82。英国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认为,“梦”的真假有无,体现了“空”“假”“中”三谛圆融思想[19]6-7。除“梦”之外,“鉴”和“空”也说明佛教哲学在《红楼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红楼梦》不仅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甚至也受到了印度佛教术语和思想的影响。比如最接近原著原意的甲戌、庚辰本皆用“好事多魔”,而并非己卯、蒙、戚诸本所谓的“好事多磨”。曹雪芹用字用词皆有新意而并非随意,“魔”字貌似谬误,实则含有深意。“魔”梵文为mara,有破坏、扰乱的意思。南朝梁武帝时“魔”以梵文的形式由印度传入中国,“磨”被改为“魔”。甲戌本中不仅多次使用“好事多魔”,而且“劫”、“刹那”等术语也频繁出现。这表明,印度佛教及其语言在向中国文化的转换和渗透中呈现了深层次性和广泛性,并对《红楼梦》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8]57-58。
(3)《红楼梦》对儒家儒教思想的吸收是非常明显的。书中既有对宋明理学的理本体的形上架构的借鉴,又有对朱熹哲学之性情论的借鉴,同时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也在贾宝玉那里可以看到,这在小说中有很多的例子,而且前人这方面的论述也很丰富。但是,在探讨儒家儒教与《红楼梦》的关系时,当时的情思潮[注]“情思潮”(the Cult of Qing)这个术语是明清之际反对理学末流工具化倾向的一种形态的界定。而“情”却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中“passion” “emotion” “love” “romantic sentiments”等术语。关于“情”范畴的内涵及十六、十七世纪明清文学的特征,见Martin W. Huang,“Sentiments of Desire: Thoughts on the Cult of Qing in Ming-Qing Literature”,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20 (1998): 153; Hsiao-peng Lu,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Anthony C. Yu,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Paolo Santangelo,Textural analysis of expressions and terms concerning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Beijing: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Publishing House,2000)。关于“情”作为“emotion” “passion” “affection”等术语在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内涵的区分,见笔者著作Gao Yuan,Freedom from Passions in Augustine (Oxford: Peter Lang,2017): 19-39.的背景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不仅揭示了《红楼梦》与程朱理学间的关系,也揭示了当时社会思潮与工具化儒教之间的矛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情思潮是促成《红楼梦》哲学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对这样的时代精神的考察将是深入《红楼梦》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除了以上古代神话寓言与儒佛道三教理论基础之外,明清之际理学家与小说家对程朱理学工具化本身也产生了反思,形成了以李贽、刘宗周、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为代表的对“以理杀人”僵化理学批判的哲学思潮[注]自明中叶至清代中期,小说家和哲学家对于理欲、情理、义利等宋明理学范畴进行了深刻反思。一种肯定“人欲”、批判“天理”的思潮成为市民社会的主流。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六经皆以情教”、黄宗羲的“复情尽性”、戴震的“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等。关于明清之际新理欲观、新情理观、新义利观,参见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191页。。他们关于“情”与“性”“理”“欲”“空”等关系的论述,给《红楼梦》提供了新的哲学视阈。情思潮的勃兴与宋明以来的性理之辨有直接的联系,构成了《红楼梦》哲学思想中关于本体之辨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对“理”“情”“性”“欲”哲学关系的重新定位(特别是将“情”置入天理人欲问题的核心进行考量),反映出明清情思潮之“尚情主义”对小说哲学的深刻影响。《红楼梦》正是在这样的情思潮涌动的背景中展现真实的社会画卷并回应了中国哲学中长期隐匿的尚情主义传统[注]方蔚林(舒也)认为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与儒法、道释相并列的一个“风骚”传统,但却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强有力的打击而隐匿不显。这种尚情主义亦在中国古代诗文传统中的“言情说”和“缘情说”等理论中有所体现,并反映于明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哲学思想中。见方蔚林(舒也)著:《中西文化与审美价值诠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因此,《红楼梦》的哲学思想是在儒佛道三教的理论基石上形成的,而情思潮则影响了《红楼梦》的价值取向和对三教思想的取舍。明晰出这个理论背景后,让我们来看《红楼梦》的哲学主题及其研究进路。
三 《红楼梦》的哲学主题和研究进路
如前所述,明清情思潮中“情”“性”“理”“欲”“空”等传统宋明理学范畴产生了新的价值诠释并影响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的哲学运思。然而,关于《红楼梦》哲学主题问题,学界则意见分歧甚大。一些学者如梅新林等围绕“梦”的范畴提出《红楼梦》的本然结构源于远古神话原型,然后演绎为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最终走向道家生命哲学的过程[17]。也有学者如余国藩、刘再复、梁归智等从“色空”范畴来看《红楼梦》的宗教信仰和形上世界,认为佛教的“色空”是这部小说的哲学基础,同时还要关注“欲”“情”“灵”,从整体上把握《红楼梦》哲学[注]参见代表作Anthony C. Yu,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Liu Zaifu,Reflection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rans.Shu Yunzhong (New York: Cambria Press,2008); 梁归智:《禅在红楼第几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亦有王国维从“欲”的角度[注]王国维引叔本华《意志观念之世界》(第四编)云:“人之意志于男女之欲,其发现也为最著,故完全之贞操,乃拒绝意志即解脱之第一步也。大自然中之法则,固自最确实者,使人人而行此格言,则人类之灭绝,自可立而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红学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页。以及爱德华(Louise P. Edwards)从“性”的角度[注]爱德华(Edwards)认为绛珠草脱去木质,化身“有情”,是因为太虚幻境的“弃石”施舍甘露。这种“情”是基于“性”之旨趣的。见Louise P. Edwards,Men &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亦参考Chuang Hsin-cheng, Comparative Thematic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1966).分别诠释《红楼梦》的哲学主旨。
在对《红楼梦》哲学主旨和核心范畴的争论中,持“空”与持“情”的观点最为激烈。持“空”的学者多从“因空见色”的十六字谶出发,认为这是曹雪芹的主题宣言与哲学宣言,刘再复正是基于此而提出欲向度、情向度、灵向度、空向度的境界理论[20];持“情”的学者反对“色空”说,如周汝昌认为“如果空空道人真是由‘空’到‘空’,那他为何又特改名为‘情’僧?…一部《红楼梦》,正是借‘空’为名,遣‘情’是实。什么‘色空观念’,岂非‘痴人说梦’。”[注]周汝昌的著作亦被翻译为英文,参见Zhou Ruchang,Between Noble and Humble: Cao Xueqin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d. Ronald R. Gray and Mark. S. Ferrara,transl. Liangmei Bao and Kyongsook Park (New York: Peter Lang,2009).[21]194周汝昌的这种观点更加倾向于脂批以及以往旧评点派的传统解释,认为“情”为《红楼梦》的主旨。如甲戌第五回脂批所言:“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清人方玉润在“情”的基础上说:“《红楼梦》一书…大旨亦黄粱梦之义,特拈出一情字做主,遂别开一情色世界…盖人生为一情字所缠,即涉无数幻境也。”[10]375
虽然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其主旨就已经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但结合《红楼梦》首回“大旨谈情”开宗明义的宣言来看,“情”应为《红楼梦》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但其并不意味着与“空”“理”“梦”等儒佛道三教范畴完全冲突,而是在小说语境中与这些核心概念产生对话结构。在“情-空”“情-理”“情-梦”对话基础上,《红楼梦》首回即点出全书“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旨归。由此,《红楼梦》如何将儒佛道三教的重要范畴化入小说论域并产生与“情”的对话结构,以“以情悟道”的方式展现“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主题思想则构成了《红楼梦》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围绕此核心命题,《红楼梦》展现了以“贾宝玉”为线索(“真事隐”)的精神嬗变以及以“石-玉-石”为布局的双重结构路径,构成了《红楼梦》哲学思想中的两条重要线索,也为红学的哲学与宗教学维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进路:
(1)贾宝玉“情”的精神境界的横向嬗变。
此线索围绕贾宝玉的精神嬗变展现“情”的哲学精神,即在大观园之“现实世界”[注]余英时认为《红楼梦》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为“理想世界”,一为“现实世界”。此两种世界体现真与浊、情与理、真与假两个相应维度。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呈现出“痴情-人情-情不情-情情”的横向境界嬗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情”与“礼”“空”“空空”等范畴之间的对话结构以及“情幻相即”的非有非无、自我破除的“情情”境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小的层层递进的对话结构,依次是:
第一,“痴情”在“至真”和“执真”的双向意义上呈现情的正价值,即在追寻自然至真的状态(实情、真情)上转向对尘世事物的执着,进而引发真假之辨,形成“真”与“假”的对话结构。
第二,“人情”是“痴情”的进一步拓展,是在自然之情的基础上打破异化人际关系的一种反礼教的思想,在“礼”与“情”的对话结构中追寻原始儒家“仁”与真情基础上的“礼”。
第三,“情不情”进一步讨论对幻情幻境执着的问题,并在“空”与“情”的对话结构中呈现“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即在破执的同时保留了“情”的主观立足境。
第四,“情情”进一步打破了“情”立足境,展现了双遣的特征,构成了“情情”与“空空”、“重玄”的对话结构,从而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禅悟呈现以空捨空和“无我-无牵挂-无碍”(二十二回)的解脱精神。
(2)“石-玉-石”结构上“情”的纵向复归的线索。
从“石-玉-石”的圆圈结构来看隐藏其中的情境界的提升是另一种研究线索。《石头记》“炼情补天”的主题直契中国哲学之“道-器”思维,在形下和形上的双重维度上呈现“理”“情”的冲突和圆融。将“情”提高至形上的高度为人性根据和世俗价值重新确立根基。“炼情补天”和“石-玉-石”小说结构是曹雪芹试图在宋明理学理本体思维模式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具体而言,《红楼梦》将情分为青埂峰上、太虚幻境和大观园中三种情场。情石自女娲神话而来,本无灵性可言,而形状粗蠢、无材补天,处于混沌玄冥的状态;及其“落堕情根”、灵性稍通,则有了思凡之念,“已发”之情随“风月情债”一道落入红尘,历情之种种而“以情悟道”;后复本还虚,以“情情”的境界重新回到玄冥,劫终之日、解脱轮回。这个生命醒悟和境界嬗变之历程,呈现出“情情”在三种情场中的体用一源的状态:“情情”既是青埂峰上的玄冥之境,也是尘世的诗情画意的生存理想。由理谶债命、无材补天之“形上之理”,经落堕情根之“理情分立”之途而入炼情补天的“以情融理”的嬗变是“情”体用一源、还债解脱的展现。
至此,在明清之际情思潮时代背景下《红楼梦》挺立出“情情”范畴。“情情”不仅以“空空”“茫茫”“渺渺”的形式表现了境界嬗变中的形上域,也以自我消融的精神试图沟通形上玄冥与形下诗情,形成了“情情”的和合之境:澄明与诗意。这种宇宙境界以荒唐意识和诗赋谶谜的形式分别体现“情情”在“浑沌”“无无”“无用”上的道家旨意以及无我随缘上的佛教解脱精神,并在“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修成圆觉”等层面呈现《红楼梦》“情空相即”“以情融理”“情梦相摄”的“情情”境界和哲学视阈。
四 小 结
虽然新红学兴起之际,《红楼梦》的思想见地和精神价值时常受到一些质疑,然而从旧评点派将其作为“悟书”评介到后来王国维等人将《红楼梦》放入哲学和宗教学视阈中进行研究则提供了另一条诠释途径。而曹雪芹本人也在开卷不久即点出此书“大旨谈情”“以情悟道”的主旨并用大量的儒佛道的术语来展示所悟之道。这些为《红楼梦》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依据。在明清情思潮背景中,《红楼梦》凸显“情”的问题并将宋明理学以来的许多重要范畴放入小说语境中来重新思考和定位。通过“情-空”“情-理”“情-梦”等多重对话形式,《红楼梦》展现了“情空相即”“以情融理”“情梦相摄”的精神意蕴。以“情”问题为核心来融摄儒佛道的思想资源并实现三教重要范畴在小说视阈下的论域转换,从而使三教冲突的价值观在特定的小说语境中得以融构并呈现独特的“情”哲学形态,表明《红楼梦》作为一部“悟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儒佛道三教理论基础上的小说形式的哲学表达。
可以看到,《红楼梦》哲学在承继以往儒佛道三教思维的基础上试图反思宋明理学末流工具化之“理本体”并尝试在小说语境中构建以“情”为本体的新哲学的构建,这不仅回应了中国古代哲学长期隐匿的尚情主义的传统,也拓延了宋明理学以降的传统论域,成为明清情思潮语境中新哲学的开掘。这为《红楼梦》置于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互动视阈下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