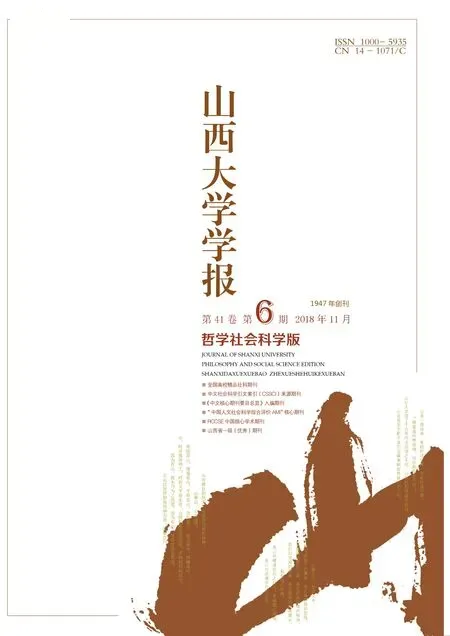民国文人的西安记忆与文学想象
王鹏程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袁枚在《赴官秦中二首》云:“闻道关中多胜迹,男儿须到古长安。”[1]149诚如袁才子所言,凡是读书人,没有不对古长安羡慕并充满向往的。长安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精神的芯片和中华文明的名片。”[2]338然而宋元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长安逐渐失去了全国的中心地位。以元初易名西安为标志,长安已由煌煌国都沦落为西北重镇。到了近现代中国,长安——西安,这座“灿烂中华文化的灿烂中心”,由于地处偏隅、经济落后、思想闭塞和文化保守,成为“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3]45但长安作为千年古都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文化遗存,却激发了一代代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走长安”,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民国时期的作家也不能置外,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充满期待地踏上长安古道,但西安的破败荒凉、凋敝落后,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安不见使人愁”的喟叹。
一 “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鲁迅等人的西安印象
1923年5月,北京女高师哲学部主任傅佩青和北大陕西籍学生张之纲受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函托,邀请北京著名学者7人来陕讲学,拉开了陕西现代学术活动的序幕。当时杂志上的讲座公告言道:
陕西向以交通不便,故名流学者之在西安讲演者,向未之有。自去年西潼汽车路告成后,交通稍便。今年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于五月间函托傅佩青及北大陕生张之纲邀请现代学者数人,来陕演讲,以提倡西北文化,并鼓励陕人研究学术之兴味。傅张二氏当即邀请七人——即北大教授美人柯乐文,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逷先,哲学教授陈百年,理科教授王抚五,哲学教员徐旭生,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吴新吾,女高师哲学部主任傅佩青——已于七月初抵西安。各界人士竭力欢迎。讲演时期由八日起。兹将诸学者讲演题目列后。至于讲演地址,闻在省立第一中学、教育厅及教育会三处云。[4]
确如讲座公告所言,陕西因交通不便,在西安到临潼公路通车以前,除了探险家和历史学家的寻宝访古*1923年9月,康有为游览华山后,到西安讲学,受到刘镇华的热烈欢迎。离开时因盗取卧龙寺宋藏经而致舆论哗然,是谓“康圣人盗经”事件。,鲜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柯乐文、朱逷先(朱希祖)、陈百年等人的西安讲学,开启了陕西现代学术活动的新的一页。
次年的5月8日,傅铜领大总统之令,由北京女高师哲学部主任转任西北大学校长。[5]上任不久,即有“拟藉暑期间延聘各大学教授来陕讲演,藉以宣传文化,输入知识”——筹办“暑期学校”之计划。傅铜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对牛津“造运动”即“为不能入大学者设法俾得略蕕高等学识之谓”深以为然,故云“此我暑期学校之所以设也。”[6]12同陕西教育厅长马凌甫商议后,傅铜呈明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得到允诺支持,遂去函邀请鲁迅赴西安讲学。傅铜委托的王捷三和王品青正在北大求学,他们知道鲁迅正拟创作历史小说,曾有去西安一游之意,便以“孔子西行不到秦”(元结《石鼓歌》)之语劝行[6]13,鲁迅慨然应允。1924年7月7日晚,鲁迅从北京西站乘火车出发赴陕讲学。同行的有《晨报》记者孙伏园、南开大学哲学教授陈定谟、人类学教授李济之、西洋史教授蒋廷黻、《京报》记者王小隐等13人。这样庞大强悍的阵容让西安的文化人充满期待。此外,暑期学校所邀学者还有东南大学教授陈中凡、刘文海、吴宓[注]被邀学者部分因故未到,实际来陕者和预告有出入。等人。暑期学校的讲座题目如下:
王桐龄: (一)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
(二) 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
刘文海:近世大国家主义
李济之:人类进化史
蒋廷黻:(一)法兰西革命史
(二) 欧洲近世史
李干臣:森林与文化
中国兵工问题
陈定谟:行为论
陈中凡:(一)中学国文教学法
(二) 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
(三) 读古书的途径
周树人: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
王来亭:(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源流
(二) 卢梭之教育观
夏元瑮:物理学最近之进步[6]7-9
这次暑期讲座的学者中,鲁迅无疑是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的一位。后来的西安也有情有义,西北大学集鲁迅墨迹的校名(新中国高校校名以毛体字为主,用“鲁体”者并不多见),西北大学校园内的鲁迅雕像,易俗社至今高悬的“古调独弹”牌匾以及津津乐道的鲁迅捐赠的五十元大洋等,足现鲁迅西安之行的影响和西安人的深情厚谊。鲁迅讲演的题目为“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实际上是《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缩编和精华,在某些论点和具体论述上,又有所发展而显得更加丰赡有力。[注]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写成,上册于他赴西安讲学前一年出版,下册于他赴西安讲学前一月印成。暑期学校开讲后,听众推举代表反映:所邀学者讲座内容与他们职业没有关系,加之无讲义和语言不通,收获甚微。据当时报纸报道:“暑期学校自开办后即有多数学员于学校大抱不满,盖听讲员大都系在小学教育界服务者,而其讲演则与小学教育毫无关系,结果不过为个人增添若干零碎知识而已。此时又因无讲义致不懂讲师语言者多莫名所谓,无法出席,故开讲之第二日即有人在黑板上大书‘既无讲义又无成书,言之谆谆,听者茫茫,师生交困,恐无好果’之语,其感于困难者可想而知,昨日全体听讲员已忍无可忍遂公推某君上讲台向众发表意见。”[7]众所皆知,鲁迅的讲演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很有魅力,但“中国小说史”这个题目学术性很强,再加之听众程度普遍不高(多为小学教师和军人),因而讲演的收效可想而知,当时报道也可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据1924年8月8日《新秦日报》报道:“报名簿上所书之七百余名听讲员,而每次出席者仅数十人,此外如下午之课堂钟点亦减去大半,且有数日无堂者,状颇萧条云。”当然,这也不能说鲁迅等人的讲座毫无意义,他们毕竟让这片古老而保守的土地沐浴到了现代学术之光。正如陈漱渝先生所言:“在绝大部分学员翘课而且天气酷热的情况下,鲁迅能够坚持授课到底,体现出一种‘韧’的精神和对学员高度负责的态度。”[8]其他学者也都能做到尽人事听天命,将讲座坚持到底,不辱教师之使命,也是难能可贵的。
鲁迅“走长安”的主要目的,是为构思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做创作上的准备。到西安之后,满目的颓败和荒凉,看不到丝毫的盛唐气象,反把以前的幻想都打破了。在同孙伏园出游时,孙看到西安到处都是木槿花,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都是白色的一大片,而别处也有木槿花,但多是红色的一两株,遂颇有感触,便对鲁迅说:“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的木槿花。”[6]70-71鲁迅静静地看着孙伏园,没有作声。估计这时他的写作计划已经作罢了。五六年后,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依然表达了“走西安”的失望——“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9]556不过,也不可将鲁迅取消《杨贵妃》写作的原因,简单地全归结为西安“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我们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生活场景从来不是他小说叙事的中心,他更侧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命运刻画,庶几可谓“心理小说”。《故事新编》所收的八篇历史小说,具体的生活和历史场景几乎完全被忽略掉。单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鲁迅完全是凭借想象写作,可谓典型的书斋写作,到不到长安,是不是“唐朝的天空”,似乎关系不大。但长安的颓败荒凉,的确让鲁迅踟蹰了。这也跟鲁迅的才情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他以心理分析为主的小说写法,人物较少,情节简单,适合中短篇的写作,倘要写长篇《杨贵妃》,唐代的历史情境、宫廷生活的具体场景、唐朝的风土人情与市井风貌,当然还有那位“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禄山,均不能不去考虑和处理。也许,鲁迅更多的踌躇在这里吧。大体而言,鲁迅对西安之行是不甚满意的。他在《说胡须》里说:“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糊里糊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10]183
如果说鲁迅在西安讲学的21天有所收获,那就是:尝试吸了一次鸦片,不过没得到什么灵感;西安的名吃羊肉泡馍和其他小吃也是尝过了;看大小雁塔,逛灞桥,游曲江,主要精力花在碑林和南院门街市,买了土俑、弩机、造像、拓片等;对京剧颇有微词、对梅兰芳热嘲冷讽的鲁迅,对秦腔却颇有兴致,接连到易俗社看了五场演出[注]鲁迅对秦腔颇有好感的原因有三:一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主管通俗教育,对移风易俗、与时俱新的易俗社颇为欣赏;二是秦腔同绍兴戏一样,慷慨刚劲,唱腔相近(有学者认为绍兴戏为秦腔旁支);三是易俗社主事者吕南仲为鲁迅老乡。。鲁迅此行留下的文字,除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日记、杂文《说胡须》与《看镜有感》、信札《致山本初枝》之外,还有为易俗社所题的“古调独弹”的匾额。有趣的是同行的北京《晨报副刊》记者孙伏园的记述:一天,他跟鲁迅去逛古董铺,见到一个动物石雕,认不出是什么动物。问店主,店主说:“夫”。孙伏园一脸茫然,鲁迅马上悟出是“鼠”。西安方音将shu读作fu。后来某天,鲁迅风趣地对孙伏园说:张秘夫(即张秘书)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11]。孙伏园对西安总体印象不佳,比如植被缺乏、文物保护不善等。但他觉得西安人不错,他认为从五胡乱华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乱,以及民国时期的军阀战争,斫伤了“陕西人的元气”,因而导致西安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这在智识阶级,或者一部分是关中的累代理学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过劳动阶级也是如此:洋车夫,骡车夫等,在街上互相冲撞,继起的大抵是一阵客气的质问,没有见过恶声相向的。”[11]这或许是他们碰到的西安人正好如此,实际同西安人的性格不合符节。孙伏园进而调侃说——“说句笑话,陕西不但人们如此,连狗们也如此。”[11]不禁使人觉得玩笑开得有点过了,对西安人有些不太恭敬。不过此行还是让他很兴奋的,他在《晨报副刊》连载的著名的《长安道上》,洋洋一万二千余字,可见感触良多。北师大教授王桐龄,讲座的题目是“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他对西安作了详细的调查访问,撰有《陕西旅行记》出版,分“长安之建筑”“长安之市街”“长安之实业”“长安之教育”等十二节,洋洋四万余字,兴味也不可不谓盎然。参加暑期学校讲学的这几位学者,乘兴而来,满目疮痍的废旧古都,难免让他们不满和失望。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了却了“男儿须到古长安”的蛊惑和念想,收获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陈中凡,感觉西安之行为平生“快事”——“游踪所及,举凡太华终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广,函谷潼关之险峻,曩昔所向往者,莫不登临,一览无胜,信足名生平之赏矣。”[12]
二 “到西北去”:“俨然是在太古时代”的陪都“西京”
1928年,民国政府提出开发西北的战略,很快得到全国的支持和呼应。政府当局和公民个人无不以建设西北为当务之急,一时间,各种关于开发建设西北的计划、方案、报告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炉,“到西北去”“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流行话语。他们或为西北开发和建设献言献策,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或游历考察西北,或到西北去工作,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作为西北桥头堡的西安,自然成为西北开发和建设的重中之重。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民国中央政府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并将西安易名为“西京”。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西安更加受到重视。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西安发展受到的限制也很大。陇海铁路从1905年开始修建,1915年才通到灵宝附近的观音堂。1931年12月,方修至陕西潼关。1934年12月27日,陇海铁路终于通车西安。陇海铁路的开通,加强了西安与中东部的联系,促进了西安与中东部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人才流动,对西安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到西北去”“开发西北”的声浪里,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严济宽,同几个青年同伴来到了西安任教。在他的印象里,“西安的民情,十分淳厚,崇尚朴质,不事浮华。从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性情是刚强的,直爽的。不像南方人的滑头滑脑,这一点还保存着古人的风度,在奸刁诡诈的二十世纪,这种人是不多见的了。可是他们也有短处,就是懒惰和吸食鸦片。”[13]他觉得,“西安人和西安的地方一样,是很古朴的”[13]:老人长袍大袖,飘飘然有古风;中年人也是长袍,不过款式多些;青年学生,夏天是白色的学生装,春秋是灰色的学生装,冬天,外面加件大衣。西装少年很少见,即使有,也是从南方来的。无论老年中年青年人,“他们所用的衣料都是棉制成的粗布,绝不用外国货的。……他们的朴素,就如江浙的乡下人差不多,这实在是一种极好的风气。”[13]尤其是西安学生的彬彬有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五四运动之后,旧礼教被打倒,不知不觉的把一般的礼貌也打倒了。于是学生不敬仰师长也成为习见的事情。但是在西安,学生们仍然是有礼貌的。他去看先生,必先敲门,见面,一立正,然后讲话,讲完话后,又一立正,始慢慢地退出。如在路上遇着先生,必一面鞠躬,一面叫‘X先生’,等先生走过了,再向前进。这样有礼的情形,在现在国内是很少见的。”[13]他觉得西安学生的天资,似乎要差一点。比如严济宽上英语课时发现,有几个人把day读die,他纠正了几次,没有一点成效。[13]总体看去,西安的教育很落后,学校虽不少,但派别太多,缺少团结一致的朝气,成绩尤少。严济宽在西安工作了半年,对西安的印象是——“西安是个弥漫着古香古色的都市,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都是东方固有的东西。”[14]和他同去西安的几位朋友,是江南的时髦少年,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一到西安,他们就要大读其诗词歌赋,大卖其古董字画,俨然是冬烘头脑的老先生,足见这古老的都市,蕴藏着极大的复古的魅力。”[14]回到上海之后,他回想到西安的生活,觉得“俨然是在太古时代一般”[13],自己是从古代到现代穿梭了一次,“差别如是之大,这实在是梦想不到的。”[13]严济宽的所见所言,在外省人对西安的感受和印象中,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王鲁彦的到来——“蓦然有一个那么有名气的文艺家到西北来,的确是很使人兴奋的。”[15]1934年2月上旬,王鲁彦离开上海到陕西合阳县立中学任教,8月下旬转任西安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教师(其间,7月下旬回上海),1935年底回到上海。在陕西期间,他先后创作了《惠泽公公》《车中》《桥上》《鼠牙》《枪》等小说,《新年试笔》《厦门<地方印象记>》《叹骷髅选》(又名《巫士的打油诗》)《婴儿日记》《父亲》《西行杂记》《西安印象》《寂寞》《四岁》《幸福的幻影》《听潮的故事》《关中琐记》《驴子和骡子》等散文,翻译了波兰作家斯文妥珂夫斯基的长篇戏剧《阿斯巴西亚》[注]连载于当时在西安出版的《西京日报》副刊《明日》上。,“把这荒僻的西北介绍到外面去”[15],同时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这些作品都在省外发表或结集出版(多在上海)。鲁彦所看到的西安,破败荒凉,寒鸦丛集。他在《西安印象》中写道:
......西安的建设还在开始的尖梢上,已修未修和正在修筑的街道泥泞难走。行人特殊的稀少,雨天里的店铺多上了牌门。只有少数沉重呆笨的骡车,这时当做了铁甲车,喀辘喀辘,忽高忽低,陷没在一二尺深的泥泞中挣扎着,摇摆着。一切显得清凉冷落。
然而,只要稍稍转晴,甚至是细雨,天空中却起了热闹,来打破地上的寂寞。
“哇——哇——”
天方黎明,穿着黑色礼服的乌鸦就开始活动了,在屋顶,在树梢,在地坪上。
接着几十只,几百只,几千只集合起来,在静寂的天空中发出刷刷的拍翅声盘旋地飞了过去。一队过去了,一队又来了,这队往东,那队往西,黑云似的在大家的头上盖了过去。这时倘若站在城外的高坡上下望,好像西安城中被地雷轰炸起了冲天的尘埃和碎片。
到了晚上,开始朦胧的时候,乌鸦又回来了,一样的成群结队从大家的头上刷了过来,仿佛西安城像一顶极大的网,把它们一一收了进去。
这些乌鸦是常年住在西安城里的,在这里生长在这里老死。它们不像南方的寒鸦,客人似的,只发现在冷天里,也很少披着白色的领带,他们的颜色和叫声很像南方人认为不祥的乌鸦,然而他们在西安人却是一种吉利的鸟儿。据说民国十九年西安的乌鸦曾经绝了迹,于是当年的西安就被军队围困了九个月之久,遭了极大的灾难。而现在,西安是已经被指定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了,所以乌鸦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计算不清有多少万只,岂非是吉利之兆?[注]这里鲁彦指的“西安围城”,实发生于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鲁彦记忆有误。[16]
女作家王莹这一时期也在西安任教,在她的眼里,西安是“一个墓场似地荒凉的旧都”,是一个沙漠里的城市。有风时黄沙满天,她“迎着那沙漠里的寒风”,离开了这个闭塞落后而又热情淳朴的古都。西安的黄昏留给了她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天空卷着了黄沙的时候,在满是乌鸦的院落里,窗口飘进了使人窒息着的叫声,屋子是灰暗的,火油灯闪闪地在寒冷的风中飘摇着,心是那么沉着的。”[17]不过西安的女儿们,天真、可爱、俭朴,她们“恨许多女孩子缠脚哩”“恨许多抽鸦片的人哩”、讨厌“街道也不清洁哩”。她们 “有真挚的热情”“有坦白的心胸”“在天真的头脑里是不断地在织着美丽的梦”[17],把对社会的不满,一件一件告诉了外地来的女老师,给王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莹以女性自身的细腻和敏感,把握住了西安女儿们的灵魂。直至今天,西安的女儿们,跟王莹所言也差不了多少。
西安古迹,多如牛毛,“任踏一砖,即疑为秦;偶拾一瓦,又疑为汉。人谓长安灰尘,皆五千年故物,信然耶?”[18]游客最怀恋者为碑林、大小雁塔、华清池、曲江、昭陵四骏(另两骏被盗卖于美国)、秦腔、咸阳古渡、周陵,当然,大家对西安的名吃也很感兴趣,比如老童家的羊肉泡,味道甘美,令不少游客垂涎。生于江苏武进的上海美专教授王济远,第一次吃羊肉泡,就咥了一大碗泡馍和羊杂碎,并连吃三碟腊羊肉,觉得热辣可口、别有风味,赞不绝口。这样的早餐,于他“平生还是第一次。”[19]西安城墙和钟鼓楼的巍峨、方正、浑厚和严肃,几乎使得所有的到访者不由自主感叹它曾经的辉煌和建造时代的雄伟浩大。1934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捷克留学生普实克到西安旅行,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的第四十七章“曾经辉煌的城市——西安府”中,他详细记叙了西安城墙、城门、钟鼓楼、碑林、小雁塔、清真寺给他留下的印象。在他看来,只有城墙可以证明这座千年古都曾有的辉煌。他觉得“最好的时光是上午在城门楼上,观看太阳刚刚露出的笑脸”。他“最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是碑林”。他将西安同意大利和北京的古城做了对比,觉得西安周围因为植被的缺乏,不能像意大利废墟那样将古迹与绿色的植物协调,带给人美丽的感伤;也不能像北京的古城那样,“使人回忆起旧时光的宏伟壮丽”,令人感到悲哀。西安——“这里的一切都覆盖着尘土,宝塔像一座座畸形的雪人站立在肮脏的工厂院子里。”[20]402西安和北平都是古都,都爱刮风,“只是西京的味道和北平不同。人们多欢喜北平,到西京的人都怀有莫奈何的心情,最欢喜西京这个地方的大概只有考古学家吧。”[21]确实如此。历史学家和批评家李长之到西安首先感受到的,是人们口语的古朴醇厚,比如答应的时候从不用“是的”或者“唯唯”,用的是秦始皇用的“制曰可”似的“对”。比如买东西换货,伙计一定是郑重严肃地说“对”,而不是“好”“可以”之类。李长之所见,西安、咸阳到处都是吸大烟的。在长安住了三个夜晚,他觉得“这古城给人印象顶深的,是感觉宗教气息的浓厚,并且想见中国当时受外邦文化影响的剧烈。还有一点,就是一到长安,才对于唐代的文字,特别是诗,格外亲切起来。附带的,也了解唐代所谓隐士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他们隐是隐在终南山,就是京城的南城门外边。这样自然是很方便的,看了风景,却还不会和政局隔膜。所以大抵隐士是只有聪明人士会做的。”[22]
三 抗战中的西安:“文艺上的一片荒原”与艺术家的“中转站”
抗战爆发以后,到过西安的文艺界同人很多,有曹靖华、丁玲、田间、臧克家、宋之的、塞克、叶以群、崔巍、王震之、贺绿汀、左明、光未然、李初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叶鼎洛、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聂绀弩、徐懋庸、艾青、舒群、庄启束、方土人、吕骥、冼星海、向培良、吴奚如、徐迟等。不过,“大家对于西安似乎都无甚留意。滞留的期间大都很短。留下影响的因此也不多。”他们离开西安,或者去延安,或者去山西,或者去重庆,很快活跃起来,“到现在,西安依然是文艺上的一片荒原!”[23]诗人徐迟在三十年代后期感受到了西安现代化的一面。他下榻在当时西安最为豪华的宾馆西京招待所,这所当时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住宿的高级场所,不禁让他感叹西安同国内的其他大城市上海、重庆乃至国外并无多大区别——“我在西京招待所住了七天。暖气管,冷暖水龙头,弹簧床。当时,我坐在圆形的餐厅内,我想,除了空气干燥一点,这跟重庆的嘉陵宾馆有什么不同? 鸡尾酒之后,又出现了冷盘、浓汤,再后是猪排、牛排、鸡、点心、水果、咖啡,味道跟重庆的胜利大厦又完全相同。”[24]304这种极为有限的现代和豪华在当时中国都市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现代与前现代的城市景观并存。正如林语堂所记:“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爱国志士,和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店和现代豪华‘中国旅行饭店’。”[25]161940年茅盾行经西安,写了《西京插曲》和《市场》两篇游记。他看到遭遇空袭的西安城房倒屋塌,到处残垣断壁,店铺书肆上摆放着乱七八糟的书籍,妓院卷帘待客——“夹在两面对峙的店铺之中,就是书摊;一折八扣的武侠神怪小说和《曾文正公家书日记》《曾左兵法》之类,并排放着,也有《牙牌神数》《新达生篇》,甚至也有《麻将谱》。但‘嫖经’的确没有,未便捏造。……在这‘市场’的一角已有了‘实践’之区。那是一排十多个‘单位’,门前都有白布门帘,但并不垂下,门内是短短一条甬道有五六个房,也有门帘这才是垂下的,有些姑娘们正在甬道上梳妆。”[26]353徐迟、林语堂、茅盾笔下的西安,是古色古香的古都,虽有零星的现代气息,但总体上破败不堪、百业凋敝、教育落后、文苑荒芜,没有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洗礼,是一个在经济思想和文学上与外隔绝的孤立的闭塞的盆地。
1940—1945年,女作家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注]《黄河》是当时西安影响最大的纯文艺刊物。。她对西安有着详细的观察,对女性的命运尤为关注。在她的眼里,在西安可以看到“两种情调不同、相差两个世纪的女人”:一种,“是代表十八世纪的女人”,“她们一双裹得像红辣椒一般的小脚,走着东倒西歪的步子,夹在人丛里面,时时都有被挤倒的危险。”[27]另一种,“是代表着二十世纪时代的新女性”,“她们穿着和男子一样的军装,打着裹腿,扎着皮带,穿着草鞋,走起路来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着胸膛,两眼直向前视。她们是正在中央战干团或者劳动营受训的‘女兵’”[27];还有无数穿着中山装或学生装的女性,有的是机关的公务员,有的是在校的学生。这两种不同的女性,常常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小脚老太们永远想不到会遇到小姑娘这样的“天足”,这些和男人一模一样的小姑娘,在她们的脑海里,“不但是个奇迹,简直是个神话。”也有开明的老太太,诅咒“自己已死去了的黄金时代”,但少之又少。比如,邻居一位开明的老太太,就不让自己的孙女缠足。在她看来,现在是大脚时代,“世界变了,缠足不时髦,再说跑警报也不方便呀。”[27]女人们很少出门,即使跑警报,也用头巾包得严严实实,尤以回民为甚。因此,在西安居住,要找到一个老妈或者奶妈,很是困难。蛮大的城市,没有荐头行。仅红十字会街有两家介绍河南妈子的挂着牌子,大车家巷张老太介绍本地的老妈子,但没有挂牌,非有熟人介绍不可。而外地人,几乎都不习惯本地的老妈子,“最大的原因是语言不通,其次是价钱太贵(她们要比河南女工贵一倍或二分之一),不清洁,而且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回家。”[27]不过也有例外,谢冰莹用过的郭妈,除了喜欢偷东西贪小便宜外,简直无可挑剔。她个性强、爱清洁,从不糟蹋东西,思想进步,同情遭遇家暴的同性,关心战事,一看到主人看报就问:“打到哪里了?日本鬼快败了吧?汪精卫死了没有?”谢冰莹称她“真是个西安的老新女性”。在谢冰莹看来,西安“妇女教育还在萌芽时期”——许多家长送他们的女儿上学,并不是他们重视妇女应该与男子一样受同等教育,而是害怕女儿不读书,不能嫁一个比较有好地位的女婿,因此他们送女儿上学,为的获到一张可以当作嫁奁用的文凭。在女孩子本身,大多数学习也不认真,将大量精力花在选择时装、烫头发和染指甲上。抗战爆发以后,许多学生流亡到西安,大量文化机关设在西安,杂志也雨后春笋般出版,西安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提升,文化教育事业大为进步。可能是西安长期作为帝都的原因,一般人的思想相当保守,妇女受到严重的轻视,男女极为不平等,女性好似一件物品一样没有半点自由。妇女识字班,很少有人去;妇女活动,很少有人参加,从事妇女工作的,一般都是外省的妇女,“西安的妇女运动实在太沉闷了。”她担心,抗战胜利后,外省妇女撤走,西安的妇女工作岂不要停顿下来。[27]正如她所担心的,西安的妇女工作非但停顿了下来,而且很长时间也没有进步。直至如今,西安的“大男子主义”仍不少见,妇女的地位也没见得提高多少。
四 余论——走长安:“人未有不思故乡者”
民国文人的西安记忆与历史想象,是对这座千年古都的追寻与凭吊,更是对这个民族过去辉煌的确认,自然也蕴含着对这个曾经文明发达的民族未来的殷切期待。因此,无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量外国人都对这座千年古都有着无限的兴趣。这从普通游客对西安的钟情和国外政要将西安作为访问首选之地不难看出。在林语堂以西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朱门》中,主人公李飞将西安视为“中国传统之锚”。虽然西安面临着由千年古都转变为现代都市的“混乱紊乱”,但“他就爱这一片纷乱的困惑”。在他事业受挫、感情失意离开西安之时,西安成为他生命力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林语堂这样写道:“他永远是西安的一部分,西安已经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西安有时像个酗酒的老太婆,不肯丢下酒杯,却把医生踢出门外。他喜欢它的稚嫩、它的紊乱、新面孔和旧风情的混合,喜欢陵寝、废宫和半掩的石碑、荒凉的古庙,喜欢它的电话、电灯和此刻疾驶的火车。”[25]161李飞的这种矛盾心理,实际上也是无数中国文人追溯历史、确认根源的隐性情结在发挥作用。民国著名文人易君左在《西安述胜》中言道:“夫游西北即等于还故乡,西北者,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人未有不思故乡者,况久飘零异域之游子乎!”[18]他说的“西北”,实际指的是“西安”。令人忧郁和伤感的是,无数的追慕者乘兴而来,辉煌的古长安杳不可见,亦无法寻觅,只能看到斑驳亏蚀的城墙和汉唐陵阙,终了只能重复那千年不变的惆怅。从鲁迅开始,民国文人的“走长安”,哪一个不是带着一腔愁绪离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