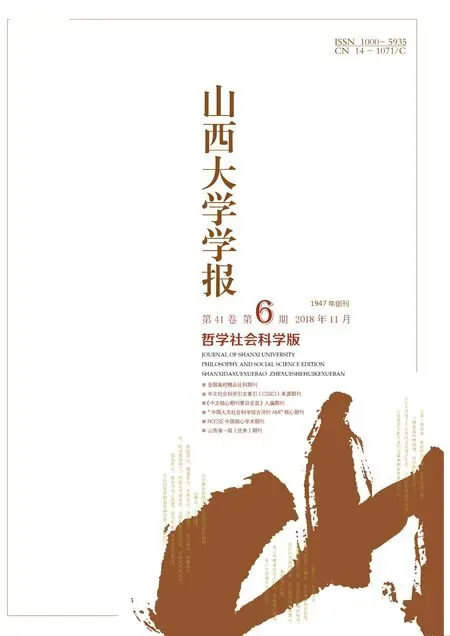张爱玲《心经》色彩意象发微
杨 韵
(名古屋大学 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日本 名古屋 464-8601)
一 引言
《心经》创作于1943年夏季,并于同年刊登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相较于闻名遐迩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名作,《心经》因其佶屈聱牙的措辞及晦涩难懂的立意一直未受重视。傅雷(1908-1966)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直言:“《心经》一篇只读到上半篇,九月期《万象》遍觅不得,故本文特置不论。好在这儿写的不是评传,挂漏也不妨”,可见傅雷对于《心经》一作,并未给出有如《金锁记》般“最圆满肯定的答复”[1]。
尽管如此,傅雷亦肯定了张爱玲(1920-1995)对作品整体“结构、节奏、色彩”的把控,并认为其刻画人物心理的写作技巧是出类拔萃的[1]。桑岛由美子在傅雷的基础上提出张爱玲具有与传统美学(美即悲哀)相悖的、“拒绝和谐与规整”的审美观,且这别具手眼的审美也如实反映在张爱玲的色彩意象书写之中;因而,其色彩意象书写兼具了“信息传递性、色彩构成主义、西欧近代绘画技法、近代审美意识”[2]等多重特质。黄擎则通过考察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回旋叙事结构,指出其具备“意象回旋、代际回旋和色彩回旋”的三重回旋特质,更进一步指出此回旋构造不仅串连了《传奇》的叙事空间与文本空间,更展现了张爱玲独有的、“进化论孕育下在中国扎根、萌芽的线性发展观”[3]。此外,邵迎建[4]、李欧梵[5]、池上贞子[6]等海派张学研究者对张爱玲的审美哲学也有所论及,于其独到之处亦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然而,关于张爱玲作品中色彩意象解读的论著依旧有限。赵静剖释了《传奇》中的绿色意象,并指出此意象同时兼备明与暗两种性质,分别在映射出主人公对生命、爱之渴望的同时,也阐发了主人公对死亡、孤寂的绝望之情;同时,赵氏亦认为这两种迥乎不同的性质均系“苍凉”色调之再现。[7]刘柯则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意象群,认为张氏调动其丰富的色彩语言叙写小说,是意图向读者展现“一个图画的世界”,更是其压抑、悲观、忧郁心境之感官再现;刘氏亦指出,张爱玲的色彩语言绝非单一的主观叙述,而是其心灵与中国古典文化、西方现代绘画、心理学技法的中西交融。[8]此外,赵京立[9]、徐丽燕[10]等亦就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进行了分析整合,但有关《心经》色彩意象的深入研读之作仍未有先例。
因此,本研究以细读文本的方式,着眼《心经》中的色彩意象书写,并将其划分为衣饰色彩与装潢色彩书写,重点解读孔雀蓝、樱桃红、硃漆红、青白、桃灰、柠檬黄、珠灰、阴灰、黯青、病色之意象。同时,本研究亦以剖判《心经》中女性人物之内面世界为目的,对隐匿于色彩意象书写中的关键信息进行寻踪觅源式精密处理,并逐一诠释其缘由,力图还原出许小寒、许太太、段绫卿三位女性人物的心象交迭变化,进而切近张爱玲之写作意图,并分解《心经》文本空间中的双重禅心结构。
二 《心经》之衣饰色彩解读
(一)孔雀蓝、白——苍凉、放逐、纯真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1828-1893)认为,人类对色彩的感知原为一种本能,而对色彩意象的认知则为“以生命直观为特征的色彩艺术创造”[11];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色彩意象源于作家的认知本能及生命演绎,投射了作家对其生命美学的感知、感悟与淬炼。张爱玲在散文《自己的文章》中对其生命美学亦有所阐扬,她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12]9。许子东则进一步指出,“张爱玲的意象技巧,和贯穿其作品的美丽的苍凉感有关”[13],认为张氏构建的意象灵魂便栖居于“苍凉”。《心经》亦是如此。文章开篇,张爱玲便借一袭孔雀蓝衣衫为许小寒祸福未卜的命运定下了苍凉的色调:
小寒穿着孔雀蓝衬衫与白袴子,孔雀蓝的衬衫消失在孔雀蓝的夜里。[14]104
在“没有星,也没有月亮”[14]104的浓浓夜色里,小寒的孔雀蓝衬衣与同样孔雀蓝的夜浑然一体,勾画出无尽苍凉的色调,此处谓之暗色。黄倩认为,孔雀蓝色是“张爱玲的挚爱”,张氏与孔雀蓝之渊源,可追溯到1944年她为《传奇》所设计的孔雀蓝色封面[15];张爱玲在散文《对照记》中也有提及,“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16];陶方宣指出,张爱玲不仅曾穿着一条“和《传奇》封面同色的孔雀蓝裙子”参加聚会,且在其为数不多的遗物中,也有一件她“最爱”的孔雀蓝镶金线的上衣[17]14。可见张氏记忆中的孔雀蓝意象,是《传奇》“浓稠”的封面,是聚会的裙子,亦是她心爱的镶金线上衣。《心经》作为《传奇》中唯一出现过孔雀蓝色意象的作品,承载的亦是这份贯穿张氏生命始终的浓稠、厚重与苍凉。引文中小寒所着孔雀蓝衬衣之暗,意在暗示她往后的情感征途时乖命蹇,在爱别离苦中延口残喘,最终被生母放逐之必然性。
而小寒所着袴子的白色则与孔雀蓝的暗色调形成鲜明对照,谓之明色;此色与张爱玲在小说《金锁记》[14]125-162中“白色的寒天”、《花凋》[14]238-286中“乳白的肉冻子”、《色戒》中“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18]、《怨女》中新娘子“头上像长上一层白珊瑚壳,在阳光中白燦燦的”[19]27-28、散文《私语》中“高大的玉兰花,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手帕,又像废纸”[12]73等作品中充斥着寒冷、死寂、拘囚、空洞、污浊的白色意象迥然相异,更贴近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个是白玫瑰,(中略)是他圣洁的妻”[20]中纯洁、无瑕的表征意义。滕守尧认为白色意象既象征着“纯洁和幼稚的儿童和女性”,又象征着丰富性与虚无性的二项对立,是兼备了双重心理感受性之色彩。[21]同理,小寒所着白袴子之意象意在营造出小寒天真烂漫甚至懵懂无知之形象,并着重渲染出小寒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孩童心智,为其后孔雀蓝色的苍凉命运色调的舒张、蔓延伸枝散叶。
(二)樱桃红——娇媚、风流
如上明暗对比在《心经》的色彩意象书写中还有多处可循,这既昭示了张氏“参差对照”[12]92-93审美哲学之内在理路,亦阐明了其对色彩表征作用之独到见解。如绫卿着一身惹眼的樱桃红色旗袍登场,与小寒苍凉的孔雀蓝色衬衫之对比亦是显豁。
一个颀长洁白,穿一件樱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绫卿。[14]104
张爱玲赋予了绫卿颀长躯体、粉妆玉砌的洁白肌肤,刻画出绫卿与生俱来的身材优势。同时,身着樱桃红色旗袍的绫卿更颇具唐寅(1470-1524)笔下桃花仙的风姿:“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中略)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22]唐寅笔下的桃花仙脱越浮世,闲庭信步于花酒之间,这与外表上看似沉声静气、安然自得的绫卿确有共同之处;究其依据,在《私语》中,张氏曾征引了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的儿歌——“桃枝桃叶作偏房”,并品评道:“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12]144-145,暗含隐居生活虽妙,“桃枝桃叶”却惜为他人侧室、不胜唏嘘之意。而绫卿相较唐寅的桃花仙也更为妖婉——明艳的樱桃红旗袍色泽饱满,衬托出绫卿的成熟韵致,确有张氏所言“不大像儿童”的风韵。对于此樱桃红色意象的调控,张爱玲更巧妙运用了色彩学理论中“色彩联想(Association)”之心理效应,即人类对特定色彩所产生的自发性、普遍性联想[23],将绫卿之人物形象与樱桃红“明曦、秀丽、浓艳”[24]的色彩意象同符合契。如此风姿绰约的桃花仙,自是引得他人驻足痴望——不由得在绫卿的娇姿媚态中流连忘返,“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而不自知。
除却旗袍,绫卿所佩戴的耳环亦为高亮度的樱桃红色。
小寒伸手拨弄绫卿戴的樱桃红月牙式的耳环子,笑道:“我要是有绫卿一半美,我早欢喜疯了!”[14]104
此处樱桃红色意象之迭用,印证了张爱玲对自身“葱绿配桃红”[12]151式参差对照的写作理念的深入贯彻,更可察知其对绫卿这一人物形象的双重象征性意象的铺排考量。在张氏所构筑的色彩意境中,“葱绿”“桃红”作为其参差对照写作技法的二元母本,衍生出浩大繁复的色彩意象群——樱桃红亦即桃红母本之衍生产物,以相承载前述张氏审美哲学之内在理路。而在当代华语圈中,以桃色暗喻男女间风流韵事的例子俯拾即是,《现代汉语词典》便将“桃色”一词释意为“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关的”[25]事物。《心经》中,绫卿初登场便着同色系旗袍并佩戴同色耳环亮相的安排也是张爱玲有意为之——意在以樱桃红色意象塑造出绫卿柳娇花媚之形象,更意图为桃色衣饰缠身的绫卿日后自甘堕入与许峰仪的桃色情感漩涡的决意埋下伏笔。
由此可见,张爱玲通过对樱桃红色意象的双重营造,构建出绫卿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内在勾连,即绫卿娇媚风流之主体形象与插足他人婚姻之客体形象的双边性、必然性的色彩意象回环。借由此色彩意象回环的承结效用,可探知张爱玲对破坏自身家庭完整性的第三者(如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的消极联想及潜在排他心理倾向。如此心理倾向,在《私语》中亦有所体现:当她得知父亲张志沂(1896-1953)与孙用蕃(1905-1986)再婚的消息时,她写道:“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阑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12]153。
(三)硃漆红、青白——情爱、畸形
然而,对于《心经》中父女情怀的刻画,张爱玲则选用了较为宽宥、率直乃至稍显稚拙、偏执的构建笔法,勾勒出小寒对峰仪盲目的爱慕之情。
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硃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14]104
顾蕾指出,小寒对峰仪的爱慕之情基于崇拜[26]59。而笔者认为,这种带有父权崇拜性质的情感的确是存在的,甚而带有病态色彩。进一步说,小寒对峰仪的情感诉求可沿流讨源自张爱玲对父亲的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1937年,遭受父亲毒打及软禁的张爱玲被困空房半余年,而软禁张氏的房间里恰有一面“青白的粉墙”。张氏将这面墙形容为有“黑影(父亲)”出没的、“片面的、癫狂的”墙[12]154,行间字里流露出对父亲的愤懑与失望。因而在《心经》文本空间的构造过程中,张爱玲亦显现出源自1937年其本人的这段“意识性无意识记忆(Recollection from unconscious memory)”[27]之病理化倾向——即其挥之不去的父爱缺失记忆机制及当自此始的病性转化之潜在表现形式,且此病性转化进程随着小寒对父爱渴求的不断加剧而呈递出正相关趋势。小寒的花洋纱袍子之配色即能阐明一二。
此衣由轻盈之质地、绮丽之配色及诡异之纹样构成,主色为硃漆红。关于张爱玲作品中的硃漆红,笔者曾考察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红色意象,并认为其功效有二:彰显使用者身份[28];塑造使用者心狠手辣之形象[29]。此外,小说《茉莉香片》[14]中的“硃漆楼梯扶手”、《怨女》中的“硃漆描金三脚架”[19]39则弥漫着颓唐、落寂的旧式苍凉,这皆是植根于张氏同样颓唐、落寂的家族记忆中的苍凉色块。而小寒的硃漆红袍子则意在表达她对生父近乎病态、癫狂之情爱,以及其郁抑不申、欲壑难填之诉求。这与唐代诗人殷璠(生卒年不详)所提倡的“兴象”之意象理念不谋而合,即“精神对物象的统摄”,抑或主观意识的“喻情”作用[30],这亦是张爱玲文学中习见的色彩意象表现形式。同时,张爱玲更是营造出“青头白脸的孩子”纹样的怪诞诡奇之感。此纹样之怪诞,在于孩子清一色青头白脸的设定,而这设定与拥有孩童心智、“神话里的小孩的脸”[14]的小寒本人相通,属于当代诗人流沙河(1931-)所定义的“喻象”,即以比喻修辞为主要手法“创造的喻事、喻情、喻理之象”[30]。根据此意象定义,此处可诠释为“小寒=青头白脸的孩子”。
究其缘由,小寒着红袍示父,是为求向峰仪示爱,更是向峰仪传达自己的爱意:见衣如见人,见童如见己——她想用全身的硃漆红、满身的孩子脸纹样让峰仪眷注自己,正如同张爱玲对父爱的渴望。可孩子脸纹样的配色却为青白,这在中国古代道家的阴阳五行理论中被判辨为不祥之兆。譬如,《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上》便有所记载:“时则有青眚青祥”[26];而关于“眚”的释意,汉书原文亦有阐明:“甚则异物生,谓之眚”[31],由此可知,青眚隐喻有不祥之兆的异物。小寒的青头白脸纹样的衣袍依照此五行理论,亦可融会为畸形、不祥之意,更可疏解为小寒本人对峰仪的爱和崇拜已然异常,是不清醒、不理智的病态之举。
张爱玲借助对“小寒=青头白脸孩子”的意象营造,完成了潜在自我与小寒的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她将自身的厄勒克特拉情结通由控制小寒这一人物的恋父行为表达,“强迫”[32]自己实现对小寒之情感需求的转移及投射。在此过程中,小寒作为被投射的客体,承担了转移的主体即张爱玲的部分病理性情感需求之作用;而张氏亦通过掌控此投射性认同行为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身父爱缺失的病理性情感需求。可见,小寒的花洋纱袍子之配色是极具精神病理性象征意义的。
(四)桃灰——韬晦、隐忍
小寒的病性恋父情结令许太太不得不过上离群索居的生活。从她的日常妆扮来看,许太太对女儿与丈夫的私情并非一无所知,而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选择退徙三舍。
许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细格子绸衫,很俊秀的一张脸,只是因为胖,有点走了样。[14]
滨田真由美指出,灰色在揭示女性人物欲言又止、屈心抑志的情感波动时发挥了独到作用[33]。如《金锁记》中“墨灰的天”“佛青袍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微微呛人的金灰”[14]等灰色意象均系如此。《心经》中,相较于灿艳的樱桃红、硃漆红,许太太的桃灰色衣衫有几分苍凉的色调。只是,此灰取桃色以调和,加绸缎之光洁柔韧以糅合,倒是隐没了桃色的妖娆、灰色的沉闷,涵育出极具许太太本色的色彩——不似小寒、绫卿般绿鬓朱颜、锋芒毕露,却又风韵犹存,不露圭角。同时,此桃灰色绸衫的细格子纹样,有如泾渭分明的棋盘线,星罗密布,网罗、监视着小寒的一言一动。由此可见,许太太看似对女儿与丈夫的越轨行为视若无睹、全身而退,实则仅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并布下了天罗地网,为他日东山再起静待时机。
然而,“俊秀的一张脸,只是因为胖,有点走了样”一文则暗含许太太如今受制于人的现状:一是峰仪的不即不离——虽保全了许太太身为许家正妻的名分,却薄情寡恩;二是小寒的若即若离——虽不至于毁冠裂裳,却公然与她分庭抗礼。这于许太太来说无疑是万般无奈的,正如那蒙上了灰色阴影的桃色一般,颇有白璧微瑕之意。此外,从许太太“九岁的孩子,早该睡觉了。还不赶紧上床去!”[14]的对白可获知,许太太对小寒的若即若离是隐忍的,甚至在隐忍中假充着溺爱。顾蕾将许太太的隐忍评释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且无论是许太太自己还是小寒所必需的隐忍”[26]65-66。但笔者认为,许太太的隐忍不过是其制衡小寒的策略,与小寒的自身诉求并无牵连。她的制衡策略完全取决于其本身,这与其所着的桃灰色绸衫无异,是一种以灰掩桃、以瑕掩瑜的自保手段。其目的有二:避免家庭纷争,维系家庭和睦,以此巩固其许家夫人之地位;在以静制动中谋求以动制静之时机的同时,保全自己与峰仪的情分,以此打击小寒与峰仪的私情。
无论如何,许太太的桃灰色绸衫发挥着近似保护色的作用,是其代表色之一,亦是其表明主观意愿、在被动中谋求战略主动的意志体现。
三 《心经》之装潢色彩剖析
(一)柠檬黄、珠灰——冲突、对立
客室的柠檬黄+珠灰配色不仅呈现出许家日常的生活样态,更显露出小寒与许太太临军对阵、且小寒微占上风之现状。
客室里,因为是夏天,主要的色调是清冷的柠檬黄与珠灰。[14]
此处,柠檬黄与珠灰的配色可分别析义为小寒与许太太的代表色。
一方面,滨畑纪运用色彩生理学理论阐明黄色意象在表达人物的“爱情需求”、尤其在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情感需求中发挥了情动作用,属于前者对后者的服从性与冲动性的自我主张之体现[34]57;而这与小寒对峰仪的情感诉求相契合——小寒在对峰仪的情感表达上向来是胆大如斗、破釜沉舟的,这是她对峰仪父权权威的绝对服从、绝对崇拜之具现。因此,柠檬黄为小寒代表色的主张是成立的。另一方面,刘菲认为黄色在中国古时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色[35],是阶级性、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反观珠灰,与许太太所着的桃灰色衣衫同为灰色系,具有进一步加深许太太在母女之战中尚处劣势、处处隐忍且受制于人的形象之效果,系许太太之代表色之二。相比代表特权阶层的黄色,珠灰显得黯然无色、霞光尽失,是下级阶层的代表色。但须强调的是,《心经》中母女之战的阶层结构并非永久固化,而是流动、可逆的。在散文《天才梦》中,张爱玲曾流露出对珠灰一色的爱重:“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12],可见张氏对珠灰的表征之意是持肯定态度的。同理,珠灰因其色带有珠光,也暗喻许太太卷土重来会有时之必然。
然而,张爱玲着意取“清冷”一词修饰柠檬黄、珠灰二色,在于点破小寒与许太太分庭抗礼、相持不下的窘境,说明小寒和许太太间的明争暗斗俨然成了许家的“主色调”;且她们纷至沓来的争斗,并未因夏天的到来而有所缓和,反倒带来了不合时节的“清冷”——这无疑是张爱玲式的反讽艺术表露。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小寒在察觉到峰仪与绫卿婚外恋时客室地席的配色。
在他们(小寒、峰仪)之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与珠灰方格子的地席(中略),零乱的早上的报纸……[14]
此处,柠檬黄与珠灰的配色运用了喻象的技法,将小寒愁肠百结、心寒胆碎之心境形容尽致。首先,地席的配色与前述主色调相符,但其象征意义却和而不同。其和在于同借柠檬黄和珠灰的明暗对比暗讽小寒与许太太的母女相争;而其不同则在于此阶段,即小寒知晓峰仪婚外情一事之际,对许太太已然有冰释之意“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怕谁?恨谁?她母亲?她自己?她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子的两个女人。”[14]的描述便是小寒有意与许太太重修盟好的最佳佐证。
其次,一直以来,小寒与许太太都是各据一方,但此格局以婚外情事件为契机被彻底打破。在小寒、峰仪之间隔着的“柠檬黄与珠灰方格子的地席”,象征着小寒与峰仪间长期存在却被置若罔闻的问题,即小寒与许太太间的矛盾已然图穷匕见:彼时,小寒与峰仪是同一阵营的,而许太太则如顾蕾所言,处于迫不得已的“母殺し(排挤生母)”之苦境[26]65-66。而此时,小寒与峰仪间嫌隙已生,他们之间隔着的物件便是其父女阵营彻底瓦解的有力证据。
然而,父女阵营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母女同盟的实现,两者指向的皆是虚空——这与万燕所言“‘心经’让人联想到梵语里‘虚妄’的主题”[36]是殊途一致的——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诠释的“空(缘起性空)”的核心思想[37]。到此,张爱玲初次迫近了《心经》一文的第一重禅心——般若空观视域下的禅那境性与美学意蕴,并将迄今为止的多元色彩意象逐步聚合、凝练、升华为极具张爱玲式禅宗色彩的审美情境,引导着文中人物进行心性调摄、心性淬炼与心性还原。
(二)阴灰、黯青、病色——黯澹、污浊、病态
《心经》后半段的色彩意象营造不仅充分表达了张爱玲迫近禅心的意志与决心,更充溢着张爱玲式的绝异“禅宗色彩”。王文娟认为,所谓禅宗色彩,即当为“禅宗理论的自然衍生和凸显”,且当是穿透离相、“体悟本真、但离妄念、本自圆成、心物两忘”之色。换言之,禅宗色彩系自然色彩与本真色彩的二元中和,即“无迹而空明的‘象惘’(虚空)”[38]。《心经》中,小寒有心与许太太联手扭转乾坤,许太太却无意与小寒重归于好——两者均为王氏所云“体悟本真”之尝试,即不加粉饰地直面真我、体味本我,进而逐步拓进“体悟本真”境界的主体性尝试。此主体性尝试,正是体证般若空观的必由之路,亦是张爱玲对引领文中人物走向心性的自我超脱的进一步尝试。如小寒只身前往段家拜访之际的色彩意境便是其呈现:
(段宅)是一座阴惨惨的灰泥住宅,洋铁水管上生满了青黯的霉苔。只有一扇窗里露出灯光,灯上罩着破报纸,仿佛屋里有病人似的。[14]
段家颓唐衰败,宅邸间的色泽明暗亦是杂然无序,这与段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相关,更与小寒悽怨不安、惨然不乐之心境相关。比如,在“一座阴惨惨的灰泥住宅”的书写中,“灰泥住宅”系对段宅整体色调的客观阐述,但“阴惨惨的”则系小寒个人的主观意识代入,更有妄诞之嫌;这表明此时小寒在“体悟本真”的主体性尝试中尚未达到王氏所揭示的“但离妄念”之境地,亦未走出张爱玲所构建的“心经”迷局,深陷晦暗。
同样晦暗的还有水管上的霉苔;“青黯”作为介乎青与绿、绿与黑的中间色,在色彩心理生理学中象征着“暂时性的无力冲动及禅学上的‘执空’(断见)冲动”[29];此色泽与阴惨惨的灰色前后呼应,以阴郁的笔致、暗淡的色调极尽描摹出小寒同样阴郁、黯澹且疲乏、偏执的心绪。不仅如此,无论“阴惨惨的灰泥”抑或“青黯的霉苔”,均弥散出肮脏不洁之感,这也印证出此刻绫卿之于小寒的感官印象——品行卑劣而龌龊、手段恶浊而无耻;也恰似绫卿所言,她是“人尽可夫”[14]的。但于小寒而言,从前的她是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的,哪怕绫卿宣称自己人尽可夫的缘由是为家计所迫。可如今,当这阴惨青黯跃入眼帘,小寒方才醒悟这令人作呕的一切竟是现实,不由对绫卿及其所为深恶痛绝。因此,此处的阴灰与黯青,起到了襄助小寒爬梳剔抉、认清现实之效。
此后的引文虽点亮了段宅的整体色调,却也暗意小寒此时的心理状态俨然病在膏肓。具体来说,“只有一扇窗里露出灯光”,且这仅有的光亮还因“罩着破报纸”而显露出病色,这说明了如下三个关键:其一,露出灯光的窗户仅仅有一,这体现出小寒认为自己重整旗鼓、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在于峰仪的自我主张;然而,这扇窗户却被设置在段家而非许家,亦表明峰仪现已心系绫卿,覆水难收。其二,“灯上罩着破报纸”既强调了段家的窘促,又映射出绫卿之于小寒如鲠在喉,是有如破报纸般遮盖住了小寒的光芒、拦路虎式的存在。其三,“仿佛屋里有病人似的”书写湮灭了段宅仅剩的光亮,意指小寒认为包括绫卿在內的段家人皆为“病人”、绫卿所为更是病态之举的潜在意识;不仅如此,此处书写更与前述的花洋纱袍子之配色遥相呼应,显露出小寒本人的病态心理。因此,此病色的指向是双向性的,既显现出小寒贬毁绫卿的潜在意识,又揭露了小寒的潜在意识本身即是异常、病态的事实,系《心经》中仅有的、明确通由装潢之病色揭示小寒病态意识之书写。
至此,小寒“体悟本真”的主体性尝试以失败告终,张爱玲却最终抵达了《心经》中禅心的第二重核心——通过揭露多元色彩意象的双向性病色及女性人物弃之不去的病态心象,进而实现对自身病性的体察、克服及超越;通过引导文中人物进行心性调摄、心性淬炼与心性还原,呈露出澄明自性、及除爱渴、哀乐两忘之参禅体势——这便是独属张爱玲的心象色彩,亦是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意象文化观中“来自于对‘心’的主观色彩意象”[39]之映现。
四 结语
括而言之,《心经》中的色彩意象书写不仅在配色上是极为考究的,还嵌入了个中人物的性格特质、心理状况等重要线索,是解读《心经》中女性人物之心象交迭变化、诠释张爱玲写作意图、分解《心经》文本空间中的双重禅心结构的关键所在。
具体说来,《心经》中的色彩意象绝非仅有苍凉之感,而是在苍凉中同时浸透着女性人物的绚烂与黯淡、纯真与世故、欢愉与悲切之心象风景,是苍凉而靡丽的。如衣饰之配色,将小寒性格之明朗,恋父之情切,命途之多舛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将许太太个性之隐忍、谋划之深远、手段之高明体现得栩栩欲活;更将段绫卿容貌之美艳、体态之诱人、艳遇之必然形容尽致。而装潢之配色,则将许家的母女之争,小寒与绫卿的亲友之争极尽描摹,更着浓墨重彩于其心理战术、心态变化、潜在意识之上,映现出许太太心机之深重、小寒心理之病态早已了然于目之事实。
然而,小寒、许太太、绫卿间的争斗历经了一个从理性到非理性、从被动到主动、从常态到病态的过程。在这冗长的过程当中,恒久不变的是峰仪选择的非固定性和必然性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峰仪见异思迁的时机、对象的非固定性及其朝秦暮楚、弃旧怜新之本性的必然性间的矛盾,致使小寒、许太太、绫卿互为替代、蛮触相争,在交替着满足家父长·峰仪一己私欲的同时,又成为彼此私欲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这退藏于秘的欲望鸿沟和瞬息万状的心象交迭变化,俨然是流动且不可控的;这使得小寒、许太太、绫卿在父权制社会这一阶层结构固化、两性秩序可控的樊笼下跋前疐后,更使得她们的同性竞争意识逐步激化、同性同盟意识被迫衰减,与倡导独立、自主、自强的女性意识觉醒之路渐行渐远,系丧失了主体色彩的、不完整、不彻底、非理性的女性亚文化群体(Female subculture)。
女性人物的主体色彩丧失,恰恰促成了张爱玲对《心经》文本空间中双重禅心结构的构想、构思与构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缘起性空”“色空不二”思想,阐释的是澄明剔透、色相俱泯、五蕴皆空的般若空观;而破除五蕴的实执、参悟般若空观的空明禅意,进而抵达澄明自性、心无挂碍之自在境界,则需要源源不竭的主体性修心、修行、修性——这亦是在探求禅理的进程中寻求真我的有效途径。张爱玲将文题定为“心经”,并将丧失主体色彩的女性人物置放于般若空观视域下的广博禅意空间之中,主要目的有三:第一、通由对小寒的投射性认同,试图寻觅小寒与潜在自我所缺失的部分主体色彩;第二、通过揭示许家父女、母女联盟的根本破灭,迫近般若空观的虚空之色并意图做出“体悟本真”的主体性尝试;第三、借助对多元色彩意象的双向性病色书写,呈露对女性人物及自我的双重病性认知和阶段性超越,体证对女性主体色彩的禅学颖悟。
可见,《心经》中呈现了一个别具匠心的多元色彩意象空间。尽管张氏并未就其所参悟的“心经”禅意加以直接阐发,却间接依托对多元色彩意象的营建,委实将其所知所感融入《心经》的二元禅意核心之中。从作品中对色彩意象的精致刻画与心象交迭之复杂呈现,读者似可察知张氏对女性独立人格发展趋向的哲人忧思,亦可觑见其对般若空观的禅意体悟,更可探寻其对潜在自我的病性超越之脉络。约言之,通由对《心经》色彩意象的多元表达的分析可知,张氏对色彩的体认可谓独特、深刻、饱满,描述丰富、贴切、生动,传神写照,有如诗眼,恰好体现出其超拔时流的独到的般若美学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学家群体中,诚罕有其比,无疑是值得深入省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