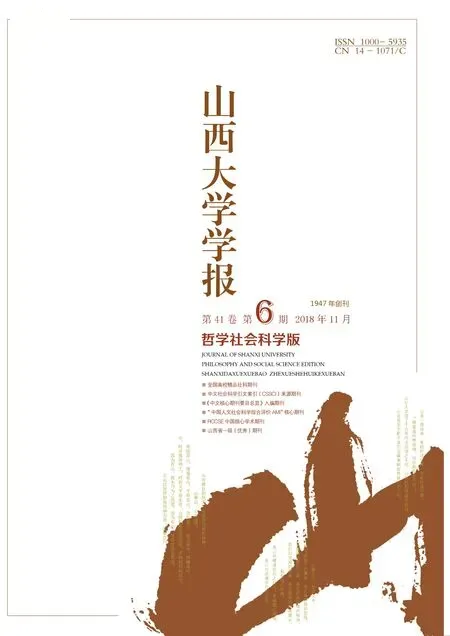义利之间:明清小说恩报叙事的复杂性
刘卫英,梁晓晓
(大连外国语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在古代的灾荒、御灾及其受苦受难故事中,有许多报恩、感戴救苦救难的民间传闻,体现出民间对于危难时“知恩图报”的推重,受恩不忘的诚信。受灾者需要救助,本质上与平日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境况类似,因而遭灾被难“受恩-感戴”与广义上的蒙恩酬恩异质同构。然而明清报恩书写,总的说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明清报恩书写与传播固然带有“以德报德”的正义性,也因其芜杂和必报之期、民俗习惯、时代局限、认知悖论等特征,难于反思。一直以来,由于强调民族侠义精神的需要,由于灾荒之中人们对受难民众的同情悯惜等等,人们更多侧重于弘扬报恩的合道德性伦理价值,知恩图报行为的诚信、侠义之可歌可泣,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报恩故事中隐含的利己动机、异常期待心理,特别是行为主体在“一报还一报”的因缘链接中,族群思维惯性潜在地销蚀着社会法则与伦理规范的影响力。这一悖论式报恩思维,与善与恶“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快乐与痛苦的情感”[1]176线性思维巧妙结合,迫使两难处境中的行为主体均以利己“优势战略”[2]为行为准则与生命追求。如此一来,绵绵不断的报恩及其影响就不再是“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简单存在状态,其深层意义如既定规则与行为主体的反规则等,值得思考。
一 恩义观念与恩报行为的习惯性模糊
报恩故事的基本分类中,“再生之德”与“一饭之恩”的观念性差异较为模糊,以其与自身利益关系更为密切,使得施受主体间的“施与报”关系备受关注。而故事文本所蕴含的文化精神,除了叙事主体的主流声音,比如典型的东方伦理观念,亦常带有“复调”,甚至“噪音”也时而萦绕其中,[3]主要是人治社会的“有规则”之下的无规则性。
首先,人在难中,得到哪怕举手之劳的恩惠,也期待必当酬报,且应以超值回报来酬答。说嘉庆年间,苏州某商携重资归乡,怜悯冒雨呼搭船者,引入舱换衣供食。那人恣意饮啖,商也毫无厌倦。数日遇群盗行劫,搭船人退盗,登岸离去。载录者认为“而商之遇险不险者,则不忍之一念为之也。”[4]本来接纳搭船,给予些衣食关照,不算太大恩惠,但可贵的是本真的同情怜悯,全无功利性的,就得到了侠客救命的巨大回报。
其次,受难者获得有意识的救命之恩,融合了“互利”因素,可能是模糊的义利关系。承继春秋战国报知遇之恩的史传传统,《水浒传》写施恩父子对牢犯武松酒肉供养,实因武松身处难中易于结交,利用他来打败蒋门神,夺回快活林。金圣叹评:“看他写快活林,朝蒋暮施,朝施暮蒋,遂令人不敢复作快意之事。”[5]其实就是争夺这一宗“好买卖”。于是有预谋的“投入”(施恩)与“产出”(报恩)是不对等的,武松后来能逃出蜈蚣岭,血溅鸳鸯楼并脱身带有侥幸性,施恩报恩动机都存有争议。
《聊斋志异》写猎户田七郎陷于贫困,田母仍对名士武承休善待七郎存有戒心,一再阻止七郎接受恩惠,担心“受人恩者急人难”,得了重赂今后恐怕要以死相报。的确,武公子是得到梦兆才有意识地同七郎结下恩义的。如非七郎因与人争猎豹摊上人命官司,武承休未必能如愿,而他这种结交下层豪士所用策略,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恩义投资”,解危急难,对方产生一种由衷的恩报冲动,在此强烈动机心甘情愿地急恩主所急,敢死轻生。东汉思想家王符体察到社会交往中这种普遍心理:“且夫恩怨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对也,恩情相向,推极其意,精诚相射,贯心达髓,爱乐之隆,轻相为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颈而不恨。”[6]但未明确说出实际上授受双方是有着等级之差的,这种“等级高低(贵贱)”决定了潜在单维指向,即下层侠士为有社会地位(有身份)者拼命,为此要先接受恩惠(有时不得已接受),进入“受恩→报恩”的伦理轨道——报恩实现。田七郎作为个体——“服从意识”的悲剧载体,其命运早在武田二人恩义关系确立时便已注定,武公子“重金买凶杀仇”成功在望了。因此但明伦从报恩实用性方面评点武公子择友:“所与皆知名士,可谓交游得人矣,而概目为‘滥交’;而以可共患难之一人,责其不识,而后郑重而出其名。轩轾之间,人品自见。彼七郎者……迨观其取与不苟,内外如一,其事亲也如此,其交友也又如此,一片赤心,满腔热血,此皆博古通今,摛华染翰,弋取闻誉者所不敢为、不能为、不肯为者,然后叹天下知名士何太多,如田七郎者又何太少也!”[7]697何守奇评曰如读《史记》的《刺客传》,方舒岩评也褒奖田七郎可比“古刺客”聂政。武公子的有意结交,导致七郎生活轨迹、社会角色的转变,报恩书写基于他较为卑微低贱的起点,将其定位于充当了有情有义的报恩“刺客”而确认他的人生价值,其实不够公平。
如果说田七郎是无奈地落入武公子预设的“被结交→受恩→酬报恩惠”伦理怪圈,那么《聊斋·崔猛》则写“位卑者”李申主动地机智地代为报恩。“喜雪不平”的崔猛代李申杀死诱赌夺妻的巨绅某甲后,李申被疑捕诬服论罪,崔猛自首、开脱李申。充军归后崔猛得到李申的帮助,但李申很难保证恩主崔猛不再招祸患,于是就代恩主崔猛去平不平,先故意与恩主闹翻[7]1660-1661。“有恩必报”,但实际上“一报还一报”的度量规则有时模糊、难于兑现。甚至必须置法于不顾,佯作不为恩遇所动或故意反目制造假象,扰乱执法者使其误判,只为避免连累恩主。在“报大于施”潜规则下,“以命相报”演化为报恩者人生的终极使命。而古代受恩义驱遣去杀人复仇的多下层人士,反映出下层民众企慕平等、友谊的情感需求,知恩必酬、不负知己的朴挚情感,这往往被蓄意利用。不难看出,这两类命运悲剧中,报恩者的心理与行为已超越了寻常的“正义”(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福利)与“非正义”(每个人得到了自己不应得到的福利或者遭受了自己不应得的祸害)[8]45,及世俗义利观念,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识,以“位卑者”抗拒宿命来实现个体自由。
其三,更值得警惕的是“一饭之恩必报”的观念,“一饭之恩”往往在被施恩者遇到饥荒、穷绝等困窘危难之际,诚然可贵,但“一饭之恩”如何来报?此与古代中原世俗崇尚凡事“有经有权”原则有关。有经有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指自然和人事遵循的不易之规,即常驻性规则;通俗讲就是有常规,但特殊情况则可变通。“一饭之恩”多被超物质意义解读。危难窘困时受人恩惠,这种接济从物质上看虽一饭之微,精神道义的“恩情债”可使受者终生感戴,报恩之社会“角色期待”,也乐于夸大、传扬“施小报大”、施恩一时而酬报于恒久。特别是在侠义崇拜的文学世界里,渴求理解、感戴知遇的心理诉求极易将“一饭之恩”泛化,从而将“一饭之恩”的偶然性精神意义看得过重,理解为人格价值确认。如《聊斋·雷曹》及其《丁前溪》《大力将军》等,皆是。蒲松龄曾注意到朋友之间的恩义关系,其价值唯有在危难时更能显现,《为人要则》中他理解:“急难,为兄弟言也,而朋友亦有之。古人云:‘得一死友’,盖一日定交,则生死以之,劳何辞,怨何避焉?友为五伦之一,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其人在,我扶其困厄;其人不在,我抚其子孙,此之谓‘石交’。设华堂之上,沥血倾心;一旦风波四起,哄然尽散,坐视颠危,而莫不一置念也者,五伦中亦何贵有朋友哉?故古人择友,友则两相关切。若酒肉相博,相与往还,此党也,非友也。”[9]前举《田七郎》武公子“结友买凶”的成功个案被充分美化了。而《雷曹》《丁前溪》《大力将军》等主人公也颇具古时“侠友”之遗风。施恩布惠者的择友交友,为的是彼此能在急难时行使朋友“共患难”的伦理责任;而承恩受惠者并不单纯地将前者视为恩主,亦将其看作可“两相关切”的石交契友。物质上的施予和承领是表面的形式,深层纽带是相知相契、“生死以之”的恩义关系。这种“关系存在”在平日仿佛不易察、不可感的一条“草蛇灰线”,危难时需要人挺身刃仇、代友理怨便骤放光芒。朋友恩义与交友价值,似乎也只有在这种危难时刻,才能真正检验出,才在报恩文化舆情中被言说、被书写。
其四,在旧有报恩逻辑的作用下,偶然之中有着必然性的认知误区,期待心理与报恩行为陷入循环怪圈。李渔《三与楼》第二回曾对报应或酬报感慨:“谁想古人的言语再说不差,‘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两句说话,虽在人口头,却不曾留心玩味。若还报得迟的,也与报得早的一样,岂不难为了等待之人?要晓得报应的迟早,就与放债取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钱;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报之心愈急,他偏不与你销缴,竟像没有报应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懒,丢在肚皮外边,他倒忽然报应起来,犹如多年的冷债,主人都忘记了,平空白地送上门来,又有非常的利息,岂不比那现计现得的更加爽快!”[10]如此根深蒂固的认知逻辑如罗素所说:“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事实上,它是一脉相承的价值观的逻辑结果。”[11]159-160由此逻辑而建构的报恩规则,常常是含糊不明的。而合乎伦理规范的报恩并无计量标准。如林琴南六七岁时从师读,师贫无米下锅,他就归家取米给师,师怒弗受。林母则呼佣赍米一石送师,后者乃受。[12]童子私拿米给师,质朴可爱,还是其母有见识,用盛情难却的“束修”古礼敬师。“知礼仪”固然重要,但将“一饭之恩”酬答的“礼教规定性”价值无限扩大,势必形成社会交往的巨大压力,可能使得一部分受恩者因情感债务的压力,而走向其他选择。
二 “施小报大”的高利贷心态
在明清恩报故事结构中,与恩义的观念性模糊相呼应的是,报恩行为的物质化与商品化。从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角度看,以金银量化的行为规则,其实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囿于传统恩报的“不平等”关系,报恩主体的思想观念与施恩者的心理期待滞后与纠结,其核心在于如何回报?有无价值标准?亚当·斯密曾认为,“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对于报恩行为而言,每一主体的劳动其“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是不同的[13]27。在中国古代一般也不这么看,一是索报有度;二是穷人受到了富贵人恩惠,多半要拿命来偿恩酬义。
首先,因得到回报者过于贪心,或无止境的期求,适得其反,断绝了曾拥有的恩义关系。此即民间AT750D型故事:“用取不完的酒报答好施者”:“一位神仙化装为乞丐经常到一家酒馆或饭店去行乞。在那里经常得到酒喝(有时吃东西),为了报答这种施舍,他把酒馆的井水变为美酒(有时是店主人要求的)。酒馆主人或饭店主人很快变富了。几年以后,这神仙重访这家酒馆,主人表现出同样的殷勤,但是表示对这神仙所给的礼物还不满足,往往是说没有可以喂猪的酒糟了。这位被激怒的神便收回了他的神奇礼物,井里的酒又变成了水。”[14]此类故事经常结合以神仙考验母题,侧重在针砭世俗之人期求施少报多,不劳而获。中国式的索报嘲笑贪婪的“点石成金”梦。冯梦龙《笑府》载一贫士遇故人,已得仙术的故人指砖成金相赠,嫌少,更指一大石狮仍不满足,问知竟愿得此指。昔日熟人“恩谊”其实有限,然而却有着无限的期待,关系必断绝终为路人。清代石成金《笑得好》则说某神仙以点石成金验看人心,不大贪财的就度化成仙。指大石变金,人仍嫌小。后遇一人,竟不要,仙问,其人却要把神仙的手指换给自己。憨斋士《笑林博记》卷三、方飞鸿《广谈助》卷三十等类似谐谑故事,仍在流传。[15]
报恩故事的“互利”书写指向,即显示出人性的弱点:索报贪婪[14]165,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性民间故事母题。如弥达斯(Midas)的神话,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为了报答,许诺国王弥达斯任何想要之物,弥达斯希望拥有“点石成金”术,于是弥达斯凡所触之物皆变成金子,他无法进食;有的异文称他无意中碰到女儿,女儿竟变成了黄金雕塑——他杀死了女儿。无奈弥达斯只好祈求狄俄倪索斯收回所赐点金术。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前43-18)《变形记》也重写了这一神话。故事昭明,贪欲一旦越过底线会带来悲剧性结局。“回报”过于巨大,以至于无法享受,由幸福转化为痛苦。“高利贷模式”索报原型还有《格林童话·渔夫与他的妻子》,来自博梅拉尼亚(波美拉尼亚,德国东北部的一个州,邻近波兰)神话,讽刺了妻子贪婪,导致受恩的神奇金鱼回报终结,变得一无所有。而俄罗斯诗人普希金(1799-1837)叙事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改写为老太婆索求持续膨胀,乃至图谋把报恩的金鱼变成奴役对象,要做海上的女霸主。[16]最后这个专横、有悖常理的老太婆又一无所有了。这一人物类型,成为人类无尽贪欲的文化象征:贪婪、残忍、自私、忘恩负义等。由此,对待报恩者的苛刻与无休止的索求,不可轻视,只当笑话说说。事实上,这些能自我膨胀的东西好比波涛汹涌的海洋,包围着人类及其家园:“家园与陆地无力同周围的大海抗衡……‘空洞的梦’在童话和长诗中表现为一连串利欲熏心的念头,从‘新木盆’到‘皇宫’:炫目的世界如幻影般展开——收拢。”国外研究者认为普希金的两个主题:“空洞的梦”和“上天对人间的戏弄”,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得到呼应,普希金的诗歌也对此非常重视。[17]故事主题也是反对不懈地追求更多东西,包括报恩期求的无休止扩大。而我们从有限资源与消费需求看,故事的生态伦理思想,特别具有现实意义。[18]
其次,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意为之的高利贷式索报。对此,当剥开一些明清小说的整体果报结构,可以更深刻解读其中长线“恩报投资”导致的人伦巨变,为其转恩为仇的可怕机制所震惊。说开货店的岑麟、鱼氏夫妇把侄子岑金当作亲子,十二岁在店帮手,十七岁为订亲卞氏(浑家鱼氏表侄女、幼年收为义女),而亲生儿子岑玉,书未读、生意不会做。精通买卖路数的侄儿侄媳(义女)提出分家。此前岑金也没少私下积蓄、约主顾。分家时撕破脸皮,岑麟不得不拿出三百两“劳务费”,侄儿岑金另开一新店。新店常把客户拉走,岑麟气病而死。借办理丧葬明慷慨、暗盘算,寡妇幼子又被占许多便宜。后遗孀鱼氏告状,让儿子串联岑金店俩伙计——都曾在老店做过伙计,一是岑麟本家族侄,一是鱼氏内侄鱼仲光的叔子,势利的俩人得了岑金财物,把贫穷孤儿寡妇撇在一边。岑麟、鱼氏夫妇当年的“施恩工程”,根本没有考虑到锱铢必较的商业氛围熏陶下,成年后的岑金有自己的利益团体,夫妻小家庭与伯父(施恩者)构成商业竞争,该会发生怎样的严重后果。且复杂的亲情关系、代沟隔阂,多年生活中形成的自卑、妒忌等,都在分家后逐渐暴发。也许,受“孝”“忠”“义”等传统伦理制约,世俗舆论易于刻板化地将感恩之情、恩报期待,缔结成“关系存在”,就伦理绑定了,难于理性思考。于是,逆向思维付之阙如,深层动因无法反思。“情感债”的多层次裹挟,往往又滋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利息”来。这也正是作为施恩者的老一辈岑麟、鱼氏过高期待所致,恩报、亲情纽带在世俗利益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当众亲邻在场,岑金索要母亲遗物时,伯侄达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19]长此以往所形成的社会潜规则,即报恩或行孝的违法违规行为,被社会舆情认定是可以理解与宽宥的,这在突出其教化功能时理直气壮,庄严得不容置辩,也留下了无法平复的漏洞,对借此设计机谋者留下了机会与理由,也为受恩一方带来了持久的内外双重压力。
再次,“江洋大盗”式报恩的利己务实。处于社会正统秩序之外的盗贼,似更了解江湖世界的复杂人性,也更理解生命意义。其报恩心理与行为常常显示出与社会伦理不同的道德规范,“同一事物可以同时既善又恶,或不善不恶”[1]169。“善恶”思想形式的模糊而又务实利己,其恩报行为呈现的惊心动魄与超常规亦不足为奇。宣鼎写淮阴粥店铺章楸范三娘夫妇,善待过路囚犯五人,温酒并尽所有来供啖嚼,针对北方人口味上了面食,众囚每人都吃了双份量,还供热水洗浴,众囚“但默询主人名氏,牢记而去”。秋,章楸忽被以窝藏罪押送姑苏与盗囚同系,方知是剧盗林黑儿一伙,将被处斩。次日林黑儿等急脱布襦给楸,告知埋宝处,刑前还不忘给章楸开脱。出狱后楸潜为五人厚葬,适时祭奠。归后拆布襦等皆金叶、珍珠,发窖藏得十万余金。作者评曰:“一饭之德,至死不忘,且报以厚贶。彼世之诵诗读书,往往身受人恩而动以反噬报之,林黑儿当哑然大笑于泉台地下也。”[20]故事属典型的“施小报大”套路。一是揭示出行为主体“无善无恶”行为的经济观念。在章楸,是遵守“面子”习俗:“每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贱的乞丐。如果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伦理准则,那就连乞丐也不能侮辱。”[11]161而对盗魁们而言,违法越轨所得“赃物”,借花献佛也好。二是,小农经济、市民阶层的商人心态之文学化书写,表现出非理性的违背礼法的报恩逻辑。试想,一个正常的理性社会,是否要提倡善良勤劳的百姓因一点普通人应有的同情心,对饥渴者提供饮食,就应该骤得巨宝、暴富?作恶多端的众盗魁,是否因临终前以赃物珠宝赠予得人,托付祭祀,就须得到持久、功臣般的酒食祭奠?这带有偶然性的报恩——施受故事的辉映下,数十年的勤勉经营,比不上一次随机性的善举;而抢劫杀人作恶半生的凶徒,只因劫来的赃物转移成功,就虽死犹荣,长久甚至几代享领供奉的馨香,这是否公平?那么,被盗首们抢劫、杀害的那些无辜受害者及其冤魂呢?他们生前辛苦得来的血汗财物甚至生命,成了盗魁们“报恩”交易的资本,公理何在?三是,侥幸心理、利己心态的线性思维。如狱吏检查出牢后多出来的衣物,藏有金箔、珍珠的布襦、半臂居然没发现?官员又能那么轻易相信盗囚出尔反尔,相信盗魁攀咬章楸是因“索伊酒肉不得,且以榴花枝挞我首,仇牵之来”?其实很简单地暗伏偷听,就会得知“醉饱至今不忘,且欲酬之大德”奥秘。而得宝暴富的章楸,偏偏要“移家姑苏,俾子孙就近展墓田,祭祀不衰。另作商贾,不复设酒肆。至今淮阴犹有艳其事者”云云,也不合情理:如此盗魁弃市的大案重案,就在姑苏本地审理、处决的,必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事隔不久,该案被攀咬又放出的“窝藏嫌疑人”,作为淮阴人,居然堂而皇之又回到异地姑苏城,且抛头露面地经商?他的故乡淮阴都罕有不知此事者,他居然敢为了子孙祭祀五位盗囚方便,就来到了结案之地?夸大报恩效应而滋生反社会倾向。
霍布斯曾说“财富就是权力”,而亚当·斯密的观点或许更准确些,他认为财产:“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13]27横行江湖的“盗囚”正是以其“不义之财”,践行着“施小报大”的社会规则。如果说“个体事物(人)”“可以通过人的现实本质”并“保持其存在的力量”。[1]173那么,恩报故事中的“高利贷”模式,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存在意义,则值得深思。如上故事虽不合礼法,却并不影响其传播乃至效仿,又于另一维度反证了明清“义利”观念模糊,甚至善恶观念有时也模棱两可,但报恩的行为逻辑其实应看得更复杂一些。
三 异类报恩的“好货好色”认同感
如果说,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一报还一报”规则暗含着“施与报”的不平等意识,那么,在人与异类的恩报关系中则要更复杂一些。事实上,在古代社会伦理规范的总体框架下,举凡异类——鬼灵神怪、“灵异”动物,往往被“以部分代全体”地置于人类中心的“他者”形象类型之中,报恩鬼灵、报恩动物自然也不例外。这类“报恩鬼”“报恩兽”形象常常是自我矛盾的奇怪组合,“它”为鬼灵时,每多为带有超自然力的诚信之人的角色;而为动物时,则大多出于本能的行为,却被灌注了人格化的恩报伦理动机。但在许多报恩文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报恩行为后,“文化他者”依旧存在着鲜明的“不如人”和“不周全”之处,突出其“工具性”特点,客观上成为违法获取钱财的工具。
对此,李剑国教授较早注意到人类之间的报恩,曾将报恩划入“伦理主题”;认为其与“非人类”的报恩行为言说有联系,但后者的报恩是有问题的,即往往不合乎道德规范:“自然报恩本身也须符合道德规范,‘义犬’的报恩方式常常是自我牺牲式的,因而就带上双重的伦理价值。但也有那种行贿主司博取功名的报恩……那种把人家的黄花闺女弄来玩弄和偷东西的报恩(《广异记·张守一》《潇湘录·牟颖》),道德的报恩采取了不道德的方式。虽然作者没有正面肯定这些行为,但也说明报恩观念中存在着糟粕和逻辑混乱。”[21]也就是以上的两种“异类”报恩存在逻辑混乱。但还应关注到的,一是习惯性伦理观念投射的群体性思维惰性。亦即将“观念联系”的“记忆”,简单的组合,就可以使“人心能从对于一物的思想,忽而转到对他物的思想,虽然此物与他物之间并无相同之处。”[1]65-66二是文学笔法的解构意义。使“善”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恶”是“阻碍我们占有任何善的东西”[1]170的简单逻辑复杂化,进而无善无恶,无正义性,不辨是非善恶,实用“利己”成为潜在规则。
首先,鬼灵报恩,往往被写成可以违反纲常礼法。鬼灵更了解人性之贪财好色。大理少卿张守一经常平反冤狱,救出死囚。一位幸运者的亡父化为老人策杖前来拜谢,承诺“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不久守一与某士人家美女两情相悦,但对方家长“防闲甚急”,守一就试求帮忙,鬼就设下帷帐,女奄然而至,鬼介绍守一为天使,于是彼此“情爱甚切”,七日后流涕而别(期间女之形体一直在家,作突然中恶状)。十年后守一又逢此鬼,鬼称“天曹相召”,诀别前赠药一丸,后来守一因“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南,用此药解除伤痛[22]卷三百三十六引《广异记》,2667。故事部分地踵步《左传》结草助战以报恩事,但鬼神为“一己之私恩”,公然违背礼法,最后竟以“天曹相召”得善果。罗素曾迷茫于中国人的生命逻辑:“所有阶级的中国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种更爱逗乐,他们从世间万物中都找到快乐,一句笑话就能化干戈为玉帛。”[11]158这一看法或许可以解读为“看淡他人”或“轻视他人的存在”,但故事引人深思,其批判意味很鲜明。
甚至,还可以利用鬼灵报恩来满足盗窃淫乱之私欲。牟颖因掩埋骸骨、祭飨亡灵获鬼报,却因报恩方式失当引起了麻烦。牟颖应梦中白衣人之请求掩埋、祭奠,然而此后他却运用“报恩鬼”予以的异能谋财谋色:“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22]卷三百五十二引《潇湘录》,2784-2785对报恩者酬答的“异术”,牟颖采取了伤天害理的“恩情消费”,近乎无止境地进行不计后果的攫取,终于酿成扰乱社会的恶性事件,他为脱法网,长久隐遁了。
其次,野生动物如老虎盗金银报答救命之恩,仿佛动物也了解人性之贪图金银。至于动物报恩的矛盾悖佐现象,更为明显。人类中心视野下的动物尤其野生动物,书写者潜在前提是低人一等的,却具有超人体能与某些人所不及的“悟性”。然而报恩过程中,难免又暴露出低于人类的逻辑思维与道德取向似是而非。只是由于报恩,偷窃变得公然施行。多年前刘守华先生注意到龙女系列的《朱蛇记》:“由于将龙女由受恩对象变成为他人报恩的工具,而且是以偷窃试题的不光彩手段来报恩,流于市井化,便又点金成铁了。”[23]很精辟。但这似乎构成一个为报恩不择手段的模式,更值得警惕。《夷坚志》写接生婆赵五嫂被求接生,来者说明自己是得道之虎,要救难产妻子,以黄金五两相谢。赵五嫂使母虎顺利产子,果得五两黄金。[26]志补卷四,1585那么,虎又从何得金?恐怕不是好来路,这就提出了一个动物不讲究(其实是无法讲究)“报恩手段”的问题。手段与目的,是否应带有统一性?以复仇故事书写作为参照,常为了斩获仇首而不择手段,类似的报恩活动及其文学表现也当作如是观。猿猴盗金银报恩亦然。说某人负箧行医被劫持,为一老猿疗病后获一帕物品酬谢,但出卖这金银时,失主认出要扭送官府。医者后来又被请入山,见老猿面有愧色,又送给一帕说从远处所得,卖了也不会出事。[26]三补,1813故事宣示,报恩可以违法盗窃,只要不被抓获就行。明清医者神秘故事系列本身就带有若干认知缺陷[27],其实也可以包括钻法律空子,却偏偏不能违反“有恩必报”世俗伦理的这一类。
清末公案小说则关注这一现象与其他母题的结合,体现出报恩理念带来的派生性效应,的确不应继续低估。同光年间《跻春台》写茂州医生乔景星医术高,心慈爱物。行医途遇二狼口衔搭链点头徘徊,内有首饰,领悟狼来求医,遂为生疽的大狼敷药。但乔医生却并没想这猛兽报恩物品由来,变卖时被疑为凶犯。他诉说离奇经历官员不信,派衙役随其入山寻狼。富有戏剧性的是那个被医好的老狼懂人语,随他来官衙作证,路上凶悍大狼还如同狗一样让恩主拴住,从围观众人中衔来“锦履”,失鞋者——凶犯只得供认。报恩狼形象与动物协助破案母题结合,虽叙事者试图以此说明道理:“乔景星救人为心,才得豺狼申冤,卒享富贵。”[28]从生态伦理角度看,故事蕴含着彼时难得的“众生平等”“敬畏生命”意识。且故事主要情节——狼报恩,狼通达人情事理并以世人喜欢的金银作为礼物,一个“人化”的狼,其报恩心理和行为,令故事充满了世俗性与传奇意味。显然,将动物的本能行为,解读为世俗人伦的对象化,属有意误读,一如哲学家的慨叹,人们爱“权力”但更爱“金钱”,因为:“金钱是享乐的途径;因而,金钱受到狂热的追求”,[11]160是明清世俗社会伦理的泛化,也是满社会追求世俗化与金钱物质至上的艺术表现。
总之,在赞美声音众多而反思罕有的古代报恩研究成果中[29],因普遍关注故事的传奇性与狂欢效应,往往遮盖了行为主体超越规范的实质,及其隐含的社会问题:一者,恩报观念的善恶与非善非恶,使行为主体遵行“有恩必报”礼法规则又游弋于法理之间。二者,恩报行为的经济动机,如“高利贷”心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义利之辨的善恶意识,与经验式“混沌的片断的知识”[1]72相结合,限制了对恩报行为书写的系统性探知与理性思考,简单直接地形成拒绝恩惠的消极抵抗力,以及表面热情应付而内心恐惧与冷漠的分裂性格。三者,恩报叙事者的人类中心理念,已潜意识地固化于施受关系的感恩表现中。报恩鬼灵、动物等“文化他者”的存在更多凭借其“工具性”价值,因其可资利用,而给予一定的存在空间。这样的“我向思维”,是传统伦理精神扩张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好货好色”物质追求的文学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