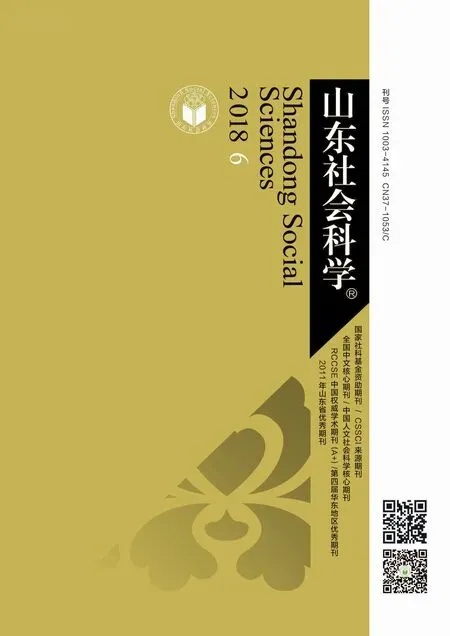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康德坐标
王时中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从“拜物教批判”到“拜权教批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曾经这样说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原来,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其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其失足在于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根本不会揭示这种虚幻形式的虚假性,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论证这种关系的正当性与必然性,“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更重要的是,与这种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相匹配的正是“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科学理论与主流意识系统之间紧密咬合、互相支援,那么,如何才可能揭示这种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呢?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编作了一个思想实验,即构造了四种生产形式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分别是“鲁滨逊式的生产方式”、“中世纪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农村家长制的生产方式”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生产方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除了第一种乃是变相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外,其他三种都是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迥异。马克思之所以构造这个思想实验,绝非无的放矢,空穴来风,其目的是要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中以“物”的形式所掩盖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差异,进而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陌生化、特殊化处理,以确立一个考察这种关系的产生、发展的理论坐标。他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能够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揭示出资本主义“拜物教”产生的根由,则拜物教的幻象也必将因此而烟消云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工作,正是从“生产(劳动)一般”入手,通过打造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概念工具,揭示了雇佣劳动成为商品之后,其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揭露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经济科学之名行反人道之实的虚假性,而且也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提供了坚定的科学依据。
以此作类比,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对权力也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谜”,即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对权力的颠倒幻觉,也类似于宗教的虚幻,我们可以称之为“拜权教”(Fetishism of power)。如果借用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风格,“权力”的神秘性也可以如此表达:权力貌似是一件简单而平凡的东西。但经过分析却表明,权力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人类经济生活中拜物教的分析与批判方法是具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能否以此为参照,揭示出“拜权教”的秘密?如果能的话,能否确立一个新的坐标,从而在继承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角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到“政治哲学建构”?
本文试图沿着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路径,引入康德的哲学作为坐标,在康德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能的关联,探讨一种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跃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关联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获得一种方位感,即通过重新定位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理论进路,明确其在物质生产的层次所展开的话语方式及其历史意义;同时,又可能获得一种方向感,即在生产与规范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建构之间,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方向。具体来说,本文以“形容语的矛盾”的处理为线索,首先考察马克思对“货币的二重性”论证与康德对“自律的可能性”论证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然后以康德所区分的“自律”与“他律”为参照,探讨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倒逼出”一个法权关系前提,确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权利科学”的可能性。
二、如何处理“形容语的矛盾”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商品的交换价值时,曾提到一个概念的“困局”:相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与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Valeur intrinsè)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6页。。正如“圆形的方”与“木制的铁”一样。因为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比,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且这个比例还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交换价值貌似是一种相对而偶然的东西,根本无法被概念化、理论化,遑论其客观性论证了。
但马克思却试图证明,商品在交换时的确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商品的天然属性的、而是具有共同尺度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商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说,商品本身便是同时兼具两重性的东西,即一方面具有价值,另一方面具有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活动中,货币正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社会职能,并展现了其二重性而并不矛盾:“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这种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便是货币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是对于货币的两重性的不理解,有人便将货币的价值视为是想象的或者是虚假的,还有人便将其理解为是天然的社会属性,因而产生了货币的魔术,即货币拜物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所要论述的,正是货币之作为特殊的商品与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二重性。而“货币的二重性”之谜,归根结底源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二重性区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这种商品所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这便是资本拜物教所极力掩饰与歪曲的“事实”,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集中批判的靶子。
由此可见,货币的二重性既来源于商品的二重性,但又高于商品的二重性。货币一旦独立出来,便成为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反过来成为了商品的“价值尺度”。与此类似,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自律”概念也具有类似于货币的二重性的特征。众所周知,就词源学的意义说,“Autonomy”是由auto与Nomo两个词根构成。希腊文中autos乃是“self”的意思,而nomos则是法律或者规则的意思。*Gerald Dwork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9.一般来说,自由乃是不受任何必然法则的限制与拘囿,但“自律”却是“自我立法”(self—legislated, self—ruled),这种“自我的立法”何以既是自由的,又是规范的?这个意义上的“自律”似乎也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Keith Lehrer, Reason and Autonomy, Autonomy, Edited by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Miller, Jr. Jeffery Pau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7.
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与康德分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都面对一个“似非而是”的“形容语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的正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所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如何理解这种抽象力的运作方式,正是人类把握社会实践生活的难点。如果说马克思通过揭示货币的二重性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铸造了坚实的理论武器,那么,考察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如何展开“自律的可能性”论证,便可能成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到“政治哲学建构”的一条“引线”。
三、从“自律的可能性”到“他律的必要性”
康德承认:“自由意志”与“法则”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元素,两者之间的统一性设定,似乎存在着一个无可逃避的悖谬。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自律”的规定性似乎陷入了循环论证:“这件事情够令人惊讶的,并且在所有其他实践知识中都没有与它同样的事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这里的问题在于,“自由”与“法则”之间的统一性证明,并不能从经验中归纳出来,也不能从任何一个外在规范中借来,“而是由于他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强加给我们,这个命题不是建立在任何直观、不论是纯粹直观还是经验性直观之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换言之,这种统一性不能通过分析的方法,而只能通过综合的方法才能实现,且这样的综合命题只有通过一个第三者,才可能把两者沟通起来。而在康德那里,自由的积极概念正是这个第三者。那么,这种自由的法则是何以推导出来的呢?
在康德看来,如果自由的积极概念能够作为沟通意志与道德法则的第三者,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先天同一性:“道德既然是从自由所固有的性质引申出来,那么,就证明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自由不能由某种所谓对人类本性的经验来充分证明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2年版,第55页。如果说在理论理性中的自由乃是作为一个“范导”的消极概念,那么,在实践理性中,对自由与道德法则之间关系的先天证明,就是这样,“每个只能按照自由观念行动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2年版,第55页。。一方面,实践的理性必须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则的创始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自身即是自由意志,只有在自由观念中,才是它自身所有的意志,在实践方面,为一切有理性的东西所有。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自由,“那本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的道德律不仅证明它是可能的,而且证明它在那些认识到这个法则对自己有约束的存在者身上是现实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而道德律作为出自自由因果性的一条法则,正是由于自由的积极概念才成为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自由乃是属于与感官世界相对的理智世界,而感官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区分,正是自由的积极概念得以可能的根据。基于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从自由到自律、从自律到道德规律之间所谓的隐蔽的循环已经站不住脚了。而自由与道德律之间的先验的综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智世界的独特性,换言之,“定言命令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由观念使我成为理智世界的一个成员” 。准此,“我的全部行动就会永远和意志的自律性相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2年版,第60页。。虽然我们还没有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的知识,但其客观实在性是毋庸置疑的:“道德律的客观实在性不能由任何演绎、任何理论的、思辨的和得到经验性支持的理性努力来证明,因而即使人们想要放弃这种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也不能由经验来证实并这样来后天地得到证明,但这种实在性却仍是独自确凿无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由此可见,自由的积极概念便是构成自由即自律这条道德法则的关键,也是论证实践理性之成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关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康德才将自由与道德律视为具有“交替性”与“同一性”的概念,“自由与意志的自身立法,两者都是自律性,从而是相交替的概念,其中的一个不能用来说明另一个,也不能作为它的根据”*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2年版,第57页。。实际上,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开始,康德就自由与道德律的关系就有所交代,“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绝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注释1。。
于是,相对于理论理性的自然必然性,自律也具有独特的客观实在性。自律的可能性,实质上就是根源于自由的因果性,而绝不是自然因果性与自然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相比,自由的因果性至少有三个不同:首先,自然必然性是外在的,被外来的原因影响,而自由的因果性则是意志所固有的性质,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能够独立起作用;其次,在自然因果性中,由于每个人均以自己的爱好为基础,不同的人之间的爱好无法协调,但自由的必然性与质料、经验无关,因此存在着先天的统一法则:“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应当把他的准则思考为实践的普遍法则,那么他就只能把这些准则思考为这样一些不是按照质料,而只是按照形式包含有意志的规定根据的原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再次,所谓自由因果性之“因果”只是一个类比,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在意志领域的推理。这就是说,意志的一切行动就是它自身的规律,而行动所依从的准则就是以自身成为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准则。“这一规律也就是定言命令的公式,是道德的原则,从而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2年版,第54页。由此可见,自由的积极概念便是构成自由即自律这条道德法则的关键,也是论证实践理性之成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关键。
但现实的人并不是完全自律的,因为人类的自由也包括任性,即从感性欲望、冲动刺激出发,这种任性与普遍的道德法则之间并不相一致;而作为普遍法则的“自律”,发布绝对命令的又是以“定言”的方式,因此,“自律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Paul Guyer, Kan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Edited by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Miller,Jr. Jeffery Pau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8.。康德因此区分了“自由的法则”与“法律的法则”,分别表现为道德意义上的“内在的自由”与法律意义上的“外在的自由”。就立法形式而言,又可以因此而区分“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法律的立法”是权利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绝对命令的要求不同,权利科学有赖于他律,即一种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并没有抹煞或者否认人的自由,恰恰是通过限制了人的任性,而提升了人的自由,并可能使得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由。从这个意义说,作为他律的“权利”与“强制的权限”是一回事,“权利科学”就是“强制科学”。
如上所论,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不仅包含着自由与法则的统一性,而且也包含着自律与他律的二重性。这也意味着,这些元素在康德哲学的立体结构中能够并存而不会自相矛盾。但相对于康德的其他著作,他在晚年以法权为主题所展开的政治学说却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那些研究《实践理性批判》的学者更愿意从自律的角度来研究康德的法哲学,另外一些研究《法权学说》的学者则更倾向于从自然法的角度来阐释康德的法哲学,而恰恰很少有学者从自律与他律、伦理与法律、纯粹之物与经验之物的二元论出发来阐释康德的法权哲学。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错失了康德哲学所处的两个思想传统的真切把握:一个是意志论传统,一个是理智论传统。*吴彦:《法、自由与强制力》,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1页。事实上,这两个传统的分歧根源于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差异:人的自由是否必然需要一个理由?意志论认为不必须,而理智论则认为这是必须的。康德的法哲学正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批判意志论的经验主义理解方式,另一方面批判自然法的理智论理解方式。换言之,在康德那里,“自律”与“他律”是并行不悖的:正因为人是自由的,因此,自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实的人却是任性的,因此需要他律,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需要法权强制的原因。如果只看到自律的可能性,而看不到他律的必要性,或者只看到他律的现实性,而看不到自律的理想性,均错失了康德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的开掘与保持正是我们用以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坐标。
四、《资本论》的法权关系前提
由上可见,康德从“自律的可能性”拓展到“他律的现实性”的论证,事实上也是“权利科学”的拓展进路。但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关系的展开与康德对“自律—他律”关系的处理,貌似还是各自为政,无法对接。笔者在以下试图表明,若能够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倒逼出”一个政治法权关系的前提,则康德与马克思便可能在“权利论”的领地上存在一个“交集”。如果这个“交集”是可能的,那么,便可以间接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康德坐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劳动力的买与卖”中论及,劳动力占有者与货币的占有者在流通领域中之所以能够结合,正是由于存在着一种“自由”、“平等”与“所有权”的法权关系条件:就自由而言,劳动者必须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包括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就平等而言,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首先是法律上平等的,才可能在市场上相遇并发生买卖关系;就所有权而言,劳动力所有者出卖的是某一个时段中的劳动力,并不是重新接受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页。。
这就意味着,只有预先存在一种法权关系,马克思才得以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进而揭示出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的秘密。*王时中:《 〈资本论〉的前提批判——以康德的权利科学为坐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2期。这也说明,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确实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平等”与“所有权”事实上恰恰是康德所肯定的处于文明状态的公民具有的权利:就“自由”而言,除了必须服从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之外,公民并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律;就“平等”而言:除了服从他自己的道德权利所加于他的义务,公民不承认在人民之中还有在他之上的人;就“独立(自主)”而言:除他自己而外,别人是不能代表一个公民的人格所有权的。“这个权利使得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继续生活下去,并不是由于别人的专横意志,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康德:《法的形而上学——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法权关系前提,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意或者无意的漠视,只有极少数学者意识到其重要性并予以揭示出来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尔·伦纳就以法律制度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题,在阐发《资本论》的理论进路的同时,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科学的研究。他建议:“全面理解法律制度在不同经济运行阶段所执行的这些功能,请参阅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认识到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重要性。马克思空前绝后,其他人都拒绝承认这个问题或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它。”*卡尔·伦纳:《私法的制度及其社会功能》,王家国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当然,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法权关系前提,与康德从自律出发对权利科学的必要性与现实性的论证,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不能完全等同。具体表现在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现实性出发,即从生产的视角出发,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康德在自律的领域中已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掉了,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更为丰富,而康德所理解的人则显得贫乏空洞。*William James Booth. The Limit of Autonomy: Marx’s Kant Critique, Kant &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ontemporary Leg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and William James Booth, 1993, p257.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康德之间不存在对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两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家族相似性”:就对象而言,两者都是对“实践”的理论构造,而差别在于,前者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去揭示拜物教的秘密,而后者是基于道德哲学的建构,从道德实践的二重性出发,去揭示他律,即法律、政治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就方法而言,两者都是“左右开弓”,以实现一种可能的综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既要批判李嘉图等将所有商品均视为有价值的唯名论观点,也要批判贝利将商品的交换价值视为客观的,进而抹杀商品使用价值的唯实论观点;康德也面对着双重的挑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遭遇到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双重挑战,在实践理性层次中所面对的乃是意志论的经验主义与自然法的理智论传统的双重挑战。如果说意志论传统开启了近代契约论的政治哲学,而理智论传统则代表着承继自古希腊柏拉图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康德论证自律之可能性的过程,似乎是在对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作出先天的综合。而综合的成果便是“自律”的实在性、必然性与可能性。如果这种综合是成功的,那么,便可以得出证明,人为自己立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但康德从“自律”到“他律”的论证过程则说明,现实的人并不是自律的,恰恰是需要他律的强制,这就是权利科学之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前提。从这个意义说,“权利论”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对接的可能“交集”。
五、结语
在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如何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法哲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沟通确立一个最大公约数,以真正切入马克思哲学的政治主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必要且非常紧迫的问题。但正如有学者所言,谁想找到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入口,并因此求教于历史与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都会遇到一个特殊的困难:“原因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提供一个封闭的、系统的法律理论,而只是在全部作品中不完整地与分散地展示了批判市民社会的法律之初步倾向。”*考夫曼等:《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以康德关于自律与他律的区分作为坐标,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及其基本问题,那么,“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之间的关系,便应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正如康德对“自律”与“目的王国”的论证一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然性论证,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理想的”,而法权关系,即“他律”,却是“现实的”。但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唯一主题,而作为社会“稳压器”与“粘合剂”的法律、道德等规范性论题,却被视为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其独立性与正当性隐而不显了,这也是科莱蒂与凯尔森等现代西方思想家之批评马克思缺乏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如上所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确蕴含着一个“法权关系”的前提,只是由于他本人的论题所限以及文本的跨文化传播、历史的命运多舛,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辨认出来,而只能借助于另一种哲学坐标的参照对其作“陌生化处理”,才可能彰显出其意义。这也反过来证明,从《资本论》只能“倒逼”出一种“权利论”而决不能直接推广到“正义论”。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主题,因为其涉及到至善、永恒与绝对等内容,在当代中国学人目前的理论储备中还缺乏可资借鉴的、直接的思想资源。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康德道德哲学对“自律”与“他律”的区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意义,主要便在于其对法权关系之必要性与正当性的论证。这也是本文以康德哲学作为坐标,试图沿着马克思所展开的“拜物教批判”路径,拓展到“拜权教批判”主题的原因所在。如果这种拓展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便可以以“拜物教批判”与“拜权教批判”之间的类比为视角,切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进而以康德对“自律”与“他律”的区分作为坐标,通过倒逼出《资本论》中的法权关系前提,将“权利论”视为康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交接点”。如果这种对接是可能的,那么,如何论证权力产生的必要性、正当性、有限性及其变异的形式,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