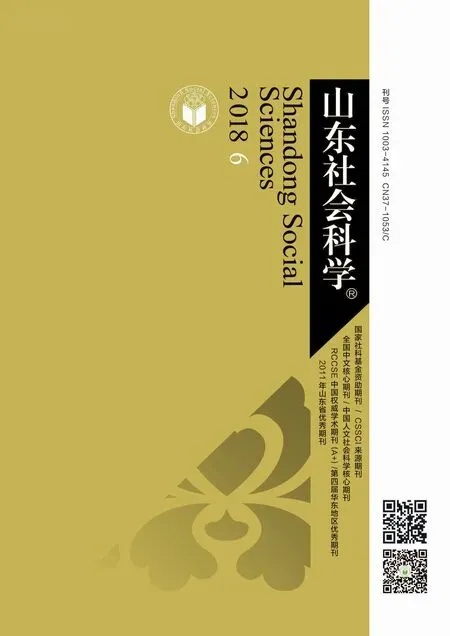人与共同体关系视域中的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
李 毅 赵 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6)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生活是以一种辅佐的方式来帮助人实现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不是在以确立政治为仅有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统帅人的生活。所以,从“人与共同体的互构”的角度来理解生活世界中的产物——政治自由,更符合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的价值取向——为了生活而政治。
一、马克思政治自由的主体
在马克思的眼中,创造历史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因此,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的内容首先强调的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对马克思而言,政治自由意味着通过实践生产出全面发展的人。这就要求消解现实生活中“人的分离”。所谓“人的分离”就是人分裂为市民社会中的人和政治领域中的人。“人的分离”涉及两方面内容:人的性质的分化(市民社会中的自私自利的人与政治领域中抽象的公民的分离,即人的现实性与真实性的分离);公民和劳动者之间身份的分离(即人性与人性的工具性的区别)因此,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的第一层涵义,就是要在消解这两重分离的基础上重建人的完整性。
马克思“政治自由”主体重建的第一个层次就是“非政治的人”。所谓非政治的人,就是非政治统治下的人。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同一的时代,人唯一的生活领域就是政治统治下的领域。人只是政治统治附属品的代名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贯穿着整个经济生活,所以政治国家很少干预经济,个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开来。人在政治统治下,辟出了一块相对“真空”的地带,一方面在这一相对真空的地带中从事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政治统治的领域中配合着政治活动。这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市民社会与政治领域中的人的分离。尽管政治在这一时期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但政治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摇了。“非政治的人”就是这种动摇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政治自由”所欲重建的主体的第一个层次。
马克思肯定市民社会带来的“人的分离”,同时看到这种分离造成了人本质上的分裂,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分裂、“人”和“公民”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人具有“私”性。可以通过形象的方式,更好地理解“私”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市民社会当作门票,把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比喻成政治统治的进行,那么门票让往日只能在剧场外游走的人们有机会进入剧场,这种进入是对人有积极作用的。在剧场内,舞台上下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舞台下的观众的欣赏如同市民社会生活的进行,舞台上是政治家在进行剧目表演。首先对于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来说,舞台下面观众的存在与否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它并不会因为观众的喜好而从根本上改变剧目内容,更不会邀请观众参与其中。诚然,观众注目的眼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观众存在的意义,但从根本上来说,戏剧没有了观众仍是戏剧。因此,对于这场有没有自己的存在都不会有本质上改变的戏剧,观众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自顾自地在台下过自己的生活。面对台上的剧目,观众席上的人群更多地是“众”,而“观”的意味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政治仍然不是生活,人仍然在私域中。所以,“私”人那单薄、纯粹的世俗生活是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要批判的对象。正如他要将政治从天国拉回现实一样,他也要将“私”人带进共同体的生活。因此,非“私”的人是马克思“政治自由”主体所要重建的第二个层面。
马克思“政治自由”主体所要重建的第三个层面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这个表达,为的是强调其内涵即“抽象公民”中的“公民”二字,以强调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而非“抽象”存在。现实的人之所以“现实”,仅仅是因为他是在决定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中存在的人。“现实的人”是“利己”的群体,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特殊的(与普遍相对的特殊)利益。对他们而言,共同体的生活只是与个人生活不大有关联的一个彼岸世界。因此,“现实的人”是缺乏社会性的人。“真正的人”虽然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但是在政治生活中至少有形式上的个体与组织的互动,对利益的追求也不再是从“特殊性”这个角度出发,所以“真正的人”更具社会性。此时,“真正的人”与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之间已经拥有缺乏真实社会性的表面关系(也就是说人与共同体之间已经有了关系)。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人是一个扬弃了抽象性的公民。因此,“真正的人”这个层次强调的其实就是人不应该只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应把自己上升到共同体的成员来考虑利益,从而使人真正具有社会性。
为了具备社会本质,“真正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地扬弃自己的“抽象性”成为类本质的人,这就是马克思政治自由主体重建的第四个层次:类本质的人。只有当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把类生活变成他的对象时,人才是类存在物。那么该怎样重建主体的“类本质”呢?其关键条件就是要实现人“把抽象的公民归复于自身”,并且“成为类存在物”。“真正的人”虽然强调了人只有在社会本质上获得自己的存在,才能够进入政治领域,进而进行政治自由的活动,但由于“真正的人”的社会本质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政治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无论是政治领域中的人还是市民社会中的人,都无法真正地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性活动),因此只有当“真正的人”自由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性活动时,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进入政治生活。因此,将“抽象”的公民变成能切实进入共同体生活中的人——类存在的人,政治自由主体才从根本上得以建立。
二、马克思政治自由的场域
人类要实现政治自由需要解决两个基础性的问题:一是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二是政治活动中主体活动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在马克思政治自由思想中,主体要实现政治自由就是要实现人与共同体的互建互构。因此,当类本质的人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时,其活动的对象是“共同体”。
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理想中,共同体最终要以社会而非国家为其形式,这是由克服人的本质二元化所决定的。在由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所造成的人的本质二元化的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解决方法不同。黑格尔采取的是“和解”式的,而马克思是非此即彼式的。黑格尔提出“合理性”这一概念,他认为,自由在国家里具备了客观性,只要人将自身嵌入这种客观性,便有了合理性,从而人就能够作为国家成员存在,这其实是社会对国家的妥协。但马克思所要的不是妥协而是建立社会,马克思指出,在解决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所造成的人的本质分裂的问题上,黑格尔将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高于且优于在当时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通过人的妥协而获得国家成员的身份,借此进入政治领域,但这种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人的本质若以国家为基点,在国家中消解社会,不但不能真正地建立起人与人的关系,反而有可能退回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对人的全面控制的危险境地。“黑格尔式的架构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而此种逻辑常被用来为极权或集权的政治统治辩护。”*伍俊斌:《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4期。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要克服由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所造成的人的本质二元化和异化,就要将国家政权交还给社会,就要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分离消解于社会中。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共同体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都是抽象的、虚假的,人们不能作为共同体真正的成员来构建他们的生活。因为“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全民联合的姿态出现,同时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形式,但是国家内部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是被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掩盖着罢了。”*秦龙:《浅析马克思关于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思想》,《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1期。所以,只有国家归复于社会,人们才能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社会环境。
马克思认为,需要和利益都是人类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利益与需要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发展需求的表现,彼此影响、转化。*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8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以个人为主体的需求只是一种天然性的事物,某个群体的利益虽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却仍是一种“私人利益”。所以,以天然性的需求和私人利益为动力,虽然可以使得人们结成特定的群体,但也留下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这样的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同体。马克思说:“那个离开了个人就会引起他反抗的共同体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7-488页。只是,该以什么为“粘合剂”才会带来如果个人离开共同体会引起他本身的反抗呢?其实这种“粘合剂”对这个个人来说,应该类似需求一般是一种类天然的事物。这种事物,可以称之为“共同需求”。这种需求的普遍性就在于,它是与马克思要求的“人的实质”是同一的,因而是一种共同需求。在共同需求的推动下,人不再是作为纯粹的个人或个别群体而存在,而是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成员。
共同体需要是以人的类存在为前提和要义的,是以人的类实质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基点。在这“同一”的驱动下,人是共同体的成员,而非纯粹的个人。而这样的联合体自然就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真实的集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以共同需要为动力,人与人之间才会真正建立起直接的而非由于外在的压迫力(比如利益交换的平等)而建立起来的联系。这样的共同体才是适合维持人的本质的场域。
马克思指出,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时,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占有”是为了“发展”。真正共同体的目的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人将自己、他人当做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这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自身的异化。“占有”将使人与人退回到私域中,政治生活将再次被供上人类生活之外的神坛。所以“占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在马克思的视阈中,“自由在他看来是人类社会消灭对抗性关系,从而告别史前时期(阶级社会)社会形式的重要特征”。*魏小萍:《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三、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建构
怎样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呢?第一个层次就是“人”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人在共同体中生活,政治作为生活而非手段。这一终极层面上关系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也就是人要完全地身处于由“可行能力”*[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于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带来的开放性中。在阶级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前,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上升到纯粹的政治生活阶段。这就产生了人和共同体之间关系构建的第二个层次: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作为。它们是马克思“政治自由”中主体和共同体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创立“人”在“共同体”中的生活
在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终极层面上,人与共同体的互构是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而展开的。所谓“公共善”就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如果并且只有某种善的利益分配不为任何人随意控制,而是由每个可能的受益者控制的,这种善就是公共善”。*[英]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曹海军、郑维东、王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公共善”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利益分配的开放性,也就是任何一种资源、利益的分配,是面向所有共同体成员而开放的。倘若不是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一旦陷入人和共同体产生间隙的局面,共同体将被降格为一种“仅仅是必要的组织”,而人又将面临本质的缺失,由此造成人无法“生活”而只能“生存”。可以说,以“公共善”为人和共同体间活动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以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建立共同体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将以什么样的动力来推动“公共善”这一价值取向发挥作用呢?这种动力就是以“社会条件”为核心的动力。所谓以“社会条件”为核心的动力,是相对于以非社会条件为核心的动力而言的。王晓升教授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驱动力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永恒的驱动力,一种是相对的驱动力。永恒的驱动力是与社会条件无关的,是人的本能,比如性本能和饥饿等生物性的本能,而相对的动力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动力。”*王晓升:《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来维系人和人所处的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那个动力,主要是非社会条件,主要以一些生物意义上的追求为动力。这里的生物意义不是指本能需求,而是相对于真正共同体中人在完全占有了自己的本质的条件下,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求而言的。后者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条件(包括人和共同体两方面的条件)。所以,以“社会条件”为核心的动力,是以创造有利于共同体和人共同发展的社会条件为内容的。相对的“非社会条件”的驱动力,则是以满足个人发展所需要条件为内容。只有以“社会条件”为核心的驱动力才可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物种,是一个类。因此,人性和人的本质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人的行为能够被认识是基于人的本质的存在。反过来说,人的本质就应该在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不是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人的本能,而是区别于人的本能的、非生物的、需要在社会条件中发挥和铸就的“潜能”。它包括了人的普遍本质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人的普遍本质”可以理解为人最根本的本质,也就是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类特性。而所谓“人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就是在普遍本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特质,它在“劳动中发展起来”,因此是“历史性”的本质。比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劳动成为一种自觉需要时,劳动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审美行为,而那时人的本质将具有相应的审美特质,但最根本的本质仍是普遍本质——人的类存在特性。
(二)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作为
构建真正共同体中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在积累物质基础的过程中,人与共同体(虽然说这时的共同体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相对健康的关系,其实质要统一于终极关系的实质中,就是要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作为。对于基本自由的实现和维护,人对国家的作为就是在国家时代里人和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主要是言说能力的表现和理性力量的显现。
1.公共性言说的回归:出版和言论
所谓“公共性”就是指是否能引起一种“联结性的力量”,它的最大功效就是维持人与人的联结。只是这种联结不同于联系或关联,它带有真正共同体成员的特质。公共性的言说在具体的政治自由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公共性言说所展示的,是一个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物时所具有的一种基本能力,这是人民能够管理国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前提。倘若没有了公共性言说,就弱化了人的社会存在性,也就弱化了人民管理国家的实质。这是马克思在批判抽象公民时所批驳的。
马克思认为,在封建制度中,只有特权阶级的人才能够进入政治领域。但由于他们颠倒了逻辑——不是首先作为社会性的人,而是首先作为一种“政治人”——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且其言说也不是“公共之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所谓的政治领域中存在的人也是抽象的人,这时的言说也只是私人之言。因此,公共性言说需要在人民对国家的作为过程中被重建,这种重建的具体表现是对一系列政治权利的维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维护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论是出版自由还是言论自由,都是公共性言说的表现,是人民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一种基本方式,它的使用体现了书写历史的过程中无比高贵的一种智慧。公共性言说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人的社会性,帮助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作为。
2.理性的承认:法律
倘若说公共性的言说是人民进入政治领域的一种基本方式的话,理性的运用则是进入政治领域并切实管理国家事务的前提条件。在管理国家的话题中,人民运用理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制定法律。人民的理性在马克思早期对法律生产的理解中,确实被列为法律合法性的来源。最能代表他的这一思想的就是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中对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评述。面对将捡枯枝也纳入反对林木盗窃相关法律的约束对象时,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他们制定出了“任何人都应该说明他的木柴的来处”的法,这其实是对公民生活的粗暴的侵犯和侮辱。这种违背人身自由原则的法律是不自由的法律。马克思批判道:“身为崇高的立法者而一分钟也不能超脱狭隘、实际而卑鄙的自私心理,不能达到客观观点的理论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马克思所提出的以人民理性立法,并不是指每个人都要以具体的方式参与到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人民理性立法是一项原则,它要求的是法律的正当性。“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规律时才起真正的作用。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人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才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而“自由的领域最终将由‘法律’规定”。*[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因此,在人民管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为公民理性立法的法律,才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反映出社会本身法则的法律。
从经验层面说,政治自由是最能体现人生命价值的经验之一。在人与共同体间关系建立 的主题上,既有终极的目标,也有当下的步骤。一个是有待实现的理想,一个是亟待实现的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自由”中建构“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