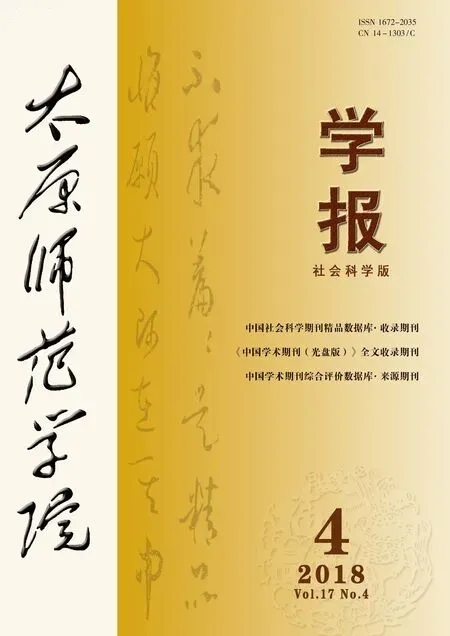清人整理郑玄《毛诗笺》的成就与局限
,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一、清人关于郑玄“诗礼之义”与毛、郑异同的基本观点
郑玄是经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清代的郑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尤其是在乾嘉汉学的鼎盛时期,几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1]53。清代的郑学复兴又是以郑玄的三礼之学为主干的,从清初的顾炎武到晚清的今文学家皮锡瑞,治学路径虽然有异,也都极力表彰郑玄传承古礼的功绩。大约在乾隆以后,“礼宗郑氏”的汉学风气逐渐形成,乾嘉学者不满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出“以礼代理”的口号,致力于古代典章礼仪、文物制度的考证,大抵就是以郑玄的三礼之学为基础的。
受此影响,清代学者对郑玄的以礼笺诗也多有继承、认同和辨析。陈启源考证《草虫》“亦既见止,亦既觏止”,即援引《郑笺》的观点,认为“《笺》以‘见止’为同牢之时,以‘觏止’为初昏之夕,因引《易》‘觏精’语证之,后儒多笑其凿。然古诗简贵,不应一事而重复言之,郑分为两义亦非无见”[2]384。朱鹤龄考证《宾之初筵》“笾豆”“殽核”等术语,认为“殽豆,实菹醢也。核笾,实桃梅之属”[3]211,也是援引《郑笺》而来的解释。陈启源和朱鹤龄都是康熙时人,所著《毛诗稽古编》与《诗经通义》专宗毛、郑,渐开清代诗经学的复古考据之风。
在乾嘉汉学时期,戴震、马瑞辰、焦循、胡承珙、程晋芳等人对郑玄的诗礼之义无论是认同还是批判,都采取了以礼笺诗的思路。戴震联系《周礼·内司服注》来解读《君子偕老》“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论证了“展衣宜白”的郑氏义。[4]564戴震还对郑玄以“无算乐”来解读《宾之初筵》“酌彼康爵”甚为赞赏,以为“非详考于礼,深知其意,不能明也”[4]579。马瑞辰是清代以礼笺诗的代表人物,所著《毛诗传笺通释》联系周代车制来解释《干旄》“素丝纰之”,认为“此当从笺说为是”。[5]419又如《关雎》“寤寐思服”,《通释》引《礼记·问丧》来证明“服”为“忧思”之意,据《士昏礼》来解释《汉广》“言秣其马”,据《仪礼》来注释《采蘋》“于以采藻”,据《周官》来解释《祈父》“予王之爪士”等等,对郑玄的诗礼之义多有发覆。在焦循看来,《驷驖》所表达的并非寻常田猎之事,由此放弃了“襄公亲贤”的郑氏义,只取“狩之为典礼”的毛说。[6]420类似的情况,胡承珙继承《毛传》以“角爵”来解读《卷耳》“酌彼兕觥”的观点,否定了郑玄的“罚爵”之说。[7]23上述诸家根据三礼解《诗》,或驳郑氏之非,或补充发明之,不一而足。在道光年间,还出现了包世荣《毛诗礼征》和朱濂《毛诗补礼》两部专书,皆以补足、发挥郑氏义为主。《毛诗礼征》认为:“郑玄以礼说诗,立义高远,始知非学礼无以言诗。”[8]106该书共列郊天、明堂、社稷、禘祫、冠礼、婚礼、飨食、燕射等四十三目,每目之下节录《通典》或考核群书以为“总叙”,选录《毛诗传笺》等发明题旨,而其中尤以《郑笺》为多。
清代出现了一批辨析毛、郑异同的诗学著作。沈镐《毛诗传笺异义解》、戴震《毛郑诗考正》、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程晋芳《毛郑异同考》、曾钊《诗毛郑异同辨》以及丁晏的《毛郑诗释》等等,这些著作既然要回到毛诗古义那里去,自然绕不开毛、郑异同这个话题。在此之前,清代前期经学家斟酌于汉、宋之间,是把毛、郑当作与朱熹《诗集传》相异的汉学总体来认识的,对汉学内部的毛、郑歧异不甚措意。*比如王夫之《诗经稗疏》“皆辨证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贺贻孙《诗触序》说“朱子所训雅、颂,圆转不滞,优于毛郑”。诗经汉学渐兴之后,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编》“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朱鹤龄著《诗经通义》宗主毛郑,力驳宋学诸说之非,也都是将毛、郑视为一体的。及至乾嘉汉学主旨的确立,汉学家法备受学者重视,诸家辨析毛、郑异同,澄清《孔疏》所致的淆乱,旨在维护《毛传》古学的纯粹性。陈奂、胡承珙、焦循等学者梳理毛诗学的发展脉络,都认为《毛传》与《郑笺》各自有别,而聚焦于孔颖达《毛诗正义》混合毛、郑所导致的诸种误失。在陈奂看来,郑玄初学韩诗,掺杂鲁诗,已非《毛传》古义。及至《毛诗正义》将二家合一,“毛虽存若亡也”。[9]2-3陈奂和胡承珙都“墨守毛义”,后者也认为《郑笺》多有申毛而不得毛义者,甚至异毛而不如毛义者,《毛诗正义》有误指《郑笺》之申毛为异毛者。在焦循看来,《毛诗正义》“往往混郑于毛,比毛于郑”,[6]395所著《毛诗补疏》极力清除孔氏混同毛郑与误释之例,申毛驳郑者为多。林伯桐所著《毛诗通考·考郑笺异义》也认为:“然《传》《笺》不同者,大抵毛义为长。”[10]277总而言之,清代前中期的诗经学史,随着专门汉学的逐渐确立,也由前期的汉、宋之争逐渐过渡到毛诗学内部的家法问题之上。以乾嘉学者的眼光视之,毛诗学经过郑玄的笺注已经不那么纯粹了,他们仔细地甄别《郑笺》之是非,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毛诗最原始的面目。
在诗经学的义理方面,曾钊《诗毛郑异同辨》云:“毛郑异同,大义有四,随文易说者不与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11]527夏炯《郑氏笺毛说》亦云:“郑氏之笺毛,表明之者多,别用己意者少。其别用己意者略有数端:一则郊禘用感生帝之说,如《生民》《商颂》诸篇,遵用纬文;一则婚姻时月独取周礼,俱与毛不同;且毛不改字,郑则多破字,故与毛异者最多。”[12]6041-6042就其大义言之,《郑笺》之异于毛者,不外礼制、谶纬、史实、破字诸端。关于婚期,毛以为在秋冬,郑则以为在仲春;关于“出封加等”之礼,毛以为古卿大夫出于封畿之外,巡视邦国,乃加以诸侯之礼,郑以为卿大夫巡视畿内,乃加一等,出于畿外则不得;稷、契之生,毛遵史实而郑用谶纬,附会出“帝王感生”的神话来;毛以为周公摄政,为王陈告必东征、诛管蔡之意,郑则以为周公避居东都,成王罪其党属,周公乃作诗劝谏成王当保全宗室之意;郑多破字、改字,而“毛无破字之理”。这些都是诗经学史上的旧题,自王肃、孔颖达以来历代都有辨说,清代学者多以尊毛为主。
二、清人对郑玄《毛诗笺》的继承、补足与完善
清人整理《郑笺》的最大成就是在礼制典章和训诂释义方面,但由于过分拘泥于《毛传》古义,产生了不少误指郑之申毛为异毛的误会。虽然如此,清人在以下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很值得称道的:
首先,他们联系《诗经》的语法和章句总体来理解文辞的意义。焦循《毛诗补疏》驳斥郑玄的误释之例,十分精辟地指出郑氏“拙于属文之法”。比如《伐木》之“我”,郑玄分而训之,焦循则认为:“五‘我’字一贯,为属文之法。郑氏拙于属文,而以上四‘我’字为族人,下一‘我’字为王。”[6]427同样的性质,《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和《卷耳》“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其中两个“我”显系同一个人,但是“郑氏不明属文之法,每于‘我’字破碎解之”。[6]427在胡承珙看来,《北山》“王事鞅掌”实为叠韵之词,不当作《郑笺》之分训。所著《毛诗后笺》云:“鞅掌,叠韵字,犹之憔悴、栖迟。憔悴为双声,栖迟为叠韵,此类形容之词,义多寓于声。此诗十二‘或’字各两两相反,栖迟、偃仰为从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义自可见。”[7]508为此批评郑玄“逐字生解,殊为迂曲”,这是很有道理的。陈奂对《诗经》“言”字的用法作出归纳:“言归,曰归也。此篇及《黄鸟》《我行其野》《有駜》皆作‘言归’,《南山》《东山》《采薇》皆作‘曰归’,《黍苗》作‘云归’,言、曰、云三字同义。……全诗‘言’字有在句首者,为发声,若《汉广》之‘言刈其楚’之类是也;有在句中者,为语助,若《柏舟》‘静言思之’之类是也。”[9]10马瑞辰认为:“《诗》中多以‘中’为语词,‘水中央’犹水之旁也,与下章‘水中坻’‘水中沚’同义。如若《正义》以‘中央’二字连读,则与下章坻、沚句不相类也。”[5]502乾嘉学者联系《诗经》的语法和章句之法来训释诗义,将语词置于诗歌章句和《诗经》总体之中进行类例的阐明,这是郑学训诂较为薄弱的地方。
其次,乾嘉学者最为擅长声训假借之法,这倒是从郑玄那里继承过来的。《郑笺》中的运用极多,诸如“某犹某也”“古者某某同”“某某声相近”“某读为某”“某之言某”等等多属此例。清人转而益精,以声音线索探明本字和本义,取得了卓越的训诂学成就。戴震著《毛郑诗考正》四卷,认为“‘讯’乃‘谇’字转写之讹”[4]567。他还认为《月出》《正月》《北山》《抑》诸诗中的“惨”字,“盖‘懆’字转写讹为‘惨’耳。懆,千到切,故与‘照’‘燎’‘绍’韵。”[4]568段玉裁更指出,“歌以讯之”的“讯之”二字皆转写讹误之例,当作“歌以谇止”,其引《广韵》《列女传》有据。[13]193从音韵角度来训正《诗经》本字,由此补充毛义,或纠正毛郑的疏失,在清代十分普遍。又如《终风》“终风且暴”之“终”字,毛郑俱以“终日”作解,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考订曰:“‘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既’、‘终’,语之转,既已之‘既’转为‘终’,犹既尽之‘既’转为‘终’耳。解者皆失之。”[14]122-123这就是说,“终”字乃是语气词,与“既”字一音之转。阮元《经传释词序》曾高度评价曰:“昔聆其《终风》诸说,始为解颐。”[15]1其他如胡承珙《毛诗后笺》之释“鞅掌”,丁晏《毛郑诗释》之释“鱣鲔发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释“我马维驹”当为“我马维骄”等等,都是因声求义得出的著名见解。
后儒不明声音通假之理,误以为经书中的假借字为本字,常常非议《郑笺》的“破字”和“改字”。对此,清人的评价最为公允。祁寯藻为沈镐的《毛诗传笺异义解》作序说:
毛公释诗自《尔雅》诂训而外,多用双声取义,或兼取同位相近之声。……此《潜研堂问答》引而申之,足以见古人诂训之学通乎声音,一善也。郑笺多破字,……使人知郑之假借,亦本于毛之谐声,而不得以破字为嫌,二善也。[16]301
也就是说,经书在草创之初常常使用声音通假字,所以才有毛、郑根据声音关系来订正本字的方法。惠士奇、陈寿祺、王引之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王引之《经义述闻序》引王念孙语说:“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学之多假借也。”[14]2郑玄的破字每为后人所诟病,然而乾嘉学者指出,《毛传》已有声训假借之法,《郑笺》发展为“因声求义”的破字之理,所“破”、所“改”实为还原经书的本字。这是清人的卓见,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郑学训诂的帮助很大。清人由此考订《诗经》的本字,补足毛、郑的疏略,或者纠正毛、郑的过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再次,清人对《郑笺》比兴观念的继承与完善。“比兴”是诗经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郑玄等汉儒坚持“兴必取义”之说。朱熹则提出“无甚义理之兴”[17]2128的观点,认为是“发端”的表现法,并无“譬喻”之意义功能。对此,清人多有反对的意见,陈启源“夫全不取义,何以备‘六义’之一乎?”[2]697严虞谆“兴必有所寄托”[18]88、魏源“诗皆以取义为兴”[19]171,以及陈奂“假物明志”的观点都是直接针对朱熹而发的,认为诗中物象皆有譬喻政教的用意。虽然如此,清人也观察到《郑笺》之“迂拙”。补拙的办法,包括体贴物理,找准“起兴”之点。陈启源提倡“必穷研物理,方可与言兴”[2]697,比如根据“震雷”“旱雷”“雨雷”的声音属性,指出《殷其雷》只取“雨雷”之声:“惟殷殷之雷有和豫之义、震动之象,王者政教号令动物而使之和,类此矣。”[2]353又如《四牡》之“鵻”,《郑笺》以鵻鸟的自由来喻说己身之劳苦,马瑞辰则取鵻鸟为“孝鸟”之义,更好地接续了君子“不遑将母”的毛诗义。严虞谆也反对朱熹“兴不取义”之说,认为“格物致知,随所感触,皆有至理”,[18]88“如《关雎》取其‘挚而有别’,《桃夭》取其‘容色少盛’,《卷耳》取其‘酿酒所须’,《草虫》取其‘物类所感’”。[18]88上述诸家精通草木鸟兽之学,在物象与经义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通过补足毛郑的方式更好地继承了毛诗学比兴阐释的义理取向。
清人也善于诉诸情理或情景体验来阐释兴诗的人情诗味。顾镇以为诗兴微妙难言,难以指说,当讽咏诵读间玩其味而达其志。为此批评郑玄和朱熹说:“康成求义太迫,以兴为喻,往往于《传》所不言,亦意为兴致,使比、兴混淆,不分区宇,其昧风人之义,而失毛氏之指远矣。朱子病其淆也,遂谓兴有全不取义,但取一二字相应者,则又矫枉而过之。”[20]380顾镇坚持汉儒“义理之兴”的观点,却不满意郑玄“以兴为喻”“求义太迫”的解释。这是清人的普遍看法,也道出了《郑笺》比兴阐释的症结——由于预设了美刺箴诲的意义终点,便采取了“逐字生解”的方法,将词与物从诗文语境中抽离出来作出政教上的比附,昧于人情诗味。在胡成珙看来,郑玄笺注《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之语,将“拒婚”的贞女解读成“欲婚”的形象,是不合情理的。所著《毛诗后笺》还原贞女面对“诬善之辞”而进行自我辩白的情景,以此兴起“本无犯礼,不畏强暴之侵陵”的《诗序》义,甚为顺畅妥帖。又如方玉润笺注《芣苢》之诗,再现了田家女拾菜欢笑的情景,结题归于“化行俗美”。崔述认为,《江有汜》之诗“自喻身世而已”,而“皆可以见先圣之化,入人之深”。[21]252如此之类,都是联系章句总体,以人情解诗而来的新说,显然比《郑笺》更具诗性活力。其实自宋代以来,人们反驳《郑笺》之“迂”“拙”,已反复强调比、兴之间的区别义,认为郑玄破碎文理,将兴诗解读成诗味索然的比体。这一点,清人论述得更多,也毋庸烦举。陈奂不仅辨别比、兴之别,且于兴体之中分出“即事而言兴者”“离事而言兴者”两种类别,前者取事类而兴,后者基于人情相似,是对毛诗学比兴观念的重要拓展。
三、清人整理《毛诗笺》的局限性
清人整理《郑笺》的研究成果,为现代诗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清人所抉发的诗礼之义,以及毛、郑异同的观点,在今天的不少著作中还能见出其所提供的思路。但是必须指出,清人尤其是乾嘉学术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过分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仅以汉学家法来评判郑学之是非,不惟夸大了《郑笺》的别毛之义,生出不少误指郑之申毛为异毛的误会,更重要的是,乾嘉学者长于知识辨析,略于价值阐释,明显地低估了郑玄诗学所蕴含的儒家意识形态内涵。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今天,仿佛郑玄只是一位精于训诂考据、擅长名物典章之学的知识学家。
但是郑玄并非一个纯粹的知识学家。包括郑玄在内的汉代儒生固然注重训诂考据的基础功夫,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知识理性,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儒家道义精神丝毫不减先秦诸子。因为按照毛诗学的解释流程,由诂、训、传、笺逐级而上指向了《毛诗序》所申发的大义,诗歌在那里被认为是圣人垂教的经典。郑玄就是“据《序》立义”的代表人物,甚至不惜“据《序》驳《传》”。《考槃笺》就是显著的一例,《诗序》以为是讥刺国君冷落贤人的诗歌,《毛传》则认为是歌颂贤人的宽厚之德,能够安享独居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完全放弃了《毛传》的训诂释义,只根据《诗序》敷衍出一个面有“虚乏之色”“怨君不用贤”的穷居者形象来。《宛丘》也是一例,所谓“子之荡兮”一语中的“子”,毛以为指大夫,郑以为指幽公,也是根据《诗序》“刺幽公也”的提示而作出的解释。在郑玄看来,《毛诗序》是子夏亲受圣人之言的产物,而孔子删诗的宗旨乃在于“足作后王之鉴”。所以说,《毛诗序》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儒家意识形态叙事,而郑玄谨遵《诗序》也足以表明其对儒家文化立场的深刻体认。这一点,如果联系郑玄诗、礼之学的总体,则不难体会。众所周知,《郑笺》几乎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文化资源,将《诗经》转换为非美即刺的史鉴文本,以及承担儒学教化的话语系统。而《郑笺》“兴者,喻也”的解释格式,也足以表明他急于教告王者,还唯恐王者不明白的心情。同时,郑注《周礼》强烈表达了“想以官制限制君权,以缓和专制的荼毒”[22]188的用心。这些都说明郑玄在汉代君权独断的处境下并没有忘记使命,而以经典之教来砭抑时政、制衡王权的良苦用心。
在郑学接受史上,宋人斥其“道统不闻”,清人奉为汉学根基,虽褒贬不同,但都大抵着眼于郑学的知识层面,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郑玄为往圣继绝学、为后王立法的宏旨。及至晚清考据学式微,学者们重申明道致用的经学旨趣,也就清晰地观察出乾嘉学的空疏乏术之弊,与此同时,对郑学的义理内涵及其精神诉求多有关注。皮锡瑞即认为“汉学未尝不讲义理”[23]12,表彰郑玄扶微继绝、辅翼圣教的功绩。陈澧指出:“盖自汉季而后,篡弑相仍,攻战日作,夷狄乱中国,佛老蚀圣教,然而经学不衰,仪礼尤重,其源皆出于郑学。”[24]282此虽是过誉之论,却也真实地道出了郑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其维系儒家风教的社会意义。在他看来,郑学兼具训诂与义理,而且意味悠长。陈澧所著《东塾读书记》云:
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此盖伤党锢之祸也。《雨无正》“维曰于仕,孔棘且殆”,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征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24]108
陈澧又著《汉儒通义》提醒学人当注意郑学中的义理信息,他从《郑笺》中整理出37个门类共90条义理语。在陈澧辑录郑学义理语的基础上,今人车行健进而指出:“郑玄在笺《诗》时所显露的对义理问题的思考及其所表现的义理之语自然会偏重在人伦政事方面,但这多少也反映了郑玄思想主人事、重实际、关怀政治现实的倾向。”[25]157总之,郑玄笺诗有“感伤时事语”,既反映了汉末时世对笺诗者的心灵挤压,更于其中融进了儒者的文化情怀。这些“溢出经文之外”的义理也表明郑玄有着系统的重建思考,又何尝不是他感时伤事的别有寄托?在陈澧看来,乾嘉汉学虽宗郑氏,但是仅限于训诂考据和典章名物的学问,未能探得郑学的精义。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