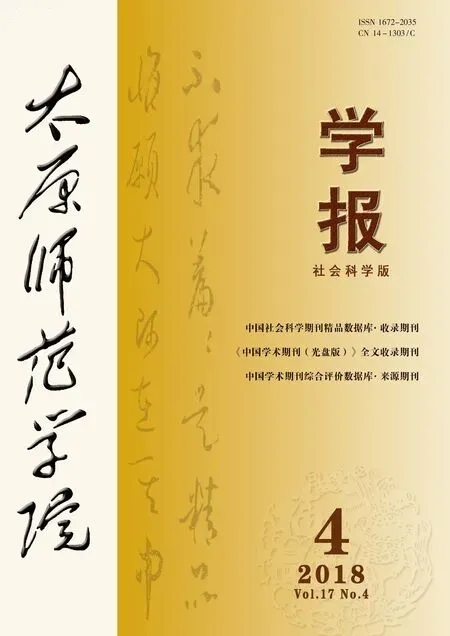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分析
——基于兴衰历程的考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1)
从历史视角来看,丝绸之路*本文所述“丝绸之路”是指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即西北丝绸之路,不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历程呈现出“钟摆”特征,这一演变包含八个完整周期及第九周期的起始期。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丝绸之路的演变处于第九周期起始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推进了丝绸之路的复兴,为丝绸之路兴盛期的长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国外相关文献来看,部分研究者对丝绸之路的缘起及变迁等展开了分析,大部分学者则更为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苏西·丹尼森(Susie Denison)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将更紧密地联结欧亚大陆。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一书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融入全球经济的战略创新。国内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方面:第一,环境或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变迁的相关性。如杜忠潮分析了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的总体兴衰之间的关系[1]50;胡文康探究了新疆段“丝绸之路”变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相关性。[2]第二,某一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变迁。如石云涛指出汉唐期间其起点发生了多次的变迁。[3]183第三,丝绸之路某一段的历史变迁。如苏海洋等撰文分析了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与变迁。[4]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丝绸之路的其他领域,如施张兵分析了当前丝绸之路的中国高铁外交;[5]袁楚风则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探究了国际化企业人权责任的国际司法监督体系。[6]国内外的这些研究成果极具价值,对后续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并未关注以下特征:兴盛和衰落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于丝绸之路的演变历程之中,这种周期性的存在使丝绸之路的演变呈现出“钟摆”特征。从实践层面来看,强化丝绸之路演变历程、演变特征、演变成因及演变趋向等的研究,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鉴于此,有必要在阐述丝绸之路演变历程及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以下问题: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成因有哪些?当代中国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SWOT)是什么?这一演变的趋向是什么?如何推进这一演变?
一、丝绸之路演变历程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标志着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在其后的两千余年中,兴盛和衰落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于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中,由此生成八个完整周期及第九周期的起始期,每一个周期均由一个兴盛期和一个衰落期共同组成,但兴盛期并非意味着整个阶段从未出现衰落迹象,衰落期也并非意味着整个阶段从未出现兴盛迹象:某些兴盛期中曾出现极短时间的衰落年份,但这一衰落并未改变兴盛这一大态势;某些衰落期之中曾出现极短时间的兴盛年份,但这一兴盛并未改变衰落这一大态势。八个完整周期及第九周期的起始期呈现如下:
(一)第一周期(公元前119年—公元72年,共190年)
这一周期始于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7]其后百余年中,西汉王朝在较长时间内比周边政权具有明显优势,丝绸之路一直呈现兴盛状态。这一兴盛状态大概在公元9年被终结。新莽取代西汉之后实施了一些错误政策(如将匈奴王的爵位降为侯爵)导致中原政权逐渐失去在西域的主导地位,丝绸之路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出现第一个衰落期。这一衰落状态在公元73年被终结,中原政权(东汉王朝)重新建立与西域的联系。
(二)第二周期(73—220年,共147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公元73年,在班超的实际运作下,东汉王朝重新建立与西域的联系,[8]16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东汉王朝与西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丝绸之路一直呈现兴盛状态。这一兴盛状态终结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中国北方陷入战乱,丝绸之路的兴盛失去重要支撑因素(中原政局稳定)。这一衰落状态直到曹魏打通西域交通之时(221)才被终结。
(三)第三周期(221—435年,共214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221年,曹魏在河西大破羌胡联军之后遣使复通西域,恢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丝绸之路再次复兴。西晋取代曹魏之后于280年统一全国,强化了丝绸之路的兴盛态势。但这一态势在301年被终止。“八王之乱”爆发、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流民起事,其后中国北方陷入长期混战,丝绸之路转而呈现出衰落状态。尽管西域多国曾在381年和382年遣使向前秦贡其方物,丝绸之路出现复兴迹象,但这一迹象消失于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之后,[9]42未能扭转丝绸之路的衰落状态。这一衰落状态直到北魏重新打通西域之时(436年)才终结。
(四)第四周期(436—623年,共187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436年,北魏使臣成功冲破柔然的阻挠到达西域,随后北魏开始集中力量开拓西域。为了突破战略困局,西魏十分重视与西域诸国发展关系,并于556年开始与突厥缔结军事联盟关系,助推了丝绸之路的兴盛。其后,随着西魏、北周和隋的军事力量增强,丝绸之路日益复兴。这一状态在616年被终止。翟让、窦建德、杜伏威三支起义军在这一年形成,中国北方陷入战乱,丝绸之路的兴盛状态中断。唐王朝建立之后逐渐消灭其他政权,最终于624年平定江南统一全国,终止了丝绸之路的衰落状态。
(五)第五周期(624—978年,共354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624年,唐王朝统一全国之后努力开拓西域,有效地推进了丝绸之路的兴盛。这一状态持续百余年,直到755年被安史之乱终结。[10]25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明显加剧,中央政府权威严重削弱;唐王朝失去对西域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态势已经呈现;西部环境明显恶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丝绸之路进入较长的衰落期,这一状态直到979年北宋灭北汉才被终止。
(六)第六周期(979—1233年,共254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979年,北宋灭北汉后开始日益关注与河西走廊及西域诸政权的交流,丝绸之路开始复兴。与之前的几次复兴相比,丝绸之路此次复兴的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与之前主导复兴的中原政权相比,北宋并未控制西域,甚至长期未能控制河湟地区(仅在北宋末期实现过短期控制)。[11]22这一兴盛期在1125年随着金攻入中原而终结,丝绸之路再次进入衰落期,这一衰落期在1234年金王朝覆灭之时才被终结。
(七)第七周期(1234—1695年,共461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1234年,蒙古帝国与南宋王朝联合灭金,中国北方再次实现统一,中国版图内阻滞丝绸之路复兴的政权全部被消灭,[10]25丝绸之路再次开始复兴。蒙古帝国在亚欧大陆的发展及南宋政权在1279年最终覆亡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兴盛,但这一状态仅持续到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中国再次出现战乱。建立于1368年的明王朝尽管在建立之后逐步扩大了版图,但这一政权始终未能控制西域中西部,察合台及帖木尔等政权长期阻碍明王朝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加之郑和下西洋的出现及之后闭关锁国政策,丝绸之路进入了一个极长的衰落期。这一衰落期直到清政府(1696年)消灭蒙古葛尔丹部才被终结。
(八)第八周期(1696—1988年,共293年)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1696年,清政府在昭莫多之战中消灭蒙古葛尔丹部这一阻滞丝绸之路复兴的政权,丝绸之路再次进入兴盛期。但丝绸之路在这一阶段只是缓慢复兴,虽然中国的政局较为稳定,但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已经完全南移,西部环境继续恶化,丝绸之路上的运输能力和运输成本与千年前相比没有显著提升。丝绸之路这一小幅度的复兴在白莲教起义之时已经式微,1842年之时被终止。《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开始更多地依靠海路贸易,丝绸之路再次进入衰落期,陕甘回乱(始于1864年)和阿古柏入侵新疆(1865年开始)加剧了这一衰落状态。尽管清王朝收复新疆(1877年)和新中国建立曾有效地改善了丝绸之路的状态,但均未能促使丝绸之路再次进入兴盛期。这一衰落期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才被终结。
(九)第九周期起始期(1989年至今)
这一周期的起点是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复兴丝绸之路的阻力显著变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助推了丝绸之路的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及实施使丝绸之路的复兴进入全新时代。
二、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总况及特征
基于演变历程的呈现能够发现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总况,并发现这一演变之中存在的诸多特征。
(一)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总况
基于丝绸之路演变周期的划分可以发现,兴盛与衰落交替出现于丝绸之路的演变历程之中,使丝绸之路的演变呈现出“钟摆运动”状态,由此生成“钟摆”型演变。这一演变的总况见表1:

表1 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总况
注:衰落时期的起始年份计入衰落期时长。比例是指兴盛期时长和衰落期时长在周期时长中所占比例。
从表1中可以看出:
1.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包括八个完整周期和第九周期起始期,不同周期总时长差异明显。时长最短的第二周期仅为147年,时长最长的第七周期长达461年,两者差值为314年,这一差值甚至大于绝大部分周期的总时长。衰落期总时长稍大于兴盛期总时长。
2.不同周期的兴盛期时长较为接近,最小值为第三周期兴盛期的79年,最大值为第四周期兴盛期的179年,两者差值为100年,这一差值仅大于第三周期兴盛期时长,大部分兴盛期时长接近或者等于145年。
3.不同周期兴盛期时长在周期时长中所占比例差异较大,最小值为第七周期兴盛期的25%,最大值为第四周期兴盛期的96%,差值为71%,这一差值甚至大于绝大部分兴盛期时长在周期时长中所占比例。时长较长的衰落期主要出现于唐中期之后。
4.不同周期的衰落期时长差异较大,最小值为第四周期衰落期的8年,最大值为第七周期衰落期的345年,两者差值为337年,这一差值大于第七周期衰落期之外所有周期衰落期的时长。
5.不同周期衰落期时长在周期时长中所占比例差异较大,最小值为第四周期衰落期的4%,最大值为第七周期衰落期的75%,差值为71%,这一差值大于第七周期衰落期之外所有周期衰落期的时长比例。
6.四个兴盛期时长在单个周期中所占比例大于50%,而且主要存在于丝绸之路两千余年演变的前半期(公元前119年至1124年期间);四个衰落期时长在单个周期中所占比例大于50%,较为均匀地分布于丝绸之路两千余年演变历程之中——公元9年至1988年的每一个五百年均存在一个时长比例大于50%的衰落期。
由上分析可知,其演变总体表现为:一是不同周期兴盛阶段的兴盛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如第一周期兴盛阶段(西汉中期)的情况明显差于第五周期的兴盛阶段(唐朝初期)。二是不同周期衰落阶段的衰落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如第六周期衰落阶段(南宋时期)的情况比其他衰落阶段更为严重。三是丝绸之路在某些衰落阶段的情况甚至优于一些兴盛阶段的情况,如清朝后期,丝绸之路的演变处于衰落阶段,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情况明显优于丝绸之路开创期(第一周期的兴盛阶段)。
(二)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特征
1.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长期存在——没有哪一个时期不属于“钟摆”型演变,但“钟摆”型演变不同时期的演变主导成因、演变幅度等存在差异。从丝绸之路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这一“钟摆”型演变具有明显的长期性——丝绸之路一直处于演变过程之中,从未出现静止状态,而且兴盛期和衰落期交替出现于这一演变之中,由此生成丝绸之路的“钟摆”型演变;从发展趋向来看,丝绸之路将出现极长兴盛期,静止状态不可能出现于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之中。如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版图内各政权“治乱状态”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力较大,但这一影响力在12世纪中期较小;从兴盛期的演变幅度对比来看,第五个兴盛期(624—754年)的演变幅度明显大于第八个兴盛期(1696—1841年)的演变幅度。
2.演变由多个阶段共同组成八个完整周期及第九周期起始期,使这一演变呈现出“钟摆”型演变状态。公元前119年至1988年这两千余年之中,基于一些标志性事件发生年份可将丝绸之路演变历程划分为十六个阶段,其中包含八个兴盛阶段和八个衰落阶段,每一个兴盛期均与一个衰落期共同组成一个演变周期。这些阶段的时长存在明显差异,丝绸之路在这些阶段的演变情况、演变的主导成因等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阶段共同组成的八个完整周期且每一个周期均包含一个兴盛期和一个衰落期,由此形成“钟摆”型演变。尽管不同时期丝绸之路演变情况(演变时长及演变幅度等)存在诸多差异,但均包含于某一个周期之中。由此可见,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3.从“时间轴”来看,丝绸之路兴盛期的演变幅度呈现出先扩大再变小这一演变形态,衰落期的演变幅度则主要呈现出不断变小这一演变形态。所谓丝绸之路的演变幅度,即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某一时期与同类别时期相比的兴盛程度大小或衰落程度大小。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不同阶段的演变幅度差异较大,如从兴盛期的对比来看,丝绸之路在第五个兴盛期(624—754年,唐朝前期)的兴盛程度明显大于此前和此后兴盛期的兴盛程度,而且兴盛程度表现出从较低到较高再到较低这一态势。从衰落期的对比来看,最初几个衰落期,常常出现丝绸之路基本被阻断这一情况,但这一情况从未出现于最后几个衰落期之中。
4.现阶段的演变展现出明显的发展性。当前,丝绸之路的演变处于第九周期起始期,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已经形成,丝绸之路的演变展现出明显的发展性,这一发展性的生成源于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效地改善了内部和外部环境并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倡议,这是丝绸之路将出现一个极长兴盛期的重要保障。
三、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成因
基于对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宏观状况及各阶段诸多史实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演变的成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国内部的治乱状态的交替出现
中国内部的“治”状态主要表现于各中原政权的兴盛期,“乱”状态则主要表现于各中原政权的乱局时期或衰落期。中国内部“治”状态的出现能够为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军事环境等,助推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中国内部“乱”状态的出现会导致丝绸之路的演变环境严重恶化,催生丝绸之路衰落期。中国内部的治乱状态的交替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出现。
同一个政权发展状态(兴盛或衰落)的演变会引致其在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如蒙古政权日益兴盛之时,其在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这是第七周期兴盛期(1234—1350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蒙古政权日益衰落之时,其在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起的是消极作用,这是第七周期衰落期(1351—1695年)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北元及后续蒙古政权退回我国北部之后,长期阻滞丝绸之路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原政权兴盛与否对丝绸之路的演变状态(兴盛或衰落)具有重要影响,即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的兴盛期大致与中原政权兴盛期重合,衰落期则大致与中原政权的乱局期或衰落期重合。
具体来说,第一个兴盛期(公元前119年—公元8年)与西汉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二个兴盛期(73—183年)与东汉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三个兴盛期(221—300年)与曹魏和西晋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四个兴盛期(436—615年)与西魏、北周和隋朝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五个兴盛期(624—754年)与唐朝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六个兴盛期(979—1124年)与北宋政权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七个兴盛期(1234—1350年)与元朝的兴盛期大致重合;第八个兴盛期(1696—1841年)与清朝的兴盛期大致重合。
第一个衰落期(9—72年)与新莽时期及西汉初期的乱局时期大致重合;第二个衰落期(184—220年)与东汉政权的衰落期大致重合;第三个衰落期(301—435年)与西晋政权的衰落期及“五胡乱华”时期大致重合;第四个衰落期(616—623年)与隋朝政权的衰落期及唐初乱局期大致重合;第五个衰落期(755—978年)与唐朝政权的衰落期及“五代十国”时期大致重合;第六个衰落期(1125—1233年)与北宋政权的衰落期及蒙古帝国崛起引致的动荡时期大致重合;第七个衰落期(1351—1695年)与蒙古政权的衰落期大致重合;第八个衰落期(1842—1988年)与清朝政权的衰落期、民国时的乱局期及新中国的外部重压期大致重合。
(二)中原政权版图大小及与丝绸之路主要政权关系的变化
某些时期,中国内部各政权均呈现出“治”的状态,但受中原政权版图过小、各政权存在利益纷争等因素影响,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阻滞。如12世纪后期,金、南宋、西夏和西辽等政权均呈现“治”的状态,但丝绸之路的演变呈现出衰落状态,原因主要是金、南宋、西夏和西辽的版图均不够大,中国的丝绸之路区域被多个政权分割,各政权之间存在利益纷争,无法在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形成合力,反而会为了争夺利益而阻滞丝绸之路的发展。与这一状况相反的是唐前期,中原政权版图极大,中国版图内的丝绸之路完全处于唐王朝控制之下,丝绸之路处于畅通状态,丝绸之路兴盛期随之出现。
具体来说,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原政权版图大小对丝绸之路演变状态具有重要影响。中原政权版图较大之时,中国版图内的丝绸之路被一个中原政权控制之时,能够为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良好政治保障、军事保障及经济保障等,关卡较少、政策统一等因素的存在使丝路贸易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率也就相对较高;中原政权版图较小之时,中国版图内的丝绸之路被多个政权控制,丝绸之路的发展难以获得良好的政治保障、军事保障及经济保障等,关卡林立、政策差异较大等因素的存在使丝路贸易成本明显上升,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率也就随之降低。二是中原政权与丝绸之路主要政权关系如何对丝绸之路演变状态具有重要影响。中原政权与丝绸之路主要政权关系良好之时,各政权合力推进丝绸之路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率随之上升;中原政权与丝绸之路主要政权关系较差之时,各政权合力推进丝绸之路发展的可能性较小,丝绸之路呈现出兴盛状态的可能性因而变小。
从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况来看,中原政权版图较大期和较小期常常交替出现,丝绸之路主要政权之间的良好关系与较差关系也常常交替出现,这两种情况对丝绸之路演变过程中出现“钟摆”状态具有重要影响。
(三)中国宏观政策的变化
中国宏观政策的变化主要是指中国版图内主要政权实施的是对外开放政策还是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版图内主要政权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会催生或强化丝绸之路兴盛期;中国版图内主要政权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会催生或强化丝绸之路衰落期。例如,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初期,蒙古帝国及元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是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兴盛期的重要原因;15世纪中期,对外开放政策已经被闭关锁国政策取代,强化了始于14世纪中期的丝绸之路衰落期。这两个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丝绸之路再一次出现“钟摆”型演变。
受版图大小及实力大小等因素影响,某一政权施行哪一类宏观政策并非丝绸之路演变状态的唯一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某一版图较小的政权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不一定能够助推丝绸之路的兴盛(或不一定能够扭转丝绸之路的衰落态势),例如,南宋王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政权地处我国东南,所注重的主要是依靠海上丝绸之路开展对外贸易,因而未能助推丝绸之路的兴盛。某一实力稍弱的政权实施阻断丝绸之路政策不一定能够真正阻滞丝绸之路的兴盛,例如,公元前1世纪,匈奴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试图阻断丝绸之路或控制丝绸之路的一些区域,但这一时期西汉王朝的整体实力强于匈奴,长期控制中国版图内的丝绸之路区域,丝绸之路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兴盛状态。
(四)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的转移
从历史演变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呈现出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渐向东部和东南部转移的态势。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尚处于中原和关中之时,只要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其他要件(如中原政权版图较大且呈现出“治”的状态)基本具备,因经济支持及文化支持的存在,丝绸之路很容易出现兴盛期。例如,东汉后期,中原地区出现严重战乱,丝绸之路进入衰落期,但这一衰落期的持续时间较短(184—220年),这是因为曹魏政权建立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北方的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的情况好转,为丝绸之路兴盛期的重新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曹魏政权建立之后又迅速打通了西域交通,为此开创了丝绸之路第三个兴盛期(221—300年)。
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不再处于中原和关中之时,即使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其他要件(如中原政权版图较大且呈现出“治”的状态)基本具备,因缺乏经济及文化的足够支持,丝绸之路较难出现兴盛期。例如,明朝中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已经完全转移至东部和东南部,这些区域紧邻海洋,依靠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对外贸易更为便捷、更为有效,这一情况的出现对第七个衰落期(1351—1695年)影响很大,是这个衰落期持续较长的重要原因。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向东部和东南部转移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盛,在某种程度上对(西北)丝绸之路形成一定压制,增加了(西北)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难度,延长了(西北)丝绸之路衰落期的时长,这意味着(西北)丝绸之路再次出现“钟摆”型演变的难度变大;丝绸之路兴盛期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版图内丝绸之路区域完全被一个政权控制,换言之,如果中国版图内丝绸之路区域被一个以上政权控制且这些政权之间的关系较差,丝绸之路兴盛期就不会出现,此即丝绸之路在元朝前期和清朝前期出现兴盛期但未在明朝时期(明朝未能控制西域大部分区域)出现兴盛期的重要原因。
基于历史比较可以发现,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持续恶化态势。这一情况的存在意味着依靠丝绸之路展开贸易的难度逐渐变大。从实例来看,丝绸之路开通早期,丝绸之路沿线诸多地方水草丰美(尤其是河西走廊部分地区),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较容易找到宿营地、补给站,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难度较小;丝绸之路开通数百年之后,受战乱、气候变化等影响,丝绸之路沿线环境逐渐恶化,诸多原本水草丰美之地变为荒漠,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较难找到宿营地、补给站,丝绸之路兴盛期的出现难度变大,这是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过程中第七个衰落期和第八个衰落期出现且持续时间极长的重要原因。而今,由于受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实行环境保护和恢复政策的影响,丝绸之路沿线环境逐渐呈现出好的态势,这为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过程中第九个兴盛期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能力相比,(西北)丝绸之路的运输能力明显较低且成本较高,这一情况的存在是诸多商人在较长时期内倾向于选择用海上丝绸之路展开贸易的重要原因,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之后(西北)丝绸之路较难出现兴盛期的重要原因。例如,(西北)丝绸之路第六个衰落期(1125—1233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南宋努力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展开对外贸易,这是(西北)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一直呈现出衰落状态的重要原因。当丝绸之路的运输能力显著提升、运输成本明显下降之时,其出现兴盛期的可能性随之变大。例如,近年中国在尖端技术的支撑下持续构建高铁网络,有效地提升了丝绸之路的运输能力且降低了运输成本,为丝绸之路第九个兴盛期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进了丝绸之路的“钟摆”型演变。
四、当代中国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SWOT分析
(一)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拥有的优势(S)
中国政局稳定且统一态势不断强化,不会再出现阻滞甚至中断丝绸之路复兴的内乱;中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闭关锁国政策不会再次出现;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绝大部分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单一国家阻断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并形成多个发展中心,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西部环境逐渐优化、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且运输成本持续下降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极具优势。
(二)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存在的劣势(W)
中国国内实现经济协同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不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些省份可能更倾向于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开贸易,丝绸之路的复兴也就较难获得最大的助力;一些国家深刻领略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之后纷纷加以效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日益趋同,抢夺了中国的一些发展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阻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涉及多种文化,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的某些冲突会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阻滞;近年,中国的诸多资源被用于地标式建筑、运动会等,未用于科技和民生等领域,且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有所下降,内需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了阻滞。
(三)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拥有的机遇(O)
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欧洲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出现强化态势,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等事件的出现加深了欧洲的“内乱”程度,欧盟各国已经较难联合出台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政策;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倾向于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为突破“马六甲海峡困局”而加强中巴经济走廊、中缅油气管道等建设,强化了丝绸之路的复兴态势。
(四)推进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面临的威胁(T)
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出于各种目的或明或暗地阻滞丝绸之路的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一些国家(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政局不稳;中国需要稳定、安全的环境来实现复兴,与中国存在争端的一些国家有可能因为意识到“中国通常不愿意破坏稳定、安全的环境”而采取一些措施在争端中获利,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形成阻滞。
五、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趋向及复兴丝绸之路的途径
当前,丝绸之路的“钟摆”型演变正处于第九周期起始期,中国在这一时期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复兴丝绸之路。在准确分析复兴丝绸之路的SWOT及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趋向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因素的具体情况实施一些举措有助于实现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第九周期兴盛期的持续发展,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
(一)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趋向
20世纪80年代末,丝绸之路进入新的兴盛期,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强化了这一复兴态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及实施则使丝绸之路的复兴进入全新时代。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丝绸之路的复兴具有如下一些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态势不断强化,各领域快速发展,催生内乱的因素不断减少,不会再出现阻滞甚至中断丝绸之路复兴的内乱;二是中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闭关锁国政策不会再次出现;三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经济发展迅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涉国家积极响应这一倡议,单一国家阻断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四是经济发展多中心状态的出现;五是西部环境的优化、运输能力的上升及运输成本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致力于在复兴丝绸之路过程中减少劣势、抓住机遇、消除威胁。从宏观上来看,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的第九周期(1989年至今)将出现一个极长兴盛期,而且这一兴盛期中丝绸之路的兴盛程度会显著高于历史上所有兴盛期。
(二)复兴丝绸之路的途径
1.强化优势。优化发展环境,持续推进中国各领域的发展,为丝绸之路兴盛期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努力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建设,防范闭关锁国政策的再次出现;在继续强化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保持或优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绝大部分国家的良好关系,进一步降低这些国家阻断丝绸之路的可能性;推进中西部经济核心区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复兴丝绸之路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推进西部环境的优化,并完善中国现有的交通网络,为丝绸之路运输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创造条件。
2.减少劣势。中国有必要在复兴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采取一些举措减少劣势,如,强化国内的经济协同发展,促使不属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省份成为复兴丝绸之路的强大“腹地”,增加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助推力;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努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强化中华文化的和谐观,降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出现冲突的可能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缓公共投资边际效益下降速度,化解内需结构性矛盾,以助力丝绸之路的复兴。
3.抓住机遇。中国须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增强经济实力,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目前,欧洲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较大困难,中国可以抓住这一时机进一步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消除这些国家联合出台不利于中国的政策的可能性。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宣传,在这一基础上深化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中国须进一步加强中巴经济走廊、中缅油气管道等建设,为丝绸之路的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4.消除威胁。对试图阻滞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国家采取反制策略,消除或减少这些国家的威胁。加强对政局不稳的国家现状的分析,准确判断这些国家政局的发展趋向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定正确的决策,避免这些国家政局动荡对中国复兴丝绸之路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多种策略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使试图危害中国利益的国家明白中国不会为了获得稳定、安全的环境而放弃国家利益,消除这些国家试图阻滞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幻想。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组成部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实施能够助推丝绸之路的复兴,使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第九周期兴盛期长期繁荣发展,为中国的复兴创造有利条件。这一过程中,中国拥有诸多优势,也存在一些劣势,面临很多机遇和威胁,强化优势、减少劣势、抓住机遇并消除威胁有助于推动丝绸之路“钟摆”型演变,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远比理论研判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采取哪些举措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有待理论研究者及实践者进一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