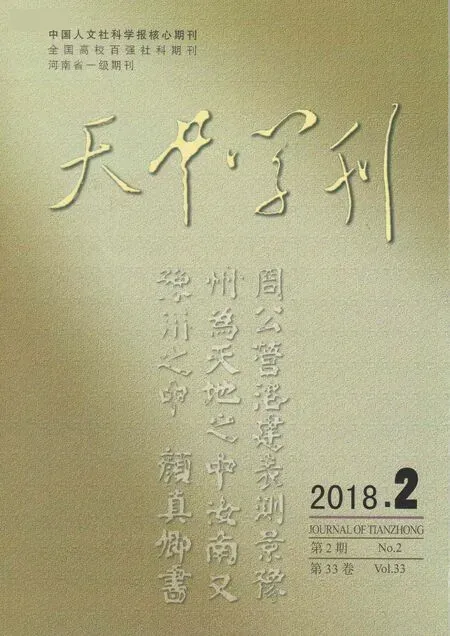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观及题跋诗创作之比较
傅元琼
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观及题跋诗创作之比较
傅元琼
(泰州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姚鼐居京时常与翁方纲谈诗论文,二人思想有契合处,亦有分歧。他们都主张中和汉宋学,持义理、考据、词章结合的文章学观点。但翁方纲力倡学人之诗,以补明诗之失;姚鼐崇尚文人之诗,对何景明、李梦阳等人多有推崇。然二人题跋诗创作,皆具质实风格。翁诗屡为人诟病的“少性情”,虽与其诗学观有关,但亦与其题跋文体的大量创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翁方纲;姚鼐;诗文观;题跋
翁方纲、姚鼐同处乾嘉时期,都反对将汉宋之学截然对立;姚鼐为文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翁方纲也把此当作诗文创作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然姚鼐以文章学为后人所推重,翁方纲则以诗学、金石学著称。二人术业之别,使其义理、考订、词章并重的主张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姚鼐的文章成为古文创作的典范作品,而翁方纲的诗文则因考据、金石书画之学的融入而为人所诟病。这种由于诗文观的不同而呈现的差异早在姚鼐与翁方纲的论学、商讨中已有明显表现。
一、姚鼐与翁方纲的“药言”之交
姚鼐长翁方纲两岁,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据《姚惜抱先生年谱》,“(乾隆)乙亥(1755年),先生年二十五岁居京师”[1],在中进士前近10年的时间里,姚鼐移居京师立馆任教,结交名士。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春姚鼐辞官返乡,居京约20年。此间翁方纲与姚鼐多有交往,这种交往在同编四库全书时尤为密切。据《翁氏家事略记》《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自癸巳春入院修书……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2]72–73;“自壬辰(1772年)、癸巳以后,每月与钱萚石、程鱼门、姚姬川、严冬友诸人作诗课”[2]74,诗文甚至是金石书画都成为他们之间谈论的话题。姚鼐虽年长,但由于翁方纲本为京都人士,友朋如云,且弱冠中举,至姚鼐中进士,翁方纲已为官十多年。加上其治学勤谨,多为友朋推敬,这些皆决定了在姚、翁二人的交往中,翁方纲所处的政治、学术地位要比姚鼐高得多。考察姚、翁交往,不难发现翁方纲在二人交游圈中的核心地位。
翁方纲时常邀请友朋集会,姚鼐曾多次为其中的一员。现姚鼐集中存《为翁正三学士题东坡天际乌云帖》《花朝雪集覃溪学士家归作此诗》《七夕集覃溪学士家观祈巧图或以为唐张萱笔也》《今岁重九翁覃溪学士登法源寺阁,作“斫”字韵七言诗,亦以属鼐而未暇为也。学士屡用其韵为诗,益奇。腊月饮学士家,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苏诗,旧藏宋中丞家者,欣赏无已,乃次重九诗韵》《冬至大风雪,次日同钱萚石詹事、程鱼门吏部、翁覃溪、钱辛楣两学士、曹习庵中允、陆耳山刑部集吴白华侍读寓,同赋得三字三十韵》等作品,可略窥姚鼐与翁方纲及其他友朋之间的交往情况。4次集会中有3次以翁方纲的家院为集会地,翁方纲在集会中的主导作用由此可略知一二。姚鼐对翁方纲的苏米斋曾赋诗曰:“宋贤遗故迹,乃在岭南山。海上流云气,冥蒙石壁间。披榛逢节使,摹石载舟还。远兴高斋对,犹令客动颜。”[3]544此诗从翁方纲祖籍福建莆田写起,紧扣其金石书画爱好及收藏,并刻画出覃溪当时聚客苏米斋共赏金石的情景。另姚鼐有《十一月十五日,雪,翁正三学士偕钱萚石詹事、辛楣学士登陶然亭,回至鼐寓舍,与程鱼门吏部、曹来殷赞善、吴白华侍读、陆耳山刑部同饮至夜,翁用东坡〈清虚堂〉韵作诗垂示,辄依奉和并呈诸公》等诗,也可证明翁方纲当时在翁、姚等人交往中的核心地位。
在翁方纲的集子中,提及与姚鼐交往的作品也不少见。《晨起同姬川陶然亭作》创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仲子自江南寄近作学古诗相质,因赋诗5首以代面谈,兼寄呈述庵、辛楣、姬川、端林》创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感旧》创作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这些作品皆是翁方纲与姚鼐几十年友谊的见证。
然而,在翁方纲与姚鼐的交往中,二人由于见解主张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与辩争也时有发生。翁方纲《感旧》曰:
昔从择友初,辛苦求良药。孰以汉学师,心弗宋儒怍。中间卢与姚,往复盟言酌……尚想桂宧灯,订我瀛池诺。(姬川南归时,于鱼门桂宧饯筵,屡及校雠时相箴切语。)竟尔雄辨骋,渐即偭规错。不以虚怀贮,安得深根托……苦言辣可憎,正未深咀嚼。(昔送姬川诗有“苦言近辣有人憎”之句,姬川作色曰:“鼐非敢憎也!”)俱成八十翁,岂比偶语谑。未得置书邮,暇且旧句削。[4]282
此诗作于耄耋之年。翁方纲回忆他与姚鼐之间的交往,颇有诤友如良药之叹。诗中提及“苦言近辣有人憎”句,见于翁方纲《送姚姬川郎中假归桐城五首》其五,诗曰:“新蔬软脆带春冰,风味端宜笋蕨胜。淡意回甘无物喻,苦言近辣有人憎……”[5]456–457此诗创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春姚鼐离京南归之际,当时姚鼐、翁方纲仅40余岁。翁方纲自言“苦言近辣”,而姚鼐因此而“作色”,不难猜测二人当初论学时相互之间的些许不快。其他4首诗记述同朝为官、同纂《四库》之情谊,论诗谈文,亦及学术及姚鼐辞官养亲之事。在姚鼐南下友朋写下的众多赠别诗作中,翁方纲所作算是其中篇幅较长者。除此之外,翁方纲还曾作赠序一则:
姬川郎中与方纲昔同馆,今同修四库书;一旦以养亲去,方纲将受言之恐后,而敢于有言者: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川自此将日闻甘言,不复闻药言,更将渐习之久,而其于人也,亦自不发药言矣。此势所必至者也。夫所谓药者必有其方,如方纲者,待药于君者也,安能为君作药言乎?吾友有钱子者,其人仁义人也。其于学行文章深得人意中所欲言,愿姬川之闻其药言也。君之门有孔生者,其人英异人也。其于学行文章乐受人之言,愿姬川之发其药言也。[6]494–496
此序颇耐人寻味,其中“药言”一词反复被提及。“药言”最早见于贾谊《新书》卷九“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7],盖指有助于国治民安的言论。而翁方纲文中所指,则是逆耳忠言。上文《感旧》中“昔从择友初,辛苦求良药”与此序中的“药言”相呼应,是翁方纲对40年前与姚鼐相处之事的回忆。逆耳之言,多不同于自己的见解,从“药言”中亦不难体味二人在学术或诗文方面的相互辩难。同时,此序写得情真意切,可见翁方纲的一片真诚。
二、“读常见书”与翁、姚诗文观的分歧
姚鼐主张读常见之书,影响极为广泛。此语首见于《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由姚鼐南归,翁方纲送行引发:
当是时,学者多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诋为空疏,掊击不遗余力,先生独反复辨论。尝言“读书者求有益于吾身心也,程子以记史书为玩物丧志,若今之为汉学者以搜残举碎、人所罕见者为功,其玩物不尤甚耶?”濒行,翁覃溪学士来乞言,先生曰:“诸君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8]
姚鼐不主张汉宋之学两立的思想由此可见一二。“乞言”事后被《经学通论》[9]《东溟文集》[10]等多书引载。此事翁方纲、姚鼐著作皆不存,且颇具传奇色彩,“乞言”二字不切合二人当时身份及在文坛中的地位,也不符合送别场景,略有抬高姚鼐的意味。而翁方纲在《渔洋载书图》的题跋中也有关于读常见之书的阐述:“况所谓真读书者,元止在童而习之之诸经、正史,穿穴玩索,且终身不能竟矣。彼拨弃目前常见之书而高谈耳目之所未及者,本非读书,直以邀名耳。”[6]1348–1351此语较姚鼐之论又入木三分。读“常见之书”,不论是翁、姚二人平日论学时的话题还是确为姚鼐的临行之言,由此可见翁方纲与姚鼐的学术观点的挈合并不局限于中和汉宋之学,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不可偏废,他们二人作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有着更多相同见解与更多相互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
翁方纲与姚鼐的交往在姚鼐南下之前较为密切,他们二人的见解既有契合处又有分歧。对二人的冲突我们从翁方纲赠序与赠别诗可知其大略,而真正能反映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则在二人的讨论中。这些讨论,或面议或书面交流,而书信,无疑是我们今天探究二人此类交流的最佳媒介。姚鼐有一篇颇能代表其文章学主张的作品《与翁学士书》,是其与翁方纲在文学主张方面见解不同而激发创作的一篇作品,文如下:
鼐再拜,谨上覃溪先生几下。昨相见承教,勉以为文之法,早起又得手书,劝掖益至,非相爱深,欲增进所不逮,曷为若此?鼐诚感荷不敢忘。虽然,鼐闻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勾)磬折,支左诎右;其释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师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伦蒙古人之射,倾首,欹肩,偻背,发则口目皆动,见者莫不笑之。然而索伦蒙古之射远贯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则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是安得有定法哉?
自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赵宋、元、明及今日,能为诗者殆数千人,而最工者数十人。此数十人,其体制固不同,所同者,意与气足主乎辞而已。人情执其学所从入者为是,而以人之学皆非也;及易人而观之,则亦然……鼐诚不工于诗,然为之数十年矣。至京师,见诸才贤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见者五六人,皆鼐所欲取其善以为师者。虽然,使鼐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则鼐尚未知所适从也。[3]84–85
此文诗文兼论,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针对诗文有无定法发表见解。姚鼐以射箭无定法比附诗文无定法可循,生动形象,却不无戏谑之意,尤其是对善射者及其弟子与蒙古人相比时的窘态,实是对翁方纲所论之法的一种侧面敲击。针对翁方纲所言的“为文之法”,姚鼐提出诗文创作“非有定法”。很明显,姚鼐是以“非有定法”驳斥与拒绝“为文之法”。言辞之中看似恭敬,但其中的不屑也表露无遗。其二,强调“意”与“气”与诗文之美的重要性。姚鼐把立意看作诗文是否优美的要素,认为“诗文美者,命意必善”;又把“气”看作诗文作品的灵魂:“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3]84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意、气、辞、声音、节奏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彩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3]84–85这些论述实际是在表达自己的诗文创作之法。姚鼐在论其法完毕后做出“是安得有定法哉”的反问,其实是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抛出自我之法,并否定翁方纲关于“法”的理论。其三,陈述自己“法乎众”的观点,以“法乎众”来拒绝翁方纲的一己之法。翁方纲论诗反对拟古,主张“师法古人,以质厚为本”“学古而不泥古”。翁方纲的这些主张在姚鼐看来是遵从翁方纲一人之法,同时又是对众家之法的忽略。因而,姚鼐对翁方纲建议有所抗拒。
在《与翁学士书》整则书信中,姚鼐言语看似谦恭有礼,实则对翁方纲建议的反对与抗拒异常决绝,其中不仅无半点思索接受的诚意且多有不屑、调谑之言,甚至在反驳过程中,故意出现偏激、矛盾之论,一面言无定法,一面以己之法作为驳斥翁方纲的武器。同时,以自己所认为的法乎善,影射翁方纲论之不善,以一己所论的“法乎众”,来拒绝翁方纲主张的“师法古人”。整篇文章,姚鼐毫不领情的意气充斥其中,可算得上是一篇体现其诗文重“意”“气”的典范之作。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二曰:“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11]然从姚鼐此书及翁方纲耄耋之年回忆的因赠别句而“作色”看,却颇见其“接人极和蔼”的另一面。从书信及翁方纲的回忆来看,若非缘于姚鼐当时的年轻气盛,则可知翁方纲、姚鼐二人歧见之深。
与姚鼐的回复相比,翁方纲写给姚鼐的书信则显示出较为明显的质厚平和风格。姚鼐《与翁学士书》的创作精确时间已难考定,据《桐城派三祖年谱》,此文作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或稍前后,作《答翁学士(覃溪)书》”[12]。在此文创作较为接近的一段时期,翁方钢曾写给姚鼐两封论诗书信,分别为《与姬川郎中论何李书》《再与姬川论何李书》。这两封信存于《复初斋文稿》第一册。前一封记于《同馆送姚姬川郎中序》文之前,与一些题跋文相混录入,大约占纸五页,前两页所记位置在题跋文的页眉处,第三、四页页眉、正文位置皆为此文,第五页页面部分记乙未年正月事,是一则关于孟法师碑的题跋。而书信文字与此跋穿插录入,穿插处信文小于页眉处无穿插者。《再与姬川论何李书》是与序文混杂而录,书信的部分篇幅记于其他文章文字的页眉空隙处,同时前后又各有整页纸张书写者。如此混杂的录入方式,或是由于书信过长,翁方纲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在写作过程中插入其他作品的创作;或是此文早已经完成,翁方纲为保存文献,重新把与姚鼐交往的资料记入赠序前后,而从文字嵌入的方式来看,书信屈就其他文字的迹象更为明显,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此两封信的创作日期极有可能要早于与其混杂而录的页面文字的创作日期。在第一封信之前及第二封信之后所记录的两篇题跋作品的日期分别为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与四月;《同馆送姚姬川郎中序》文云:“乾隆三十九年冬,姬川郎中以养母告归,明年春将出都,以诗别馆中僚友……馆中人慕其孝养之诚,咸和诗以美之,而属方纲为之序。”[13]100–102据《惜抱轩诗文集》诗集,卷八有《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乙未为乾隆四十年,而在此前并无此类诗作,翁方纲所做的五首赠别诗后有小注曰“以下乙未”,也是创作于乾隆四十年。以此与序参读可知,此序的创作时间为乾隆四十年春,且极有可能在二月至四月间。同时,我们也可得出结论,翁方纲写给姚鼐的两封书信,创作时间应不晚于这段时间,或与姚鼐所作《与翁学士书》的时间较为相近。然从内容上看,这两封书信似并非姚鼐回复中所提及的“手书”。此二书却在反映二人“药言”之交上,较为突出地代表了翁方纲的态度,并集中体现了翁方纲的诗学观点。
翁方纲的诗学理论“肌理说”的提出是为消除明代诗歌诸家泥古、虚空的弊端。李梦阳、何景明是前七子的领军人物,前七子为反对台阁体的诗风,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一些生机,然由于过分强调复古,又有其弊端。反对前七子的过分拟古,是翁方纲诗歌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翁方纲的《与姬川郎中论何李书》《再与姬川郎中论何李书》二文篇幅极长,在翁方纲诗文中比较少见。第一书开篇曰:
君子不以鄙言为妄,容而纳之,且或动见颜色。方纲于今世未见有受言若此者,非执事性肫挚而契进于善不能及此。以方纲之愚,复何敢有所论辨以渎左右?而今有不得不明白剖说者。昨见㧑约道执事所以成就惓惓之意,于诗则曰宜法何、李,此方纲所以不能嘿息者也。[13]89
㧑约姓孔名广森,受知于姚鼐。翁方纲曾作《孔㧑约集序》,其中称自己与㧑约“相与对榻论析非一日矣”[6]138–139,可见二人交往亦较频繁。此信由翁方纲听孔广森言姚鼐建议其学诗宜法何景明、李梦阳引发,然由开头几句极易品得翁、姚二人曾经交往的不愉快。但翁方纲此番有关何、李诗的论述却不厌其烦,他陈述自己的观点,指摘何、李之诗的弊端,认为何、李之诗对于盛唐诗歌来说,是“袭其貌,演其腔,吞剥其句与言,在明人已有剪彩为花、木鱼为馔、尸舍珠贝为珥之喻矣。此即语言气象,尚且不得谓之肖”[13]91。何、李诗只得盛唐诗之貌而不得其神,早在明代已有人批驳。在翁方纲看来,何、李诗之长在语言气象,不足在缺乏根柢融贯。因此,他以根柢之虚空而否定前七子,而重视意、气、辞的姚鼐对以语言气象见长的何、李诗持认可态度,则难免使二人的诗学观点呈现对立状态。接下来是翁方纲对其重视“根柢”的解释:“若以根柢言之,则唐人各有唐人之学识,凡一家之气、体、声、律,皆有其自出之本焉。自出之本奈何?曰性情而已矣,时势而已矣,境遇、学术而已矣。”[13]91以唐及唐前各家诗作各有自家特色来反证前七子模拟之非,主张在义理上与古人合,而不仅仅是貌袭。最后从学术角度论述前七子诗歌之不可学的原因,进一步批驳李、何诗“意气凌人,虚骄而已”的弊端,并称:“使昔之献吉、仲默生于今日,将亦必帖然平心,去其矜骄之气,而为质实之言。举所谓空同、大复集者,厌而自焚之矣,而岂有吾辈尚学之理哉?”[13]92–93以何、李若生清代当自焚其诗反对姚鼐学习何、李之诗的主张,极有力度。如果姚鼐之《与翁学士书》是对此类书信的回复,其中的意气蓬勃、当仁不让或并不难理解。同时,翁方纲以“矜骄之气”与“质实之言”相对,提出自己反对气盛之诗的观点。从姚鼐书对意、气、辞等的强调,也可看出二人诗学观点分歧的针锋相对。
但翁方纲此信与姚鼐书不同的是,不仅其论证有力,且语气较为诚恳。信末云:“何、李在诗家为前辈,方纲岂敢僭论?顾学者用力之途,则不可误涉足焉,不仅为㧑约也。抑犹望于执事之尽弃其夙闻,于何、李之为诗者而易辙焉。则作诗与解经诚为一事矣,不然则学自学,而诗自诗,诚其人而伪其言也,窃为执事惜。”[13]93–94翁方纲反复强调以学为诗,学诗结合,真诚劝说姚鼐放弃对何、李诗歌的推崇,确如姚鼐书中所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吐胸臆相教”。在此书后,翁方纲又作《再与姬川论何李书》,此书乃抱疾而作,但更加不厌其详,尤见翁方纲待人赤诚。书信开篇多为套语。然覃溪与姚鼐论何、李诗的第二书,则以肺腑之言始。其曰:“君子之学,未有以口舌争者也,以心融而已;未有以意气胜者也,以心平而已……而谓方纲不喜何、李,不深求之,其可乎?夫何、李则奚性情学术之有哉?此言一出,似乎过当。而方纲敢于为此言者,试观其集而知之矣。”[13]97“心融”是翁方纲的待人之道,“心平”,则见翁方纲之秉性。不以口舌争,不以意气盛,或是针对姚鼐之回信有感而发。姚鼐此书今不见于其文集,书信内容、态度我们只能从翁方纲的回信中略知一二。翁方纲的回复中多提及姚鼐书信所涉言语。对姚鼐“谓方纲不喜何、李,不深求之”“谓方纲论明诗太过”“谓学杜者昌黎、子瞻、山谷、空同(李梦阳)俱在宋二陈(陈与义、陈师道)、海叟(袁凯)之上”等问题[13]98,翁方纲分别给予详细答复并结合具体实例,说明何、李诗歌复古模拟之弊,甚至其对后七子的影响也剖论甚详;并借姜夔语,以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为例,表达自己“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的观点①[13]98,同时以证何景明、李梦阳等人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若使何、李早悟,有何、李之笔力气魄,而充以自己实学实境,则明之诗可以云诗矣”[13]102,从而阐明其“以学为诗”的诗学主张,并再次把此主张推荐给姚鼐,认为“执事之学之识,则可以为诗者也,则可以为经学,诗学合一之诗者也。既可以为第一等之诗,而甘为等而下之之诗,曰何、李固当如此也。明人固皆尝如此也,执事请反而思之,恐当哑然自笑者也”[13]103–104。翁方纲推行自己的诗学主张,劝告友人的不懈与不厌其烦,颇见其为学之执着与为人之挚诚。同时,翁方纲质厚平和的文风在此二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质厚平和,是翁方纲诗文的总体风格,也是其性情在诗文中的反映。
综观姚鼐、翁方纲的论诗书,不难发现二者在诗学观点与文章创作风格方面存在的差异。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姚鼐论诗主张意、气、辞三者并重,提倡文人之诗的创作,而翁方纲则将为文之法融入诗歌创作,提倡笔力气魄与实学熔为一炉的质厚平和的“学人之诗”。翁方纲与姚鼐之间的论争,归根到底是由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不同而引发;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主张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和此二人作为金石学家与文章学家各自不同的专长有着莫大关系。翁、姚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诗歌创作中也各自呈现不同的书写视角。
三、翁方纲与姚鼐题跋的比较
翁方纲诗歌较为质实,而姚鼐的诗歌创作则相对更重意境气势。现以二人对同一幅《祈巧图》的题跋为例略作分析。张宣《祈巧图》,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八,又称《汉宫祈巧图》:“绢本,挂幅长四尺七寸,阔三尺二寸,唐张萱真迹,流传者绝少,此图乃其尤最者。向蔵宣和御府,所作朱栏碧瓦,曲折工丽,极尽六宫之胜,几筵盘盂,种种臻妙。宫嫔三十一人,晚妆妍靓,端雅丰厚,各具意态。至于庭柯掩霭,俨然夜色,洵非神手不办也。”[14]姚鼐、翁方纲题跋张宣《祈巧图》是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的七夕。此图当时为陆费墀收藏,七夕日,由陆氏携至翁方纲苏米斋。当时共同欣赏者还有钱载、钱大昕、程晋芳、曹仁虎、陆锡熊诸人。关于此图,翁方纲作《七夕萚石、辛楣、鱼门、习庵、姬川、耳山、丹叔小集苏米斋,丹叔携所藏唐张萱〈祈巧图〉同赋》,诗曰:
去秋秋暑非积霖,椒花舫子书不蟫(鱼门、寓斋)。斜街斜月上我襟,此帧在壁静愔愔。瓜花匜粉围鼎琛,一人顾步梧影森,二人昂首同穿针。戏盆者亦绣帨紟,一掩纨扇旁沈吟,一于树侧三花阴。花复绕出于髻簪,葵黄桂净露涔涔。我时送友凉不禁,更订斯夕指斯今。聚散阴雨毎难任,八人如期果招寻。我斋虽浅坐转深,绢端如有风露音。兰堂玉殿锵鸣金,神光离合灯不侵。九衢人海几同岑,斯夕觞为斯画斟。寸丝零落如球琳,生气炯炯栏砌林。照见世间隙驹骎,多少匠巧枨触心。三伏已过云不霒,空窗卷待白河沈,曙光耿耿闻惊禽。[5]450
姚鼐作《七夕集覃溪学士家观〈祈巧图〉,或以为唐张萱笔也》,曰:
骊山秋树围宫殿,列屋同居异欢宴。人人七夕望牵牛,岁岁秋风落团扇。渭南渭北明河光,张生腕底风露凉。定知纨袖停针后,金井殒梧听漏长。玉貌绮罗天宝末,霜霰未深炎已夺。宫中儿女为情死,墙外书生筹国活。烧烛披图又一时,夜深题作女郎诗。青天纤月长如此,巧拙人闲那得知。[3]457
翁、姚二诗一立足画作原貌及与之相关的事实的再现,一立足于自我情怀及人生命运、兴废之感的抒发。前者注重的是学术,出于一金石学家的责任。后者注重的是抒情,有浓郁的抒情言志的传统特色。两首诗作,一为客观题记,一为主观写情,分别代表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特色。如果以文人之诗的标准衡量,翁方纲的作品无疑难与姚作比肩;但若从学人之诗的角度考量,则翁方纲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为我们了解《祈巧图》所发挥的题跋功能同样为姚鼐诗所无法比拟。
翁方纲与姚鼐关于《祈巧图》的题跋大体代表了二人诗歌的基本特色。然翁方纲其他题材的诗作及部分题跋诗尤其是题画诗中,也不乏文人之诗的作品。而对于姚鼐来说,文人之诗是其诗歌的主要创作类型,但从题跋类作品来看,其诗作也有一些受题跋文体学术性相对较强的影响,更具学人之诗的特征。如《今岁重九翁覃溪学士登法源寺阁,作“斫”字韵七言诗,亦以属鼐而未暇为也。学士屡用其韵为诗,益奇。腊月饮学士家,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苏诗,旧藏宋中丞家者,欣赏无已,乃次重九诗韵》:
学士金石搜南朔,揽异为诗工刻斫。闭门高兴逸如云,舒纸挥毫疾逾飑。今秋九月金垂砌,西岭无云玉出璞。霜寒勇上寺楼看,风舞悬幡翩不卓。成诗渊海得骊珠,欲和空仓饥雀啄。兹晨招客为看书,来似鸿俦飞扑扑。雕镌远有嘉泰字,收藏近与商邱较。苏诗传世几千首,高语去天真一握。当年狱案可悲伤,他日注家还舛驳。此编晚出施顾手,党禁正解东南角。后来补阙更何如,虎贲虽在中郎邈。耽诗爱古皆结习,计短衡长非大觉。曾薄富贵书何厚,甘典衣裘襟可捉。子瞻自是千载人,学士岂比无心学。佳本与公吾亦欣,叩门会办来观数。[3]457–458
另如《为翁正三学士题东坡天际乌云帖》:
东坡自谓字无法,天巧绳墨何从施。青霄碧海纵游戏,自中律度精毫厘。尝托西湖佳丽地,仍记闲情书小诗。前人不见蔡君谟,后人不识柯九思。人生翰墨细事耳,古今相接良赖之。学士新作苏米斋,欲饱看字輖饥。此册神妙尤所秘,云烟阅世怜公痴。今朝我更作公病,敛册向箧重手持。日午来看到昏黑,兀兀不乐归车驰。学士平生妙临本,试作尝眩真鉴知。请烦冰雪襟怀手,再写佳人绝妙辞。[3]452
此诗的重客观与翁方纲《祈巧诗》并无太大区别,笔法平实,呈现出与《七夕集覃溪学士家观〈祈巧图〉,或以为唐张萱笔也》截然不同的风格。然而,姚鼐的题跋诗作以题画诗为主,画作题跋多以画面景、物、事触动作者思绪与情感,从而与画作产生共鸣,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翁方纲主张以学为诗,但其题画诗中,主观情感表达相对碑刻、书法题跋较常见。姚鼐的题画之作更加如此,但以上所举几例也在一个侧面表明实学盛行的时代即使是不主张以学为诗的文人,其题跋也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一些重实色彩。而翁方纲作为当时金石之学的擎天柱,在学术责任感与实学之风的影响下,作品重学重实风格的出现,有其合理性。翁方纲以金石书画之学入诗,也是在“肌理说”的约束与指导下,尝试在诗歌创作中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结合,使诗歌在承载学术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其审美价值。
翁方纲与姚鼐多次论争,表现了二人在诗歌创作中的分歧,而金石书画题跋风格的相似,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石书画题跋的文体传统所决定。文章学家与金石学家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二人在散文创作中金石书画题跋文体所占比例的差距。翁方纲大量金石书画题跋的创作,影响着其诗文整体风格,从而使质实、多考订等题跋文体通常具备的因素,成为以审美为评判标准而忽略题跋文体特征的批评家诟病翁方纲诗文的理由。质实、重考订是乾嘉时期学术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金石书画题跋的文体特点。而翁方纲对金石书画之学的嗜爱,以学入诗,义理、考据、词章结合的观点,则在主观上推动着金石书画题跋文体创作的辉煌,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金石之学在清代的独立与繁兴。因此,翁方纲屡遭诟病的诗文,其实对金石书画题跋及金石学的发展有着他人无法替代的意义。
注释:
①孙守真疑翁方纲原稿“求”前脱一“不”字,为“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参见“任真的网路书房”《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http://13165621.blog.hexun.com/69855915_d.html)第545页。
[1] 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M].清同治七年刻本.
[2] 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M].乾嘉名儒年谱本:册8.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一)[M]//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影印李以烜光绪补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7] 贾谊.新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9–70.
[8]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社,1991:1134.
[9] 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76.
[10] 姚莹.东溟文集[M].清中复堂全集本.
[11]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96.
[12] 孟醒任.桐城派三祖年谱[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63.
[13] 翁方纲.复初斋文稿:册1[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4]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523.
〔责任编辑 刘小兵〕
2017-08-19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汉语言文学”(PPZY2015C207)
傅元琼(1971―),女,山东兰陵人,讲师,博士。
I206
A
1006–5261(2018)02–0108–07
——翁方纲定武《兰亭》的收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