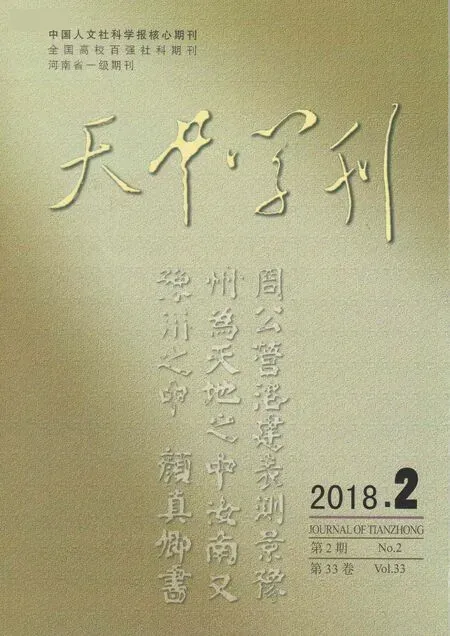小议《太平广记》中的人狐冲突
高小慧
小议《太平广记》中的人狐冲突
高小慧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太平广记》中的人狐冲突主要表现为狐祟人、魅人,人疑狐、杀狐。人狐冲突的原因可以从狐作祟魅人以及人对狐的敌对心理两个方面来寻找。狐作祟魅人虽然可恶,但并不危及人类的生命,还有许多狐单纯率真,颇具人情味。然而人对狐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敬畏、供奉狐,另一方面厌恶、杀害狐,这两方面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也是一致的,都是出于人对狐扰乱人间的畏惧与不满。所以,狐的妖性便成了狐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人;狐;冲突;狐妖根源
在古代志怪小说中,许多动物以人的形象混迹于人类社会,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超越,其中说狐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并且不断发展丰富,成为一个“汇集了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哲学的……诸多元素的文化符号,积淀在华夏民族的精神文化史上”[1]。《太平广记 · 狐部》是狐类故事的大汇编。总体上来说,《太平广记》中人狐关系以斗争冲突为主要特征。《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至第四百五十五卷为说狐故事,共9卷83篇,其中唐前作品不足10篇,其余大多数引自唐人作品,以《广异记》最多。
按照内容,《太平广记》中狐故事可分为4类:一是狐的介绍,如《说狐》《瑞应》《胡道洽》《周文王》《狐神》《狐龙》《沧州民》,虽是简单的介绍,但所介绍的已经是不同寻常之狐。二是狐兆,如《夏侯藻》《北齐后主》单纯预兆福祸吉凶。另外,《李林甫》《李揆》虽然也有狐兆的情节,但李林甫一见狐就要搭箭射狐,李揆则命侍童逐狐,无论狐所预兆的是吉是凶,人对狐的出现都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态度,所以这两篇并不是单纯的预兆福祸。三是人狐和谐,分为人狐真爱故事、狐报恩故事和人狐合作故事三种,如《任氏传》《计真》《王璿》《姚坤》《李氏》《韦明府》《杨氏女》《文狐》等。四是人狐冲突。除了前三类之外,《太平广记》更多地给我们呈现了程度不一的人狐冲突,其中体现人狐冲突的故事有60多篇,占全部说狐故事的76%。
一、人狐冲突
(一)人狐冲突
人狐冲突主要表现为狐祟人、魅人,人疑狐、杀狐。
1. 狐祟人、魅人
狐作祟的手段有很多,比如纵火(《管辂》)、截发(《靳守贞》)、行骗(《张简》)、占据府宅(《宋大贤》)等。另外,狐魅人的例子也有很多,如《陈羡》《刘甲》《张例》《僧宴通》等。狐如此作祟、魅人,扰乱人的正常生活,致使人类怀恨在心。
2. 人疑狐、杀狐
先看以下几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汉广川王》)
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长孙甲》)
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上官翼》)
人总是担心狐来欺骗、伤害自己,所以对狐绝少心慈手软,无冤无仇的尚且不放过,如《汉广川王》,何况是欺骗自己,魅惑亲朋的狐?
(二)人狐冲突的根源
站在人类角度来说,人狐之斗根源于狐作祟魅人令人类恼恨不已。狐的恶行最严重的是魅惑人,狐魅人的直接后果是使人得狐魅病。古人相信,如果被狐所魅,人的魂魄就会被狐夺走,出现言行举止或精神上的异样,常表现为神志不清,无法控制自我的情绪,变得喜怒无常:
韦明府女“昏狂妄语”(《韦明府》)
张立本女“狂号呼泣不已”(《张立本》)
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张谨》)
王黯发狂大叫……忽而欣笑(《王黯》)
张例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张例》)
由以上几则可以看出,《太平广记》所记载的狐魅人于人身体无伤,仅仅停留在迷惑人的神志方面,《杨伯成》篇如是道出:“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从狐狸的角度出发,人狐之斗许多时候是因为人类对狐的敌对行为,比如抢夺狐狸的天书,无缘无故追赶杀伤狐狸等。如《张简栖》中,张简栖吓跑了专心读书的狐狸,拿走了狐狸掉落的册子,狐狸曾多次向张简栖索要册子,张简栖为了在人前炫耀偏是不还,狐狸只好采取欺骗的手段,变成张简栖的朋友取回了自己的小册子。《汉广川王》中,白狐无故被广川王挖掘栾书墓时用戟伤了左脚,因此白狐在梦中也用手杖敲广川王的左脚,造成广川王醒后左脚肿痛。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二、人狐之斗中的人与狐
(一)人的中心地位与胜利者姿态
魏晋时期道教确立了“人”在万物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人化”成为万物变化的趋向。道教体系中的神仙已开始脱离上古神话中半人半兽的形态,转而以人为主要形态,如西王母的形象,在《山海经》中的描述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而在《汉武帝内传》中则完全人形化:
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褡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许多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老子、姜太公,也都被列入了道教仙谱,并且道教的神仙思想还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这一切都显示了道教对人力量的肯定以及对万物以“人”为中心思想的确立。
宗教迷信思想是志怪小说兴盛的土壤,道教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也在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代的此类作品中有所体现。在这类作品中,人在大多数故事中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人可以战胜狐,使役狐,决定狐的命运,极少有人在人狐之斗中丧命于狐。如《陈斐》《长孙无忌》《上官翼》《大安和尚》等。
(二)狐变人
《太平广记》中的狐多数都可化为人形,以人的形态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狐狸要与人正常交往,必须变化成人,消除人类的敌对态度,得到人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魏晋时期道教确立了“人”在万物中的中心地位,“人化”成为万物变化的趋向。
《太平广记》之狐不仅常常化为美女、丈夫,有时候还喜欢冒充神佛菩萨。狐通过读天书修道成仙,在半仙非仙时,往往自称是神佛或变幻为菩萨模样,欺骗百姓,让人们祭祀它,尊敬它,《僧服礼》《大安和尚》《叶法善》《长孙甲》诸篇都出现了狐狸假冒神佛菩萨的情节。为什么狐狸变人还不过瘾,又突发奇想要变成神佛菩萨呢?这要从人对待神与狐的差别说起。
在《长孙甲》一篇中,人对待神、妖的差别就十分明显:
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到,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
菩萨来了就恭敬诚恳,礼数备至,狐狸来了就杀死,人对神、狐表现出的这两种极端态度,体现了道教所宣扬的人对神、妖的态度,即神拯救人而精怪只会害人,所以应当敬神除妖。其实,一些狐狸假扮神佛菩萨只不过是想体验一下被人敬奉的感觉,并无恶意。
(三)狐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
在人狐斗争中,狐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这在《何让之》和《王生》两文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何让之》中,狐让志静和尚作为中间人劝说何让之归还自己的天试文书,并送给何让之三百匹绢用以赎回文书,但何让之不仅不还书,还赖掉了已经收用的绢,狐狸只好变成何让之的亲人欺骗何让之,终于拿回了文书。此狐遭人欺负,却又先礼后兵,不能不说是何让之太过分了。《王生》中,王生用弹弓射伤了一只狐的眼睛,并拿走了狐逃走时遗落的黄纸书,当天晚上,狐不顾眼伤化成人来到王生住宿的客店,想要夺回天书,但被店主人发现了它的狐狸尾巴,狐前前后后又历时许久,直到用计谋把王生弄得家道败落,才变成王生的弟弟夺回了天书。天书是狐的看家法宝,犹如命根,绝对丢舍不得,更因为天书得自天宫,不能泄露于人世,所以修仙之狐为了夺回天书不得不与人类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极能忍耐,无论用多长时间,用何种办法,只要能够夺回天书,它们都会去做,直到夺回天书为止。
狐在斗争中还展示了自己的才智。《焦练师》中的阿胡冒充太上老君智胜老道,是一个正面形象。阿胡学到了焦练师的全部本领后要离开,焦练师却不放行,还想要捉住阿胡,但阿胡总能随机应变,焦练师就设坛让太上老君帮他收狐,说狐侮辱了他,太上老君果然出现了,并且用刀砍断了狐腰,正当焦练师欢庆之时,太上老君忽然从云中下来,变成阿胡走了。阿胡化为太上老君,上演一出斩狐戏,实是无心戏弄自己的老师,不过是将计就计,寻求脱身的一个方法罢了。
然而更多的狐在人狐之斗中却由于过于单纯而吃了人类的亏。《祁县民》中,狐妇以为自己变成了人的样子就能够像真正的人一样与人类坦诚交往,于是天真地请求村民让自己搭一程便车,然而由于农民看到有一条狐狸尾巴垂了下来,这只狐狸便悲惨地被农民用镰刀砍断了尾巴。这只狐何罪之有,它从始至终对人类都没有防备之心,更不要提什么伤害之意了,只因过于天真,幻想能够与人类和平共处,最终被人类伤害。
大多数狐都天性率真,它们接近人的出发点也没有恶意。《孙岩》中,孙岩娶妻三年不知妻是狐,显然,狐与孙岩的结合对孙岩是无害的,否则三年下来,孙岩早就非痴即亡了,由此可见狐只是想和孙岩做长久夫妻罢了。再如《李元恭》中,胡郎仰慕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又与李元恭之子以学问相交,不仅与李子畅谈南北古今,解答李子的各种疑问,还为崔氏请来众多良师,教授她经史、书法、音乐等知识。胡郎完全把崔氏当成妻子加以尊重,把李子当成朋友而真挚诚恳地对待,然而这只是胡郎的一厢情愿罢了,积年累月像家人一样的相处最终也没有换来李家对胡郎的释怀。
(四)人类的虚伪、无情与残忍
有时候,人战胜狐不是因为狐已经脱去狡猾的外衣,而是因为人的虚伪、无情与残忍。《李元恭》中,当李子向胡郎建议让其明媒正娶崔氏时,其实已经布好了圈套,等待没有防人之心的胡郎往里跳,只有胡郎还在那里自惭形秽,感激不尽,欣喜若狂。李家一旦知道了胡郎的居所,马上往狐狸洞里灌水逼出胡郎并杀之而后快。面对胡郎的死,与之朝夕相处的李子与崔氏竟然无动于衷,反而显得人比狐更冷酷无情。《韦明府》《汧阳令》与《李元恭》颇为相似,都是雄狐先利用不正当手段得到一位美丽的女子,致使女子家人怀恨在心,表面上与狐女婿友好,实际上无时无刻不想着杀死它。最终人类成功了,但传达到读者内心的并不是人战胜妖的欣慰,而是惭愧于人性之丑陋。《张直方》中,狐狸热情招待迷路的张直方,又愿意把狐女嫁给他,即使当众狐知道张直方是臭名昭著的王知古的朋友时,也只是慌忙咒骂、驱赶张直方,并没有害死他,张直方回去后反而带领王知古回来杀害了百余头狐。人之无情、残忍可见一斑。
(五)狐对人狐关系的调和
在人狐的恶劣关系中,对其关系进行调和的始终是狐,但接受与否仍旧在于人,显示了人的主动权。《何让之》中,虽然何让之无礼在先,抢走了狐狸的天试文书,但狐狸并不想就此与人类结仇,而是拜托志静和尚劝说何让之归还文书,并许以好处。有些狐还主动与人修好,如《李氏》中狐弟弟主动帮助李家人赶走了狐哥哥,自己也不再来,自始至终也没有做什么作祟魅人的事情。《李苌》篇中也是狐主动出来帮助李苌驱赶其他作祟的狐。
无论人类怎样伤害狐,狐却极少进行报复,如《崔昌》《林景玄》《刘元鼎》,即使有狐对人进行报复,也都是很宽容的,有时还以德报怨。《唐参军》中赵门福的同伴康三被唐参军仆人杀死,赵门福也仅仅是戏弄了唐参军请来捉狐的和尚。《李苌》中李苌杀死狐的母亲,狐知李苌是误杀,并不计较,反而帮助李苌祛除狐祟。《李自良》中,李自良夺走了狐狸的文书,狐答应只要李自良留下文书,就会优厚地报答他,李自良同意后,狐果真使李自良的官职从牙门将军升到了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
三、人对狐的复杂态度
(一)敬畏、供奉
《太平广记 · 狐神》篇: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仙。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人们相信,狐是最灵异的动物,在唐代,民间家家供奉狐仙。狐仙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是狐聪明、狡黠、幽默、诙谐,而且法力高强,能通天入地、洞达阴阳、预测吉凶,帮助人趋福避祸,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在民间,各家供奉狐仙,求其保佑,甚至有一人即供一狐仙,俗呼为本身狐仙。但在我国传统神仙谱系中却不屑于提及这位狐仙,在众多寺庙道观中也见不到狐仙大人的神像,所以狐仙并非正仙。我国历史上也曾多次禁止狐信仰,但屡禁不止,人们不能明目张胆地祭祀,只好改为家祀。
狐信仰在河南、江苏、河北、山西、辽宁、山东等地都很流行,这些地方曾以狐为图腾,有些地区就是以狐命名的,如“狐”即山西永和西南,“狐苏”即今辽宁辽阳东南约八十里大屯附近,此外还有“狐人”“狐父”“狐奴”等。北方民间信仰“四仙”,即狐、鼬、蛇、艾虎。由以上几位仙爷的原形观之,民间对于狐狸的信仰并非出于恭敬,厌恶的成分只怕更多一些。何以见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民间狐信禁忌:
(1) 忌呼名。敬奉狐仙不能直呼“狐狸”,不同地区称呼不一,常见的有胡大仙、胡三太爷、胡仙姑、老胡家等。
(2) 忌提醒。人们相信一个人所说的话,狐狸在千里之外也能感知,所以不能说出来,以免招来狐狸。
(3) 忌狩猎。传说经常猎狐的人没有好下场。
(4) 忌伤害。主要是担心狐狸报复。
(5) 忌养犬。因为狗是狐的天敌,信狐的人家都不养狗。
(6) 忌封闭。“信狐人家的楼门屋室忌封闭严实,在设计建造时于门槛下面要留狐路,以供仙家出入。”[2]22
(7) 忌遇狐。“民俗中,早出门,特别是太阳出以前出门做事(尤其是做买卖)。如果碰见狐或鼬,就干脆折回家,避免做事不顺利,或有灾祸。”[2]22–23
(8) 忌吹笛。鲁南流传着“狐女吹笛”的故事。一个贫穷的男孩夜里在瓜园吹笛,每晚有一女孩前来听他吹笛,后二人结为夫妇,才知是狐女。因此父母禁止孩子夜晚吹笛,怕引来狐狸精,至今依然如此。
(9) 忌数鸡。农户晚上一般不数鸡,以免招来狐狸偷鸡。
(10) 忌脏物。“忌在宅院里随便撒尿、泼脏水,忌在院子里晾晒妇女的亵衣。”[2]23
所谓忌吹笛,无非是害怕招来狐女,而忌脏物则是讨厌狐狸但又敢怒不敢言的表现罢了,人们认为狐是骚臭肮脏的,所以才忌脏物。由以上禁忌可知,人们敬奉狐仙,是惧怕远大于敬爱,最主要是害怕遭到狐狸的骚扰报复。因为狐狸害人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太广,影响太深,以至于人们想到狐都觉得害怕,仿佛人在想到狐的那一刹那,狐就已经在人的心坎上坐着,自己想什么狐都知道,并且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二)厌恶、杀害
既然人们供奉狐仙,为何还要大肆杀狐,难道不怕触犯“神明”吗?
神的产生,就是因为人类畏惧自然中的某些事物因而将其敬奉起来的,渴望得其佑护,免其伤害。从这种心理出发,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神最初也都是人面兽身的怪物。而人们敬狐仙也正是出于对狐的惧怕心理。在民间,狐昼伏夜出,潜入人家窃鸡盗食,捉弄家畜,在自己经常出没的地方撒尿,尿液散发出的强烈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但狐又生性狡黠,不易捕捉。由于担心狐作祟和狐报复,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心理,为了消除这种畏惧,人类要么将其供着免灾,要么将其杀掉。因此,《太平广记》中出现那种大肆杀狐的现象,仿佛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了。
四、狐的悲惨命运
(一)狐妖性的根源
人类杀死狐狸是为了防止狐狸害人。从狐的自然属性来看,它栖息森林、草原、半沙漠、丘陵地带,居树洞或土穴中,傍晚出外觅食,天明始归,杂食虫类、两栖类、爬行类、小型鸟兽和野果等。为什么作品中的狐狸就成了作祟媚人的妖兽了呢?
首先,与狐自身的动物特性有关。“狐是自然物,但在狐文化中,狐基本上不以狐的原生态形式出现,狐是被夸张、变形、虚化了的狐,狐成为观念的载体。狐的被灵化和妖化,是在其原生态基础上进行的。”[3]1从狐的自然特征来看,狐是一种外表很美丽的动物:狐的脸呈倒三角形,颇似人类脸型中的瓜子脸,脸部器官给人以细腻精致的感觉;狐性情温和,身上的毛蓬松柔软美丽,身姿曲线优美,极易令人联想到温柔典雅的女性。因此在狐故事当中,狐狸往往化身为美丽的女子。另外,我国民间确实存在“狐魅”这种病,不少医书都有“狐魅病”的记载。《汉语大辞典》关于“狐魅疾”的解释是:“旧说被狐蛊所致的一种精神错乱病。”狐魅病其症为夜寐梦见与陌生异性交合,夜夜如此。《本草纲目 · 拾遗》还记载有治狐魅方:“珍珠兰味辛,窨茶香郁,其根有毒……此根狐肉沾之即死,性能毒狐,尤捷效也。”[4]281明代的《针灸大成》也两处提到“狐魅神邪迷附癫狂”的针灸处方。以上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狐狸变成美女魅惑男子就成了理所当然,狐狸也被视为淫兽。不仅如此,凡是性感美丽的女子也会被人们指为“狐狸精”。此外,狐狸的毛色多呈现赤褐、黄褐、灰褐色,远看仿佛一团火,因此《刘元鼎》中写道:狐“夜击尾火出”,《何让之》中写道:“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这样家中突然失火被认为是狐狸所为也就顺其自然了。加之狐狸的眼睛在黑夜中发出绿光,总是出没于坟地,人们又自然地将其与鬼联系起来。从狐的习性看,狐狸经常出没于坟丘土穴,昼伏夜出,行踪诡秘,因此夜间出现盗窃之类的事情多会加诸狐身。
其次,与道教思想有关。道教的长生思想投射到自然万物中便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 · 登涉》中所说:“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耳目,而常试人。”[5]424这种思想再具体到动物身上便是《抱朴子 · 对俗》中所说:“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5]60因此,在道教的影响下,凡是有了一定年数的自然物都可成精成怪。道教认为鬼怪都是狰狞可怖、危害人间的,所以成精的狐狸必定做不出什么好事来。因此,《太平广记》中的狐狸之所以要祸乱人间,没有其他的原因,就因为它们是妖怪。《太平广记 · 说狐》也有定论:“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妇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再次,与此类故事的创作动机有关。志怪小说多是作者对街谈巷议进行的忠实记录。人们在讲述这类故事时,为了强调人的正义与力量,必然将与人对抗的狐狸视作为非作歹之徒,其结局也只能是非死即伤。毕竟对于人来说,狐狸是异类,即使变化成人,也不能为人所接受。
由于上述原因,狐狸必然作祟魅人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人狐冲突时,狐狸只能面对必死的命运。
(二)狐的悲惨命运
整体来说,《太平广记》中的狐性情并不凶残,妖异性较弱,对人也造不成过大危害,并且大多都具有人情味,但狐仍然常被视为妖兽,结局大都十分悲惨,如表1所示。

表1 《太平广记》中狐的命运
无论狐有没有对人类做过什么,有没有真正伤害到人类,狐到了人手中往往难以脱身,天狐也不能幸免。
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刘甲》)
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李参军》)
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郑宏之》)
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谢混之》)
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刘元鼎》)
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锸,且掘且燻。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罥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张直方》)
如果杀掉邪恶凶残之狐是为了报仇泄恨,是正义之举,那么如此大肆焚杀成群没有还手之力的狐狸岂不是滥杀无辜吗?不仅如此,《姚坤》篇中猎人捕捉狐狸,狐狸不能报复猎人,却只能报答从猎人手中释放狐狸的人;《谢混之》中人类滥杀狐狸,狐狸却连告状都不行。
多数狐所遭受的来自人类的伤害都是值得我们同情惋惜的。《尹瑗》中的白衣书生自称姓朱,来向尹瑗学习,“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因为“深爱之”,所以当尹瑗得到一瓶好酒时,就邀请朱生一起喝,朱生先是推说有病不敢喝酒,因为怕现出原形而葬送与尹瑗的友谊,但又担心惹尹瑗不高兴,或许还出于对尹瑗的信任和对二人友情的笃定,朱生还是喝了个酩酊大醉。但当朱生酒醉化为一老狐时,尽管尹瑗“深爱之”却也“即杀之”。《郑宏之》中,郑宏之住进长时间没人居住的官署,狐王化成贵人带着随从欲夺住所,郑宏之请狐王入座,他们谈了一宿,说得很投机,当狐王沉浸其中,完全没有防备时,郑宏之挥剑刺狐,血流满地。《李元恭》中,胡郎比常人更具人性和学识,十分值得交往,但李家人始终对胡郎之狐的身份耿耿于怀,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这是人狐关系的一大遗憾。
由于人对狐的过度防备,即使狐变成了人也得不到人类的认可,纵然人狐之间有过亲密关系,一旦人类发现对方是狐,所有情谊都难以唤起人类对狐的怜悯之心。在隋代王度的《古镜记》中,狐精鹦鹉在临死之前道出心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虽然没有做什么害人的事情,但因为是狐狸变化的,终究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太平广记》大多数狐悲剧命运的原因。
由于民间对于狐仙的祭祀与禁忌,人们不自觉地关注狐狸,创造更多狐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促进了此类小说的发展,而小说中所记录的故事,又影响着人们对狐的看法。于是民间信仰与狐小说互相推动,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狐故事的发展。
[1] 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J].文学遗产,2006(1):46–56.
[2] 山民.中国民俗文丛 · 狐狸信仰之谜[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3]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5] 葛洪.抱朴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杨宁〕
2017-09-05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王铎与明清之际的中原诗学”(2015-JCZD -006);全国高古委直接资助项目“刘嵩阳彭玉平集校注”(1534)
高小慧(1975―),女,河南平舆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I206.2
A
1006–5261(2018)02–00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