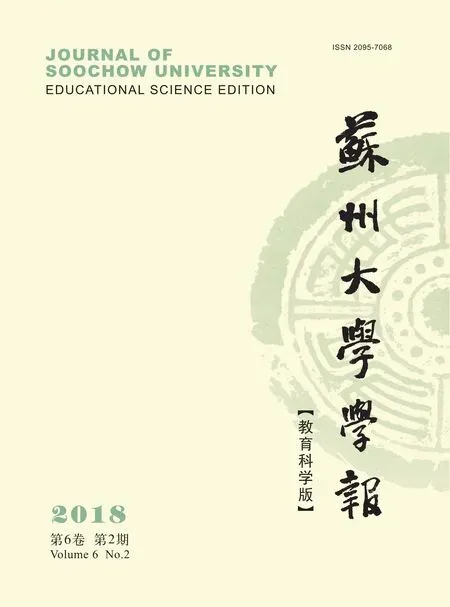历史深处的心理学史研究—基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思考*
崔 光 辉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作为一名心理学史研究者,面对当下国内研究时,最深的感受是“停滞”。停滞意为遇到阻碍,驻足不前。这个词有着很强的时间意味。这里先将“阻碍”放在一边,来看与时间关系更密切的“不前”。需要说明的是,时间未必是向前的,在佛家的世界中,世界是轮回的。“不前”并非指时间停止或其他,它更多地意味着,没有新东西生发出来。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心理学史本就是过去的事情,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内容?心理学史研究者们对此很难苟同,因为这样一来,研究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研究过去的事情,会有新东西出来吗?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一种解答认为,研究可以揭示出不为学界所知的内容:对历史来说,是发生过的;而对学界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这个回答很精巧,却容易让人难过,因为最终还是没有“新”内容出来。
让我们回到心理学史本身。这里涉及的关键主题,是“过去”。心理学史是关于过去的心理学的人、物、事等。“过去”是什么呢?或许从这里,可以找到新的解答。关于过去,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过去是物理时间的一部分。物理时间,如同钟表指针所指示的那样,从过去均匀地经过每一时刻,到现在乃至未来。在这一运转过程中,现在和未来不断成为过去,过去则永不再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于心理学史研究者来说,过去虽无法再现,却会留下各种痕迹,如当事人的著作、书信、日记等。这些事物成为档案。研究者通过考察档案,来推断心理学的历史。这种理解与前面精巧答案有着一致的立场。过去就是过去,不会有新的内容出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所秉持的,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晚期的身体现象学观点。从身体现象学来看,前一种理解中,当事人是抽身而出的,如同万能的神,从空中打量时间。如果从当事人的经验出发,就会发现,时间并非如钟表所指示的那样。例如,在当事人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并非均匀地排列。某些过去可能会缩短,而另一些过去,如刻骨铭心的经历,可能会无限延长。最令人惊讶的,过去并非已随风消逝,而是留存于当前。
打个比方,前一种理解将时间假定为一条水平的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均匀地分布其中;而身体现象学要将这条线竖起来,将时间视作垂直的。这样,过去就在现在之下;或者说,过去就在当前,只是一直在潜意识中沉默着,没有浮现出来。钱穆曾说过,世上之所以有鬼,乃是因为在生者的世界中,逝者所使用事物遗留人间,于是便有鬼来替代逝者。①承严亮先生告知,谨致谢忱。从身体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往事并不如轻烟般散去,而是留存下来,附着于现在。生者睹物思人,其实是往事浮上心头而已。
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提出“垂直历史”的概念,来指代身体现象学视角中的历史。垂直历史首先意味着,历史是在当下的,它如同考古发掘到的遗迹,就在人们脚下。心理学史研究者无法也无须回到过去。历史可以通过档案,直接呈现在研究者面前。陆志韦在诗集《渡河》中,收录了一首题为《我的事业》的诗:我在困苦的生命里/做登天的事业。/把已经死去的希望/当作石级。/我还靠这已经死去的希望/同山下的人相接。/再希望几回,/再失望几回,/再死几回,/就可同山顶上得胜的人并立。/或者上帝晓得的,/我的失败就是我的事业。读这首诗时,陆志韦的“事业”情形,其中的困苦与坚持,跃然纸上。
其次,历史是无限的。它的浮现是部分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有未知的部分,处于沉默的潜意识深渊中。心理学史研究者如同傅斯年所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从而展开各种不同的研究。有人会关注陆志韦的诗歌与记忆研究的关系;有人会发掘诗中观念与社会背景的呼应;还有的会考察陆志韦在科学研究与诗歌创作间的张力。理论视角不同,历史会浮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何种理论视角,都无法穷尽全部的历史。
最后,历史处于生成变化中。有关垂直之线的时间比喻是有问题的。梅洛-庞蒂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书中,使用了时间球茎(bulb)的说法。在时间的球茎中,过去处于潜意识的深渊,现在则变动不居。过去自潜意识中浮现,其实参与到现在的变化中。过去的每一次浮现,都会在当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往事浮上心头,不断会有新的感受生发出来,思念因此意味隽永,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研究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解读陆志韦的诗歌,其实是历史沿不同角度的生成变化。理论视角所提供的,乃是历史生成的不同方向。
心理学史研究因此是创造的过程。研究者以“同情之理解”,带着切身感受,全心投入到研究中。于是历史的各种面貌,自深渊中浮现。每一次浮现,都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心理学史研究者,如同冯友兰所提出的,在“接着讲”历史。历史研究由此生生不已,永无止境。
由此来看,当前国内心理学史界的“不前”,问题或许在于心理学史研究者是否沉浸在历史之中。研究者虽然研究历史,却未必全心投入历史具体情境中。国内学界流行的做法,将心理学史简化为观念层面的心理学演进历程。心理学历程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1879年以来心理学观念和研究的历史,尤其是心理学流派的思想史。这种做法最初的学科处境,在于通过引介英语世界心理学进展,为国内心理学重新起步奠基。之后由于英语世界各种心理学新思潮的出现,这种引介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苟存。观念引介停留于观念层面,对历史进行抽象和剥离,从而使得丰富的过去无法在当前浮现。当引介告一段落时,研究者不得不面临长期以来历史的缺席。
对于心理学史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具体处境。研究者所需做的,是以“同情之理解”,突破观念的藩篱,深入描绘历史的丰富面貌。在心理学史的深处,人、物、事等都是无限复杂的。1965年,《行为科学史杂志》创刊号登出的第一篇论文,是波林关于莱比锡心理学实验室创建年份的考证。波林发现,早期学者对于该年份的描述是多样的,并非绝对的1879年,即使冯特本人也曾给出不同的答案。当时的心理学,也绝非单纯的科学心理学。罗杰·史密斯在所著《诺顿人文科学史》(1997)中指出,当时德国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在于为哲学提供认识论基础,冯特、布伦塔诺和狄尔泰均是如此,缪勒和艾宾浩斯更接近科学性形态的心理学;英国心理学游离于学院外;法国与意大利的心理学则与反对天主教联系在一起;美国心理学则关注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
研究者使用观念时,目的应在于参与到历史的生成变化中,而非通过观念远离历史,从而使自己陷入停滞的境地。观念应是历史得以生成的维度,而非历史的终结。在梅洛-庞蒂看来,历史研究应该成为一种诗歌,通过言说来展现历史的深度。如果通过观念远离过去,历史研究将成为一种独断论的理性主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变化并非乱象丛生,它与地理乃至世界天然地交织在一起。世界是永恒的。史铁生曾在《我与地坛》中说过,世界“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它在当下“常新”又“始终如一”。心理学史研究者则是这永恒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如同史铁生笔下的孩子:某一天有人消失了,或许山洼中会跑上来一个孩子,那孩子虽不是这人,却与这人一样,是永恒世界绵延的一个片段。这样就可以理解,心理学史研究者既在历史的创造中得到滋养,又在历史的深度中如临深渊,战战兢兢;既滋味隽永,又永在途中。个中感受,或许如同陆志韦另一首题为《忆Michigan湖某夜》的诗中所写:
Michigan湖只有万古的回音,/教我把痛苦的良心,狭窄的私情,/放在一片浪花上,眼望月光尽处。/Michigan送了浪花来,一定会带浪花去/我眼前一曲沙滩,背后一代柏树,/在这万古的声音中,不向月光诉苦/柏树,月光,月光,柏树,/你们是Michigan的,不是我的。/我对面的人,我心头一切忧虑恐怖/你们是全世界的,不是我的。/我此刻记不得过去,又梦不成将来,/且踏一片浪花,跟万古的声音,回到月光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