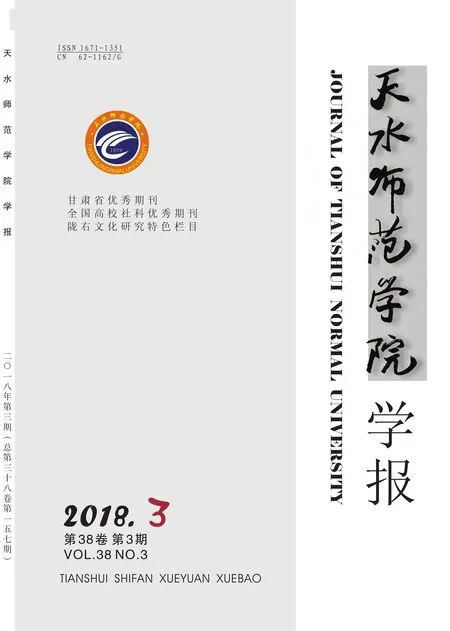敦煌文书中“使客”“客僧”考释
魏睿骜,陈红静
(1.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2.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00)
归义军政权作为晚唐五代宋初活跃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地方政权,正式设立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因沙州豪强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并奉土归唐而建。众所周知,晚唐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其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乱时期,各地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频繁更替。而在这种混乱变幻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敦煌地方政权——归义军政权——却未受唐王朝倾覆和五代中原王朝迭兴的影响,一直延续了近两百年时间,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现象背后的原因虽为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这一时期,归义军政权积极开展与周边政权的交往活动,缓解双边关系。其中有“使客”和“客僧”两种身份值得我们注意。学界在研究归义军对外交往活动中,多将此两词直接理解为使者和僧人使者,未对其具体含义作进一步辨析。本文欲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利用敦煌文献和传统文献对此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一
归义军时期“使客”“客僧”的相关记载,就目前所见主要出现在以下几篇敦煌文书中,相关记载如下:
(1)P.3569,该文书双面抄写,正面为《太公家教一卷》,背面抄《唐光启三年(887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中有“使客”一词:
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去三月廿二日已后,两件请本粟叁拾伍驮,合纳酒捌拾柒瓮半。至今月廿二日,记卅一日,伏缘使客西庭、摖微、及凉州、肃州、蕃使繁多,日供酒两瓮半以上,今准本数欠三五瓮,中间缘有四五月艰难之济,本省全绝,家贫无可吹□,朝忧败阙。伏乞仁恩,支本少多,充供客使。伏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光启三年四月日龙县丞牒。[1]622
(2)P.2032,该文书双面抄写,正面为《维摩疏卷第五》,中有品题:不思议品第六、观众生品第七、佛道品第八、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背面抄《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有“使客”“客僧”二词:
面叁斗伍胜,油胜半,屈客僧及使客送路用;面伍升,伊州客僧来时看用。[1]506-507
(3)敦煌研究院藏001,原件首尾并残,共49行,现已割裂为二,前半截现存敦煌研究院,后半截原为董希文收藏。经施萍婷先生研究认为该“酒帐立于乾德二年(964年)的可能性最大”。[2]缀合后的文书(董希文旧藏+敦煌研究院藏001+P.2629)中有“使客”的记载,具体记载如下:
(十月)十四日,衙内看使客酒壹斗。同日,设伊州使酒贰斗。[1]276
二
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龙县丞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请支酒本所上的牒文,二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判词批复,三是酒司官员押衙阴季丰算会牒。上述录文仅为第一部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归义军设置酒司,作为管理官府酿酒业及为官府提供酒类的专门机构。[3]而官酒户则为服务于酒司的专业酿酒人户。此件文书反映的即为唐光启三年(887年)归义军周边政权的“使客”来到敦煌,归义军酒司负责供酒招待,所供之酒由官酒户酿造而成。[4]在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客僧”和“使客”并列出现,陈大为、[5]王宝珠[6]等在对归义军对外交往活动进行论述时均引用此条,都将其作为周边政权出使归义军的使者看待。对董希文旧藏+敦煌研究院藏001+P.2629《年代不明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进行最先研究的为施萍婷先生,在对“衙内看使客酒壹斗”之“衙内”进行解释时认为:“衙内为藩镇亲卫之官,多以子弟担任,世俗相沿,习惯上把贵家子弟称为‘衙内’。”[7]而冯培红先生则认为“节度使府衙内负责招待使客的机构即客司”,[8]此处将“衙内”理解为归义军的使客招待机构——客司。该《酒破历》中多次出现“衙内”一词,“同日夜,衙内看甘州使酒伍斗”;“六日,衙内面前看南山酒壹斗”;“廿六日,衙内看甘州使酒叁斗伍升”等,从上述材料中可看出,“衙内”往往与周边政权使者招待相并列。因此,此“衙内”理解为归义军使者招待机构——客司更确切。
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活跃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地方政权,统辖中心为河西敦煌地区。由于地处边陲,如何正确处理与各时期不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主宰归义军政治路线和统治方略的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政权的兴盛,对周边政权,乃至中原王朝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归义军与周边政权时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各地使者纷至沓来。对出使归义军的周边政权的使者,敦煌文书中往往将其记载为“甘州使”、“伊州使”、“于阗使”等,例如S.3728《乙卯年(955年)二、三月押衙知柴场司安祐成状并判凭》:“(三月)十八日,迎甘州使付设司柽刺叁束”;[1]620S.1366《年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新来伊州使下檐细供两分,面五升,用麦八升五合,油一合六勺”;[1]282P.3160v《辛亥年(951年)押衙知内宅司宋迁嗣枡破用历状并判凭》:“廿日看于阗使煮肉两束”[1]614等。而“使客”和“客僧”作为周边政权来往敦煌归义军的使者的称呼,主要反映在上文所列三篇文书中。需要注意的是在P.3569v《唐光启三年(887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中又记载到“伏乞仁恩,支本少多,充供客使”。此处充供的“客使”当即该文书上文提到的“使客西庭、摖微、及凉州、肃州、蕃使”。可见,“客使”当即“使客”。正史中亦多有关于“使客”、“客使”的记载,《魏书·蠕蠕传》记肃宗曾于显阳殿接待各藩国使客,“十月,肃宗临显阳殿,引从五品以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环等人,就庭中北面。”[9]《新唐书·焉耆传》记载,武后时鉴于来往使者繁多,曾下令减轻西域焉耆等小国接待使客的负担,“武后长安时,以其国小人寡,过使客不堪其劳,诏四镇经略使禁止傔使私马、无品者肉食。”[10]6227《旧唐书·礼仪三》:“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11]884-885《新唐书·礼乐一》:“初,司空行乐县,谒者、赞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庙子孙、从享群官、诸方客使入就位。”[10]318两《唐书》所载材料介绍了唐庭接待“诸方客使”的规格和程序。综合以上史料可知,不论敦煌文献还是传统文献中多将“使客”、“客使”作为使者看待。
三
关于“客僧”的记载,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主要反映在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面叁斗伍胜,油胜半,屈客僧及使客送路用”“面伍升,伊州客僧来时看用”中。另外,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文书S.0545v《吐蕃戌年永安寺僧惠照具当寺应管主客僧名数状》也有关于“客僧”的记载:
永安寺状上。当寺应管主客僧总卅六人。利宽、法照、证因、光证、昙隐、惠哲、归信、远真、凝然、文惠、智岩、法福、惠林、惠寂、惠幽、法进、解脱、戒郎、弘恩、法寂、惠琮、智光、惠照、贞顺、戒□、惠宗、道空、法因、道成、法清、会恩、绍□、□□、智捷、光济、志真。右通当寺僧名具如前数,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戌年九月日僧惠照牒。[12]
文书中吐蕃“戌年”,唐耕耦先生认为当为806年。永安寺僧惠照将该寺所管主、客僧三十六人名录上报吐蕃设置于沙州的寺院管理机构。此处将主、客僧一同统计,无法具体分清永安寺主、客僧的具体名数。该文书中“客僧”是相对于“主僧”而言,即一般意义上的游方僧,是被当作暂住者的身份看待。但这样模糊的身份记录,又可看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外来“客僧”在寺院内地位的日益“主僧”化。其他文献中亦多将“客僧”作为游方僧看待,例如《旧唐书·郎余令传》中载:“时有客僧聚众欲自焚,长史裴照率官属欲往观之。”[11]4961此处客僧当为游历至此的僧人,因为某件事情而欲通过自焚来解决;《全唐文·王师德等造像记》中有“刘客僧”的记载。[13]该文为刘客僧等三十人共同造像所记的愿文。“刘客僧”有可能为人名如此,但也不排除为民众对其简称,即一位姓刘的外来僧人;《全唐诗》卷八百六十四《赠僧》诗序载“大历中,有郎子神降于桐庐女子王法智,自言姓滕名传胤……每与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有客僧诣法智乞丐,神赠诗云(后略)”,[14]以上史料无疑均将“客僧”理解为“游方僧”之意,而敦煌文书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所载之“客僧”似不为此解。据该文书记载,净土寺需供给叁斗伍胜面、一胜半油给客僧及使客回去路上使用。“使客”根据以上解释,即为“使者”之意,而此处所供给的油、面是由两者共同使用,因此可知“客僧”是与“使客”一同出使敦煌的僧人使者,可能因其身份的特殊而单独列出。另外,从字义上来看,“客”本身就有出使他国使臣之意。《说文解字·宀》部:“客,《周礼·大行人》大宾大客别其辞。诸侯谓之大宾,其孤卿谓之大客。《司仪》曰:‘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相为宾,诸公之臣,侯伯子男之臣相为客是也’”。[15]以上解释的依据来源于《大行人》及《司仪》。《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郑玄注:“大宾要服以内诸侯,大客谓其孤卿。”[16]239《周礼·秋官·司仪》记:“凡诸伯子男之臣,以其国之爵相为客而相礼。”[16]247此处“客”即为使臣之意,所出使国根据其在本国原爵位的高低以定接待的礼仪标准。“客僧”作为以僧人身份充使的理解在敦煌文书以外的文献中出现较少,反映了归义军时期外来使者身份上的特点。
四
往来于敦煌的使团中,以僧人身份充使较为普遍。究其缘由,时河西地区宝刹林立,佛教兴盛。不乏有许多佛法高深的大德来往于河西各政权间布道说法,他们其中还有些会参与到佛经的翻译工作中,吴法成即是其中一位。郑炳林通过敦煌汉文文书关于法成的记载,论证认为“法成译经主要在沙州永康寺、甘州修多寺,翻译的经主要是《诸星母陀罗尼经》;讲经是于大中十年至十三年在沙州开元寺讲授《瑜伽师地论》。”[17]与归义军进行使者往来的主要为于阗、西州、甘州、肃州等政权,而这些地区无疑均为信奉佛教的地区。这些政权在与中央王朝的使者往来中,亦多以僧人充当使臣。《宋会要辑稿·藩夷四》回鹘条载:“(乾德三年)十一月,遣僧法渊贡佛牙及琉璃器、琥珀盏。”[18]9767“真宗咸平元年四月,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等来贡”。[18]9768可见“僧侣作为使者在当时的西北地区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佛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佛教文化的交流状况。”[19]作为周边政权出使敦煌地区的使者,“使客”的身份较为多样,既可为官员、商人,又可为平民或僧人。而“客僧”作为出使敦煌的特殊的使者,其身份较为固定,即仅以僧人充使。
归义军政权由于地处边陲,如何正确处理与各时期不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主宰归义军政治路线和统治方略的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政权的兴盛。因此归义军与周边政权之间的使者往来较为频繁,“使客”和“客僧”正是归义军对周边政权出使敦煌的使者的另一种称呼。在该称呼中“使客”身份较为多样,而“客僧”则仅指代以僧人身份充使的使者。河西地区僧人充使较为普遍,究其缘由,与该地区佛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