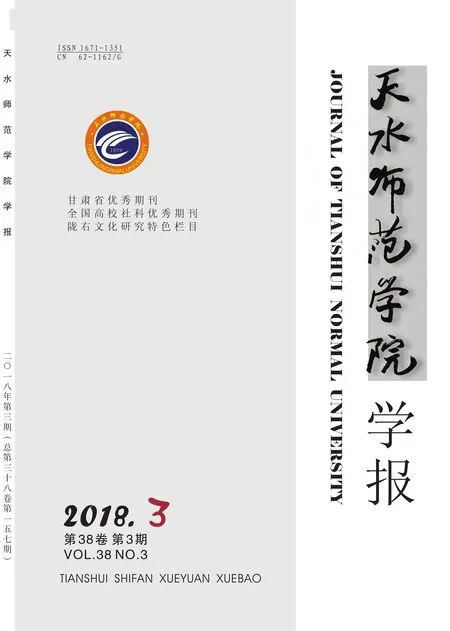写本情境下S.2682+P.3128综合研究
谭 茹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20世纪以来,随着敦煌写本图版逐渐电子化,以及敦煌学研究不断深入,敦煌写本的情境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写本情境研究就是在写本整体性的基础之上,将写本的物质形态、抄写风格、写本内容、杂抄等各部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关注写本原有的写本生态和写本个性。本文在S.2682+P.3128缀合的基础上,从写本状况、写本综合研究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目的在于考证S.2682+P.3128写本的所有者、抄写顺序及写本性质。①P.3128写本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版可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349-353页;《敦煌宝藏》第126册348-353页。S.2682写本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图版可参考《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182-185页,《敦煌宝藏》第22册218-227页。本文所使用两写本的彩色图版均在国际敦煌项目网站(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下载。
一、写本状况
S.2682首尾俱残,正面前端上方有4行破损。P.3128首残尾全。S.2682尾部可与P.3128首部相连,缀合后写本尺寸为29.9×509.9cm.写本由12纸粘合而成,每纸大小不一,双面书写。正面有乌丝栏,其宽窄多处不一致。天头、地脚高度约1厘米,抄写《大佛名忏悔文》,字迹工整平正,楷书,为一人所书。背面共抄写《社斋文》、“曲子词15首”、《不知名变文》《太子成道经》4部作品,行楷,为同一人所书,书写流畅。写本纸张较薄,两面墨迹有互渗现象。由于粘合处有书写痕迹,写本当为粘合后抄写。
(一)《大佛名忏悔文》(拟题)
抄于S.2682+P.3128正面,共332行,S.2682存1-212行,P.3128存213-332.未见题名,据《伯希和劫经录》补。[1]280段与段之间以空格或隔行为标志,行间较少讹误和改字。
(二)《社斋文》(首题)
抄于S.2682+P.3128背面第一纸,存10行整,题名原有,题名后空一格抄写正文。起“盖闻光辉鹫岭,弘大法以生慈”,迄“炉焚凈土之香,幡花散”,该文又见于P.3545、S.4976.校之他本,S.2682+P.3128约余170字未抄。剩余未抄之内容:“伏愿……次用庄严,诸贤社即体。惟愿……次用庄严,持炉施主集体。惟愿……斋成佛果,摩诃般若”格套化倾向非常明显。加之S.2682+P.3128背面抄写格式严谨,不同内容之间隔数行再作抄写,不似杂抄。因此S.2682+P.3128《社斋文》未抄部分可能是抄写者故意为之,以便练习时或在斋会上诵唱之时能够随机应变。
(三)曲子词15首(拟题)
“曲子词15首”抄于《社斋文》之后,隔数行抄写。存46行,内容完整,起“曲子菩萨蛮”,迄“争似圣明天”。每调前书“曲子”加调名,共15首。依次是:《曲子菩萨蛮》3首:《敦煌古往出神将》《再安社稷垂衣理》《千年凤阙争雄弃》;《曲子浣溪沙》6首②写本原写作《浪淘沙》,诸家皆改。:《倦却诗书上钩船》《喜观华筵戏大贤》《好是身沾圣主恩》《却卦录兰用笔章》《五里竿头风欲平》《结草城楼不忘恩》;《曲子望江南》4首:《曹公德》《敦煌县》《龙沙塞》《边塞苦》;《曲子感皇恩》2首:《四海天下及诸州》《当今圣寿比南山》,同调曲子用“同前”和“又同前”表示。其中有八首曲子词见于其他写本:《千年凤阙争雄弃》《倦却诗书上钩船》《五里竿头风欲平》3首见于S.2607,《喜观华筵戏大贤》见于P.4692,《曹公德》和《边塞苦》2首见于S.5556,《敦煌县》见于P.3911、P.2809,《龙沙塞》见于P.3911、P.2809、S.5556。
(四)《太子成道经》(补题)
倒书,抄于S.2682+P.3128背面最左端,共190行,S.2682存1-174行,P.3128存175-190行,内容完整,未见题名,题目据P.2999补。散文、韵文各自成段,正文内韵文每行2句,文末解座文每行3句。韵文前书“吟”、“吟云”标记。该文又见P.2999、 S.548、 S.2352、 P.2924、 P.2299、S.4626、BD8436(潜80)七个写本。
(五)《不知名变文》(拟题)
倒书,抄于《太子成道经》和“曲子词15首”间,共23行,内容完整,未见题名。散文、韵文合抄,未分段,本文仅见于P.3128。文中多次出现夹行小字或小字抄写的“道个甚言语也”和“佛子”,我们认为这是判断文章性质的重要标志。
敦煌学界对S.2682+P.3128《不知名变文》定名历来存有争议,王庆菽在《敦煌变文集》一书中因其不知敷演何经,定为《不知名变文》;[2]814在同书中,王重民怀疑是押座文的另一种体式;[2]816任半塘在《唐戏弄》中认为是一种戏剧;[3]908-909周绍良在《〈敦煌变文集〉中几个卷子定名之商榷》一文指出这篇《不知名变文》应改题作《散座文》。[4]104黄征、张涌泉在《敦煌变文校注》一书中同周绍良持相同意见,定名为《解座文》;[5]1191曲金良在《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书中同任半塘持相同意见,认为此文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小剧本”。[6]276戚世隽在《对敦煌写卷中“剧本”资料的检讨》一文中认为,敦煌写本之中并不存在“戏剧”,S.2682+P.3128所抄写的这一篇文章是变文的一种。[7]125
从所抄内容来看,写本抄写了一对贫贱夫妻之间的对话,在散韵交替处以夹行小字或小于正常书写的字体书“道个甚言语也”,这种表达方式在其他变文中亦常常能够见到,如《八相变》中提到:“当尔之时,道个甚言语……”、“于此之时,道何言语……”;《破魔变文》:“魔王当尔之时,道何言语……”、“当去之时、道何言语……”,可见,“道个甚言语也”句实为变文韵散转换时经常使用到的套语。
从体制上看,写本抄写的内容在情节上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唱白转换明显,具有韵散转换的标志,符合变文“散韵组合”、“说唱兼行”、“讲唱故事”的特点。虽然其后有散座文的套语,但是《太子成道经》《破魔变》等变文结尾亦有此散座话语。可见,变文结尾有散座文的情况非常常见,无需另立它类。综上,我们更认同王庆菽先生的观点,定名为《不知名变文》,更为确切。
(六)“惠深文书”
写本背面左端尚空余十行左右的空白未抄。于《太子成道经》前两行倒书“惠深文书”4字。
二、写本所有者
S.2682+P.3128写本卷背末“惠深文书”四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惠深其人为寺院一僧人,敦煌写本P.3212《辛丑年惠深牒》和S.3708《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日弟子监使惠深等状》皆有对惠深的记载。据上述写本提供的“辛丑年”和“太平兴国六年(981)”的时间信息,惠深应该生活在五代至宋初,写本的抄写时间也大致在这个时间段。“惠深文书”这种题记形式在敦煌写本中并非一例,S.6417斋文集中,《三长邑义社斋文》尾题“贞明陆年庚辰岁二月十、廿日金光寺僧戒荣裹白转念”,后六篇均题“戒荣文本”或“戒荣文一本”。“惠深文书”同“戒荣文本”的性质相同,说明这个本子归惠深个人所有,是写本的所有者。
三、抄写顺序
S.2682+P.3128写本共抄写《大佛名忏悔文》《社斋文》《曲子词》《太子成道经》《不知名变文》六篇文章。整个写本的字体不一、笔画粗细不一、用墨浓淡不一、书写各个部分渐次潦草,因此可断定写本应是由不同的人多次抄写而成。
写本正面《大佛名忏悔文》相对背面保存的更加完好,且在整个写本中最为工整、规范,应是最先抄写的内容,且与背面抄写之人应为俩人。我们认为S.2682+P.3128写本背面是对正面《大佛名忏悔文》和纸张的重复利用。
写本背面“惠深文书”字迹与其他内容一致,则惠深为背面抄写者是可以确定的。《社斋文》“曲子词15首”同《不知名变文》《太子成道经》相互颠倒。《社斋文》与“曲子词15首”之间,《太子成道经》与《不知名变文》之间均有明显空隙,而“曲子词15首”与《不知名变文》之间抄写相当紧密,并且《不知名变文》后面字体相较“曲子词15首”变得小而密,因此可断定《不知名变文》的抄写当晚于“曲子词15首”;再《太子成道经》和《不知名变文》同为倒书,《太子成道经》抄写在《不知名变文》前面,因此《太子成道经》抄写时间应晚于“曲子词15首”且早于《不知名变文》;“惠深文书”笔画粗细同《社斋文》一致,同《太子成道经》《不知名变文》颠倒,则“惠深文书”和《社斋文》可能抄写于同一时间,正常的文书抄写大多都在最后落款,因此《太子成道经》和《不知名变文》或抄于《社斋文》之前;综上,我们认为惠深可能先抄“曲子词15首”,再抄写《太子成道经》和《不知名变文》,后在曲子词前空白部分抄写《社斋文》,同时在卷尾留下自己的名字以作标记。因此写本的抄写顺序应为:《大佛名忏悔文》→“曲子词15首”→《太子成道经》→《不知名变文》→《社斋文》→“惠深文书”。
四、写本性质
(一)《大佛名忏悔文》
《大佛名忏悔文》是用于佛教忏悔仪式上的佛教作品,张小艳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一书中指出,S.5800《光化三年(900)正月一日己后讲下破除数》、P.2040v《净土寺食物等品入破历》两写本中的“忏子”即指“忏悔文”。并提出:“忏悔”是对自己以往所造恶业的陈述,藉此悔罪以求福的一种宗教仪式,“忏悔文”就是在悔罪求福时诵唱的文本。[8]282-283从S.5800、P.2040v两个写本中我们还能看到,忏悔仪式在敦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佛教活动,僧众们往往通过以粮食换纸的形式抄写忏悔文,并且还要向寺院施以食物以示自己忏悔的诚意。同时,汪娟在《敦煌本〈大佛略忏〉在佛教忏悔文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大佛略忏》不仅是用来读诵的教科书,也是实际礼拜、忏悔所用的行仪文,因其多引用大乘经典立说,故能受到高僧大德的重视。[9]388-402在敦煌俗讲仪式上,忏悔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一步。S.2682+P.3128所抄《大佛名忏悔文》是敦煌寺院中僧徒在佛教忏悔仪式上诵读的忏悔文本。因为该内容符合惠深僧人的身份,因此惠深可能在利用正面抄写的《大佛名忏悔文》的基础上在背面继续抄写其他内容。
(二)曲子词15首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提到曲子词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和迎合各阶层民众的歌词内容,使当时上至文人骚客,下至平民百姓,“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争相欣赏”,且“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远远超过现当代社会对音乐的追求,并且还恐怕“差晚看不及也。”[10]75曲子词之所以在宫廷内外、饮酒宴会、勾栏瓦肆,各种场合上深受喜爱,其原因在于曲子词本身是在民间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能够展现广阔的民间生活以及反映人民的心声。此外,曲子词依托燕乐作腔,曲调易于传诵,民间普及度高,使得它非常适合于宴会、典礼等公众场合的唱诵表演。
敦煌S.2682+P.3128写本中的15首曲子词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反映忠君爱国思想:《菩萨蛮·再安社稷垂衣理》《菩萨蛮·千年凤阙争雄弃》《浣溪沙·喜观华筵戏大贤》《浣溪沙·好是身沾圣主恩》《浣溪沙·却卦绿兰用笔章》《感皇恩·四海天下及诸州》《感皇恩·当今圣寿比南山》;第二,表达对边塞将领勇猛征战、保家护国的赞美:《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望江南·曹公德》《望江南·敦煌县》《望江南·龙沙塞》《望江南·边塞苦》;第三,表达对人生不同追求的理想信念:《浣溪沙·倦却诗书上钩船》《浣溪沙·五里竿头风欲平》);第四,劝人及时报恩,共存修善的佛教理念:《浣溪沙·结草城楼不忘恩》。
结合写本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S.2682+P.3128写本中抄录的15首曲子词可能有以下几种用途:首先,作为讲唱文学之一种的曲子词在唐五代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写本所抄曲子词不排除抄写者因个人喜爱抄写的情况。其次,据饶宗颐研究,敦煌僧人诵习乐府小曲,六朝以来已蔚然成风,如宋之惠休,齐之宝月,梁之法云,皆其著者。[11]37-38同时,“由于和尚需要学习写一点韵文来表达思想作为说偈之用,他们便很应该学术‘唱导’的工作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所以要接受念经、唱诵、撰拟文辞的训练。又由于唐季的和尚要修习‘声赞科’这类学科,因此他们要抄写曲子、声赞一类的韵文。”[12]149-159唐五代敦煌斋会云集,僧人积极参与到世俗斋会之中,但是参加斋会之前僧人们需要自己先做唱导准备,因此S.2682+P.3128所抄曲子词可能是惠深平时为唱诵念经、作韵学习的需要而抄。最后,据我们所知,历史上的敦煌作为一个佛教圣地,每年要举行多场形式不一、内容丰富的斋会活动,在斋会活动中,僧人为了吸引听众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斋会的参与热情,往往会咏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曲调,S.2682+P.3128所抄曲子词多次出现在其他写本之中,证明这些曲子词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因此曲子词不排除在斋会仪式上诵读的可能性。
此外关于“曲子词15首”的抄写目的,有些学者认为是无意识抄写于一处的杂抄或者是用作保存文本之用。[13-14]但是通过对写本整体细致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曲子词的抄写是有意识的,是经过选择的。首先,从曲子词的内容来看,此15首曲子词的内容大多积极正面,多为关心国家大事、百姓生活之作,境界开阔,思想深邃。其次,此15首曲子词中未有对男女之情的唱咏及对女性装扮、闺阁之描写,没有传统词作香艳内容之描写,这同惠深的僧人身份不谋而合。再次,从这15首词在各写本中反复出现的频率来看,词中所选用的词调均当时流行于敦煌之曲调。这些曲调扎根于敦煌民众中,抄写者选用这些敦煌人民耳熟能详的词调,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讲唱时和听众产生共鸣的需要。因此,这15首曲子词在内容上符合惠深的僧人身份,在使用上,满足惠深日常唱诵练习和参加僧俗活动的需要,并非是杂抄或作保存文本之用。
(三)《社斋文》
《社斋文》是在敦煌三长邑义斋会上的讲诵文本。郝春文在《敦煌写本斋文的分类与定名》一文中提到:“目前所见的敦煌社斋文文本具有斋仪和实用文书两重属性,当某个僧人拿着某篇斋文到其所适用的斋会上去宣读时,这篇斋文就成了实用文书。斋文所具有的斋仪特点是指每篇斋文对与其同类的每个斋会都适用。”[15]16-23S.2682+P.3128所抄之《社斋文》并没有像其它两个写本那样直接提及“三长邑义”,而且斋文也未抄写“斋义回向”的部分,因此《社斋文》可能具有文范的作用。
(四)《太子成道经》
《太子成道经》是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的变文故事,又名《佛本行集经变文》。文章先赞美佛往生时的种种美行,紧接着诵押座文,然后讲述了悉达太子托胎、降生、纳妃、出游、雪山求道之事。文章在将尽之处加入耶输生子一事,文末以七言散座文结尾。《太子成道经》一文韵散结合,说唱兼行。散文部分以白话、口语为主,兼以四六骈体,但内容通俗易懂。韵文部分每以“吟”“吟云”“云云”开端,句式上以七言为主,部分地方夹以杂言,少则两联,多则六联;在用韵上,偶句押韵,大致合韵,全文每部分之唱词押韵不同。整篇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生动有趣,语言连贯通顺。从讲唱文学的角度来看,《太子成道经》一文虽然以“经”命名,但是已经基本脱离了枯燥的经条义理,以及讲经文那种重复引经,据以讲说的程序。取而代之的是在句式上韵散结合;在韵式上唱词押韵,散说口语化;在结构上配以押座文、解座文;在情节上完整生动的一则故事。同时,《太子成道经》在散文转韵文部分,出现了“吟”“吟云”“云云”等变文常见套语,在题材上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变文”。因此,我们认为《太子成道经》并非经文或讲经文,而是一篇通俗的讲唱文学作品,是一篇变文。
(五)《不知名变文》
多个研究者都曾注意到的《不知名变文》中反复出现小字抄写“佛子”的现象,胡适认为“佛子”二字为“看官们”之意,是对听众们说的话。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一书中认为“佛子”是在应该“宣扬佛号”的地方所使用的。[16]184戚世隽认为“佛子”实则为讲唱中,让观众跟着讲唱人一起重复之语句,是变文的常见体制,日后宝卷宣讲中仍有此形式。[7]125实则,在敦煌变文讲经文中,“佛子”一词多次出现,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一文中多次云:“称三五声佛名,佛子”,《欢喜国王缘》一文共有四处注语:“观世音菩萨,佛子”,《维摩诘经押座文》唱词后或注“念菩萨,佛子”,或注“佛子”。《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唱词后亦用小字注:“观世音菩萨”,我们认为“佛子”的功用应是为提升听众对俗讲仪式的参与度,在标注佛子处俗讲僧要提醒观众一同念佛(或念观世音菩萨),这样也能解释“佛子”在敦煌写本中为什么往往以小字标之。《不知名变文》的讲唱性和文学性都非常明显,应该是在敦煌俗讲上使用的文本。
以上的五篇文章,都是讲唱文学文本,其中《大佛名忏悔文》《太子成道经》《不知名变文》与佛教关系密切,应是在佛教俗讲上使用的文本;“曲子词15首”应是惠深平时练习之用,以为了在讲唱活动时能够吸引观众兴趣、提升听众对俗讲活动的参与热情;《社斋文》则是为了参加斋会活动而抄。
在敦煌佛教兴盛的氛围下,斋会活动往往会请僧人到场讲唱,而僧人们也要通过这种形式加强寺院和私社的联系以及为寺院募捐资金。[15]16-23所以僧人们既要向听众宣扬佛教义理,又要能够调动听众的积极性,让听众更多的参与到斋会活动之中。这些就要求僧人唱诵不同文体,以满足听众的不同需要。唐五代时期,敦煌一些大的寺院有教坊一类的机构,其中有戏场、乐舞队、声音人等,僧人要进行诵经、作偈、唱导的专业训练。[12]115-130S.2682+P.3128写本在内容上包含丰富,既有佛教之忏悔文,亦有民间流行之曲子词和变文故事,符合敦煌佛教活动的需求。
综上,我们认为S.2682+P.3128写本是惠深编写的自用本,该写本是他平时学习并参与僧俗仪式活动的备用讲诵文稿,其编写目的在于满足惠深日常训练和讲经说法的需要。
五、结 语
通过对写本情境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S.2682+P.3128写本是敦煌某寺院僧人惠深为了满足日常唱诵练习及参加僧俗活动的需要所抄。从写本内容来看,惠深要求写本内容积极向上,能够表现佛教思想,在内容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倾向性。通过对S.2682+P.3128写本的分析,不难发现,敦煌写本的抄写有很多内在的关联性,写本中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内容或者一些蛛丝马迹都能够引发一些学术探讨和研究。
相对于刻本的“千篇一律”,学界一些专家学者都开始注意到写本具有的丰富“个性”。如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林聪明《敦煌文书学》、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的关系》、方广锠《方广锠序跋杂文集》、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郝春文《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伏俊琏《构建写本文献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读张涌泉教授〈敦煌写本文献学〉》《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概论》等,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写本学”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对写本进行综合研究,关注写本内容之间的不同联系,打破敦煌文献原有“专辑”整理的思路,从写本学的角度对写本情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敦煌学未来的继续发展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或许能够为我们日后的研究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提供更多的学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