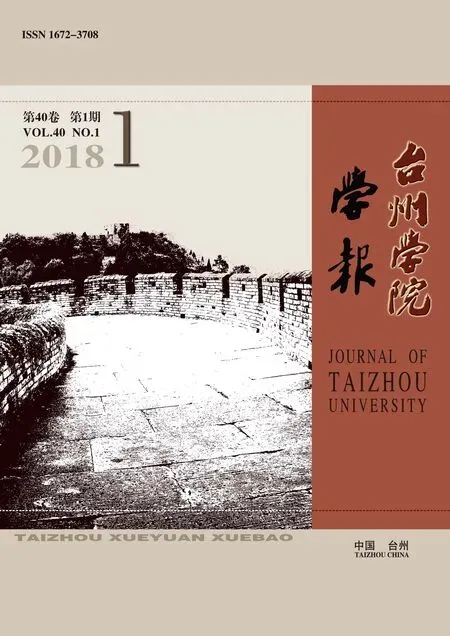试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浙江的“清乡”运动*
郑建锋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清乡”是日伪合作在1941-1945年的非常时期内,在华中(主要指江浙沪一带)和华南占领区内推行的一项法西斯和殖民主义性质的运动。“清乡”以江苏苏州为中心,向外作断续辐射,遍及苏浙沪等省沦陷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军事清剿,政治布控,经济掠夺,思想奴化,一体化的“清乡”活动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抗日力量大大受损,社会经济衰弱不堪。“清乡”是日本推行伪化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确立其政权在被占领区的有效武器。研究该运动对于认识日伪在沦陷区建立殖民统治和推行残酷掠夺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该方面研究薄弱,而区域研究和微观研究更为缺乏。本文以浙江为空间范围,考察了日伪在浙江省的“清乡”活动,揭露了日伪对沦陷区人民带来的残酷暴行,试图从日伪浙江的“清乡”来透视其在整个沦陷区“清乡”的运作状况。
一、“清乡”之由来
“清乡”的出台和实施,是日伪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汪精卫曾说,“清乡”的宗旨和目的在于“确立治安,改善经济生活”,进而“使农村得以安堵,耕地得以整理”,“交通之恢复,实业之振兴”[1]2。但是,细加考察,双方的目的远较此险恶和卑劣。
发动太平洋战争、争夺东南亚沿线,是日本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关键一步。为此,日本必须要紧缩中国兵力以便调集到东南亚地区。但是,因其抢占了大片中国领土,驻扎了大批日军,要进行兵力大调度,又要打击抗日武装,兵源就显得捉襟见肘,1942年其在华中地区兵力才仅仅14万余人。另一方面,日本资源匮乏,加上对华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力,要支持长期战争,必须“以战养战”,巩固在战略资源丰富的华中地区的统治,为此,必须要培植汉奸势力,“以华制华”,这成为日本扶植汪伪政权实施“清乡”的根本意图。
汪伪政权要反共建国,巩固并扩大对东南沦陷区的统治,掠夺更多的财富,也需要借助日本来推行“清乡”运动。尽管汪伪政权是全国性政权,但实际势力所及,仅是对南京、安徽和苏浙沪一带的几个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的点线扼守,根基极为薄弱,“欲藉清乡来奠定其政治的初基,实现其局部的和平,并欲于‘清乡运动’中扩张汪派的势力,排斥维新派的势力”,还能“征收田赋,以期解救财政上的困难”[2]。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清乡”,汪伪政权要“得到一片完全自由行使权利的地方”[3]。汪伪还积极反共,把清剿共产党列入“清乡”的首要任务,言明“共党是奉行第三国际使命,违反民族利益,危害中国,扰乱农村,破坏东亚合作的唯一之大敌”,必须加以剪除才能维护“东亚和平”[1]14。
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需要,经过日方主军事汪伪主政治的协议分工后,就紧锣密鼓地策划“清乡”机构的设立。1941年5月11日,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在南京马台街正式成立,汪精卫兼任委员长,陈公博与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兼秘书长。清乡委员会下设4处2室4个设计委员会,机构庞大。6月26日,日伪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由李士群、汪曼云兼任正、副主任。随着苏州办事处的运行,“凡与清乡有关各机关先后在苏州设置本部,苏州几成为清乡城”[1]415。1941年7月,汪伪“清乡”网罩苏州周围市县,并逐渐向浙江推及,浙江沦陷区人民灾难临头。
二、浙江“清乡”机构的组建与运行
有关浙江地区的“清乡”始于日伪在太湖东南地区(江浙两省境内太湖东南的沿岸地区或邻近地区)推行的第一期“清乡”运动。
1941年7月1日,清乡委员会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办事处及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在浙江嘉兴成立,汪曼云任办事处主任。清乡督察专员公署下辖善兴(嘉善和嘉兴)、松江、吴江、清浦四个特别区公署。正是“清乡”区域的地跨两省,而实权被李士群操纵,引起浙江方面日伪不满而对“清乡”工作加以掣肘,故到9月中旬,便“突然夭折”[4]299。太湖“清乡”一年,成效不够显明,“清剿”“共党”的首要工作也没有多大起色;同时因太平洋战争的人力物力需要,1942年6月4日,汪精卫决定“将清乡地区扩张至苏浙沪各地”[1]33。
清乡委员会—→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特别区公署(执行机构)—→区公所—→乡镇保甲机构
为了掠夺庵东盐场及其周围地区的盐和棉花,切断上海浦东游击队与浙东游击队的联系,日伪于1943年2月起在余姚庵东地区实施“清乡”,由清乡委员会浙东办事处处长沈尔乔主持,行政独立,区域面积为89.54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余姚县和庵东地区。1943年4月行政权划归伪浙江省政府,6月份将浙东办事处改为余姚地区清乡办事处,所有清乡事务由余姚县政府办理,直至抗战结束。
杭州地区的“清乡”早在1941年下半年就已开始,名为“治安整理工作”,实则是日伪在浙江“清乡”的预演,但真正的大规模“清乡”是在1943年。1943年6月7日,杭州地区清乡办事处成立,傅式说兼任主任,谭书奎任秘书长。9月底,在长安镇成立浙江省第二清乡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徐季敦兼任督察专员。9月29日,傅式说与日军枪部队长内田孝行签订《关于浙江省第二清乡区清乡工作之协定》,规定10月1日起“清乡”,区域为崇德、桐乡两县、海宁大部和嘉兴、嘉善、德清、杭县四县一部分地区;随后又签《关于浙江省第二清乡区清乡工作推进之协定》,“扩大工作于浙江省第二清乡区重点区域以外之全部,并强力推进之”[1]209。此次“清乡”,直至日本投降方告结束,浙江大部沦陷区深受其害。
三、日伪全方位“清乡”及其运作
汪精卫一再声称,发动“清乡”的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在“清乡”第二年便抛出了“思想清乡”的阴谋,大谈“清乡必先清心”,“清乡”是“心理上的建设”[6]。由此可见,“清乡”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思想的,是全方位的“清乡”。
日伪在浙江推行“清乡”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清乡中心工作,首推军事。军事如不能开拓,其他一切皆无从设施。”[1]16“清乡”兵力由日本方面领导,以枪部队和其扶植的浙江保安队和警察为主体。“清乡”工作开展后,日伪就积极改组训练伪警,整编“清乡队”,设置特区警察局训练警察,扩充警力,协助日军从事“扫荡”。在对浙“清乡”中,汪伪投入的伪军警数目较大,其配置大致如下:嘉兴地区4023人,杭州地区3700人,庵东地区3000余人[1]434-436。
“军事清乡”首先是进行“扫荡”。清乡一开始,先是在浙江沦陷区划出“清乡区”,然后征发民工、砖瓦和竹竿等,在周围广筑碉堡炮楼,构筑封锁沟和铁丝网,在交通线和河道湖面加紧舟车的巡逻。封锁完成后,日伪即出动兵力对抗日力量和政府机关进行“扫荡”。对于抗日根据地和活动中心,则采取拉网式、梳篦式战术,分进合击;同时在包围圈内增设据点,坚壁清野,致使许多地方都荒芜一片。1943年1月到2月,余姚日伪宪兵、保安队等2000多人,混编成“清乡队”,对庵东盐场进行“清乡”,残害民众,烧杀抢掠,把余姚变成了“活地狱”。
其次就是对沦陷区军民的“封锁政策”。一般是强征竹篱笆材料和铁丝,同时训练专业封锁人员,圈定“封锁区”。为了对“封锁区”内的民众加以控制,在各个出入口,设立大小“检问所”,盘查出入人员,有些据点还设碉堡,配备日伪军守卫。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4月,日伪在浙江“清乡区”修建封锁线长达187公里,大小“检问所”40个[7]。1943年4月到5月,日伪军强制庵东群众将东起新浦沿闸口、西至英生街的沿南封锁线塘堤,筑高50公分,加阔4公尺,铺成32公里长的泥面公路,设“检问所”22处,大小碉堡22座[8]。日伪为了修建封锁线,还肆意损害人民的财产。“日伪军担心农村中抗日力量攻打县城,强令将沿城四周两里以内的树木砍伐光,单是东门一带被破坏的桑园就有几百亩。”[9]人民自由也受到绝对限制,出入“封锁区”必须携带“良民证”等证件。对于不满人员或钻篱笆人员,轻则关押处罚,重则枪杀。
随着“军事清乡”而来的是“政治清乡”。日伪“清乡”“特别着重于‘政治’方面的阴谋,由‘政治’的阴谋而达到‘军事’‘经济’阴谋的兑取”[5]14-17,从而加强伪化统治。“政治清乡”实质就是集警察伪化、保甲连坐、团体监控为一体的法西斯主义殖民统治。
“政治清乡”特别注重建立警察保安系统,强化伪政权。汪伪政府在“清乡区”内除设有清乡警察总队外,省有保安司令部,区有保安处,县有保安大队,还设置警务督导室对警务督导,以期增进工作效能。日伪企图通过建立层层武装机器,肃清游匪,根除地痞莠民,协助催征赋税,编组保甲,从而使“治安得以确立,民生得以昭苏”[1]434。据伪省府统计,浙江三个清乡区共配备警察保安人数为8254人,大约每200人中就有一个安保人员。在招收的警察和保安队伍中,人员大多是平民,多为被迫加入。当然也有不少国民党游杂部队和地痞流氓,充入警察保安系统,对平民实施监控,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体系。
社会上与学术界对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议论不休,学者们各持己见,抒发了对该项政策利弊的分析。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综合自身利弊以及国家发展环境来进行充分讨论,因此,更适合利用美国旧金山韦克里教授提出的事态分析法(又 称 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分析法)进行讨论,充分将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以及威胁(Threats)进行论证。
编组保甲也是日伪在浙江“政治清乡”的重要内容。“自治工作,厥以保甲为首要。”[1]436保甲首先要设置保甲训练班,经培训合格分发浙江各特别区充任保甲室主任、区长、指导员,担任职务。保甲编组,首在对治安确立之城镇编组,次及实施封锁后之乡镇,再次及经过军事“扫荡”之乡镇。同时还实行恶毒的“连坐切结”制度,规定,“如该结内藏有要匪及匪物”,一经查出,“同结者与匪同罪”[10],以此来笼络民众,分化抗日力量。1942年汪伪成立了“治安办事处”,设置在杭州市郊,大搞“保甲连坐”,妄图步步推进,压缩抗日活动空间,切断政府、民众、反日力量之间的关系,使沦陷区民众成为日伪忠实的“奴仆”。为此,在180万人的三个清乡区内不惜设置了3978个保,38921个甲[1]437,日伪严密统治由此可见一斑。保甲制度的推行,增加了浙江日伪的收入,强化了对沦陷区的奴化统治。
为加强社会团体控制,大搞“自卫团”和社团。“自卫团”是以地痞流氓等为主要成员组织的准军事性反动团体,主要用于“防剿”抗日军民,“编组保甲,辅助(日伪)军警维持地方治安”[11]。团丁平时维护治安,入室查口,协助追寻“共匪”;战时参加修筑军事设施,有时参加战斗。为造就地方有力之团队,日伪特别注重对团丁的操练和干部的训练,最终训练团丁近20万人。同时,为加强对社会各团体的控制,汪伪当局着重调整旧有人民团体和各种行会组织,规定工商业行会凡满七家者,责令组织同业工会、重订宗旨和政纲来顺应日伪需要,如第一清乡区就在半年内新增和调整了各种团体321个。
“经济清乡”是日伪“清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日伪延续统治的生命线。汪精卫极度关注两个问题,“一、清乡前后的人口比较;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比较。”[4]314人口越多,掠夺对象就越多,赋税收入就越多。可见,“经济清乡”乃是掠夺和剥削的代名词而已。
“经济清乡”的第一步棋是物资统制和物资掠夺。日伪通过物资管制法规和条例,对粮食、棉花、盐、金属矿石等重要物资实施严控。为了控制掠夺杭嘉湖地区的米、丝和余姚庵东的盐场,日伪专门建立了华中蚕丝公司和华丰公司。日伪的物资统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日伪搜刮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切断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从经济上困死抗日军民。日伪把粮食、棉花、茶叶等农产品列为重点掠夺物资对象,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发,利用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强行摊派,公开搜刮。1943年6月,汪伪嘉善县长胡弘玑帮助日寇抢收军米,并与奸商勾结,强行派征军米每亩八斗七升四合,仅路北就被抢劫去67000余石[12]。二是强制低价贸易,价格仅及市价一半。1943年日军成立由汉奸沈师石负责的“嘉兴军米商采购商会”,强购军米,规定每亩征购军米八斗,按市价半数计价。三是抢劫和勒索,并以武力相威胁。1943年秋,日伪在硖石火车站的大“检问所”对来往旅客公然勒索,仅一班火车就搜刮到8000多元(文中货币单位均为汪伪储备券)。
通过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是日伪在浙“经济清乡”中的主要手段。为有条不紊的稽征“清乡区”赋税,日伪在各特区设置赋税管理处,每处择扼要地点设置赋税稽征所5所,并在各乡镇分设保甲纳税会。为改进“清乡区”税务,以期赋税征收的所谓“合理化”,特设置浙江税制审议委员会。在所有赋税中,“田赋”被视为最大之税源。后来由于田赋税征收情况不佳,伪浙江省政府提出整顿田赋,提高税率,所征田赋税率折合达到70%;而且加征数量,如1942年日伪规定浙西田赋按每亩18元,户捐按每亩3元计征[13]。其次就是营业税和营业专税,由于是肥缺,因而狠加重征。浙江“清乡”地区1942年下半年田赋收入、营业税、营业专税占总收入38.43%,1943年上半年三项合计就上升到总收入的84.87%。可见,日伪剥削之重。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捐税,日伪以整顿为名,巧立名目,如货物进城税、茶碗捐等,以致于到1944年浙西捐税竟然达35种之多。据伪浙江省政府统计,日伪浙江“清乡”地区的赋税收入1943年上半年度为2525万余元,而下半年度则猛增到7160万元。沉重的赋税压在“清乡区”人民的头上,人民苦不堪言,讥讽“清乡”为“清箱”。
在日伪的“清乡”计划中,“思想清乡”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汪精卫深知精神统治的重要性,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从而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任所谓的和平运动。通过此举,日伪对“清乡区”人民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得到空前强化。
“清乡”宣传是伴随“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鼓噪起来的舆论恶浪,是“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之一。日伪在浙设立了清乡宣传委员会、清乡宣传总队、清乡政工团等机构,各县、乡镇也设置了宣传机构,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宣传网络,犹如一架精神奴役机器置于人民头上。同时出版“清乡”报纸、期刊,举办“清乡”展览,张贴“清乡”标语,散发“清乡”传单,甚至在食物包装袋、发票上都印上“清乡”标语。1943年11月,日伪在崇德县城创办《崇德新报》,出八开三日刊,作为宣传奴化教育之主要工具。嘉善县也创立了《新报》,宣导奴化,标榜汪伪的“正统”。此外,日伪还举行纪念日来扩大宣传,举行流动剧团巡回公演。日伪搞的“清乡”宣传,内容无非都是“中日共存共荣”、“和平反共建国”之类,妄图以此来毒化和腐蚀沦陷区人民,摧毁人民的爱国和革命精神。
“思想清乡”重点就是所谓的“清乡特种教育”。特种教育的目标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之谬妄,及共产党之罪恶……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信念。”[1]369汪伪为此在浙江设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对清乡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施行所谓的特种教育,开办扩张学校和社教单位。首先是把学校作为推行“特种教育”的基地,主要在浙西和路东展开。针对青少年学生,编印发放了“特种教育”教材10多种,如《领袖言论》、《清乡讲义》等。针对教师,则加以“特种教育培训”。汪伪教育部统一规定学校教材,其中充斥着“中日亲善,和平反共”等内容,还强迫师生进行对外联动宣传。在加强社教方面,则普遍设立民教馆和民众学校,定期强迫组织民众上课、谈心得,增强民众对“大东亚”和汪伪政府的信任和热爱。1943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日伪仅在浙江第二期“清乡”中进行伪化的中学就有6所,完全小学47所,初级小学182所,所设民教馆35所,民众学校25所[1]506。
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也是日伪实行“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首先,逼迫青少年参加伪教育组织,组编青年团和童子军。1942年底,浙江成立“清乡区青少年队”,诱逼大批青少年参加。其次,利用寒暑假抽训中小学体育教师,组成训练班,在嘉兴和杭州共训练261人。训练结束回到各地协助组织青少年团和青年学校,推行“汪精卫主义”文化教育。再者,对中小学生灌输法西斯主义奴化教育。1944年春,伪崇德县政府开办了伪崇德县立中学,每周开设两节“青训课”,对青少年进行严格的武士道精神训练,“邀请”日军头目训话,并强迫学生呼喊“大日本万岁”等口号;音乐课则教唱《大东亚进行曲》、《支那之夜》等歌曲,千方百计地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心理戕害。
综上所述,日伪处心积虑地在沦陷区实施全方位“清乡”运动,以华制华,推行伪化统治,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抗日军民坚持积极顽强斗争,使得日伪“清乡”不仅未能最终达到其恶毒目的,反而加速了其走向败亡的进程。
参考文献:
[1]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贺扬灵.浙西三十年度敌伪阴谋总分析[M].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秘书处,1940:59.
[3]蔡德金.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28.
[4]黄美真.伪庭幽影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5]贺扬灵.浙西反清乡战斗及其成果[M].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秘书处,1942.
[6]汪精卫.清乡工作之要义[J].政治月刊,第七卷,第2-3合期,1943:2-3.
[7]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6)[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94.
[8]慈溪文史(10)[M].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5:142.
[9]桐乡文史资料(1)[M].桐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5:47.
[10]复旦大学历史系.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335.
[11]佚名.清乡地区各特别区自卫团组织暂行条例[J].中华日报,1941-7-31(2).
[12]嘉兴市文史资料(1)[M].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6:78.
[13]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