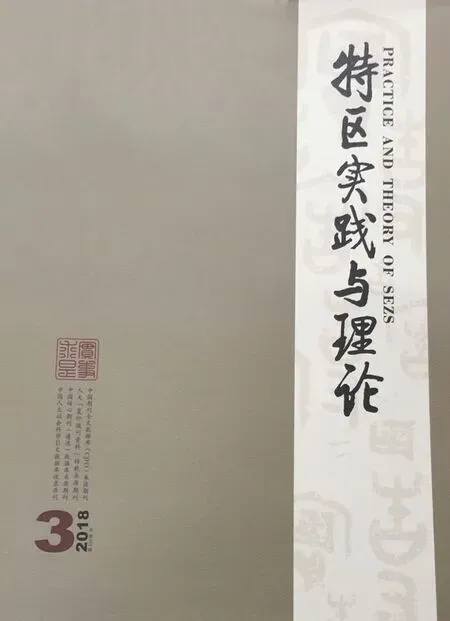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与礼乐教化
王法强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下,政治正当性问题始终是政治生活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议题。因为任何政权想要实现长治久安,“除了需要具备镇压性的力量外,尚须具有意识形态的说服工作,让人民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①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达成团结一致的习俗、个人利益、纯粹的情感或理想动机,对于一个既定的支配来说,并不能构成足够可靠的基础。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政治正当性的信仰。”②[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可见,只有人民对现存体制充分信任,亦即对其政治正当性抱有信仰,这个国家才会真正实现安定和谐,国泰民安。
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儒家有关政治正当性信仰的思考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一、天命与民意: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两大维度
与西方政治思想家主要通过政治制度的安排,强调主权应当由谁来掌握的致思路数不同,儒家思考政治正当性问题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那就是“天命”和“民意”。天命和民意可以说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两大最为重要的政治价值维度。
如果说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催迫着古代中国人立足于从超越人类的视界来审视和思考人间秩序的合理安排和公正治理的问题的话,那么,对民的重视和对民心民意的尊重,则促使着古代中国人必须从民惟邦本的立场来审视和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正确治理之道和权力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当然,天命和民意并非两种独立的要素,而是紧密相连的,或者说二者具有一体性。天命所在,也就意味着民心所向,反之亦然。因此,统治者能否赢得天命以及天命的丧失与否,其实最终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儒家有关政治正当性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肇始于“武王克商”事件。所谓“宪章文武”即表明儒家政统来源于周文王、周武王所创发的典章制度与价值信念。如何对获得的统治权进行合理解释,亦即对其政治正当性进行辩护,是周初统治者所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周人认为商朝灭亡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周能够取代商,是由于天命已转移到了文王身上。“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尚书·大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康诰》)然而,正因为“天命靡常”可转移的缘故,一个政权想要长久地保有天命,则需要君王自觉“敬德”、“以德配天”,正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周人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发现了上天的意志与民众的意愿通常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也就是说,天意与民意具有共通性,对于人民意愿的满足,君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民众就可借助上天的权威,来评判君王行使权力的正当与否。
从上述政治解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周初统治者对其政治正当性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多重正当性,即君德、天命、民意三者共同构成了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基础。而且,三者之间还形成了相互间的关联与平衡。①董琳利:《简论“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周人所创发的这种“天命”论构成了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思想源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天命正当性信仰发展为中道的执政理念,如尧、舜、禹三圣王禅让之际告诫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也就是说,只有认真奉行公正的治理原则,让天下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才能“永享天禄”,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在政权转移的正当性问题上,孟子强调“天与人归”的政治理念,“‘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汉代大儒董仲舒借助于“五德终始”说与阴阳五行宇宙图式重构了传统天命说,为汉帝国提供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意识形态模式,对于维系汉王朝的长期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核心要义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一方面,强调民众要服从君主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于天命的权威来限制君权。总之,这种“天命”论政治正当性信仰既揭示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又对于长久维系其政治秩序提出了限制性条件。
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另一重要维度或最为关键的要素即为民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集中表达了儒家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即把人民视为邦国的根本,把政治视为固本安邦的神圣事业。儒家对于民心、民意一直高度重视,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统治权的最终归宿,亦即民意是衡量政治正当性的标准。如对孟子来讲,最大的政治问题便是如何赢得民心的问题,在孟子看来,权力的转移和运用只有赢得民众的支持,才具有正当性。那么,统治者具体怎么做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呢?依孟子之见,统治者只要能够行王道、施仁政,并能够与人民同好恶、共忧乐,便可以赢得民众的支持,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也指日可待。对孟子而言,“政治之为政治,说到底乃是一种最能充分而淋漓尽致地发挥人类休戚与共的精神和实现君民一体化的情感交融与共鸣的场域。这是从君民相互依存、彼此应良性互动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政治生活的实质,基于这一理解,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对于人民的真正意愿和民生需求作出积极而负责任的回应乃是其应尽的职责”。①林存光:《“民惟邦本”:政治的民本含义——孟子民本之学的政治哲学阐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因而,孟子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站在民惟邦本的立场上,企图唤起的是统治者对自身天赋良心善性的发现以及对于构成其统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的民心民意的认可与尊重。荀子亦高度重视民本问题,将民众的支持作为政治正当性信仰的基础,“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这种“舟——水”之喻的经典表达,无疑道出了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正当性信仰的真谛。历代儒者或士大夫都高扬民本理念,自觉担负起为民请命的道义使命,甚至于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证明了民意为上的政治正当性信仰及其伟大力量。
总之,天命与民意构成了儒家思考政治正当性信仰问题的两大维度。而且,天命与民意互为支撑、融为一体,才符合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真精神。在今天看来,儒家民本思想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值得我们加以珍视的强调“负责制政府”的重要精神遗产。它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度成熟的政治理性精神,它强调人民是政治的真正目的,要求统治者必须承担起理应担当的政治职责,必须对于人民的真正意愿和民生需求做出积极而负责任的回应,并承认人民拥有评判政府好坏和反抗暴政的最终的正当权利。
二、民惟邦本:君民共同体的构建
政治的真正意蕴和目的,是“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②[美]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2版),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这就需要人们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协作性的行动,以便共同创造美好社会生活的愿景,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共同体理念和政治智慧。
儒家之所以推崇“民惟邦本”的政治正当性信仰,实则在他们看来统治者和人民理应构成一个休戚与共、痛痒相关、血脉命运密切相连的“君民共同体”。正如《大学》所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因此,正确的治国理政之道便必须本着民惟邦本的信念而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如孟子提出首先要“制民之产”,即强调统治者有责任和义务来保障民生,为人民创造一些经济条件,从而“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③[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0页。另外,对于“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国家也有义务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这些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积极价值,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更是难能可贵。
就共同体的创建而言,儒家文化天然具备形成共同体的“基因”——在宗法制的社会里人总是处于各种伦理关系中,“通过德性的践行与人际交往的良性互动,构建并形成一种优良的人类关系模式与和谐的共同体生活秩序”。④林存光:《儒家视域中的人际正义及其实践性特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因而,儒家始终坚持以修身为根本、以齐家为始基、以孝悌之道和伦理情谊为纽带,以便构建一种优良的社会生活秩序,乃至进一步推扩拓展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目标。《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若想构建一个和谐的君民共同体,首先都需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这自然离不开教化的作用。事实上,孔孟古典儒家都十分注重百姓的“养”和“教”问题。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
可见,无论是孔子所提出了“庶——富——教”安民三部曲,还是孟子所主张的仁政教民举措,都突出强调了君主的“养民”、“教民”职责。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儒家的社会理想在于构建一种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共同体生活愿景。
虽然君王有教化民众的职责,但事实上通常承担教化职责的是士人君子。也就是说,士人常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君主←士→民众。
“士人于是就居间对双方作功夫: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晓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大要总是抬出伦理之大道理来,唤起双方理性,责成自尽其应尽之义。”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士人君子的责任担当精神,对上“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意在“建立一种师友道义相交的精神共同体,进而力图在公共政治领域推广此师友之道,以塑造一种协同合作的道义性政治关系来实现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②林存光、杜德荣:《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与深刻意蕴》,《天府新论》2017年第5期。对下强调承担辅君化民的教化职责,如孟子所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值得注意是,孟子所强调的这种精英意识绝非与民众意愿相脱离,而是自觉担负起表达民意的职责。
总之,在儒家“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指引下,君主自觉担负起恤民、养民、教民的职责,再加上士人君子的辅助、调节,那么,构建“君民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便会实现。
三、 礼乐和合的共同体运作机制
对于共同体内部的秩序安定,儒家礼乐文明可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无论是最初的周公“制礼作乐”,“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③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3页。还是后来的“伦理本位”社会,“向外‘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向内‘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使全社会通过‘礼’构成一上下贯通、涵浑蕴藉之伦理整体”。④陈续前:《礼:从周公到孔子》,《孔子研究》2009年第4期。因而,礼乐实乃充当着共同体内部规则的角色。具体而言,礼乐的秩序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层面:
(一)礼序乐和的功能定位
有关礼、乐的功能,《礼记·乐记》篇论之甚详,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等。可见,礼的作用在于使事物条理有序,乐的作用在于使事物得以和谐,正所谓“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的这种“别异”功能在社会生活的各种礼仪中均可得以体现,如《礼记·经解》篇所言: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
其中,丧祭礼、婚姻礼属于家庭、家族内的伦理规范,乡饮酒礼属于乡里社群的伦理规范,朝觐礼、聘问礼则属于诸侯国乃至“天下”的伦理规范。可见,礼可作为适用于各级共同体的伦理规则,而且蕴含着一定的道德教化属性。然而,共同体若仅仅依靠礼仪规范的话则可能会产生“礼胜则离”的流弊,因而需要乐来配合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实上,乐的协调功能同样也可适用于各级共同体,乐的感通性可以使处于不同伦理角色中的人们共同得到心灵的抚慰,生发出“和敬”、“和顺”、“和亲”之情。如果说礼主要规范的是人们的外在举止,那么,乐则进一步调节人们的内在情感。这样,通过礼序乐和的巧妙结合,便会实现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局面,“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进而言之,在社会风俗的教化方面,礼乐的功能亦比较显著,“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二)礼乐的利益调节功能
若要长久维系共同体内部的和谐稳定,就要妥善处理好个体需求的满足与共同体秩序的维护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阿米泰·伊兹欧尼所言:“共同体成员的个体需求并不是只要成为共同体的一分子便能得到满足。个体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共同体对共同善的定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成员,但任何共同体的成员都有不同的需要。另外,共同体成员还有自我表现的需要。”而如果个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便可能产生对共同体的离心力,“而离心力达到很强的程度就会破坏共同的纽带和文化”。①[美]阿米泰·伊兹欧尼:《回应性共同体:一种共同体主义的视角》,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页。事实上,荀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证礼的起源的,正如《荀子·礼论》篇所言:
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样,先王通过制礼来厘定“度量分界”,保障每个人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资源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与有序运转。另一方面,礼乐还具有涵养性情的作用。《礼记·乐记》篇作出了精辟阐发,如: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可见,礼乐在人的情欲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了君王的身正示范效应,即以礼乐调理身心最终会使人们归于和顺。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人祸之所以起及其所以烈,实为愚蔽偏执之情与强暴冲动之气两大问题。……礼乐运动,以求消弭人祸于无形。”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这里所讲的“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就是要人们远离愚蔽、强暴之情气而保持清明安和的心态,正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礼乐所涵养的礼让德性还蕴含着一种利益共享机制,尤其是作为统治者,切不可与民争利,而应与民共享、“与民同乐”。③干春松:《“让”:儒家伦理中的分享与共同体建构》,《新东方》2016年第6期。不惟如此,在“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中,整个宗族与乡里内也“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之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盖无力负担,人亦相谅;既有力量,则所负义务随之而宽”。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0页。这种注重情谊的互助共享机制无疑有助于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
(三)礼乐贵和的价值取向
丁鼎先生在考察、总结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时指出:“‘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⑤丁鼎:《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事实上,儒家礼乐文化的“贵和”取向是比较突出的,如“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等。然而,“贵和”究竟如何落实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呢?这便涉及儒家“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致和之道。孔子将“和而不同”看作是处理一般人际之间和不同意见之间关系的理想准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的思想蕴涵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哲理,因为“和”意味着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需要平衡诸方面的矛盾,亦即实现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我们的先哲还特别重视人类合作中的“求同存异”问题。人类的任何一项事业都有赖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合作,这既需要充分尊重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知识能力及意见表达等,同时强调人们之间同心同德的合作意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就人际之间的合作关系而言,“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都同样重要,两者并不矛盾。“和而不同”的思想内含着对多元事实的承认,蕴涵着对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接受与包容的态度,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而“求同存异”注重的是以“同舟而济”、休戚与共的共同感来构筑人类合作的基础,即在达成某种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或在某种远大而共同的理想目标的指引下,暂时将易于引发或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异”的一面放在一边,通过协同合作来共同推动人类某项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是传统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关涉获取政权与稳定统治的正当性辩护。无论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辞》)的口号,还是陆贾“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谏言,都点明了儒家政治正当性信仰的要义,即敬畏天命与顺乎民意。天命与民意具有一体性,天命通过民意来表达,因而一个政权的获取与稳定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民众的支持。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政治格言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君民共同体理念与政治智慧。而对于维护君民共同体的安定秩序,离不开士人君子的礼乐教化作用。无论是礼序乐和的功能定位及其利益调节机制,还是“贵和”价值理念等都可为维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1]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董琳利.简论“武王克商”的政治正当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5).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林存光.“民惟邦本”:政治的民本含义——孟子民本之学的政治哲学阐释[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7][美]安德鲁·海伍德著.政治学(第2版)[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英]霍布豪斯著.自由主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林存光.儒家视域中的人际正义及其实践性特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1).
[1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林存光,杜德荣.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与深刻意蕴[J].天府新论,2017,(5).
[1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陈续前.礼:从周公到孔子[J].孔子研究,2009,(4).
[14]干春松.“让”:儒家伦理中的分享与共同体建构[J].新东方,2016,(6).
[15]丁鼎.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