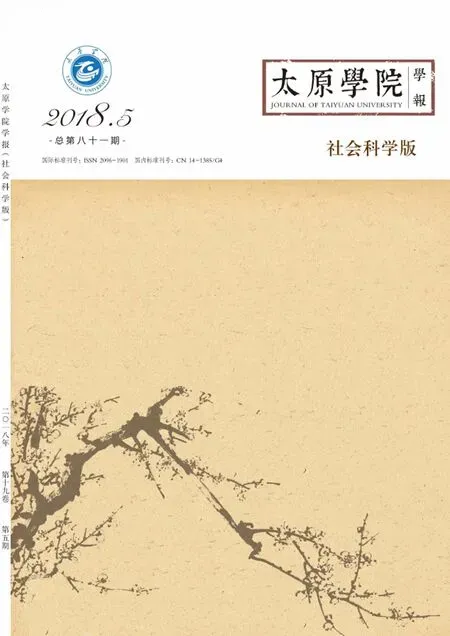作为一种时间/历史意识的审美现代性
巩 晓 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审美现代性,正如它作为一个时期概念的名词一样,反映的始终是一种对时间/历史的新认识,以及它在审美领域的表现。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审美领域的现代性特征反映出的正是这一种“现代”的时间/历史意识,无论它有五副面孔还是更多面孔。
一、审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意识
从“现代”“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这组相似性概念中品味出时间意味并不需要太多理论敏感。不论是形容词、名词还是将它限定在美学领域,或是仅仅指一种具有共性又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们始终联系着时期概念。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文版序言中引用的尼采的话:“历史概念没有定义,只有历史”[1]中文版序02,他又十分中肯地补充说:“这些历史往往交织着争论、冲突与悖论。”[1] 中文版序02可见,现代性不仅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且它的历史性如其他理论概念一样也是双重的,它既寓于历史之中,又存在自身的历史性特征。因此可以说,现代性解释历史,并被历史所解释。这并非是有意做同义反复的语言游戏,甚至有理由相信,在现代性的映照下,与其相关的人、艺术作品、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具有了这种历史意识的自觉。
首先,从词源学意义上看,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就是天然的: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成功,在早期中世纪拉丁文中出现了形容词“modernus”,它源出“modo”这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语(意思是“现在”“此刻”“刚才”“很快”)。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任何出现时包括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同“antiquus”(古代)相对,后者指一种就质而言的“古老”(古老=一流=工艺精良=有可敬的传统=典范,等等)……自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以来,“现代”对过去的权威一直怀有深刻的矛盾心理,越来越将自己系着于转瞬即逝的“今天”及其需求、梦想或梦魇,并转而着眼于未来,把它看成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到来的希望,或是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与颓废的前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1] 中文版序01-02
“现代”意义之中的现在性意涵,突出了当下的意义概念,从而区别于古代。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此时此地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把整体性的一条连续性的线性时间(无论它是循环的还是不可逆的)线条割断。过去、现代和未来三者之间的分野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此基础上,“现代”也就肯定了自身的意义,并且建构了与过去和未来的新型关系。而后者,可能是它关注更多的一方。
在审美领域,现代性(这里主要谈审美现代性)表现出与历史传统的主动性决裂。审美现代的对立姿态是鲜明的,但它更是具有主动性的。也就是说,尽管审美现代性一开始就表现出激烈的反叛姿态。但是,客观上它与历史传统以及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反叛可以看做是审美现代性的先声。如果说存在断裂,与其说断裂是文化上的,不如说是发生了时间/历史意识的断裂。卡林内斯库举司汤达在《意大利绘画史》(1817)中对浪漫主义的看法为例:
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无论是较长的还是较短的),也不是一种特殊风格,而是一种当代生活意识,一种最直接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他的浪漫主义不止是一种含悖论的常识:由于它暗示了‘浪漫’和‘现代’之间的同义性,由于它传达出强烈的时间意识,我们可以说它是波德莱尔现代性理论的雏形。[1]39
司汤达对浪漫主义的时间性、新奇性的强调是对于传统的反叛,是另一种不同于抵达超验的雄心,是一种对艺术天才的雄心。这种雄心是属于当代时期的,也就是一种现实感。“对于司汤达,浪漫主义的概念体现了变化、相对性的观念,尤其是现时(presentness)的观念,这使得它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四十年后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重合。”[1]40就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来讲,浪漫主义与传统的断裂之后,其与现代性在此就现出了历史联系。此后,从现代主义到先锋派,再到颓废派的不合作态度,再到新的先锋派(后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的历时性衍进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骨”。对于审美现代性来说这种主动性地与历史的决裂始终在发生,尽管很多时候仅仅能把这种“决裂”看做一种态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反传统是审美现代性固有的历史意识特点。
审美现代性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主动性决裂的过程。浪漫主义与宗教文化密不可分,但是,与浪漫派相结合的现代性同基督教的关系并非结合得如表面上看去那么紧密。浪漫派的宗教色彩不过是以基督教的资源和材料,甚至宗教某些可不断阐释的教义或教派之间的裂隙来作为资源对抗理性主义的教条和艺术上的干瘪。对于基督教末世论或者千禧年主义的强调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为放弃永恒美的寻求找理由。同样的,对基督教的美与异教的美之间的“不可跨越的鸿沟”的强调也是强调历史有其走向,它走向终结,而永恒美无可企及。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尽管“上帝之死”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从宗教中来,它开始进而反驳宗教思想。卡林内斯库说:“这一次,现代性和基督教之间的分裂似乎是彻底的。”[1]64客观上说,审美现代性从来没能割断与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关系,但是审美现代性作为一个时期概念又始终表现出与传统的决裂态度,尽管这并不妨碍它将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传统材料都尽数拿来为我所用。审美现代性一贯努力做到名实相符,证明自己绝非过去的东西,而是一个全新的“现在”。
审美现代性将“现在”突出强调出来,整个历史不再是一条平滑延伸的或直或曲的模糊的线,它似乎是从现今发出的一道光,过去和未来都在它的映照下才能见出本色。这一点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契合之处。新历史主义研究了历史的编撰性、叙事性和修辞性等文本特征,从而指认历史文本普遍具有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特征,模糊了史实与虚构的边界。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曾直言:“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2]中文版序05这就将历史研究从对史实的考古本身拉回到现时性的目的,强调了历史为现代人所写,更是为现代服务。卡林内斯库谈到培根在“童年的无经验”和“老年的智慧”之间建立的悖论时说:“我们现代人才是真正的古人”。[1]23他说:“因为我们所谓的古代人仅仅相对于我们才是古代的和较年老的,就世界而言他们显然比我们年轻。”[1]23-24培根的意思是我们的时代比起过去阅历丰富而获取了更多的经验,就像一个“老人”在他一生中储备了更多的经验一样。尽管,不无厚今薄古之嫌,“在培根的知识进步观中,在他对古代权威(其煊赫的古老性仅仅是一种视觉幻象)的含蓄拒绝中,所涉及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时间特性。”[1]25这种时间意识也反映了个人生命短暂易逝的线段性特征与更长的时间中无法企及的过去和未来给人的悖谬式感触。审美现代性从“现在”的角度看待整体的历史,悄然地排除了历史中与“现在”无关的部分。像新历史主义对历史书写主体的强调一样,审美现代性也突出强调了现代、现代人处于整体性的历史时间的中心地位。对于审美现代性来说,正是“现代”把浑然一体的历史线索分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部分。相应的,这三个部分的重要性也有了排序,“现在”是第一位的,它是“未来”的基础;“未来”和“现在”成为一体,不可分隔,它既是现在的永恒动力——一个乌托邦,也是“现在”的目的和理想前景,排在第二位;而“过去”只不过是一种资源,有时甚至说不上是一种反面参照,因为其经常被悬置,显然只能位列最后。有意思的是,当想象一个终极的未来时,出现了“乌托邦”这个概念。“乌托邦概念最初是基于一种空间联想(topos-地方,u-没有 ,utopia-乌有之地)”[1]65不禁让人联想起作为空间的伊甸园或是天堂,这个想象中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来自传统,不论是宗教的还是其他传统文化的。而“乌托邦想象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发展,是现代贬低过去和未来日益具有重要性的又一证据”[1]66,过去失去了它的终极意义,留存的是其功利性的价值。因此,“古人模仿现代人”也不过是借古人的美学材料表达现代性的审美新意识。这正是:“‘现代/古代’这种术语对立变成了美学纷争的一种标准形式。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了文学艺术通过否定既有趣味范型获得发展的模式。”[1]35与其说这种范型否定的是既有趣味,不如说它否定的是既有的整体性的时间/历史意识,强调了以“现在”为基准的线段式时间感触——一种与过去的时间的主动性决裂。
二、审美现代性的时间/历史意识之特征
审美现代性在审美和艺术风格上的特点都与它自身的时间/历史意识密切相关。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言,既是由于现代概念先天是由时期概念来确定的,也是由于它主动在与传统的决裂和否定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决定的。关于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卡林内斯库说:“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permanence)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immanence)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之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1]01也就是说,具体来看审美现代性至少具有新颖性、当下性和瞬时性三方面的特征。当然,尽管审美现代性一贯对整体性历史持不屑态度,对过去持否定态度,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仍然要以历史的延续性特征为参照,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时间/历史意识的审美现代性之特征始终是寓于历史之中的。
审美现代性作为肇始的突出特点就是其新颖性(newness),庞德的“使之新” (Make it new!)是审美现代性的训谕。要锐意求新就要从旧的一切中脱离出来,这就决定了审美现代性一开始就具有的否定式和战斗性特质,也就催生出了“先锋派”。“先锋派”这个概念具有军事内涵,被描述得具有一种青年式的激进和激情,而思考是置于其后的。“战斗”“颂扬”“必然”这类词汇将艺术形式的发展更新加进了社会革命实践的色彩。因此,作为先锋派先声的浪漫主义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对艺术之外因素的规避也是一种不顺从的否定式态度,甚至是对艺术可以影响社会发展的一种信心表达。浪漫派遵从传统的观点,认为诗人具有先知的特质,艺术似乎可以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发展,在这里艺术先锋性与政治的革命性就发生了关联。尽管事实上二者之间一直在博弈,真正的蜜月仅仅存在于理论构想之中。无论是否过于轻率,先锋派以其激进的姿态,甚至不惜自毁与过去甚至自我的“现在”决裂,不断致力于推陈出新,这是审美现代性最初也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当下性(immediacy)或称现时性(presentness)是审美现代性的又一突出特征。在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中,现代性与现时性是一体的,共同组成了整体性历史的反面。这里的当下性不仅限于此时此刻或者“当代”,即使对于过去,也用一种当下性的态度去把捉,因为过去的每个时间点也曾经是当下。这里不妨这样理解:审美现代性要求重新发现最具体而微的每时每刻的重要性,包括过去的每时每刻,因为它们也都曾经是具有当下性的、独特的,按照芝诺所言处于“飞矢不动”状态时的时间点。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颓废派的特征——其对于极其精微的细节的关注了。如果说颓废有三个主要特点——极度精致、抬高想象力而损毁理性和打破边界——的话,前两者无疑都有涉审美现代性对于当下的强调。极度精致的细节描写突出了事物此刻的存在状态,同时也是对于极为精微的心理感触的表达。“颓废中的社会”与艺术领域的颓废派不谋而合,无论是审美要素还是社会因素都大量随机地涌现,并不构成合力。“抬高想象力而摧毁理性”也是同样,想象力也是此时此刻的想象力、一种现代性的想象力。在波德莱尔看来:“往昔的杰作如果被当成范本,只会妨碍对现代性的想象性追寻。”[1]51而理性仍然是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推演,具有前因后果,这些并非当下性所强调的内容。然而,到了媚俗艺术这儿,则强调了一种“即时性”原则,这种即时性既是对当下性的强调,或者称为对“现在”的强调,也是对于现在的“扼杀”,后者是对“瞬时性”的强调,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媚俗艺术和超凡脱俗的纯粹审美领域的艺术毫不搭界,由于“历史地看,媚俗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另一种现代性侵入艺术领域的结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与商业利益”[1]06,所以,媚俗艺术的即时性原则尽管显出“一切为了现在”的及时行乐的面目,动机却不在审美领域的不断自由发展上,它掺杂了许多享乐成分,而“享乐”实质上具有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在卡林内斯库看来这便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趣味。
瞬时性(transitoriness)反映出审美现代性的短暂易逝和变动不居两方面的特点。与美的超验性永恒观点相对,审美现代性对于“死亡”的强调远远多于“永生”。尼采谈“上帝死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等等观点都是对时间/历史终结的强调。时间/历史的绵延不绝不再被重视,个人的生命感受中的时间得到突出,并拟化了人类历史的终结,因而时间成为了线段式的时间,它具有终点。在先锋派那里,甚至毫不拒斥自杀式的倾向,因为对于死亡的强调便证明了生的瞬时性。
到了这里先锋派已经与颓废主义联系到一起。显然,“颓废”本身就意味着无可避免的衰朽,而美学上的“颓废主义”更是一开始就致力于促成这种衰朽。生命和世界迅速衰竭,死亡和终结于前方召唤导致的颓废观也促成了对当下性的强调。这种“敏锐不安的紧迫感”似乎与基督教的救赎观念不谋而合,时间如此短暂易逝,迫不及待地催促人起而行之。因此,“颓废被感觉成一种独特的危机,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去做那些为了自己和同类的获救必须做的事而不再等待就变得极端重要。从世界的终结正在迅速临近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单独的瞬间都是决定性的。”[1]166回到媚俗艺术的即时性原则,它对于当下的强调和瞬间、迅速、毫不费力地获得正是其另一特征,当然它也是快速衰竭的。一切艺术的,甚至是乏味的东西、杂物、垃圾都可以成为时尚,一切都可以被利用,当然,也迅速地被抛弃,甚至时间本身也是如此。瞬间的短暂易逝也就意味着它的变动不居。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甚至更远),就人的体验看来,时间机器的运转不断加速。求新求变是两种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基本要求,审美现代性从主动性地与过去决裂,谋求新颖性,逐渐发展到对不断变化的现在难以把控的无力感,变化逐渐成为了整个具有现代感的生活之中人们的普遍感受。随着现代性的发展,“求变”变成了“无所不在的变化感”。
运动和变化是审美现代性的状态,在流动不居的世界面前,人们甚至有些手足无措。瞬间不断向人涌来,又轻易地滑走,它存在又陷于虚空,它凝结了全部意义——包括过去和未来,却又毫无意义,因为它不断流动,始终处于缺席。值得深思的是,瞬间性蕴含的变动不居的特点似乎仅仅是一种微观的现象,宏观来看:“变化无处不在,但从文化上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中。”[1]160瞬间的变化波动不仅相互抵消,而且消耗了结构性异变的能量,正如迈耶认为的:“今天的艺术典型特征是一种‘波动稳定状态’”[1]160。这种“静态平衡”本身也是瞬间性激发的危机。总之,“瞬间”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间的悖论,必须不断地填补它,用一切可以得来的资源,高雅的艺术或者过去的一顶破草帽,但这些都不能真正在时间中立足。到了后现代阶段,“现代”的时间概念已经被抽空,瞬间不是一个瞬间,而是无数不断向前滚动的瞬间,它看似那么重要,实则并不存在,而人们为了摆脱这种无力感,只有不断地填满它,当然这也促成了它更快地衰竭。瞬间性,无论是强调时间的衰竭还是其流动不居的特点,与其说是扼杀时间,不如说是扼杀对于时间的厌倦。
审美现代性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时间意识以树立自身的审美标准。其新颖性、当下性和瞬间性特征都是基于时间/历史的纵向延续性所形成的特点。可以说,现代性突出“现在”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种时间意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乃至社会的各个层面。
三、审美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语境
审美现代性不仅树立了自己的时间/历史意识,具有其自身的突出特征,而且也处于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密切联系,并且这种联系的趋势走向是日渐紧密的。特别是到了后现代时期,即使再谈“艺术的独立性”也都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立场。确切地说,艺术从来不曾真正地脱离过生活,仅仅是“关系性”或者“语境论”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从内隐变得外显了。审美现代性从发生伊始就寓于矛盾与悖论之中,它在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胶着角力之中不断发展,并且经过两个世纪多的风云变幻,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脉络。
如果说审美现代性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直在与传统抗争的话,它在历史的横截面中则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狭路相逢。审美现代性居于双重悖论之中,它要反审美传统,又居于传统之中;它反资本主义现代性,又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语境。第一重悖论,前文已有所述。关于第二点,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带动了审美现代性的发展,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了审美现代性的趣味,经过了一系列冲突与互相攻击之后,资本主义现代性甚至以各种方式对审美现代性进行收编和裹挟,甚至利用。到了后现代时期,很难说还存在两种现代性,因为两者已经难以区分了。尽管如此,在整个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之中,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各个层面上的冲突是至为明显的。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二者的历史意识的冲突。资本主义秉持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念。尽管它也将时间划入世俗的领域,使其成为线性不可逆的时间,采用以“现在”为中心视点观照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但它仍然借助传统的秩序逻辑,制造进步的神话,制造一个不同于宗教的,却又与宗教有着很高相似度的世俗乌托邦神话。而审美现代性对于“现在”的看法没有功利的乌托邦建构目的,事实上,时间/历史意识在审美现代性这里,既然与传统决裂,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竭,至于其后是否还会再度复兴,这并不是审美现代性重点考虑的问题,它考虑的是处于“现代”的审美问题,当然还有它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讲求的理性的、秩序的、模式化的、标准化的观念对于审美想象性的独特性、想象力的戕害。
从审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分歧引发了审美现代性的一系列悖论,首先就是“人”的问题。按照现代性鲜明的时间/历史意识,“人”自然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福柯认为:“‘人’的实际历史非常短。他所得出的广为人知的一个结论是,对西方世界来说‘人是一种新近的发明’(始于十八世纪末),而且这种发明已经过时。”[1]141宗教意识的退场自然不久将连带着人的危机。尼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宣告了‘人’的最终死亡和超人的出现。”[1]137尼采所指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出来的人,具有神性的人。因此,这里的“人之死”,并不指向世俗的人的死亡,或者说人作为一种生物仍然存在,但是作为具有超越性的精神的人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里,“颓废派” 似乎反对的是虚假的人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制作出来的人,并非真正的人。而“某种反人本主义的进攻策略”,一方面直接表现出异化或非人化的可怕现实,祛除资产阶级加之在这些现实上的甜蜜遮蔽,把赤裸裸的现实揭露出来;另一方面,它又认为这些遮蔽或许诺与资本主义整个机制是一体的,它们根本上都是真正的非人化,不过带着糖衣而已,而这层“人本主义”文化的甜蜜糖衣甚至是资本主义非人化的帮凶,“人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因此,“颓废派”的指归似乎还是要回到真正的人、完满的人,并不是否认人的存在。当然,内在地讨论“人究竟是什么”的取向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性在审美领域的表现形式。当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内驱力是力比多的时候,“把人的无意识和生物本能提到首位”[3]62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子;当德勒兹谈到人是“一部欲望机器”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技术主义的面影。“欲望机器(机器化)是一项技术革命,甚至是整个技术革命及其余波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欲望由体力生产转向机器生产。[4]63这似乎也在证明,尽管审美现代性的反人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制约下理性的、制度化的人的反对,但是,它的理论还是扎根于这个由科学进步神话构造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因此,审美现代性究竟是提倡人本主义的还是反人本主义的始终是一个悖论,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人”这个概念。我以为,不妨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对于审美现代性来说“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5]78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了它的不同侧面罢了。
其次,在审美现代性的“颓废”和“进步”之间确实形成了一个悖论。前文已经提到过颓废的三方面特点:极度精致、抬高想象力而损毁理性和打破边界。前两者已经详细分析过,打破边界,或者称之为“解阈”的方式以实现力量分离从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进步神话”形成一种阻碍。“解阈”与“结阈”相对,借用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解阈”理论来说,“解阈”是一种站在更高角度形成的“共同体”,而“结阈”是一种“结构”行为。共同体(communitas)与结构(structure)相对,结构指的是区分、划界、排序和对等级秩序的创见,共同体指的是擦抹、跨界、混合和对等级秩序的拆除[注]John Fowles. The Aristos [M].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64:14.转引自:肖锦龙.结阈和解阈——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身份建构[J].北京社会科学,2017(02):4-12.。但有趣的是这种“解阈”的趋势现今又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走向,成为了流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所以颓废已经不是浪漫主义运动发展中形成的反科学与反理性的倾向了,“高度的技术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其融洽。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后果。”[1]169很显然,说到“颓废即进步”时并不是一种乐观的立场,颓废也不因此获得更多的积极意义,颓废“打破边界”的特点仅仅显明了它在反驳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又暗合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趋势。或许在尼采对于“颓废”的辩证考量之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到颓废与进步之间的矛盾。尼采担心的是,颓废容易用虚构来包装真理,通过借助想象的方式,然后这种虚构又被认为是合理的,就会“把幻象当成现实”进而再次进入到一个新的“虚幻空间”,也就是“超生命的价值”无视颓废一开始是借想象力来反对理想的乌托邦的。但是:
尼采会说,超生命的价值根本上就是反生命的价值,从而也是颓废的标志。当颓废把生活本身之外的意义归于生活时,当它引入一个救赎的“彼岸“的观念时(无论这个“彼岸”是根据基督教的“死后生活”还是根据现代的世俗乌托邦构想出来的),它就是在反对现实生活。从美学上讲,现代颓废者——以瓦格纳为代表——可以很容易地从革命主义走到虚无主义再走到基督教。所有这些可供选择的形式都表达了同样的对于救赎的基本需求,并试图颠覆真实生活的“趋附”(Yes-saying)精神。[1]211
尼采认为,颓废的发展演变会形成一种理知上的轮回,基督教本身的教义当然具有超越性,但是同时基督教也在世俗生活中引起人的精神上的麻醉或者成为“受难”的哲学。从而,颓废派也就脱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取悦群众的(crowd-pleasing)”特性相联系起来。颓废与进步的悖论说明:审美现代性中的“颓废”这副面孔尽管极力表现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反叛和否定,仍然不能摆脱它所处的这重历史语境。
再者,审美现代性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悖论似乎集中于媚俗艺术之中,媚俗艺术毫不掩饰它自身的工业特征、它的不甚高雅的趣味,甚至它的意识形态目的,这一切本身似乎对于媚俗艺术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表演。像审美现代性的诸多悖论一样,时间问题似乎也是媚俗艺术自身悖论的根源,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闲暇时间的问题和怀旧问题。先来看闲暇时间的悖论。媚俗艺术直接作用于闲暇时间,它是闲暇时间中的一种享乐性奖赏,也是闲暇时间空洞的填充物,因为闲暇时间既是对于工作时间的补偿,同时也是一种“负担”。资本主义现代性要求“扼杀”闲暇时间,尽管闲暇是对工作的补偿,但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看来闲暇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不能构成世俗乌托邦式的未来(“工作时间”才能)。而审美领域的艺术又耗费大量的时间,它本身是一种具有自身审美目的性的行为,不与社会的发展发生直接的关系。媚俗艺术却不是这样,相比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它显然更倾向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或者更为“折中”地说,它居于二者之间。因此,媚俗艺术必须“即时见效”“即时获得”,与其说艺术被运用于炫耀,不如说是用“拥有感”填补迅速易逝的时间空洞。怀旧问题是关于媚俗艺术的另一个时间性问题。过去对于注重当下和现时的两种现代性来说都是一种可供摄取的材料资源。但是,媚俗艺术对于过去的取用似乎有些不加选择:
我们只要想想日渐其多的怀旧商店出售的那些可怕的老“古玩”就足够了——烂靴子,破马车轮子,陶瓷夜壶,两三代之前用的笨拙的浴缸,以及无数其他破破烂烂的“古董”,许多人把它们当做我们祖父母辈生活的美好世界的遗物来赏玩儿。[1]258
过去的残留物是情感的寄居所,这昭示了闲暇的现在不能产生情感,“工作时间”完全是模式化的,显然也不能产生情感,因此情感似乎只存在于“过去”。然而,这里的“过去”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过去,过去已经成为了一个世俗想象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乌托邦不再存在于不断发展、物质更为丰富便利、科技更为先进的未来。更可悲的是,“过去”也是由瞬时性的当下构成,也就是说,并不真正存在一个美好的过去,旧时的遗物同样是当时就迅速被遗弃的媚俗艺术品。居于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或者后现代时期的人,他的情感只能在“时差”中存在,并且流动易逝,保质期极为短暂,甚至可以说情感并不存在于现实中,或者现实中的人毫无情感可言。这当然使人联想到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其不断发展中对人的异化,如果说得更严重一些,“现代”已经不存在未来,因为乌托邦被置于逝去的历史之中了,现在也已经被抽空,需要用无数事实上就在当下被遗弃的时尚来填补。
结语
无论如何,审美现代性都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时间/历史意识,它关注时间、谈论时间,又困惑于时间。现代性以其魄力重新定义了时间/历史,它通过全新的时间规划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其中资本主义现代性信心更加充沛,自认为能够征服时间、利用时间;审美现代性却在时时提醒着时间本身的“非理性”可能,这是“有死的人”以其线段式的人生无法窥见历史的全貌的经验感受引起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向前的力量,审美现代性则在逡巡徘徊中对它进行反思,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正反两面的完整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如今已经异变或逐渐凋零,一个更立体多维的历史景观呼之欲出,但是,反观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种种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和思想的成果都有其深刻的价值。毕竟,只要人类一天还不能乘坐时间之矢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自由穿梭,时间/历史问题就仍然会不断诘问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