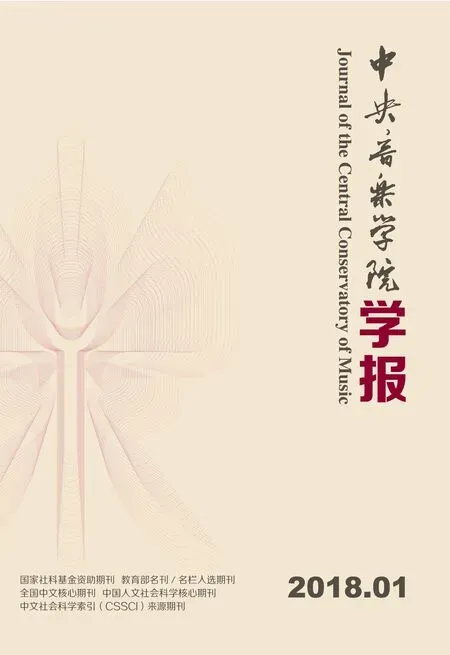民族音乐教研的新视点:族体变化与混生音乐
关于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众多学者发表了很多文论。2017年6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组织大家讨论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与作曲人才培养问题,笔者认为在今日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本文所谓“新视点”,指的是“民族”和“音乐”这两个关键词本身意蕴的变化,希望引起关注。本文以会议发言为基础,具体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也作为笔者承担的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混生音乐族性的美学分析”阶段性成果。
一、重提民族音乐的当下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历经百余年,自然人已经更替了若干代,并且出现了种种“代沟”。就民族传统音乐而言,识者因辈分不同而有差异。中国大陆对民族音乐的看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以下划分仅为笔者个人的看法。①2017年12月11日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主办的“新时期中国音乐发展战略高端论坛暨2017中国基地学术委员会工作年会”上,袁静芳教授谈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时划分的不同时期为20世纪60年代后、80年代后和21世纪以来,与本文的划分大致相同。
第一个时期出现在20世纪上叶西学东渐高潮时代,当时的成年国人还能体验中西碰撞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分立为国粹派、崇西派和结合派,后者又分西体中用派和中体西用派。本来中华民族文化占据、生息在整个中国大地,并未受到挤压。历史上的四夷音乐像涓涓细流汇入黄河,并未改变黄河的颜色。近现代正是因为西方强势的蓝色海洋文化铺天盖地而来,跟在坚船利炮后面进入国门,亦有留洋学子主动引入国门,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逐渐被边缘化,顽强而艰难地存活于民间,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有学者注意到它的存活率与地域的偏僻程度成正比。不过,依照“传统音乐”的“3+1(×5)”划分法,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民歌、说唱、戏曲、歌舞和器乐)命运各有不同。其时的“新音乐”将传统音乐作为创作资源(创作结果则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在新文化语境中学者或音乐家进行了相关活动。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结束的时期。此时期“传统音乐”被剔除了“封建迷信的糟粕”,只剩下民间音乐中“健康”的部分。“传统音乐”甚至等于“民间音乐”(或“民间传统音乐”,这也是延安新传统的延伸)。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音乐中最精致高级的当属宫廷音乐,因为只有宫廷拥有最大的权力、财力、物力、人力,皇帝本人受过最好的教育,包括音乐教育。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活态宫廷音乐依旧朦胧地回响于想象之中,虽然有极少的专家试图恢复它们。当然,重新发掘历史上的宫廷音乐,在今天并非要恢复“宫廷”,而是作为历史研究活态资料和审美资源。
第三个时期发生在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以来,与“全球化-多元化”语境重合。20世纪70年代末至80、9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西学东渐,各种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大量涌入,现代西方音乐和音乐理论被迎进国门,其结果出现了“新潮音乐”(新混生音乐)。为了探索西方无调性-噪音思维与中国传统和新传统音乐对接的窍门,民族音乐被再度尝试“借尸还魂”。21世纪初纷纷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加入全球非遗保护行列。这一时期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对所有其他音乐学学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笔者观察到作曲界一些民族音乐低谷现象。音乐类非遗保护似乎并没有造成音乐创作新的民族化浪潮。国内外作曲界悄悄流行一种观念,即“个性比民族性更重要”。从学理上说,民族性确实还是一定范围的共性,只在不同民族之间比较时才体现彼此的个性。西方早在20世纪初从共性写作转向个性写作的现代主义音乐发展时期,个人的个性就被进一步凸现出来,并常常超越民族的个性。只有民族乐派保持着艺术音乐和民间传统音乐之间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混生音乐的种类)。如今,在新生代作曲家那里,无论采取什么作曲技法,似乎个性比民族性受到更多的重视。
第四个阶段是当下。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发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次年才公布完整文字版,但是主要精神已经传遍各地,中华美学精神,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中国软实力等等被极大强调。加之“一带一路”强调音乐艺术在民族文化之间情感纽带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再次受到空前的关注。从现状看,未统计的考察结果是,20世纪50-60年代、70-80年代及90-21世纪初出生的各代人群,逐渐远离传统音乐文化,呈现“递远”状况,因此重提民族音乐就是要拉近他们与传统音乐文化的距离。依笔者意见,目前的呼吁与呼应,可以用民族音乐复兴的第四次浪潮来命名。这是政治家和音乐家“同频共振”的呼吁和呼应,《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及时组织专题讨论,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实现第四次浪潮中民族音乐教研及人才培养的愿景,需要探讨以下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民族”的双重变化和民族音乐的“混生化”问题。
二、“民族”的双重变化
其一,原生民族族性的弱化甚至消失,使之虚幻化,即名存实亡;若要持续,则需要重构,从自然态置换为人工态。
原生民族(ethnos)与根源音乐(original music)相应,与“原种”(stock)和“基因”(gene)相关。也就是近年来国内媒体发端、全国采纳的“原生态音乐”这一新词的指谓。学界习惯使用传统音乐(traditional music)这个词。综合国际学界观点,取其通约说法,族体可分为种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
由于迁徙、交流、混杂等各种原因,以种族为基础的音乐文化局面逐渐被打破,学界更愿意以族群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族群音乐文化就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各族群所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同,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各自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独特的音乐文化。像丝绸之路这样的跨界交流时有发生;族群之间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因此,自古以来族群构成不断变化。但是人类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还是能勾勒出众多族群在历史时空流变、分布的谱系。在今天这个历史截面,各族群及其音乐文化被描绘成一幅“多元音乐文化生态”的画面。世界民族音乐还被划分出9个或11个“色彩区”;每个色彩区内又被划分出若干子色彩区*陈自明:《研究世界民族音乐 共享世界音乐资源——在第二届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2006年,第2期,第17页。。
国家概念的族体,是由若干族群或民族构成的。例如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或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多以这些民族为对象。大的民族如汉族,则以地区、乐种和事项等来限定论域。而在“中西关系”“未来发展”等言论中的“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nation层次)。“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中已经逐渐成为新族体、具有新族性、拥有新音乐。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原生族体的族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即逐渐中性化。*宋瑾:《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引论)——多元音乐文化新样态预测》,《交响》,2006年,第3期,第45-58页。
相关的问题是,原生族体的称谓依旧,但指谓或内涵已经改变。随着人的自然更替,新人新时代,无论是全球化、西方化,还是现代化、中性化,原生族体的族性都在淡化,或者说,原有族性不断减弱甚至消失,这意味着各原生族体趋于名存实亡。通常,民族音乐的变异缘因在于环境和族性的变异。环境变异是缘,族性变异是因,变异因缘和合导致乐种变异。族性内在于族群成员的身心,外显于音乐观念的表达、音乐行为和音声。归根到底,族性的变异是民族音乐变异的根本原因。族性变异,导致族群音乐选择的改变。其中,音乐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导致民族音乐的改变。反过来,变异的民族音乐又在应用中巩固或强化新族性,塑造新生代的族性。需要澄清的是族体族性的遗传变异和杂交变异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遗传变异通常基因未质变,原生族体还保持了原有族性;杂交变异基因改变了,出现了新族体和族性。民族传统音乐在自然传承中的变异,只要没有质变,就还是原生乐种。一旦和外来音乐杂交,就改变了基因,成为混生音乐。在命名上,新族体仍然采用原生族体的名称,而新音乐也归属于名存实亡的原生族体,如族性已经由中西结合的新文化塑造的现代国人,依然采用“中华民族”称谓;新音乐依然归属“中华民族”。
斗转星移,人非昔人,时过境迁,或事过境迁。事实上完全恢复原有族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重建过程尽量恢复原有族性的成分。希望不是简单地捡回原初族性的碎片,镶嵌在新族性上作为点缀。还需要处理好“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重建族性应细致考察以下族体重组和新族体出世的情形。
其二,原生民族在中性化过程被重组,出现了新生族体,后者成为当今社会群体的实体。
除了上述原生族体的名实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新生族体的出现。一方面是原生族体分裂重组,另一方面是全新族体应运而生。
原生族体分裂重组的典型事例是宗教群体成分的变化。各原生宗教本来隶属于原生族群,或隶属于特定区域的民族,如今,各宗教愈来愈脱离原生族体,“凌驾于”原生族体之上,成为独立的族体。这些来自不同原生族群的人员在宗教归化过程,已经培养了新的族性,即信徒共同的心性及其表现,重组为新族体。俄罗斯著名女作曲家古拜杜琳娜的身份认同即为东正教。她说,要问我的音乐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在于我的归属,即东正教。*古拜杜琳娜在2012年10月中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周的演讲。
随着社会的“开化”,在原生族体被视为“正常的”性取向是异性恋,其他都是离经叛道的。如今,不同性取向者在一些地区逐渐受到平等对待,在另一些地区则不同程度被“宽容”。这样,性取向成为一种族性,也重组了不同的“性族”。这些族群亦由不同原生族体成员构成。在音乐选择上,不同性族也有不同表现。这些都在“社会性别”语境中被表达出来。例如西方一个男同性恋群体,喜欢通过歌剧女主角来抒发自己的情思,甚至进行“跨性别认同”*〔美〕露丝·索莉,谢仲浩译:《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75页。,把自己“同化”于女主角,因此该群体被称为“歌剧女王”。
在现代化都市,杂居着多个族群。如今,城市在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中性化的场所和熔炉,并使融入其内的族群成员都不同程度被去族性化、中性化。与此同时,重新划分社会群体,结成新族群。如“上班族”“白领”“蓝领”“黑领”“农民工”“移民”等。这些重新集结的族体,都是原生族体分裂重组的。他们各有各的音乐选择。
相对而言的新新人类,构成了新族体,拥有新族性。典型者如“第五空间”的“赛伯族”(cybernation)、赛伯格(cyborg)等。他们的音乐选择如网络歌曲、口技打击乐(beatbox)、VR、AI音乐等等。此外,还可以划分出更多类型的新族体。如在殖民主义语境中,有“西方人”“东方人”“香蕉人”“山药人”等。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中,还出现了迎合西方人东方想象的“某某族人”及其“传统音乐”,乡村也出现迎合城里人乡村想象的“某某族人”及其“传统音乐”。*宋瑾:《乡村视野的城市音乐》,《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第76—84,6页。
全球化语境中还划分了“全球人”(globals)和“本地人”(locals),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不赘述。在文化身份认同中,出现了“世界公民”“地球村村民”等,即消解或放弃原生族体族性的中性人。在音乐领域,有作曲家不仅放弃原生族性,还放弃“西方/东方”的纠结,认同自我非中非西(中性人)的文化身份,如陈其钢等;或认同地球村民的文化身份,如高为杰等。*宋瑾:《民族性与文化身份认同/当今中国作曲家思想焦点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62—68页。有些作曲者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没有民族属性的中性化特点,透露出作曲者中性化的心性。有些年轻作曲家的电子音乐作品表现出更典型的中性化特征,也反映了他们相应的心性。
原生族体的族性变化,新生族体的涌现,都有相应的音乐行为和结果。这些是当前民族音乐教研需要高度重视的变化。
三、“民族音乐”混生化
就像今天已经没有纯种的民族一样,也没有纯种的民族音乐。“文化基因”仅仅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原种”的隐喻。除了原生音乐传承中的自然变异之外,常见不同文化的音乐杂交现象;杂交结果即混生音乐(hybrid music)。从根源看,有双源混生音乐,如中西结合的“新音乐”,还有多源混生音乐,如吉普赛人将印度、阿拉伯和西班牙犹太文化三源混合的弗拉门戈(Flamengo);有一度混生音乐,如各殖民地跟西方古典音乐结合的音乐,还有再度混生音乐,如一度混生的爵士乐(非洲、美洲混生)与巴赫音乐再度混生的“摇摆巴赫”。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我国的“新音乐”为例来阐述问题。它属于双源混生音乐的种类。
对应20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名同实异的族性和群体,出现了“新音乐”。“新”意味着与传统音乐不同;不同在于它是中西结合的混生音乐。这是新文化新音乐运动的双重结果。中华民族名下的新生代,以新文化替代传统文化,塑造了自己的新族性。新型“中华儿女”在国粹派、崇洋派和结合派的对峙中选择了后者,选择了新音乐。笼统地说,今天用民族乐器(乐队)表演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属于“中体西用”,用西方乐器(乐队)表演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属于“西体中用”。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音乐逐渐成了主流,建国后成了官方音乐的主要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新音乐。它是中国人创作的,曲调具有一定的五声性(如在分解三和弦的旋律上加“大六度音”),但旋法却符合欧洲大小调体系的功能和声,而且确实配上了这种和声;采用西方军乐队演奏,带有西方进行曲的律动风格等等。有学者指出,新音乐可以说是中国的音乐,也可以说是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这就出现了新课题——混生音乐族性归属问题。多年前香港学者刘靖之在若干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他列举的例子是贺绿汀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他指出这个作品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乐器、曲式、复调也是西方的(西方和声作了民族化处理,如弱化功能进行),只有五声曲调是中国的。为此,可以说该作品是中国作品,也可以说它是中国风格的西方作品。多年之后,2015年11月28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后现代与民族音乐学”会议上,伍国栋恰恰对《牧童短笛》进行“民族性”分析,指出其各方面的传统音乐因素,包括曲体结构等等。事后笔者追问:这些都是作曲家自己的想法吗?答曰:没有找到作曲家自己的语言表达,是分析、关联思考的结果。可见,混生音乐的族性归属问题还须继续思考。
从源头上看,学堂乐歌是中国新音乐的最初样式。它由留学东洋的李叔同等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曲调,填上中国歌词而成。当时人们尽量选择五声性明显的曲调,如《送别》等。由于旋法、和声等造成风格的新异感,许多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新音乐重镇上海来“赶鲜”。那些动荡的岁月造就了新族性的中华儿女,造就了新音乐文化,形成了新传统。今日不少学者自觉在新旧双重传统的语境中看待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建构。*例如2017年11月5日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任方冰的发言题目《双重传统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其他学者的发言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涉及古代和现代的双重传统或双重视域。多年来由于我们处在自身的新文化传统和新音乐功用关系中,把新音乐理所当然看作自己的民族音乐(发展了的民族音乐),对它的族性特征和归属问题未见专门探讨或深入充分研究,甚至没有提出像刘靖之那样的疑问,抑或答复刘靖之的疑问。需要追问的是,作为混生音乐,新音乐体现了怎样的族性,以及怎样体现这种族性?
简要地说,族性指族体特点,包括族群共有的心性及其外显。心性乃精神核心。族群的心性和文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文化内化为心性,心性外化为文化。内在的族性可以通过外显的文化呈现出来。内在心性大致包括“局内观”“局内感”和“局内情”,外显文化大致体现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有物质载体),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方面。“局内观”是民族音乐学的关键词之一,指族群成员的观念。就音乐而言,指音乐观念(含概念)。也即梅里亚姆“概念、行为、音声”的第一项。不同民族有不同音乐观。例如伊斯兰民族认为“宗教音乐”不是音乐。*Eckhard Newbauer,Veronica Doubleday,“Islamic Religious Music”,Stanley Sadie(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Edition 2,vol.12,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2001,p.599.“局内感”是笔者提出来的,指族群成员所具有的独特乐感。相对于“地方性知识”,可以称之为“地方性乐感”。这种乐感体现在民族音乐的感性特征或韵味上。“局内情”也是笔者提出来的,指族群成员在身份认同中体现的情感和态度。有些局内人具有良好的局内观和局内感,可以为采风者提供丰富的地方音乐知识,精湛的地方音乐表演,但是内心却不一定热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隐藏着“向上流动”*〔美〕布鲁斯·罗宾斯,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的意愿,遇到机会就远走高飞。因此,局内情对一个族群的凝聚力而言非常重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族群音乐文化特点的重要根源。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族性,外部体现为“新文化”,内部体现为新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新族性便由中西文化一道塑造而成。
新族群的“地方性乐感”,其“地方”不是自然地理的位置,而是新的社会空间,或社会关系、社会交际空间。歌星的粉丝可以构成一个社会空间,其中的群体拥有相同或相似的音乐偏好、选择和行为。在第五空间,赛伯族可以从连通全球的网络获取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并介入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族性。
总之,不同族体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混生音乐。混生音乐体现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特征。中西结合的“新音乐”具有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基因”,呈现出杂交的感性特征。从所有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新音乐看,它们共同具有西方大小调体系音乐的基因,相互之间的区别在于各自原生族群音乐文化基因的呈现。这正是各东方国家将混生的新音乐据为己有的依据。问题在于不少“新潮音乐”中原生民族音乐的成分不明显甚至听不出来,或者说感性上无效,只能通过乐谱分析寻找民族音乐的蛛丝马迹。因此从感性上看,它们具有中性化特点。这需要专题研究,在此不赘。
结 语
其一,以往研究习惯于针对原生族体及其传统音乐,如今应关注再生族体和新生族体,考察、研究其相应的音乐。就原生族体音乐文化的研究,要避免将“传统音乐”等同于“民间音乐”。
其二,从混生音乐角度重新考量新音乐、新潮音乐和新民乐等的族性特征,探讨其族体归属,包括族体名存实异的情形、新族性特点及其在音乐上的体现等。
其三,关注混生音乐族性特征的感性效果,避免仅仅作乐谱分析的“纸上谈兵”。可借助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寻找族性外显的“知觉恒常”限度。这里最困难之处在于把握形变神不变的“文化气质”的感受尺度。
其四,民族音乐教研要区分两种“变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在加入行动的同时,出现了“传承/保护”与“发展/创新”之间该如何取舍的争议。其中还出现对两种“变异”的混淆和困惑——传统音乐在历史中的变异和20世纪以来新文化新音乐的变异。有人指出“传统是一条河”,传统本身是变化的,因此现在仍然要走新音乐所走的混生音乐道路,继续借鉴西方音乐文化来发展我们的音乐文化。本文认为,传统音乐在历史中的变异属于文化基因未质变的“遗传变异”,近现代西学东渐出现的新音乐变异属于基因改变的“杂交变异”。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存在着西方音乐、传统音乐、新音乐(含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含新民乐)。新音乐是传统音乐和西方艺术音乐中的古典音乐结合的混生音乐,新潮音乐是传统音乐和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现代音乐结合的混生音乐,流行音乐本身是多源混生音乐,新民乐是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二度混生音乐。从各类音乐存活的真实情况看,传统音乐处境最差,有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因此“非遗”要保护或抢救的是传统音乐。从全球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说,保护每一元是首要的任务。显而易见的是,比起新音乐来,传统音乐离西方音乐更远,二者分辨率更高。当然,保护是为了分享,为了全球多元音乐文化生态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