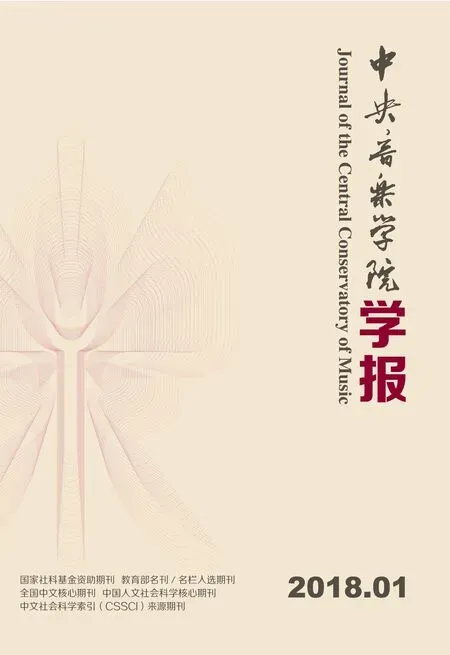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真的如此多变吗?
〔俄〕阿·亚·卡拉廖夫 著
王愫怡 译
郭伟国 校
一
鼻子,用来嗅气味并做出选择。艺术家不过是像猪一样嗅出松露的味道。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每当艺术领域产生新的学派并在风格上发生巨大转变时,人们总是对之前的音乐风格产生质疑,或索性全盘否定。比如巴赫的音乐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遗忘;大部分浪漫派作曲家认为古典乐派的宫廷音乐过于固守规则;很多20世纪的作曲家反过来又对浪漫派夸张的多愁善感、矫揉造作和空前的悲怆表现出不屑。同样,20世纪下半叶的先锋派代表,依照历史规律又批判了之前的作曲家,如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亨德米特、布里顿和稍晚些的勋伯格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在这一时期却有一个例外,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作曲家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特别是他晚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创作质量、艺术价值以及历史意义方面都没有遭到质疑,之后的现代派作曲家态度也和先锋派类似。在此,我们并非在强调斯特拉文斯基赢得了多少空前的声誉,获取了多少听众的青睐,而是在探讨他对音乐家,尤其是对作曲家的影响力之强大,令他享有了如此高的权威,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不同于其他现代派作曲家;其次是现实对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迫切的需要。这种迫切性与音乐语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当代音乐与他的音乐语言迥然不同;在曲式、配器甚至整个作曲技术方面也与斯特拉文斯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个“未知”的迫切性在美学、创作思想方面意义深远,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具有崇高的使命!
在与斯特拉文斯基相关的书籍和访谈录中,涉及了很多极其有趣的问题,但都未能解释其作品成功的原因。事实上,大部分伟大的艺术家在探讨个人作品的时候总是非常主观和模糊,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在这一点上斯特拉文斯基很清晰,他曾说:“作曲家和艺术家不会去考虑概念性的问题,要毕加索或斯特拉文斯基用语言描述其绘画和音乐的具体内容,这是没有意义的……”*Игорь Стравинский(伊·斯特拉文斯基),Роберт Крафт(罗·克拉夫特),Диалоги(《访谈录》),Л.,(列宁格勒)Музыка(音乐出版社),1971,с.216。因此,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明确地给了我们对其音乐本质作出假设的权利。当我们聆听斯特拉文斯基选自圣经题材的歌剧《洪水》(TheFlood)时,就让我们暂时忘掉在不同文章和书籍中频繁出现的那些对斯特拉文斯基惯用的标签吧!如“多元风格”“新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讽刺手法”等等。
在听歌剧《洪水》之前,我们首先回想一下斯特拉文斯基曾说过的话:“音乐不表达什么,也不描绘什么。”可晚些时候他又说:“音乐的本质是在表达其音乐本身。”用音乐表达其音乐本身又怎么可能不表达什么呢?音乐又是如何表达其音乐本身的呢?这是看似奇怪的说法,甚至有点矛盾。设想音乐如果不描写来势凶猛的灾难、生命的消逝,戏剧亦就不复存在了。
歌剧《洪水》起初是一幅静止的画面,四周围绕着紧张的“弦乐”,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打开了“阀门”,增加了一批“新的水源”(长笛、单簧管和大号)。那种在险情中大声呐喊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其他作曲家如勋伯格、亨德米特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中,然而他们的音乐与斯特拉文斯基相比显然有所不同,其本质上更偏向传统,有发展部、冲突对比、有起伏和高潮,更不用说浪漫派作曲家的作品了[比较圣桑的《洪水》(LeDéluge)]。那么斯特拉文斯基戏剧性、英雄性、抒情性的主题在哪里呢?没有!只有“音调”或“情绪氛围”。那种在猖獗的灾难面前显得无助又恐惧的情绪气氛,或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正义与胜利的场面,又或是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以音乐史中前人的美学观念来看,斯特拉文斯基有关“洪水”这个题材的写作在情节方面的描写几乎为零。他并没有试图表现得令人震惊,或塑造一个等待上帝来拯救的慌恐场景。他的音乐只表现了雄伟与迷人的美。这种美从何而来?它描述了什么?以往有过类似的情形吗?
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音乐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当然,其中也存在斯特拉文斯基对新音乐的影响。如两个亚当斯(J.Adams,J.L.Adams)和雷西(S.Reish),像所有其他的美国作曲家一样,在欧洲同样有安德里森(L.Andriessen)、里盖蒂(G.Ligeti)、布列兹(P.Boulez)、米赫耶(T.Murail)和格里赛(G.Grisey)。但是,斯特拉文斯基之前并不知道他们。那更早些时候有过类似风格的作曲家吗?我们浏览一下约400年前的音乐史,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期的音乐,是否存在过同样“另类”的作曲家呢?恐怕在那个时期要找到标题性的器乐曲都很难!那时的标题性音乐只有“战役”和“狩猎”类的题材,例如:安德烈·加布里埃利(Andrea Gabrieli)的《战役》(Battaglia),它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洪水》一样充盈着静止的状态,音乐材料不断围绕着同一个和弦,有时会出现属和弦和几次下属和弦,完全没有心理描写、戏剧性冲突或其他前面所提到过的一些特性。同时,这个音乐也“不表达什么”,要知道,那时加布里埃利还不知道音乐应该表达什么!这是基歇尔(A.Kircher)*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和耶稣会士。和马泰松(Mattheson)*马泰松(Johann Mattheson,1681-1764),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评论家。稍晚些在理论书中提到过的。
让我们再看看选自蒙特威尔第的《圣歌》(CanticumSacrum)(第1、2首)和《晚祷》(Vespro)(第1乐章)中的例子,其在内容上更贴近、更鲜明地体现出音乐的本质是在表达其音乐本身。从整体的形态来看,可以假设斯特拉文斯基将蒙特威尔第的音乐作为了一个创作蓝本。但是,从歌剧《洪水》的开始已经表明,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斯特拉文斯基和蒙特威尔第的创作都没有任何共同点。那么总体框架呢?要知道,产生两个在音乐内容上几乎相同的例子是罕见的。那么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到底是从哪里仿照而来的呢?
接下来再看看斯特拉文斯基的选自《弥撒曲》的“羔羊经”(AgnusDei),甚至不用找出一对例子,显然斯特拉文斯基运用了严格写作风格,它像是早期的音乐,如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de Machaut)的《弥撒曲》。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声称在完成自己的《弥撒曲》后才了解了到马肖的《弥撒曲》,实际比较两部作品,又是从纵向横向看来都没有一点共同之处。难道他们只有不固定的节奏和运用卡农演唱歌词的手法相同吗?那么斯特拉文斯基的《弥撒曲》到底源自哪里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到底与同时期作曲家有哪些区别?”“巴洛克以前的音乐与17世纪至20世纪期间的音乐到底有哪些区别?”当然,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在第二个问题上已经指出了方向。
首先,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更早的音乐基本都是声乐作品,即便有器乐的参与,也几乎与声乐旋律没有区别,都是可以演唱的。早期的音乐形式在规模上并不庞大,原则上,音乐线条的基本构成因素最先是音调,其次是节奏。音乐要求在纵向上只能使用乐音,即协和音程。音色,在那时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无论是演唱还是弹奏的声部只要音域合适就可以了。
音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人声的音调在当时的欧洲几乎体现在了所有的专业音乐中(从多声部音乐产生到16世纪以前)。音调与歌词有着天然、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宗教歌词”。有关自己的音乐,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句话非常贴切:“语言是最初的表达,对我来说它也是真正最直接的真理。”*Игорь Стравинский(伊·斯特拉文斯基),Роберт Крафт(罗·克拉夫特),Диалоги(《访谈录》),Л.(列宁格勒),Музыка(音乐出版社),1971,с.177。早期音乐使用“绘词法”,“歌词至上”,欧洲音乐语言的形成并非是偶然的,当时对音乐的理解完全依靠歌词,随后又引发了对记谱的需求。对音调的要求如歌词一样严谨稳固,不允许存在任何“无礼”的处理。
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欧洲的音乐史经历了重大的变革,音乐的含义有所改变,从“绘词法”开始向“情感论”转变,并很快对音乐理论产生了影响。这场变革进行的速度极快,短短的十几年音乐语言就被完全颠覆了。从以声乐作品为主的音乐转变为包含声乐部分的器乐作品(如巴赫,此时并非谈论类似19世纪的美声唱法)。和声、节奏与器乐织体的意义急速发展,音乐变得更加戏剧化了,相继出现了和声功能对比、调性对比以及音乐材料之间的对比。实际上某些新的元素在早些时候已经出现萌芽,如器乐织体早在16世纪“法国游吟诗人”的音乐中就诞生了,当时的流行短诗被改编为键盘器乐曲演奏。然而形势以惊人的速度变化并影响着至少一代人,蒙特威尔第有幸参与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他称之为“第一常规”(prima prattica,亦译:第一实践)与“第二常规”(second prattica,亦译:第二实践)。这一时期音乐风格与技术急剧转变的速度甚至超越了斯特拉文斯基所有变奏手法的速度。
对于广大的当代音乐爱好者来说,音乐的发展、矛盾冲突和戏剧性是音乐形式中最显而易见的特征,他们很难想象与之截然相反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不理解(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现代音乐),这不仅仅是针对广大听众,对于从事音乐专业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它简直就是在描述“另一个世界”。
从17世纪开始,音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情感论”时代,音乐开始用来表达感情。如果生活在巴罗克时期的作曲家,没有摒弃之前的音乐形式,那么在古典时期以至于浪漫时期的人们就不会记住他的名字。结果,主题动机被发展为源源不断的旋律,而“兰迪尼终止式”已经沦落到马戏团的美声唱法中。
任何一个时期的音乐总会在某个时候走到尽头。极具影响力、充分表达情感的、伟大而优美的戏剧音乐,于20世纪下半叶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最后为其创作的伟大作曲家大概就是肖斯塔科维奇。这一时期任何类型的音乐(也包括摇滚乐)都截然不同,当然除了已成体系的学院派。它们没有戏剧性,也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冲突,也没有解决冲突的音乐材料。这并不意味着新音乐又回到了歌词与音调的层面,此种音乐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即使有过也显然不是现在的样子。虽说如此,可为什么一些作曲家开始为自己的器乐作品配歌词呢?如贝尔格、诺诺和克那伊费尔(Knaifel)等等。有关21世纪音乐的讨论最好还是推迟到22世纪进行吧!我们暂且返回到斯特拉文斯基,一位将先前的音乐风格几乎“扫地出门”,仅仅靠笔头创作就将我们带入了当今音乐圣殿的作曲家。
斯特拉文斯基仿佛是同时代作曲家中的“白乌鸦”,他的风格处于戏剧音乐与自由音乐创作时代的夹层。有意思的是,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对此并不完全了解。他将自己与勋伯格作比较时,将勋伯格称为“革命者”,将自己称为“复兴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浪漫派作曲家马勒晚期的音乐是维也纳乐派自然而合乎逻辑的延伸,那么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时常被“古老”的外表所掩盖,但却完全属于“新”音乐。同时期的作曲家们在表现形式上虽迥然不同,但大都倾向于调性主题音乐。斯特拉文斯基的调性主题音乐没有过渡,没有连接部,没有副主题材料,用斯特拉文斯的话说,每次新的转折、新音程的出现都是建立在之前总的材料基础上的。这是斯特拉文斯基在发表对调性主题音乐的宣言吗?在时间的长河里,他最大限度地浓缩了各种音乐风格,可以用分钟来测量(甚至包含了巴罗克之前的风格)。一切外部环境造就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在20世纪下半叶先锋派中脱颖而出,对于许多现代派作曲家的诞生来说也都是异曲同工。20世纪还选择了谁?梅西安(O.Messiaen)?他也同样将音乐推向了一个全新领域。以上说法尤其体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晚期作品中,又很适合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作曲家的创作之路,有遵循传统美学的《火鸟》(Firebird),以及高度集中经文歌建构的《安魂圣歌》(RequiemCanticles)。
二
按照法国人对俄罗斯“五人团”的评论套路,我很怕法国音乐家(特别是拉威尔)带着愤怒的感受去评论《彼得鲁什卡》,结果事情还是不出所料地发生了。
——伊·斯特拉文斯基
斯特拉文斯基青年时期的音乐生活如梦幻般美好,家庭为其提供了优越的生活保障。他拥有个人房产,由马车夫送他去名校上学。大学期间他想去学校则去,不想去则不去。他的父亲是马林剧院的一位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斯特拉文斯基几乎每天都去马林剧院看演出,更重要的是看排练,在剧院期间斯特拉文斯基开始接触到现代派艺术。因此,他从小就接受了优秀的家庭音乐启蒙教育。之后,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里亚多夫学习作曲和配器,在俄罗斯这已经是顶级的音乐教育了。对音乐极大的兴趣促使斯特拉文斯基异常勤奋,学习内容包含了所有古典音乐,同时也研究瓦格纳。他采用了所有可以了解到现代音乐的方法,听音乐会,买下所有在柜台上可以看到的包括最新版本的总谱,在拿到总谱后都要在钢琴上弹奏一番,尤其是斯克里亚宾和德彪西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对于德国音乐的关注很谨慎,这方面明显受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影响,总的来说是受“彼得堡乐派”的影响,与德国的一切相抗争,这种抗争一直延续到最后。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早期作品鲜明的民族色彩上,还包括作曲技法和配器手法。在斯特拉文斯基晚期的作品中,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配器手法的痕迹仍依稀可见,对纵向进行的密切关注,认真倾听和斟酌每一个和弦及和声之间的关系。纵向音符的排列取决于和声的音响效果以及对音色的要求。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受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晚期作品中传统戏剧和装饰美学的影响,这完全属于时代精神潜移默化的结果。施尼特凯(A.Schnittke)曾说过:“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切作品都是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金鸡》(TheGoldenCockerel)和《不死的卡谢》(Kashcheytheimmortal)中‘走出来的’,对此他本人也并不否认。”施尼特凯的文章《斯特拉文斯基音乐逻辑特征中的矛盾》*转引自И.Ф.Стравинский(伊·斯特拉文斯基),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文章与材料》),М.(莫斯科),Советский композитор(苏联作曲家出版社),1973。是有关斯特拉文斯基最宝贵的文字记载之一,作者具备精准的观察力,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在本文的后面还会提到。
第二位对年轻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思维产生深远影响的作曲家是德彪西。在这一点上,显然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也给予了肯定。《火鸟》不用说,《彼得鲁什卡》(Petrushka)的几处颤音几乎引自德彪西的《节日》。有趣的是,这些积聚能量的乐队语言被用来承担过渡或连接的功能,即这类线条元素在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仅仅是昙花一现。继《春之祭》之后就很难再找到受德彪西音乐语言影响的地方了,但是,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情况一样,德彪西的美学观点以及世界观对其影响更深远,德彪西是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位“非戏剧性”的作曲家。产生德彪西的原因并不重要(如民族音乐的复兴,反瓦格纳派,印象派),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结果,在近四百年间创作的音乐中首次出现了“非戏剧性音乐”,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斯特拉文斯基一生的音乐创作命运。斯特拉文斯基从未改变过对德彪西的看法,对其音乐作品毕恭毕敬。甚至,当斯特拉文斯基得知德彪西关注了他的音乐之后会一直引以为荣。
施尼特凯曾在文章中回忆到,斯特拉文斯基唯一一次最重要的风格和审美的转折发生在1913至1914年间,即作品《春之祭》(TheRiteofSpring)与《婚礼》(LesNoces)期间。此时,斯特拉文斯基已满30岁。如果留意音乐史中的记载,大部分作曲家的生平在30岁左右都会发生重大事件,作曲家通常会在这个阶段形成个人风格。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那些生命很短暂的作曲家,如莫扎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斯特拉文斯基像在《春之祭》中一样在《婚礼》中使用了大型管弦乐队编制。经过了多次的改写最终结束在了四个P的弱力度记号上,作曲家没有在钢琴上使用类似标记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那时乐器的机械装置还很难保证与作曲家的要求同步!从那以后,斯特拉文斯基再也没使用过如此华丽的乐队编制,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伟大的配器大师。当然,这只是作品的外貌特征,其实是音乐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从《婚礼》开始出现了“调性主题”,有关这种思维方式上文提到过。所有连接功能的材料都消失不见了,音乐结构的共性就是时间的运动,甚至在钢琴协奏曲中管乐并没有提前一小节演奏前奏,没有任何一小节的开场白和解说。斯特拉文斯基毫不留情地与每一种已经受到欢迎的效果进行对抗,特别是极受欢迎的那一种。那么,莫非斯特拉文斯基最著名的三部芭蕾舞剧并未代表完整的斯特拉文斯基?尽管它体现了斯特拉文斯基绝世的天赋,辉煌的交响音效,革新性以及听众的热爱等等,但这对作曲家本人来说还只是自我发现的开始。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音乐在风格上的差别很大,《火鸟》与《彼得鲁什卡》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了他的《士兵的故事》(L’HistoireduSoldat)与《诗篇交响曲》(SymphonyofPsalms)或者与《竞赛》(Agon)之间的差距。
作品《火鸟》还完全处在彼得堡乐派传统的范围内。作曲家用奇妙的、色彩斑斓的有声乐队讲述着童话故事。在该抒情的地方,音乐是优美的;在该神秘的地方,音乐则显得深不可测;凶神恶煞的形象,音乐听起来既刻薄又强硬。一切都很自然,都以它该有的形式存在着,这也正是斯特拉文斯基早期芭蕾舞作品深得人心的原因,观众们看到的是一场常规题材的芭蕾舞场面,头脑没有被其中那微妙的奇怪的东西所影响。然而,难道和声语言也是常规的吗?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其实,早在《彼得鲁什卡》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比如题材方面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神话传说,而是更贴近现代生活习俗以小剧场为场景的梦幻爱情故事,并且融合了某些现实主义元素。音乐也不再是符合常规的彼得堡乐派风格。首先,采用了独特的城市歌曲素材,所谓与乡村“真正的民歌”相比有些平庸和堕落的音乐;其次,非常大众化,体现生活原貌的素材在芭蕾舞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音乐的呈现几乎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没有任何改动、解说以及潜台词,完全以人们所熟知的样子搬上舞台。
此种艺术手法成为了斯特拉文斯基最基本的创作手法之一,并且体现在了不同的作品中。如《婚礼》中的酒宴,所有人同时聊天、叫喊、歌唱、说着俄罗斯人都难懂的方言;还有《俄狄浦斯王》(OedipusRex)中克里昂的咏叹调那“格格不入”的C大调三和弦(继勋伯格的《月光下的彼埃罗》和他本人的《春之祭》之后使用此和弦是何等的勇敢!甚至是何等的傲慢啊!);再来看根据佩尔戈莱西主题改编的歌剧《普钦内拉》(Pulcinella),根据勃兰登堡协奏曲改编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Oaks)《洪水》(水,水来了,水,水来了……)。这其中似乎蕴含着佛教意味,只可意会,无法解释。斯特拉文斯基用一生的时间尝试了形形色色的音乐风格,因此无论是俄罗斯风格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其他时期,其音乐在本质上并没有严格的风格界限,斯特拉文斯基本人看待这些风格并非像公认的那样。俄罗斯的婚礼仪式采用了飞快的速度,不可思议的打击乐组合与四台钢琴担任伴奏;“巴罗克式的”《敦巴顿橡树》起初完全没有低音(这在巴罗克时期怎么可能发生?),而当低音进入的时候也是断断续续的,甚至有点不合时宜;《诗篇交响曲》中的赋格主题没有使用减音程,而是使用了增音程;《俄狄浦斯王》中伊奥斯出现时演唱的“荣耀之歌”结束于高声部,选自俄罗斯士兵歌曲的副旋律等等,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并非说明斯特拉文斯基对音乐形象的认识有误,甚至令其歪曲,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与众不同,也许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说,这正是更加准确的定义。
依照斯特拉文斯基本人的观点,《春之祭》相比较《彼得鲁什卡》要逊色一些,然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春之祭》在构思上先于《彼得鲁什卡》。那么,让我们先放下在芭蕾舞剧中还没有展示过的古代俄罗斯仪式中的“现实”题材,将注意力放在音乐织体中具有革命性变化的节奏构造上吧。
斯特拉文斯基的节奏来源于俄罗斯民歌中多变、不规则的节拍和重音变化,有关这个观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之前的作曲家尤其是彼得堡乐派的作曲家已经开始关注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节奏特点。因此,斯特拉文斯基在这方面完全走在了传统的轨道上。但是,“强力集团”的作曲家包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运用民歌素材时,将它的不规则节拍改写成了规则的形式,只萃取了材料中的民族特色因素,增添了音乐的民族色彩性,基本上是将俄罗斯民族旋律放入了欧式规则的节拍中。《火鸟》与《彼得鲁什卡》的节奏节拍基本上也都是按照此种手法组织构成的。而在创作《春之祭》时,斯特拉文斯基突然意识到对于节奏完全没有必要按照惯用的方法去刻意“梳理”,如果采用民间音乐中多变的节拍会更有意思,可以最大程度地使用民间音乐动机。
这种不整齐、不规则的节奏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手法,但从本质上依照听觉感知特点来看不可以延续过长,因为缺少了时间上的定位会令人感到单调,丧失了动力感。斯特拉文斯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用了固定音型来构成时间上的参照点。因此,在《春之祭》中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大量运用固定音型并非偶然,于此同时加入了复杂不规则的节奏模式。固定音型几乎总是出现在低音声部,如准则一样伴有定音鼓的参与,主题线条构建在不断变化的悠长曲调形态中,形成了节奏对位。多变的节拍和固定音型似乎成为了斯特拉文斯基风格显著的标志。在晚期作品(如《进台咏》(Introitus)、《洪水》以及《安魂圣歌》)中,固定音型转变成平稳的定音鼓震音弱奏,同样承担着“时间参照点”的功能。
《春之祭》与之前斯特拉文斯基创作的作品相比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春之祭》以及《婚礼》中所使用的俄罗斯民间音乐素材数量并不多,在这一点上似乎容易被忽略。到底什么是“俄罗斯式”的音调?如在“献祭的舞蹈”“大地的崇拜”“春天的征兆”“祖先的仪式”,《婚礼》的第二幕(除了中间部分有一段不长的模仿教堂音乐的片段)中,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地方。是“原始的”三、四个音符组成的音列吗?奥尔夫也使用此类音列,更不用说亚当斯和赖赫了。如今看来,真正的“俄罗斯”音乐语言似乎是不规则的节奏和悠长曲调的变奏。的确是这样吗?也许可以借助奥斯卡·王尔德的观点“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来回答。斯特拉文斯基用自己的音乐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民间音乐传统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后出现的另一种“真实”的样子?也许这才是它真正该有的样子?
这里还适合引用斯特拉文斯基的一句话:“如果对民族音乐断章取义则不能算真正的成功,追求乐队的音响效果和标新立异的演奏形式不能成为颠覆它的理由。如果脱离了民族音乐的根,将失去它原本的魅力。”*Андриссен Л.(路·安德里森),Шёнбергер Э.(埃·勋伯格勒),Часы Аполлона.О Стравинском(《阿波罗的时间,有关斯特拉文斯基》),СПб.(圣彼得堡):Институт ПРО АРТЕ(俄罗斯文化艺术慈善基金学院),2003,с.221。这是在晚些时候的说法,显然在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还没有这样的领悟,因为他早期的芭蕾舞剧正是以追求乐队音响效果和标新立异的演奏形式为目标,然而这个说法证明了继《春之祭》之后作曲家在创作审美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三
技艺精湛的作曲家不模仿,而是艺术地窃取。
——伊·斯特拉文斯基
斯特拉文斯基对《婚礼》的总谱进行了多次修改,这表明作曲家想避免过多花哨的效果和形式主义,并非一时兴起。作为真正的艺术家,斯特拉文斯基突然意识到必须要对直觉有所改变,而使真正的作品成形得晚一些。这也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配器中音调、节奏和声音特性的纵向关系被作曲家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改变著名的《春之祭》引子中所有独奏乐器的位置,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芭蕾舞剧的配器还有些含混,1914年以后,斯特拉文斯基的基本配器手法已经像其他作曲家一样有了明确的轮廓,此时的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形成了某种瞬间就能辨识出的音乐风格。其中,基本配器手法中的重要元素是钢琴的敲击声及其模进。斯特拉文斯基的钢琴识体并非像许多作曲家(如普罗科菲耶夫、勃拉姆斯)总谱中常见的钢琴织体形式,而是冲击式、清晰快速的下落式,非连奏的。此种手法绝没有给音乐减分,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也曾回应说,毫无疑问,这是有意而为之的。1914年以后,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基本特征就是非连奏或断奏,这些标志性的象征符号都是从《婚礼》开始的,最极端的时候使用了四台钢琴演奏。1917年以后,斯特拉文斯基开始避免使用大型交响乐队编制,众人猜测是贾吉列夫的财政出了问题,有趣的是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从未有过此种解释,因为实际原因是创作上的问题。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音乐发展阶段,因此还可以作为社会艺术学的最直接实例。
《婚礼》充分体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基本创作构思和手法,一些变奏手法甚至在作曲家一生的创作中都在使用。首先,音乐材料的集聚是空前的,阅读清晰的语言解释所需时间,反而比作品本身更长!当然,这也与题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斯特拉文斯基完全省略了连接段、过渡段、引子等等,所有非主题性的材料结构。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来看这一现象,完全没有动机的发展和材料的展开,只有音程的分裂、集合与变化。音乐积聚了疯狂的能量,却只有戏剧性的征兆,而并没有戏剧性的展开。实际上,音乐是在不断地展现一个又一个新的材料,有时材料会再次出现,甚至不只一次,偶尔材料规律性地重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传统曲式,有时则与传统曲式没有任何联系。
让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婚礼》的曲式结构。第一幕,abab//TTcT//ab(字母T表示三音列曲调,在第一幕中出现过三次),有点像复三部曲式,第一部和再现部(这里暂且可以使用这个词)也可以看成是多段体曲式。第二幕,aaa//bbb//cdT//aae//f//ghg//ikl,其中有一些重复的材料构成了内部联系,但是已经与传统曲式没有相似之处了。第三幕,T//b/T/a//b//b/a//Tc//ddd(单斜杠表示音乐材料同时发声),又是相同的情况,材料具备内部联系,但无法纳入任何传统曲式中。而在第四幕中,画结构图已经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一种音乐材料出现过第二次。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其他大量作品中,其结构图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如《三乐章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曲式结构图,由四部分组成:abaca//defdghf//abi(fuga)//kf。只有《敦巴顿橡树园》的曲式结构图比传统的《诗篇交响曲》更接近传统。大多数分析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的文章或论文都提到其中有一些传统曲式的影子,如赋格,因此画出它的曲式图相对容易些。显然,音乐理论家们都非常乐意去分析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因为这很轻松,而不愿意去弄清楚德彪西或斯特拉文斯基的曲式结构,这要困难得多(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同样也很难分析)。
看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处理一些现代音乐结构形成的准则问题,即新的问题(或者说是被遗忘的旧问题)。音乐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其构成复杂,并且呈现出不规则的模式。同常规的音调节奏相比,音乐织体构成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如音色、音区、音响甚至间接的音乐元素。此外,任何元素又似乎都与音调有着某种联系,如,节奏、音色等等。因此从传统的角度分析现代曲式,分析的方法与作品复杂的网状结构关系完全没有符合的地方,或者只是表面相似(无意的巧合)。无需引用不必要的新概念,我们利用已经存在的艺术学术语“块茎论”(法语rhizome)来称呼。块茎区别于常见的根,因为它没有中心,也没有目标方向,它的根成网状,朝不同的方向恣意生长、无序发展。这个术语是由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提出的,之后成为了后现代的基本概念之一。“块茎论”提出的对艺术作品构成材料进行非线性的组织手法,在整体上与传统的确定性结构相对立。如果留意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终乐章的曲式,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杂的三维结构图,其内部包含着彼此深层连接的标题性元素,斯特拉文斯基在其《访谈录》中谈论过。
在这类结构中是否存在着偶然因素?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斯特拉文斯基曾对此发表过想法:“事实上,我创作的过程是由偶然的审美因素决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真正的意外。”这句万能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斯特拉文斯基各种类型的音乐。从传统曲式角度分析,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的确是偶然的,而且并非是绝对的。它也许还有其他可能,上面举例分析的曲式图中的字母也可以改变位置,但结果听起来是肯定不合适的,因为它“并非是真正的意外”。从纵向构成来看是不协和的,时常由古典乐派音乐中所谓的“堕落的和弦”构成,但并非任意构成。关于这个问题安德里森在有关斯特拉文斯基的书籍*Андриссен Л.(路·安德里森),Шёнбергер Э.(埃·勋伯格勒),Часы Аполлона.О Стравинском(《阿波罗的时间,有关斯特拉文斯基》),СПб.(圣彼得堡):Институт ПРО АРТЕ(俄罗斯文化艺术慈善基金学院),2003。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一句针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纵向构成很可爱的描述:“它包含了‘正确’的错音。”可能性有很多,但又并非是“真正的意外”。事实上这种“并非真正的意外”在很多现今的作曲家身上都存在,也包括最保守的古典乐派,或许这就是艺术的主要构成因素,使作品区别于单纯的模仿(学徒式、电脑拷贝以及其他形式)。
我们回头看《婚礼》,探讨一下对于所有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都很重要问题——主题。他使用文字材料作为音乐表达的手段。歌词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说并没有深奥到超出其文字本意,哪怕是在音乐发展中起推动作用的文字也都是最直接的表达。之前已经阐述过斯特拉文斯基充满了早期音乐精神的说法:“语言是最初的表达,对我来说它也是真正最直接的真理。”歌词对于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过程意义重大,因为语言同时也是声音,是音乐的构成元素,文本的内容还会牵扯到整部作品的音乐语言、时间感以及风格特征。典型的例子如《俄狄浦斯王》的歌词按照斯特拉文斯基的想法从法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其目的就是为了从语言中获得“神圣”的精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的原型发生在希腊。在这部作品中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拉丁语,这不仅仅是语言的发音以及音乐受制于歌词等问题,还存在被称之为欧洲文化源头的“响亮的拉丁语”的意识概念。
渗透到音乐线条中的语言会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诗篇交响曲》中“天主颂”的节奏型采用了俄语版的发音“Господи помилуй”(求主怜悯)。斯特拉文斯基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安魂圣歌》中,再一次用管弦乐队清晰地模仿了俄语版“求主怜悯”的发音。他曾坦言,关于这种创作方式他会一直思考到生命的尽头。
有关将语言发音如何渗透到音乐旋律线条中的方法,表现得最为全面的还属作品《婚礼》。这部作品与古代的俄语发音密不可分,可以说,从真正意义上来看这其中包含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材料。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也许是第一位)使用了对于当代俄罗斯人来说都似天书般难懂的古代语言。斯特拉文斯基甚至没有力求使整个文本清晰易读,而是同时使用了两三个甚至四个不同内容的歌词。听众们接收到的都是分离的单词和零碎的短语,很多时候其发音成为了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通过声音来表达,语言也是通过声音来表达,因此,可以说文本也是音乐的一种。在作品的某些地方文本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使20世纪末的音乐已经接近于“text-soundmusic”(文本声音音乐)。采用文本作为音乐材料已经成为斯特拉文斯基风格中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尤其考虑到他的声乐作品几乎占据了全部作品的一半数量,而另一半作品又大多带有合唱。如果排除纯粹的歌剧作曲家,占有如此大比例声乐作品的作曲家在巴罗克之后是少有的,20世纪的卡·奥尔夫(Carl Orff)可以算上一位,那么19世纪呢?大概只有勃拉姆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区别于同时期作曲家的。
谈到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不能忽略他音乐中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频繁使用的斯特拉文斯基本人称之为“模型”的元素,即有意识地将大家所熟知的前辈作曲家的音乐风格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元素在某些作品中的数量之大,以至于听众感觉作曲家仿佛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幅“临摹”作品。然而此种感觉通常不会超过2、3秒(在《仙女之吻》(TheFary’sKiss)和《普钦内拉》中大概持续了5、6秒)。很快我们会意识到此处的风格不太一样,如果是“临摹”作品应该处理得更精确些。例如《钢琴和管乐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引子,仿佛是法国序曲中的慢板,带有特色的附点节奏、柱式和声、平静的旋律以及问答式的结构,一切都是合适的,这些拓扑学*拓扑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高度抽象的一门几何学,即研究空间在某种变换下的不变性质。音乐符号将我们带回到了18世纪。然而其他部分从第一个和弦开始就不再合适了。乐器的音响与风格相互冲突,从第三个和弦开始大小调混用,纵向和声由正确的“错音”构成(安德里森的说法),终止停留在意料之外的和弦上,乐句结构开始被打乱,有时出现和弦空缺,仿佛出现了“绊脚石”。这哪里是“临摹”作品呢?施尼特凯将此种手法称之为“伪风格摹仿”。斯特拉文斯基并没有试图让我们相信所听到的音乐是来自18世纪的,恰恰相反,他在时刻提醒我们所处的时代是20世纪,然而这些提醒每一次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斯特拉文斯基在使用其他作曲家的风格时挑选了具有其内在意义的因素(音乐、文化或历史方面)来作为他个人音乐中的材料。
难道19世纪的作曲家不是这样创作的吗?那么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何处理民族音乐素材的呢?有时直接引用旋律,有时根据民歌风格自创。但是,没有作曲家试图将自创的旋律达到与民歌难以分辨的程度,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位听众将鲍罗廷的《波罗维茨少女合唱》标记为真正的民间音乐,作品从和声、声部进行、曲式及其他作曲技术方面来看都应归属为19世纪音乐,并且是“强力集团”彼得堡乐派的风格。斯特拉文斯基最先充分拓展了传统民间音乐在现代音乐中的运用与实践。他利用一切地域的音乐文化,一切无论是纯粹风格还是无名作者的元素,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作为个人音乐的表现手段。斯特拉文斯基直接引用民族音乐情况很少,研究人员的统计结果各不相同,但针对其全部作品的普遍统计结果不超过15—20个材料。使用其他作曲家主题材料的数量也不多,如在《普尔钦奈拉》和《仙女之吻》这两部芭蕾舞剧中有一些独特之处,在《致敬前奏曲》(GreetingPrelude)中有两处有趣的片段。斯特拉文斯基的手法既非拼贴,也非多元化风格,因为其音乐中经常会出现斯特拉文斯基式的纵向排列、节奏模式与配器手段,即个人风格。
斯特拉文斯基风格中的灵活性与多变性经常被夸大。事实上,斯特拉文斯基总是毫不妥协地坚持着个人风格,譬如他从来没有为一部电影写过配乐,虽然有段时间曾考虑过,但每次总有偶然情况的干扰,这也是顺应了自然规律吧。很难想象一部好莱坞大片配上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将是什么效果,他篡改美国国歌的事件差点成为丑闻,*斯特拉文斯基1939年移居美国以后,为在波士顿的一次演出改编了美国国歌《星条旗在飘扬》,他被带到警察那里,由于他篡改了美国国歌,险些被逮捕。只因斯特拉文斯基无法不使用独有的手法进行演出,一些怀有爱国情怀的观众善意地称他为“过度勇敢者”。
回到标题中提出的问题,答案是这样的: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演变自然也存在于任何一位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中,尤其是比较长寿的艺术家。他唯一一次风格的剧烈转变是发生在《春之祭》之后,在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认清并找到了个人风格,继而完全展现在下一部作品《婚礼》中。根据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可以看出,大部分作曲家探索个人成熟风格的年龄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对于作曲家来说,这显然是最重要的年龄段。斯特拉文斯基在此后的风格变化中进行得相当平缓,其音乐风格在演变中看似最剧烈的时候也没有脱离其基本的原则(美学基础、节奏模式、曲式结构、歌词的意义、配器),而只是将“不同的模型更换了位置”,增加了文化“注解”,还有一些斯特拉文斯基风格存在的特征(俄罗斯的民间音乐、18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这种演变的过程是循序渐进并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延续了戏剧与音乐情感内容的发展规律,在符合逻辑发展的前提下伴随着的一系列新技术产生的。如果说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是令情绪的高涨达到极点,那么斯特拉文斯基终于摆脱了戏剧情感表达的音乐,令其返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所履行的责任并改写了其历史意义。
(本文为2013年11月“第三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分析论坛”大师讲座内容,文章作者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二期“重逢俄罗斯专题”发表过《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对配器的对立态度》)